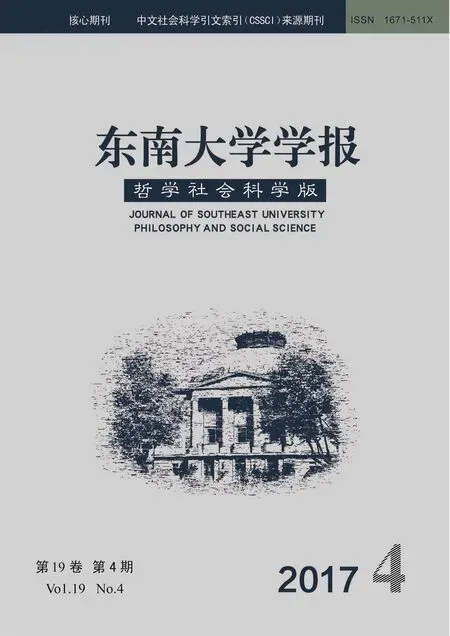从理性到合理性: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之嬗变
张轶瑶,李 超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南京医学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6)
从理性到合理性: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之嬗变
张轶瑶1,李 超2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南京医学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6)
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从理性到合理性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必然性一方面来自于《正义论》中所构建的社会正义理论内部逻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性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之基本诉求。从对理性自主的强调到对公共合理性的辩护,实际上体现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康德道德哲学立场到黑格尔政治哲学立场的偏移。相对于康德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与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在事实上更具有理论亲缘性。
理性;合理性;自由意志;重叠共识;罗尔斯;黑格尔
对于罗尔斯而言,《正义论》(1971)的创作基于两个最根本的理论背景:对康德主义的坚决拥护以及对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直接批判。在此基础上,罗尔斯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契约理论。随后,经过对自己正义理论的反思以及对各种批评的回应,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1993)中修正了其正义理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阐释。在这一系列的修正和辩护过程中,罗尔斯自由主义思想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隐秘的变化①在西方世界中,罗尔斯前后著作之间的变化和“不一致”,其实在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中已经有所揭示,但是大多数批评者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只是论证罗尔斯对康德主义的偏离,以用来驳斥推翻罗尔斯自己所宣示的立场,其意并不在厘清罗尔斯真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而在国内的相关著作中,只有张国清先生在其一篇名为《罗尔斯的秘密以及后果(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的文章中注意到了除传统的“卢梭—洛克—康德”以外的其他哲学体系,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对罗尔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构建上的影响。但作者以罗尔斯掩盖自己真实理论体系的原因为重点,分析了罗尔斯与其启蒙之师斯退士(Walter T. Stace)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而对于这些哲学思想在罗尔斯理论体系中影响之具体体现则显得浅尝辄止,让人意犹未尽。,这些变化广泛而深入地反映在罗尔斯《正义论》之后的诸著作中。本文试图以罗尔斯自由主义核心概念的演变为切入点,结合罗尔斯后期的反思性理论著作②主要包括《政治哲学史讲义》(2000)、《道德哲学史讲义》(2001)、《做为公平的正义》(2001)等著作以及一些体现其思想演进的重要论文。,论证支撑其思想体系的哲学理论之内部演化,从而指出在罗尔斯自己声称所遵循的“洛克—卢梭—康德”的契约主义路线之外,还至少隐藏着另外一条哲学路径,即“康德—黑格尔”的自由主义路径。一般认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反对契约主义的③大致来说,在对待传统契约主义观点的态度上,黑格尔主张采用一种非抽象性的观点来审视人性,拒绝契约主义那种将个体视作“原子式的存在”的论调,并否定国家的合法性是基于原始契约正当性的政治哲学立场。,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关于契约理论的陈述④罗尔斯认为,“契约术语的优点是它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正义诸原则可以被构想成为那些被理性的人们选择的原则,并且用这样的方法,正义的概念可以被解释及判断其正当性”。(参见 Rawls J.的《A Theory of Justic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4-15.)就此而言,罗尔斯正义理论所要坚持的契约主义立场的确是黑格尔哲学曾经所批判的。则至少首先在文字态度上明确了划分了他自己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立场。但事实上,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很多模糊性正是由于其所打算坚持的传统契约主义与现代性社会基本事实之间的诸多不相容而造成的。本文试图指出,在对正义理论的修正过程中,罗尔斯正是考虑借鉴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思想,试图消除康德哲学中个体理性的抽象性和形式主义缺陷,澄清现代性多元社会中个体(理性)与公共性(合理性)之间真正关系的,最终实现正义原则的当代政治实践。
一、罗尔斯语境下个体理性的理论困境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自己所设计的原初状态下的代理人为一种以理性自主为本质特征的道德人。但是,罗尔斯语境下的理性道德人既与康德道德哲学中那种“有理性的存在者”所指的“理性”基本范畴不同,又与功利主义的“经济理性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康德的话语体系下,“理性”是伦理生活中的道德人之本质,它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和辩护理由;而罗尔斯则明确指出,理性的概念必须以经济理论为标准而尽可能狭义地理解为“采用最有效的方式达成特定的目的”,并且应该尽量避免将任何有争议的伦理原理引进其中[1]12。另一方面,罗尔斯虽然主张将理性限制在经济理论中,但也不赞同功利主义那种将“善”之本质视作可以被“计算的福利”的主张;恰恰相反,在罗尔斯看来,不允许某人根据其最珍视的坚定信念来生活而可能带来的风险代价,是任何的经济或政治利益都不能补偿的[1]181-183。具体来讲,罗尔斯的“理性代理人”是指这样一群人:在原初状态下,这些身处无知之幕背后的当事人对一切外在事物一无所知,他们只是纯粹的自我利益追逐者;并且可以由此设定,这些当事人之间是相互平等且漠不关心的[1]12。在罗尔斯看来,确立原始契约的代理人必须具有以上的理性特征,才能够确保契约的公正与正义。因为这些自主的个体会将自身交付给那些他们所选择的诸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会因此从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性中摆脱出来。所以,他行动所依据的原则,“不会因为他的社会地位或天然禀赋,或者因为他所生活的具体社会的观点,或者因为他偶然想要得到的具体东西而得以采纳”[1]222。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设定既不同于康德哲学,也异于功利主义,是一种极富创建性的尝试。但也正是这种试图突破传统的预设,使得其最早的正义理论内部在逻辑上出现了某种断裂。而这一断裂对于其理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来说所构成的威胁是巨大的。
1.正义理论的内部矛盾:审慎原则与绝对命令之间的不一致
在《正义论》中,为了能证明这些代理人所订立的诸正义原则的正当性,罗尔斯将自己的正义理论诉之于一种“理性—选择”理论,并且坚称,“正义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1]15。而在这些正义原则获得了正当性证明的前提下,罗尔斯则进一步尝试将“理性—选择”与康德的“自治”概念整合起来,从而将这些正义原则“纳入绝对命令的范围”[1]22。可以看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实际上关涉两个关键步骤:第一,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论证在原始状态下所选择的诸正义原则正当性;第二,论证将这些正义原则能够被归类于绝对命令,用以指导和规范道德实践。罗尔斯的这一证成性路径强调了道德主体的理性自主与理性自治这两个本质特征[2]229-249,但是这两个步骤,或者说罗尔斯要实现的这两个目的之间,在逻辑上却是有着某种不一致的。
在的第一个步骤中,罗尔斯要求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代理人不能被某种特别的道德学说影响其判断,那么,根据罗尔斯的“理性—选择”理论,审慎原则就成了在原初状态中唯一能够指导人们做出判断和选择的东西[3]158-189。也就是说,在罗尔斯那里,审慎原则就是个体理性在原初状态的根本体现。所以,在第二个步骤中,罗尔斯就试图将基于理性选择,即基于一种审慎原则而得到的正义原则视作康德式的“绝对命令”,从而使得正义原则的道德合法性根基获得确证。但是,在从第一个步骤向第二个步骤的演进中,或者是说,在从个体自主向主体自治的转换过程中,却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康德那里,审慎原则恰恰是被当做一种假言命令而非绝对命令来看待的。康德明确指出,“对于他自己的最大幸福在技能的选择方式上可以被称之为审慎。因此,……即审慎规则,这个命令仍然总是假言的;行动并不是被绝对命令的,而是其他目的的手段”[4]33。这就意味着,罗尔斯的第二个步骤(目的)如果仅仅依赖审慎原则而不借助于康德语境下的理性概念,是无法得以证成的。所以,两个步骤中的理性概念,即根据审慎原则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与绝对命令下的“理性自治”各自所指的“理性”概念,其实是不一致的。正如后来郝费(Otfried Höffe)所指出的,将正义原则看成是绝对命令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们可以坚称罗尔斯想要从一种理性的审慎选择中演绎出正义的诸原则[5]59。这一缺陷对于罗尔斯的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完整性来讲,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
2.正义理论的政治实践问题:个体理性自主与现代社会公共生活诉求之间的断裂
除了正义理论的内部矛盾,罗尔斯在对正义理论反思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现代性社会是基于一个“理性多元化”的事实之上的。这首先意味着,在由基本权利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环境下,冲突的多样性及不可调和性便会成为社会的合理事实,这使得“综合性学说将会产生”[6]36。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这些综合学说都是完整且相互独立的,它们有着不可通约的意义目的或价值观点;但另一方面,个体在政治生活中作为社会之公民,如果不能让自己承担起那种与同胞共享的正义概念,则可能会因此“远离我们的政治社会,而退回到社会世界中”,或者会因为“感到受了冷落”而变得“孤独或愤世嫉俗的”[7]128。所以,罗尔斯清楚地知道,当个体在其自身内部发生分裂时,是必须要求助于政治哲学的[6]44。如此一来,一种现代性的社会正义概念则必然是一个“尽可能地独立于有争议的哲学和宗教学说”[8]224的公共概念;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个体的道德善渊源,而是由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所组成的社会基本结构,以及在这一制度中所决定和应用的诸正义原则。
在这一基本社会前提下,罗尔斯划分出了人的“道德概念”和“政治概念”。一方面,他认为,各种合理性综合学说只是与人的道德概念相关,它展示了自由个体追逐某种道德价值的可能性,体现了个体在道德世界的理性自主;而与人的政治概念相关的则是社会基本结构以及其所对应的诸正义原则,它们为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行为提供了辩护理由,体现了公民在政治世界的社会正义。换言之,前者是个体的伦理自治,而后者则是公民的政治自治,而人们则必须将“政治生活的这种充分自治需求及权利与个体性的伦理价值区分开来”[9]579。罗尔斯的这一区分实际上暗示着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理性自主所追求的道德善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由于理性(the rational)概念实际上由大量的综合性道德哲学学说所构成的[9]6,而这些学说相互之间又是独立的,甚至是分裂的,那么,每一个理性人就都可能有他自己关于世界的那种具体的、特别的概念,并且这些关于“善”的概念本质上具有不可通约的异质性,甚至是相互排斥或对立的。而另一方面,对于人们政治生活的目的来说,我们所主张的任何原则却都必须是要满足公共性的要求的,这一事实本身不仅是所有的个体必须理解并遵守的原则,而且必须是被“广泛认知的”[10]521。所以,个体所追求的善实际上并不是属于公共领域,它既不能为个体的社会生活提供合法性身份证明,也不能成为正义原则被选择的依据。虽然在道德世界中,我们可能会因我们自己的综合性学说而信奉某种道德信条,但在公共争论中,我们则应该寻求一种政治的、公共的原因来支持我们的论点[11]273。
罗尔斯的这一发现意味着,在一个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伦理自治要求和作为公民的政治自治诉求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一个断裂带的,因为个体在道德世界的理性自主并不能为公民在政治世界的行为实践提供一种辩护性理由。所以,在罗尔斯看来,由于在现代性社会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正义概念……必须允许多种冲突,以及那些事实上不可通约的,关于意义、价值以及人生目的的诸概念(或者……‘善的概念’)”[10]424-425,那么,由那些独立的“综合性道德学说”所构成的个体理性自主,就已经不再适用于一种现代性社会中的正义理论。
二、合理性概念对正义理论的修正
罗尔斯语境下理性概念的这些矛盾和断裂使得他不得不重新考虑正义理论的理论建构问题。在罗尔斯看来,一个“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核心概念既要在他的思想实验中能够修正个体自主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关系,又要能够在政治生活中调和“综合性道德学说”和社会正义的公共性要求,从而为个体的行为实践提供一种可辩护的公共理由。在罗尔斯看来,一种建立在理性多元主义基础之上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概念则恰好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罗尔斯首先承认了自己的正义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他说,“在《正义论》中,将正义理论描述成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一部分是一个错误。……我本应该说的是,作为公正的正义概念运用了一种服从于合理性条件的理性选择叙述。……并没有那种想法,即试图将理性(the rational)的观念作为唯一的规范性观念,在一种可加以利用的框架内,试图推导出正义语境”[8]223-251,fn20。进一步地,他调整了与合理性相关的两个概念:第一,他修正了《正义论》中关于“基本善”(primary good)的定义,将合理多元性事实和政治公共性的考虑纳入其中;第二,他重新考虑了原初状态下人们的道德能力,从而授予人们在原初状态下的两种基本道德力量——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善观念的能力*罗尔斯将这两种道德力量分别描述为“从正义的公共概念中去理解、应用和行动的能力”和“形成、修正以及理性的去从事某人理性利益或善之概念的能力”。参见文献[10]。。根据罗尔斯的这一修正,原初状态下的个体理性自治便可以与理性选择理论相融合:首先,代理人的理性特征(即代理人作为平等、自由的道德人,都追逐着自己的利益)使得他们有了最初的获得各种善观念的能力;而同时,罗尔斯所赋予的道德人的两种基本力量(即正义感以及善观念能力中修改善之概念、从事理性利益的能力)则是基于合理性的那种“包括(道德)中与‘公正的社会合作’观念相联系的那一部分”[6]51的公共性事实而设定的,它为个体利益的相互承认提供了条件,并且为原始契约的合法性提供了保证。通过这样的修正,原初状态下道德人的基本特征便具有了理性与合理性的双重特征。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这些设定中,合理性限制了“理性可以追求的最终目的”而预设了并统治着理性[10]515-532,因此,在罗尔斯的思想实验中,原初状态下道德人的根本特征便由《正义论》中的理性演变成了后来的合理性。
而另一方面,基于上文所述的个体理性自主与现代性政治生活之公共性诉求不相一致的事实,罗尔斯认为合理性概念也恰好可以弥补个体性和公共性的这种分裂:一方面,由于将“包容原则应用于哲学其自身”[8]224,合理性首先会允许一个足够宽敞的伦理自治空间,让个体拥有追求各种道德善的自由;另一方面,因为具有合理性特征的公民又会“将彼此看做是自由且平等的道德人”,并且会“为彼此提供公正的社会合作条约”[9]579,所以,合理性为社会中的广泛政治自治提供了一条可能性途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详细阐释道:
当那些平等的人之间说,如果保证其他人也会这样去做,那么他们愿意提出作为合作公正条款的原则和标准,并且欣然遵守这些原则和标准时,人们在一个基本层面上就是具有合理性的(reasonable)。这些规则被人们看做是对每个人都是可以合理接受的,并且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是可以证明正当的;并且他们已经做好讨论其他人提出的公正条款的准备。[6]49
从罗尔斯所描述的合理性特征来看,他并不考虑将合理性“从理性中派生出来”[6]52,而打算将其归结于对道德平等的现代性承诺[10]518。也就是说,罗尔斯并不会将合理性看做是一种超越于诸多对立的道德承诺之上的个体理性能力标准,而是将合理性本身就看成一种道德承诺。而这也就意味着,合理性并非是广泛适用于不同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不同社会存在类型的[8]225,它仅仅适合于以多样性综合学说为特征的现代性民主社会之中。这样一来,罗尔斯实际上就是将自己正义理论的性质从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变成了一种以实践为目的的政治理念,这也是罗尔斯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根据罗尔斯所设定的合理性基本特征,即“适合于一种被他称之为合理多元主义的情景中”[9]421,那么合理性就不仅可以是某种综合道德学说的特征,它还可以是一个社会公民的本质特征。可见,在罗尔斯那里,合理性概念既是原初状态下原始契约的公正性保证,也为政治公共性特征的需要而提供的道德辩护理由。
三、从理性到合理性: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影响
罗尔斯对理性的重视逐渐演变为对合理性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了罗尔斯意欲将自己的理论构建从一种道德普遍理论转向一种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也暗示了罗尔斯实际上放弃了将正义原则视作绝对命令的康德主义哲学立场。虽然一些契约主义者坚持认为《政治自由主义》比《正义论》采用了一种“更具有一致性和野心的观点”,并且始终号召,要将罗尔斯的著作“尽量避免和另一位作者联系起来:黑格尔”[12]81-110,但罗尔斯自己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承认,“在《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史中,我将他的(指黑格尔——笔者)自由主义视作一个重要的样本。其他诸如此类的样本是康德,以及明显更少一点的,密尔(J.S. Mill)”[13]366。
自由意志对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是极具启示性意义的,或者说,自由意志问题在整个自由主义思想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康德那里,自由意志在理性(reason)中有它的起源和规定,它不受任何情感的、智力的、美学的或者社会的经验影响,“一个善良意志是好的并不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或产生的东西,并不是根据为达到一些建议目的的合适性,而仅仅是依据意志力(das Wollen)本身”[14]12。可见,在康德看来,自由意志实际上是反对任何外在的规定而内在于道德主体自身的。也就是说,意志只有成为义务的意志时,才是充分自由的,而相应的,只有当个体遵守义务时,他才是自由和自愿行为的。由于义务“是行为出于对法的尊重的需要”[14]21,因而这样的义务要求个体回避任何的外部规定,以逃脱各种“偏好”的约束而成为绝对命令:每个人的意志是一种其箴言的总和赋予了普遍律法的意志,这一原则(……)将会非常适应成为绝对命令,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普遍立法的观点并不是基于任何兴趣,并且因此它独立于所有可能的命令,它才是绝对的。[14]49由此,一个关于纯粹义务的普遍法则得以建立: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15]31通过这个绝对命令,自由意志成了主体确立其道德身份的依据和准则,而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则成为了一个自治的、拥有绝对权力的道德主体,道德意识从而获得了普遍立法者的地位。康德的论证到此戛然而止。
在黑格尔看来,这样一种关于自由意志的论证是不充分也不完整的,所以康德关于自由意志论证所结束的地方实际上也正是黑格尔将要开始的地方。因此,在关于自由意志的基础问题上,黑格尔实际上并非全盘否定了康德的观点,恰恰相反,他基本上是同意康德那种将自由意志看做是内在于并规定着道德主体的观点的,将自由意志看做是“内在的、与自身独自相关的”[16]89。不过,黑格尔虽保留了康德的观点,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自由意志实现自身的最终形态,因为这一阶段的自由意志还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不确定的东西。若要真正实现自身,自由意志还必须“作为一个内容和对象从无差别的不确定性向差别性、规定性以及确定性安置的转变”[16]33,这才是黑格尔真正想要说明白的问题。可以看出,康德道德哲学中所论证的自由意志之发展过程并未被黑格尔所拒绝,只是在他看来,康德的自由意志最终还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在黑格尔特有的术语中,那种被他称作“抽象”的意思是指那种还未顺利成为真正之实体的东西,是那种还不能够展现、执行其存在之实质的东西。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自由意志要最终实现自身,就还必须走出主体自身而面向世界。也就是说,除了保持自身严格的纯粹性外,道德主体必须去充当一个“社会存在者”,它必须接受成为外部世界或他人“感兴趣的客体”。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关于自由意志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并未将自由意志从“应当是”(ought to be)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却是必须的,因为“那些普遍合法的(正当的)的东西也是普遍有效的”,而“那些‘应当是’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是’(is),并且那种离开(真实)存在的‘应当是’,是没有实质的”[17]151。
罗尔斯显然是认清了康德和黑格尔在自由意志上的真正分歧,并且倾向于接受黑格尔的观点的。他在讲授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就曾将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解释为“意愿其自身作为自由的意志”[13]330,并且由此评论道,“黑格尔将康德看做是被一种为了彻底纯粹的、从道德律法自身出发而行动的意欲,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打动的”[13]335。罗尔斯的这一阐释和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他准确无误地指出了两者的差异所在。而更进一步的,罗尔斯认为政治哲学“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应该是’的世界,那个位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地方(正如黑格尔认为的康德哲学所做的),而是一个实现其自由的眼前世界”[13]332。从这一陈述上来看,显然罗尔斯是更愿意接受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康德的主张的。
四、政治实践:重叠共识与黑格尔的整体性考虑
熟悉黑格尔哲学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人会发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其自由意志的第二阶段,与罗尔斯的理性概念是完全对应的”[18]756-780。概括地说,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语境中被看做是一个主观性得到解放的领域: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以其具体目的为自身对象”[16]122,通过自由意志的作用使得个体的潜能、德性能力以及创造能力得以最大化发展,个体自由也由此得以展现。所以,黑格尔也将自由意志在市民社会的这一发展阶段称作“为其自身”(for itself)的阶段。黑格尔所论述的在市民社会阶段中的自由意志与罗尔斯语境下个体对道德善的理性自主状态是高度一致的。如果将黑格尔的意志自由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置换成罗尔斯的术语,则可以阐述为,在我们的“社会世界”中,个体可以自主地选择或支持一种“综合性道德学说”,这些综合性学说包括“什么是在人类生活的价值概念,个人的美德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并且当我们确立起这些学说以后,它“(在我们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限定下)对我们的行为多加指导”[19]424。由此,那些社会的基本善通过这些综合性学说而得以确立,并且作为一种“必需品和通用手段”,它们使人们“意识到且练习他们的道德力量,并追求他们的最终目的”[10]526。在这样的情景中,这些基本善被看做是理性的,因为这体现了个体对他们自己所赞成综合道德学说的某种偏好。实际上,无论是黑格尔所谓市民社会中的意志自由,还是罗尔斯术语下社会世界中的理性自主,其实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思:个体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1.以整体性为支撑的反思性自我意识与以公共性为前提的综合性学说
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个体主观性的彻底解放虽然并不是自由意志发展最高阶段,也不能确保自由的真正实现,但它却是现代性国家精神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必要环节。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的意志自由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自由,而“特殊性本身是无限的无节制,这种无节制的形式本身就是无限量的”[16]123(ad)。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自由意志停滞在市民社会阶段,那么个体通过他的思想方式和反思,则可以任意且无限地“扩大他的各种欲望”,这些欲望“不是一个像动物本能一样的封闭圆圈”,而是将自由“带入一个错误的无限之中”[16]123(ad)。黑格尔的这一论证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被他称之为“反思的自我意识”的自由意志在传统世界是没有发展余地的:因为传统城邦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还未足够强大到允许个体充分发展他们的主观性。所以,个体对自我满足的追求对一个共同体的完整性构成了威胁,传统社会对这种“自我满足的特性感到恐惧”,并且将个体的主观性自我主张看做是“一种伦理堕落的侵犯和世界衰败的终极原因”[16]123,而这种“错误的无限”正是传统社会想要避免的最大危险。在黑格尔看来,能够接受并使这种个体反思性得以生存的东西并不是别的,正是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在现代性特征不断发展这一历史背景下,现代性国家比传统国家更加完善和强壮,它的原则“具有巨大的强度和深度”,以至于能够在“允许主体性原则在个人自我满足特质的极端中朝着它的顶端发展”的同时,又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将主体性“带回到真实的联合体中,并且因此坚持这一联合体在主观性原则自身当中”[16]161。
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在罗尔斯那里同样得到了回应。在罗尔斯看来,个人的“综合性道德学说”同样也不能满足以多元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的要求。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理性自主在其关于道德理由的陈述里并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他赋予了合理性和公共理由以绝对的优先权,“合理性被包含建立原初状态的背景之中,它框定了参与者的讨论范围,并使得他们处于对称的地位”[10]529。而在《正义论》以后的著作中,罗尔斯不仅赋予了公共理由一个更清楚的角色,而且让公共性具有了更高的要求。正如Charles Larmore所注意到的:“当我们使自己的理由符合他人的理由时,我们是尊重公共理由的……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正义概念是我们所认可签署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可能发现的不同原因,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为了我们偶尔会共享的原因,而是为了那些对我们而言有价值的原因,因为我们能够相互承认它们。”[20]368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公共性而构建出来的合理性概念就不再仅仅是各种原则的正当性来源,它也是那些背负着不同的综合性道德学说的个体能够达成共识的缘由;而理性也因为被合理性绝对地限制了“能被追求的最终目的”[10]530而从属于合理性。而另一方面,罗尔斯则认为能够使得个体理性地存在及其充分地发展得以保障的东西,正是现代性的“社会基本结构”以及应用于这一结构的各种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基本结构所授予的个体的公共身份(或合法身份),成了个体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能够拥有其特殊潜力的根本性条件。进一步的,为了给理性提供最大的生存空间以允许个体性的最广泛发展,罗尔斯又限定了合理性的行为领域范围将它与政治边界接壤,他强调“作为公正的正义强调这一差别:它肯定所有人的政治自治,但是留下了伦理自治重量的空间给公民根据他们的综合性学说而各自决定”[6]78,并且明确表示,政治自由主义保障所有公民所通用的充足的财富(基本善),所以他们能够聪明地利用其自由的行使[13]366。那么,罗尔斯断言,在一个“合作的公正系统”[6]15中,所有个体的基本善都在相互间得以充分肯定和认可,“我们可以合理地预期,他者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同样地可以接受那些理由”[9]579。实际上,罗尔斯这种对社会基本结构的信任与黑格尔那种“不必为主体性焦虑”所暗示出的对现代性国家的信心是如出一辙的。可见,正如黑格尔将反思性自我意识置于现代性国家的整体性考虑之中一样,罗尔斯也将主体性理性自主纳入到公共生活的考量之中的。或者可以说,正是因为黑格尔透过现代性社会的种种现象而发现的主体性时代特征,才给了罗尔斯关于在多元主义事实基础上构建起合理性概念的启示。
2.公民的“重叠共识”与黑格尔关于自由意志的“和解”
除上文所述,罗尔斯和黑格尔两者在具体论证特殊性(理性自主)与整体性(公共性)的关系上,也体现出了一种理论上的相关性和亲缘性。在对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关系做出阐释之前,黑格尔将一种“共同意志”从普遍意志中区分了出来。在其对关于契约的解析中,黑格尔将那种“只能由双方当事人设定”而达到“定在的共同意志”看做是一种共同意志[21]82。在他看来,这样的共同意志并不能体现合理性的那种“普遍性与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21]254,因为它的目的是从个体的“任性出发”的。在本质上,这种共同意志仍然是一种“特殊意志”[21]90,它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公共性特征。而相类似的,罗尔斯在对重叠共识与理性自主的关系做出说明之前,也将公共意志与共同意志做了某种区分,只不过在罗尔斯的语境中,“契约”这一术语则被他置换为了“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6]147-149。他认为,“权宜之计”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利益”或“群体利益”上的“权威的共识”,或者是一种建立在“政治谈判”上的结果[6]147。在罗尔斯看来,这种权宜之计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是一种“依赖于利益集中的条件环境”之“偶然性”结果[6]147,而真正的社会稳定性却要以“能够被具有理性与合理性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所接受,并且诉之于他们的公共理性”为目的[6]143,所以它并不是全体公民的公共意志,也不具有根本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罗尔斯作出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因为黑格尔关于共同意志的观点所直接针对的就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契约主义观点,而在现代性社会中公共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上缺乏一种系统的论证,这正是传统契约主义的关键症结所在。实际上,黑格尔与罗尔斯的这种区分都传达出同一种意思:那些能为现代性社会提供正当性(合法性)辩护的诸依据,都必须将基于主体反思的特殊性和基于多元事实的公共性纳入其中。在黑格尔的术语中,它表现为“伦理”,即那种“主观的善和客观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善的统一”[21]162;而在罗尔斯的语境下,它表现为“合理性”,即那种“要求将包容原则运用于哲学自身”,并“能够帮助公民同胞在政治争论中提供一些道德辩护,而且这些道德辩护也能够是公共的”政治概念[19]430。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伦理”的现实形式就是现代性国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主观自由与客观自由根据一种普遍的规律和原则得以统一[21]254,也就是说,它们在伦理中根据概念产生了“调和”[21]162。而在罗尔斯那里,“合理性”则具体应用于宪政民主的基本社会结构中,它体现为基于个体综合性学说与公民正义政治概念的需要而达成的重叠共识。由此一来,重叠共识便成为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在这种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诸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既确定了一种综合性学说,又坚持了一种(正义的)政治概念”[6]608-609。
无论是黑格尔所要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调和”,还是罗尔斯想要达成的“重叠共识”,现代性社会中的这一目的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都是必要且必须的。具体来说,这种“和解”在黑格尔的观点中可以表达为:共同体的总体性关系到个体的普遍性,即作为公民的政治身份以及政治自由;个体如果被他的同胞所承认,他则获得了普遍性或政治自由。换句话说,普遍性或政治自由的存在实际上取决于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相互间将彼此看成是普遍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个体,即,作为一个应得到与“我自己”同样尊重、同样考虑、同样利益和同等关怀的实体。正如威尔(Eric Weil)对黑格尔正确解读的,“实质性的自由并不是个体的任意(……)就其意愿在一个自由的共同体中的人之自由而言,这个人才是自由的”[22]36。这一评论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中个体的政治自由必然地会支持共同体中所有个体的自由,也就是说,个体特殊性为什么要与整体普遍性达成某种“和解”。类似于黑格尔的观点,罗尔斯同样坚持,政治哲学家必须使他们自己与现代性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多元性相一致,并且因此而协助建立一种包括带有很多不同世界观的社会合作的政体。所以,必然的,现代政治哲学“从一些共识出发:从那些为了基于政治正义基础而达到一种可行的一致的目的,我们和他人都承认是正确的,或者合理的前提出发”[19]426-427。正如Jean Hampton所评论的,罗尔斯为我们“制作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即无论政治哲学是否应该涉及其他任何东西,“它都应该关注如何最好地创造一个真实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个作为共享的承诺,能够为那些在其他方面被道德、宗教和哲学的不同而分裂的东西而服务的政治自由主义”[23]809。而重叠共识则体现了这一要义,因为它“在一个或多或少正义的宪政民主社会中,包括了所有可能会持续并获得支持者的相互对立的哲学和宗教学说”[8]421。这样一来,一种重叠共识使得许多重要道德承诺的实质性一致意见成为必须,那么,以“公平的正义”作为核心的重叠共识在成为一种政治信念的同时,也具有了“道德信念”的本质[6]119。
实际上,无论是黑格尔的“和解”还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都意味着在多元环境下一种对“他者”的承认。也就是说,将“他”看做是“我”所希望“我”被他人所接受的那样。将他人看做是与“我自己”严格平等的存在者意味着“我”必须接受“他”与“我”不同的部分,即,“他”的理性自主部分,那样,“我”则同样会希望我的同胞能够接受“我”以及“我”与他者的不同。如此,他者与“我”就都作为一个独立理性的存在者而又可能在一起生活。简言之,在黑格尔的术语中,承认的这一行为使得民族成员在现代性国家中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解;而在罗尔斯的语境下,则使得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理性自主在合理性要求下达成了诸种重叠共识。总的来说,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共享着类似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并不是康德所要达到的。黑格尔和罗尔斯都试图让个体去“面向一个开放的世界”,并且寻求能调解合理性与理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可能性条件。他们的哲学理论是想要建立起一种经验的、可践行的理论,并且这一理论检验了政治自由如何能够被获得。当然,从两个人的整个哲学体系来说,黑格尔与罗尔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不同的,黑格尔“和解”的理念是基于国家正义的天然合法性,要求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相“调和”,最终确立起国家的绝对精神和权威;而罗尔斯则是基于道德多元性的事实,使得理性自主与政治社会的公共性要求达成一致,从而证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当性。正如内格尔(Thomas Nagel)所说,根据罗尔斯的观点,“政治理论的终极目的”将会是“对每一个被要求生活在某种政治体系下的人证明这个政治体系的正当性”[24]33。显然,罗尔斯的理论旨趣与黑格尔是大相径庭的,或者说,在理论旨趣上面,罗尔斯更倾向于康德哲学,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再累述。
五、结 语
总之,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英美世界现代政治哲学的代表,他的确吸收了除康德哲学以外的其他哲学思想。这一事实也许使得罗尔斯在传统契约主义立场上有所让步,或者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与他的《正义论》所体现的“野心”相比,罗尔斯在后来的著作中对康德主义立场的坚持做出了一些妥协和退让。但是这种在契约主义立场上的退让并不意味着罗尔斯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失败的或退步的,相反,可以说他基于一种现代性要求,恰恰弥补了传统契约主义的不足和缺陷。同时,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理论也启发了一些新的思想,比如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塔米尔(Yael Tamir)关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等,都将罗尔斯的“合理性”概念和公共性要求视作重要参考。可以说,作为一种到今天仍在西方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政治哲学思想,对罗尔斯做这种理论渊源上的审视是非常必要的。
[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 Susan Moller Okin. Reason and Feeling in Thinking about Justice[J]. Ethics, no.2, 1989.
[3] Audard C. Principes de justice et principes du libéralisme: la “neutralit?” de la théorie de Rawls[C]//C. Audard, J.-P. Dupuy and R. Sève (Eds.), Individu et justice sociale: Autour de John Rawls. Editions du Seuil, 1988.转引自:Allyn Fives. Reasonableness, Pluralism, and Liberal Moral Doctrines[J]. Value Inquiry: 321-339, 2010.
[4] Emanuel Kan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M]. Bobbs-Merrill, 1974.
[5] Otfried Höffe. Dans quelle mesure la théorie de John Rawls est-elle kantienne?[C]//C. Audard, J.-P. Dupuy and R. Sève (Eds.), Individu et justice sociale: Autour de John Rawls. Editions du Seui, 1988.转引自:Ragip Ege and Herrade Igersheim.Rawls with Hegel: The concept of “Liberalism of freedom”[J]. Euro. J.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5-47,2008.
[6]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7]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M]. ed. Erin Kel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 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J].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1985(14).
[9] 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C]//Samuel Freeman. ed., John Raw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John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J].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No.9, 1980(77).
[11] Paul Weithman. Deliberative Character[J].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3, no.3, 2005.
[12] Munoz-Dardé V. Le partage des raisons[J]. Revue de Philosophie Economique, 2003(7).转引自:Ragip Ege and Herrade Igersheim. Rawls with Hegel: The concept of “Liberalism of freedom”[J]. Euro. J.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5-47, 2008.
[13] 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M]. In B. Herman (Ed.),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 Kant 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M]. Bobbs-Merrill, 1949.
[15]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韩水法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16] Hegel G W F. Philosophy of Right[M]. T.M. Knox,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7] Hegel G W 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M]. A.V. Miller,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8] Michael L. Frazer. John Rawls: Between Two Enlightenments[J]. Political Theory, Vol.35, No.6. 2007.
[19] John Rawls. 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C]//Samuel Freeman, ed.,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Charles Larmore. Public Reason[C]//Samuel Freem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aw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张企泰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22] Weil, E. Hegel et l’Etat.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74. 转引自:Ragip Ege and Herrade Igersheim. Rawls with Hegel: The concept of “Liberalism of freedom”[J]. Euro. J.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25-47,2008.
[23] Jean Hampton. Should Political Philosophy Be Done without Metaphysics?[J]. Ethics 99, No.4,July, 1989.
[24] Thomas Nagel. Equality and Partialit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责任编辑 许丽玉)
2017-01-20
张轶瑶(1985—),女,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西方现当代伦理学理论。
D091
A
1671-511X(2017)04-00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