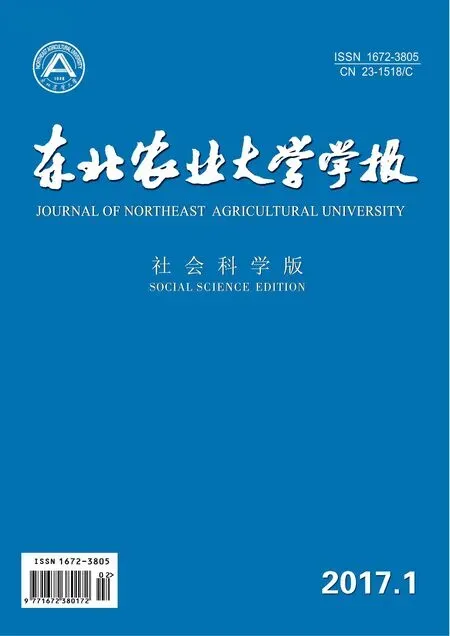罗兰·巴特理论视域下的福楼拜作品
——以《布瓦尔与佩库歇》为例
魏琛琳
(香港大学,香港 999077)
罗兰·巴特理论视域下的福楼拜作品
——以《布瓦尔与佩库歇》为例
魏琛琳
(香港大学,香港 999077)
福楼拜晚期作品《布瓦尔与佩库歇》被认为是超越时代的巅峰之作,体现其创作风格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发展演变。将作品置于罗兰·巴特理论视域下,发现其与“零度写作”“作者已死”“写作风格先天性”“文本模仿性”“无意义的终极意义”等理论存在契合之处,可为解读福楼拜作品提供新视角。
罗兰·巴特;福楼拜;《布瓦尔与佩库歇》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其创作生涯前半期以《包法利夫人》为代表,表现出现实实主义风格及一定浪漫主义色彩;后期创作风格多样,呈现出自然主义甚至现代主义特征。《布瓦尔与佩库歇》为福楼拜最后一部作品,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但其思想性和写作手法明显不同于福楼拜其他作品。本文以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理论阐述福楼拜创作,从比较文学角度论述二者之间的互为认同。
一、“零度写作”与“绝对真空的客观性”
(一)以沉默方式存在的“零度写作”和“作者已死”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文学界认为作品是创造的产物,是外部客观世界在作者头脑中的投射,作者主动创造作品,而读者只能被动接受。对此,罗兰·巴特提出“文本”概念,并在《从作品到文本》中明确提出文本与作品不同,作品受限于作者的创作技巧,而文本“由语言决定:它只作为一种话语(discourse)而存在”[1],其意义源于文学结构,而非作者创作。因此,作者主体想象被否定。
罗兰·巴特极力强调文本的独立性,提出“零度写作”和“作者已死”概念。罗兰·巴特将一种脱离文学语言,但并非通过混淆句法、解放词语的社会语境摆脱文学套语的写作称为“白色写作”,又称“零度写作”。即一种“直陈式写作”,或“非语式写作”,亦可称为不做判断的“新闻式写作”,特点是“存在于各种呼声和判决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又毫不介入,其恰好由后者的‘不在’构成,但这种‘不在’是完全的,不包括任何隐蔽处或任何隐秘,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纯洁的写作。”[2]
“零度写作”意图消除写作的干预性、价值评判与功利色彩,从而扩大写作本身的容量及可能性。于是语言摆脱工具性地位,以沉默方式存在,因此在“零度写作”中,语言呈现一种纯中性的可变迁的方程式状态。
“作者之死”意在放开文本的专名权和垄断权,让文本充分“自我嬉戏”。作者退场导致的沉默显然是另一种形式的零度。罗兰·巴特区分“作者”与“作家”两个概念,认为前者以语言实现既定写作目的,后者则将读者引向写作活动本身。于作家而言,写作本身即目的,而“现实”唯一的责任即支持文学作为一种写作活动而存在。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对此观点分析更为详尽。简而论之,意在表明“(叙事中的)说者不是(生活中的)写者,而去写的人也非所是的人。”[3]叙事文学被抽离了具体事件,仅保留叙事写作本身,展开叙事的并非作家,而是语言结构。因此,写作是作家的自由,是一种形式、言语的自由,其与读者、政治、伦理的自由全然无涉。
(二)“作家——艺匠”式写作
就古典写作而言,形式仅有工具价值。罗兰·巴特削弱作家主体地位的理念直接导致其对形式的强调,成就其著名的“作家——艺匠”式写作。
“作家——艺匠”式写作的提出源于1850年前后文学界的一个争议,即写作在寻求其托词(alibis)。许多作家试图以劳动价值取代写作的实用价值,即“写作将不是因其用途,而是因其花费的劳动而被保全。”[4]罗兰·巴特认为,以劳动价值取代写作的实用价值,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劳作,故称为“作家——艺匠”式写作。作家被封闭在一种传奇性界域内,加工、削切、磨光和镶嵌其形式,以便将个人孤独和努力转化为规则时间内之劳动。
罗兰·巴特还强调字词本身的厚度、字词的空间和物质性。他认为写作是对语言的实践,而语言在写作中获取活力。语言是写作的内容、物质性目标、托付性场所和价值所在。写作是不及物的,没有宾语、外部世界以及语言之外的遥远目的地。
(三)福楼拜作品在形式上契合罗兰·巴特理论
福楼拜试图确立“作家”而非“作者”地位,与罗兰·巴特主张一致。他倡导写作时应“回到写作自身”,追求“绝对真空的客观性”。
“回到写作自身”,对福楼拜而言首先表现为取消内容和形式的对立,即将形式视为内容,将内容视为实现形式的手段。福楼拜将思维与写作等同视之,两者均为一种活动。写作不再被视为一定思想和激情的最终表达,而是完整的存在,达到“绝对真空的客观性”。其次,罗兰·巴特认为“写作本质即拒绝回答‘谁在讲话’”。纵览福楼拜创作,其很少在作品中直接表明见解或通过作品交流,如罗兰·巴特在《S/Z》中描述:“他不停地玩弄代码,结果人们永远也不知道他是否对其所写的东西负责。”[5]
福楼拜给路易丝·高来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理想的事,我愿意做的事,就是写一本关于虚无的书,一本与书外任何事物都无关的书,它依靠自己风格的内在力量站立起来,正像地球无需支撑而维持在空中一样;它也将是一本没有主题的书,或者至少难以察知它的主题在哪里……最好的书是那些包含材料最少的书。”[4]后来他再次论述形式与思想风格,“对我来说,在一定的句子里,只要没有把形式和实质分离开来,我都会坚持认为这两个词是毫无意义的。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反之亦然。在艺术世界里,美从形式渗出,有如我们自己的世界,从形式生出诱惑和爱。同样,你也不能从观念里剔除形式,因为观念仅仅依赖形式而存在。你去设想一种没有形式的观念吧,这根本不可能,正如一种形式不可能不表达某种观念。”[6]
福楼拜让形式摆脱对内容的依赖,使形式获得独立地位,甚至对内容产生影响,表现在其对意义的消解——福楼拜作品动人之处,在于作品功利色彩消失和主题意义衰退,即通过结构、风格等纯粹力量的结合实现。福楼拜认为,思想性主题即作家整体视野的最终组织原则,“它常把有力的特性隐藏在外观变化之下,达于不可言说”。福楼拜倡导艺术超越生活的形式主义美学理想,他甚至说过一些极端的话,如“我愿意创作这样一类书,它只要求写下一些句子”“主题这个词是无意义的”“对于我来说,作品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等,足见其重视艺术形式。他在形式上花费大量劳动,使形式不再被专断的意识形态利用。此技艺式写作不仅成为作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拯救术,还通过不易令人察觉的独特方式揭发和嘲讽世界的愚蠢。福楼拜于艺术形式探究方面的明显自觉,一定程度上契合罗兰·巴特“作家——艺匠”式写作。
就创作风格而言,福楼拜注重日常生活。与其他作家预设主题、带有目的性的创作不同,他常不惜笔墨描写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力求精确“再现”而非“加工”日常生活。其笔下极少人工编排与臆造的戏剧性,更鲜见惊心动魄的开端或令人拍案叫绝的结尾,仅以真实取胜。以吃饭为例,巴尔扎克曾将埃克托·曼兰与暴发户攫取财富的贪婪联系在一起,但福楼拜仅止步于对包法利夫人烦闷和无奈的客观描写,并未加入主观引导性评论。奥尔巴赫也对爱玛吃饭的段落大为赞赏,认为其再现“无形式的悲剧……福楼拜是直接捕获这种心理学状况长期性特征的第一人”[7]。福楼拜作品主题意义的衰退使其整体创作风格呈现独特魅力。
二、福楼拜创作与罗兰·巴特“写作风格先天性”的共通
(一)罗兰·巴特“写作风格先天性”论述
语言结构是作家的“他者”,作家无法挣脱的地平线。但同样的语言结构,作家姿态与作品不同——写作风格即差异形成原因。罗兰·巴特将风格和作家本身及经历联系起来,认为形象、叙述方式、词汇等作品要素均取决于风格,“于是在风格名义下形成一种自足性语言,只浸入作者个人、隐私的神话学中,浸入此种言语的形而上学中。”[8]罗兰·巴特认为写作风格缘于一种生物学基础,是文学习惯的私人部分,是“作家的事物、光彩和牢房”[8],是作家的本能冲动,应归属于发生学。因此,写作风格至少有一半是先天性的。
(二)福楼拜主体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
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不同性质的材料,都会获得‘他本人风格情调的深刻印迹’[9]”说法正确与否时,曾如此介绍福楼拜创作:“福楼拜式宛若在一块浑然整料上雕镌而成的史诗小说”[9],或如《布瓦尔与佩库歇》之类,虽“汇融了内容极不相同的材料”,但材料性质差异却“服从于贯穿作品始终的个人风格和情调,服从于一个统一的世界,统一的意识”[9]。福楼拜的个性、社会政治立场及哲学观念等主体因素,深刻影响其创作。
1.个性。福楼拜特立独行,藐视法律规范,作品呈现离经叛道倾向,其本人也曾因小说创作“道德败坏”而被指控。
以《布瓦尔和佩库歇》为例,佩库歇认为:“罪恶是自然的属性,有如火灾和风暴。”[10]布瓦尔和佩库歇抨击神学目的论。二人认为恶魔、混乱等,不过是人们为满足自我目的制造的成见。如布瓦尔说:“为什么是恶魔?当瞎子、白痴、杀人凶手来到世上时,我们觉得那是混乱,仿佛我们了解什么是秩序似的,仿佛大自然的活动都有目的似的!”[10]而当两人因怀疑上帝而被攻击时,布瓦尔果断地说:“是的,我怀疑上帝!”[10]佩库歇更指出上帝无视历史上国王被谋杀、人民遭屠戮,认为上帝并不偏爱人类,却“照顾小鸟”,还“让鳌虾长爪子”,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上帝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过是具有各种自然属性的上帝。所以布瓦尔和佩库歇认为,攻击者实际站在旧神学立场看待问题,将美好且符合目的性的一面归功于上帝,而将丑恶和混乱归咎于魔鬼,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布瓦尔和佩库歇在世俗里必然被归入伤风败俗、道德败坏、诲淫诲盗者之列,并被罗福以“再言此论必要坐牢”威胁。二人观点带有明显的福楼拜自身性格烙印。
2.社会政治立场。福楼拜曾对记者毫不讳言,“我憎恨日常生活”[11],甚至写出“生活这么可怕,人们只有回避生活才能忍受它。[12]”由此类不满社会的言论可见,福楼拜坚持拒绝大众化并反抗世俗现代性的立场。
此外,因福楼拜厌恶人类,致其作品充满虚无主义。他曾写道:“我一个人抵得上克鲁瓦塞的十二个选民”“我一点也不恨公社社员,原因是我不会去恨疯狗”“我相信人群、畜群总是可恨的”“如果法国不是像现在这样总而言之被大群人统治,而是由名流才子掌权,我们能落到今天的地步吗?”对现实的憎恨投射到创作中,《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以冷静态度面对现代的愚蠢①“现代的愚蠢”一词来自米兰·昆德拉对福楼拜《庸见词典》的评论:“现代的愚蠢并不意味着无知,而意味着固有观念的无思想性。”;《萨朗波》《圣安东尼的诱惑》借助古代和异域题材表达对现代社会的逃避;《流行观念词典》以直接方式嘲讽现代的愚蠢。在《布瓦尔和佩库歇》中,两位主人公追求知识,福楼拜将其对不同读物的信仰荒诞化,如花园的设计中将园艺学变成笑话,将爱情转化为性病等,以尝试的失败印证信仰的愚蠢,揭发和批判世俗愚昧和科学蠢行。
除作品主题,人物形象亦蕴含福楼拜拒绝大众化和批判世俗的立场。他笔下人物有的浅薄、庸俗、空虚,有的痴呆、少语、无法理解他人,有的欲望过于强烈,有的冷漠、自私、残忍,甚至有精神问题,时而喋喋不休,时而废话连篇……这些人物表现的笨拙、愚蠢乃至病态,均体现福楼拜对现实的憎恶。
3.哲学立场。(1)否定自由意志。福楼拜否定自由意志,同样影响其创作风格。“你,自由!一落地,就呈有一切父母的疾苦;一生下,就收到所有罪恶的种子,甚至于你的愚蠢、你评判自己、人生与环境的标准。”[13]他认为,人的自由有限,人无法选择与生俱来的一切,而是被不加协商地抛到这个世界。甚至人的出生也是命里注定,“因为你的父亲有一天从宴会回来,喝多了酒,听多了脏话……”[13]以及“我否认个体的自由,因为我不觉得我自由”[13]。
这种自由意志否定论在《布瓦尔与佩库歇》中有明显体现。就布瓦尔而言,人的犯罪由本性决定。道德无法战胜本性,自由意志并不存在。腿的活动表面看是自由的,实际受活动动机决定;杂货店老板是否分财产给穷人,取决于其本性。决定来源于动机,而动机则出自众多考量。依同样逻辑,佩库歇认为罪恶是自然属性,完全不受个人意志支配。主人公的观点、行为均带有福楼拜印记。
(2)死亡迷恋与虚无主义。面对进步和文明事实,福楼拜和当时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一样倍感失落,并因此产生颓废思想。
福楼拜很多作品表现其厌恶文明事实、世俗世界和人类本身,有些作品甚至带有明确的死亡意识,表达对死亡以及腐烂的迷恋。以《布瓦尔与佩库歇》为例,两位主人公散步时,一股臭味使其停住脚步。作品这样描述:“他们看见石子地上的荆棘丛中躺着一条腐烂的死狗。四肢已经干了。死狗龇牙咧嘴,发蓝的下唇里露出乳白色的獠牙;已看不见肚子,因为肚子上蒙了一层土灰色的东西,似乎在微微颤动,原来那里爬满了乱躜乱动的寄生虫。在太阳的刺激下,在苍蝇的嗡嗡声中,虫子躁动不安,它们周围极度难闻的臭味仿佛在折磨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10]此颓废意识最终将福楼拜推向虚无主义,在探讨死亡时,作品表现出与《等待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是两个单身汉,同样怀疑上帝存在,同样妄想自杀。布瓦尔和佩库歇认为生的痛苦或虚无比死亡更可怕,与生活的荒谬相比,死亡反而更有价值。“说到底,死亡并不存在。那是去露水里,去微风里,去天上的星星里……我们面临的虚无并不比我们身后的虚无更可怕……什么东西都比现在这种单调、荒谬、毫无希望的生活有价值。”[10]除《布瓦尔与佩库歇》,《萨朗波》《圣安东尼的诱惑》等晚期作品中描写的自律性、去中心的分裂性和语言的狂欢性均体现此风格特点,类似某种精神分裂式书写体。也许在此意义上,萨特才说福楼拜的句子“没有血脉”“没有一丝生气”。
三、福楼拜作品体现的“文本模仿性”
(一)罗兰·巴特文本、回声、参照的论述
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罗兰·巴特认为作品是有章可循、有语法构造的长句,有凝集力和中心点的逻各斯类型。但在《作者之死》中,罗兰·巴特又以写作取代文学,不再依赖固定秩序,也不拘泥于深层结构法则,而是一种“转抄”,文本彼此间模仿,甚至改写和复制,将此次写作融入其他写作再加以变更,即其论述的“模仿性”。
具体而言,罗兰·巴特认为任何文本皆非始源性的,而是临时组装物,是对先在、现成文本的回声、引文、参照,具有模仿性。每个文本和其他文本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纠缠、纷争,既相互参照又相互区别,显示出各自独特性。文本间无内在语法联系,因此并不构成封闭系统,即“文本和文本之间没有任何隶属、控制、支配和权力关系,只有相互之间的指涉关系。”[14]
(二)福楼拜的戏拟揭破现代文化抄写实质
福楼拜揭破现代文化的抄写实质,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化和所谓的科学、民主社会里,陈词滥调成为现代精神、价值观和各种流行观念的载体,实质在于复制他人语言,导致原创性退化和堕落。
在此基础上,他直面自我写作创造性的匮乏。《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白日梦是流行小说的复制,郝麦的“科学”文字是药学文本的复制,爱玛死亡场景甚至参照搬医学说明书,揭示现代时期原创性的普遍匮乏。《布瓦尔与佩库歇》亦如此,以陈词滥调建构人物性格及行为,指出现代人愚蠢、空洞的语言实质,更暴露出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无聊和意义贫乏。“福楼拜意识到写作不过是重复别人的老套,作家则是布瓦尔和佩库歇那样的抄写员。”[15]
抄写员职业特殊,如机器一般按指令抄写,实际暗示了作品主题基调。两位主人公生活中的有意模仿行为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因继承一笔遗产,二人从抄写任务中解脱,但不得不复制(另一种形式的抄写)由书写权威规定、表现在理论和实用科学、教育及其他领域中的行为,还常因无法理解和遵循说明书而失败。又如二人多次提及生活中的千篇一律,“视野里的东西永远千篇一律:正面的田野,右边的教堂,左边的一排白杨树……老是那副可怜巴巴的模样。”[10]评论大仲马“书里有多少陈词滥调啊!”[10]认为司各特小说“画面千篇一律,全是彻头彻尾的假象”“厌倦了那些书里千篇一律的故事结局”[10]。从主人公视角隐喻描写创造力匮乏,侧面揭示现代文化的抄写实质。
布瓦尔和佩库歇许多行为带有戏拟和模仿性质。他们亵渎一切,以夸张滑稽的方式将事物喜剧化、低俗化。在乡下走廊里,他们怪声怪调朗诵拉辛和莫里哀的伟大悲剧。演出时,“布瓦尔像在法兰西剧院一样走步,一只手放在佩库歇肩上,还不时地停下脚步,左顾右盼,伸出双臂控诉命运。”[10]“在表演法兰斯学院院士马蒙代尔的剧本《克雷奥帕特》时,打算让自己发出‘眼镜蛇的嘘嘘声’,而实际却发出沃康松的自动木偶的叫声。”[10]主人公化装后在农庄里“粉墨登场”,此时有蜘蛛爬来爬去的客厅是对剧院的戏拟,铺了抹布的椅子是对观众坐席的戏拟……如此,《布瓦尔和佩库歇》被写成一部异类并陈的小说,罗兰·巴尔特的文本、回声、参照论或受此启发。
文体方面,与《包法利夫人》中关于风景、日落、大海等的谈话及浪漫主义流行话语系统极为相似,本文认为《布瓦尔与佩库歇》亦借鉴其他文本文学体裁,小说背景为两位抄写员退休后隐居乡间,希望开始单纯、悠闲、幸福的人生,一定程度上借鉴描写乡下生活的牧歌体,但并非描写牧歌式罗曼蒂克爱情,而是让男主人公滑稽使用、模仿话语和知识,构成该文本“决定性特征”。小说涉及农学、园艺学、化学、医学、生理学、地质学、矿产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诗学、美学、政治学、哲学、宗教、教育学等,不仅反映当时科学思潮流行的时代特征,更是对百科全书体的戏拟。此类模仿的区别性特征在于主要人物遭遇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失败,进而把“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变成玩笑。此即福楼拜于文体层面对牧歌体和百科全书体的援引和参照。
戏拟及其决定性存在消解着福楼拜作品主题意旨表达,使读者无法得到确定视角和结论,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作品表现性,达到“无意义的终极意义”。
四、福楼拜作品呼应罗兰·巴特“无意义的终极意义”理论
(一)“无意义的终极意义”
传统诗学认为,若文学作品意义缺失或具不确定性,作品阅读惯例即遭到破坏,读者无法将其带至期待视野。因此,根据传统诗学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作品中一切层次均为提供意义而存在。
罗兰·巴特认为,文本并非封闭的意义实体,而是一个无内在结构、无终极意义、无固定所指和外部范围的能指群。毕竟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在阅读中随时产生新想法,成为“意义生产者”扩展了作品意义,但此意义不完全取决于读者,应该说作品自身的消解和聚合亦从未停止。因此,罗兰·巴特认为,在理论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实际均无确定的终极意义。
福楼拜作品意义即无边界,甚至空洞。如《布瓦尔与佩库歇》中,当两位主人公于乡间别墅中临窗远望,“对面是田野,右边有一个粮仓、一座教堂的钟楼;左边是绿帘一般密密的杨树。两条主要的小径,十字交叉,把园子分为四块。几个花圃都种着蔬菜;矮矮的柏树和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东一处西一处点缀其间。园子的一边有一架紫藤,从那里可以直达诺曼底地区特有的那种葡萄棚;另一边是支撑一排排果树的山墙;园子深处,一道栅栏面朝乡野。墙外是菜园,走过金榆树林荫小径可以看到一丛小树;栅栏后面是一条小路。”[10]读者见此番描述,通常视其架构的世界为真实存在,但作品意义却依然难以捉摸。很多学者特别关注福楼拜此类描写和其中的数据记录,并最终将其释为无意义。追逐无意义,为福楼拜作品突出特征之一。
(二)反讽手法导致作者隐去和终极意义缺失
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的整体性不在于起因(作者),而在于其目的性(读者),“为使写作更有前景,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之死为代价”[16]。
“福楼拜凭着驾驭那浸透了不确定性的反讽,造成对写作有益的艰难:他不中断众符码的运转,因此,人们绝不知晓他是不是造成作品如此面目的原因(不知晓他的语言背后是否有个主体),这显然是写作的标志;因为写作的本质是从来不回答谁在说话这个问题。”[5]乔纳森·卡勒对此评价:“好像罗兰·巴特的意思是说:随着福楼拜的出现,‘后现代主义的符码被写下了’。”[17]后现代主义者巴恩斯则说:“对反讽的热爱是关于福楼拜的最现代的事件之一。”[18]
具体而言,传统反讽文字表达常与意义不符,但读者仍可从中获得终极意义。而哈桑解释后现代主义“非人化”中“反讽”义项时说:“反讽成为根本的、自我毁灭性的表演,意义的熵状态,以及荒诞喜剧,黑色幽默,疯狂戏拟和滑稽戏,粗俗的否定。”[19]认为反讽为未完成性的狡猾暗示,即无终极意义。
福楼拜作品多以反讽保持其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布瓦尔和佩库歇》即一部充满反讽意味之作。罗兰·巴特曾评价:“反讽的不确定性是福楼拜作品尤其是《布瓦尔和佩库歇》的一个标志。”[5]他认为,《布瓦尔和佩库歇》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空洞、重复、无深度主题。充斥“说教的、政治的群体语言,从未顾及其说话内容的重复”,其中的“文化谚语”“科学俗语”腐烂、陈旧、令人作呕,使人无法卒读,而“反讽几乎消除不了这种定型构建的范围,因为反讽是……将某种新符码添加到他想驱除的符码、定型上去……作者对付层出不穷的定型仅有的本领就是不带引号地进入到文化符码这种定型中去,把文本生产出来。”[5]
《布瓦尔和佩库歇》贡献在于其进入定型化的文化符码中,展示写作功能,消解此语言控制彼语言的力量(威胁),释言之言(即关于语言的语言,或元语言——引者)一旦形成,即将其消解,同时作者语言也与各定型化语言混同,显示出荒唐可笑的状貌[5]。现代文化颇具融合世俗语言、人物语言和作者语言特点之能,《布瓦尔和佩库歇》无疑为文化的同化物,其缺乏中心、本源,是一种复制的复制,而非某种创造性来源。此为“捣乱性叙事作品的技巧”,或“向文学和社会成规挑战的技巧”。
福楼拜对此陈词滥调态度既含糊不清,又饱含揶揄。此“既是反讽的魅力,也是反讽的危险:它似乎允许作家从作品中隐退,但实际上仍然暗示了他的存在。”[18]因此人们无从得知谁在控制语言。反讽亦破坏文字表达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将现代主义主题表演推向自我毁灭,与意义的毁灭结合,达到意义缺失或不确定。
五、结论
总之,福楼拜取消形式和内容间等级秩序,提高了形式的地位,使形式对意义产生一定消解作用,启示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和“作家——艺匠”式写作;同时福楼拜个体特点对作品影响与罗兰·巴特“写作风格先天性”观点多有契合;此外,抛离作者主观因素(福楼拜卒于罗兰·巴特出生前,无法借鉴其理论),福楼拜在作品内容和形式上采用的戏拟体现了罗兰·巴特“文本模仿性”理论,其文本的主观意义通过反讽等手法得以消解,恰好印证罗兰·巴特“无意义的终极意义”理论,二人诸如此类的契合还有很多。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桥梁”人物福楼拜,将其作品隐去“作者——叙述者”、强调形式、消解意义,以及运用戏拟和反讽手法等,均为现代小说理论提供重要范例,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罗兰·巴特,而罗兰·巴特文学理论亦可为解读福楼拜作品提供新视角。
[1]杨扬,蒋瑞华.从作品到文本[J].文艺理论研究,1988(5).
[2]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李幼蒸,译.符号学历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Steegmuller,Francis.The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1830-1857 [M].Cambridge:The Ber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5]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福楼拜.福楼拜文学书简[M]//刘方,译.福楼拜小说全集:三故事,布瓦尔和佩库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Erich Auerbach.Madame Bovary[M]//Raymond Giraud.Flaubert: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Hall, 1964.
[8]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符号学历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0]福楼拜.布瓦尔和佩库歇[M]//刘方,译.福楼拜小说全集:三故事,布瓦尔和佩库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1]格兰特.现实主义[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12]欧·豪.现代主义的概念.刘长缨,译.[M]//袁可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3]李健吾.福楼拜评传[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4]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5]Felman S.Modernity of the Commonplace[M]//Laurence M.Porter. Critical Essays on Gustave Flaubert.Boston:G K Hall,1986.
[16]Roland Barthes.Lesson in Writing[M].//Stephen Heath.Image Music Text.Waukegan:Fontana Press,1977.
[17]Culler J.The Uses of Madame Bovary[J].Diacritics,1981(3).
[18]Julian B.Flaubert’s Parrot[M].London:Jonathan Cape,1984.
[19]Ihab Habib Hassan.POST Modern ISM:A Practical Biography [M]//Ihab Habi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
I106
A
1672-3805(2017)01-0058-07
:2016-11-20
魏琛琳(1992-),女,香港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化身份、古典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