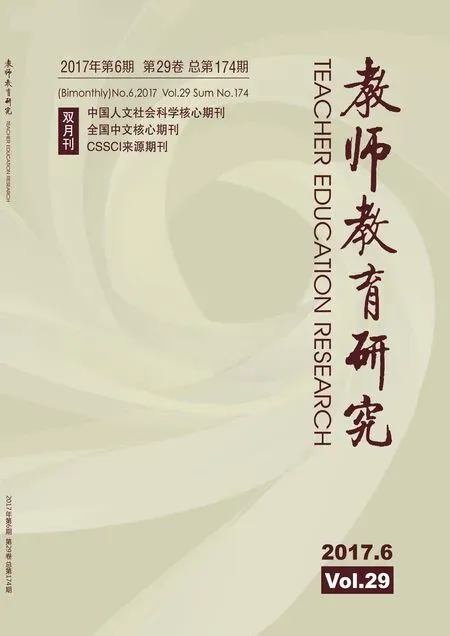论学生课堂教学参与中教师的话语能力
——基于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理论的探析
王 珊,吴 娱
(1.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与心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学生课堂教学参与能有效地保障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多数教师在其课堂教学中都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促进学生的参与。但无论何种教学措施,其实施都以语言或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为载体,因而教师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学生课堂教学参与的质量。教师的话语能力并非简单地指教师的教学语言技能。在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视域下,教师的话语能力不仅是看教师能否进行合乎语法规则的表达,它更是指教师对课堂话语社会建构性的洞察能力、对结构性话语的自反性思考能力*自反性思考能力是指教师能在教学实践中洞悉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能对沉淀于自身话语背后的那些业已成习的观念信仰系统进行批判性地审视和反思的能力。布迪厄指出,反思就是对理论、知识自身的自反性思考,是反过来思考言说者自己以及言说思考者自己(《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华康德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38-44)。自反性思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它意味着分析者将他的分析工具转而针对自身。教师对话语结构的自反性思考意味着教师能够将自身话语作为反思和批判对象,这是一种类似“自我清理”的工作,它把分析的矛头指向话语生产者自己及其所在的社会关系。、策略性地改变话语规则体系以重建课堂话语秩序及其权力关系的能力。由于在日常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洞悉话语背后隐性的权力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因而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行为出现不同程度的机械化或形式化倾向。因此,基于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理论探析学生课堂教学参与中教师的话语能力,意在唤醒教师调控自身话语规则体系的自觉性,促进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话语能力以实现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实质性参与。
一、学生课堂教学参与中教师的话语能力缘何重要
自从上世纪70年代起,课堂讨论作为学生课堂教学参与的重要形式受到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者(Mulryan,1995;[1]Fassinger,1995;[2]Dallimore et al., 2004[3])在研究课堂中的提问、质疑、讨论等言语活动以及做笔记、倾听后的肢体反应等非言语活动后指出,学习投入程度较高的任务专注型参与中教师的言语鼓励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后,Fredricks等人的研究也指出,“教师支持”是影响学生课堂教学参与的重要因素。[4]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开展了针对我国中小学课堂参与的实证研究。吴康宁等以教师课堂言语行为为“观察窗口”,指出“定向者”角色是我国中小学课堂中教师扮演的主要角色。作为“定向者”的教师往往采用“提问”的方式来控制课堂,“强制”或引导学生的课堂参与。[5]这类研究揭示出在我国的中小学课堂中,教师对课堂教学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学生参与流于形式的问题十分突出。本世纪初曾琦团队的调查研究也显示,我国中小学课堂中学生的参与“仅仅是教师组织教学的手段”,学生在参与过程中“更多是对教师意志的服从”。[6]
学生课堂教学参与是主体性参与,这早已成为教育界人士广泛共识。课堂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教师主导下由学生以主体身份参与的一种特殊认识过程。学生作为课堂教学中学的主体,其存在的意义指向课堂教学目的层面;教师作为教的主体,其存在意义指向教学服务的层面。正因如此,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地位虽是参与性的,但却是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无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处于何种主导地位,都不能忽视学生作为参与教学过程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人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和实质。否则,课堂教学中的学生参与要么被教师限定在特定的活动中,沦为迎合教学上外部需求的形式;要么在教师垄断性的话语中被置空,学生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几乎很难被他们自己所知,导致学习主体被客体化。
学生课堂教学参与形式化倾向的出现并非教师所愿,绝大多数教师采取各种措施激发学生的课堂教学参与正是为了实现学生“学”的主体性。为何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上述结果与目的的背离、实践与认识的偏差?原因虽然很多也很复杂,但教师是否具备一定的话语能力是其中关键的因素。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过程是在教师话语主导下学生学习的投入过程,教师的话语能力在根本上影响着学生实质性参与的实现程度。教师能否理解意义生产的社会性,是否能够自觉地把握话语规则体系的形成及变化过程并使其服务于教育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堂知识的建构方向以及学生学习意义空间的营造。[7]若教师缺乏文化视野及批判心灵,则难以通过抗拒既有文本的方式重建课堂合理的话语秩序,从而导致教师优势话语垄断课堂、学生参与流于形式。所以,教师是否具备一定的话语能力对于实现学生的实质性参与至关重要。
二、学生课堂教学参与中教师的话语能力要素
批判话语分析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不以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功能为研究目标,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剖析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8]费尔克拉夫是当代批判话语分析的杰出代表,他创建了通过分析话语形式来研究语言、权力及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动态辩证关系,社会结构既是话语实践的条件,又是话语实践的一个结果。[9]话语一方面建构了社会事实,而另一方面这些被话语建构的社会事实在制度化、习俗化的过程中又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成为规制话语实践的结构性力量。这种辩证的话语观提升了语言反思理论的实践范式,它要求主体对自身在知识引领的话语斗争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不时作出反省,以免陷入意识形态的漩涡。基于费尔克拉夫“结构—建构”的话语观,教师的话语能力首先要求教师对自身话语保持警觉,能够在批判的文化视野下审视话语背后的知识信仰体系,发觉那些业以成习的观念系统对课堂权力关系的影响和规制,也才可能实现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实质性参与。
费尔克拉夫不仅创建了这样一套关于话语的社会理论,更提供了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话语批判技术,从而为课堂教学中教师改变自身话语规则体系以保持自身话语的可协商性提供了实现路径。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三维批判话语分析模式在语言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桥梁,将社会性的关联和文本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对文本的语言学进行分析,对文本与话语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对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通过分析话语秩序与文本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发现文本的形式特征在各种层面上如何获得意识形态方面的介入,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同时,这种社会取向的话语分析方法本身也孕育着某种改变既定权力格局的潜在力量。因而批判话语分析技术的引入也就意味着教师能够通过改变话语规则体系来实现对自身话语的控制,从而避免教师话语异化为霸权话语以致学生参与流于形式。所以,批判话语觉醒意识和话语控制能力是学生课堂教学参与中教师话语能力的两大基本要素。
(一)批判话语的觉醒意识
批判话语的觉醒意识即教师能自觉审视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观念信仰体系的意识,它是教师对话语结构性力量的批判反思意识以及反操纵的敏感性。费尔克拉夫在批判传统语言学将语言“形式”与“意义”二分对立的基础上,借鉴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主张语言形式必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他指出语言只是话语的外在形式,沉淀于社会结构中基本的认知信仰系统才是话语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意识形态决定着语言再现形式的选择。基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费尔克拉夫认为意识形态被建构到话语实践形式或意义的各种维度中,并致力于统治关系的生产、再生产或改变。[10]
尽管费尔克拉夫认识到意识形态在文化心理上对人的操纵和控制,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结构化的思维低估了主体的能动性。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费尔克拉夫采纳了福柯早期研究中对话语建构性的强调,即话语建构社会,包括建构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但费尔克拉夫始终坚持一种折中的立场,他一方面批判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带有太过浓厚的结构决定论色彩,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作为外在强制性结构对话语固化的认知;另一方面,他对福柯关于话语建构社会事实的态度持保留意见,认为话语世界与非话语世界处于辩证的关系中,它们不断内化对方但却不能完全消解对方。正是基于这种“结构—建构”的辩证话语观,批判话语分析引入教师话语能力研究具有了更深层次的解放旨趣。
在批判话语分析的视域下,课堂不再是一个物理属性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场所”或“政治空间”,课堂中弥漫着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权力与支配关系。例如,教师常常借助组织职位赋予的权威来强化自己作为合法性解释者的身份和地位,渲染出教师话语的一般性甚至是普适性。有些教师习惯用“老师认为……”而不是用去身份属性的“我认为……”这样的语言表达,无意中强化学生对教师权威身份的认同,塑造出教师话语更具合法性的“误识”。教师还经常通过提问、评论以及对话语的控制来掌控课堂知识的建构方向,形成课堂中立即、封闭和单向的话语模式。如要求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教师提问作出反应,问题的答案不仅被窄化为“是与不是”的二分式选择,更将学术形态知识视为评价的唯一合法性标准。话语模式是人们不自觉的、想当然的关于世界运作的方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11]上述课堂话语模式一旦形成,其在实质上已经成为规制性的结构力量,它使师生对话被限定在封闭性的意义结构中。
因此,教师必须对自身话语保持警觉,才可能发现隐藏在话语背后的诸如师道尊严、师尊生卑等陋习俗念;也才能发觉社会功利取向的意识形态如何主导教师习得的话语形式,进而使他们不自觉地以学术形态知识体系去定位学生未来的社会位置。依据批判话语分析所给予的话语秩序生产图式,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它生成于无形历史赋予的语境结构中。一旦话语主体进入这种话语秩序,他们便会不自觉地选择、遵循和利用这种话语秩序的规则来交往。由于教师自身就是教育话语的重要载体和主要生产者,任何僵化的意识形态和霸权话语都会给学生实质性参与课堂教学带来威胁。所以,教师批判话语的觉醒意识意味着教师能意识到话语本身是习俗规范及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反映,进而能不断提醒自己在教学中保持自身话语的可批判性;它还意味着话语主体具有反思、抵抗和改造结构的潜力,即教师能够借助话语分析发现“结构之洞”,进而积极采取行动以扭转课堂权力格局、促进学生实质性参与。
(二)话语控制能力
教师的话语控制能力即教师有意识地改变话语规则体系以构建师生间合理交往关系和课堂权力秩序的能力。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秩序由语体、话语实践和风格构成,它们分别关涉“交往方式”、“表征方式”和“存在方式”。[12]语体建构社会“关系”,话语角度建构“观念”,风格建构“身份”。教师选择何种语体、从何种话语角度阐释、其话语又有何种风格偏好等,都将影响课堂中师生沟通的意愿、学生知识和观念系统建构的方向以及师生对课堂中双方身份地位的认知。例如,在今天的课堂中有太多的教师话语以“霸权”的方式过滤掉了实质性对话中应有的课堂“沉默”、排挤掉了学生学习意义发生的真实空间。在热闹激烈的课堂讨论后,全班几十个不同的脑袋竟然只剩下同一种认同;在那些经过教研团队反复“打磨”的课堂上,师生间的对话精致得几乎没有一丝“留白”。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过,“凡可说的都能说清楚”,“不可言说的必须付诸沉默”。[13]但是在教师话语霸权的控制下,“师问生答”的形式对话替代了酝酿高层次认知参与的意义协商,那些学生参与过程中本应有的因疑生困、再由困顿而缄默的情境自然不见影踪。
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霸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它通过对思想的控制和影响来实现基于妥协和自愿结盟的支配关系。[14]话语霸权并不以强制性力量去实现其统治效果,它往往通过“虚假认识”以自然而然的常识形态建构权力关系。批判话语分析技术为教师话语摆脱霸权意识指明了道路。教师可以通过改变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等话语要素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组合方式来实现对自身话语的控制。因而教师的话语控制能力一方面指教师能基于教育情境创造性地改变各话语要素的表现形式以促进学生实质性参与的能力。例如,语体可以是独白或对话,但课堂对话不仅仅指面对面的口头会话,还泛指具有实质意义上相互介入的符号表征。在笔者观察过的课堂中,某小学语文特级教师就是通过改变对话的表现形式,建构了课堂自由民主的话语秩序。上课伊始,这位教师只要求学生用不同的手势对别人的观点表示同意、不同意或不置可否。随着课堂民主参与氛围逐渐建立,该教师要求学生不再使用手势表达而是必须用语言来说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该教师正是通过改变话语要素的表现形式将“发声”的权利和意义诠释的空间还给了学生,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学生的实质性参与。
另一方面,教师对话语的控制能力还体现在他们对不同话语要素的搭配上。语体、话语角度和风格之间的不同组合方式直接影响着教师话语的可对话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实质性参与的实现程度。例如,在独白式的讲授中,教师对阐述的内容是深描还是淡写?又如,对同一内容的讲解,教师选取不同的话语角度又将在何种意义上影响课堂知识的建构方向?再如,即使是在独白式的讲授这种语体中,教师的话语风格是偏向主观感受还是凸显客观事实?是偏好断言式的表达还是使用诸如“或许”、“可能”等情态副词以削弱自身话语的权威性?这些话语要素的不同组合和搭配都将影响师生间交往的意愿以及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大小。
三、提高教师话语能力以实现学生实质性参与的建议
(一)拓展教师文化批判视野以唤起话语批判意识的觉醒
教师对课堂话语的自觉控制始于其批判话语意识的觉醒。只有积极促进教师批判话语意识的觉醒,他们对课堂教学语言的认识才能超越教学技能的层面,而深入到对话语“生产性”和“互文性”的认识。批判话语理论为教师认识语言形式之外的社会意义生产功能提供了文化的视野。费尔克拉夫在其批判话语理论体系中明确指出,话语实践在对文本进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同时,也赋予了文本解释以特殊意义的社会认识。[15]所以,任何话语实践都是将他者的“声音”编制在自己的意义表达中,任何话语形式都有一定的意义诉求,都是在精心运作的“结构”或“解构”过程中以话语蕴藉的方法和策略潜藏着某种特定意义和规范。课堂话语也是这样无数条意义相互编织的“互文链”。因而加强教师对批判话语理论的学习、深化教师对语言“形式—功能”的理解,他们才能对课程话语/文本进行自主批判性解读,并进一步洞察封闭性意义结构的生产路径。
因此,在各级各类的教师培训中,我们不应仅仅为教师提供语言知识的学习或沟通技能的训练,更应为他们提供较为系统的话语理论学习。正如费尔克拉夫指出,话语知识已经成为社会斗争中人们争相谋求的资源。[16]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指出,批判话语分析的应用能促进教师对课堂教育实践的反思和追问。[17]在批判话语的理论视野中探讨教师发展的问题,将更有利于发掘遏制教师发展的语言根源。[18]所以,拓展教师的文化批判视野能够促进教师主动审视日常教育行为,发觉“教育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观念系统。具有批判心灵的教师也会自觉地将各类课程材料、教师话语和学生话语视为教育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批判性分析自觉降低教学中自身意义表达的权威性和排他性,为学生实质性参与课堂教学提供更多机会。
(二)在实现课堂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中提升教师话语控制能力
话语能力是关于语言实际运用的能力,它包含着对具体教育语境及其交际情境的洞察,因而教师话语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大量的课堂对话实践。但这种对话必须是具有实质意义介入的对话,即它不是教师话语霸权控制下的问答行为,而是学习共同体以探究真理为旨趣的平等交流、合理质疑、批判性思考和意义达成与共享的过程。批判社会学派代表哈贝马斯曾提出一种“理想言语情境”,即一种自由透明的交往条件。[19]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免于受压制和免除不平等的“理想言语情境”中,以沟通为目的的对话才可能实现。而这个过程恰恰又是在不完满的交往中,不断追求完满交往条件得以实现的过程。同样,在课堂教学中要实现师生间以沟通为目的的对话,也必须改变教师优势话语权对课堂的控制,破除不平等的话语秩序对对话中实质意义介入的干扰。所以课堂实质性对话的实现过程,也是教师不断调整话语要素的表达和组合形式以使课堂言说情境逐渐逼近完满和理想状态的过程。在这个教师话语不断“袪魅”的过程中,教师的话语控制能力也得到磨练和提升。
当然,要实现课堂中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还需要学校管理者、教育研究者、教师以及学生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学校管理者应有意识地加强同大学等学术组织的合作,创造各种机会促进中小学教师同教育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帮助教师开展更多的有关教师话语的行动研究。这种行动研究可有效提高教师对课堂话语实践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以及批判反思力,从而提高教师对话语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话语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学生语言能力的提升。因而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设计开放性的对话情境使学生经历探索和发表活动,并在此过程中扩张学生抽象词汇的数量,使他们精通抽象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和事物的原理法则。伴随学生语言组织能力的提升,师生对话中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惊喜”和“意外”,这样更能激发教师改变话语规则体系以促进学生的参与。当然,具有实质意义的对话不仅是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也包括教师基于自反性思考的自我内对话。这种自我内对话促使教师批判性地思考教学中琐碎的语言细节,努力去发掘这些语言形式背后到底具有何种价值、如何被赋予了何种意义,而自己又该如何改变话语要素的表现形式以重构合理的话语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话语控制能力将得到不断提高。
[1]MulryanCM.Fifth and sixth grader’s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ve small groups in mathematics [J].TheElementarySchoolJournal,1995(95):297-310.
[2]FassingerP A.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why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class [J].TeachingSociology, 1995(24):25-33.
[3]Dallimore E J., Julie H H., Marjorie B P.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nd Discussion Effectiveness:Student-Generated Strategies [J].CommunicationEducation, 2004,53(1):103-115.
[4]Jennifer A. Fredricks,Phyllis C. Blumenfeld, Alison H. ParisAlison H. Paris. 2004. School Engagement: Potential of the Concept, State of the Evidence[J].ReviewofEducationalResearch, 2004, 74(1): 59-109.
[5]吴康宁,程晓樵,吴永军,刘云杉.教师课堂角色类型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4):1-8.
[6]曾琦.学生课堂参与现状分析及教育对策——对学生主体参与观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8):42-45.
[7]王熙.试论价值教育中教师的话语能力[J].全球教育展望,2014(9):59-67.
[8]Chouliaraki,L.,N.Fairclough.DiscourseinLateModernity[M].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1-2.
[9][10][14][15]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9,81,85-86,74.
[11]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72.
[12]Norman Fairclough. Semiotic Aspec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Learning[A]. Rebecca Rogers.AnIntroductionto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inEducation[C].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2011:119.
[13]陈嘉映.维特根斯坦读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53.
[16]Norman Fairclough. Technologisation of Discourse[A]. R.Caldas-Coulthard, M. Coulthard.TextsandPractices:Readingsi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C]. London: Routledge, 1996:49-56.
[17]王攀峰.批判性话语分析:当代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81-86.
[18]胡云飞.教师发展路向的批判话语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5(4):70-73.
[19]Jürgen Habermas.MoralconsciousnessandCommunicativeActio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