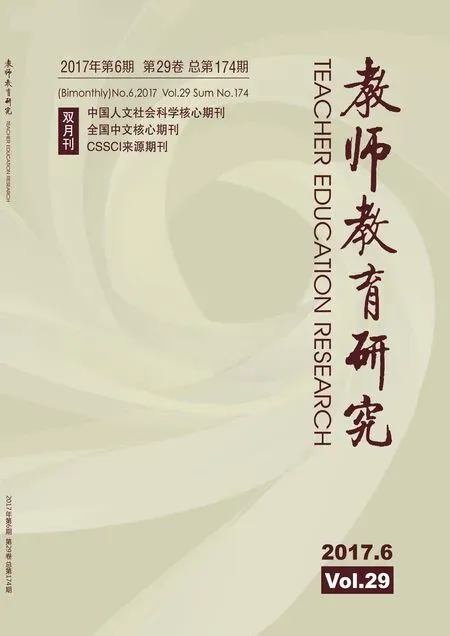教师生命理想的缺失与重建
王红霞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一、教师生命理想的意蕴
教师首先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生命的存在。生命本质是一种精神性存在,理想是精神成长的驱动力。教师其次作为一种社会角色而存在,教师角色的最大价值在于“生命的示范性”。两种“存在”天然地要求教师将职业活动看作生命成长和价值实现的手段,以生命主体的自我完善去引导学生生命的发展。
(一)生命的意义在于理想
诚如冯友兰所说:“意义发生于自觉及了解。任何事物,如果我们对它能够了解,便有意义;否则便无意义。了解越多,越有意义,了解得少,便没有多大的意义。”[1]同样的,假如我们能够了解生命,生命便有意义,倘使我们不能了解生命,人生和生命便无意义。人的生命有生理生命和精神生命,相比生理意义上的生命体,对于人来说,更为本质的是精神上的生命体。人对生命的精神性了解多少、认识多少,人的生命就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义。精神生命包括认知和情感层面、道德和意识层面、审美和理想信念层面等精神性要素,理想和信念是这一切精神性要素成长的驱动力,当有了理想信念,精神的其他层次会在它驱动下往前生长,人的精神生命就此展开。所以人生的意义在于理想、在于一种精神上的追求。不同的人,人生理想不一样,对人生的觉解也不一样,也就有着不同的人生意义与人生境界。
(二)赋予学生生命理想是教育工作的应有之义
人既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也生活在意义世界中,教育既要教人怎样生存即如何在物质世界中提升生理生命的质量,又要教人为何而生存即如何在意义世界中提升精神生命的质量。这样的教育才能让人过上完整而幸福的生活,这样的人性才是完善的。教育既以完整生命、完善人性为己职,就决不可忽视人的意义世界的建构,忽视对学生进行生命理想的启迪。
生命理想兼具时代性与个体性。“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每个时代的教育都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都需要确立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生命理想”。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和不同的思考方式,就形成了不同时代的教育理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子”是理想的生命标杆。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命理想就是拥有生命自觉的生命,它也因此成为我们时代的教育理想。“怎样的人生是值得过的?”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学习和接受教育才能真正建构起自己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所表征的并非是人的“是其所是”,而是“应其所是”。人要用意义世界去引导、规约人的物质世界,使一切物质世界的发展都能具有人独有的意义,归属于人的意义世界。
(三)教师是传递生命理想的人
教师是学生精神生命的塑造者,也是自身精神生命的创造者。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教师,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指出“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2]所谓的智慧在中国文化里更多地指“想明白人生的根本道理、把握人生的能力”,在西方文化里更多地指“想明白世界的根本道理、把握世界的能力”,虽然中西方文化的侧重点不同,但综合起来,智慧就是想明白人生和世界的根本道理、把握人生和世界的能力。也就是在认识层面,教师是对生命的理想、人生的意义有充分的了解并达成自觉的人。在实践层面,教师是学生生命的榜样,他们致力于以生命实践影响学生、帮助学生掌握生存的知能、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引导学生逐步树立生命理想。如前所述,我们这个时代教师要传递的生命理想是拥有“生命自觉”的生命,生命自觉之人是拥有自我生命自觉的人、拥有对他人生命自觉的人、拥有对外在生境自觉的人、能够自觉将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生境沟通转化的人。[3]
二、教师生命理想的缺失
生命理想是对生命的一种内在目的和意义的寻求。现代人生活在由资本和技术构成的文明中,借助于技术,资本向外生长的本质将现代人的生活规定为不停地向外追逐,没有时间向内思考怎样的人生值得过。于是人类的物质世界越来越丰富、精神与意义世界越来越退化到边缘地位。生命理想缺失是现代人共同遭遇的困境。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就像诺瓦里斯所说,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中国现代化付出的代价之一是人们摆脱了物质上的普遍贫困,换来了精神上的普遍不安宁。教师群体也不能幸免。教师生命理想的缺失集中表现为:一没有德性,二没有创造性。
(一)德性缺失
德性有两层内涵,本体论意义上的德性是指万事万物的本源,包含着生命力、并依靠自身力量生成和发展,是道德和智慧的辩证统一。伦理学意义上的德性是指人为了追求善的生活而培植的自我内在品格和道德。我们在伦理学意义上来讨论教师德性,它是教师个体为实现“好的教育生活”、获得“生命价值实现”而不断完善自身生命的内在道德标尺,是教师生命存在和主体性发展的确证。
1.强调外在规范抑制了教师德性生长
专业化框架下的师德强调教师的职业伦理或道德。它是教师集体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是一种规则伦理或手册伦理,多以规范的形式存在。爱岗、敬业、勤恳、团结、专心致志、遵守准则等成了伟大的道德,它们成为教师日常行为的规范与规则的同时解除了教师内在的力量、驱除了内在的审判。职业伦理使教师产生了道德盲视,无法意识到更普遍的人类德性,使他们将遵守外在规范、规则,进行重复性的劳动视为有道德。职业伦理使教师的主体性得以遮蔽,教师不再关心“什么是好的(和坏的)品行”、而是关心“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行为”;教师不再思考“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思考“我应该做什么”。
对职业伦理的强调抑制了教师德性的生长。教师德性主要包括:(1)教师关怀。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师爱,教师关怀凭借榜样的力量。教师首先是自我生命的关怀者和守望者,其次要关怀和守望学生生命和精神成长。(2)教师公正。是指教师要承认每个学生生命的独特性、尊重并宽容每个生命的差异性、给予每个学生应该得到的合理需要和合理评价。教师公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主体性。(3)教师责任感。责任感可以使教师的主体性得以真正完善,主体性或德性的发展是实践的,具备责任感的教师才可能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教育实践中发展自我、成就学生。缺乏责任感的主体必然表现出任性与盲目。
2.不追求生命的卓越发展
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获得外在利益,比如荣誉或金钱,也可以获得两种内在利益:一种是实践本身的成果即学生的卓越;一种是实践者本人内心的充实,进而找到教育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外在利益获得的条件是教师具备从业资格和专业知能,内在利益的获得必须以具备德性品质为前提,“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由于教师“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具体表现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教师主体性参与不足,使得教师难以关注自我生命的内在丰富与超越、也无法追求学生生命的卓越成长,教师的人性光辉、人格魅力淡出了教育生活。在我国中小学教师中,普遍存在着“自我消耗式”的“奉献”,教师在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以后,发现自己最后剩下的仅仅是所教授学科的知识点。
(二)创造性不足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主张:“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是教师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关怀学生生命的一种事业。不同于科学创造,教师创造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教师创造指向完整的人和完整的生命,更主要的是推动学生自主发展、自我创造,因为“独立地创造”正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方式。现今教师创造不足复制有余。
1.教师创造的内在动力不足
创造是教师内在尊严与欢乐的源泉、是教师生命价值实现的过程。德性是教师创造的内在动力,有德性的教师才会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每一个可能性抱有巨大的教育热情,教师德性的自我实现即是教师创造。德性缺失的情况下,教师成为了谋生的职业,职业驱除了“我”的用力,教育变成“无我”的工作。教师不再追问“我”的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同时,也会忘记、忽视或抹杀学生的生命性,真实的人的教育不见了。而对“人”、对“生命”的认识与关怀,以及由此形成的教学观、人才观、成才观才是决定教师能否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开展创造性教育行为的关键因素。
2.无思与平庸之恶进一步限制了教师的创造
现代正规的学校教育制度总体上以科学活动方式为参照,追求客观化、标准化、齐一化,教师在课程设置、课程与教学设计、实施与教学评价上少有自由空间,升学竞争、标准化考试、无个性特色要求的教学评估以及由市场和商品化催生出来的教学参考书、教师手册等,都使教师很容易成为制度和市场的奴隶。
德性驱除时,教师被简化为“实践工作者”,服从和遵守已有的制度设计成为高效实践的首要原则。教师进入一个普遍的“无思”状态,正如苏格拉底曾说:“谁力所不及,谁不想思考,谁就去行动。”“无思”产生的平庸之恶不仅限制了教师的创造,还可能将教师置身于可怕的险境。
三、教师生命理想缺失的原因
我们着重从历史传统、教师职业专业化的要求、教师生存的现实环境等多方面分析教师生命理想缺失的原因。
(一)受历史传统和文化影响,教师主体意识不足
1.人的精神价值在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得不到承认
生命理想是基于人对生命的自我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信念和美好追求,它属于人的精神层面,举凡精神的东西只能为精神的主体所拥有。而精神是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是自我意识。诚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没有办法申诉自由,因其没有自我意识,并不是精神的主体。人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神圣的价值,具有实用品格的中国文化不重视精神价值,这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最缺少的是形而上学和个人主义,缺少了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4]中国儒家倡导“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并未得到发扬,想反,“能近取譬”[5]被归结成了孝道,由“孝”及“忠”,刑成了三纲五常一整套等级伦理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我们看不到个体生命的地位。
相对于主体意识即自我意识不足,也就是精神性不强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国人来说,也就很少自觉到生命理想的存在与意义或价值了。
2.重视教师职业工具价值的历史传统,使得教师的自我意识未广泛觉醒
几千年来,对教师职业价值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社会功能上,“尊师”是为了“重道”和重“教化”。先秦儒家中,荀子是明确提出“尊师”之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教育具有教化人的作用,强调:“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6]《学记》则进一步提出“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7]把能否当好教师与仕途直接联系起来。法家所说的“法”与“吏”大不同于儒家的“道”和“师”,但两家关于教育者在治国、重道、教化、强法中的工具价值的认同却是一致的。随后几千年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教师的职业工具价值并无大变。“废科举,兴学校”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组织上的“官”与“师”的分离,对于教师群体职业意识的独立性和民主意识的产生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近代社会的教师职业价值依然主要强调其对于社会的工具价值,只是这种工具价值由古代的“传道”变为近代的“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以及富国强民的技术”。教师职业的内在价值问题并未被尖锐地提出和进行过认真探讨,教师群体的职业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广泛觉醒。作为历史的传统,它依然以当代的形式和内容存活在今日的中国。[8]
(二)教师专业化带来教师信仰的失落与教育意义的消解
现代社会解构了教师信仰,职业化、专业化表达了工具主义的要求并成为教师的迷信。学校教育中的劳动分工使单个的人无法把握整体的意义。
1. 教师从信仰者发展为专业者,带来的是教师信仰的失落
教师专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道德的发展,即让一个教师懂得如何专业性地教学,更为根本的是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教师自我认同。教师专业化不仅影响教师“如何去做”(how to)的行为方式,更为重要的是影响或决定教师对“为了什么”(what for)而做的回答。
无论从发生学还是从词源学上,我们都不难看出,古典时期的西方教师是作为一种神圣性的行为的信仰承诺,它是一个使命、诫命。教师以对正义、真知的寻求与探问、对自我与他人成长的理性关注以及对精神自由的守护为无条件志向。中国历史上的教师则以“传道”作为最为根本的价值诉求。历史地看,中西方社会中的教师是“为了追求正义和真理”“为了传递社会的核心价值”,他们是社会的精神脊梁、是理想的生命标杆。伴随着现代观念的发展,教师的使命感和神圣追求失魅了。现代精神认为人并不具有追求真理、正义的自然需要,对于人而言,重要的是根据现实安排好生活。“自我保全”成为现代人所有行为的根源,经济、文化、道德和教育的建构皆产生于或围绕于“自我保全”的要求。为了“自我保全”,人类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大胆征服和改造自然,教育问题变成了如何高效益地为工厂提供劳动力。肇始于工业工厂的专业化就是为了实现最大效益,对高效益的教学追求使得教师专业化成为教师发展的典范。“为了自我保全”、“为了生产”僭越于“为了追求正义和真理”之上时,作为谋生或获利的教师意识就诞生了,教师从古代信仰的代言人变为现代一种职业。
2.学校教育中的劳动分工进一步消解了单个教师的教育意义
专业化是劳动分工的需要,教师专业化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学校教育中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带来的是空间碎片化,这种碎片化正以几何级数加速繁殖。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即使是生产一根缝衣服的针,都需要非常复杂的劳动分工。”因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空间的进步巨大,但人们不再去思考“个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时间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科技的进步、现代性的发端、现代启蒙运动等,但还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分工。也就是说,劳动分工带来对劳动意义的消解,北京大学格非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对时间的沉思,空间不过是绚丽的荒芜。”
学生的生命成长是整体性的,每个阶段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每一项工作都对学生成长可能具有意义。今天学校教育的劳动分工,使得教育一个人的完整行为在教师身上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存在,教师成了“单科教师”、“各科教师”、“阶段教师”。单个教师看不到学生成长的整体,看不到自己的工作在学生生命成长中的整体意义。他们知道所有的教师共同完成了一个人的教育,但他们彼此之间又毫不了解,因为“我”只知道自己服务于一个自己毫不知晓的行为。马克思认为:“分工使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9]在学校,学生被抽象化为教育流水生产线上的产品,教师被抽象化为生产流水线上主管不同工序的工人,学校则成为生产某种产品的企业。
(三)受功利主义影响,教师成为了“只见事实的人”
当下学校教育中功利主义无处不在,和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一样,功利主义也建立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胡塞尔曾深刻地揭示过现代科学的特征,他指出:“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10]因此,建立在现代实证科学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做”的哲学,其信条是效益最大化,它排除了对目的自身的追问,结果往往为了效率、效益而忽视人性、损坏精神。功利主义用数据和事实来标识效益,比如学生的分数、优秀率、录取率、各种比赛的证书等,凡是数据能标识的才是学校最为关心的,教师用功利取代了对崇高、神圣的信仰。事实上,教育中最重要的恰恰无法用数据和事实加以标识,比如学生的内在生命的生长:自我意识的增强、情感的丰富、思维的发展、德性的完善、理想与信念的确立。功利主义下的学校和教师“只见事实”、“不见学生”。
四、重建教师生命理想的思考
生命理想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对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一种回归。我们尝试着在教师的教育生活中讨论教师生命理想重建或培育的一般性策略。
(一)改变教师在校生存方式,促进教师主体性回归
“人的存在有别于并优越于动物的生存之处,根本上在于它赋有意义并追求意义。”但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又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而是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进行价值创造和意义生成。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然状态是充满创造性的。生命理想缺失是教师生存方式的异化。文化与教育传统抑制了教师主体性生长、基于工具理性主义的教师专业发展消解了教师的文化身份(使命感)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遮蔽了教师的生命理想,造成现代教师学校生存方式之主要问题是被动生存、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追寻价值与意义。
为重建教师的生命理想,必须以教师的生命发展价值取向为基点,改变教师生存方式,促使教师的主体性回归。这一改变的实践突破,集中表现在教师应“以培育学生的生命自觉作为核心目标”去进行教学研究与实践、发挥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唯有在此活动领域中有了转型性变化,唯有教师自身的职业生命状态因创造而焕发出活力,教师日常生活状态才会有根本的改变。教师研究旨在改变教师仅仅作为人类文明和知识传递的执行者、规定的学科教学的被动执行者,赋予教师自我发展的机会,倡导教师成为自己生命价值的创造者和自己生存意义的守护者。当教师以研究者进入教育世界,教育世界就成了教师认识和改造的世界、成为了客体,教师就成了教育世界的主体。作为教育生活的主体,认识教育生活的意义、改进和创造教育生活便成为主体的内在需要。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是教师创造自我独立个性和生命价值的一种高级形式。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就是研究怎样使每项教学活动都有教育的意义,怎样在学生身上实现教育的意义。当今学校教育实践中,教师要改变劳动分工带来的教育意义的消解,一条最为基本的改变渠道是,通过教学研究深度开发不同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使“教”与“育”在学科教学中真正得到融通,使教育的融通渗透到学校每节课的日常教学之中。
(二)重视教师个人化哲学观的形成,使教师成为“教育生活的定义者”
教师专业化这一转型的现代性后果是:教育生活中的教师“无信仰”、“无思”、“无抵制”、自我遗忘与制造由此而产生的“恶行”。因此,专业化语境下培育教师生命理想,必须使教师成为思考的力量、成为教育生活世界的核心。从理论上来说,生活世界就是人的世界,是属于人、为了人并由人加以解释、建构、体验和改造。[11]生活世界之可能在于主观意向和主观视界的存在。主观意向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意志自由,主观视界的存在依赖于独特的认识框架。因此,要使教师成为生活世界的主人,必须重视培养教师的自由意志和独特的认识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帮助教师形成个人化的哲学观。
正如乔治·F·奈勒在《教育哲学》导论中所说“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的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有哲学观的教师才会有理想追求和信念、有行为方向与准则、有认识与行为的特定思维逻辑,他在教育实践中所产生的能量是“行为式的”,这种“行为”表达着思考和追求,要求思考自身的行为是否服务于或有益于自己的教育信仰。它不仅追问“how to”,而且追问“what for”,这个行为本身能够产生“抵制”“不服从”,并“拒绝”违背其教育理念的行为发生。真正的“思”伴随着主体“我”出现了,教师从“简化的实践工作者”成为了“教育生活的定义者”。
(三)引导教师阅读经典,建构教师精神世界
要改变教师生活世界日益外在化、标准化、碎片化,重要的是要帮助教师建构内部的精神世界。当我们向内追问现代教师遭遇的生命困境时,会发现现代教师的心灵最没有力量。教师不再为追求正义和真理而是为追求效益和谋生从事教学时,教师的精神世界日益萎缩。因为“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12]人类智慧、信仰与理想会滋养人的心灵、使心灵充满力量。人文经典书籍最能传递人类的智慧、培养教师的教育信仰和教育理想。人类在各个领域不断取得进步,如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唯有在思想领域从来没有什么进步,智慧在古代、思想从来是旧的。人类的智慧以人文经典书籍的形式被世代传承。现代人距离智慧、信仰、理想最为遥远,获得智慧、信仰、理想的方法是阅读人文类经典。
人文经典包括哲学类书籍,如中国的《论语》、《学记》、《大学》、《孟子》,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人文经典还包括史学类书籍,如司马迁的《史记》等。不仅包括哲学类与史学类书籍,人文经典也包括文学类书籍,如《红楼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此外,中西教育经典名著也会给教师带来教育理想和信仰的力量,如陶行知的《中国教育的改造》、柏拉图的《理想国》、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尔》、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等。当教师阅读经典的时候,就是在与这些伟大的人进行心灵对话、在观察和理解他们对于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与思考、在体会他们赋予教育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严肃责任感。当教师阅读经典时获得向内阅读自身经历的机会。
(四)帮助教师寻找生命理想的现实榜样
教育生活中的校长应成为教师建立生命理想的第一榜样。当今中国学校教育倡导的教育家办学即与这种精神要求相契合。真的教育家首先是哲学家,就哲学家来说,知识和品德不可分,哲学家是用生命在实践他的人生信仰与追求。其次,同行榜样具有强大的教育力量。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对职业本身价值的追求与对生命的热爱、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一心为教育的高尚人格,可以唤醒并强化教师的生命理想、教育理想。比如上海基础教育领域的于漪老师,在论及教师责任与使命时,她认为教师“一个肩膀担着每个家庭的未来,另一个肩膀担着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正是对教育抱有神圣的使命感,使她始终保持着对教育的敬畏之心。对教育榜样的学习和宣传可以在个体身上产生一种“替代性强化”或“替代性学习”的作用,从而建立新的行为模式,而行为模式的持续改变必然会影响人的观念系统的变化。
[1]冯友兰.境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1.
[2] 韩婴.韩诗外传(卷五)[EB/OL]. [2017-10-01]. http://www.guoxue123.com / jinbu / 0101 / 03hswz / 007.htm.
[3] 李政涛.生命自觉与教育学自觉[J].教育研究,2010(4):5-7.
[4] 周国平.灵魂只能独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36.
[5] 论语·雍也(第二十八)[EB/OL]. [2017-10-01]. http://www.ldbj.com/lunyu/lunyuquanwen.htm.
[6] [7]孙培青,等.中国教育思想史(第1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93,192.
[8] 叶澜等.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
[10]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
[11] 石中英.教育信仰与教育生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0(2):29.
[12] (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