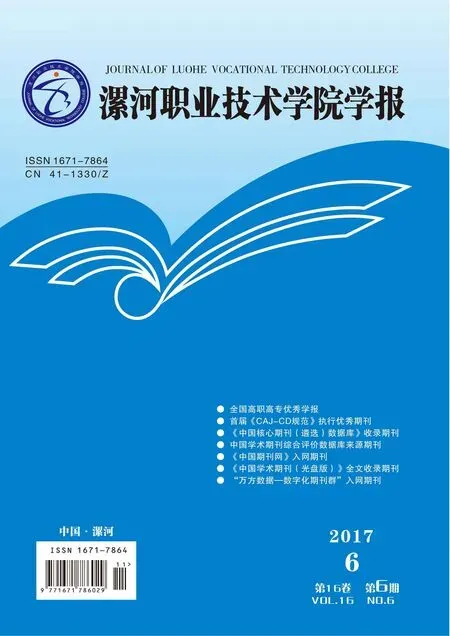《孔雀东南飞》与《苔丝》主人公命运悲剧解读
杨秋霞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孔雀东南飞》与《苔丝》主人公命运悲剧解读
杨秋霞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刘兰芝与苔丝的悲剧在中外文学史上堪称经典,专家学者们也分别对两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作了大量研究,而将二人的悲剧结合当时社会环境综合起来探究共同的命运根源者却是寥寥无几。二者悲剧看似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不同的家庭背景使然,实则都是当时的“霸权式”的男权意识推动,她们因无法摆脱男权制思想的戕害,所以不自觉地一步一步走向生命的完结。
男权思想;苔丝;刘兰芝;性别角色;命运悲剧
《德伯家的苔丝》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的杰出作品。作品描述了家庭贫困的苔丝受父命去贵族家里攀亲,遭遇一系列不幸,杀死情人,最终被判死刑的故事。《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长篇叙事诗,该诗风格质朴、人物鲜活、情节震撼人心,影响深远。对于二者的悲剧结局,古今中外学者分别做了大量研究,从封建家长制和人物各自的性格角度进行分析,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寻找其共性来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方面却是一片空白。仔细研读两部著作,结合当时社会背景,不难发现,男权思想始终贯穿着二者的一生。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农业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而农业生产,男劳动力又是主要的承担者,女性是被动的,是附属品,正如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发展而来…”[1]因此女人本身虽经叛逆阶段,但最终要向男权社会屈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3]。本文就从女性主义者的视角,从作品所叙述故事的几个时间段,来研究当时的男权思想对二者悲剧的渗透。
一、苔丝的“攀亲被诱奸”到“回父母家”与刘的“为君妇”到“被归遣”过程中,男权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家贫,苔丝受父命去贵族家攀亲,致使其被诱奸,这是典型的男权思想的体现。正如布莱恩·特纳所言:“妇女的从属地位并非本质的生理结果,而是因为文化把女人的衍生性阐释为自然的牢不可破的连接性。当然,‘文化’与‘自然’的差别本身也是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分类图式把女人列入低级的‘自然’范畴,把男人归为高级的社会范畴”[4]。苔丝的父亲德北打发自己十七岁的苔丝去德伯老太那攀亲,希冀遇到贵族王子娶苔丝为妻。苔丝婚姻不能自主,同时印证了儒家的女人“从父”与西方的婚前的女人是父亲的“玩偶女人”的论点。苔丝遇到了德伯老太的独子亚雷后,被骗了贞操。回家后,“可是你却没有让他娶你”,其母的思想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经济着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女儿的声誉,可以说后者更重要。苔丝虽不是主动去攀亲,但是却在家人以及家庭处境的压力下,希望依靠别人来改变自身状况。苔丝与其母的这种习惯性思维,在男权面前的无意识的自我认同正是那个时代已经沉积下来的男权思想的自然体现。
同样,有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在男权文化大背景下,性别偏见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彻底性,总是让男女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刘“为君妇”到“被归遣”,也说明女性在男权制主宰下,女性观念道德的被压迫。诗中焦母要驱遣刘的理由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说明在焦母心中,是有一个儿媳妇或者标准女人的形象的,那就是几千年来男权社会产生出来的女性的标准形象——没有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就是要求女性不能有一点自由意识的色彩。然而刘并不完全是对焦母的逆来顺受,从她的话中“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可以看出,刘是满腹怨气。她自视才高,琴棋书画,却事事不顺心。敢于抱怨夫妻不能朝夕相伴,抱怨婆母的挑三拣四。在封建的家长制社会,对婆母的话,不管对错,媳妇都要遵从,而刘却敢于提出抗议,这在婆母眼里就是大逆不道,婆母不满就可以命儿子休妻。所以刘的被驱遣并不是焦母认为刘懒惰,而是触犯了男权社会的女性评判标准。在焦母要驱逐刘的时候,我们看焦的表现,跪告——表态“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见状,槌床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时,焦默无声,再拜阿母之后回房,哽咽着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吾今且报府,还必相迎娶”,不是我要休了你,是母亲逼迫的,我得上班去了,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去接你回家。焦能做到的只有这些,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更积极的办法。他不可能改变母亲的封建男权制思想,也不可能意识到自身的习惯性的男权制的思维,也就更加不可能去反抗其母与他本人所代表的男权制力量,不敢反抗也无意识去反抗。
二、苔丝“回娘家”——“再次委身亚雷”,刘“被回家”——“亲父兄逼婚”,这一过程中两主人公也逃脱不了男权的压制
男权制的社会没有一丝对女人的尊重,其强权与虚伪可见一斑。苔丝在被亚雷诱奸后,依然舍弃没有爱情的情感关系。孩子夭折后,迫于经济原因外出谋生,在牧奶场遇见了克莱,两人相爱。结婚当晚,克莱讲述了他曾经荒唐放纵的生活,苔丝原谅了他。这种原谅不只出于对克莱的爱,更是认为男女有别,这是苔丝对男权社会下性别角色的无意识的认同。但是在苔丝坦诚了自己的过去后,克莱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克莱能够接受自己不贞的经历,却无法忍受苔丝的过去,这正反映出男人主宰一切的男权思维。苔丝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经济贫困者往往要被社会挤出正常的生活轨道”[5]。其父嗜酒如命,无力养家,幻想依靠名门望族的姓氏来改变命运。当时的社会也无法为这样的女子提供自力更生的制度保障,女人的职责就是“事在供酒肉而已”[6]。苔丝为全家的生计,不得不寄希望于亚雷,依靠男人来改善经济状况而不是自力更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女性沦为男人的附庸,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再看这一过程中,男权制下刘的境遇。回到家里“县令来提亲”时,母亲了解女儿性格,只得“谢媒人”,之后“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深受男权思想熏染的刘也只好“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由从夫到从父兄,刘冲不破男权的牢笼,自身也带有无意识的男权思维。迎亲场面描写: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即使这样显赫的未婚夫也不能博得刘的倾心,刘的心中还是只有焦,其显赫程度与刘的追求纯真的爱情或者说是“从夫”“从父兄”的思维定势形成强烈的对比——即便是这样,刘还是被迫要与县令儿子成亲,其中其哥哥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刘口中我们可以得知,其哥哥性格暴戾强横“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在听说是刘数次拒婚之后,“怅然心中烦”非常不耐烦,而且与刘对话之后刘根本都没有反抗,相比刘对刘母的诚恳,说明刘非常了解兄长性格,蛮横无理,与哥哥根本就没道理可讲;在对待县令公子提亲一事,哥哥的一句“作计何不量!”,一声责备:你真是不懂事!之前你只是嫁了一个小小府吏,现在竟有豪门贵族来提亲,条件较之与焦仲卿相比,县令公子能保你一生荣华富贵,这样的如意郎君你还不嫁?其中也不乏包含长兄对刘无辜被遣的愤怒以及对妹妹未来的担忧。有人认为这是他趋炎附势市侩形象的表现,但我认为,这也是他在那种社会制度和生活环境下,其自身的无意识的男权思维,认为女人就应该嫁个男人,不允许女人的独立存在。集体无意识的男权思维对女性的压制迫害,在作品中出现的几位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苔丝“杀死亚雷”,刘“举身赴清池”,在男权制思想的毒害之下,作品中人物自身也具有着无意识的男权思想
克莱无法接受苔丝的过去也无法容忍亚雷活在这世上,这种思想本身就是霸权式的男权思维,甚至可以因为贞洁的观念去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当克莱回心转意去找苔丝,苔丝以为幸福回来了,却又遇到亚雷的嘲讽与欺骗,并受到威胁。正是亚雷“霸权性”的男权意识,导致苔丝的“醒悟”,认为是亚雷毁了她的一生,促使她杀死了亚雷。表面看来,是苔丝对亚雷的恨意产生杀害的心理,仔细分析便知,因为亚雷使她失去克莱,因为男权思想让克莱嫌弃苔丝,因为苔丝在一种男权笼罩下找不回自己的爱,所以才杀死亚雷。包括苔丝获绞刑,也是男权制下的道德、法律所致。在苔丝遭受亚雷的侵犯的时候,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在杀死亚雷后,男权社会的法律迅速起了作用。女人没有伸张正义的权利,正如西蒙·波娃所说的:“她们只是一种对象性存在,没有自由意志”[7]。
再看刘,她认为“理实如兄言”,哥哥说的对,不该“中道还家门”,那就该“处分适兄意”,一切都由哥哥来安排吧。刘在无法得到母亲的支持,同时又有父兄的逼迫,在如此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刘的内心世界紧张不安,她对自身身份的直觉意识,使得她无法抗拒来自父兄所代表的男权力量,这就是当时男权社会束缚下的女性的无意识地服从男权制的思想。焦仲卿把刘要再嫁的原因归咎于刘的不守诺言,见利忘义,继而对刘冷嘲热讽,“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做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的一番话即为其心中所想,心中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使然,他把这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刘却不自责,他的无意识的男权制的思想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对这一切负责。休妻承诺要接刘回家,可是却迟迟不见焦的身影。首先是焦失约在先,但却指责刘做得不对,这是他头脑中男权思想在作祟,认为男性对女性的掌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便离婚了也可以左右着刘是否可再嫁。而深受男权压迫的刘听了自然也会认为自己负了丈夫的深情厚谊,“举身赴清池”也就避免不了。仔细分析,刘的死不是为践行爱情誓言,她是死于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且这种思想意识不是刘一个人的,是当时人们的集体共识。综合来看,刘的死是当时社会男权制下家长制思想和个人性格综合起来造成的悲剧。
结合两部作品所处的时代特征,不难发现,古代的东西方文明都是以男性为轴心的,是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男权思想造成了两主人公命运的结局。在维多利亚时代,苔丝生活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男性与女性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说过:“从奥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化都是以男性为模特的”[8]。身处那个时代的苔丝无法逃脱男权制下女人角色的被曲解,无法摆脱男权意识对女人的戕害。同样,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下常道”。在这样封建礼教严酷压制下,“刘的抗争也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9]。尽管两主人公都具有追求爱情的反叛的性格特征,但终究作为个体的人还是要回归社会的。她们始终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强加的思想意志,这就使她们不得不站在男权社会的立场来审视自己,也就为她们的悲剧添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男权制下的宗教、法律、习俗等重重枷锁迫使她们一步一步走向了生命的终结。
[1] Peter. Widdowso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2] 系辞上传[EB/OL].http//www.tl5000.com/13jing / yi/008 htm, 2010-2-10/2010-5-10.
[3] 系辞上传[EB/OL].http//www. zx. Tang. cn/zhou yi/tanyuan / 200904/5. htm, 2010 -2-10/2010-5-10.
[4] [美]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90-191.
[5] 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76.
[6] 吕美颐.中国近代妇女运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45.
[7]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66.
[8] 许玉乾,崔文良,等.走向女人深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2.
[9] 游芳.《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特征[J].闽西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学报,2007(9):76.
[责任编辑宋占业]
2017-07-27
杨秋霞(1980-),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淮定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教学与经济管理研究。
10.3969/j.issn.1671-7864.2017.06.013
I06
A
1671-7864(2017)06-004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