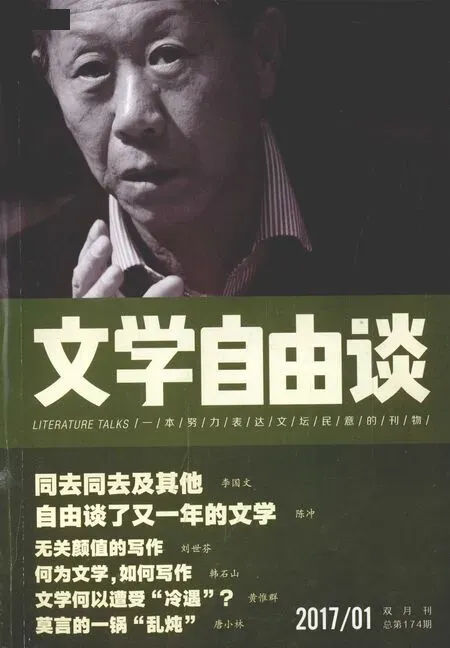何为文学,如何写作
韩石山
何为文学,如何写作
韩石山
感谢杜海先生的邀请,让我这个文学上的老兵,来讲讲写作。
事先定的题目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体会》。 我想先离开这个题,讲讲扬州,讲讲何为文学,如何写作。 这样,再拐到传记文学的写作就不会蹈空,就能落到实处。
扬州,一把文人的洒金折扇
十一二年前,2005 年吧,我还在《山西文学》杂志做事,春夏之交,带着编辑部的人员,来苏皖一带采风。 在南京转了两天,《钟山》编辑部的朋友问我,还想去哪儿,我说扬州。 他以为我去了扬州,还要去苏州、无锡,我说哪儿都不去了,就去扬州。 那次在扬州,也是杜海先生接待的。
为什么我对扬州如此情有独钟呢?
不是谁教的,是喜爱旧体诗词,喜爱旧文化,自个悟出来的。不来扬州,你对古典文学就没有切近的体验。 到了扬州,等于你踩着杜牧的脚印走过。
文化这个东西,有点像美女,从来就是嫌贫爱富,追逐“高大上”。 北京哪儿美女最多? 网上看吧,最好的图片,差不多全是三里屯的街拍。古代的扬州,就是中国的三里屯,是性情的释放地,也是文化的陶冶地。 有没有真性情,有没有真才华,不来扬州待上一段时间,你是不知道的,别人也是不认可的。
杜牧有句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都说这是他回首往事的感叹,我看不是。他并没有在扬州待过那么长时间,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期许,一种奢望。等于说,如果我能像南柯一梦那样,在扬州住上一段时间,让青楼女子欣赏我的才华,即便斥我为轻薄、不厚道,也是值得的。
现在一说青楼,就是做那个事的地方。 其实,专做那个事的地方叫窑子。 青楼可以做那个事,但不是专做那个事;做跟做也不一样,是释放性情,也是陶冶性情,讲究的是情调,是风雅。 这个道理,是没法跟现在的人讲清楚的,你说了半天,他最后会问你,花那么多钱,不做那事,不是太亏了吗? 这么一说,你还跟他说什么?正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也。
扬州文风之盛,史书多有记载。名人里头,生在扬州,来过扬州,吟咏过扬州的,不计其数。 最可称道的,该是“扬州八怪”。 过去说是“怪”,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有前卫意识,得风气之先。
如果以物件作喻,杭州是一柄花伞,情侣依偎着去游西湖;苏州是一把绢质的团扇,美女拿起遮住半个脸蛋。扬州则是一把洒金的折扇,文人拿在手里,哧喇一下甩开,哧喇一下收起,要多风流有多风流,要多洒脱有多洒脱。
园林、饮食、名士、美女,可说是扬州的文化标志,再加上雕版印刷,就构成一幅文人雅集图:精致的园林里,几个名士,吃着可口的饭菜,美女相伴,拿着雕版古籍,吟诗作赋,何其风雅。 看来这种流风遗韵,扬州市作家协会是传承下来了——我在别处也讲过课,多是在高楼里,在教室里,你们可倒好,在这样一个明清风格的园林里,叫萃园。这么冷的天,窗外还是一丛一丛的绿。
在这样一个地方谈文学,我有一种回到往昔的感觉。
文学,一个比科学更需要才智的行业
中国旧文化里,将世间的事物分作两类,一类是“道”,一类是“术”。 道是方法,是要达到的境界;术是手段,是具体的作为。后世不说“道”了,说学,说学科,比如科学、算学、医学。 什么是“学”呢? 就是通过“术”而能达到“道”的境界的行业。 只有术,而不会达到道的行业,是不能叫做学的,比如街上有扫地的,你不能说还有门学问叫扫地学。
从这个道理上讲,文学,就是通过文字的写作,而能达到文学的境界的行业。 光是用文字来写作,说自己写的是小说,是诗歌,是不能称之为文学的。 只有达到文学的境界的,才能称之为文学。上个世纪 20 年代,中华书局创办不久,舒新城先生是总编辑,有个名人写来信,给他推荐一个年轻人写的诗集。舒看了,在信上批了句话:“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一串的字。 ”
据说现在,我们每年要出好几百部长篇小说,短篇恐怕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 这些东西,出版是在文学出版社,发表是在文学刊物。 作者说他们写的是文学作品,我们也都这么认为。
真的是吗?
这不等于说文学是个篮子,就像俗话说的,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捡到文学这个篮子里的,就都是文学。
这一现象,多少年前,我就注意到了。很想写文章说一下,可一想,这样说了,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也就忍住没有说。贼心不死,这个意思,现在还是说说吧。
十多年前,在《徐志摩传》的《序》里,借说自己的书做由头,我说:“读者先生,千万别把这本书当做什么传记文学。若存了这个念头,我劝你还是放弃。习文三十多年,我已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 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要容易,连点都不用, 只要一放进文学的筐子里 (比如小说) 就是文学了。 ”(《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 页)
人微言轻,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会听。
过了七八年, 德国汉学家顾彬著文说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下子炸了窝,觉得这个德国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群情激愤,一片哗然,直疑心这家伙是八国联军的后代,要再一次火烧圆明园。 顾彬后来说,他说的垃圾,主要是指小说,诗歌是好的,还举了几个著名的诗人。
我的看法不同。 我觉得,如果说当代小说是垃圾的话,当代诗歌更是垃圾。
顾彬所以会有这个看法,我估计他的汉语言文学的认识水准不低,而欣赏水准,却属于浅易的那种。 他不知道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也不知道中国现代诗人在新诗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只看了些当代诗人翻译成德语的诗歌。 诗,是要有韵律的,不是分成行就叫诗。 新诗是舶来品,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孙大雨、戴望舒诸人,在建立新诗的音节或者说是音步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可惜他们的试验,还没有取得成功,就迎来了一个“诗崩律坏”的时代,评判是诗不是诗,只看分行就行了,他们前期的试验,全都打了水漂,不会有人再去理会。中国的诗人分行写了,外国的翻译家,不会也这样粗鄙,按原来的行儿翻译。 他们一定是按照作者的意思,翻译成德文诗的形式。这样,顾先生看到的,就是既有韵律之美又有思想冲击力的中国的诗歌了。于是乎,他说诗歌的情况不坏。
公允地说,中国的小说里、诗歌里,都有好的东西。但是大多数,说是垃圾有点过的话,像舒新城先生那样,说是“一串一串的字”,该是不为过的。 好的总是极少数,要不就不能叫好的了。
在人类前行的历史上,任何可以称之为“学”的行业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担负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将人类在这一行业里已然达到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
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才智,跟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才智,应当说是一样的高;某种程度上,还应当更高。好些科学家,说他的灵感来自于名诗的吟咏,作家绝不会说他的灵感来自一次科学的实验。
举个小例子。杨振宁的理科成绩,一定是很好的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上世纪 70 年代吧,他回国参观,在北京遇见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此人着实不简单,当过美国的亚洲学会的会长,是大师级的学者。 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前后差一年考取公派赴美留学的资格。 闲谈中,说起当年留美考试,杨说,炳棣啊,你比我高三分。这已经是很尊重了。但何不买这个账,当即说,不对,我比你高七分。这是何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写的,同时说,历年留学考试中,分数最高的是钱钟书。那时候公派出国的人很少,谁是什么成绩,大家都知道。
他们说的是外语考试的分数。看书时,我算了一下三人的成绩,钱是 83 分,何不会超过这个分数,若是七十七八的话,杨也就是 70 分的样子。他们都是清华毕业的。成绩的好坏,就是这门学科的好坏,一点侥幸都没有。
这三个人,都是中国的顶级人材,钱是作家(也是诗人),何是历史学家,杨是物理学家,也可说是科学家。杨得了诺奖,钱和何,也在他们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 这是不是可以说,作家和学者的才智一点也不比一个科学家低呢?
文学的境界,说白了就是智慧的境界。
什么叫文学?就是用文字写下的,达到文学这个境界的作品。
反过来说,没有达到文学境界的作品,叫什么都可以,只是别叫文学。
写作,跟读者的智力较量
前面说的太沉重了,这里,不妨换个轻松的说法。
我是 12 月 21 号晚上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就是 20 号,在故宫东侧的太庙,就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日本大书法家井上有一的作品展。 井上已去世多年,来参加开幕式的,是井上的老朋友,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海上雅臣先生。 我不是书法家,为什么要我去呢?海上先生的《井上有一传》在中国出版时,我给写过序,这样我就去了。这次展览,分别在东西两配殿里举办,东配殿展出的是井上有人的书法,西配殿里展出的是 13 位中国书法家的作品。
在东配殿的展版上,有海上先生写的前言,说这次展览,还有友情参展的各位作家的作品。 他没有说这 13 位是书法家,而说是作家,即作书之人。
来的火车上,睡不着,我就想,是不是在日本对书法家的称谓比在中国要尊贵一些,也就谨慎一些?仿此例,我们对作家,是不是叫写家更合适呢?即这是一个写文章的人。
古人说,唯名与器不可假于人。 我们现在给人名分,实在是太随意了。取得太轻易了,自己就不珍惜,别人也不会很看重。当下文化上的混乱、粗鄙,这该也是一个原因。
如何写作? 我有一个老观念,那就是,写作是一种智力的较量。是作家自己跟自己智力的较量,更是作家跟读者智力的较量。读者每买一本书看,除了已然成为名著,慕名而买之外,大都是抱着较量的心理,就是,看看这个家伙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看书的过程,像是在猜一个谜,只有这个谜还有趣,他又猜出来了,才觉得有意思。太浅了,他笑话你;太深了,他理解不了,也不会服气。
跟作家做智力较量,这让人听起来像是说笑话。 在中国,好长一个时期,当作家的多是考不上大学,为了找出路才去写作的。让考上大学的,跟没有考上大学的,去较量智力,不是笑话是什么? 作家自己,怕也没这个勇气。
我是 1965 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社会上对考文科的人,多持鄙弃的态度,以为是数理化不行,才考文科。 确实有数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的,可也确实有文科不行才考理工科的,怎么就不说呢? 事实上,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要出成果,都需要一流的才智。
我上学学的是历史,没有学成,是混出来的。过去写小说,很少跟人说我是大学历史系出来的。为什么呢?你说了加不了分,还减分。 懂得的人说,你是斯文扫地,陪太子读书;不懂得的人,说上过大学的,怎么会写小说?成了自取其辱。我后来不写小说,转而做现代文学研究,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跟这个不无关系。
在火车上,想的最多的是,怎样跟朋友们谈小说写作。 我是不写小说了,但对文学的研究,对小说的关注,从没有停止。
当代小说写作的问题,跟写新诗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 大体说来就是,一批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在那里自拉自唱,自得其乐。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现象,比如 1958 年的全民写诗运动,那时也跟疯了一样,小学生写诗,老农民写诗,只要是个顺口溜,就说是诗。再有一比,就是现在的广场舞,会不会都可以跳。 现在成了只要会写字就敢写小说,写下一行一行的字,连起来是一段,一段一段连起来是一节,一节一节连起来是一章,一章一章连起来就是一本书了。至于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怕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个字,一个是“编”,一个是“写”。编下的写出来,就是小说,是小说就是文学。写出文学作品的人,能不是作家吗?
这些人,可以说,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东西。
路上我一直在想,该用个什么最简单的例子,朋友们一听就知道什么是小说写作,什么是瞎编瞎写?
小说写作的关键,或者说小说写作的秘籍,以我的理解应当是,人物在低层面上的冲突,在高层面上达到和谐。具体地说,就是人物在社会层面上的冲突,在人性层面上达到和谐;在欲望的层面上发生的冲突,在理智的层面上达到和谐。几乎所有的文学名著,都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比如《红与黑》,比如《包法利夫人》。上世纪 30 年代,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不是这样。他们的写作观念是,人物在经济层面的冲突,在阶级斗争的层面上,通过斗争得以解决。 比如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
这道理太玄了,说了很难让人一听就明白。
想啊想,还真让我想到一个例子。
前几年,我在写一个历史长篇小说,叫《边将》,写了好几年。儿子让我上微信,我嫌麻烦,就没上;现在《边将》写完了,两个月前,儿子给开了微信。 没事了,常上去浏览。 有个段子,也是正好在火车上,让我想起来了。
说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爷坐夜车,坐的是卧铺,上面是个年轻姑娘,一直在看手机,看电影吧,声音不大,呜里呜噜说个不停,扰得大爷没法入睡。后半夜了,大爷实在忍不住了,敲敲上面的床,说:“姑娘,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 ”姑娘俯下身子,看了看,说:“嗯,上来吧! ”过后大爷对人说,代沟真好。
这个段子,真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名著的缩微版。 你看嘛,冲突是社会问题引起的,一个老年人,一个年轻人,一个要看手机,一个要睡觉,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真是烦死了。 无奈之下,提出了自己的抗议,“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接下来极有可能引发一场争吵。但是,同样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姑娘看这个大爷模样也还将就,人家又是如此文明地提出要求,想了想,说“上来吧”。 原本是一场社会冲突,在人性的层面上达到了和谐。
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在这样的较量中,失败的极有可以是读者。 当然,也会有聪明的读者,预测到后来准定有那样的事儿,要不他设定一个大爷一个姑娘做什么?
现在再来推测一下,这样的题材,给了一个不会写小说,却爱写小说的人,会写成什么样子?一种可能是,姑娘在上铺,看黄片,看得来了情绪,又无处发泄,便撩逗下面的大爷。 大爷呢,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当即从命。 毕竟上了年纪,爬到半截掉了下来,又往上爬,爬上去倒也如狼似虎。再一种可能是,这个大爷是个老色鬼,一看这个卧铺车厢里没有外人,就打上了姑娘的主意,如何撩逗,如何云雨一番。
两者不同在哪儿呢?
前者有构思,有起伏,有因果,有事情的进行,还有事件所达到的思想的境界。 后者,只是叙事,只是描写;而这个故事,跟上窑子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跟强奸也没有差别,不过是野地里换到了火车上。
前者是文学作品,后者,只能说是文字垃圾。
这样就该明白,有结构,有意境,才叫文学——当然是通过叙事与描写达到的。 光有叙事,光有描写,不能叫文学。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作品的语言,能不能达到文学的层面。在这上头,可以说,简洁与冗繁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清楚,耐读,有文学的意味。更高级的,还会有一种内在的韵律。
诸位都是成熟的写作者,这上头就不多说了。
传记,五十年之毋庸他人烦劳
现在该谈传记文学了。
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就转向了传记文学的写作。 这样说,也是从了俗;严格地说,应当是人物传记的写作。至于是不是传记文学,那要看你的作品的语言,达没达到文学的层面。
2011 年之前,我一共写了三部传记,分别是《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和《张颔传》。张颔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仍健在,1920 年生,今年 97 岁了。 这几年,我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历史小说《边将》,已完成;一本是《徐永昌将军传》,正在写着,快写完了。 徐永昌这个人,好多人可能不甚了解,说一件事就知道了。 1945 年 9 月,盟军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主持其事的,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 每个国家各派一个代表,在降书上签字。中国的签字代表就是徐永昌将军。整个抗战期间,他是军令部长,可以说所有大的战役,全是他策划并发布命令的。这个人是山西原平人。一位原平籍的出版社社长要我写他的传记。
我动手写《李健吾传》的时候,写传记的人还不是很多。这几年,一下子热了起来。作家出版社曾组织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工程,此前此后,各省也都有类似的举措。 好些作家转向了传记写作,最多的是写报告文学的人。对这个,我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说,这是好事。
对组织方式,还是有点看法的。 不是说现在的不好,是说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我以为,这样的大工程,应当用现代的方式进行。比如,你要写一百个文化名人,谁是合适的写作者呢? 不能说是你指定,也不能说是他报名;这两种办法,都有相当的风险,就是钱花了,东西出来了,但是不尽如人意。
现代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在媒体上登广告,提出条件,然后组织一个高水平的审核班子,到时候也许会缴来三部五部,经过审核,谁的好,出谁的,给以巨额的报酬。 只有这样,才能将最好的作品征集来,为后世提供最好的传记版本。
有人说,你不给钱,我就不写。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给了钱也写不好。
写作,应该是一种舍得投资的事,完成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花钱是本分。
我写《李健吾传》时,只是说自己要写,花多少钱觉得都是应当的。一两年内,都没有跟出版社联系过。后来,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么一本书,他们也正要出《李健吾文集》,就拿过去出了。 《李健吾传》写了四年,1993 年开始,1997 年出版。
写《徐志摩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听说我写了《李健吾传》(当时还没出来),说他们正在组织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些大名头的人物,都有人写了,出版了,还有三个人,让我选一个。问哪三个,说是何其芳、冯雪峰、徐志摩。朋友以为我会写何其芳或是冯雪峰,料不到的是,我说写徐志摩吧。他们问我一年行不行,我说肯定不行。两年呢?我说不要定死了,我争取早点写成就是了。 结果是,我写了四年才完成。 1997 年接下的活儿,2000 年秋天交稿,2001 年初出版。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呢?
我完全是按照历史著作的路数写的。
上大学的时候,看过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知道写传记要先编年谱,我是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编年谱。 这两本书,都是用了三年的时间编年谱,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书。
年谱怎么编呢,就是把传主一生的行事,按年月日编下来。有日的编在日下;没日而有月的,编在月下;没月而有年的,编在年下;连年也没有的,总有个大致时间段,就放在这个时间段某年之下。年谱编成了,传主生平事业,就全都理清了。前后有了照应,左右有了依傍,性格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事情的原委可由果求因。 写起来,就能做到起承转合,浑然一体。
写人物传记,还有一点要记取,就是要舍得买书。 只要花了钱,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事。 比如说,徐志摩办过《晨报副刊》,我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有次去琉璃厂闲逛,看见一家旧书店卖《晨报副刊》的影印本,一套十几大册,售价两千六百元。买还是不买,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元。想了想,这书虽是应出版社之邀写的,但它是我自己的著作。狠了狠心,还是借钱买下了。后来证明,这套书是买对了。这样的书,拿在手里随意翻看,跟从图书馆借出来,只能在阅览室查一两条资料,是不一样的。从随意翻看中,找出许多资料,写了十几篇文章。对《徐志摩传》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后来编《徐志摩全集》时,又从中翻检出多篇徐的佚文。
在写几本传记的过程中,还有个体会,就是别人对我的预期,比我自己对自己的预期,总是要大许多。 比如,我自找传主,选了个李健吾就觉得很幸运了;别人让我写,就让写徐志摩。 前几年,我自己找传主,写了个《张颔传》;别人找我写,就让我写徐永昌将军传》。
再有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管是别人的委托,还是自己的寻找,既然选定了一个人物,一定要尽心尽力,把这个传记写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最好能立下这样的心志,甚至不妨夸下这样的海口:这个人物的传记我写了,几十年内毋庸他人烦劳。
这是多大的气派,又是多高的品格!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杜海先生,谢谢在座的诸位朋友,谢谢前面的几位美女!
(本文为作者在扬州市文学创作高研班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