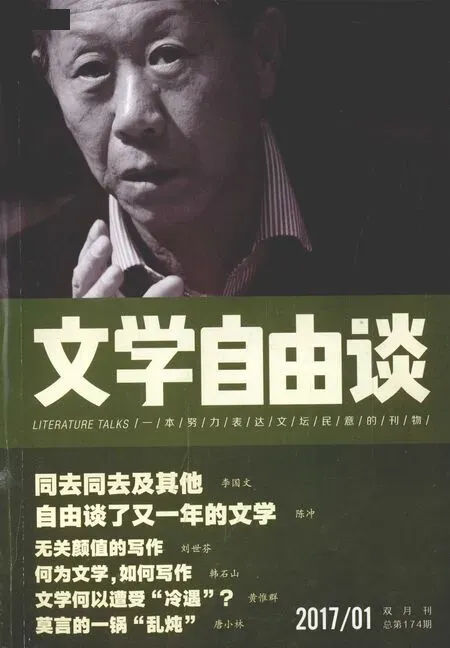拉美,云南和你隔一层壁?
冉隆中
拉美,云南和你隔一层壁?
冉隆中
我的书架上,安静地躺着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正度 32开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译者是当时北大西语系、复旦外文系等翻译大佬,其中有翻译家吴健恒从西班牙语直译的 《百年孤独》(他好像两次翻译出版过这本对中国和世界影响巨大的拉美名著)。 原作者则名气更大: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等等。 传说这套书在旧书市场已经身价不菲。
说到拉美文学和拉美作家,经历过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文学热的当时的“文青”(现在很多都退休了),莫不记忆犹新。 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引爆”是在上世纪的 60 年代,那时,关于美洲,大部分国人只是在地球仪上知道有拉美诸国,在现实生活中则知道头号敌人是北美洲的美帝。 那时谈文学还比较奢侈,遑论国外文学。 改革了,开放了,信息鸿沟慢慢填平了,国外风景如在目前了,人们才知道,在美帝之外,世界还有无数的精彩——其中就包括对中国文人而言十分“高大上”的拉美文学。 1982 年,马尔克斯凭一部《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直接引爆了中国文坛的拉美文学热。中国文学界似乎从这里看到了自己问鼎世界文坛高峰的希望。可以说,马尔克斯吊起了中国作家的胃口,无论是当时风头正盛的“重放鲜花”,还是初登文坛一夜爆红的后起新秀,都踮着脚尖,翘望瑞典文学院的殿堂,等着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也有通过官府或企业去和据说是诺奖文学评委中唯一的中国通马悦然勾兑的——云南就有一家当时靠某口服液横扫市场、牛气冲天的民企,因为老板或老板身边有一干人等热爱文学,居然也策划了诺奖评委老马的中国行。 当时很多文人都产生了某种错觉:既然拉美行,中国为什么就不行?
其实也说不上是错觉。 若干年后的 2012 年 10 月 10 日夜,与我的小儿子诞生的同一时刻,消息传出,中国作家莫言成为大陆公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而其创作源头正是从对拉美作家的仿写开始的。后来,莫言在谈到自己早期受到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影响时说:“我在 1985 年写的作品,思想上艺术上无疑都受到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主要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 ” 贾平凹也说:“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学,喜欢那个马尔克斯还有略萨……他们创造的那些形式是多么大胆,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什么都可以拿来写小说,这对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当头一个轰隆的响雷!”不仅是莫言和贾平凹,在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刺激下,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文学界都在积极关注马尔克斯,并出现了一股势头强劲的模仿、借鉴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热潮。 “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这句马尔克斯在巴黎阅读卡夫卡时所顿悟的话,在此时已成为接触到马尔克斯和其他拉美作家的作品的中国小说家们的共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经验,催生了中国 1980 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启悟了一大批作家。 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扎西达娃的雪域高原系列、马原的秘境西藏系列,尤其是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用文字塑造的他的家族史,和他笔下那些非英雄化潮流下的民间草莽,无不打上拉美文学的鲜明印记。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轨迹:从 1980 年代的《透明的红萝卜》《冈底斯的诱惑》《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到 1990 年代的 《白鹿原》《尘埃落定》,再到新世纪之初的《受活》,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经历了从倏然众声喧哗到逐渐悄无声息的变化。魔幻现实主义受到狂热推崇的时期,也是民间文化元素进入文学视野最充分的时期。 各种民间传说、乡野俚俗、宗教故事、历史神话,被当作最有表现力的文学素材,得以大量挖掘,反复呈现;“神秘中国”“古怪族群”“原始部落”等成为中国作家津津乐道的文学形象,所谓最具个性的地域品格和民族特色的文学背后,都可以照见拉美魔幻的影子。 那一时期,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略萨,大概是在中国最响亮的拉美名字。拉美文学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是因为民族和历史中某种内在的相似属性,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作家之间找到了某些共鸣或启悟。 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T.肖认为:“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 ”当拉美文学这些“影响的种子”降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中国大地上时,奇迹发生了:当时全中国最有理想的年轻作家都在疯魔一般熟读拉美作家,开口闭口几乎都在谈论拉美作品——如今很难想象,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一个作家如果不读拉美作品,或者不知道一两个拉美作家名字,那将是如何的老土。
而云南,更是从地理的民族的神话的甚至气候的多重因素上,找到了自以为与拉美文学最接近的某些特质。一位当时客居云南的著名小说家,将云南可以书写的文学特质元素概括为三个词五个字:宗教、神秘、性。 他以发表在《十月》上的《野店》来印证了自己的文学宣言——那正是充满了云南边地神秘宗教色彩和野性性爱内容的一部作品。除了内容上的仿写,修辞和词语的模仿也许更为直接。 翻翻那时云南作家的许多作品,开头几乎都是“我爷爷娶我奶奶的时候……”“多年以后……” 或者 “当面对行刑队的时候……”这样的句式。很多云南作家都学会了这样的技巧。聪明一点的作家或者会改写成这样:“1870 年 6 月的一个黄昏, 太阳就像病了,苍白,缓慢,孤独,茫然,迟迟不肯落山……街道泥泞肮脏,人们艰难地游走其间,年轻人和老年人走路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有人在训斥苍蝇:天都快黑了,还出来找死? ”这是一部获得众多好评的云南作家的小说的开头段落;仔细一看,仍然是色彩鲜明的马尔克斯或者博尔赫斯。 这种言必称拉美的现象,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国内文坛基本绝迹,而云南似乎比别处要固执一些。就在016 年云南某地召开的创作研讨会上, 一个外地大牌评论家用手指敲打着几部云南作家的作品,指出其开头还在不断仿写最让他反感的“拉美句式”,由此结论:云南人,太固执太落伍了!
上世纪 80 年代初,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确实席卷过中国文坛。 当时的中国文坛充满了“现实魔幻化”,或者“魔幻现实化”的大量作品。 如今的文坛,好像把这个词组拆分了,“魔幻”归了儿童文学,于是出现了儿童文学的穿越热或者魔法姐姐,“现实主义”继续留在了文学阵营里,当年那些以模仿起家如今依然健在的作家,如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莫言、余华、马原等等,无不归位于现实主义麾下,以主动的撤退或疏离的姿态,宣告了自己文学主体走向自觉和艺术风格的成熟。 莫言在世纪之交写作《檀香刑》时,甚至以将具有魔幻意味的几万字文稿“推倒重来”的壮举,宣告了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 李锐也对自己曾模仿马尔克斯的魔幻叙事表示了不满,在《旧址》重印时,他主动将有着《百年孤独》印记的小说第一句“事后有人想起来”删去。 到是云南的一些作家,依然痴迷于拉美文风,至今不改,显示出文学的某种执著。 在我看来,这其实并无不可。 因为,从地理的民族的神话的甚至气候的某些相似性方面,说不定让隔山隔海隔年隔代的作家们,在精神气质上早有了某些接近呢。如果不是只注重对拉美文学皮毛的关注,而是对拉美文学内在精神品质的深度借鉴,比如去看看博尔赫斯——这个在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方面都有惊人成就的拉美作家,是如何打通三种文体取得成就的? 有一种很生动的说法是:“他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的小说是诗;他的诗歌又往往使人觉得像散文。 沟通三者的桥梁是他的思想。 ”有人评价他:“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 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幻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笔。”他的作品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学的非现实感”。 他的作品对幻想文学贡献巨大。人们注意到博尔赫斯不断恶化的眼疾似乎有助于他那些创造性的文学语言,毕竟,“诗人,和盲人一样,能暗中视物”。而我们的很多作家,却是更擅长于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我的案头,还有一个物件,与拉美有关:玛卡。 有块状的玛卡,粉状的玛卡;有散放的玛卡,也有精装的胶囊玛卡。 玛卡在中国的种植和传播,比拉美文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还要神速。 它被神话为最厉害的“肾动力”,一度成为中国男人补肾的标配食物。 这些原产地属于拉美的物种,近年来在云南山地大量栽种,以至于从最初的物以稀为贵到很快烂大街——玛卡收获的季节,我在云南几乎所有的乡镇街市上,都可以看到黑的白的紫的玛卡,如同长得还没苏醒的小萝卜头,蜷缩在苍蝇聚集尘土横飞的集市上。百度词典上一搜,即见:玛卡(学名:Lepidium meyenii Walp,西班牙语:Maca),主要出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和中国云南丽江,是一种十字花科植物……玛卡富含高单位营养素,对人体有滋补强身的功用。黑色玛卡是被公认为效果最好的玛卡,产量极少。玛卡原产高海拔山区,适宜在高海拔、低纬度、高昼夜温差、微酸性砂壤、阳光充足的土地中生长;种植地区主要分布于南美州安第斯山脉以及中国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地区,这两大主产区有较大面积的适种土地。而云南其他地区和新疆、西藏等地,也有少量种植。
原来如此! 拉美,难道云南和你隔一层壁?
我似乎找到了云南作家痴迷拉美文学至今不改的原因。
2016 年 11 月 23 日,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