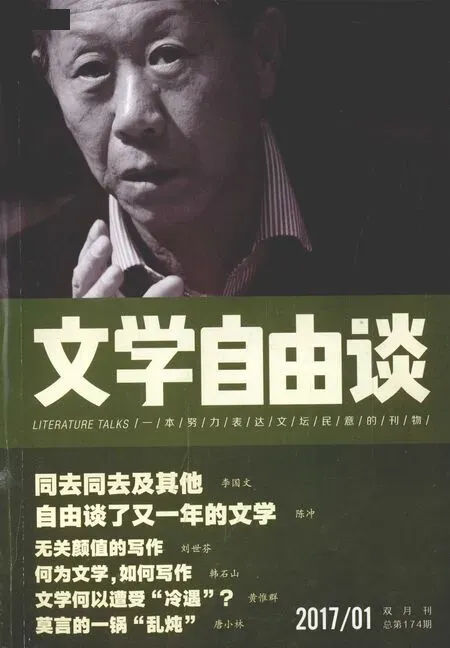自由谈了又一年的文学
陈冲
自由谈了又一年的文学
陈冲
这个标题在语法上有点绕。我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个“文学”主语)又自由地谈了一年。 不,这个意思是不对的,“文学”并不是到处都可以“自由谈”的。比如在有些地方,倘若一篇谈文学的文章,后面没有 20 个以上的“注释”,没有标明是某省或全国某个社科研究项目(须有项目批准文号)的阶段性成果,是很可能被“免谈”的。 事实上,可以“自由谈”文学的地方并不多。 把这个问题扔到我面前的,是《文学自由谈》的编者。 他要我“谈谈对小刊的看法”,不仅前面加了“恳请”,还极是恳切地问:“我们这一年的工作能打几分?”这让我立刻想到前年临近年尾时开的那个会。实际上,那是一个当着一群铁杆作者的面所开的新老主编的交接会,作者们表达的希望是刊物能保持原来的特点。此番以对小刊的看法”垂询,显然要的就是对那个问题的答案。这是个挺难给出的答案,虽然也有偷懒的办法。世界上几乎所有难办的事都有偷懒的办法。比如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只要改变一下统计方法和统计标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即刻便从 6102 万锐减到只有 902 万了,而且还由统计方给出了很专业的论证,证明后面这个数字才是正确的。如果我说“小刊”很好地保持了原来的特点,比如它的小开本——其实那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书刊,甚至只是“内刊”,虽然内容的信息量基本为零,却都很舍得花钱把开本做大,而其结果就是不方便拿在手里看,只能放在桌子上看,而且因为它往往不能自动摊开,还得用手扶着,或者用重物压着才能看。 古人用“手不释卷”来形容爱读书的人,可见书原是要拿在手里看的。常见有人为人们不再读纸质书而忧虑,其实那是纸质书自找的。《文学自由谈》仍然是可以拿在手里看的小开本,这就很好——不过单说这个,好像还交不了账。说白了,大家心里都明白,人们关心的是还能不能“自由谈”文学。真正的难度也在这里。盖什么才叫“自由谈”,怎样才算“自由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举例来说,有一种文章,言不及义,言不及物,言不及文本,就是一套套空泛的车轱辘话在那里来回转,按老底子的规矩,这种东西是不够发表水平的,现在却也自由地谈出来了。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不知道,反正我期待的不是这个。 那么,怎样区别“自由谈”和非自由谈呢? 以我的经验,鉴别一条生产线的好坏,最可靠的办法是看它的产品。 那么,文学的“自由谈”或非自由谈,就看它谈出来的文学是什么模样。 所以,本文的标题,虽然事件的主体仍然是文学,但在语法上,文学却是宾语,受词。
这就对了。“自由谈”出来的文学,和“按要求”或“凭想象”谈出来的文学,模样儿是不一样的。 “小刊”新年第一期的第一篇,就是个彰明的显证。按批评学的分类,文学批评的对象大略有三,一是作家,二是作品,三是文学现象,此文当属第三类。不过,按通常“学术规范”的要求,能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现象起码都应该在文学范畴之内,比如思潮、风格、流派等等,而此文的批评对象却不是这些。可也是,现在的作家们都在努力地保持思想一致,哪里会有自搞一套的风格,自成一伙的流派,更不要说什么思潮了。 然而,此文所指涉的那些事,你又很难说它们不是文学现象,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些文学范畴以外的文学现象。都是哪些事,恕我不在此一一列举了,有兴趣您可以读一读原文。 不过我可以举几个我很有共鸣的事,比如各种各样的精品扶持工程,各种各样的评审评选评奖,各种各样的封经许典的需要出大力流大汗的艰苦奋斗(前不久看到有人称之为“忙于颁发经典证书”,虽然够俏皮, 却明显低估了这个过程的劳动强度和筛选难度)。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有些地方的作协主席换届时所经历的那些艰难险阻。这种事,倒是应该第一时间写进当代文学史的。同样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写法,用的并不是那种归纳法,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倒是只说些具体人具体事。 比如它说到李霁宇的不甘心,认定自己某一部长篇的价值要五十年后才可能被人们认识到,也说到陈世旭的淡然,直称我们这一代人,哪里有什么经典可言,还说到那位正在被经典化的路遥,虽然动机卑微,但在弄文学的过程中,却是无比的忘我、投入、拼命、纯粹,将那些攀爬的欲望抛到了九霄云外。 是的,这就是“自由谈”了。 这样地来“自由谈”文学,你就可以明白文章的标题为什么叫《丧钟为谁而鸣》了。
按经典的说法,文学的盛衰,与“世道”并不具有正比关系。事实上,让许多中国作家心向往之的拉美文学爆炸,恰恰发生在那地方政治混乱经济疲软的时期。但有些国人的思维习惯,还是相信盛世理应出欢歌的定式。好多极有才干的人都在为这事儿忙碌,加班加点,鏖战不止,呕心沥血地想让人相信,一个作品只要在中国得到了好评,拿到世界上去也必定是处在最优秀的作品之列。区区身在事外,站在一边闲看,看得久了,也略有一点心得体会,那就是,在“有高原缺高峰”的原则确定之后,把这个“高原”描述成啥样儿,就成了把文学描述成啥样儿的关键。
其实呢,如果不把“高峰”绝对化,非得海拔 8000 多米的珠穆朗玛峰才算高峰,而是采取更包容的态度,比如把海拔只有不到 1500 米的五老峰也算上——旅游手册就介绍说,“五老峰位于庐山的东南侧,为庐山著名的高峰,海拔 1436 米”,站在上面,同样可有“日近云低”的感觉,则我们的文学也还是有一点“高峰”的。 先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接着是刘慈欣获得了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然后是曹文轩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最近则有 80 后女作家郝景芳获得了雨果奖的中短篇小说奖。能获得这些有世界影响力的奖项,虽然不是就能“代表一切”,毕竟也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你尽可以怀疑那些洋评委们的眼力是不是出了问题,但这些奖项的影响力就在那儿摆着。
同样道理,“高原”也有一个海拔的问题。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5000 米,而内蒙古高原海拔 1000—1400 米。 话说回来,这 1400 米其实才比庐山五老峰低 36 米。
然而,在“自由谈”出来的文学里,高原的样貌不是拿海拔来说事儿的。文学的度量衡不以“米”为单位。不是你把一些作家作品说得怎么怎么好,文学就成了青藏高原了。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也不是你给一些作家作品挑了点毛病,文学就成了内蒙古高原了。 “小刊”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致力于干这个活儿,而这个队伍的相对稳定,就保证了刊物特点和水平的稳定。在2016 年的“小刊”中,唐小林分别批评了王安忆、李佩甫的作品,曹澍则分别批评了方方、蒋韵的作品。 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说法,但他们的说法是建立在文本解读基础之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是作家把作品写成了这样,然后才是批评家对这样写不以为然。作家为什么会把作品写成这样,或为什么要这样地来写这个作品,用一个曾经流行过的说法,那是个“操作”问题。 “操作”之所以会有问题,正因为它是一种操作,而“高原”上的文学操作是有难度的操作,发生一点误操作,或被人认为是误操作,都是很正常的事,也是“高原”上正该有的景观。 我对唐、曹二位都没什么了解,但私心揣测,对于那些不是通过文学操作写出来的作品,而是用其他方法,比如用魔术手法变出来的作品,他们恐怕就批评不动了。 当然,这二位也不会跟着去叫好打赏。须是在“按要求”或“凭想象”谈出来的文学中,“高原”上才会这样地鸟儿叫马儿跑。 这一年里,唐小林还批评了余秋雨,曹澍则批评了易中天。 这种事做做固然亦无妨,但不宜做太多。这不是“高原”上的事儿,最多能算坝上的事儿。而在另一块场地里,唐小林批评了程光炜,王晓华批评了陈晓明。 这个事儿做得很有价值,但要真正做到位又很不容易。被批评的这两位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比批评他们的那两位的学问恐怕高得不是一点半点。 但那两位批评的并不是这两位的学问,而是……是什么呢?还真不好说。 一段时间以来,文学批评的功能正在异化,变成了产品质量检验所。 问题是,人家那些检验所里使用的仪表设备,还得经常请人来校正,而我们的文学批评,却好像压根儿不存在批评文章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让人很容易想起那部叫《鸟人》的美国电影。如果“小刊”有志于在这方面做些贡献,我想那应该是件功德无量的事。
“小刊”今年第三期还刊有黄惟群对《繁花》的批评。我“另起一行”来说这事儿,当然是因为觉得它有另列一段的意义。 《繁花》得了“茅奖”,若说它不在高原在坝上,有点过分,但它确实不是一部按文学操作法操作出来的小说,是一部一般批评家批评不动的小说。 它刚出版的时候,一片叫好声,完全是戏园子里的那种碰头彩。叫好的焦点,是它的上海方言和上海风俗。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地有了不同的声音,而异议的焦点,也是它的上海方言和上海风俗。于是“高原”上就出现了一道奇妙的景观:主要是一些“外地人”,在那里为《繁花》的上海方言和上海风俗一击三叹,而那个年代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或对那个年代的上海生活有认知、有了解的人,却在说“不是格能一种样子格哇”。 但一击三叹的文章好写,说不是这种样子的文章就不好写了。不是这种样子是什么样子?你就是另写一部《蓝屋》也说不清楚。所以就只能私下里说说,偶尔能见诸文字的,也仅限于某些会议发言摘要中的几句话。黄惟群的这一篇,是我见到的第一篇认认真真地批评《繁花》的文章。敢写这么不好写的文章,单是那勇气便差堪嘉许,至于他勇到后来自己又有点含糊,咱们后面再说。 他很精准地意识到了这部小说的要害。比如方言的使用:一个地方会有很多别处没有的方言,你在小说里用哪些不用哪些,要有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当然是选那些独特的、有表现力的词语。 按黄文的说法,《繁花》里用得最多的是“不响”:“据说有人统计……从头到尾出现过一千五百多个‘不响’”,其中的绝大多数,这个词语都不携带任何信息。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对了,是个品格、品质、品味的问题。什么叫“上海话”?按专家的说法,真正地道的上海本地土话,近似于现在上海周边县——比如青浦县——的方言,而后来在浦西被广泛使用的上海话,却是在上海的几家夜总会里“杂交”产生的。 夜总会不是那些住在“下只脚”的人们常去的地方,它是有一定“精英性”的。实际上,在老底子的上海,对读物或者叫书的品格、品质、品味,是分得清清爽爽的。 四马路(福州路)有一段开着好多家书店,等到天黑亮了路灯,这些书店打烊了,马路两边便道上就摆出了书摊。 我那时候买书,如果要买《孤儿历险记》《顽童流浪记》,或是《爱的教育》《伊索寓言》之类,得白天去书店买;如果要买《天宝图》《地宝图》《大侠霍元甲》,就得天夜了去摊头上买。 那时候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王先生白相上海滩》,讲的是有个叫王先生的白相人,在上海没啥目的地兜来兜去白相相,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白相的人物和事体,比如弄堂里总有人大清老早地喊叫:“拎出来!”当然更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下作男女和下作事体,野鸡、妓女、舞女、交际花等等,还有轧姘头之类——对了,就是类似《繁花》里不厌其烦生拉硬拽也要喋喋不休的香烟牌子、六合粉、老虎灶、旗袍、夜总会、租界巡捕、阳春面、旧棉鞋、码头、仓库、驳船等等。 目的很明确:满足那些不久前刚到上海来闯码头的外地人对上海的好奇心、猎奇心,顺带着也起一点导游的作用。它也使用了一种不常见的语言,其中夹杂了很多上海话,但不是那种场面上的上海话,而是一种——当时对这种上海话有一个特定的称谓,叫“洋泾浜”。由于这本书的预定受众很清晰,写手也相当胜任,常有一些出彩的描写和段落,且有一样好处,就是能用一个有点个性特点的人物,把那些原本互不搭界一地鸡毛的东西串接起来,所以一时卖得颇好。 记得当时还有一本同类的书,叫《汗把滥的五爷》,专讲上海的赌场和赌博的,却是用了一种广东人讲的洋泾浜上海话,比如那个“汗把滥”,其实就是赌牌时“梭哈”的意思,所以也挺有销路。当然,你要买的话,须得天夜以后到摊头上买,白天营业的书店不卖这种书。至于黄惟群勇到最后自己也有点含糊了,恐怕还是受了“茅奖”的影响。其实《繁花》得“茅奖”,是可以用概率论解释的。 概率的分布,虽然不全是,但往往是“各相同性”的。 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同一个时间段之内,所拥有的学养、见识、品味堪称一等的批评家,大略有十位左右。 如果说忽然间就同时拥有了一百位这样的批评家了,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如果组织一个十五人左右的评委,把这十位一等批评家筛选出来,再配上一些必要的局部制衡因素,然后放手让他们按自己的学养、眼光、品位去评,那评出来的结果,虽然也会有争议,但交给历史去评判,应该是“没闲话”的。问题是中国当下不存在这种筛选机制。 中国所使用的这台筛选机,太像一只黑箱,无论你从输入端怎样给它输入满满的正能量,输出端给出的运算结果,总让人觉得它进行的是一次逆淘汰运算。于是就有了六十多人的评委。如果概率分布仍然是各向同性的,那么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其中一等的十位,二等的二十位,三等的三十位。当然,这只是概率论的解释。 向毛主席保证,在我的心目中,现任的六十多位评委都是顶呱呱一等的,如果其中的哪位疑心自己会不会被算在二等或三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若来问我,我只能“不响”。
“小刊”所拥有的相对稳定的作者队伍,仍然保持着基本稳定,大略十几位吧,不过我不拉名单了;万一把哪位名头不大的列上了,却把名头大的漏掉了,那是很没面子的事。这不是圆滑,而是原则,因为咱们是在探讨批评学,不是名单学。 还是只说我最感兴趣的几位。原来的“老戏骨”李国文年事已高,不再期期露面,但今年还是贡献了一篇,写的是鲍照,却稍带着把李白挖苦了一通。 李白的有些行状,确实很像现在的所谓文学活动家,但他的诗是真好,不似现在的活动家只会活动,而且特别擅长于把平平常常的作品活动到高原上去。韩石山、李建军都有多篇文章贡献。 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韩石山讲到了山药蛋派,而李建军讲到了孙犁。韩石山是在一个对青年学子的演讲中谈到这个话题的,他告诫年轻人对老作家要尊重,但不要学他们的写法。 他有一段话是对山药蛋派的分析,也可以说是对这个派的反思或再认识。他的看法是很务实的,我想应能代表山西文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反思或再认识。不过,他也比较滑头,给自己留了余地,说如果你没有充分的自信,这也是一条路,说不定多少年后,还能落个“山药蛋派第八代传人”的美誉。相比之下,河北的文学界对荷花淀派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六七十年前的那个丘陵地带上,没什么长进。李建军是在与汪曾祺的对比中来谈孙犁的,尤其是对他们晚年的作品和思想做了不少有趣的分析,但在文章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荷花淀派”。我能意会,他或许取的是那种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荷花淀派”的观点,因为孙犁自己就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派”。 李建军终归是局外人,认为不存在这么一个派,不提它就完了,但河北文学界恐怕不能一撒手一合眼就完了。有句老话说,人不找事事找人。前不久,河北籍的北京作家付秀莹,出了一部长篇小说《陌上》,那腰封上面头一行大字就给出了定语:荷花淀派传人清丽柔美的韵致”, 只是没像韩石山预测的那样标明是第几代传人,自然也就省略了都是通过谁谁和谁谁才传到她这一代的。 其实《陌上》是一部风格甚至文体都很独特的长篇,很值得批评家们去做一番文本解析。现在没来由就把人家归入荷花淀派,相当于把它放在了丘陵地带上,你是想让人读它,还是不想让人读?
“小刊”也有新作者,其中比较打眼的,一位是《文学报》的前主编陈歆耕,另一位则是“小刊”的前主编任芙康。陈歆耕谈先锋文学的那篇,刊于头条;而任芙康的每期一篇,篇篇都是压卷。陈歆耕谈先锋文学,直接就把“衰败”写在了标题里,他甚至没怎么说凭什么就认定它早已衰败,直接就讲它是怎样衰败的,为什么会衰败。这样的“自由谈”确实不能算十分的严谨缜密,但读起来确实痛快淋漓。任芙康的压卷却是一些小文字,即便是一些骨子里坚硬硌手的文字,也总是往“小”里写。“小刊”上每期都有前主编漫声细语地说几句悄悄话,让人安心,放心。
呀啦索,这就是文学高原。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
段崇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以纵横交错的基本构架,较全面而深入地展示了短篇小说0年的演变过程和深层规律,着力探索了短篇小说的文体演变、艺术规律,重点评述了数十位重要短篇小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