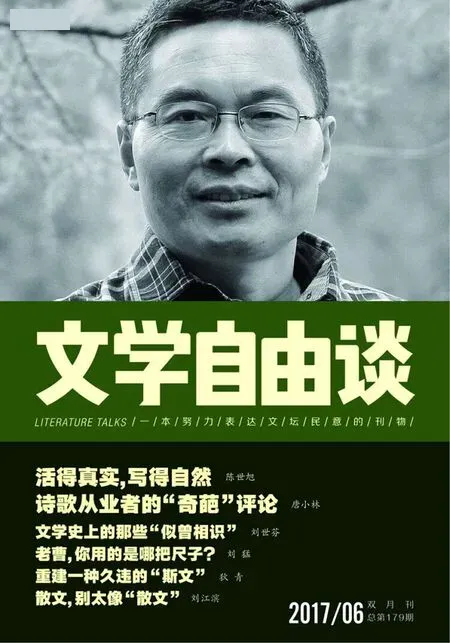重读《水浒》,几点体会
汤 达
重读《水浒》,几点体会
汤 达
1
首先是叙事的速度。古典小说无论中西,速度都比现代小说快。18世纪西方小说,像歌德、克莱斯特、伏尔泰的作品,都是一口气到底,不拖泥带水,不徘徊伤感。现在的小说则喜欢放大,凝视,迟滞,仿佛不如此则不深刻,不能体现出现代性。现代主义讲内在凝视,小说日渐小众,脱离市民阶层,转为精英主义,搞纯小说,玩形式,失去了那股朝气。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强调未来文学的几个价值,其中之一就是快。今天,小说叙事需要回归快,是因为小说要对抗影像文化。优秀的影视作品,两个小时可以讲述一个庞杂的故事,而如今的小说呢?两个小时读个中篇,可能只读到一个婆媳矛盾。
而要想速度快,人物必须多。《水浒》写人,大多未交代前史,比如,武松如何习得一身武艺?宋江可曾考过功名?只字未提。故事讲到某个人物,专注于他的现时,每一个人物专注一段故事,讲完再传给下一个,此间并不补前辍后,保持阅读快感和叙事强度。西方小说追求所谓社会性,强调人物的来龙去脉,全仗人物少,如要写一百零八人,光人物简史,就能让人生厌。
快而不失真,最难。《三国演义》失真了,《说岳全传》之类完全不着调。如何做到?一是靠细节,《水浒》虽快,而细节充盈,相比之下,《三国演义》纯是话本而已。二是情节密集,且出人意料,一波三折,武松打虎那会儿,哨棒偏偏就折断了,读者明知打虎结局,还是忍不住捏上一把汗。三是紧贴人物,不落俗套,不搞脸谱化,亦正亦邪,半魔半神,黑白难分,这样的人物才立得住。
2
其次是童话气质。《水浒》有明确的定位,既然不是世情小说,人物就不要贴近生活,而是要保持距离。整个小说世界都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也是引导。但又不能完全脱离,脱离了就是《西游记》,就是《三国演义》。梁山好汉个个藐视现实人生,豪情满腹,快意生死,但他们生活的环境却是市井的。人物要飞升,环境在下坠,形成天然的张力。如果你真的沉入现实去写,写鸡毛蒜皮,写琐碎人生,就被现实困住了,小家子气,而且效果弄出来,可能还比不上影视的力度。
把人物超脱出来写,考验作者的气势。气势小,写写官场小说,写写今天的类型小说。写水浒,要大气,要草莽之气。读完《水浒》,日常人生之蝇营狗苟,顿时消散,令人大呼畅快。读《史记》与此相同,难怪金圣叹评《水浒》,总是往《史记》上靠。这种气势的铺陈,岂不是高境界?我不爱读《红与黑》,不爱读巴尔扎克,不爱读中国当代的新写实主义,都因为他们气势太小,把人心胸都读小了。
当代不少作家,行文颇受《水浒》影响,但只有阿城意识到心胸这回事。《棋王》的世界,人物实在没有飞升的余地,那就干脆沉入棋局,不假外求,自造豪侠之气,读起来很提神。刘震云的小说,速度也快,人物也多,语言也干净,读完《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畅快完了,还是压抑,就是没有飞升的空间。贾平凹《废都》学古典小说,为什么不像?人物庸俗,而场景超脱,整个搞反了。至于金庸,他是学了《水浒》的,但仅仅学个空壳,文字像那么回事,人物和环境则全是架空的,太飘,超不出类型文学的范畴。
3
长篇小说的经营布局,实在太重要了。《水浒》一出手,就比同时期西方小说高明不少。一个高俅做开局,就不着痕迹地带出王进、史进、林冲一众好汉;而主角宋江,到第十七回才出场。不如此,如何写出一百零八人?西方同时期的流浪汉小说,如今好莱坞的英雄模式,现实主义的家族小说、双线结构,以至今天美剧的多线叙事,面对水浒这样的布局,都要望洋兴叹。
那么,为何现代中国不肯向古典小说学习,一定要学西方?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难度。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难度大于西方小说,因为它非个人化。一点家长里短,写不成中国古典小说,却可以借用西方叙事,完成所谓艺术。现代以来,写长篇小说,三两个主要人物就够了,但中国古典小说不行。以前我也认为西方小说胜在深刻,中国小说骨子里是通俗的。但现在不这样认为。中国小说是极简主义的真宗师。繁复不代表深刻,快和轻不代表浅薄。繁复有时只是为了化解难度,另辟蹊径。文学的最高形态是诗歌,一种最简洁的文学形式。
单凭个人才智,要写出《水浒传》,塑造那么多鲜活的人物,那么多奇崛的故事,难度太大,几近不可能。《红楼梦》是有自身经验做底子的,不可复制,也没法闭门虚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靠的则是历史沉淀。其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经过几代说书人集体创作,且经过无数听众的临场检验,已然定型,好比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糟糕的部分传不下来,写进书中的多是精华。仅凭这一点,《水浒》跟现在的长篇小说就不是一回事。
4
写历史小说,人物最好是正史不载的,如此才有发挥余地;或者是相隔久远的,无从考证,也可以发挥。隔着百十来年,历史人物就不能戏说,只好写家族史。《三国演义》为什么写得不够灵气?因为正史对它还是有所限制。它可以不尊重历史真实,但没办法完全撇开既定的人物关系。徐复观说,小说叙事中情感真实胜过历史真实,如果你写一部关于孙中山的历史小说,情感真实肯定会被历史真实压抑。但如果写《白鹿原》,你就可以放开了,顺着自己的情感和体验来走笔,容易写出个人化的信史。
姚雪垠《李自成》就有这样的遗憾。不光是意识形态问题,主要还是现实主义写法的问题,技术本身的毛病。熊召政的《张居正》、唐浩明的《曾国藩》之类,病症相同。以家族小说的形式写正史人物,强行以小说体裁比附历史研究,既写不成信史,也达不到艺术,有灵气才怪。小说体裁有自身的特点,有它擅长的领域,也有它自身的局限。至于《少年天子》一类小说,跟今天的古装帝王剧有什么区别?找不到小说艺术的定位,就谈不到创新和传世。
那么,用小说写正史人物,有没有成功先例?有。英国作家希拉里·曼特尔写克伦威尔,相距四百多年的人物;三部曲中的头两部《狼厅》《提堂》,蝉联英国布克奖,获得一致好评。作者用的笔法是莎士比亚的,用历史剧的方式处理正史题材,讲究对话和思辨,不以细节取胜,不提供全景图像,但写出来更大气,不戏说,不失真,有诗意,有智趣,是我们中国没有的传统。
用文学写史,需要尊重自己的传统,尊重小说艺术的传统。
5
当然,《水浒》绝非完美。上半部,也就是前三十二回,到花荣落草为止,堪称绝伦。此时主角明确,重点分明。高俅、王进、史进做引子,到鲁智深进入正题。人物虽多,有轻重之分。鲁达写了六回,林冲写了六回,杨志写了四回,武松写了十回,宋江又穿插了好几回。晁盖、柴进等人,来头不小,但故事不奇,都只做伏笔和过渡,充当配角。主次分明、张弛有度,才有节奏可言。下半部就少了许多趣味,要凑一百零八个好汉,凭空要宋江多遭几回罪,一旦住店,必然被绑,必然有人出来相救,不如此,人物如何凑齐?凑出来的人物也很难保证个性充沛,多谋财害命之徒,对宋江的顶礼膜拜也缺少说服力。下半部的看点在李逵、卢俊义,这两个人物顽强支撑着门面。所有人物的轨迹,都要依着既定的故事脉络走,纵使施耐庵本领再高,也不免局促。
伟大的小说多少都会失控,也应该留一点失控的余地。那是小说智慧高于作者智慧的一点灵光。
《壶中书影》(修订版)
曹正文著 文汇出版社
一本评说130位文人奇闻趣事的热销书,增订版添加46篇新作。每篇千字有余,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且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