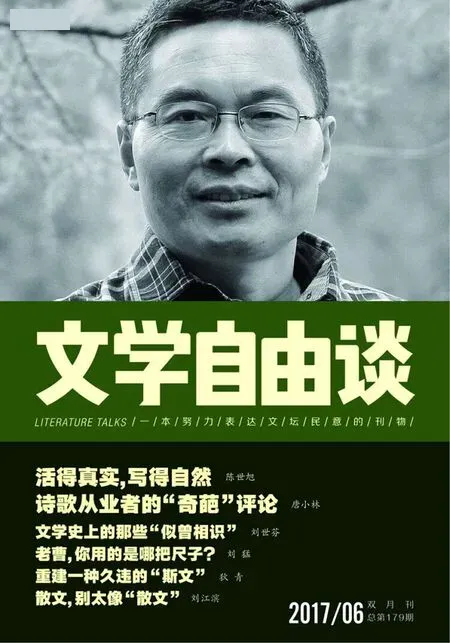小说走到今天
段崇轩
小说走到今天
段崇轩
从新时期文学到多元化时期文学,已走过40年历程。小说作为一种“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形式”(卢卡契)的重量级文体,正面临着困境与突围。刘勰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置身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与转型期,面对广大读者越来越丰富、精微、挑剔的审美需求,小说应该怎样变、怎样写,已然成为一个紧要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学背景下,毕飞宇出版了他的课堂讲稿集《小说课》,让我们眼前一亮、心里一震,引发出诸多思考。
这部不足13万字的讲稿集,解读的都是古今中外经典的作家作品,探索的是小说的深层规律与艺术技巧,作者融理论修养、创作经验与当下文学问题为“一堂”,充分显示出一个睿智、博学、洒脱的小说理论家形象。其实这只是他文学理论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创作谈、访谈录,构成了他颇具规模的小说理论和小说美学。在此之前,毕飞宇在读者心目中,是一个敏锐、聪慧、新潮的小说作者。现在二者重合,呈现出一个更为丰富、通达的学者化作家形象。来自一线创作的艺术感悟和理论思考,往往是鲜活的、珍贵的。我们从毕飞宇的小说理论中,或许可以领悟到小说创作的诸多基本规律,发现当下小说创作出现问题的某些症结,看清小说发展的多条路径吧。
理论与创作,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活动和创造性劳动。有的作家专注于小说创作,不擅长或不喜欢理论,一样写出了独树一帜的优秀作品;有的作家兼顾创作与理论,同样创作出引领潮流的杰出之作。后者有老一代作家中的王蒙、汪曾祺、林斤澜,有中青年作家中的韩少功、王安忆、残雪、马原、格非、毕飞宇等等。一般来说,后一类作家更容易写出具有思想和艺术深度的作品,其创作潜力也会更丰富、长久一些。当然,理论有时也会伤害创作,譬如思想压抑了感觉和感情,理念误导了思维和判断等等。在60后作家中,毕飞宇既对理论感兴趣,也是一位具有创作激情的作家。在他那里,创作与理论互相激发、相辅相成,促使他成为一位备受关注、独领风骚的作家。诚然,在毕飞宇的写作中,偶尔也有议论溢出、理念先行的现象,但总体上可以说瑕不掩瑜。毕飞宇的小说创作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作品以独特、精湛的题材内容,犀利、深邃的思想意蕴,雅致、超然的艺术形式,赢得了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他的短篇小说 《蛐蛐 蛐蛐》《地球上的王家庄》《哺乳期的女人》《是谁在深夜说话》,中篇小说《青衣》《玉米》《玉秀》《玉秧》,长篇小说《平原》《推拿》等,成为颇有影响的作品。毕飞宇的小说理论同样是他文学“双引擎”中不可或缺的一翼。他发表有二十多篇谈生活和写作的“创作谈”短章,四十余篇与编辑、记者、评论家的访谈对话。新近出版的《小说课》,则是他作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课堂上的讲稿集录。创作谈、访谈录、讲课稿,共同构成了他的小说理论成果。他的小说理论是建立在从古到今的经典文学沃土之上的,是生长于他孜孜矻矻的创作实践之中的。尽管他的小说理论还不那么严谨、系统、规范,但它鲜活、现实感强、有价值。
今天的小说发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青年作家特别是80后、90后作家的创作中,有一种“去经典化”思潮。他们疏离甚至摒弃经典文学的传统和经验,热衷于个人的、亲历的、清浅的自由写作模式,导致小说文体变得小、浅、软。我们应当从毕飞宇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中,获得一些新的启迪和经验。
毕飞宇的小说理论的探索和建构,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融合与创新,使毕飞宇走上一条宽阔、坚实的小说之路。从新时期文学迄今的40年间,我们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乃至各种表现方法,轮番使用了一遍,到现在反而觉得山穷水尽,哪一种主义流派都不灵了。其实在今天,哪一种单一的方法和手法,都难以表现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社会人生,只有以宽广的胸怀,融合各种主义、流派,然后形成一种新的手法,才有可能创作出与世道人心相契合的作品来。毕飞宇1991年走上文坛,发表了一批解构、反思历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如《孤岛》《楚水》《叙事》《祖宗》等。这些小说显然吸纳了当时国内的先锋派小说创作手法和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想。虽然写得不错,但仍然是“大路货”。到1995年之后,他开始检讨自己,觉得这种依赖西方“拐杖”的写法难以致远,他要重新寻找自己的路子,从历史回到现实,从想象回到生活。从最开始钟情现代主义而“鄙视”现实主义,到重新认识现实主义,走过了一个艰难的摸索过程。从此之后,他多次谈到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认识。2000年他说:“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的、‘是这样’的那种。我就想看看,‘现实主义’到了我的身上会是一副什么样子。”2006年他说:“我理解的现实主义就两个词:关注和情怀……我指的关注是一种精神向度,对某一事物有所关注,坚决不让自己游移。”2012年他说:“我是一个注重现实性的写作者,我始终在问自己:现实性到底在哪里?我的答案是,在人物的内部。我理解的现实性永远在主体的这一边,而不是相反。”同时,他还多次强调,现实主义就是要表现一日三餐、世态人情,揭示人们所受的“伤害”、内心的“疼痛”、情感中“柔软的部分”。从这些反思和论述中不难看出,毕飞宇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从理念出发看取生活,作家高高在上调度一切的创作弊端,而是把现实主义拉回到了最坚实的地面,最内在的人心上。他汲纳了现实主义关注当下、针砭时弊,直面人生、揭示人的情感“痛点”的现实品格,同时又坚持了现代主义关注个体心灵、人的尊严,赋予普世价值、人文情怀的精神宗旨,形成了一种以现实主义为内容主体、现代主义为精神圭臬的小说之路。2000年之后,他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彩虹》《家事》《青衣》《玉米》《平原》《推拿》等小说,体现了他在创作上的兼容追求,在理论上的不断深化。
执着地探索和营造小说中的形而上世界,使毕飞宇形成了自己丰盈的艺术世界和独特的小说理论。他的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他极善于在形象世界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柳暗花明、山重水复的精神世界来,这后一个世界就是形而上世界。对形而上世界这一课题,毕飞宇似乎没有作过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但他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上已然直抵堂奥。他在《小说课》的作家作品解读中,关注和阐释最多的,也往往是文本中的形而上世界。譬如对《红楼梦》,他说:“……结构相当复杂,但是,它的硬性结构是倒金字塔,从很小的‘色’开始,越写越大,越写越结实,越来越虚无,最终抵达了‘空’。 ”譬如对《故乡》,他说:“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譬如对汪曾祺《受戒》,他说:“小说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鸟类欢快的飞翔,还有伤感的天空,它无边无际。”譬如对蒲松龄《促织》,他说:“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毕飞宇有一种敏锐而精准的艺术直觉和理性直觉,他能从文本有形的形象世界中,看到隐含在其中的无形的精神世界,如作品的情调、思想、格局、境界等等,并分析出作家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法,创造了这样的艺术至境。
小说作为一种文字组成的有机的艺术生命体,它是由有形的形象世界和无形的精神世界水乳交融的。但我们历来对有形的形象世界研究甚多,而对无形的精神世界探索较少,以致后者成为一片“神秘的星空”。在小说形而上世界这个课题上,中外一些作家和理论家,也曾发表过一些精辟见解,而较为系统、深入论述的是波兰哲学家、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他在代表作《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把文学文本分成语言层、图式化外观层、意义层、意象层四个层次,说:“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表现出形而上学性质才达到它的顶峰。然而那种独特的艺术性却全靠文学艺术作品中完成这种表现的方式。”他所划分的文本的第三、第四两个层面就属于形而上世界。文学作品的构成犹如一个社会,既有经济基础、又有上层建筑;如同一个人,有形的是他的肉体形貌,无形的是他的灵魂精神。由物象到精神、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人事才上升到人类的普遍境遇,作品中的微观世界才升华为宏观世界的隐喻和象征;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正在后者之中。而文学作品的形而上世界,又是复杂、微妙、混沌的,它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丰富、独特的感性形象,如环境描写、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这都是有形的物象,但一经作家心灵的孕育,就散发出独有的光彩;二是新颖、深广的理性内涵,如主题思想、哲理意蕴、价值观念等;三是开阔、超拔的审美境界,如生命体验、艺术风格、精神气象等。毕飞宇在经典作品解读中,突出地阐释了文本中的形而上世界,在创作实践中,又营造了一个个鲜活而深远的精神世界。我们在读他的 《武松打虎》《彩虹》《虚构》《孤岛》《青衣》《平原》 等作品时,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他真诚的情感、激越的思想和超然的审美境界。
努力把握和运用小说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方式,使毕飞宇真正深入了小说的深层和肌理,形成了一种多元多态、自成一家的小说艺术理论和创作经验。进入21世纪的小说艺术,在内容、思想、形式、手法等发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更高、更细、更严的要求,这就需要在继承融合各种主义流派乃至新文体的精华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新的小说之路。但当下的现状是,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探索,似乎停止了脚步,部分中老年作家坚守在传统现实主义的“堡垒”中,不再汲纳新的东西,不再思考怎样创新,一些青年作家则疏离和丢弃了经典文学传统和经验,在自造的文学小天地中自娱自乐。正是在文学的继承和创新上,毕飞宇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当他真正认识了现实主义的强劲生命力的时候,他老老实实地遵循小说的基本规律,编织故事情节,描绘典型环境,刻画人物形象,营造文本结构,使小说建立在一种坚实的根基上。同时他又纯熟地运用现代主义形式和手法,譬如象征、变形、荒诞等技巧,这是他惯用的艺术方法;他还擅长创造一种悠远、诗意的艺术意境,喜欢赋予作品一种睿智、深刻的哲理内涵,致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浓郁的现代品格。他在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言上也是苦心经营的。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叙述视角都是围绕“我”“你”“他”三种形式展开的。毕飞宇认为,常用的“我”和“他”两种视角,都有自身的局限,经过精心探索,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第二’人称”。他说:“这个‘第二’人称却不是‘第二人称’。简单地说,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的平均值。”这种重合式的叙述视角,规避了原有的局限,可以更加贴近生活和人物,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他特别重视小说的叙事语言,认为语言绝不是作家手里的工具,而是整个主体的外化。他的小说语言以叙事为主体,把描写化入叙事中,使叙述形象化,整个叙事语言优雅、抒情、机智、柔美、凝重。“轻柔而凝重”既是他的语言个性,也是他的小说风格。
小说永远是一种生长的艺术,它只有不断地吸纳时代精神、经典精华、作家创新,才能蓬勃地成长起来。毕飞宇作为60后中的优秀作家,他的小说理论和创作经验,蕴含了一代作家的艰难探索和坚实脚印,昭示了中国小说通向未来的一种路径,值得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