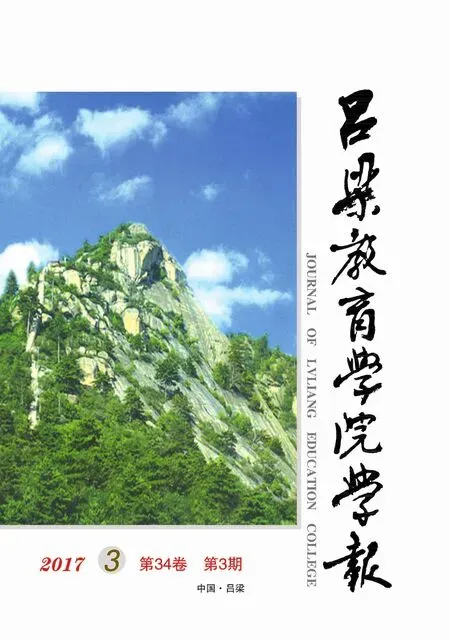规范视阈下的主观罪过
陈文昊,郭自力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理论研究】
规范视阈下的主观罪过
陈文昊,郭自力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传统理论认为我国《刑法》第14条中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系独立要素,以此构建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双重标准体系。但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罪过体系存在各种问题:无法周延心神丧失者主观罪过、强调意志因素悖离实践、不当增加证明成本、不当扩大故意的成立范围。因此,应当从规范的角度理解罪过形态,将意志因素从主观心态中剔除,并以一般人的标准重构认识因素,将低于一般人标准的认识水平者统一以一般标准加以评价。在此意义上,应当将我国《刑法》第14条中的“意志因素”解释为对行为的意志。
认识因素;意志因素;规范论
一、问题意识
我国传统理论在主观罪过问题的处理上,往往是基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双重标准展开的。例如,将直接故意锁定为“明知”的认识因素以及“希望”的意志因素,将间接故意锁定为“明知可能”的认识因素以及“放任”的意志因素。这种理解其实是将我国《刑法》第14条中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与“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作为相互独立的两组因素看待,在此基础之上探讨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界分问题。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常常会出现认识因素接近于直接故意、意志因素接近于间接故意抑或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如何确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存在疑问的。例如,行为人想杀死仇人,就从化学实验室偷回了一瓶不确定是否有毒的药品掺入被害人的饮料之中,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对这种药品的认识程度仅限于“可能造成危害结果”,但在意志因素上却是“希望”被害人死亡。再如,行为人在妻子的碗中掺入毒药,并看见妻子与其子分食,行为人明知这种毒药必然会造成妻子和孩子一起死亡,但在意志因素上为了避免事发,只得放任妻子被毒死。在这两种情况下,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像是两架马车驶向了不同的方向,结论令人莫衷一是。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认识因素还是意志因素作为确立主观罪过的标准呢?一般认为,认识是在意志的支配下实现的,因此,在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对立之中,起到主导地位的是意志因素,它决定了结果的发生。[1]并且,主流观点对我国《刑法》第14条的解读也是认为其采用了“容认说”,也就是说,行为人容许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就成立故意,这显然是偏重于对意志因素的把握。可以说,我国在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上采取的是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双重标准说。但是随着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和相关案件的涌现,现有学说的弊病及其与司法实践的脱节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二、通说标准的缺陷清算
以意志因素为核心展开的主观罪过评价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分侧重于事实层面的评价。因为行为人“意欲如何”,显然是一个事实的认定问题,这一事实评价的存在也同时锁住了认识因素的规范评价的可能性,使得主观罪过沦为单纯的事实问题,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不自洽
心神丧失者是否具有故意?对于从事实层面上理解主观罪过的观点来说,这一问题是切中要害的。根据通说的观点,责任能力并非责任的前提,而是与主观罪过相并列的责任要素。[2]这就意味着,精神病人、未达责任年龄者之所以不予处罚,不是因为其不具有责任的故意,而是因为责任能力的阙如。也就是说,即使是心神丧失者,也具备主观罪过。
但是,心神丧失者在当时的情境下并不具备辨认、控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认为其具有故意所需要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呢?这显然是存在疑问的。例如,行为人在酒醉状态下驾驶机动车的,不可能具有事实上的认识因素或者意志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危险驾驶罪所需的故意难以认定。再如,行为人处于酒醉状态之下实施抢劫的,并不具有事实上的认识因素或意志因素,由于抢劫罪不存在过失的犯罪形态,只得按照无罪处理,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当。由此可见,试图从事实层面理解心神丧失者故意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
司法实践中对心神丧失者的犯罪行为一般以故意犯论处。例如,以下的甄建平故意杀人案、徐守荣强奸案、贺某抢劫案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2012年7月22日14时许,被告人甄建平酒后遇见社区治保主任周某(男,殁年54岁),被害人见被告人醉酒便劝其回家,二人发生口角。被告人取来两把尖刀,不顾群众劝阻,猛刺周某胸部、腰部等处数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甄建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141号
2013年5月12日中午,被告人徐守荣在饮酒后,驾驶三轮摩托车在街上游荡,突然看见被害人许某(女,殁年7岁)独自在路上行走,即停车强行将其摁入三轮摩托车后斗内,驾车至一荒地上将被害人奸淫。后徐守荣害怕行径被人发现,遂起杀人灭口之心,就用石头将被害人砸死。法院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徐守荣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徐守荣有期徒刑八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4)鲁刑二复字第9号
2015年1月17日3时许,被告人贺某在酒后向被害人讨烟未果,见被害人口袋有50元现金和手机,就用言语胁迫的方式从被害人处抢得人民币50元、白色手机一部,后被告人将该部手机卖给李某乙,赃款挥霍。法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15)宁刑终字第166号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在心神丧失状态下实施犯罪并不影响犯罪故意的成立,倘若从事实层面理解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并不能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二)不妥当
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双重标准说在很多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具有妥当性,难以为一般公众所接受。例如,一个无知的人,想要剖开别人的脑袋一探究竟,他不知道这种行为会导致他人死亡,也不意欲杀人只是想“一探究竟”。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行为人成立故意杀人罪呢?
如果强调故意的意志因素,以上的案例的被告人可能并不能认定为直接故意,甚至可能不成立故意。因为仅凭“不意欲杀人”这一措辞,似乎就可以阻却被告人的故意心态,但这样的结论难以为一般人所接受。其实,从心理学上讲,“意欲”本身就是与动机相缠混的一个概念,例如,行为人以致命手段伤害他人是为了劫取财物,在此期间并没有想造成他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能否就此认为“劫取财物”的意志因素可以阻却故意杀人的意志因素了呢?或者说,如果行为人辩解说:“我只是为了劫取财物才施加致命的伤害行为,并不想杀死他”,能否就此否定行为人的故意呢?结论恐怕是否定的。司法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案例,以潘某故意杀人案为例:
潘某系农民,与妻子廖某育有一女儿,潘某想再与廖某生一个儿子,廖某坚决反对,并私下去医院植入节育环。1998年8月,潘某知道此事以后,与廖某发生争吵,大喊要取出节育环。一怒之下,被告人将廖某按到在床上,用杀猪刀剖开廖某腹部,并翻找节育环,导致廖某当场死亡。事后,潘某一直声称其“生活在偏僻山区、没有文化,不懂医学知识”。[3]
本案中,愚昧无知的行为人潘某可能切实地没有认识到其行为会导致被害人的死亡,也并未有过将被害人置于死地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放任”的主观心态其实并不妥当。因此,仅从纯粹事实的角度考察,就不能认为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甚至连故意也难以证立。
司法实践中,有人杀人是为了践行迷信,有人投毒是为了检验药性,有人放火是为了寻求刺激,这些情况下,“不知道”或者“不意欲”显然不可以成为故意的阻却事由。在日常生活中,谁坚持“一公斤铁重于一公斤棉花”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错误悖谬,谁就立刻面临遭受自然惩罚的危险。[4]同样,谁不服从科学规律行事,必然会给自己带来自然的惩罚,一所不符合静力学的房子很快就会倒塌。[5]如果坚持事实层面的“不知道”或者“不意欲”可以抹煞行为人的主观意图,那么“无知”就是作为给行为人的惠赐,但这未免过于奢侈。
(三)不经济
成本-收益分析在法律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为识别、量化和比较某一法律的成本、收益提供了系统分析框架。[6]将一个犯罪人以刑法绳之以法,会对潜在的犯罪人产生威慑作用,从而激励犯罪分子减少在非法活动中投入的时间,或者选择不进入非法活动市场,进而起到降低犯罪率的作用,这便是惩罚一个犯罪人所得的收益。但是另一方面,从立案、侦查阶段,到起诉、审判阶段,再到执行阶段,这一流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与社会成本,例如,根据实证统计,仅就执行成本而言,关押一个罪犯的年费用高达7266元,相当于一个大学生的年开销;另外,我国目前,监狱基本设施项目支出30多亿,数目十分可观。[7]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惩罚一个罪犯所得的社会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将一个行为人送入形式轨道才具有正效应。雅各布斯教授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并主张将刑罚作为没有其他制裁措施的最后手段,例如对于性犯罪人而言,如果在医学上成功地研制出了可以医治他的处方以后,就可以考虑对他免除刑事责任,这其中便体现出鲜明的成本-收益考量。
在所有的犯罪治理成本中,取证成本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因此,现代刑法致力于将取证成本尽可能地降低到一定的范畴之内,以保证刑事诉讼系统的经济性,而对事实证明的着力过猛显然与这一旨趣相悖离。实际上,对主观要素取证需要花费的成本更大。例如,一把插入被害人后背的刀足以证明作案的手段;一段完整记录投毒过程的视频足以证明故意杀人的客观要件。但是,试图证明行为人主观要件中的认识因素抑或意志因素需要依赖于更多的客观证据,例如,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日里是否存在积怨,行为人对药物致死过程的了解程度,在取证上都需要大费周章。在主观罪过的证明上,过分依赖于事实认定显然有欠经济性的考虑。
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无法通过客观证据链得到周延证明,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实践中将被告人口供奉为圭臬的做法。从心理学上来看,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是一种瞬息万变的要素,时而汹涌澎湃,时而捉摸不定,有时顿起杀意,而后幡然悔悟,这种情况下,试图通过客观证据加以周延的尝试只能以失败告终。在这点上,劳东燕教授的评价可谓切中要害:“将意志因素作为界定故意的标准,容易导致对被告人口供的依赖,在刑讯逼供沉疴难治的今天,这种做法无疑与刑事法治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8]
(四)不谦抑
过分倚赖于意志因素的做法也可能导致直接故意认定上的泛滥。“意欲他人死亡”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被归于一种基于“死亡本能”的潜意识体现,如果这种潜意识偶然地进入了意识的层面,能否就此认定行为人的直接故意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在著名的“雷击案”中*大致案情为:行为人意欲被害人被雷劈死,因此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劝诱被害人去跑步,被害人果然被雷劈死。,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会赞同不将被害人死亡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结论。在另一起案例中,行为人经过精密的测量预知某时某地方会发生雷击,而使被害人在此等候的,多数学者会认为行为人故意杀人罪成立。但是,如果将两个案例加以对比会发现,两个案例中的行为人都是“意欲被害人死亡”,在意志因素相弥合情况下,何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金德教授也举出了一个类似的例子:丈夫劝说妻子乘坐火车,他希望发生火车事故,意欲妻子死亡;后来火车真的发生了事故,造成妻子的死亡。在这个例子中,丈夫没有认识到可借以作出有足够可能性的结果预测的事实情状,因而不成立故意。但是,如果丈夫知道有恐怖分子计划在这辆列车上实施爆炸而劝说妻子乘坐火车的,就可以肯定成立必要的故意了。[9]
由此可见,无论是“雷击案”这组案例中,抑或是金德教授所举的一组案例中,起到区分的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意志因素,而是认识程度的不同。过分倚重于行为人“意欲如何”,很容易就走入主观归罪的危险领域。例如,行为人与被害人积怨已久,常常扬言要杀了被害人,在一次争斗中,行为人推了被害人一把,被害人脚下一滑,倒在地上死亡。这种情况下,如果从“二人积怨已久”的客观事实推定行为人具有故意杀人的意志因素,很有可能得出行为人具有直接故意的结论,但这显然不当。受到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判断体系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倚重“有无积怨”的考察,在有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合理的判决,以李术川犯故意杀人罪为例:
李术川与被害人李某甲系同母异父兄弟,二人长期因林地权属、边界等问题存在纠纷并存有积怨。2015年3月7日10时许,二人又发生口角,继而引发相互抓扯、殴打,李术川因面部、裆部被抓扯,并担心李某甲还会伤害自己,于是捡起砖块连续多次砸向李某甲面部,致李某甲死亡。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李术川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雅刑初字第13号
本案判决中似乎暗含着这样的逻辑暗线:行为人与被告人积怨极深,因此行为人有杀人的意志因素,因此行为人故意杀人罪成立。但是,这种结论的得出似乎过于简单,在双方的扭打中,行为人捡起砖块击打被害人实属应激的反抗行为,而且根据一般人的观念出发,用砖块击打面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致人死亡的盖然性,其实是存在疑问的。由此可见,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双重标准说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做了不当的评价。
三、规范上的罪过体系重构
立足于事实判断的、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双重标准说存在不自洽、不妥当、不经济、不谦抑等种种缺陷,因此需要对罪过形态的认定标准进行规范上的彻底改造。不得不提的是,意志因素是在规范上评价主观罪过的最大障碍,因为意志因素只能是存在论上的,换言之,行为人“意欲如何”只有可能从事实上进行界定。例如,行为人希望、放任结果的发生,抑或是排斥、抵触结果的出现,都需要通过个案进行具体的判断,只能从事实层面上进行考察。所以,在规范罪过体系的构建进路上,第一步就是将意志因素从主观要件中剪除,在此之后,就要将事实上的认识因素通过一般人的评价机制转变为规范上的评价标准。
(一)意志因素的剪除
如上文所述,对意志因素的过分倚重导致了逻辑的不自洽,以及司法实践中的不协调。那么,能否将意志因素彻底从主观的评价之中剔除出去呢?笔者对此采肯定回答。
首先,从“故意”概念的设立初衷来说,就没有将意志因素包容在内。《尚书·财传》曰:“故者,知而故犯也。过者,不知而误犯”。张斐在《注律表》中也指出,“其知而犯之谓故”。由此可见,最早的故意是以“知”为核心的,至于是否“意欲”,并不影响故意的认定。无独有偶的是,西方理论中的“故意”最早也以认识因素为核心展开。在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结果归责的消弭、主观要素的出现,都是旨在限制古代刑法中的株连与连带,因此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有所认识为必要条件。在罗马法时期,对故意责任的认定就是以行为人对结果有无预见为标准的。[10]
其次,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说,“知”本身就对“欲”起到了牵引的作用。例如,行为人想割断仇人的攀山绳使其坠崖身亡,但他突然发现,绳子的另一端还拉着行为人的朋友和世交甲,如果割断绳索,甲也会一同摔死。两相权衡之下,行为人还是割断绳索,导致仇人连同甲一起摔下山崖。本案中,行为人对仇人的主观罪过系直接故意,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在于,行为人对甲的主观心态如何评价呢?如果仅仅着眼于意志因素,就会陷入逻辑的泥潭无法自拔。诚然,行为人与甲系朋友、世交的关系,行为人在割断绳子之时可能热泪盈眶、依依不舍,但能否就此认为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系间接故意甚至是过失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对这份友情与世交加以评价,可以说是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但刑法的评价对象恰恰并非这份友情或世交,而是行为人在确信会导致甲死亡的情况下割断绳索的行为,因此,刑法不能仅凭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行为人的罪过做降格评价。
最后,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理论嬗变来看,均有向认识因素倚重的趋势。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间接故意”,英美法系中的“轻率”(recklessness)是以认识因素为基准的。这就意味着,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具有“实质而不合理的风险”(substantial and unjustifiable risk),却不顾风险实施特定行为,就可以认定为“轻率”的罪过形式。例如,在一起案件中,被告人Parkers使用公用电话时因为与他人发生争吵,在盛怒之下摔下电话导致听筒损坏的,法庭适用轻率对被告人按照故意毁坏财物定罪。[11]由此可见,英美法系中的轻率作为一种主观心态,与故意的区分就在于对风险的认识程度不同。
德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对于“故意”的立场,近年以来也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向。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同意”不再被理解为符合行为人的期望,而是“尽管具有特别的危险性且不能信赖运气,但行为人仍然实施该计划,将所认识到的危险交由运气支配时,就成立同意”。质言之,“同意”仅仅表明行为人算计了可能的结果,并在此范围内接受了这样的结果。[12]
综上所述,将意志因素从主观要素的队列之中“驱逐出去”并不存在过多的障碍;以认识因素征表行为人的意志倾向,是规范罪过理论体系构建的必然道路。
(二)认识因素的规范化重构
意志因素的剪除意味着对客观事实的第一步弱化,但是仍然无法解决行为人在确实无知的情况下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况。例如上文所举的潘某故意杀人案中,如果潘某在事实上确确实实地没有认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影响故意的成立呢?
规范论对此的回应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脑袋无法经受剧烈的打击,他就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他不能充分保护自己的脑袋;再如,如果一个人认为2加3等于4或6,他的日常计划就会失败。[13]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应当认识到的内容,就应当对这种不具有正当理由的“没有认识”答责。例如,行为人在足球场看一场比赛,行为人激动地用力摔出了手中的啤酒瓶,在摔出啤酒瓶之后,行为人才意识到会伤人,于是,他大声喊叫“啤酒瓶”,结果砸中一名观众并致其死亡。而在两个月以前,这个球迷在另一个球场上扔出的啤酒瓶曾砸伤了一位观众。那么,这个球迷这次的行为就不是过失致人死亡,而是故意杀人,尽管行为人在摔出啤酒瓶时没有认识到会砸死他人。但这种认识阙如,完全不具有任何理性的根据,是必须完全由行为人负责消除的没有认识。严格地说,这种没有认识其实不是行为人“没有认识”,而是行为人“不想认识”,只要稍微关心一下他人的生命就能避免结果的发生。
因此,规范论的视阈之下,评价的重点并不是行为人“是否认识”,而是行为人“应当认识”。如果从一般人的视角出发,一个行为具有造成危害结果的极高的盖然性,并且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就应当被认定为直接故意。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就不得将“没有认识”作为阻却故意的挡箭牌,因为行为人的社会角色赋予了其必要的认识义务。同样的道理,如果在社会一般人看来,一个行为具有造成危害结果的高度盖然性,并且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就可以认定故意的成立;如果社会一般人认为一种行为具有造成危险结果的相当盖然性,并且行为人实施了该行为,就应当认定行为人至少具有过失。
到此为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存在论与规范论视阈下的罪过体系之间的差异。将以意志因素为核心展开的主观罪过评价体系通过公式表现出来,可以写作以下形式:
1.直接故意=明知+希望
2.间接故意=明知可能+放任
3.轻信过失=明知可能+否定
4.疏忽过失=应当知道而不知
而规范视阈下的罪过评价机制可以拆分为以下公式:
1.直接故意=一般人看来极高盖然性+实施该行为
2.间接故意=一般人看来高度盖然性+实施该行为
3.过失=一般人看来相当盖然性+实施该行为
将以上的两组公式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存在论与规范论两种视角下罪过体系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轻信过失这三种罪过上。这三种罪过形式在传统理论中都需要以行为人的事实上的“认识”为要件,因此,惩罚这三种罪过下行为人的依据就落脚于行为人在明知危害结果的情况下仍然实施一定的行为,也就是“明知故犯”。但是,规范论的视阈下,处罚的范围发生了进一步的扩容。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一般人看来具有一定盖然性的行为,不管其主观状态如何,都不影响特定罪过形态的认定。因此,规范的主观罪过体系下,处罚行为人的依据就变成了“明知故犯”,以及“应知而不知”。可以说,在社会风险泛滥、犯罪行为延烧的现代社会,对“应知而不知”进行归责与惩罚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三)一般人标准的构建
在整个规范的罪过体系之中,处于最核心位置的显然就是“一般人标准”的问题。按照一般预防的社会需要来确定罪责,弱化行为人个体的能力的考量,是整个规范评价体系的核心。[14]
首先,如果行为人的认知标准低于一般人应当的认知标准,那么即使他不具有事实上的认识,也存在可非难的罪过。上文提到的精神病人、未成年人、醉态者,即使没有事实上的认识因素,但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准评价之,就可以认为其具有相应罪过。例如,在一般人看来,“用刀刺杀”具有极高的导致他人死亡的盖然性,“向他人扔砸石子”具有相当的导致他人死亡的盖然性。因此,精神病人用刀刺杀被害人的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精神病人向他人扔砸石子导致他人死亡的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的构成要件。之所以做这样的差异化处理,并不是因为精神病人在前者的场合认识到了危害结果,在后者的场合没有认识到危害结果,而是特定行为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盖然性不同。
并且,即使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低于一般水平,也不能通过反证其不具有认识从而推翻故意的认定。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在行为人的认知能力低于一般水平的场合,对行为人主观罪过的认定并非一种推定,而是一种不可推翻的规范评价,这种规范评价无需证据证明,也不可以被反证推翻。
其次,当行为人的认知能力高于一般人的场合,应当如何界定这里的“一般人”呢?是理解为“社会的一般人”,还是“与行为人处于相同地位的一般人”呢?更近一步说,在规范的罪过体系中,每个人格体必须在任何时候激活一切能力吗?还是允许他能力的休眠呢?
在笔者来看,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讨论。第一,在作为与不作为的场合,结论可能就有所不同。例如,在雅各布斯教授所举的著名的“毒蘑菇案”中*大致案情为:一个生物系的大学生,作为临时的餐馆服务员,当他端着一盘异域菜品,他发现一株有毒植物,但不动声色地端给客人,能否归责于他呢?,客人的死亡结果显然不应当归责于行为人的不作为。但是,换一种场景来看,倘若作为生物系大学生的行为人发现了餐厅后院有几颗“毒蘑菇”而将其掺入菜肴之中的,结论恐怕就是行为人具有故意了。换言之,在前一种不作为的场合,还是以“社会一般人”的标尺来衡量行为人应然的认知水平的,因为从社会一般人来看,“食用蘑菇”并不具有相当的危险性,从而阻却了行为人的罪过。而在后一种作为的场合,是以“与行为人处于相同地位的一般人”标准来约束行为人的主观的。因为在一个生物系大学生来看,这种“毒蘑菇”导致他人死亡的盖然性几乎接近于100%,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肯定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成立。由此可见,在作为与不作为的场合,基于作为犯对结果支配性更强的缘故,“一般人”的含义是不同的。
第二,行为人的社会角色也影响到了“一般人”的界定。正如雅各布斯教授指出的,需要区分“能力”与“角色”的不同意涵。“一种特别的知识,不属于角色,不属于构造人格体的物质,因此,没有必要为了避免损害调动这种能力。因为人格体都是按照‘当为’而非‘能够’展开的”。[15]还是以“毒蘑菇案”为例加以说明,如果客人中毒死亡的结果不应当归于这名大学生,那么应该归于谁呢?显然是选购食材的采购员以及负责料理的厨师。这是因为,采购员以及厨师承担者保障客人饮食安全的特殊社会角色,因此在“一般人”的确定上,就应当锁定为高于一般人的采购员或者厨师的行业标准。
总结而言,规范罪过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将低于一般社会公众认知水平的行为人适用一般人标准,从而纳入犯罪圈之中调整。而对于高于社会一般人认知水平的行为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量行为范式、社会角色等因素,对“一般人”的外延加以界定,不可一概而论。
四、规范上的罪过体系在我国的展开
规范的罪过体系需要在我国《刑法》的框架之下加以审视,并且对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解决有所裨益。
(一)对于我国《刑法》第14条的解读
传统理论对于我国《刑法》14条的理解往往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与“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作为两个独立的要素加以分析,用公式表达的话,可以表述为:
故意=认识因素+意志因素
进一步又可以拆分为两个公式:
1.直接故意=明知+希望
2.间接故意=明知可能+放任
但是如上文所述,规范的罪过体系需要对意志因素从主观要件中裁剪出去,因此,在对《刑法》第14条的理解上,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笔者认为,劳东燕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将《刑法》第14条的结果理解为抽象的法益侵害结果是妥当的。具体而言,可以在承认故意的行为犯的基础之上,将《刑法》第14条的结果理解为由行为造成的抽象化的结果,[16]这样一来,传统理论中对“结果”的希望或放任就转变为对“行为”的希望或放任。也就是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可以理解为“希望或者放任危险行为”。倘若做这样的理解,“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要件在实践中就变得不具有实际意义了。
将意志因素从主观要件中剔除之后,就需要对认识因素做规范化的理解了。在这里,“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从应然的层面加以阐释,也就是应当解释为“应当明知自己的行为有发生社会结果的高度盖然性”或“在一般人看来有发生社会结果的高度盖然性”。实际上,我国《刑法》条文中的“明知”不可以一律理解为事实上的知道,在很多情况下都应当从“应当知道”的角度加以阐释,我国《刑法》第301条包庇罪中对“犯罪的人”要求的“明知”就是如此。例如,行为人为一个神色匆匆的、没有身份信息的人提供了住所,即使其没有在事实层面认识到行为人是“犯罪的人”,也不影响包庇罪中“明知”的成立。这是因为,看到一个神色匆匆的、没有身份信息的人要求提供住宿,却没有认识到他可能是“犯罪的人”,这本来就不具有被社会宽恕的正当理由,因此,《刑法》第301条包庇罪中对“犯罪的人”要求的“明知”应当理解为“应当知道”。《刑法》分则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表明,“明知”一词在理解上不可以做狭隘、简单的事实层面的解读。
(二)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例分析
规范的罪过理论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多疑难案件的解决有所裨益,这不仅体现在规范评价使得举证上的负担有所减轻,而且表现为剔除意志因素之后只需单纯考虑规范上的认识因素,因而更加简便易行。下面以蒋勇等过失致人死亡罪与孙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例进行剖析:
1.蒋勇等过失致人死亡罪
2005年8月13日,被告人蒋勇、李刚驾车与徐维勤的农用车相遇,双方为让道问题发生口角,并开始下车扭打。尔后,蒋勇、李刚欲驾车离开现场,被害人徐维勤拉住被告人的农用车前方反光镜不让离开。蒋勇驾车以每小时20公里的时速前行,车上的李刚为了阻止被害人上车,将被害人的双手沿着护栏搬开,被害人失控倒下,被车后轮当场轧死。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蒋勇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判处李刚有期徒刑3年零六个月。[17]
其实,类似这种“驾车拖拽致死”的案例在我国并不罕见,但最终认定的罪名与处断刑相差很大:
1996年6月18日,被告人王征宇驾驶轿车,前方的执勤民警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王征宇急着赶路并没有停车,并保持每小时100公里的行驶速度,连续驶过两道关卡。执勤民警得知情况后,即设路障拦截王征宇,民警陆卫涛站在路障旁,并开照明设备指示。被告人王征宇看到这一情况仍不停车,驾车冲向路障,导致陆卫涛当场死亡。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8]
2008年12月4日,被告人杨春驾驶货车到被害人吴某的店里送货,二人发生口角。后杨春欲离开,吴某抓住副驾驶车门和车厢挡板阻止其离开。张春见状仍驾车低速行驶,在路口转弯时导致吴某跌倒,遭后轮碾压致死。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4年。[19]
对比以上三个案例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驾车拖拽致死”这类案例的把握还是界限分明的。从规范的角度来看,三个案件主观罪过认定的关键就在于一般人严重导致实害结果的盖然性。可以发现,三起案例中唯一认定为故意的王征宇案中,被告人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强行冲撞障碍物,这种行为在一般人看来造成危害结果的盖然性极高。而在另外两起案件中,行为人都是在慢速前行的情况下导致他人死亡的,因而造成危害结果的盖然性要比王征宇案低得多,考虑到这一点,这两起案件不仅在罪过上被认定为过失,而且在处断刑上不能与王征宇案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按照传统理论中以意志因素为核心的双重标准,那么三起案件中的意志因素并不容易区分,因为三起案件中的被告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都是抱着“无所谓”、“冷漠”、“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何以区分三者的主观心态呢?想来是存在疑问的。
2.孙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008年12月14日,被告人孙某大量饮酒后驾车,先是撞上一辆比亚迪轿车车尾。在此之后,被告人继续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先后与4辆轿车相撞,造成四人死亡、一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5万余元。经鉴定,被告人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的瞬间速度达到每小时134-138公里。最终,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行为人无期徒刑。
本案中,司法机关面临的最大障碍是被告人饮酒的问题,从事实上来看,行为人在醉酒的状态之下缺乏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仅凭这一点能否否定行为人的故意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笔者看来,与其在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之中缠混地评价罪过,不如从规范的角度评价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正如上文所述,在司法实践中,醉酒状态并不影响故意与过失的认定,只要行为人的危险行为在一般人来看具有极高的盖然性,就可以认定为直接故意。从这样的进路切入本案可以发现,孙某以每小时134-138公里速度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显然符合故意的外观,在这种情况下,将被告人的行为评价为直接故意是不存在问题的。
五、结语——规范论引发的反思
正如周光权教授指出的,20世纪以来刑法学的核心问题最终成了如何处理事实和价值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承认“眼见未必为实”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如何进行规范评价的问题。[20]近年以来,规范论对刑法体系的渗透已经呈愈演愈烈的态势。价值判断方法一方面承认罪刑法定原则、责任主义原则,肯定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另一方面,能够通过价值判断,为德日犯罪论体系的认定提供实质根据,减少处罚上的漏洞,贯通李斯特所称的“刑法与形势政策”鸿沟。正如雅各布斯指出的:目的论者认为立法者和刑法科学本身存在逻辑上的客观联系,我们见证了建立于本体论之上的刑法教义学的没落。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规范论的体系构架中存在诸多的问题,在接受上必须采取审慎态度。显然,极端价值判断的越位可能导致对事实的忽视,将人完全作为工具进行评价。例如过于强调国家规范的权威性,这也正是雅各布斯“敌人刑法”遭到广泛批判的原因。诚然,古典的犯罪体系已然在新的哲学思潮被鲸吞蚕食,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解读也由千人一面走向言人人殊。规范论高举“眼见未必为实”的大旗,将传统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废墟踩在脚下,在此背景下,传统刑法理论的涅槃与重生势在必行。我们应当做的是顺应形势,规避风险,转“危机”为“机遇”,这才是距离正义最近的选择。
[1]周光权.刑法总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3.
[2]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制出版社,2011:279.
[3]李兰英.间接故意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204.
[4]冯军.刑法的规范化诠释[J].法商研究,2005(6):63.
[5][德]京特·雅各布斯.行为责任刑法——机能性描述[M].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8.
[6]周林彬.法律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3.
[7]李赓.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3:13.
[8]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79.
[9][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犯罪构造中的主观构成要件——及对客观归属学说的批判[J].蔡桂生译,刑事法评论,2012(30):202.
[10]蔡墩铭.唐律与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M].台北:汉苑出版社,2976:156.
[11]刘士心.美国刑法中的犯罪论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7.
[12]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5-186.
[13][德]京特·雅各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M].冯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7.
[14][德]罗克辛.构建刑法体系的思考[J].蔡桂生,译.中外法学,2010(1):21.
[15][德]京特·雅各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M].冯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89.
[16]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8.
[17]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80.
[18]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53.
[19]陈兴良,张军,胡云腾.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19.
[20]周光权.价值判断与中国刑法学知识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4):126.
[21]周光权.价值判断与中国刑法学知识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4):126.
2017-08-12
陈文昊(1992-),男,江苏镇江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郭自力(1955-),男,河南焦作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刑法。
D924.1
A
1672-2086(2017)03-0044-07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