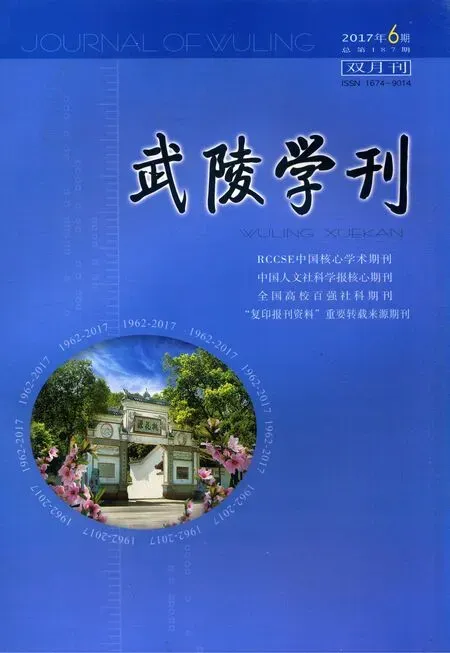适应与过渡: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析论
段锐超
(陕西理工大学 图书馆,陕西 汉中 723000)
适应与过渡: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析论
段锐超
(陕西理工大学 图书馆,陕西 汉中 723000)
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是一种特殊任官制度,包括世袭刺史、世袭郡守及世袭县令等三种形式。这一制度的实施,分别有优容权臣以达成暂时平衡、笼络边酋以借力守边以及赏功旌义等目的,彰显出世袭社会背景下世家大族与豪强酋帅对行政权力的垄断性特征。时人以世为家乡州郡县长官为荣的观念,是其产生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该制度可视为由酋长制走向郡县制的一种过渡形式,它适应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因而在实践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与专一制皇权的矛盾终究不可调和。北周统治者适时改制,对世袭州郡县者改为赐予五等爵,从制度上推动了北周封建化进程。该制度的实施、演变和废止的过程,也是北朝文化认同进程逐步深入的反映。该制度的影响远及后世。
州郡县长官世袭制;行政官职世袭;世袭刺史;选举社会;北朝
选举制是北朝任官制度的主流,占据主导地位。但北朝的州郡县长官世袭制,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三级行政长官任官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逐渐加强的大背景下,遗世独立,顽强存在,背离于历史发展趋势,因而极具特色。所以,对该制度进行专题研究,厘清其施行背景、原因、范围、过程、影响及其存在与消失的意义,释读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认同信息,自有其学术价值。
周一良先生《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及张旭华先生《“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对西魏、北周的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分别从民族政策、任官制度的角度有所论及[1]117-176[2]。本文拟将该制度置于一个较长历史时段内和选举社会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希望可以使作为任官制度之一环的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更加清晰,进而深化对北朝制度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北朝民族认同进程的认识。
一、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实施及授职对象
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是指朝廷在制度上授权特定地方的行政权力由同一血缘家庭或家族内部承袭和独享,而不许该家庭或家族以外的人染指的一种任官制度。其表现形式包括世袭刺史、世袭郡守及世袭县令三种。由于北朝军政一体化,世袭刺史、世袭郡守和世袭县令自然不仅可以临民,还可以领兵。
(一)世袭刺史
相关事例最早见于《魏书·咸阳王禧传》:“有司奏冀州人苏僧瓘等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请世胙冀州。诏曰:‘利建虽古,未必今宜;经野由君,理非下请。邑采之封,自有别式。’”[3]535咸阳王元禧是北魏孝文帝之弟。民众所请被孝文帝以不合时宜及程序不当等为由予以否决。
世袭刺史的受任始见于《魏书·敬宗孝庄帝纪》:“(建义元年即528年十一月)戊寅,以上党王天穆为大将军、开府,世袭并州刺史。”[3]261元天穆本是北魏皇室疏属,却又是权臣尔朱荣心腹。在“政出权胡,……牧守皆出其门”[4]292的形势下,被委以并州刺史重任。尔朱荣率兵赴洛阳威凌朝廷,曾令元天穆留后。孝庄帝即位,元天穆被封为上党王,召赴京师,屡次作为统帅出征,但应仍同时遥领并州刺史一职。尔朱荣擒葛荣后,元天穆“寻监国史,录尚书事,开府,世袭并州刺史”[3]355,获得了世袭刺史的权利和荣耀,开刺史世袭之先河。《元天穆墓志》给出了朝廷授予其世袭刺史的理由:“又以王纂荫乾晖,本枝皇干,体密君亲,义形家国;与天柱潜结玄图,显成大义,一旧威灵,再造区夏;虽疏画山川,开锡土宇,礼命光照,器像雕蔚,犹不足以酬静难济时之功,报扶危定倾之绩。除世袭并州刺史,本官、王如故。”[4]278即所谓不“除世袭并州刺史”不足以酬其大功。
孝庄帝刺杀尔朱荣和元天穆后,任命侍中、司空公杨津为骠骑大将军、并州刺史,但因形势急变,杨津未能赴任,遂改由太原太守、长广王晔行并州刺史[3]267。元晔被权臣尔朱兆、尔朱世隆共推为魏主,实为傀儡。元晔任命尔朱兆为并州刺史,“寻加都督十州诸军事,世袭并州刺史”[3]1663-1664。但不久尔朱兆被高欢诛灭,尔朱氏集团亦告覆灭。
所以,元天穆、尔朱兆的世袭并州刺史都没有完成传袭。
尔朱荣以其部民为核心组建劲旅,控制朝政,平息了六镇暴动及继之而起的其他反叛。元天穆、尔朱兆二人都是凭借这一凌驾于朝廷之上的军事集团力量获得世袭并州刺史职位的。对朝廷而言,是威压凌逼下的暂时妥协,而元天穆、尔朱兆自恃战功和武力接受世袭刺史的行为,也是其肆意妄为的不臣表现。
北魏末另一世袭刺史是权臣高欢,高欢于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获任世袭定州刺史。《魏书·出帝纪》:“帝以世易,复除齐献武王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九万,并前十五万户。”[3]282《北史》卷六《高祖神武帝纪》及《北齐书》卷一《神武上》记载相同。世袭定州刺史是高欢所获得的超级权利之一。不过雄才大略的高欢可能不久即主动放弃了这一权利,但史籍载之不详。《魏书·孝静帝纪》:“(天平三年即536年秋)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南道行台,节度诸军南讨。”[3]300可知东魏孝静帝天平中侯景曾出任定州刺史,定州刺史已非高欢。高欢曾经固让天柱大将军,并请求让爵分邑,以表示一种姿态:“(太昌元年即532年五月)戊戌,以齐献武王固让,听解天柱大将军,减封五万户,余悉如故。”[3]283“(永熙二年即533年八月)癸酉,齐献武王上表固让王爵,不许;请分邑十万户,节降为品,回授勋义,从之。”[3]288官职爵邑,对于实权在握但仍不乏反对者的高欢来说意义不大,反易授人以柄,故如其自求解除世袭定州刺史亦不难理解。
北魏末另有羌酋梁景叡获任世袭河州刺史,这一授任应与其世为部落酋帅的身份、军事实力及在河州当地的影响力有关。《北史·梁景叡传》:“梁览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难走西羌,世为部落酋帅。”孝昌初,梁景叡散财募兵,参与破莫折念生、胡琛等起义军的军事行动,拥有一定实力。《北史·梁览传》记孝庄帝授梁景叡世袭刺史较详:“永安中(528—530年),诏大鸿胪琅邪王皓就策授世为河州刺史。”[5]1806又《魏书·出帝纪》载:(永熙二年即533年三月)“戊申,以使持节、都督河渭部(鄯)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世袭河州刺史梁景叡为仪同三司。”[3]287但据《北史·宋世良传》,梁景叡其实对朝廷不恭:“河州刺史梁景叡,枹罕羌首,恃远不敬,其贺正使人,频年称疾。”[5]941梁景叡后被宇文泰所杀,其子梁鹳雀并未能袭任河州刺史[5]1806。
西魏有蔡阳蛮王鲁超明为世袭南雍州刺史。《周书·异域传上·蛮传》:“大统五年(539年),蔡阳蛮王鲁超明内属,以为南雍州刺史,仍世袭焉。”[6]888西魏时,又有巴人泉元礼为世袭洛州刺史。泉氏世为洛州雄豪。泉元礼率乡人袭州城,斩东魏所署洛州刺史杜窋(亦为当地豪族),西魏“朝廷嘉之,拜卫将军、车骑大将军,世袭洛州刺史”。泉元礼在沙苑之战中战死,朝廷“复以(泉)仲遵为洛州刺史”[6]788。泉仲遵是泉元礼之弟。这是第一例兄终弟及传袭世袭刺史的例子,但经过了朝廷任命的必需程序,而且泉元礼系为国战死。泉氏本世袭丰阳县令(见下文),又世袭洛州刺史,两级行政机构都被其家族掌控。杜窋为洛州刺史时,“巴人素轻杜而重泉”,泉氏在洛州有其民间基础和固有势力,外人很难在当地立足。钟盛先生在其《西魏北周“作牧本州”考析》一文中,认为“世袭也是获取本州刺史的一种途径,典型者有泉企父子、李长寿父子等”[7]。钟先生的观点颇具启发意义,但所举“世袭”的例子不甚妥当,其中泉企并未任世袭刺史,李长寿父子虽相继任广州刺史,但并无世袭刺史之名。
由上述数例可知,北朝世袭刺史的授予对象,一是权臣,如元天穆、尔朱兆、高欢等,一是居于偏远地方的少数民族首领如羌酋梁景叡、蔡阳蛮王鲁超明、巴酋泉元礼等。
北朝还有一种虽无世袭之名,却有世为某州刺史之实的任职情形。《北齐书·封隆之传附子子绘传》载:“子绘祖父世为本州,百姓素所归附。”高归彦反于冀州,北齐武成帝因封氏“世载名德,恩洽彼州”,委派封子绘至冀州慰抚。子绘巡城晓以祸福,结果民吏降款相继。“贼平,仍敕子绘权行州事”[8]306。封氏三代都曾任其家乡冀州的刺史。《封子绘墓志》对此亦有记载:“大宁二年,除都官尚书,寻行冀州事。先日,司空、太保二公并临冀部。至是公复行焉。三叶本岳,世论归美。”[4]424另有毕氏世为兖州刺史:“(毕)义云盛称门阀,云我累世本州刺史。”[8]世为某州刺史,是当时的一种政治现象,并不罕有,与当时社会上以世为家乡州郡县长官为荣的观念有关,这恐怕也是“世袭某州刺史”出现于北朝且易于被接受的社会心理基础。另有南朝降将司马楚之与子司马金龙、司马跃相继任朔州刺史,“镇会云中,朔土服其威德”[3]860。当然,这几例虽都是父子兄弟任职相继,但毕竟并无世袭之名,且与世袭刺史有质的不同。
(二)世袭郡守
世袭郡守的实例较少。西魏上洛邑阳人阳雄,世为豪族,随宇文泰屡经战阵,多有战功,“前后增邑四百五十户,世袭邑阳郡守”[6]797。对于阳雄的族别,周一良先生疑其亦为“巴氐之类”。
另有北魏彭城吕县人孙道登,在北魏孝庄帝永安初(永安元年为528年)被南朝梁将领韦休等俘获后,临刃不惧,拒绝劝降乡曲,遂被害。当时有这种节义壮举的还有宗女等人。他们为子弟赢得了出任并承袭五品郡守的资格:“二州表其节义,道登等并赐五品郡、五等子爵,听子弟承袭。”[3]1895孙道登等人的子弟可以承袭的,既有五等子爵,又有五品郡守官职,但未言明何郡,这里的“听子弟承袭”应即世袭之意,因为以功获赐的子爵不可能只许传袭一代,则五品郡职亦同。
可见世袭郡守被用以赏功旌义,一是授予有功的地方豪族,一是授予节义突出者。
(三)世袭县令
前文提及,西魏时巴人泉氏世袭洛州刺史。早在北魏时,泉氏已世袭丰阳令。《周书·泉企传》载,北魏上洛丰阳人泉企(上文提及之泉元礼为其长子),世为商洛雄豪。“曾祖景言,魏建节将军,假宜阳郡守,世袭本县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复为建节将军、宜阳郡守,领本县令,降爵为伯。”泉企九岁丧父,十二岁时,乡人三百余人前往州府请泉企为县令,州府申报朝廷。吏部尚书郭祚因泉企年少,欲选遣他人先担任县令之职,待完成一个任期后,再由泉企接任。宣武帝却不以为然,认为泉企即将成人,又为本乡拥戴,更重要的是其家本世袭丰阳县令,“何为舍此世袭,更求一限”,遂依其乡人所请。泉企次子泉仲遵,年十四为本县令。泉仲遵子泉暅起家本县令[6]785。则泉氏自泉景言获任世袭丰阳县令后,至少五代递相传袭丰阳县令一职,此职成为泉氏一门的禁脔和起家官职,他人无权染指。从泉氏任职的过程亦可看出,子弟袭任父兄的世袭县令之职尚需经过州府报请朝廷批准。
世袭州郡县地方行政长官之例,北魏最多,除上洛丰阳泉氏世袭丰阳县令的开始时间在北魏早中期以外,其他各例皆见于北魏末期政局开始动荡之后。西魏北周则有多例。东魏只见高欢一例,而北齐开国后,地方行政官职的世袭不见于史。另外,因父死王事等原因,朝廷诏子袭父职之类事例甚多,因非世袭,兹不赘述。
二、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实施背景与实质
北朝统治者对郡县制和选官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3]32“罢侯置守,历年永久,统以方牧,仍世相循。”[3]1899但在特殊情势下,统治者仍然容忍或者说借助了地方行政长官世袭这一形式,走了回头路。
由上文的例子可知,世袭行政长官的辖区,分为两类,一是边远地区,如河州、洛州、南雍州等地;一是心腹重区,如并州、定州等地。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授职对象为两类人:边远地区的酋豪和权臣。
(一)世袭制的实施背景
1.与魏晋南北朝的世袭社会背景有关。魏晋南北朝的世袭社会背景有助于解释地方行政官职世袭制何以产生。何怀宏先生按照社会提供给个人的实现和发展自己机会的差异,把社会分为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前者是一种“血而优则仕”的社会,血统或家世是取得精英地位的首要条件;后者是一种“学而优则仕”的社会,血统或家世不是选才用人的必要考虑因素[9]。他把西周至春秋时代的社会形态称为世袭社会,把秦汉至晚清的社会形态大致上归为选举社会,但同时又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视为特例,认为依据权力分配的标准,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还是应被称之为“世袭社会”,这样就有了一种在两个“选举社会”之间夹持一个“世袭社会”的情况。当然它又有别于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典型世袭社会[10]。
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视为世袭社会,确实可以解释许多当时的特有社会现象。虽然何怀宏先生的观察视野主要及于魏晋和南朝,但相对于秦汉官僚制下的选举社会而言,北朝确实跟魏晋南朝一样,保留了或者说重现了更多的世袭社会的残余。在北朝,一般来说,出身比能力对于获取政治权力等社会资源更为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出身于非世族家庭几乎意味着终身仕进艰难,出头无望。某些行政职位被某一家庭或家族垄断这一政治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世袭社会的一种表征。例如北魏司州牧这一重要职务几乎为元氏宗室所垄断。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正彰显出世袭社会背景下权臣与豪强酋帅对行政权力的垄断性,更是将北朝作为一种世袭社会的特征表露无疑。只不过这种世袭并不是一种自然承袭,还要经过皇帝的主动或被动的授职这一程序,这一点与典型的世袭社会有所不同,从而也体现出了时代的进步。
2.与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及时人以世为家乡州郡县长官为荣的观念有关。具体到制度建设上,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产生,与当时尚未找到更加公平、更有效率、辐射面更广的选举制度有关。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选举制度因制度本身的缺陷,已被世家大族利用、扭曲和异化,成为其垄断美职和维护特权的工具。以至于“到南北朝末年,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严重妨碍了人才的任用,动摇了中央政权的社会基础”[11]。而更有利于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尚处于孕育阶段。社会上存在着崇尚世族门阀的价值取向和将世代出任家乡州郡县长官视为荣耀的观念和氛围。人们对豪强世族认同度较高,豪强世族出任家乡的行政长官易于被当地人接受。这是州郡县长官世袭制产生和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如上文所举封子绘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三代任家乡冀州的刺史,“三叶本岳,世论归美”,正是北朝这一社会心理现象的典型表现。世袭刺史是“作牧本州”的一种特殊形式。乡人集体请求州府以使十二岁的泉企袭任丰阳县令,也是这种群体性心理的反映。
张旭华先生认为,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是西魏、北周以九品中正制为主导的任官制度的重要补充,是对北魏以来的方隅豪族与巴氐豪酋世代垄断州郡县职的公开承认,并使之合法化与制度化。西魏、北周的选官体制仍然具有较为浓厚的门第色彩,而非史籍所谓“周氏以降,选无清浊”[2]。
3.与当地的部族势力仍然强大和北朝政府欲取得其支持有关。单就获得世袭权利者为豪酋的情形而言,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实施,当与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较低、部族文化传统深厚和部族势力仍然强大有关。秦汉以降,作为选举社会重要标志的郡县制成为行政制度的主流和正轨,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袭社会”之下,行政制度上虽仍以郡县制为主,但统治者在局地又因地制宜,实行有别于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即为其一。
上文中提及的河州、洛州、南雍州等地,就当时而言,基本上属于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边远地区,交通不便,且处于分裂时期的军事斗争前沿,居民以少数族为主,具有深厚的部族文化传统,郡县制在当地并未取得高度发展。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与中心地区存在着社会经济方面的结构性差别,也存在着文化性差别。这些地区的被授予世袭行政职务者,是拥有较强部族武装的少数族地方酋豪,朝廷以赏功的形式授予其世袭行政官职,对其安抚笼络,示以优遇,借以更好地管理边疆地区。如西魏朝廷使泉氏世袭洛州刺史和丰阳县令,既是承认现实,又是希望收其效用。周一良先生认为宇文氏对巴氐酋豪广加联络并特别优待,目的是确保这些巴氐部族所据地区的安定并借助其武力在山东和江南作战[1]172。又如吴永章先生认为北朝对归附的蛮族首领,一概加以委用,把安抚之策摆在重要地位,以赢得其支持[12]。
北魏建国后虽然一直推行“离散部落”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实施得并不彻底,北朝的领民酋长世袭制(与酋长制有所不同)在郡县制之外长期存在。领民酋长对所辖区域和部族享有较大的自治权,代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保守性势力,对郡县制的推行必然形成阻碍,影响国家的行政官职设置和行政官僚体系建设。
所以说,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出现并不突兀,是朝廷在尚不能完全将一些边疆地区或新附少数族势力与内地同等管理的情况下,暂时遵从其地其民旧俗,承认其部族首领世袭领民的既成事实和权利,以变通的方式加以管理,绥靖边疆,安抚新附,属羁縻方式和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时自会予以变改。
4.与某一时期臣权势力过于强大有关。就获得世袭权利者为权臣的情形而言,朝廷授予其世袭刺史,不过是对其表示的优容妥协,以此求得暂时的平衡,反映出君权与臣权的尖锐矛盾和权臣势力的强大。刺史被世袭的州本来是朝廷的心腹重区,却成为权臣的基地和大后方,实际早已被其牢牢控制,朝廷力不能制。如北魏授予尔朱兆等世袭刺史之职,肇因于北魏后期及东魏君纲不振、强臣专权,对于皇帝而言属不得已而为之。
(二)世袭制的实质
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有两种表现形式:权臣世袭刺史与豪酋世袭州郡县长官,两者的实质大不相同。
权臣世袭州刺史反映出的是朝廷对叛逆的无奈。权臣控制下的世袭州,俨然是国中之国,朝廷对其已然失控,只能听之任之,仅维持表面上的君臣关系。这种情形下的由权臣主导的刺史世袭制的实施,披着朝廷授职的外衣,但本质上是一种权臣对朝廷叛逆的不臣之举,反映出的是朝廷对权臣叛逆行为的无奈。如北魏末年朝廷对权臣尔朱兆的授职即属于这种情形,只不过尔朱氏的并州刺史世袭乃因政治风云的变幻,最终未能变成现实。
历史发展是曲折向前的,就尔朱兆、高欢等个例而言,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实施,恐怕是一种郡县制的倒退形式。
豪酋世袭州郡县长官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暂时让渡。对于在少数族地区实行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较之酋长制或领民酋长世袭制,已经前进了一步。边疆地区的世袭刺史等世袭行政长官,与世袭的酋长不同,虽然两者对辖地的治理方式未必有重大区别,但前者有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名义,朝廷名义上已将其势力纳入了行政体系中,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只不过对其内部管理结构的干预仍然较少。如北朝以归附的蛮族首领田益宗为南荆州刺史,“所统守宰,任其铨置”[3]1370,间接反映出北朝政府对蛮族等少数族的管理方式和状态。田益宗还不是世袭刺史,作为世袭南雍州刺史的蛮王鲁超明必然拥有与田益宗同等甚至更大的“铨置”权。
对于这些酋豪,朝廷基本上可控,主动使用这种任职方式只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地方。多数酋豪(如泉氏、鲁氏)的世袭刺史,本由其军功和忠诚所致。世袭刺史在性质上应介于刺史与部落酋长之间,趋于封建行政化而又仍带有部落旧制色彩。该制度可视为由酋长制或领民酋长制走向郡县制的一种过渡形式。
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可资参照,即南朝实施的左州左郡左县制度。左郡左县之名首见于刘宋,萧梁时极盛,左郡之上产生左州。其设立以蛮酋的归附为前提,均有实地,且权力世袭。长吏皆为蛮酋,一般无政府军队戍守。左郡左县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与朝廷关系复杂,但左郡左县制的实行,说明少数民族都已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有利于向编户转化和民族融合的最终完成[13]。“然数世之后,终必别简人以代之”[14],政府仍以实施郡县制为长远目标。
三、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停废及其意义
针对权臣实施的世袭制,随着权臣的覆亡或者权臣的放弃而终止。如前所述,高欢在北魏末任世袭定州刺史,其任职时间最晚只可能延续到东魏天平三年,此外,东魏北齐再未见任职世袭州郡县长官的例子。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东魏北齐的少数族地区,州郡县长官世袭制也并未实施开来。
而在西魏北周少数族地区实行的州郡县长官世袭制,适应了特殊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符合现实需要,因而在实践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与专一制皇权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其过渡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在完成其使命后,被停废或取代不可避免。
(一)世袭制的停废
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在西魏北周得到了实施和延续,其废止也有明确的时间,即北周武帝时。《周书·武帝纪上》载:保定三年(563)九月己丑,“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县封男”[6]69。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宣告终结。北周朝廷将州郡县长官世袭改成了爵位世袭,对原拥有世袭州郡县特权者,在彻底剥夺其世袭行政权力的同时,用世袭爵位的方式予以替代式补偿。
保定为周武帝的第一个年号,其时北周的实权掌控在其堂兄、权臣宇文护之手,停废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宇文护作出的。随着北周代魏的平稳过渡,中央集权的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改制的时机已然成熟,宇文护遂作出这一重要决策。政策的推行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具有其特殊性和时代性,产生和延续于世袭社会背景较为突出和选举制度不完善的北朝时期,是中央政府与权臣或地方少数族政治军事力量角力与平衡的产物,并非一种常态化和一般性的制度设计,与当时通行的选举制相对立,施行范围有限,更不能说代表了一种方向。
该制度在北周的继续实施,虽说是一种对现状的承认和延续,但毕竟与单一制皇权世袭和郡县制持续发展的历史大势背道而驰,虽不无积极的一面,但其弊端和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行政权力在家庭或家族中传递,似乎又回到了世卿世禄制时代。地方的世袭行政长官虽然像一般行政长官一样每一任有相同的任期,但可以连任,实质上是终身制,除非朝廷以升职等方式将其调离。另外虽然其权力名义上也来自于朝廷任命,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朝廷对其内部具体管理事务的干预恐怕更少。如上文所提及的世袭河州刺史梁景叡对朝廷“恃远不敬,其贺正使人,频年称疾”,显示出朝廷在当地的权威性和控制力有限。这一制度不仅不能保障选贤与能,而且其长期执行,会产生一个隐患,即地方势力的坐大。这种弊端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警惕。当时机成熟,即中央政权趋于稳定和中央集权的力量足够强大时,统治者就会适时改制,将所涉及的州郡纳入到郡县制的轨道上来。
(二)世袭制停废的意义
1.推动了北周封建化的进程。北周州郡县长官世袭制走向终结,是皇权和封建制扩张与奴隶制残余逐渐被剔除和部落制走向衰落的结果。废止州郡县长官世袭,代之以爵位世袭,使这些边远民族地区在行政管理上与内地无别,将其完全纳入普通的行政管理体系,强化了官僚体系建设和对边远地区的管理与控制,从而扩大了郡县制的适用范围,有益于加强中央集权,为推动北周的封建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反过来看,这一政策转向,也是中央权威和对地方控制力足够强大的结果。
州郡县长官世袭制与封爵制都是剥削制度和特权垄断的产物,有着内在的联系。相对来说,爵位世袭是一种常态,因爵位世袭主要是经济利益的传袭,附带获得相应的政治资格和政治荣誉,而官职世袭所传袭的主要是行政权力。宇文护的改革,完成了一种利益转换,即官与爵的置换,革除一人一姓对一地方行政权力的垄断,但又使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得到了一定补偿和新的保障,以另一种形式呈现,而非予以硬性剥夺,所以未出现大的阻力和震荡,这也是此项改革得以成功的前提。
2.客观上推动了北朝制度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进程。不同地区的制度安排之所以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性是其内在原因。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本质上是一种囿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而实行的有限自治,是一种暂时性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北周州郡县长官世袭制走向终结,是职官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中世袭因素的剔除过程,是行政制度上向郡县制的靠拢和回归。
就实质而言,取消一姓一族的世袭行政特权,有助于促使部落制、酋长制衰落和部落民、部曲到编户的转化,为民族交融清扫障碍,形成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有助于减少差异性,增进同质性。就心理而言,郡县制必然提升民族地区的民众对郡县制和选官制度的制度文化认同,使之逐渐深入人心,进而促进民族认同。
宇文护改制的顺利实施,本身也是制度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
3.维护了安定统一的局面。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君权与臣权始终是既相互博弈又相互利用的两对矛盾。中央权力和君权,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公权。州郡县长官世袭,本质上是公权让渡,化公为私,公权私用,易导致地方权力过大。从历史实践看,这种状况可能会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虽然一般尚不足以掀起风浪,但严重者会形成尾大不掉难以控制的独立王国,影响到稳定和统一。尹辰先生就认为军权分散与军权失控是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成因之一[15]。
废止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从制度上切断了边远地区强力家族对带兵权和领民权的垄断,有效消除了地方势力的割据隐患和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和阻力,是一项防患于未然的举措。这一举措也必将对所在地方的民众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将其对豪族的依赖和信任,转化为对朝廷的认同和忠诚,提升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统一和加速一体化进程。
四、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对后世的影响
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负面性使北周统治者下决心将其废止,只通过选举授职,地方行政官员皆由朝廷委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以来作为个别现象的“行政官职世袭化”的苗头并没有被后来者彻底消除,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影响力超出了北朝,至唐初,还发展出了“代袭刺史(即世袭刺史,避唐太宗讳改)制”,一度影响到唐朝的制度建设取向。北朝行政长官世袭制可被认为是后世各种形式的地方行政官职世袭之滥觞。
唐太宗李世民显然对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的弊端认识不足且高估其积极的一面,使刺史世袭制一度恢复。《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一年即637年六月)己未,定制诸王为世封刺史。戊辰,定制勋臣为世封刺史。”[16]48《旧唐书·房玄龄传》:“十一年,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并代袭刺史。”[16]2461墓志资料对此也有反映。《李恪墓志》:“又与诸王同诏代袭安州刺史。”[17]获得刺史世袭特权的都是宗室或开国功臣。由于代袭刺史制度弊端明显,在长孙无忌、房玄龄、马周、于志宁等大臣以“重裂山河,愈彰滥赏”[18]“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16]2694等理由固谏之下,“(贞观十三年)二月丙子,停世袭刺史”[16]50,功臣被改封公爵。长孙无忌等人反对分封世袭刺史,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防止出现分裂割据局面无疑有积极意义。亦可见行政官职世袭已经不合时宜,失去了其适宜存在的土壤。
王夫之针对唐太宗授予功臣世袭刺史一事,在其《读通鉴论》之《论刺史世袭》中曰:“太宗以荆王元景、长孙无忌等为诸州刺史,子孙世袭,而无忌等不愿受封,足以达人情矣。夫人之情,俾其子孙世有其土,世役其民,席富贵于无穷,岂有不欲者哉?知其适以殄绝其苗裔而祸天下,苟非至愚,未有不视为陷阱者也。……时所不可为,非贪叨无已、怀奸欲叛者,固永终知敝而不愿也。马周曰:‘孩童嗣职,万一骄愚,兆庶被殃,国家受败。’则不忍毒害见存之百姓,宁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稍有识者,固闻之而寒心也。……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而公薄之,岂强公以茅土邪?’强人而授之国,为天下嗤而已矣,恶足辩?”[19]王夫之谈到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对立,承柳宗元《封建论》的观点,阐述了分封制(行政长官世袭制)的危害,指出若非“怀奸欲叛者”,是永不愿接受分封的,并认为马周等大臣已认识到行政官职世袭制在获得行政人才上的不确定性,因为假若受封茅土者子孙非适宜其位之人,将危及民众与国家,同时危及其自身与家族,因此这一制度于国于家皆有潜在危害。由此可见,郡县制与选官制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已经深入人心,而唐初大臣对行政官职世袭制的潜在危害具有清醒的认识和警惕,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北周废止州郡县长官世袭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证明。
但在边远地区特别是一些初附之区,唐朝政府推行的羁縻州制度与北朝州郡县长官世袭制有较大的相似性。《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20]1113如《新唐书·地理志三·河北道·幽州范阳郡》载燕州“以首领世袭刺史”[20]1020。也有一些边远“正州”以部落首领世袭刺史、司马,如剑南道西部十余州[21]。这都是唐中央政府审时度势、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需要的结果。
北宋有折氏世袭府州知州,乃因北宋中央对地方控制力不足,尊重府州折氏的特殊性,同时利用其捍卫边疆对抗西夏。北宋府州折氏的世袭制,绝非一种简单的普通的世袭制,而是一种中央主导下的血缘加能力的复合型世袭制,是一特殊的成功案例[22]。宋代于西南地区仍延续羁縻州制度。
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其他各种形式的变相的世袭制仍然不时出现,余响不绝,并伴随封建社会始终。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皇权世袭制和家天下制度的存在,以及君权与臣权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利用的复杂关系的作用。只有当皇权世袭也被连根拔掉的时候,州郡县长官世袭制以及军镇长官世袭制等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具有落后性和不稳定因素的世袭制才会彻底绝迹。
[1]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G]//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2]张旭华.“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J].史学集刊,2012(4):13-22.
[3]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G].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5]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1.
[7]钟盛.西魏北周“作牧本州”考析[G].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9:85-104.
[8]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576.
[9]何怀宏.世袭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10]何怀宏.世袭社会的另一种形态——对六朝士族社会的一个初步观察[J].史学月刊,2011(2):29-54.
[11]王力平.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9-43.
[12]吴永章.北朝与蛮族[J].民族论坛,1987(1):53-60.
[13]方高峰.试论左郡左县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2):23-30.
[1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06.
[15]尹辰.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成因及其后果[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84-88.
[16]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郑炳林,张全民,等.唐李恪墓志铭考释与有关问题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7(3):5-22.
[18]长孙无忌,等.请罢功臣世袭表[M]//李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3147.
[19]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702-703.
[20]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王义康.唐代“蕃州”监察制度试探[J].民族研究,2015(3):74-84.
[22]姜锡东.北宋府州折氏的忠诚与世袭制[J].社会科学战线,2016(10):111-119.
(责任编辑:田 皓)
K239.2
A
1674-9014(2017)06-0106-08
2017-06-22
段锐超,男,山西临汾人,陕西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及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