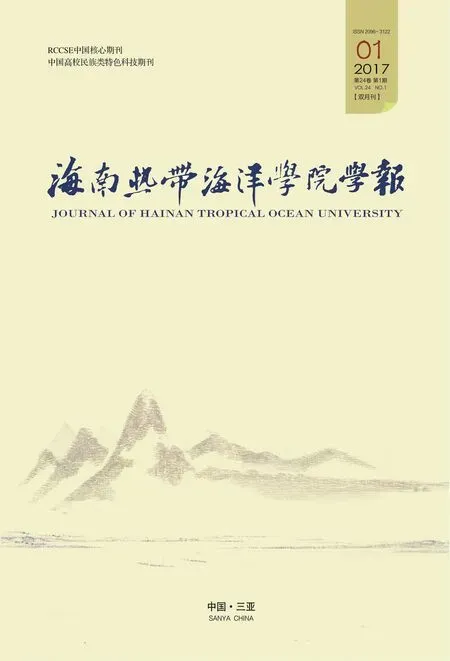清末重庆女子教育探析
吴洪成,贺美燃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探析
吴洪成,贺美燃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在近代社会变革及外来文明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其中以女子小学堂、女子师范学堂为主,虽然办学性质仍残留浓厚的封建性与保守性,但是所包含的进步教育的因素占据着突出地位,并且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相统一。清末重庆女子教育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历史缩影,对之加以探析不仅可以深化对清末重庆教育改革的理解,而且有助于认识近代内陆地区女子教育演变的曲折历程及深层内涵。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新学制
女子教育是一个教育历史的概念。女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过着受屈辱、受蔑视的生活,在母系社会时期,她们曾是社会的主宰者、权力的执掌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广义的教育活动中也占据着重要的支配地位。原始社会的未成年人实行“儿童公育”,由氏族统一抚养,婴儿出世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一社会状况就可以论证这一史实的实然性存在。步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子的社会地位才开始降低。沿至封建社会中后期,女子的社会身份与教育权同时滑落低谷,一蹶不振。直到近代后期,随着社会解放运动的深入,新社会制度的建立,男女平权、共同接受教育已成为女子教育的内涵,主要是适应女性生理、心理的教育设计或职业技术的专门培训。考诸历史,中国近代新式的普通教育与女子教育均产生于清末维新运动时期,至清末民初形成为制度化,取得了学制中的地位及法律的尊严。
清末的重庆是隶属于四川省东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下辖广阔的嘉陵江下游、长江上游城镇乡村。近代四川的教育顺应了社会教育发展的大潮流,加快着女子教育的发展步伐。在20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四川(含重庆)女子学堂的发展十分迅猛,占全国总数的16.4%,仅次于江苏、直隶两省。民国以后,重庆行政区划及地位屡有变更,特别是1997年以后,在原重庆辖区基础上,将涪陵、万县、黔江三地划入,建立了新的重庆直辖市。本文是以重庆直辖市的行政辖地来探讨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相关问题的。
一、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产生背景
沿袭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教育体系中是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为千百年来人们遵从的信条。重庆地处中国腹地,自古以来风气闭塞,观念陈旧滞后,更是深受这种封建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因循守旧,教育和科举的僵化腐朽,使得重庆士绅把女子送到私塾或书院读书的寥寥无几。即使让女儿入家塾或族塾的蒙学教育机构,也只是让她们识几个字,读些《女儿经》《女诫》之类的书,目的在于养成知书识礼的闺秀。她们普遍以“相夫教子”为至上使命,“治国平天下”那是与她们不相干的。清末以女学堂为中心的女子教育对传统女子教育而言是一场剧烈的教育性别革命。
(一) 社会变革对重庆女子教育的催化
19世纪中叶,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急速地走向衰败,社会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广阔地体现在从社会经济到社会政治,从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在中国社会经历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巨大变动的背景下,清末重庆的女子教育拉开了帷幕。
1895年,以“公车上书”为转折点的戊戌变法,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了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并向全国各地蔓延扩展。1896年,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在重庆兴起。维新思想家宋育仁回川,把维新变法的火种带到重庆,他联络了一批在渝的爱国维新志士,创办报刊,制造舆论,宣传变法维新,使维新运动形成了一定声势,并逐渐向其他城市扩展。报刊、翻译、出版等文化事业,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通风气,启迪民智,改革社会的一种有效的手段。1897年11月,四川第一家报刊——《渝报》在重庆创刊,宋育仁任总理,设成都、嘉定等22个代派处,省外有北京、天津、上海等26个代派处,可见其影响范围之广大。1898年的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保国、保种、救亡图存而提倡的重视女子教育、兴办女学的口号并没有因为维新变法的失败而被打入冷宫。*参见吴洪成《重庆教育史——从巴国到清代:重庆的学校》,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清末时期,女子接受教育的价值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女子学校逐渐扎稳根基。
1901年,迫于国内外形势危机造成的强大压力,为了延续岌岌可危的统治政权,清政府被迫宣布实行新政。此后,朝野条陈请办女学堂者日众,各地开始先后兴办私立女学堂。190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编印女子学堂用书,为女学堂的教学提供了可靠的教学资源。当时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及讨论评述的时文不胜枚举。陈以益于1901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是当时竭力倡导和宣传女子教育的媒体,主要包括论著、教育、家庭、社会文艺、记载等栏目,其在重庆的发行量、销售量很大,表明了市场传播的成效非常显著。该刊提倡女学对国家富强的作用以及女学关系到国之强弱与种族存亡的观点。其第一、二号刊载的《论禁女学堂之非》指出:“中国人民之所以弱,由女子之不强也;人民之所以愚,由女子之无学也。教育之所以不发达者,由女子之无教育也。”[1]从而推出了“文明之发达,必由于教育。教育之普及,必肇自家庭”的结论[1]。 所以,女子教育普及了,女子的一切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190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女子世界》的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2]丹忱在《女子世界》第四期上发文大力倡导兴办女学。《女子世界》提出了解决女权问题的根本在于兴办女学的观点,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可以使其养成独立人格,摆脱依赖性。针对大多数女子目不识丁的现状,如果要兴女学就一定要先读书,读有用的书,有能力还可以出外留学。*参见雷良波,陈阳凤,熊贤军《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1906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那拉氏迫于全国人民兴女学的压力正式面谕学部举办女学。
在这些进步思想的指导之下,重庆的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性。女子接受教育的程度同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同样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女子教育作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生事物也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发展态势。
(二)西方外来文明对女子教育的触动
西方外来文明的影响和近代科技的传入,冲击了我国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放弃了妄自尊大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是女子教育发轫的重要条件。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及“开民智、兴学堂”社会潮流的震荡,重庆的社会习尚发生了转移,新式女子教育便开始滥觞。1897年,立德乐夫人在重庆倡导天足会,响应者因而在江津、巴县先后发起建立天足会,并拟定了《天足渝会简明章程》,规定:“入会者女不得缠足,子不得娶缠足之妇。入会者女年十岁上,已缠足者愿否解放,听其自便;十岁以下均须一律解放。”[3]消息传出,“一时闻风欣慕,愿如会约者,颇不乏人”[3]。
光绪二十三年(1897),美国基督教布道会在巴县城区曾家岩村创办私立淑德女中学堂。外国传教士来华办学,是欧美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但在客观上,对传播西方文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亦起了一定作用。
近代社会剧变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西方文化传播所带来的思想启蒙,促使清末重庆女子开始意识到命运要由自己掌握,要勇敢地走出家庭,迈向社会,要求女性同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上述历史场景的诸多因素交错影响下,重庆近代女子教育拉开帷幕,并在艰难历程中开拓演进的征程,成为近代重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历史影响
在近代中国最早创办女子学堂的是西方传教士,从1844年开始,他们就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创办了第一批女学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女塾。零星出现的早期教会女学从办学体制、课程设置到教育方式等方面都冲击了中国的封建道德秩序,突破了中国女界的禁锢,培养了一批知识女性及专业人才。
西方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也极大地影响了重庆开明人士的思想,他们开始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观念进行反思,提出“参访西法,增设女塾”的主张。1903年,重庆便成立了“女学会”,其目的是为“振兴女学”,决定先就重庆城中设女学堂,待“规模周备,经费充足”,再行推广。并制定《重庆女学会章程》,规定宗旨是:“凡有关于女学之责任,如整齐学务,建立学堂,编书购器等事,本会皆尽力肩任之。无论会内外诸友,有以女学事询或托办有关女学之事,本会皆可代办。总期化无学之女为有学,无用之女为有用。”[4]在未立学堂时,先立“女师范学堂”,“以广师资而便学者”。[4]女学会的成立为重庆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和舆论导向。
女子教育的兴起使民间送女孩入学者多了起来,女学发展的前景透露曙光,但是,兴办女学的阻力依然强大。1904年1月,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在《奏定蒙养园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指出:“中国此时情景,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5]他们认为“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开展的女子教育实际上是家庭教育,开办的女子学校实际上是“幼稚园”,也就是家庭中以相夫教子、三从四德为核心的贤妻良母教育。直到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我国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以及《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这标志着中国女子第一次获得了享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利。女学堂章程的制定,对于女子教育发展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
章程下达后,重庆各州县纷纷设立女子学堂。虽然遭到保守势力阻挠,甚至是对女学的破坏。但是,在政府顶层设计及政策力量的推动下,女学堂作为新生事物的出现犹如雨后春笋,不断生长,蔚为大势所趋,不可遏制。清末重庆以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的发展最为可观。
(一) 女子小学堂
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小学“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6]。女子小学堂分为初等、高等、两等并设三种。初等小学堂分为修身、算数、国文、体操、女红五种;高等小学堂分为修身、图文、算术、地理、格致、中国历史、女红、图画、体操九科。女子初等小学学制为4年,授课时数是24到28小时,女子高等小学为28到30小时。重庆积极响应清政府的办学号召,按照章程规定大力兴办女子小学堂。
在重庆所辖区县中以重庆铜梁县女学堂最为显著,也是当时四川最早创办的女学堂。1903年,黄德润耗资万金在重庆市铜梁县城创办了4所女学堂。最初是在县城内的敬节堂拨借场地创办了女子小学堂,之后,入学者人数增加到50多人,地小难容,于是又在城内的养老院借房屋添设了一所女子小学堂。由于县城北路安居,南路户口繁多,为满足更多女学生接受教育的需求,又开设了一所女学堂。学堂主要招收7-8岁至10岁的女童入学读书,习字学算,所学科目包括修身、算术、图文、女红等。县人胡凤岚自日本回川后被延聘为新开办的高等女子小学堂堂长。该校主要教授修身、国文、算术、地理、格致、女红、体操、图画等课程,与清末女子高等小学堂课程计划一致。*参见杜亚泉,胡愈之《各省教育汇志》,载《东方杂志》,1904年第5期,第123页。上述女子学堂的课程编制及教学内容除了使女子学习掌握新的知识技能外,还包括了期于实践躬行而设置的修身、家事、裁缝、手艺等课程,体现了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的价值取向。铜梁县女学堂的创立具有书写清末重庆女子教育新篇章的地位。
1905年,长寿县知县唐我圻以600金购买林庄学堂外的韩侍郎花厅作为校舍,创办女学。其后渐次扩大,学科设置亦趋完善。*参见黄荣主编,四川省长寿县教育局教育志办公室编《长寿教育志》,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1906年,綦江创办女子小学堂1所。同年,丰都县节妇黄张氏认捐千金设私立女子小学。秀山县邑绅岳子厚自捐学费,在城内设立女学,聘请女教习,招收女生30余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统计全蜀女学共得二十余区。宣统二年(1910),江北县开办县立宾兴女子小学,堂址在毗卢寺,为该县女子教育的先始。宣统元年(1909)开县女子初等小学堂成立。在重庆这些学堂中,有些女学堂是教会办的,如:1911年在永川城内福音堂兴办懿德女校,这是一所教会办的,仅供信奉耶酥教的女子读书,有学生10余人。到1907年时,全国共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其分布状况如下表:

表1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国女子学堂分布及状况一览表*相关数据引自[清]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学部总务司,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行。
由此可见,1907年,四川(含重庆)共有女子学堂70处,仅次于直隶(121)、江苏(72),远多于其他省份,除未能统计的外,占全国女子学堂总数(428)的16.4%;女学生2246人,仅次于江苏(3395)、直隶(2523),远多于其他省份,占全国女学生总数(15456)的14.5%。可见四川、重庆女学的发展优势明显,是中西部女子教育的先进地区。
(二)女子师范学堂
19世纪末,由于兴学导致师资匮乏,中国有识之士才认识到师范教育的重要作用。我国近代重视师范教育之议,发端于梁启超。他于1896年发表《论师范》一文。在该篇文献中,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府州县学官,“号称冷宦,不复事事”,而书院山长、蒙馆学究,虽然数量可观,“车载斗量,趾踵相接”,但总体素质低下。而洋务派所办的洋务学堂,如同文馆、水师学堂等聘请洋教习,仍是弊端丛生,主要原因是“西人言语不勇,必俟翻译辗转,多半失真”。由此,注定了发展新教育不能一味依靠洋教习来进行。梁启超最后明确提出师范是“群学之基”,教师是“学子之根核”,“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7]1897年4月8日,南洋公学开学,先设师范院,表征着中国师范教育迈出了第一步,使师资养成有了专设机构。兴办女子师范教育也顺应潮流跟上了时代的步伐,其风气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重庆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为争取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以“振兴女学”为先务,重庆女学会决定在重庆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为女学的推广准备师资力量。1904年,重庆女学会女子师范学堂诞生,该校又称巴县女子师范学堂,校址位于巴县城内全节堂。1905年春,《重庆日报》的创办人卞小吾在重庆培德学堂建立了女工讲习所,招收女工“半工半读,既授以文化,又授以技术,参加学习的女工均以放足,服饰亦甚简洁”[8]。此为重庆女子职业教育的萌芽,其开风之气之先的意义自然突出。
《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幼儿保育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9]。女子师范学堂分为初、高两等,学制各四年,每年45周,每周34点钟上课时间。每州县必须设立一所女子师范学堂,初办可由官府筹设,也可民办。毕业于女子高等小学四年级年15岁以上或毕业于女子高等小学二年级年13岁以上且家世清白、品行端正、身体健全者可入女子师范科学习。学习科目分为修身、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算术、格致、图画、家事、裁缝、手艺、音乐、体操等,家庭困难者,可不课音乐。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女子师范学堂包括四川淑行女学堂和巴县女子师范学堂。
1907年,华阳举人陈慎言在成都创立的“四川淑行女学堂”,招收能识字、会书写的女子,分别教授初高中课程,成效显著。不久,清朝学部命令各省在省城设立一所女子师范学堂,于是,该校改名为“成都淑行女子师范”。1907年8月招收师范生一班,学制两年。学生于1909年7月毕业,经过考试,“成绩甚优”。除招新生外,该校女生有志愿学师范者“亦可就近升级”。1911年,该校创办人之一陈罗徵之女宝琼女士留日归来,开办保育科,培养保育人员。在陈慎言先生的精心管理与经营下,学校扩充校址,增加班次,提高教学质量,成为了四川省女学的榜样。1914年改名为“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参见应竞丽,姜晓宇《四川女性教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81页。成都是四川的省会,其榜样作用的力量影响了全省,包括当时积极办学的重庆。重庆女子师范教育有了新的起色,如合川嘉懿女子高小,1910年办,附师范1班,初等1班;主要开设修身、教育、国文、地理、历史、图画、格致、家事、手艺、裁缝、音乐、体操等课程;设堂长1人,以男子年高有德者充当;学监1人,以女子充当;教习数人,男女参半。重庆女子师范教育在清末新教育的大浪潮下发展起来。尤其是巴县女子师范学堂堪为代表。学校按清末女子师范教育的办学要求、课程计划及组织方法开展教育活动。由于当时国内师资力量不足,在女子教育领域,数理、教育学科方面更为短缺,于是,聘请了日本女教习大田喜智从事教学及组织活动。大田喜智生于日本千叶县,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渡海来华。1906年7月,任巴县女子师范学堂教习,她以自身丰富的专业学科知识和成熟的教育经验,推动着该校不断向前发展。1910年5月,大田喜智晋升为巴县女子师范学堂的管理者之一,直至1913年1月离校。当时,大田喜智与重庆府中学堂的藤川勇吉一起在内陆腹心重镇任教,为重庆的中日教育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 历史影响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历史影响是多元的,既有纵向延续的作用,也有思想观念或认识内容的借鉴与启迪。这里主要从前者立论,略述民国时期重庆女子教育的延续性。以下仍对应于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类型加以介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初年,女子小学堂发生了如下变化:1.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2.女子高小以上可以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3.特设之女学校章程,暂时照旧。4.课程标准,女子不另行规定一套。之后,壬子葵丑学制的颁布再次明确了男女同校。男女同校的初等小学可由市、镇、乡设立,6至14岁的男女儿童均可以入学接受教育。初等小学校所修科目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图画、手工、唱歌等;高等小学校的课程主要有修身、国文、算术、中华历史、地理、理化、博物、手工、体操、唱歌、外国语、农工商业等,男女课程基本没有区别。1912年成立的重庆巴县县立第一女子小学,现重庆南岸区龙门浩小学,在当时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同校,所设课程与上述规定基本相同,可见重庆女子小学校同样符合上述小学的教育变化趋势。从课程教学内容的编制来看,“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办学目标走向边缘甚至淡出,更加体现了培养女国民的质量要求。女子教育热潮的兴起使得全国女小学生在1912年达到了130984人,1919年达到了215626人,是1907年的18倍,发展速度实属之快。民国初期,重庆的女子教育相对于清末而言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初等小学男女同校的实现为女子初等教育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也为民国后期1919年至1949年重庆男女教育在宪法及学制框架、规程内的平权和民主性拉开了序幕。
民国时期,1914年8月,四川省为培养小学、幼儿园教师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首招旧制师范预科,之后添设保姆科、小学幼稚园、初中、高中。行政机构设教务处、训导处,事务处。学制预科1年,本科4年。*参见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最初女师招收学生,凡年满15岁以上的未婚女生,高小毕业具有同等学力者,身体健康无残疾的,均可报名投考,录取成绩优良者。肄业时间为5年,保姆班则只两年。因当时社会不重视幼稚教育,保姆班毕业生就业难,第一班于1916年暑期毕业后,即停招。*参见文化教育科学编,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页。该校的校训是“诚朴宏毅”,经蒙裁成校长详细解说,即为:做诚实不欺的人,做诚正不阿的人,做诚恳和善的人,做坚强不从俗的人;生活要朴素,思想要纯正;目光要远大,志气要恢宏;目标看准,坚毅向前,不达目的,绝不终止。他说:“你们再不能像从前的女子,一切依人靠人,听人主宰。须知前人能轰轰烈烈干的事,你们也能干;男子能干的事,你们女子也能干,千万不可自暴自弃。”[10]可见当时重庆有识之士改变女子生存现状和创办女子教育的坚定决心。1935年,该校改名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正是在近代女子师范教育这片肥沃土壤的培育下,重庆女子师范教育的规格不断向上提升。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作为战时首都(陪都)的重庆地位上升。1940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重庆江津县白沙镇成立,后成为国统区的最高女子学府,主要开设教育、国文、理工、英语、史地、音乐、家政七系及体育专修科,后来陆续增设了数学系、国文专修科及国语专修科。各系均为5年制,在校修业4年,第5年充任实习教师,毕业发给学士学位文凭。建国后,1950年,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师范相关系科)合并组建为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现在的西南大学。可见,重庆女子教育在从前的基础上又迈上了更高的台阶,踏上了高等教育的远大征程。
三、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评价
从原始社会开始女性在教育上就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进入父系社会之前妇女在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劳动中就是主力和骨干,也是生产技能和知识的主要传授者。女性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也是得天独厚的,“庠”是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原始学校的萌芽,由部落退下来的女酋长在其中集中教养儿童。虽然从进入父系社会开始女性的地位逐渐走低,但是不可磨灭其之前的功绩和重要性。*参见闫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进入近代以后,女学开始逐渐得到发展,女性的地位慢慢回升。女学的创立是中国传统教育结构重大变化的特征,也是教育近代化改造与现代性增长的显著标志。它的出现有力地冲击封建上层建筑,挑战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价值取向,同时有助于改变“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男性在外赚钱养家,生活衣食无忧”[11]的社会传统观念。这不仅对教育发展影响深远,而且对社会风气的转变,男女平等社会氛围的形成及传统伦理观的革命都有一定的意义。
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发展加快了重庆教育的近代化步伐,改革了学校教育男性性别特权垄断一贯模式,挣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束缚,为女子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迈开了第一步。女子教育打破了重庆过去的女子只知道在家相夫教子、纺纱织布的局面,开始接触新知识、新生活,为以后社会破除对女性的偏见,解除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女子社会地位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重庆地处中国腹地,风气闭塞,文化上因循守旧,使得重庆士林乃至一般民众对女子教育的态度非常冷漠,甚至敌视。然而,随着清末至民国整个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女子学堂的增多,女子入学人数也越来越多,重庆社会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向文明开化,女学的兴办对于重庆转移社会风气,开通民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长期闭关、开放不久,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传统势力异常强大的内陆腹心地域重庆设立女学,进行学制创新,并且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进步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积极宣传和参与、开明士绅的热心捐助、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都是分不开的。诚然,清末女学堂深受“贤妻良母”主义办学方针的影响,在经历了辛亥革命民主运动的冲击后的民国时期得到改观,但是仍有残留,以致沉渣不断泛起。对此本文不再讨论。总之,清末重庆女子教育的产生与民国时期的发展有助于涵养重庆女子新国民德性,学习并掌握近代科学文化及知识技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意识和服务社会国家的能力,为她们从家庭走向社会、从愚昧走向文明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
同时,清末女子教育不仅为我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向纵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加速了女子教育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为我国现代女子教育的建立打下了深厚根基。清末女子教育扩展和丰富了现代教育的内容,从教学科目的设置到教学内容的安排,既有国文、外语、数学、理化、历史,又有女红、生物、教育及家事,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女性教育的内容。清末女子学堂的建立,学制、就学年限、教学组织管理及考评机制的安排等规划设计,尽管还不够完善,但确实使我国女子教育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道路。女子教育制度的确立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现代学制的性别角色平等地位的确立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清末女子教育还促进了女性教育思想的发展,从清末女子教育初创时的“贤妻良母”到1922年“壬戌学制”男女教育在学制上平等的“自立自强”思想的转变,促进了女子男女平等意识的形成。重庆清末的女子教育就是中国内陆地区的一个典型案例,也具有上述内容的特性。由此,中国现代女性不仅追求教育平等,还不断实现婚姻自由,职业自由,形成了知识女性群体。知识女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行业部门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使其不论在自身家庭领域还是现代社会舞台都能够彰显女性魅力,焕发女性光彩。当今的时代,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女子教育问题,建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女子教育课程及培训体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女子教育发展指标及管理机制,并逐渐确立女子家庭、职业、社会的良性循环系统,从而有效确立女性在社会事业中合理角色担当的正确走向。使女性在人格健全、地位平等、身心完善的综合素质能力基础上,不断为我国的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和民族繁荣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1]陈以益.论禁女学堂之非[J].女报,1901(1): 11-13.
[2]丁初我.发刊词[J].女子世界创刊号,1904(1): 1-2.
[3]宋育人.天足渝会简明章程[J].渝报,1897(9): 7-10.
[4]杨庶堪,朱必谦.教育附录:重庆女学会章程[J].广益丛报,1902(9): 51-54.
[5]舒新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381.
[6][清]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女子学堂章程[G]//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73.
[7]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师范[C].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42-144.
[8]稚珊.卞小吾遇难纪实[G]//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16.
[9]舒新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811.
[10]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608.
[11]戴哲.女性的个人成长,中产阶级的危机以及都市文化——以日剧《昼颜》为例[J].琼州学院学报,2016(4):100-106.
(编校:何军民)
Women’s education in Chongq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 Hong-cheng, HE Mei-ran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tarted in Chongqing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social changes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The major forms were female primary schools and women’s normal schools. Although it still retained strong feudalism and conservatism, its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factor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and this was quite harmonious with the pa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The Chongqing women’s education was an epitome of modern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To make an analysis on this issue can not only get a better knowledge about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ongqing educ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woman education in inland China.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ongqing; Education of women; New schooling system.
格式:吴洪成.清末重庆女子教育探析[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7(1):101-108.
2016-12-04
吴洪成(1963-),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 贺美燃(1992-),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G529
A
2096-3122(2017) 01-0101-08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