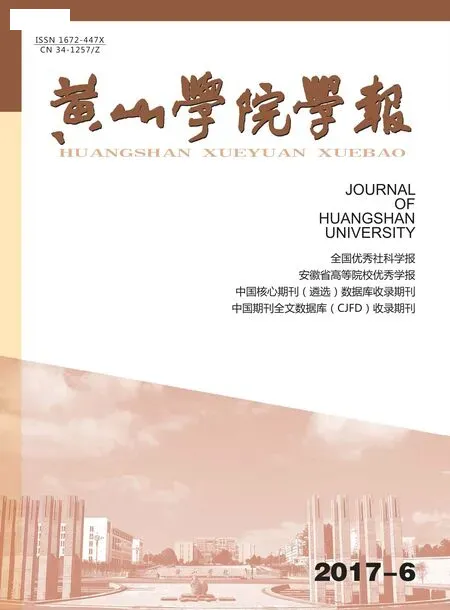阮籍《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王 菁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铜陵244000)
一、《乐论》的思想渊源
青龙四年 (236年)因魏明帝曹叡西取长安大钟,关内侯高堂隆上书劝阻,引发了一场由钟的违制上升到礼乐本质的争论。阮籍的《乐论》应该也是为这场争论而作,大约作于正始初年,正是阮籍有着“济世志”的年代。以刘子的提问开篇,重在陈述“移风易俗”也就是音乐的教化功能。从“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可看出音乐不仅要体现天地自然之和,还必须“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要求音乐要与礼配合,符合礼的规定。《乐论》是阮籍论乐的专著,其美学思想融合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一方面以“和”作为乐的本质属性,以“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为目的,要求阴阳协调的音声律吕去适应万物之情气,另一方面在音乐中仍然继承儒家思想,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所以,《乐论》的核心是主张“以和为美”,要求音乐与天地自然乃至人心的和谐。儒家是最早把“中和”的思想贯穿到审美观念中的,所以“和”的观念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的农耕时期。
二、“和”的音乐本质
远古时期,是生产力极其低下、分工极不平等的社会,同时也是人类天性最为解放、与自然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它促成了人们从自然的本体出发,有意识的把握其中的度,以达到和谐的状态。先秦是“和”的发展时期,思想家们开始以礼仪来规范审美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和谐,“以和为美”的观念就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儒、道两家通过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加上各家的深化与完善,使“和”这一思想理论更加丰富。春秋时期“以和为美”的观念强调达到“和”的境界,必须主体与客体相互配合,而客观审美对象是否和谐,取决于是否为人的主体所接受。“从主体感受来说,外界的和谐导致内心的和谐,由此产生美感,形成主客体相交融的和乐境界。 ”[1]89
儒家宣扬仁义,强调人道,所以贴近百姓生活,为人民所接受。统治者也依靠仁义来巩固政权,赢得民心,因而仁义也被统治者所利用。“中庸是一种德行,又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美学思想,”[2]13作为德行,要求主体在情感的发泄与控制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作为思想方法,中庸强调看问题不偏不倚,反对片面,主张以和谐的方式解决问题。作为美学思想,中庸体现的是中和之美,会把人生和社会中的喜剧和悲剧因素调和起来,就如阮籍在《乐论》中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呈现一种和谐的状态。
先秦时期儒家的“中和”思想在《周易》尤其是《易传》中得到了更加深刻和严密的论证。《周易》者,谓之“周转变易”。乃“日、月”阴阳交合,引万物之变。它以建立一个“弥纶天地之道”为己任,追求宇宙间的普遍和谐。这种和谐以天地定位、阴阳协调为基础,在阴阳刚柔的对立统一中追求和谐与流变;在山川相通、雷风激荡、水火交化的现象中体现自然界的和谐。自然界的和谐孕育了音乐的和谐本质,阴阳之道,一动一静,构成宇宙万物生化的力量。“乐者,天地之和也”说明阴阳之道和谐有序的运动,正是天地之大美所在。而宇宙的和谐包涵了音乐的和谐,天地大美实际上就是音乐之美。阴阳之道是指宇宙间天地万物的运行变化规律,即自然之道。以乾坤两卦为核心,天地万物为范围,演示阴阳刚柔的交合变化,这就是易道的自然属性。音乐为天地万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自然之道是音乐的本体。所以,《周易》的和是充满发展和变化的,并且吸收了春秋期间“以和为美”的观念,用来补充“中和”之美。道家的和谐,是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之上。《乐记》也是把音乐放在天地之间,以天地之和为音乐和谐的依据,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观点,从天地万物的自然运动中引导出音乐和谐的本质,其根本还是在易道。庄子进一步指出,只有顺应天和,才能实行人和、天下和,也就是无为之治,使人各安天命,将天地之和作为人和、心和的最高标准。与春秋期间儒家学派的“和”相比,道家的“和”更加看重天地之和的自然无为,是一种非道德非伦理的自然和谐,道家认为最高境界的和谐美存在于精神领域,宇宙一切具体事物都是有限的、有差别的,只有万物背后的道才是不偏的。因此,“和”才是道,才是大美。庄子认为,只有超越时空、生死和自然的特性才是大美、至乐。要达到这样的精神境界,就要追求精神的自由和性情的和谐。
阮籍在《乐论》中说:“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3]16-17乐,是天地之和的体现,而和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因此,想要获得音乐和谐就得“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而“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就是自然之道,所以也是音乐和谐的根本。所以阮籍以对易道的体会将天地之体、自然之道作为音乐和谐的最高本体。儒家的“中和”是将对立的两端加以调和统一,而道家的“和”却并非将矛盾均衡化,而是主张消除差别,融合矛盾,从而达到一种无差别的“大和”境界,“道”能否与主体相一致,关键在于修德。因此,庄子推崇的“德”是摆脱外界的束缚,平静如水,使心境纯正如一,这样就能进入“物化”的境界。
儒家追求“大乐与天地同和”表现在“以和为美”的追求上,“和”的本意是表现一种关系与状态的和谐。古代的哲学家认为,宇宙间的自然与万物虽然不断在运动变化,但同时又处在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中。阴阳的交替,万物的生长与灭亡,都是遵循这种“中和”的自然规律的。所以,“‘中和’既是人道,也是天道。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遂形成一种和乐与尚‘和’的文化传统”[4]93所以,在人的审美意识中,人与自然、与社会都应该是和谐统一的。所以,“和”是社会万物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依据。所以有“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同时,“和”也是人生美学所追求的审美领域。作为美学范畴,《尚书·尧典》是最早谈到“和”的,其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中的“和”是指音乐应该达到一种与自然、与天地和谐统一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乐记》中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
“和”在审美领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和”体现了自然宇宙本身的和谐,这也是天地万物间各因素的和谐统一。其次,中国美学强调“天人之和”“天地之和”,体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之美,达到人与自然界审美的最高领域。再次,“和”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强调“允执其中”,行事不偏不倚,以“中庸”“中和”为统一个体与社会和谐的最高审美原则。如“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因为“和”必须“比中而行”,所以人们实现情感与道德、个体与群体的和谐统一是必须以礼为前提的。儒家思想将礼与“中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礼乐统一、以道制欲的美学思想。最后,儒家美学强调人的道德与情感、内在与外在都必须达到和谐统一。
三、“和”的教化作用
在周代雅乐体系中,钟和钟乐成为区分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到春秋末年以后,礼崩乐坏,社会上开始有对钟乐的僭越。史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将铸一套无射律的编钟,并在其下方小三度加上一个声高为“大林”的钟。按乐律来看,并没有违反西周编钟设计上“钟尚宇”的规律。但却遭到了单穆公的反对,他从国家财政、听觉审美、乐以通政的角度来劝阻。而周景王却未听从劝阻,问于伶州鸠。伶州鸠从乐器制度谈起,从“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的角度来劝阻。在单穆公与伶州鸠看来,“大林”的音域比较低,撞击之后产生的泛音使人听之并不和谐。而钟声是否和谐是以人耳的听觉感知度作为检验标准的。从他们的劝辞可以看出,一方面强调钟声和谐才能内心和谐,听觉的和谐必须以乐音的和谐为条件。对于人来说,外界的和谐才能导致内心和谐,达到主客体相融合的境界。另一方面乐音的和谐必须以乐器制度和乐律制度为基础。他们劝阻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铸无射而为之大林”,而是想劝周景王不要铸钟。他们担心的也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不和,而是为了避免因铸钟而导致国库空虚、政治动荡等一系列后果。“声和——心和——人和——政和”的思维模式一直贯穿在他们的观念中,由此可见,在单穆公和伶州鸠的思想中,“和”这一审美概念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将“和”的认识从音乐理论扩大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一时期“和”观念的发展对先秦各家思想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旧的礼乐系统面临深刻的危机。孔子的“中和”美学思想,是建立在礼乐文化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更加强调用道德来规范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比单穆公、伶州鸠的思想更加带有政治色彩。孔子认为,要实现“中和”的思想,必须以礼义来节制。所以孔子的“中和”结合了殷周的礼乐思想和春秋以来“以和为美”的观念,并将“中和”与礼义结合起来,因此既有道德方面的因素又有了礼法的成分。后来的荀子便从礼法与道德两方面发展了孔子的“中和”思想,对后世的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强调“中和”是天地的纲常对人情的规范与约束。天地间万物的井然有序、生生不息就是“礼”的和谐,而人世间与天地间的秩序都是礼义规范制约所致,夸大了“礼”的作用。荀子认为,“礼”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作用,关键在于“分”。使万物皆得其宜,持其中行,互不错位,“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只有“分”,才能使和谐建立在礼义有序、贵贱分明的社会秩序之上。他的和谐论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从人性论来说,他认为人生来就是存在各种欲望的,这种欲望是天然合理的,但必须以礼来引导、调节。礼义是使人的情欲合理满足的前提。所以,“中和”之美与封建大一统的专制思想在荀子这里已经产生了萌芽。因此,儒家学派的“和”不但包含音声的和谐,还强调音乐的“雅正”。所以,《礼记·乐施》中有:“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5]48可见作者强调乐的教育比礼的教育更加重要。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前提是礼乐的制约,艺术是和谐之情的表现。阮籍在《通老论》中也说:“圣人明于天下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这说明生活的和谐也是由于礼的制约。儒家心中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秩序之上的。
儒家美学认为,在这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中,为表达人心中的愉悦,产生了欢乐的音乐。阮籍在《乐论》中说儒家认为音乐的本质就是“和”,也就是快乐。还以夏桀、商纣和胡亥为例,认为他们爱好悲哀之乐才会导致亡国,所以应该坚决摒弃。他认为凡是不能表现“中和”之意,不能表达愉悦之情的就会导致阴阳失和,这样的音声只能称之为哀。儒家还认为悲哀之音使人气息紊乱,内心不再平和。《乐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有:“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奈何俯仰叹息,以此称乐乎?”他认为不符合“中和”要求的,不能表现愉悦之情的,只能称之为“哀”。这样的音声使阴阳不调,人心紊乱,甚至有亡国之祸。所以他明确反对哀怨之音,推崇正乐、雅乐。这样不仅对音乐造成了限制,也使审美对象有了局限性。到了两汉时期,更是将儒学与政治教化结合起来。以儒学为法度,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却轻视个体的价值,因此导致了汉魏美学的发展与解放。董仲舒的“中和”之美,承袭了《周易》的思想,赋予天以情感色彩,一方面将天人格化,另一方面将人自然化,并使二者互相沟通。他通过政治、“中和、至和”强调人以天道为本,阐述人和以天和为本,天和决定人和,天、人是相互感应的。这样的思想明显带有了封建专制政权的色彩。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最为繁盛的时期,“和”的审美范畴也比两汉更为深入,正始年间的王弼、何晏吸取了老庄的学说并根据道家的理想人格从玄学角度论述“和”的境界,即主体以虚静无为的状态才能进入遨游于万物之中的精神境界。因此,这一时期美学思想中的“和”除了吸收先秦两汉儒家的“中和”观念之外,还加入了玄学的成分。所以嵇康提出 “和声无象,哀心有主”,以玄学的“和”来解释传统儒家的乐论之“和”。与汉代相比,文学已经摆脱了儒家经学的束缚,开始探索音乐的内部规律和特殊性的问题。道家思想逐渐突显出来,其既与儒家思想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与儒家思想有融合互补的一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6]117
[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袁济喜.和:审美理想之维[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3]李生龙.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M].长沙:岳麓书社,2009.
[4]李天道.儒家以仁义求同乐之人生审美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