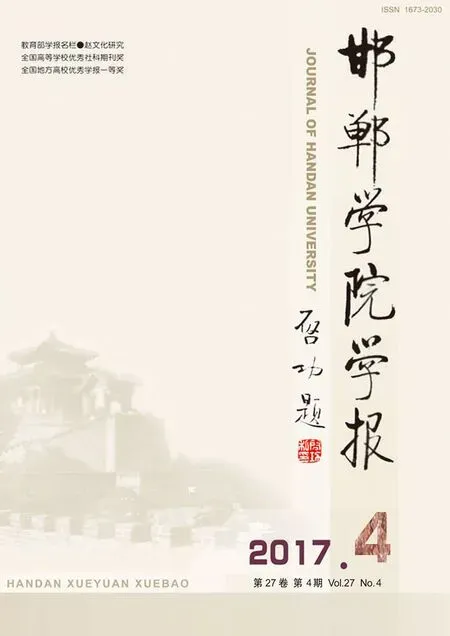论李春雷报告文学语言的诗化特征
李 铮
论李春雷报告文学语言的诗化特征
李 铮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李春雷创作的报告文学在语言上有着诗歌的风格与特点。注重语言的跳跃性,营造有韵味的诗意“空白”;同时讲究语言富有节奏韵律之美;为传达细腻、幽微的感觉,作者大力借鉴诗歌建构意象的方法。正是因为这些鲜明特点,李春雷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地位和影响,显得异常卓越。
李春雷;报告文学;诗化;跳跃;节奏;意象
河北作家李春雷从20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如今已发表作品 700 余篇,其中以报告文学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蝉联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代表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等19部,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余篇。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鉴于此,他被评论界誉为“中国短篇报告文学之王”,这是当之无愧的。”[1]
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类报道写作,强调记录真实,反映真实,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随着时代的发展,报告文学日渐繁盛,但也浮现诸多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艺术角度来看,现在的报告文学,不少只是报告,没有文学,……过于粗粝和简陋,缺乏艺术的再生力和感染力。”[2]20由此可见,文学性的不断缺失已使报告文学的艺术性大大受损。有评论进一步指出:“我们很多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缺失,主要是语言艺术的缺失。我们很多报告文学的语言已经公文化、新闻化,甚至垃圾化了。那些语言,没有任何水色和灵气,就像锯木机下的木渣。”[2]21很明显,在评论家看来,语言艺术的缺失正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缺失的关键。
然而,李春雷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语言却非常富有文学性。如雷达指出,李春雷的作品有“出色的想象力,开阔的眼界”和“他那不时显现的诗化的叙述格调”。[3]李良亦持同样看法,“作家李春雷出道于新闻写作而不为其羁绊,以诗化的语言、散文的笔法行文铺排,文字不张扬却很有质感,极富表现力。”[4]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结合具体文本,分析李春雷报告文学语言的诗化特征,揭示其作品的艺术魅力,或可为当代的纪实类文学的创作提供语言与叙述上的一些借鉴。
一、语言的“跳跃”与“留白”
诗歌语言的特点之一便是跳跃性。古典诗歌、诗词的语言、诗句之间的内容和时空的跳跃十分明显。小说和散文的叙述、描写语言一般连贯而完整,然而在诗歌的创作中,由于文体本身字数所限,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用充足的文字展开一个完整的场景或者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诗人常常让诗歌句子中的词汇、句子之间进行跳跃式的组接与拼贴而不使用任何过渡文字或关联词语,所以诗歌语言常常体现出不连贯、不完整的特点。但是,在诗人去掉想象、事物、时空之间的表面联系及句子中表达诗意的关联词后,文本看似变得分崩离析,却没有使诗意变得支离破碎,反而从诗人情思的内在联系上更大地概括和扩张了诗意。如温庭筠在《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种语言的跳跃,既能使诗词更加精练,又能使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清代中期文学家及著名思想家方东树认为,诗人写诗“语不接而意接”[5]414,正是这种跳跃,使诗人减少了不少空间转换和事件发展的叙述语言,反而使诗歌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还促使读者以想象去联结、补充语言跳跃留下的各种空白,从而为想象展开了一番全新的天地。
正如这首《商山早行》,作者温庭筠对意象进行跳跃式的组合,仅仅是“鸡声”、“茅店”、“月”和“人迹”、“板桥”、“霜”这六个意象的拼贴,就勾勒出了旅人商山早行的场景:清晨清冷空气中回荡的声声鸡鸣,深蓝的天幕上闪烁的星星和还未落下的月亮,弯曲道路上一座空荡的木板桥,上面的白霜拓下了早行人的足迹。这样的场景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思考空间,如此诗味,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李春雷报告文学的创作中,亦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借鉴诗歌语言方式,运用简洁的字句进行意象的拼贴、组合,以进行审美的再造与审美场域的建立。
在2014年发表的《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中,关于习近平与贾大山初次见面的场景,作者就巧妙地采用了这种方法。习近平与贾大山第一次见面时并不是很顺利。由于习贾两人相互之间并不了解,加之年轻的习近平刚到正定县任职不久。两人第一次见面,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根据作者考证,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两人初次见面,遇上这样的情况可以说非常尴尬,这种尴尬情况对作者的表现能力是一个挑战。然而,更难的地方还不在此处,而在于两人在最初的尴尬后,很快便相视一笑“泯恩仇”。这个过程在日常的生活中并不鲜见,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一般写作者却极难用文字恰如其分地传递出这种转折的巧妙感觉。然而,在这里作者显示出了极为深厚的功力,非常巧妙地写到:
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抑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贾大山还不到40岁,已获得全国大奖,作品收入中学课本,声名正隆,风头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依然笑容满面。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但不一会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主人和客人,已经握手言欢了。
作者在这里首先简单交代了背景,然后选取了“停滞”、“尴尬”、“重新活跃”、“握手言欢”这几个场景进行跳跃式的组合,故意略写了其中微妙的转化。最令人称奇的是,联系作者在上文寥寥数语介绍的背景后,这种充满了诗化语言特征的“跳跃”非但没有显出缺失与不足,反而充满了叙事的张力,使整个过程在读者脑中丰满和充盈起来,这无疑与古典诗词的写作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习贾二人由初见面的尴尬到握手言欢,这个极为微妙难言的过程对一般写作者来说极难表达得恰到好处。然而在李春雷的笔下,这个困难被作者以充满诗化特征的巧妙语言和精心布局给一一化解,不露痕迹不动声色地将这个生动的见面场景传递给了读者,充分展现出了诗化语言的奇妙之处。
同样的手法在《南寺掌——“我的抗日战争”纪实之八》这篇文章中也有体现。文中的主人公——禄元媳妇,是南寺掌村中的积极分子,某天她接到任务要为八路军制作一批军装。在作者笔下,制作军装的布匹染色过程运用了诗化的语言手法进行处理:
领回来的布匹全是白土布,需要染色。…… 火光熊熊中,水气腾腾中,一块块土白布变了颜色,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变成了大地的颜色,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变成了八路军的颜色……
寥寥数语,勾勒简练,没有用写实的手法具体写白布染色的具体过程和步骤,而是用“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变成了大地的颜色,变成了树皮的颜色,变成了八路军的颜色”这样的诗化的语言来一笔带过。在这里,作者“省略”了很多内容。如何架灶支锅,如何盛水烧火等等,这一系列具体而又详实步骤,作者都没有在文本中表现。然而,一块白土布在大锅中渐渐翻滚慢慢着色的这个过程,却充满诗意地在读者心里扎下了根。作者用这种手法,写出了一般报告文学语言缺乏的一种诗意之美。
在《太行八勇——华北民间抗战人物之一》这篇文章中,作者写到:
战场上的破废枪支、弹壳,拆毁的铁轨、汽车,还有从民间收来的废铜烂铁,纷纷向这里跑来。大丰沟里热火朝天。不长时间,龙泉观院子里装满火药的地雷、手榴弹便堆成了小山,像山民们秋后收获的核桃、黑枣。而后,一夜之间,却又全部飞走了……
这段文字记述了大丰沟枪械所,也就是后来闻名军史的晋冀鲁豫边区最大的兵工厂——西达兵工厂前身最早的运转情况。在作者笔下,“废铜烂铁”会“跑来”,“地雷、手榴弹”能“飞走”,在纪实类的作品中,一般作者很少会使用这样的语言,因为一旦下笔不慎就极易被诟病为“不真实”或“虚构”。但事实上,“虚构”与“非虚构”之区别并不在于一两个具体的词语或是句子,而在于作者的叙事能多大程度上符合人们的“心里真实”。而作者的诗化“留白”语言,一方面满足了文字表现的艺术需要,一方面又符合了人们内心可以接受的“艺术的真实。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仍然用诗化语言来艺术地处理这个枪械所的生产步骤。四处的破旧金属都被运到这里来,然后很快生产的产品便“堆成了小山”,像村民们收获的“核桃”与“黑枣”,然后一夜之间又“全部飞走”。同上文一样,作者没有将枪械所详细的生产步骤一一写出,但这一“来”一“走”,却将枪械所生产的大致运行情况生动地传递给了读者,那热火朝天的生产场面与生产出的“累累硕果”,这个过程如同放电影一般在读者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复写着。
二、节奏韵律之美
诗歌语言的一大特点是句式整齐,韵律和谐。诗歌也因此读起来节奏感鲜明,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颂。语言的音乐美,在诗歌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诗歌是一种最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艺术,特别讲究韵律谐美,悦耳动听。……因此,它要根据感情的性质、变化安排语言的节调、韵律,从而准确地传达生活的节拍、音响,恰如其分地表现跌宕起伏的感情,形成一个情思、声调谐美的艺术整体。”[6]160
从这里可以看出,节奏与音韵是诗歌独有的传情达意的利器,诗歌的这种特点是其他任意文体都难以比及的。郭沫若说;“节奏之予诗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没有诗是没有节奏的,没有节奏的便不是诗。”[7]229这其中,《诗经》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诗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诗歌典籍。其中的诗歌,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典范。“《诗经》作为诗歌需要达到语言优美、韵律和谐、节奏铿锵、句式整齐等诗化语言的基本要求,逐渐形成了以四言二拍为主的基本旋律。”[8]100节奏和音韵都是诗歌传情达意的重要手法,《诗经》之所以能够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无论是内容上充满感情色彩的渲染抒情,还是朗朗上口的口头吟咏传唱,都与它自身的节奏与音韵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春雷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吸取了古诗在音韵、节奏上的这些特点,接纳了诗歌语言中押韵、对偶、叠词等这些修饰手法;同时借鉴诗歌语言短小精练的特点,有意运用一些文言句式,同时对长句进行合理的拆分,精当地运用标点符号增加停顿。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使作品的语言精短,玲珑精美,节奏和谐,顿挫有致,更具诗化特征。
在李春雷的成名作《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密密麻麻的人们粘在高炉上,白天太阳是灯,夜晚灯是太阳,像蚂蚁搬家一样把一块块耐火砖、一块块冷却壁衔接上去,像蜘蛛结网一样把一道道进水管、进风管、测温管盘绕在炉体内外;像蜜蜂筑巢一样把一个个渣口、风口、铁口镶嵌在炉壁上……
这段描述有很强的节奏感,“白天太阳是灯,夜晚灯是太阳”;同时又有着类似于近体诗的对仗,“像蜘蛛结网一样把一道道进水管、进风管、测温管盘绕在炉体内外;像蜜蜂筑巢一样把一个个渣口、风口、铁口镶嵌在炉壁上……”这样的手法既突出了工人们夜以继日的辛劳,也从侧面将高炉的建设介绍给了读者。蚂蚁搬家,蜘蛛结网,蜜蜂筑巢,这三个词语不仅能从叙事上将高炉建设过程生动形象地展现给读者,也能构成修辞上的排比,可谓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在《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中,作者记述了贾大山的创作过程:
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打腹稿。构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冥想,一枝一叶,一蘖一苞,苞满生萼,萼中有蕊,日益丰盈。……三番五次之后,落笔上纸,字字珠玑,一词不易,即可面世。
这段描述充满了诗歌语言的特色,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还抑扬顿挫、节奏鲜明,如江河直泄,滔滔不绝。这样的行文将抽象的创作过程一一具象,让读者读起来气脉畅通,酣畅淋漓。
同时,这样的方式更加突出了贾大山本身的创作能力。1978年,贾大山以小说《取经》荣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全国文学界,一度与贾平凹齐名。这样一个作家,他究竟是如何创作的?又有哪些异于常人的地方?显然,作者通过这样诗意化的叙述,跳出了过分拘泥于细节“现实”的窠臼,不仅生动而鲜活地向我们勾勒出了贾大山异于常人的创作过程,更着重体现了贾大山本人作为一个优秀作家所拥有的敏捷才思。
同样还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写景铺陈时同样运用了充满节奏张力的诗化语言。如“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岁月如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春、夏、秋、冬的一联四字句,季节上春夏秋冬依次承接,语言上采用了四字句并列,不仅在景物描写上有类似于国画技法中淡笔勾勒的手法,而且读起来节奏铿锵,简短有力,铺排适当。这无疑在报告文学的语言中是颇为少见的。
在《木棉花开》中,当任仲夷刚到广州任职时,作者这样写到:
省委大院里植满了榕树,这南国的公民,站在温润的海风中,挂着毛毛绒绒、长长短短的胡须,苍老而又年轻,很像此时的他。但他似乎更喜欢木棉树,高大挺拔,苍劲有力。二月料峭,忽地一夜春风,千树万树骤然迸发,那硕大丰腴的花瓣红彤彤的,恰似一团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又如英姿勃发的丈夫,用刚健的臂膀傲然挽起娇美的新娘,虽然来去匆匆,却也轰轰烈烈。
任仲夷刚到广州时,肩负着广东改革开放建设的艰巨任务。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试办经济特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一项前途未知的工作。面前不平坦的路途之下隐藏着一个个地雷炸弹,背后则更是十几亿人聚焦的目光。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作者用巧妙的文学语言将任仲夷的心境写出。
到广东上任时,任仲夷已经66岁了,但是他即将开展的工作则是中国历经了苦难之后崭新的探索,作者首先用“挂着毛毛绒绒、长长短短的胡须,苍老而又年轻”这样的语言,而后又巧妙地化用了唐代诗人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写木棉树,他笔下的木棉树花瓣是“红彤彤”的,“恰似一团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像一位英姿勃发的丈夫,“虽然来去匆匆,却也轰轰烈烈。”
这段文字描写运用叠词,巧用标点,在音韵上回环往复,在句法上短小精炼,是李春雷语言诗化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如此,在这诗意的语言背后,却传递着更为深广的内涵。
熟悉时代背景的读者都十分清楚,这段文字的描写虽然充满诗意,但是这背后,不正是任仲夷克服千难万险,下定决心在广东力行改革的真实写照吗?作者虽用诗意的描写将这个过程与心境写出,但现实往往是真实而残酷的。用诗化语言的柔美来处理坚硬如铁的事实,两下对比,体现了跨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审美张力,体现出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三、以意象传递感觉
意象在诗歌的语言当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诗歌的创作就是诗人寻找客观事物作为意象、建构意象语言、从而使其主观情感能够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的过程。意象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着强大的力量,它借用生活中常见的具体形象或画面来比拟地表现人们在理智和感情等诸多方面的独特体会和经验;从形象描绘和感情描绘相结合的角度写景抒情,寓主观情感、深刻哲理于客观事物的形象描绘之中;它还具有丰富的审美属性,带给人们美的感受和启迪,具有突出的美学功能。总之,诗歌意象语言的形象描绘功能和感情描绘功能,使诗歌意象语言带给人们外在形式和内在意蕴的双重美感。
除了上文列举的两个特点之外,李春雷在创作中擅长利用各种意象传情达意。他把难以捉摸的感觉用可视可触的客观物质来形容,用具象形容抽象;同时擅用富有想象力的诗化语言来逼真地描摹事物细节;他的描写极富张力,不仅可以用极具诗意的语言睥睨山河,又能用极细微的笔触举重若轻。大小对比之间,文字的张力毕现。这种特征鲜明的诗化语言不仅使文本更加形象生动富于可读性,更重要的是,它使文本从清晰的真实中蒸腾出一种诗歌一般的亦真亦幻意境之美,从审美上更上一层楼,直击了人心深处被日常语言与感觉所麻木和遮蔽了的那种最微妙的突触。
人内心抽象的感觉最难用语言进行具体地描绘。但在反映汶川大地震的名篇《夜宿棚花村》中,作者用独特的语言传递了遭受震灾的小村之痛:
震后又下起大雨,全村人跪在山坡上,以手掘土,就地葬埋了死者,大人们像孩子一样嚎哭着,孩子们则像大人一样冷峻。恐惧像四周的大山一样黑魆魆的,那是鬼魅的影子?直到两天后,外面的援救才进来。但是,身受重伤的小村像一条刮去鳞片的鱼,时时疼痛,撕心裂肺的疼痛。[9]205
遭受了灾难的小村是无疑是痛苦的,然而这是怎样一种痛?又该怎样将这种感受真实地传达给读者?显然,抽象的痛是无法直接描写的。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充分发挥了自身独特的语言功力,“大人们像孩子一样嚎哭着,孩子们则像大人一样冷峻。”这描述很值得玩味,大人像孩子一样嚎哭,孩子像大人一样冷峻,大人与孩子的身份与表现令人惊奇地出现了与正常生活秩序下截然不同的异位。虽然初看奇特,但细细想来却符合情理。在大自然的伟力面前,崩摧异位的不仅只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也同受重创。从大人与孩子产生近乎“精神分裂异位”式的表现这一点来看,大地震之下山河的崩摧异位,同样也带来了人们精神世界中秩序的崩溃与错置。这场地震的威力无疑给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双重打击。作者的描述还没有结束,在第一轮的精神打击过后,“恐惧像四周的大山一样黑魆魆的,那是鬼魅的影子?”在这里,人们从最初慌乱中稍微平静下来的内心又开始颤动,恐惧的滕蔓在人们心底滋生蔓延出来,紧紧地绞缠着人们已经脆弱不堪的内心,“身受重伤的小村像一条刮去鳞片的鱼,时时疼痛,撕心裂肺的疼痛。”作者将小村比作一条鱼,鱼刮去鳞片后的痛苦不难想象,借用这种痛来借比小村所遭遇的苦难,可谓是直抵人心的神来之笔。
痛苦与快乐是人最为重要的两种情绪。作者的语言不仅能极为微妙地将人心底的苦痛描绘,同样也能将人眉宇间难察的欢愉托出。
在《木棉花开》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任仲夷愉悦心情的文字。当时,广东省委拟派梁湘赴深圳特区任职,但出于种种原因,梁湘不愿赴任,矛盾在此激发。面对这种情况,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约谈梁湘,两人畅谈至深夜方才云开雾散。在结尾处,作者这样写到:
任仲夷猛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着。雪亮的灯光下,浑圆的银白色的笑声在四壁间清脆地撞击着、回响着,他头上的丝丝白发也仿佛是一绺绺导电的钨丝,在闪烁着明晃晃的辉光。
迷雾散尽,玉宇澄清,双方自然是皆大欢喜。作者在这里同样运用充满诗化特征的语言充满想象力地描写了任仲夷的“笑声”与“白发”。在作者笔下,笑声是“浑圆的”,是能一扫阴霾的亮亮的“银白色”;同样,它也能在“四壁间”清脆地“撞击”、“回响”的。任仲夷头上的白发则成为了“导电的钨丝”,在雪亮的灯光之下,“闪烁着明晃晃的辉光”。这段描写中,作者通过形象的比喻和语言节奏、色彩来将笑声赋予了形状、颜色、甚至声音之后的“声音”,将带来欢愉的因素由单纯的笑声本身扩展到了颜色,甚至是笑声“碰撞”带来的又一重声音;将白发形容为导电的钨丝,闪烁着光芒,这不仅仅是灯光的光芒,更是智慧如电,在思维的网络中畅游而发出的光辉。在这几个方面的诗意描写下,作者将各种无形、无色、无声的客观事物一一具象化,单纯的笑声超越了仅仅是难题解决之后狭义的愉悦,而更多的扩展到了更大的空间中,闪耀的白发也不仅仅是灯光下的景象,而是被涂抹了象征着未来更加光明的色彩。
李春雷的语言极富想象力,在对事物富有想象力的精细描摹上,突出体现了他语言的诗化特征。在《枣花吹满头》这篇文章中,作者就运用充满诗化想象的语言进行了书写:
在中国北方平原乡村,枣树可能是春天里最后一个醒来的植物。惊蛰清明,谷雨小满,当春天的锣鼓铿铿锵锵地敲响的时候,当敏感的春花如花蕊夫人般争先恐后地粉黛登场的时候,它却像一个懒散的老农,穿着皂黑的粗布棉袄,仍然蹲在阳光下打盹儿。直到芒种过后,它才瞪开惺忪的眼。一旦醒来,便厚积薄发,排山倒海。
这段文字对小堤村的枣树进行了富含诗意的描写。将枣树比作一个“懒散的老农”,在春季的锣鼓“铿铿锵锵地敲响的时候”仍然在打盹,等到芒种过后,才“厚积薄发,排山倒海”。作者用极具特色的诗化语言进行书写,充满美感地写出了春季枣树的生长特点。
他的描写极富张力,收放自如。睥睨山河的气势将宏大的环境描写微缩于股掌之中:
在《摇着轮椅上北大》中:
如果说南方是一株四季常绿的大榕树的话,那么一条条大江大河就是它粗壮的躯干。那一条条横七竖八的支流呢,就是它茂密的枝杈了。那些密如蛛网的无名的河流汊湾呢,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大榕树身上千千万万根毛茸茸的胡须了。而那些生活在水边的人群呢,就是它枯枯荣荣的叶片了。它们共同组成了南方深密的历史,又鲜活地站在南方的晚风中,不知疲惫的摇曳着,细语着,酿造着南方特有的风情和灵秀……
作者将广阔的南方地区比作一棵榕树,粗壮的躯干是大江大河,横七竖八的支流是茂密的枝杈,再小一些的汊湾则是树上挂着的毛茸茸的胡须,人们则是枯枯荣荣的叶片。这种充分发挥的想象力与艺术的感受力,不仅准确把握了南方地区、流淌的江河、随处可见的河流汊湾、依水而生的居民之间的关系,更用诗一般的语言极为形象地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书写,充分体现出了作家超强的艺术感受力、想象力、表现力。作者站在高山之巅的广阔视野与心细如发的纤毫笔端构成的文本张力在这里显现无遗。
四、结语
在当今纪实类文学的创作中,“记录真实”的旗帜高扬,但“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大纛却没有真真正正地飘扬起来。或许,如何处理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正是让这两面大旗同时飘扬的一个极大障碍。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外的非虚构写作传入中国,引发了一股新的热潮。然而在这股热潮背后,大量应运而生的作品仍旧存在着语言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巨大缺失。在这双重背景下,李春雷报告文学作品的语言诗化特征,或许能给我们处理类似问题以极大的启示,而此亦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
[1]李炳银. “天机云锦用在我”[N]. 光明日报,2013-04-16(014).
[2]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报告文学艺术论[M].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3]奏响时代的音符:李春雷报告文学创作回眸[J]. 文艺报·周六版,2009(15).
[4]李良. 报告文学的“硬”与“柔”——从李春雷《木棉花开》说起[J]. 长城,2010(3).
[5]方东树. 昭味詹言[M]//张葆全. 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词典.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6]张海宽. 诗歌创作漫谈[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
[7]郭沫若. 论节奏[M]//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8]孙力平. 中国古典诗歌句法流变史略[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9]傅溪鹏. 2008中国报告文学年选[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I207.5
A
1673-2030(2017)04-0102-06
2017-09-10
2017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702050101)阶段性成果
李铮(1992—),男,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文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