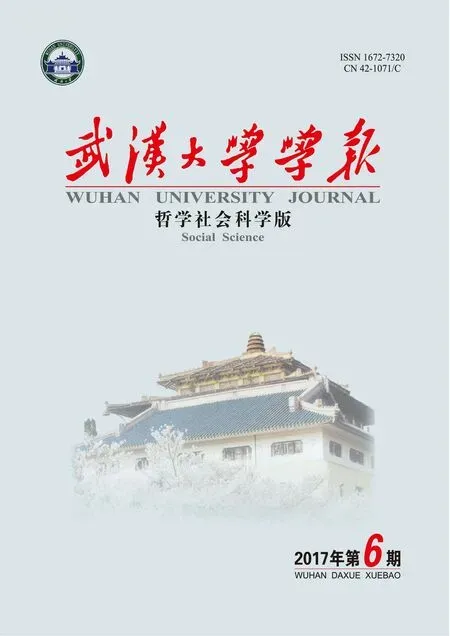自然主义与目的论
——兼评蒯因的本体论
陈晓平
自然主义与目的论
——兼评蒯因的本体论
陈晓平
蒯因的自然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显著标志是把哲学化归为自然科学,把认识论化归为经验心理学或进化认识论。无论实用主义还是进化论都与目的论密切相关,这使自然主义与目的论有着不解之缘。“自然”概念和目的论的结合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就体现出来。康德提出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进一步为目的论奠定了哲学基础。由于蒯因摈弃了包括目的论在内的全部先验哲学,这不仅使自然主义失去根基,而且使其充斥矛盾,这在其本体论中显得尤为突出。
自然主义; 目的论; 本体论; 实用主义; 蒯因
当代自然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蒯因把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自然主义的理论来源,进而将超越自然科学的“第一哲学”和传统认识论予以取缔;或者说,他把哲学归入自然科学,把认识论归入经验心理学或进化认识论。不过,实用主义不可避免地与目的论相关联,因为所谓“实用”就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这使得自然主义与目的论有着不解之缘。其实,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结合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体现出来,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又与康德的目的论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探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目的论及其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自然主义思潮是十分必要的。
一、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与目的论
“自然”这个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他的“物理学”就是关于自然的学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是与“目的”密切相关的,他说:“自然就是目的或‘为了什么’。”(亚里士多德,1982:48,194a)不过,“自然”的含义并非单一的,亚里士多德将它与所谓的“四因”联系起来,这四因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虽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却有较多的含混之处。例如,亚里士多德有时把除质料因以外的其他三因合并起来,从而使四因变成二因或三因。他说:形式、动力和目的这“后三者常常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形式和目的是同一的,而运动变化的根源又和这两者是同种的”(亚里士多德,1982:60,198a)。不过,他更多地强调目的因与形式因之间的同一性,说道:“既然自然有两种涵义,一为质料,一为形式;后者是终结;其余一切都是为了终结,那么,形式该就是这个目的因了。”(亚里士多德,1982:64,199a) “形式或实体是生成的目的。”(亚里士多德,2003:90,1015a)
需要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把“形式”和“实体”联系起来,从而把“目的”与“实体”或“现实”联系起来。他解释说:“质料潜在地存在着,因为它要进入形式,只有存在在形式中的时候,它才现实地存在。”(亚里士多德,2003:187,1050a) “现实就是目的,正是为它的潜能才被提出来。动物观看并不是为了有视觉,而是有视觉为了观看。”(亚里士多德,2003:187,1050a)
潜在的质料通过具有某种形式而成为现实存在的实体,而这正是目的。须强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现实或实体主要是指动态的功能如观看,而不是静态的对象如视觉。这意味着,与目的密切相关的是具有某种功能的动态实体,这样的实体正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功能系统。据此,当亚里士多德说“一切实体都是自然,因为自然总是某种实体”(亚里士多德,2003:90,1015a),其确切的意思是:一切功能系统都是自然,自然总是某种功能系统。正因为看到这一点,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明确地指出,系统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目的性”,“这是亚里士多德首创的概念”(贝塔朗菲,1987:73)。
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的多种含义进行分析之后总结说:“自然的原始的首要的意义是,在其自身之内有这样一种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发轫于此而被称为自然。”(亚里士多德,2003:90,1015a)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使质料和运动成为自然的实体是什么呢?答曰:形式和目的。不过,形式和目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存在于事物“自身之内”的“运动本原”。
目的是存在于事物自身之内的运动本原,这不难理解;但说形式也是如此则有些费解。其实,亚里士多德对此也颇费踌躇,以致他有时又说出相反的话,如:“于没有运动变化的对象,就是指‘形式’。”(亚里士多德,1982:60,198a)按此说法,当质料通过形式而成为现实,那对象是指静态的实体,而不是动态的实体,如一块放在地上的石头。
笔者倾向于保留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的静态说法,以此让“四因”各司其职,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不至于把四因归并为二因或三因。四因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当质料通过形式而成为现实的,那现实的对象是指静态的实体;与之不同,动力为达到目的而产生的结果则是一个动态的实体即功能系统。可见,质料因和形式因比动力因和目的因低一个层次,前二者形成的是静态实体,为后二者形成的动态实体即功能系统提供了结构要素;或者说,后二者形成的功能系统以前二者为基础而实现了自己的动态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对于功能系统而言是恰如其分的,这使其原先存在的一些混乱之处得以澄清和协调。在这里,关键是把实体分为静态的和动态的,静态实体是动态实体即功能系统的结构要素。
既然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在其自身之内有这样一种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那么一切自然过程都是动态的,因而都是有目的的;如他所说:“自然是一种原因,并且就是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1982:65,199b)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件自然的事情就不可以不是为了目的,也不是因为这样比较好些,恰如天下雨不是为了使谷物生长,而只是由于必然呢?”(亚里士多德,1982:62,198b)尽管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专门用一节来回答,但是他的回答主要是在人工事件与自然事件之间作类比,因而难免是牵强附会因而缺乏说服力的*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章第八节。。
我们不妨把这一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但却没能解决的问题称为“亚里士多德问题”。亚里士多德问题非常重要,涉及目的论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对这个问题给予彻底回答的是康德,即把“合目的性”作为一条先验原则引入。
二、康德的先验目的论与自然进化论
康德的一句名言是“人为自然立法”。如果说,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着重于讨论人如何为自然确立“因果律”之法,那么,在其《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着重于讨论人如何为自然确立“合目的性”之法。康德说道:
“在自然的纯粹机械的因果作用不能使我们足够前进到远处这种情况下,为目的所确定的自然中的结合与形式这个概念,至少是又一条原理把自然的现象归结为规则的。因为我们的这样做是提出一个目的性根据,我们从而赋予对象的概念——好像那个概念是在自然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发现似的——以关于这个对象的因果作用,或者应该说,我们从而和这种的因果作用作类比——就是和像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所经验的因果作用作类比——来描写这个对象的可能性,而这样就把自然看为是具有它自己在技巧上活动的一种能力。”(康德,1987:5)
康德在这里所说的自然是目的性自然,相应地,这里所说的原因是“目的性原因”或“目的性根据”,它是因果律之外的“又一条原理”,用以“把自然的现象归结为规则的”。这条原理康德常称为“合目的性”,并强调自然的合目的性本质上是人赋予的,是人的合目的性的“类比”或外化,从而使得“好像那个概念是在自然里面而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发现似的”。
康德明确地宣称:“自然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是判断力的一个超验(先验论的)原理。”(康德,1964:19) “为了自然的可能性,判断力也是一个先验原理,但仅在主观方面,借助它提供规律以指导对自然的反思,这规律不是给予自然的,而是给予它自己的。”(康德,1964:24)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是人为自己立法,进而指导人们为自然立法,即先验的因果律;因此,合目的性原则比因果律更为基本,尽管二者都是先验的。
关于前一节所提到的亚里士多德问题,康德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并给以回答:“最后就有了这个问题:这一切上面的自然各界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和什么缘故的呢?我们说,是为着人类的,……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唯一无二的存在者能够形成目的的概念,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的。”(康德,1987:89)
我们看到,康德把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合目的现象归结为合乎人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对象本身的目的。这也就是说,只有人具有内在目的,而其他对象的目的虽然貌似内在的,其实是人从外面加入的。这样便回答了亚里士多德问题,即:“为什么一件自然的事情就不可以不是为了目的,……而只是由于必然呢?”对此,康德的回答是:因为人是有内在目的的,而其他一切自然事物的目的最终都是人的目的,而不是它们本身“必然”具有的;只有人的合目的性是必然的和先验的。
在先验的合目的性原则的指导下,人们为自然立法,使自然中的各种事物“好像”具有各自的合目的性和因果性。康德举例说:“在谈到鸟的构造时,例如举出鸟骨的形成中空,鸟翼的位置的利于飞翔,鸟尾的便于转向,是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单单看自然中的有效关系而不求助于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即目的关系,上述的一切都是高度不必然的。意思就是,自然作为单纯的机械作用来看,是能在千百种其他不同的方式上出现而不会恰恰碰见基于像这种原理的统一,而且因之我们是要只在自然的概念以外而不在它的里面,才可以指望在验前(先验地——引者注)发现那种统一的小小一点根据的影子。”(康德,1987:4)
在这里,康德实际上是把后来被达尔文称为“进化论”的东西奠基于先验目的论之上,因为所谓“进化”就是接近某种目的的发展,而这种目的最终是人的先验合目的性。如,为了“飞翔”的目的而鸟翼长在有利的位置、鸟骨形成中空的,为了“转向”的目的而长出鸟尾来,等等;这种进化的目的是人从外边加给自然如鸟的,而不是人以外的其他自然物固有的。按照康德说法,那就是:“如果我们单单看自然中的有效关系而不求助于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即目的关系,上述的一切都是高度不必然的。”
我们看到,康德所奉行的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他所说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或者说他把自然看作为实现人之目的的功能系统,即他所说的人所构造的“目的的一个体系”。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则显得不太彻底,尽管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进化论提供了哲学上的根据。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没有引入“先验的合目的性”,这使“亚里士多德问题”没能得到较好的回答。不过,亚里士多德在回答的过程中却初步提出“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他谈道:“在事物的所有部分结合得宛如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发生的那样时,这些由于自发而形成得很合适的事物就生存了下来;反之,凡不是这样生长起来的那些事物就灭亡了。”(亚里士多德,1982:62,198b)这显然是比达尔文早两千多年就出现的进化论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把进化论奠定于目的论的哲学基础之上。
事实上,达尔文注意到亚里士多德有关进化论的论述,他在《物种起源》第一页的脚注中加以引用,并评论说:“我们看到了自然选择原理的萌芽,但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原理还没有充分的了解,从他论牙齿的形成即可看出。”(达尔文,1997:1)达尔文基本上是以科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亚里士多德的进化论思想的,他只注意亚里士多德对生物进化的细节(如牙齿进化)阐述得不够充分,但却忽略了他深刻的目的论思想。
可以说,达尔文只是从科学方面使进化论得以长足的发展,但在哲学上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退步;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尚且如此,遑论与康德相比。如果说,达尔文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这样的表现尚可理解,那么作为哲学家的蒯因也主张摈弃目的论,而且比起达尔文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则是令人费解和遗憾的。
三、蒯因对目的论的摈弃
以蒯因为首的当代自然主义是要取消人在自然中的特殊地位,相反地把人加以自然化,而不是把自然加以人化,其做法就是彻底摈弃目的论,以致摈弃全部先验哲学。
蒯因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口号,即把哲学化归为自然科学,把认识论化归为经验心理学或进化认识论。蒯因在其纲领性文献《自然化认识论》中宣称:“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相反这样说可能是更有益处的:认识论依然将继续存在下去,尽管它是在一种新的背景下并以一种被澄清了的身份出现的。认识论,或者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简单地落入了作为心理学的因而也是作为自然科学的一章的地位。”(蒯因,2007c:409-410)
既然蒯因取消了哲学和认识论不同于科学的独特地位,当然也就取消了哲学的先验性,包括先验的合目的性,因为科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经验性。蒯因赞赏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的这一说法:“我们重要的范畴(空间、时间、数)都是由进化而培育的生物学上的变异。”(蒯因,1990:38)而反对像康德那样把空间、时间、数等看作“先验范畴”。 蒯因宣称:“在哲学上,我坚持杜威(实用主义者——引者注)的自然主义。……这里,没有先验(a prior)哲学的位置。”(蒯因,2007b:368)相应地,蒯因在很大程度上把认识论看作进化认识论,他以赞赏的口吻评论说:“他们(詹姆斯和杜威——引者注)可以严肃地采用自然主义的,发生的认识论,就像他们严肃地对待其他科学一样。”(蒯因,1990:38)
需强调,蒯因所说的进化认识论属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他像达尔文一样是摈弃目的论的,而仅仅把进化论看作一门类似于物理学的自然科学。蒯因谈道:“自然主义并不抛弃认识论,而是使它与经验心理学相似。……进化和自然选择无疑地会在这个说明中起作用,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将自由地应用物理学。”(蒯因,1990:34)
众所周知,休谟问题即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事实上,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对休谟问题的一种回答。他说:“我并未发现我们今天距休谟离开我们之处前进多远。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蒯因,2007c:402)蒯因沿着休谟的心理主义路线,把认识论化归为经验心理学,进而把进化认识论作为澄清休谟问题的一种手段。他说:“还有这个被心理学家坎贝尔(D. T. Campbell)称为进化认识论的领域,……既然我们允许认识论从自然科学中得到资源,那么,进化有助于去澄清的一个更明显地属于认识论的话题,就是归纳。”(蒯因,2007c:415)
然而,在笔者看来,无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还是从进化认识论的角度,蒯因摈弃目的论都是不恰当的。从学理上讲,实用主义以目的论为基础,因为“实用”只能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实用”。另一方面,认识进化论属于人之进化论的一部分,是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依据的,即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于生物进化来说,“适者”的“适”就是实用,它是相对于生存之目的而言的。可见,进化论不可避免地要以目的论为基础。本文的上一节已经阐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不彻底的,最终要以康德的先验目的论作为基础。因此,当代自然主义一旦摈弃先验目的论,它所奉行的实用主义和进化认识论在哲学上便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
进而言之,适者生存就是适应环境,从而把环境为我所用,以使生命体更好地生存。生命体适应环境是一种双向反馈的互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而使生命体与环境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功能系统。所谓“功能”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没有目的就无所谓功能。这种基于某种目的的功能系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或“实体”。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把内在目的赋予各个功能系统,那么康德则把内在目的仅仅赋予人,再由人从外面把目的加入各个功能系统。人所特有的内在目的就是先验的合目的性。
由于蒯因把包括目的论在内的一切先验哲学一股脑儿地抛在一边,这使当代自然主义不仅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而且充满矛盾或不协调性。对此,我们以蒯因的本体论为例加以分析。
四、蒯因本体论的内在矛盾
在《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论中的地位》这篇文章中,蒯因把经验主义的发展分为五个转折:“第一个是从观念转向语词,第二个是语义的焦点从词项转向语句,第三个是语义的焦点从语句转向语句系统,第四个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即摈弃分析-综合的二元论,第五个是自然主义,即摈弃先于科学的第一哲学的目标。”(蒯因,1990:31)
需要指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仅发生在蒯因所说的第一和第二个转折,也延续到他所说的第三个转折,即意义的载体由语句转向语句系统。蒯因把第二个转折的结果称为“语境定义理论”,用以取代以前的“语词定义理论”。以前是首先确定语词的意义,然后由语词的意义来确定包含那些语词的语句的意义。与之不同,语境定义是用语句的意义来确定这些语句所共同包含的某个语词的意义,这些语句就提供了关于那个语词的语境。如果说第二个转折所产生的是语句语境的意义理论,那么第三个转折所产生的便是语句系统的意义理论。显然,语句系统是一个更大的语境,它决定了其中每一个语句的意义,而不是由语句的意义来决定语句系统的意义。我们不妨把蒯因所说的经验主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转折统称为“语境主义转折”。
蒯因对语境主义转折给予极高的评价,说道:“语境定义预示着在语义学中的一场革命:它也许不像天文学中的哥白尼革命那么突然,但作为中心的转变来说却与它相似。”(蒯因,1990:32)应该说,蒯因的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哥白尼革命是把宇宙的中心由地球改为太阳,语境主义革命是把语言意义的中心由语词改为语境。
语境主义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导致本体论的语言学转向,即蒯因常说的自然主义本体论。一个语境决定了其中各个语句的意义,进而决定了其中各个语词的意义,其中包括语词的指称对象。语词的指称对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体”或“本体”,本体论的语言学转向由此而产生。由于语言本体论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而语境是可以转换的,所以语言本体论是相对的和多元的;据此,我们可把自然主义的本体论称之为“语境主义多元论”。与之对照,以往的本体论是超越一切语境的绝对本体论,通常称之为“形而上学本体论”。
蒯因在《论何物存在》一文中提出他的语境主义本体论,其著名口号是“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亦即“存在就是论域中的成员”。我们知道,约束变项的值域即论域是相对于一个理论系统或语言系统而言的,不同的理论系统有着不同的论域。这样,何物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便成为一个语言系统之内的问题,本体论成为相对的而不绝对的,超越任何语言系统的绝对本体论即形而上学本体论是无意义的。
蒯因举例说:“这里我们有两个相互抗衡的概念结构;现象主义的和物理主义的。哪一个应当占优势呢?每一个都有它的优点;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特殊的简单性。我认为每一个都应当加以发展。的确,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更基本的,虽然在不同的意义上:一个在认识论上是基本的,另一个在物理学上是基本的。”(蒯因,1987:17)在此,蒯因比较了现象主义和物理主义这两种语言系统或“概念结构”,二者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即现象的本体论和物理的本体论。一般而言,这两种本体论无所谓孰优孰劣,取决于当事人看问题的角度。
一个理论就是一个语境,至少是一个语境的一部分。既然诸多理论或语境是平起平坐的,隶属于它们的诸多论域及相应的本体论也是平起平坐的,这就是语境主义的多元本体论。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往往不能同时采用几个不同的理论或处于不同的语境,必须选择其中某一个作为谈话的平台或基础。那么,如何在诸多平行的本体论中选择其中一个呢?对此,蒯因给出的回答是:根据实用的标准。
蒯因说道:“我提出一个明显的标准,根据它来判定一个理论在本体论上作出什么许诺。但实际上要采取什么本体论的问题仍未解决,我所提出的明显的忠告就是宽容和实验精神。”(蒯因,1987:18)蒯因所说的“宽容精神”就是不要把不同的本体论看作是水火不容的,而把它们仅仅看作不同理论的“本体论承诺”。蒯因所说的“实验精神”就是实用主义,即根据实际需要在多个本体论中进行选择。在实用标准中,蒯因特别强调简单性原则,因为“简单性的规则的确是把感觉材料分配给对象的指导原则。”(蒯因,1987:16)
以上就是蒯因的语境主义本体论的基本思想。由于语境是相对的和多样的,所以语境主义本体论的特征就是相对性和多元性。蒯因十分强调本体论的相对性特征,并以此为题来阐述自然主义的本体论,说道:“当我们和杜威一道转向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即行为主义的意义论时,我们所放弃的并不仅仅是言语的博物馆图像,我们也放弃了对于确定性的信念。”(蒯因,2007b:370)然而,这种相对性和多元性的本体论与蒯因在另外的场合把自然主义冠以“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做法是相违的。
例如,蒯因在讨论经验主义的“第五个转折”时谈道:“对于像我这样的自然主义哲学家来说,物理现象,一直到最具假说性的粒子,都是真实的,尽管这种对它们的承认,像所有科学一样,是服从于修正的。”(蒯因,1990:37)在此,蒯因主张一种真实的本体论即物理主义,而把与之对立的本体论看作不真实的;这样,他便由多元本体论转向一元本体论。蒯因在其最后一本专著《从刺激到科学》中明确地倡导物理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一元本体论,说道:“物理主义是唯物主义,除开承认数学的抽象对象之外,是直截了当的一元论。”(蒯因,2007a:565)
我们看到,蒯因的本体论存在着语境主义多元论与物理主义一元论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当代自然主义的本体论不具有逻辑的合理性;或者说,当代自然主义缺乏理论上的自洽性。究其原因,蒯因只是将实用主义原则贯彻于语境主义多元论之中,而在其物理主义一元论中则被摈弃掉了;因为物理主义一元论是把物理现象置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即具有真实性,无须通过实用标准而把它看作相对的,并与其他本体论相并列。
可以说,蒯因的自然主义的逻辑不协调性是很突出的,甚至可以看作此理论的特征之一。再如对待先验哲学的态度,蒯因也是不一致的。前面提到,蒯因明确地表明自然主义与先验哲学是不共戴天的,宣称自然主义理论中“没有先验哲学的位置。”(蒯因,2007b:368)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处,蒯因却说:“由于其难以捉摸性,由于其不时出现的空虚性(除非相对于一个更宽广的背景),在某种突然相当清楚并且甚是宽容的意义上,真和本体论可以说属于超验的(transcendental)形而上学。”(蒯因,2007b:399)这样一来,蒯因便把他作为“真实的本体论”的物理主义放在超验或先验的形而上学的位置上;或者说,先验哲学被蒯因从前门驱赶出去,又被他从后门接纳进来。
在笔者看来,蒯因对待先验哲学的这种矛盾态度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他像休谟一样彻底地摈弃一切形而上学。然而,在当代哲学中蒯因却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具体地说,在当年逻辑经验主义步休谟之后尘,以“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风靡一时之际,蒯因以反潮流的姿态闪亮登场,其力作《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和《论何物存在》等把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以一种新的方式引进哲学,这预示着他与休谟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但是,当蒯因后来以自然主义自居的时候,却摆出一副休谟哲学继承者的姿态。他说道:“在信条方面,我并未发现我们今天距休谟离开我们之处前进多远。休谟的困境就是人类的困境。”(蒯因,2007c:402)
其实,蒯因的自然主义即取消“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主张正是以著名的“休谟问题”的无解性作为理由的,即他所说的“人类的困境”。然而,当蒯因主张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时候,却不加说明地把这一“人类的困境”搁置一旁,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德始终如一地把解决休谟问题作为自己的哲学使命,并由此引出他的先验哲学或形而上学。
康德评论道:“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休谟并没有给这一类知识带来什么光明,不过他却打出来一颗火星。”(康德,5-6)在康德看来,休谟问题打出来的“火星”就是康德自己的先验哲学。
总而言之,蒯因的自然主义之所以是前后矛盾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对形而上学或先验哲学予以摈弃,包括对康德目的论的拒斥。可以说,丢掉目的论和先验哲学的自然主义是盲目和破碎的,难以自圆其说或自成体系。
[1] 贝塔朗菲(1987).一般系统论.林康义、魏宏森、寇世琪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 达尔文(1997),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 康德(1964).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 康德(1978).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5] 康德(1987).判断力批判:下.韦卓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6] 蒯因(1987).论何物存在.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宋文淦、张家龙等译.上海:上海译出版社.
[7] 蒯因(1990).实用主义者在经验论中的地位.李真译.哲学译丛,6.
[8] 蒯因(2007).从刺激到科学.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蒯因(2007).本体论的相对性.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0] 蒯因(2007).自然化的认识论.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亚里士多德(1982).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2] 亚里士多德(2003).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NaturalismandTeleology:And a Comment on Quine’s Ontology
ChenXiaopi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sources of Quine’s naturalism are pragmatism and empiricism, and its significant point is that philosophy is reduced into natural science, and epistemology is reduced into empirical psychology or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Both pragmatism and evolutionism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eleology, thus there is an indissoluble bound between naturalism and tele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concept “nature” and teleology was embodied in Aristotle’s philosophy long before. Kant proposed the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 of purposefulness, and further provided a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teleology. Because Quine completely abandon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eleology), his naturalism not only loses its root but has contradictions, particularly acute in his ontology.
naturalism; teleology; ontology; pragmatism; Quine
10.14086/j.cnki.wujss.2017.06.004
B017;B085
A
1672-7320(2017)06-0042-07
2017-08-13
■作者地址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B016)
■责任编辑何坤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