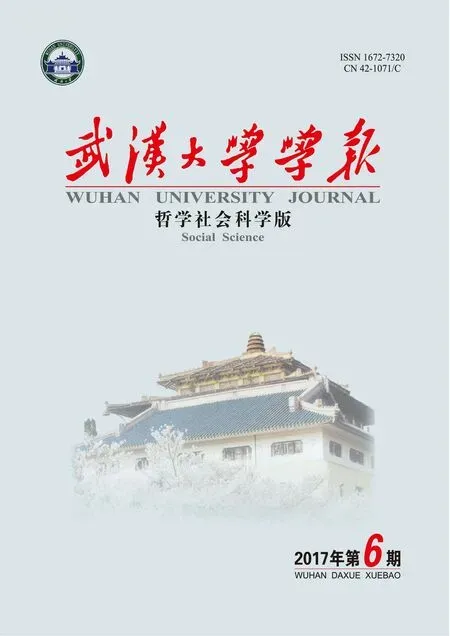中国地方官员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张三保 熊 雅
中国地方官员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张三保 熊 雅
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驱动因素的既有探讨,经历了从强调制度安排到聚焦地方官员的演变。对地方官员的研究,又兼及静态特征和动态过程。本文基于高阶理论,致力于从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地方官员与辖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制度因素。在静态层面,分析了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年龄和任期、人格特征、个人品德和行政价值观等五方面的前因。在动态层面,展示了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腐败行为等六方面的效应。之后,从激励机制着手,分析了影响地方官员发挥作用的因素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地方官员; 经济增长; 高阶理论; 激励机制
一、引 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因而,对其驱动因素的探讨至今炙手可热。然而,对驱动因素的早期探索,往往强调制度安排,而忽略了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的创始人Hambrick与Mason(1984:193-206)认为,高层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如年龄、任期、教育水平、性别、职业背景、种族、财务状况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他们的认知水平与价值观,进而影响其所在组织的绩效。
基于该理论,后续研究陆续考察了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如张尔升、胡国柳,2013:71-83)*本文所讨论的地方官员主要指省级官员。因为我国地方行政区域主要划分为省市县镇乡五级,省级官员是连接中央与市县镇乡的至关重要的一环,且在考察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时,考虑到数据获取的便利程度,既有研究也多采用了省级数据。。其逻辑在于: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地方官员即便面临相同或相似的制度环境,其人口统计特征的异质性,也会使辖区经济绩效呈现差异。基于严谨的计量分析,领导者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确实得到了支持(Jones & Olken,2005:835-864)。然而,这类研究较多集中于静态层面的人口统计特征。
进一步的研究,则考察了地方官员的动态要素对区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地方官员为争夺晋升职位而进行的博弈,被称为“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4:6)。政治晋升等官员治理因素,被视为解释地方官员大力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线索(王贤彬、徐现祥,2009:2)。比如,实证表明,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周黎安等,2005:1-17)。这说明,除了财政激励外,政府内部治理尤其是政治晋升,对于地方官员选择发展地方经济的方式具有重大影响(Blanchard & Shleifer,2001:171-179;Maskin,2000:359-378;Whiting & Park,2003:729-732;Zhou,2002;Zhuravskaya,2000:337-368;Bardhan,2006:1-18)。此后,Jin,Qian和Weingast(1999:1719-1742)指出,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的激励,与政治晋升的博弈形成互补,从而共同解释了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经济的行为。
本文基于管理学中的高阶理论,并结合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采用系统的文献分析法,梳理了学界探索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的脉络,致力于将高阶理论的解释范围,从微观的企业管理领域拓展到宏观的经济学与政治学领域,并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启示。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静态层面,探讨地方官员显性与隐性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第三部分在动态层面,归纳地方官员不同行为的效应(如图1)。在此基础上,文章第四部分分析了影响地方官员效能的制度因素。最后,对应前述特征与制度要素,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未来研究与改革方向。

图1 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图
二、静态视角:地方官员的人口统计特征
地方官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中,专业禀赋、年龄、任期和工作背景等显性特征,以及人格特征、品德、行政价值观等隐性特征,均被证实对辖区经济增长具有影响。
(一) 显性特征
专业禀赋方面,少数学者定量识别了官员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如,张尔升(2012:72-86)发现,关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为负,而其综合学科禀赋和受教育年限则为正。类似结论为政府选拔任用干部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选拔干部时,可着重考虑有综合专业禀赋、知识面广泛的候选人,通过设置受教育年限任职门槛,确保官员发展经济的能力。
就年龄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年轻的地方官员拥有更好的仕途(曹春方、马连福,2012:93-107)。Yao和Zhang(2011:19-28)也发现,在市级官员晋升中,年龄越小的市级官员,职业生涯的发展机会越大,因此他们也更加重视提升绩效,来争取晋升。类似地,王贤彬、徐现祥和李郇(2009:1301-1328)研究表明,年龄较大官员的更替,更易对经济造成消极影响。此外,中央政府一系列“干部年轻化”的制度安排,也促使地方官员的趋于年轻。
任期方面,过长或过短,都不利于地方官员获得良好的区域经济绩效。当任期过短时,地方官员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新项目常常在上马不久,便因地方官员的离任而中断;与此同时,晋升竞争会导致地方官员在做经济决策时,偏向能带来短期经济增长的第二产业,忽视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第三产业(佟健、宋小宁,2011:30-36)。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会带来过大的机会成本,使地区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相反,当任期过长时,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会逐渐降低;对自身晋升的预期降低,使之前的强激励转化为弱激励;基于公平理论可知,当对自身投入未取得相应回报时,不公平感会刺激地方官员采取行动,要么是降低投入,要么是离开情境,直到降低这种不公平感。具体而言,张军、高远(2007,91-103)发现,官员的任期短于4年和5年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线性为正;当在任年数长于4年和5年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线性为负。
此外,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16-26)发现,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轨迹在任期内呈现“倒U型”,即:在任期的早期,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逐渐上升,但到了任期的一定时间点,随着任期的增长,省长省委书记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倒U型”还要分类而论:本省晋升的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绩效符合原结论;但是,外省晋升、中央调任或从外省平调的地方官员,其经济增长轨迹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从地方官员的去向来看,调往中央和平调的地方官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经济增长轨迹。
(二) 隐性特征
1.人格特征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就需要、自我效能感、处世态度、人际关系等方面。比如,余君(2006)发现,公务员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工作特征和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绩效的关系,当高成就需要的人从事低重要性的工作时,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会低于低成就需要的人从事类似的工作。又如,王登峰和崔红(2008:828-838)认为,领导干部追求成功和成就(处世态度)、对人宽和(人际关系)和坚韧踏实(才干)等人格特点,与较高的工作绩效显著相关;而待人热情(人际关系)、直率(情绪性)、易作决断(才干)、谨小慎微(行事风格)和活跃等人格特点,则与较低的工作绩效显著相关。
2.个人品德
梅继霞(2014:69-73)发现,公务员品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务员品德结构、品德测评、品德与绩效的关系及公务员品德建设四个方面。公务员品德考察难以实施组织,其判定标准主观性太强,因此公信力很低(袁忠,2011:126-130)。为克服这一研究难题,王登峰等(2007:770-773)将党政领导干部的胜任特征分为“德”和“才”两部分。其中,政治素质、以人为本和自我约束可以归为“德”的范畴,而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则归为“才”的范畴。他们发现,“德”的成分对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比“才”的成分更明显,而“才”的成分对工作绩效的抑制作用比“德”的成分更明显。
另一些研究则进一步证实,党政干部的某些品德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比如,李辉和晏勋(2007:70-71)指出,公务员品德中的民主作风、创新能力、求实精神等因素均正向影响其工作绩效。又如,李明和凌文辁(2011:91-94)结果表明,领导者的品德魅力和模范表率作用,对下属的行为态度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作用。
3.行政价值观
个人价值观不但影响个体行为,且对群体行为乃至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了规范、解释和预测(辛志勇、金盛华,2002:27-32)。因而,研究地方官员的行政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刘祖云(2003:37-41)提出了公务员行政价值观的理念,并将其理解为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准则。徐增辉和喻剑利(2001:11-12)则将其视为行政主体特定的行政思想、观念、行为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追求。赵龙(2006)将行政价值观划分为法治、公正、服务与自我等四个价值观维度,研究证实:公务员的服务价值观维度与其任务绩效显著相关;行政价值观良好的公务员,能够较好的完成工作任务,具有较高的工作奉献精神,更容易得到同事的信任、与人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动态视角:地方官员的交替与晋升
从动态层面考察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代表了近年的研究主流。这些动态要素主要包括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腐败行为等。
(一) 地方官员的来源与去向
地方官员的不同来源,反映了他们差异化的工作经历与体验。那么,官员来源的差异,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何区别?目前,地方官员的来源主要可分为五种:省内晋升、外省晋升、来自中央、外省平调和来自企业。其中,省晋升是最主要来源。对于前四种来源的地方官员,王贤彬、徐现祥(2007:18-31)发现,平调和外省晋升的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绩效最大(11%),本省晋升的次之(10.5%),来自中央的最小(9.5%)。作为补充,张尔升(2010:129-138)实证表明,有企业背景的地方官员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弱负效应;但处于市场经济中时,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效应。
关于地方官员去向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经济增长对于地方官员去向的反作用。比如,王贤彬(2010)将地方官员离任后的去向主要划分为四类:平调、调入中央、退居二线和其他。其中,退居二线的占最大比例,且比重不断下降;其次是调往中央的,且呈持续上升之势。在四种去向中,调入中央的地方官员,其经济增长平均而言最低。这显然与之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相悖,即具有良好经济增长绩效的地方官员,会有更大的晋升几率(Li & Zhou,2005:1743-1762)。所以,中央在决定官员去向时,不单单是考察经济增长,还有着更复杂的考核体系。
(二) 地方官员的交流
干部交流对于带动全国、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王贤彬(2010)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速显著提高1%左右。这种正效应显著存在于1990年代后。这与我国干部交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现实相吻合。可见,加速完善干部交流制度,能扩大地方官员对于地方经济的积极影响。
目前,干部交流的趋势,主要是地方官员从沿海发达地区流向内地、东北等稍落后省份。具体而言,在对干部交流分类讨论中发现,从沿海交流到内地的省长,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内地向内部的省长交流,影响却不十分显著;在沿海省区内部的交流,则并不存在这种效应(王贤彬,2010)。基于对沿海省份成功发展模式的深刻认识,交流到内地的地方官员对内地省份的经济增长绩效,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从管理学角度而言,异质性的群体往往更能促进组织发展,让组织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显然,省内交流的官员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因此,沿海地区的内部干部交流,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
(三) 地方官员的更替
干部队伍追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的一系列变革,使得地方官员更替成为一种常态。Jones和Olken(2005:835-864)研究表明,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会对经济增长绩效带来显著影响。但并未涉及这种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长期还是短期。王贤彬等人(2009:58-79)的研究则发现,地方官员的不连续更替,使地方经济在短期内呈负向波动。
事实上,地方官员更替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未形成定论。这是因为,更替行为往往会涉及一位官员的离任,以及一位官员的上任。首先,官员的年龄与职业生涯阶段会调节更替行为对经济绩效的作用:较年轻的地方官员,一般处于职业生涯中的建设发展期,往往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动力,去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建设;而年龄相对较大的地方官员,一般处于职业生涯的后期,往往追求稳定,维护已获得的地位和成就,不期望在工作上有更大作为,工作动力和成就感都会下降。此外,还需考虑地方官员的适应性:无论是何种来源的地方官员发生更替行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新职位。何况,政策的连续性决定了地方经济的变动程度,而影响政策连续性的,又包括地方官员工作经验、教育背景、性格偏好等因素。
(四) 地方官员的晋升竞争
地方官员围绕地方GDP展开竞争的同时,又为争夺晋升机会而竞争。因此,在决策时,他们不仅会考虑经济行为带来的GDP收益,也会思考这种经济行为能为自身政治晋升带来的便利。在此种情境下,利己不利人的事情激励最充分,而利己又利人的双赢合作则明显激励不足(周黎安,2004:33-40)。因为从激励的角度而言,在成本可承受范围内,地方官员为了提升自己与其他竞争对手的相对位次,不仅会被激励实施能提高自己排名的行为,也会设法阻碍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比如我们常说的地区间贸易壁垒现象,就源于此。因此,不难理解地方官员为获得职务晋升而表现出的、追求地区“公共利益”的行为——援助之手,以及为了追求某些“纯粹的”私人利益的行为——攫取之手。
1.援助之手
晋升锦标赛对地方官员的强激励作用,促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被动监督,转变为地方官员对中央的主动服从,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地方官员热衷于GDP和相关经济指标排名,积极招商引资,推动就业。另外,与行政和财政分权激励相比,晋升锦标赛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奖励承诺比较可信。一方面,中央作为委托人事先下达明确指标,参与人通过可量化的GDP,便能够清楚了解自身绩效,这种指标的可信度很高。另一方面,中央不需再花费任何其他资源来激励地方官员——在晋升锦标赛中,职位晋升被设定为一种激励因素;在并未花费其他成本的前提下,反而最大化了现有资源的激励效果。作为锦标赛中的获利者,晋升的官员作为上一级,在决定下级的晋升时,会自动维护该体制的正常运行。
2.攫取之手
GDP的考核体系,使地方官员只关注能够被考核和量化的经济指标,而忽视不在考核范围内或难以衡量的考核指标。比如,地方官员热衷于面子工程,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不利于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发展经济,纵容地方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浪费能源,在财政上一味地支持企业扩张。这种考核体系的扭曲,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导致政府失灵问题。不少文献从政治晋升竞争的角度,解释了上文提到的重复投资、产业趋同、边界效应等现象(张晔、刘志彪,2005:62-67;舒洪冰,2006:26-28;范迪军,2005:9-13;周黎安,2011:15-26)。比如,张晔等人(2005:63-68)认为,地方官员的相对业绩比较,以及害怕落后的风险规避态度,是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
(五) 地方官员的腐败行为
关于地方官员腐败行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腐败行为可以抵制官僚主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Beck & Maher,1986:157-161)。更多学者认为,腐败行为会阻碍地方经济的发展,导致政府失灵(Shleifer & Vishny,1998:599-618;Wei,1997;Tanzi & Davoodi,2001:197-222;周黎安、陶婧,2009:57-69)。目前,中国呈现腐败行为泛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存的趋势,如果腐败会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低效率,那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为何以惊人速度增长呢?
要探讨腐败行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要明晰官员腐败行为的动因。郭广珍和彭坤(2011:75-80)认为,官员对政治晋升的评价、分权程度等都会影响腐败水平:当官员对政治晋升的评价高时,官员对腐败行为的评价会降低,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减少;分权程度则与腐败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唐志军、向国成和谌莹(2013:3-14)从晋升竞争的角度研究发现,地区间的增长条件、政治环境、反腐败投入、司法的公正与透明度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地方官员是致力于腐败还是清廉。盛宇明(2000:52-59)认为,目前中国的腐败泛滥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存在更多的腐败供给源,以及对腐败更强的需求。
四、影响地方官员作用程度的制度动因
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在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多方面要素,既推动了地方官员发展辖区经济,也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一) 央地分权制度
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和财政分权,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发展资金后,地方官员能够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发展规划。在强经济激励下,各地区展开了激烈竞争,以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可避免的,这种制度安排很容易形成激励扭曲,使地区间竞争由良性转变为恶性竞争,与之相伴的是各种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现象、腐败行为(郑毓盛、李崇高,2003:64-72;傅勇,2007;周业安,2003:97-103;谢晓波,2004;沈立人、戴园晨,1990:12-19;姚洋、杨雷,2003:27-33)。另外,上级政府凭借领导权威将事权下放的同时,却未将相应的财权赋予下级政府,由此导致的财权与事权失衡,使得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政府支出,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二) 晋升锦标赛制度
晋升锦标赛将关心仕途的地方官员置于强激励下。有限的晋升职位意味着,一个人获得晋升机会的同时,将直接降低另一人的提升机会。这种非输即赢的淘汰赛,使各级官员为GDP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发展辖区经济。但是,地方官员往往更关注能被考核的发展指标,热衷于“面子工程”,忽视对民生有建设性作用的发展计划,造成了产业乃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除了有限的晋升职位,年龄、学历等方面的制度限制,也让一部分原本具有晋升资格的地方官员失去晋升机会。晋升无望的地方官员遭遇“天花板”之后,会对工作消极怠慢,甚至还很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三) 绩效考评制度
地方官员的个人绩效测评,是政府整体绩效管理的重要部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理论薄弱与认识不足。我国对于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绩效理论的总结和分析,缺少对中国政府及地方官员特色的分析。同时,政府往往对绩效评价认识落后,未给予足够重视。其二,考评指标不够科学。指标选取过于随意,过分强调规模、总量、速度等上级政府关注的、容易考量的数量指标,而忽视效益、质量、结构等容易被上级政府和较难考核落实的质量指标。其三,评价过程有待改进。在评价过程中缺乏独立、多元的评价主体。理应作为评价主体的公众被忽视,上级政府和领导反而成了政府绩效考核的评估主体。在结果运用上,只重评估而轻反馈,考核结果未得到合理应用。同时,评估方法选取也不够科学,人为因素干扰比较大,常常出现走过程,形式主义、受人情关系牵制等问题。其四,评估法制化水平较低。缺乏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绩效管理进行明确详细的规定。
(四) 关系文化
处于经济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腐败行为泛滥并存。毋庸讳言,存在一部分没有优秀政绩的地方官员,依靠“关系”网络同样达到了晋升目的,这种关系文化的存在,弱化了晋升锦标赛机制的正激励作用,使地方官员建立了错误的权力观。那部分缺乏关系而有才能的地方官员,很可能因为晋升无望,不再全身心投入地方经济建设,并滋生腐败行为。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 关注官员隐性静态
静态层面的既往研究,多从地方官员的年龄、任期、专业禀赋、受教育程度等显性的人口统计特征切入,考察它们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认知、情绪因素、价值观等隐性因素的效应。因此,未来研究若能借鉴管理心理学对管理过程中个体价值观、心理表现和规律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进一步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行政价值观、人格特征、品德等隐性个人特征的影响,将为解释地方官员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地方官员治理与激励提供新的视角。
(二) 考察官员动态行为
如前所述,前期对动态层面要素的探索,多集中于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方面,鲜有研究从个体层次出发,关注地方官员的自身行为(如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一方面挖掘地方官员腐败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比较它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等激励因素的作用差异;另一方面可以考察地方官员的来源、去向、交流、更替、晋升竞争等因素与腐败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地区经济绩效的影响。比如考察交流官员的最佳任期、官员交流与腐败行为的关系等等。此外,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省级层次,未来也可将分析层次内化到市级乃至县级层次。最后,从统计上说,样本量的扩展将更有利于结论的稳健性,甚至有助于捕捉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界限等微妙结论。
(三) 探索作用机制
现有对地方官员辖区经济增长绩效的探讨,多涉及地方官员的直接效应,较少探讨作用机制。比如,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地方官员选择哪种方式来发展地区经济等等。事实上,在不同地区、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历史时期,其代表的资源禀赋并不相同,由此导致地方官员影响辖区经济的方式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因而,这种差异有待未来继续深入讨论。此外,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潜在反作用及其可能的方式,既有研究多将其作为控制因素,未来可再进一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官员的反作用及其作用机制。
(四) 完善激励机制
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还受到地方官员激励机制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聚焦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如何保证事权与财权的一致性?第二,在完善地方官员晋升机制时,如何设置职级,如何建立与职级相匹配的报酬水平?第三,在改革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时,是否应该降低GDP指标的比重?降低到何种比例是合适的?与此同时,应该增加那些民生指标的考核?第四,在指标考核执行过程中,如何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减少对晋升锦标赛模式的依赖?
[1] 杰瑞·伯格(2004).人格心理学.陈会昌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 曹春方、马连福(2012).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经济科学,3.
[3] 范迪军(2005).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博弈实证分析——以“铁本”事件为例.淮南师范学院学报,4.
[4] 傅 勇(2007).中国式分权、地方财政模式与公共物品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复旦大学.
[5] 郭广珍、彭 坤(2011).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当代经济科学,2.
[6] 李 辉、晏 勋(2007).公务员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对业绩影响的实证分析.时代经贸(中旬刊),8.
[7] 李 明、凌文辁(2011).“以德为先”选拔领导必要性的实证研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1.
[8] 刘祖云(2003).行政价值观乃公共行政之“魂”.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6.
[9] 梅继霞(2014).公务员品德国内研究述评.行政论坛,2.
[10] 沈立人、戴园晨(1990).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经济研究,3.
[11] 盛宇明(2000).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5.
[12] 舒洪冰(2006).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基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视角.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6.
[13] 唐志军等(2013).晋升锦标赛与地方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的研究.上海经济研究,4.
[14] 佟 健、宋小宁(2011).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隐性激励机制——基于职业生涯考虑模型.当代财经,6.
[15] 王登峰、崔 红(2008).领导干部的人格特点与工作绩效的关系:QZPS与NEO PI-R的比较.心理学报,7.
[16] 王登峰等(2007).工作绩效的结构及其与胜任特征的关系.心理科学,4.
[17] 王贤彬(2010).中国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
[18] 王贤彬、徐现祥(2008).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证据.管理世界,3.
[19] 王贤彬、徐现祥(2009).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南开经济研究,2.
[20] 王贤彬等(2009).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4.
[21] 魏 姝(2013).中国官员激励机制的发展与改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4.
[22] 谢晓波(2004).经济转型中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
[23] 辛志勇、金盛华(2002).西方学校价值观教育方法的发展及其启示.比较教育研究,4.
[24] 徐现祥等(2007).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经济研究,9.
[25] 徐增辉、喻剑利(2001).转型期中国行政价值观的转变.行政与法,2.
[26] 姚 洋、杨 雷(2003).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战略与管理,3.
[27] 余 君(2006).基层公务员工作特征及其与人格特质、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关系研究,浙江大学.
[28] 袁 忠(2011).领导干部道德考评的困境及其制度创新.理论月刊,5.
[29] 张尔升(2010).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证据.中国工业经济,3.
[30] 张尔升(2012).地方官员的专业禀赋与经济增长——以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面板数据为例.制度经济学研究,1.
[31] 张尔升、胡国柳(2013).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与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基于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分析视角.中国软科学,6.
[32] 张 军、高 远(2007).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经济研究,11.
[33] 张 晔、刘志彪(2005).产业趋同:地方官员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家,6.
[34] 赵 龙(2006).公务员行政价值观与工作绩效.河南大学.
[35] 郑毓盛、李崇高(2003).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中国社会科学,1.
[36] 周黎安(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6.
[37] 周黎安等(2005).相对绩效考核: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经验研究.经济学报.1.
[38] 周黎安、陶婧(2009).政府规模、市场化与地区腐败问题研究.经济研究,1.
[39] 周黎安、陶婧(2011).官员晋升竞争与边界效应:以省区交界地带的经济发展为例.金融研究,3.
[40] 周业安(2003).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
[41] P.K.Bardhan(2006).Awakening Giants,Feet of Clay: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JournalofSouthAsianDevelopment,1(1):1-18.
[42] P.J.Beck & M.W.Maher(1986).A Comparison of Bribery and Bidding in Thin Markets.EconomicLetters, 20(1):157-161.
[43] O.Blanchard & A.Shleifer(2001).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How Much Progress?IMFStaffPapers,48(1):171-179.
[44] A.H.Goodall et al.(2005).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20(3):835-864.
[45] D.C.Hambrick & P.A.Mason(1984).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9(2):193-206.
[46] Jin Hehui et al.(1999).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 Styl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 89(1):1719-1742.
[47] Li Hongbin & Zhou Li’an(2005).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89(9):1743-1762.
[48] E.Maskin et al.(2000).Incentives,Information,and Organization Form.ReviewofEconomicStudies, 67(2):359-378.
[49] G.Montinola(1995).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Politics,48(1):50-81.
[50] A.Shleifer & R.W.Vishny(1993).Corrup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108(3):599-618.
[51] V.Tanzi & H.R.Davoodi(2001).Corruption,Growth,and Public Finances.PoliticalEconomyofCorruption,5(3):197-222.
[52] Wei Shangjin(2000).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82(1):1-11.
[53] S.H.Whiting & A.Park(2003).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36(6):729-732.
[54] Yang Yao & Zhang Muyang(2011).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ournalofEconomicGrowth, 13(14):19-28.
[55] Zhou Li’an(2002).Career Concerns,Incentive Contracts,and Contract Renegoti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Ph.D.thesis,Stanford University.
[56] E.Zhuravskaya(2000).Incentives to Provide Local Public Goods:Fiscal Federalism,Russian Style.JournalofPublicEconomics,76(3):337-368.
LocalOfficials’ConductandRegionalEconomicGrowthinTransitionalChina
ZhangSanbao
(Wuhan University)
XiongYa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driven forces of miracl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 to that of local officials.Moreover,the studies on local officials include st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Based on Upper Echelons Theory,we aim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official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which may affect such relationship,from perspective of multi-discipline.Specifically,we firstly analyzed static factors including professional skills,age and tenure,personality,personal morality,and administrative values.Following that,we illustrated local officials’ origination,destination,exchange,turnover,political promotion mechanism,and corruption behaviors.After that,we explored thos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influences of local official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Finally,future directions of research and reform were proposed.
local officials; economic growth; Upper Echelons Theory; incentive mechanism
10.14086/j.cnki.wujss.2017.06.003
F207
A
1672-7320(2017)06-0033-09
2016-12-23
■作者地址张三保,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熊 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714021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YJC630226)
■责任编辑刘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