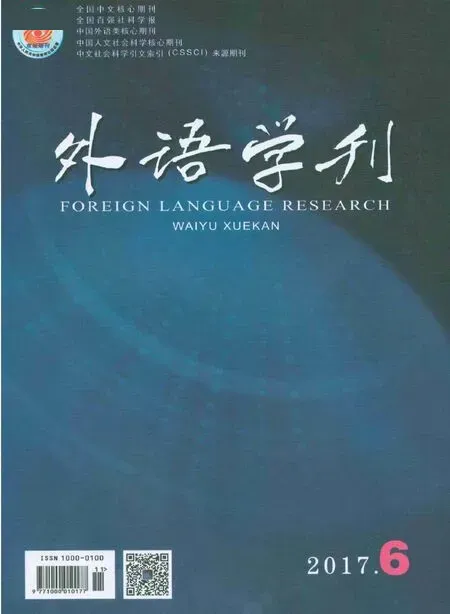多重实在的符号*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83)
1 从意义到符号
胡塞尔(E.Husserl)把符号分为“表达符号”(expression)和“辨识符号”(indication),主要围绕符号的生产和感知两个基本点而形成其理论思路(Husserl 2001a:181-205)。但从符号回溯过去,则是“自我”(ego)这个核心,也就是说,“自我”构成感知、知觉、理解、判断主体自身、他人和外界的中心。“自我”成为意义之源,意义诞生于“自我”的反思。意义的构建使人超越自身生物有机体的存在,超越对象界的物质感知,超越对他人的外部形态的接触。这种超越实现“自我”对于精神或观念世界的构建和拥有,并由此确立人区别于一般生物有机体的价值高贵性。可以说,人生活并存在于意义中。但是,“自我”作为人的原初领域,并非能自动派生意义。只有在“自我”反思、质疑、确认主体的存在状态及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时候,只有在“自我”与包括环境和他人在内的他者互动的过程中,才能建立基于“自我”的意义格局。“自我”建立的这种意义格局为人提供生活世界的座标,构成人生活的动力,也成为其超越工具性存在的生活目标。
但是,从意义到符号并不一定构成前后相继的关系,意义的构建不过是“自我”不断分解和综合各种经验,并由此形成直觉和判断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具有分节能力的语言符号。意义是经验不断清晰化的结果,而语言符号的逻辑性、节奏性和系统性使意义的构成具有分析和关联经验时的逻辑线索;同时,区分同一经验要素或不同经验类型,并把多种经验统一到一定的意义格局里,形成意义的统一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符号,尤其是语言符号,与意义的构成同步。甚言之,不存在离开语言符号的意义形成过程。正如胡塞尔指出,谈及语言,至少关联到言说(speaking)、思考(thinking)和所思(what is thought)3个维度,而这3个维度的不可分割性恰恰说明语言与思考的结合构成意义的必由之路(Husserl 2001b:8-9)。
说语言符号和意义的构成过程同步,并不意味着语言符号必须外化为听得到的语音,看得见的印刷文字,才能与意义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在独言(monologue)而非对话的状态,在沉思而非互动的状态,意义就已经启动旅程,而启动的一刹那等同于反思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又依托于处于想象状态的语言符号,也即想象中的语词,而非外化之后听得见的语音或看得见的印刷文字。由于意义和语词符号结合得如此紧密,甚至合二为一,因此当语词抽去意义,就成为仅仅是口中发出的声音或纸上遗留的痕迹,由此也失去语词符号的成立条件。语言符号的合理性在于对意义的同步性支撑,但语言符号并非在发生学含义上和意义处于先后相继的关系。虽然如此,语言符号又作为意义的外衣包裹着意义,使之根本上区别于意义,但又构成意义不可脱卸的外衣。正如社会人、文化人和文明人需要外衣而不能裸露肉身一样,外衣包裹着肉身,区别于肉身,但又成为不可脱卸的外衣。同理,意义理论实质上就是语言符号学,或包裹着意义的语言符号理论。符号与意义的这种微妙关系,反映出符号不过是为意义的表达而生。表达的对象是“自我”的意义格局,而这个“自我”的意义又来自“自我”意志的驱动。
所以,胡塞尔提出“表达符号”是最基本的符号,其理论价值在于揭示符号的来源及符号成立的合理性这两个重大问题:符号诞生于意义,并因意义的构成和表达而获得成立的合理性。由于意义的构成始自“自我”的反思,并且符号伴随着意义的整个形成过程,因此所谓“表达符号”既是意义的符号,又是“自我”反思需要的主体意志的体现。但至此,符号尚未完成其外化过程。符号的外化或客体化,是意义从建构走向分享和理解的必然。意义的分享和理解设定“自我”之外他者的存在,而他者对主体“自我”的意义把握又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间隔,而穿越身体的厚度,去把握主体的意义格局,直至抵达意义的源头即主体的意志,呼唤着一条能够凭借而又需要减少风阻的途径。
符号从想象状态转化为外化的形态,为上述途径提供最适宜的条件。外化的符号形态,其适宜性在于:第一,符号在想象状态已经和“自我”构建的意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意义的外衣,是距离意义最近的薄膜,因此从外化的符号形态出发是接近符号想象状态并触及意义格局的优选方式。第二,在各种符号类型中,语言符号具有典型的社会制度性,存在着人际间监督、纠正、约定、共识的共享基础,也即葛兰西所说的“规范语法”(normative grammar)的作用(Gramsci 2000:357-358),对于保持符号与意义的稳定耦合,规范社会共同体成员可能发生的个体偏差,具有其他类型的符号以及任何其他物质要素所不具备的优势。第三,语言符号的物质依托,即声音,来自生物有机体意义上的人的唯一可以社会化的出口,且具有人际间最大可能的转述和传递空间,是通向内在“自我”的最便捷的通道。这些适宜性为符号从想象状态转化为外化或客体化的语言符号提供充分的条件。转化或客体化之后的符号成为“辨识符号”,从而完成符号从“表达符号”到“辨识符号”的历程。
正是因为符号从想象状态转化为外化或客体化的形态,意义才从“自我”的内在领域导向外部,而符号外部性的获得使得符号开始具有代表或代替背后的意义他性,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符号性质。所以,听到外化出来的语音符号,看到外化出来的文字符号,以及身体其他外化出来的表情和体态,意识到这些事物的符号性,就是意识到在这些语音符号、文字符号、表情或体态符号背后还存在着听不见、看不到的意义。这些外化的符号成为识别背后意义的标识。我们可以看到,从“表达符号”到“辨识符号”,不仅仅是符号从想象状态进入外化或客体化状态,而且意味着,理论的视角发生从“自我”到他者的转换,从符号的生产到符号接受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并非由他者完成,而是由主体“自我”完成整个生产过程。从想象状态的语词符号到言说出来的语音符号,或写出来的文字符号,或身体呈现出来的表情或体态符号,这个过程来自主体,并由主体完成,也意味着主体“自我”的意义格局经历从构建到传达的过程。
但是,借助外化的符号,进入意义的传达阶段,符号主体虽然完成这样的生产过程,但由于传达本身设定他者的存在,且以他者为目的,因此需要他者的合作。他者的合作始于对符号主体所传达符号的辨识,但不停留于符号的辨识,而是需要经由外化的符号抵达符号主体的内在意义格局,直至主体的意志。这意味着,通过他者的合作,从外化的符号到“自我”的意义格局形成返回主体自身的符号运行过程,也使意义和符号在想象状态下的统一性转变为外化状态的统一性。但这两种统一性又不完全等同,也并非将想象状态下的意义和符号的统一性简单复制为外化状态下的统一性。根本差异在于:符号外化之后,进入传达阶段,需要主体之外他者的参与,而他者的参与并非停留于识别外化的符号形态,而是通过对外化符号形态的识别,启动对主体意义格局的回溯,从而形成主体自身调整意义格局,重构意义过程的外部压力。因此,符号外化之后的形态通常表现为复杂的话语形式,包括主体对于所要传达意义的说明、解释、澄清和确认等复杂过程。这个传达过程的复杂性,并非由于主体表达意义的能力不足,也不是因为主体在符号外化之前对于意义的构建发生错误,而是因为他者开始介入意义的构建和表达。因此,主体和他者在此形成意义和符号的统一性,已经不是原初主体通过想象状态的符号所构建的意义格局,而是主体和他者合作构建的意义,是双方碰撞和协调之后达成的关于意义的理解和共识,是一种新的意义统一性。从这一角度理解,意义已经由原初的“自我”意志转变为主体和他者共同形成的主体间意义。这也是符号外化之后和外化之前在意义构成上的差异。
2 从符号到实在
主体间意义的形成,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意义的领域从内部“自我”延伸到主体外部,同时也对“自我”的意义构建提出更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的艰巨性表现在:主体“自我”不能仅仅通过自身的反思就可以完成意义的全部构建工作,而必须在和他人形成的关系之中,并以他人的态度和意见作为重要参考,在他人的理解和认同过程中,不断重构着意义的格局。因此,意义的领域也呈现出多重化的结果。在立足于主体“自我”反思的前提下,多重化的意义领域分别表现为“自我”意义领域、心理意义领域、主体间意义领域和物质事物意义领域等多种状态。但是,这些多重意义领域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主体的“自我”加工。因此,各种意义领域都因为最终和主体“自我”相关联,而模糊各领域之间的界线。对心理的感受形成的意义领域归根结底是“自我”反思的结果;主体间的意义领域归根结底也是主体“自我”借鉴他人意见和态度并由主体最终反思形成的结果;各种物质事物的意义领域也不过是主体“自我”观照之后的投射结果。
但是,外化的符号形态对这些多重意义领域进行区分:心理活动以外化的表情和体态作为证明;主体间意义以主体和他者的对话为外化的证明;物质事物的意义以对其“价值特征”(value characteristics)的标签性语词为外化的证明。外化的符号既是意义领域的形式区分,又借此构成不同的实在(reality)。关联主体“自我”反思时,它们是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意义领域,而以外化的符号为尺度时,它们又是不同的实在。外化的符号形态帮助人从主体世界迈向外部世界,但正因为符号的存在,这一迈进过程仍时刻和主体的世界发生着关联。在这里产生个体与社会的界线,同时又使个体和社会处于切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
正因为从主体“自我”的意义领域向社会实在的转换,主体“自我”的视野从直接、眼前的周边社会延伸到间接、遥远的陌生社会,而这个转换以外化或客体化的符号为最重要的途径。外化的语言符号具有“疏离”(detachment)和“整合”(integration)的辩证能力(Berger, Luckmann 1991:52, 116)。也即反映社会生活经验,但又超越于情景化的经验偶然性,从偶发的经验片段中分离出来,形成对各种相关经验的概括、抽象和范畴化的“分离”能力,以及将时空遥远的不在场经验眼前化的“整合”能力。语言符号的这种辩证能力也使得个体和社会通过符号而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语言符号对于实在做出多重区分,但语言的这种辩证能力又为多重实在之间形成内在联系提供支撑。语言符号的分离能力实质表现为对于经验现象的抽象和概括的类型化能力,为主体间对于符号所承载意义的沟通和共享提供超越偶发性差异的基础,同时也为多重实在意义维度形成统一提供条件。另一方面,语言符号的“整合”能力为把超出主体“自我”时空范围的实在领域拉近到主体经验和反思的可及性范围提供可能。语言符号的这种辩证能力从另一侧面又说明:对于实在的多重性,除意义领域和外化符号两种透视角度外,尚有主体感知范围这一视角。从意义领域的角度划分实在的是胡塞尔,从主体感知范围的角度划分实在的是詹姆斯(W. James),从外化符号关联的角度解释实在的构成,并凸显日常生活实在的压倒性价值的是舒尔茨(A. Schutz)。
胡塞尔依据意义构成的理论视角将实在的领域划分为物质事物、生物有机体、心理和心理自我4类。意义构成的对象区分为上述4类,但最终又统一到“自我”的反思,并通过意义的主体格局而实现实在的统一性。在服从意义统一性的前提下,多重实在间的符号以及对于多重实在的不同感知过程都退居次要地位。胡塞尔这种对于意义的回溯视角,可以解释个体与社会关联时的心理维度,但是符号的外化形态似乎仅仅成为服务于意义表达的外部辨识,而缺少任何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时间轴线上衡量,当符号主体消失久远,外化的符号形态则容易成为无法还原其表达意义和主体意志的空洞标识,而符号区分的实在也将变得不可识别和理解。在获得意义世界的同时,我们可能丧失符号的世界。即使符号世界存在,也仅仅表现在符号主体出现的同时代,而难以回溯到符号主体消失的过去。在胡塞尔看来,外化的符号形态如此居于附属地位,不过是通往主体意义的一个驿站,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影响通向意义旅途的挂碍越少越好。这个极端就是德里达(J. Derrida)所说的语言符号的透明性(Derrida 1973:120)。索绪尔(F. Saussure)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理似乎佐证符号透明性的重要性。但透明的极端就是放弃符号,如同直抵裸体就不需要外衣一样,这样又回到符号的想象状态,而否定符号外化或客体化的必要,更是否定符号自主和独立的可能。
詹姆斯将实在划分为日常生活世界、幻想、宗教和科学等亚领域,其基本出发点是主体的感觉和感知。从感觉或感知的范围审视,日常生活构成主体能够操控并直接作用的实在领域具有压倒性优势。超出主体可控范围的实在之于日常生活世界则具有主体难以直接感觉或感知的超验性,如幻想、宗教和科学等实在。詹姆斯在强调感觉和感知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多重实在的构成离不开主体的关联性,也就是说,无论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性实在,还是幻想、宗教和科学等超验性实在,都因为和主体发生关联才获得本体论的存在。即使在日常生活世界,由于主体关联性的差异,又分化为不同主体的日常生活亚领域(sub-universes)。但是,这些超出主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超验实在如何才能和主体发生关联,詹姆斯隐约意识到符号的作用。针对这个符号的作用,詹姆斯提出一个新名词——“符号的震荡”(shock of symbol),旨在说明从日常生活的实在进入超验的实在领域需要某种中介进行桥接,而介于不同实在之间的符号履行着通知经验主体,预备进入另一实在的作用。詹姆斯所说的“符号的震荡”又常被替换为“差异的震荡”(shock of difference)(James 1950: 254),这个震荡的来源在于不同实在间的鲜明差异性,而符号发挥的功能恰恰是减缓震荡的作用。但是,无论震荡还是减震,符号对于詹姆斯的多重实在或日常生活世界的亚领域都处于工具性地位。如果对这种工具性符号进行形态学的分类和解释,则始终处于工具性符号学的范畴,而上升不到哲学符号学的层次。
舒尔茨虽然尝试沿着詹姆斯的理论路线建立一个多重实在的系统理论,也对胡塞尔的主体间共现观以及胡塞尔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非批判性知识,即理所当然的常识理论有所借鉴,并且也特别注意到詹姆斯多重实在间“震荡符号”的存在及其价值(Schutz 1962:343),但舒尔茨似乎忽略胡塞尔最核心的意义理论,因此建立的多重实在系统理论实际上并未超越基于符号的工具性地位而确立其哲学学说的层次。但舒尔茨的理论让我们注意到对于多重实在间符号的作用须要给予特别的学术关注。问题仅仅在于:从多重实在间的符号出发,而不是从主体“自我”出发,或经验的内在构成出发研究符号问题,已经远远偏离哲学精神。但舒尔茨对于哲学精神的偏离恰恰把他的研究价值引向社会学方向。就符号对于社会构成的作用这一问题,至杜尔干为止,似乎停留于“集体表现”的理论认识(卢德平 2013:10)。虽然后来社会学家戈夫曼(E. Goffman)和布鲁姆(H. Blumer)等人对于符号的社会功能做过更深入的研究(Goffman 1974:496-559,Blumer 1986:78-89),但其基本理论出发点都是将符号看成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表征,而把符号的意义来源以及主体“自我”之于符号过程的内在关系都完全抛弃。这个抛弃意味着对符号与实在关系的思考从哲学思辨进入实证的社会学领域。
3 实在的回溯
围绕这一理论问题,在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和詹姆斯的“多种实在”(many realities)及其所谓“亚领域”理论问世之前,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偏向:(1)对于符号与实在关系的思考基本上是把实在框定在抽象和去情境的意义上进行,关注焦点主要是实在与符号处于何种性质的关系。对于实在的构成不再细究,也从来没有人意识到需要对实在本身进行再深入的分析。(2)作为对第一种偏向的纠正,符号思想史上对于和符号关联之后实在所发生的变化进行一定的探索,承认产生符号化的实在,以及主体意向投射后的实在,但这种实在,理论上不过是原先实在的变形,并非什么不同的实在,更谈不上多种实在、多重实在。所以,这一纠偏的努力仍然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性,或至少在基本理论框架上并未实现突破。(3)与对实在构成的较少关注相比,包括符号学在内的哲学史更热衷于探究符号的特性、分类和功能等,形成以模糊的实在为轴心思考符号多样性、多元性的形式化倾向。
对于索绪尔和皮尔士(C. Peirce)经典符号学说的理论限度的考察也揭示出:对于实在的理论简化结果,直接影响到对于符号本身的研究,也使得派生于这一理论局限性的经典符号理论难以获得突破的方向。这一理论限度的方法论原因可以概括为:把实在设定为理论的常数,而把符号视为围绕这一常数形成的变量。在面对现象意义上的实在所具有的个别性和多样性特征的时候,索绪尔采取对实在的回避态度,并通过去除个别性、多样性而形成的指向普遍性、概括性的概念层面,把多样性的实在替换为普遍性的概念,提出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形成关于符号与实在关系思考的理论闭合(江怡 2014:6)。皮尔士则通过对普遍性和可能性的探寻,放弃对现象意义上的实在的考察。或者说,在皮尔士那里,现象意义上的实在不过是普遍性和可能性意义上的实在的载体,并成为实现后者,再现后者的手段(卢德平 2016:116-117)。索绪尔和皮尔士代表的经典符号学对于实在的回避或简化导致符号学较少关注实在的类型,以及实在与意义构成的关联,由此走向去除主体意义构建过程的符号形态学方向。
江怡. 作为哲学家的索绪尔[J]. 外语学刊, 2014(1).
卢德平. 从索绪尔到戈夫曼:符号学的转折[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9).
卢德平. 实用主义哲学与皮尔士经典符号学说的确立[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Berger, P.L., Luckmann, T.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ATreatiseofSociologyofKnowledge[M]. London: Penguin, 1991.
Blumer, H.Symbolic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andMethod[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Derrida, J.SpeechandPhenomena[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73.
Goffman, E.FrameAnalysis[M]. Bo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1974.
Gramsci, A.TheGramsciReader:SelectedWritings1916-1935[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Husserl, E.LogicalInvestigations[M]. London: Routledge, 2001a.
Husserl, E.AnalysesConcerningPassiveandActiveSynthesis:LecturesonTranscendentalLogic[M]. Dordrecht: Kluwer, 2001b.
James, W.ThePrinciplesofPsychology[M]. New York: Dover, 1950.
Schutz, A.CollectedPapersI[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