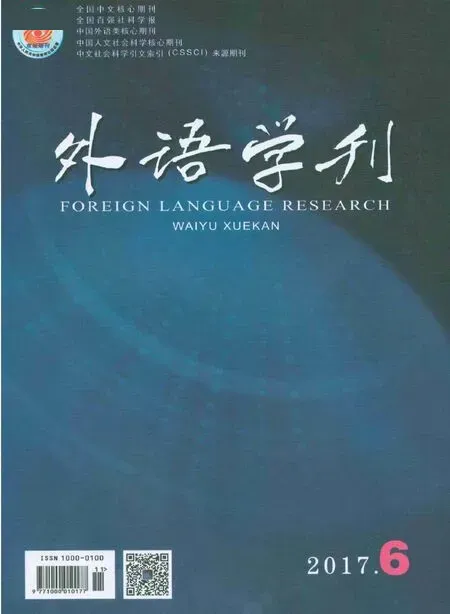大数据时代的语言哲学研究*
——从概念变化到范式转变
杜世洪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1 引言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说:“历史如果不被我们看成轶事或年表的堆栈的话,那么,它就能对我们现在所深信不疑的科学现象产生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库恩 2003:1)。库恩道出科学革命的“概念变化”(conceptual change)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科学发展是缓慢还是急速,科学的每一次革命都会体现出相应的概念变化和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毕竟,“科学革命主要指的是科学观念的变革”(李醒民 2010:1126)。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最早发表于1962年,距今已有五十多年,也正是在这五十多年里科学研究的信息化与数据化脚步急速加快,科学研究进入“大数据时代”(Big Data Era),正在“催生最大的数据变革”(徐子沛 2013:285)。大数据技术为哲学社会科学开启新的研究领域(Foster et al. 2017:1)。
2001年美国著名IT分析公司美达集团的分析师道格·雷尼(Doug Laney)对大数据概念进行界定(Laney 2001)。2012年美国IT分析界巨头嘉特纳集团公司正式提出大数据的概念和分析框架。2012年3月29日,美国政府网站白宫网发文说,奥巴马政府于今日公布“大数据研究与发展倡议”(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Kalil 2012)。这一信息的发布标志着世界迎来“大数据元年”,大数据时代的序幕拉开(Qiu,Wicks 2014:xxi)。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但自然科学研究进入新时期,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会因此而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正如文旭(2014)等学者预言的那样,外语教育的科研工作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等都会出现新的研究局面。这就意味着各具体科学会因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变化。
大数据不只是信息技术的创新,“我们在广泛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同时必须深入挖掘其中的人文精神”(陈仕伟 2016:50)。从哲学的方法论看,大数据时代将会引发科学研究的概念变化和范式转变,将会引起新一轮科学革命。既然科学革命具有概念变化和范式转变,那么在大数据时代里,以概念考察为核心内容的语言哲学研究将会面临怎样的概念变化和范式转变呢?这正契合钱冠连(2017)关于“语言哲学家在第二次哲学启蒙的时点上如何自处”的问题。
2 大数据时代特征与语言哲学研究的关系
要讨论语言哲学研究的概念变化和范式转变,就要探究语言哲学研究同大数据之间的关系,这就要从大数据的特点和影响谈起。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在其合著的《大数据:一场将转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思维的革命》(BigData:ARe-volutionthatWillTransformHowWeLive,Work,andThink)里说:大数据标志着一场重大革命的到来,它不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而且还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Mayer-Schönberger,Cukier 2013:11)。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生活、工作和思维这3者往往通过语言而交织在一起。毕竟,想象一门语言就是想象与之对应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 2001:13)。我们的生活形式具有海量数据的储存,大数据势必会为语言认知、自然语言处理带来巨大变化(Agerri et al. 2015:36-42)。既然在大数据时代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会出现改变,那么引起这些改变的大数据时代的特点是什么。
大数据时代的标志是数据的海量汇集,指数据或信息量特别巨大而无法再用传统的常规办法加以处理,需要信息处理方法的转变。大数据实质上是,在互联网时代人工智能和计算科学研究的数据化进程中,涉及到信息处理的自然科学领域里出现规模极大的数据收集与处理。目前,对“究竟什么是大数据”(Mauro et al. 2014)这一问题虽然争议不大,但是,以大数据为发展目标的数据化进程变化很大,因而在认识上存在一些差异。大数据的数据化进程以信息的“海量汇集”和“专门利用”为特征,它经历渐变、巨变、聚变直至信息爆炸这一过程,是最近五十多年里(特别是互联网时代里)多种学科、多种技术交融与衍化的结果(Hurwitz et al. 2013:10)。大数据本身源于社会,而大数据化进程首先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然后逐步迈向人文社会科学,并最后以渗透的方式又回归到整个人类社会。从而引发一场转变我们生活、工作和思维的革命。
大数据时代的实践特征就是大数据的专门利用。2001年,雷尼根据大数据的特点使用volume,velocity和variety(简称3V)正式界定“大数据”概念,这里的3V可简略为“三极”:极大——数据量与规模极大;极速——数据处理速度达到极速; 极多——数据类型分布极多(Laney 2001)。嘉特纳集团兼并美达集团后,2012年对大数据的特征做出补充,在原有的3V基础上增加veracity,极真——大数据提供的信息极为真实。后来,人们发现大数据的特征还有“第五极”,极高——大数据的价值极高。这“五极”(5V)是对大数据的正面特征的认识。随着研究的推进,人们又发现大数据还具有负面特征:极易变化(variability)和极为复杂(complexity)。既然大数据的“七极”特征是极大、极速、极多、极高、极真、极易变化和极为复杂,那么正确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至关重要(Ji et al. 2013:1)。
大数据时代信息处理的行为特征是正确的数据挖掘,而数据挖掘究竟同语言哲学研究具有什么联系?数据挖掘本身属于经验科学操作层面的“数据计算”和“数据使用”的行为,它为解决管理、行政、商务、社会、媒介、人工智能、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等领域的复杂问题,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Chu 2014:V)。因为有大数据作为支撑,加上正确的数据挖掘,在大数据的专门利用中,过去那种因为经验狭隘、数据不足以及方法局限造成的“大海捞针”式的难题,将不再是难题。人类行为会因为“大海捞针”的成功而出现新的思想特征。
人类行为模式的突破是思想认识疆域的延伸。正确的数据挖掘这种行为反映大数据时代的思想特征。如果拥有的数据种类与样式足够丰富、数据汇集足够完整、行为目标足够明确,那么拥有这样的大数据,人类在认知活动中就仿若拥有“天眼”。这意味着“上帝之眼”走向人间,不再虚幻而会真实地出现在大数据时代的认知活动中。这会在各门具体学科研究领域里,引发思想重心的转变和问题焦点的转变。有大数据的存在,对真之本体论式追问(如“什么是真?”)就会让位给对意义的追问,因为一切的真都会在大数据里自然存在,反映出多元世界观里多元的真,“真”与“真”的关系成为研究中心。这在思想重心上,会出现从追求事物的因果(cause)关系到追求事物的相关(correlation)关系的转变。在具体研究问题的关注焦点上,会出现从对“为什么”的追问到有多少个“什么”存在上来(Mayer-Schönberger, Cukier 2013:18),即转移到追问“有多少具体的什么”存在于大数据中。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挖掘不仅因其实用价值而越来越重要,而且在方法论上越来越复杂,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因此,正确的方法论是大数据时代急需的哲学指导,这就需要从大数据的“经验科学”层面升华到“理性的思辨”层面上来。
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在《真理和其它迷团》(TruthandOtherEnigmas)里说,语言哲学是一切的基础,语言哲学是哲学思辨的基础,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分析才能进入思想考察(Dummett 1996:441-442)。从达米特的这一观点看,关于大数据的哲学思辨终究离不开语言分析。其实,理论层面的大数据研究并不能离开语言层面的研究。2013年5月30日在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举办的第十届世界电子世界杯(ESWC)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语义学和大数据”(Semantics and Big Data)。这次会议明确指出,大数据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人工智能和计算科学等领域,因为大数据的研究在本质上是语义学的研究,大数据研究会涉及到庞大的“语义网络”(the semantic web)(Cimiao et al. 2013:18)和“智能网络”(the intelligent web)的研发与利用(Shroff 2013:xiv)。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的认知特征和语言哲学研究的关系可以概括如下:大数据时代因其构成特征、思想特征和行为特征而给人们生活、工作和思维带来巨大变革;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前,“大海捞针”式的难题总是无法解决,而大数据时代就是要让传统的“大海捞针”式的各种难题得到充足的数据支撑直至问题的消解或解决。这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体现为思想上的概念变化,然后逐步形成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大数据时代的哲学研究会出现两大转变:其一,从追问事物间“因果关系”转变到重视事物间的“相关关系”的追问;其二,从追问事物内在性质“为什么”的“所以然”转变到追问“有多少个什么”相互存在的“量与然”的认知活动上来。这两大转变终究会体现在我们赖以生活的语言里,因为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而且语言分析还是思想分析的必由之路;因此,大数据时代的语言分析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其转变首先表现为概念变化,然后会在语言哲学研究领域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从对概念属性的考察转变为对概念变化的考察。
3 从概念属性考察到概念变化考察
关于大数据的研究,本质上离不开语义研究。Erl等人说,大数据的储存以概念为单位,对大数据的利用其实就是对概念做语义考察(Erl et al. 2016:91)。在大数据时代里,语义考察离不开概念考察,因此,维特根斯坦的论断仍然具有指导作用。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活动就是“通过能够说清楚的”把“不能说清楚的指示出来”(Baker, Hacker 1980:467; Wittgenstein 1999:77);哲学尝试在我们的知识体系里为语言建立一种秩序,而带着这一理念,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来澄清、治疗或消解哲学问题(Baker,Hacker 1980:484;Wittgenstein 1999:51;杜世洪 2010:7-13)。哲学的概念考察首先要回答“什么是概念”,然后在具体的认识指导下进行与之对应的语言概念分析活动。沿着这一路径,大数据时代的概念考察势必会发生从概念属性考察到概念变化考察的范式转变。不过,在大数据时代语言哲学的范式转变过程中,对概念属性的考察虽不再是焦点,但仍是考察的出发点。
在概念属性的考察上,大数据时代的语言哲学研究仍然需要回答“什么是概念”。这一问题属于对概念本质的追问。在哲学研究的传统中,追问“什么是概念”如同追问“什么是本质”以及“什么是真”一样,属于“形上学”(metaphysics)的本体论问题,而回答本体论问题的方式却离不开知识论的方法。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语言哲学研究,正如布兰顿所说,对真的追问已经不太重要,而重要的是对意义的考察(Brandom 2009:156)。维特根斯坦说,“本质对我们隐藏着”,哲学要“把一切摆到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维特根斯坦 2001:65,76)。维特根斯坦这话切合的正是大数据时代对事物的关系认识的方法与内容的转变:在方法上是从解释转变到描写,大数据面前无需解释;而在内容上是从注重事物间的因果性转移到事物间的具体联系上来,大数据面前“是什么”显而易见而不须探究“为什么”。“什么是概念”这一问题在大数据面前必将有海量数据来显示概念如其所是的存在状态,而概念的本质在存在中显现出来。
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哲学、心理科学、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就这一问题给出不尽相同的回答,但无论什么样的回答,关于概念的认识都不会是孤立的(Jakendoff 1999:305)。对于概念性质的认识,保罗·萨迦德(Paul Thagard)认为概念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别:实体概念与非实体概念(见表1所示)。

表1 哲学和心理学关于概念性质的不同认识
注:此表改编自萨迦德的分类表(Thagard 1992:18)
萨迦德在表1中提供的是关于概念性质的认识,其中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就概念本身而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认识。而且既有的关于概念的认识仍然处于争论之中。正如福多(J.A. Fodor)所说,无论是认知科学还是哲学,关于概念研究的那些现有理论都很难说是严格而有效的(Fodor 1998:23)。这话出自福多的《概念:认知科学犯错之处》(Concepts:WhereCognitiveScienceWentWrong)一书。正如这本书名所示,福多所言是对现代认知科学关于概念研究的批判,认为概念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认知科学恰恰就在对概念本身的认识上出现错误。那么,现有的关于概念的理论有哪些,它们为何会出现错误。
关于“概念是什么”的研究,目前大致有5类方法:定义法、原型法、词汇表征法、心理框架法和命题结构法。定义法和原型法相似性很大,主要是用区别性特征和典型特征来界定具体的概念。定义法和原型法是“经典方法”(Smith 1998:501-526),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方法对抽象的和具体的实体概念具有一定的定义效果,比如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幸福”以及“什么是鸟”等。原型法常与范畴界定关联。词汇表征法常常涉及单个词汇携带的概念内容。心理框架法主要把概念当成思想、信念和知识的基本单位,概念本身具有一系列知识属性。命题结构法把概念看成“主词—谓词”构成的“论元结构”。尽管这5类方法关于“概念是什么”看法各有差别,但是它们拥有共同的认识——“概念具有属性”。
从现代哲学看,无论是像弗雷格(G. Frege)那样把概念同“对象”(object)及其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考察,还是维特根斯坦那样把概念同语词使用中的“意义”(meaning)联系起来研究,概念考察其实离不开对概念属性的考察。这一点在词汇表征法和心理框架法中尤为明显。回答“某一概念X是什么”,其实就是回答“拥有某一概念X的情形是什么样子”,“拥有一个概念X就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即拥有X这个概念就能够识别X的一切” (Fodor 1995:1-25)。在实用主义范式下,拥有一个概念就是能够做符合该概念性质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能够思考该概念的性质。
关于概念属性的考察实际上是对概念的生成或者说起源的考察。其实,概念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哲学上的因果论问题,即追问什么引起什么概念。在“语言分析哲学”(杜世洪 李飞 2013:9-15),特别是“实用主义语言哲学”(杜世洪 2014:1-7)的视野下,概念总是同“语言表达式”联系在一起。考察概念势必要借助于相应的“语言表达式”,其实对概念属性的考察仍离不开语言表达式。这里的语言表达式可能是表达“自然类别”(natural kinds)的语词(如“鸟”的概念),可能是用于概括某种系统知识的术语(如“量子力学”这一概念),可能是认知主体的心理意向在语言符号上的凝定(如“我心有大海”),可能是心理某种观念的语言符号化(如“他要做个大善人”),可能是借助语词在经验层面上对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进行的综合判断(如“王冕死了父亲”“我的心在流血”等),可能是借助于语词在先验层面上进行的分析判断(如“平面三角形有3个内角”),等等。
语言表达式只是概念的表现形式。在语言形式长度上,概念表现为语词、词组和命题语句等。这样的表现形式是静态的。值得注意的是,语词最为基本,是所有概念表达式都具有的成分。弗雷格认为,要区分概念(concept)和对象(Frege 1952:42-55)。对象通常是用专名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且对象本身是完整的和饱和的,但对象的专名本身又可成为概念。概念的语言表达式是不完整的(incomplete)和未饱和的(unsaturated)。在概念层面上,语词或词组是未饱和的表达,未饱和的表达可以作为谓词与某个专名联系在一起而形成命题。在弗雷格看来,关于X的概念可以用函数关系来表示:f(x)=(X)+谓词(1-n),n分布范围从1到无穷大(唐其敏 杜世洪 2016:63-69)。
从弗雷格的概念观出发,我们认为概念表现形式可以用公式来表示:概念的语言表达式=(主词)+(谓词)。二者加上括号,意思是一个概念表达的是“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主词承载的是“概念核”,谓词负载的是概念属性,用公式表示为:概念的语言表达式=(概念核)+(概念属性)。一个“概念核”完全可能具有多种属性,而且同一概念核与不同的属性结合起来,会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式。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的语言表达式的成分
在语言表达中,承载“概念核”的主词不能省略,而负载概念属性的谓词可以省略,而且即便在没有省略谓词的情况下,表达出来的谓词也只是某一概念的一种属性或者部分属性。即,要表达一个概念,一定要把“概念核”以主词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一个概念的属性不可能而且没必要全部同时表达出来,甚至根本不需要明确表达这一概念的任何属性。例如,“中国人”可能会是省略属性表达的一个概念表达式,也可能以“中国人”为主词把中国人的属性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中国人很勤劳”“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到处都是”“中国人是亚洲人”“中国人什么都吃”“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等。如图1所示,静态的概念属性考察,就要尽量穷尽一个“概念核”到底会与多少个概念属性发生联系,从而形成命题,通过相应的语言表达式呈现出来。
在日常语言中,属于自然语词的“哈密瓜”“鸟”等, 属于虚构语词的“王母娘娘”“金山”“独角兽”等,属于心理感受的抽象语词如“幸福”“嫉妒”等,属于特殊场景的语词如“国宴”“化妆舞会”等,属于学科知识的专业术语如“量子力学”“转基因”等,这些一个个孤立的语词都可能成为单独的概念表达式,因为它们都可以作为主词而与某些能负载概念属性的谓词结合起来。当然,这些看起来孤立的语词完全可以同其它语词结合使用,形成完整的表达,以便实现话语交流的目的。这里要注意的是,拥有这样的同一语词并不意味着拥有同一的概念。例如,艾滋病这一语词,在普通人、艾滋病专家和艾滋病患者这3类人中具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他们拥有不同的关于艾滋病的概念属性。又如,当有人说“我对国宴没什么概念”时,似乎是说“我”没有参加国宴的经历,其实,这里体现的是“我”虽然能使用“国宴”这一语词,但是“我”没有关于“国宴”的构成属性。
“艾滋病”和“国宴”这两个例子反映出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指称问题、意义问题以及语词使用与概念考察的问题。语言哲学界关于通名、专名的问题、关于指称的问题、关于名称的外延与内涵的问题等都属于概念考察工作。在方法上属于分析方法,其实,在追问“指称”和“意义”这些概念的性质时,语言哲学研究仍然具有本体论的追问方式,仍然离不开形上学。即便在追问“指称的呈现方式”和“意义的表达方式”时,语言哲学的研究仍然属于静态的概念考察,即聚焦到某一概念上,对这个概念进行详尽的属性分析。
大数据时代的概念考察无疑要继承概念考察的传统,更重要的是要开启概念考察的动态方法。因为统一在静态语词下的概念属性一直在变化,即承载概念核的主词会与不同的新增属性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概念考察势必要由原来的静态属性考察转变到各概念属性的相关性揭示上来。动态的概念考察必定要考察概念属性的时空变化问题,还说明概念的活性问题,即进行专门用途的数据挖掘时,不须要考察某一概念的全部属性,而须要考察该概念的相关属性。这可以用图2表示。

图2 概念相关属性示意图
4 大数据时代关于概念活性与概念属性的时空变化的考察
大数据时代注重追问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这在语言哲学研究中对应的是关于概念活性的考察以及概念属性的时空变化的考察。一个概念有多个属性,而且还会增加新的属性,但是只有那些具有活性的属性才会与其它事物对应的属性发生关系。这就是说,对事物相关性的考察其实就是对概念活性的考察。
科学上的重大革命在概念层面上都是针对具体的概念属性进行的,当人们专注考察某种特定的属性时,受到关注的属性就属于概念的活性属性。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的地心说,其中的活性属性考察重点就是“谁是天体运行的中心”。牛顿的机械力学,加上他的物理学,取代笛卡尔的宇宙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牛顿物理学进行扬弃;而量子力学的出现是对牛顿物理学的彻底革命。所有这些重大变革其实都是围绕某一特定概念的活性属性的考察进行的。既然大数据时代会带来重大的变革,那么其中的概念考察就要围绕概念活性进行。这方面的考察工作需要在庞大的语义网和智力网中搜寻相关属性及其赖以存在的“数据语境”(datum context)。在数据语境中对活性属性的考察,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方向虽然目前尚需大量研究的投入,但在学理上,这种研究可以追溯到罗素及穆尔的感觉—资料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关于概念变化的考察会在“语言内”(intra-lingual)和“语际间”(inter-lingual)反映出来。概念是由具体的语言表达式呈现出来,那么用于概念表达的语词会反映出概念属性的时空变化,即语词既会承载时间维度下保留的概念属性,又会承载空间维度下保留的概念属性。例如,很多年前的冬天,大雪纷飞,后院的树雪满枝头。很多年后,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如果还说:后院的树雪满枝头。这时,“后院的树雪满枝头”这句话会留下什么思考呢,这句话的内容是否为真。在极端的直接指称论者面前,这句话在多年前的冬天是真实的,因为当时确实如此,而在多年后的夏天,面对后院的这棵树说这话,就不真,而且似乎也没有意义。对此,弗雷格会说,这里涉及到两个层面的理解:“真”是指语句内容同外部世界具体情况相符合,这是极端指称论的理解,是弗雷格要批判的理解;按照这一理解,“后院的树雪满枝头”在多年前的冬天说是真的,而在多年后的夏夜却是假的;这里要注意的是,判断这句话的真假时,表面上使用的是外部世界的指称的符合状况,其实,这里还存在着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判断,而这个用来判断冬天和夏天时说同一句话的思想观念却并没有变;所以,另一种理解就是“真”,指关于外部世界形成的思想,这是弗雷格认同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冬天里说“后院的树雪满枝头”与夏天里说“后院的树雪满枝头”具有同样的指称内容,同样是真的,因为有同样的思想,而不同点在于这句话呈现的时空发生变化,使用这句话的意义也就不一样。
在大数据时代里,面对海量的数据,尤其须要注意对概念时空变化的考察。例如,语言内的时空变化现象,语词“床”属于自然词类,它的静态概念属性后来出现“窄化”,于是,就会出现用“窄化”的“床”来理解唐代的“床”。于是,李白《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的“床”被误解为睡觉的“床”,而鲜有人知道那是指“井栏杆”。同样,《水浒传》的“病关索杨雄”“病大虫薛永”等中的“病”字,在宋元时代却还有“赛得过,比得上”的意思。概念的时空变化体现在语言上是以细枝末节的方式进行,而大数据为这些细节变化的知识累积及理解提供支撑(Olsher 2014:131)。
语际间概念属性的时空变化仍然会通过语言内的时空变化来体现,即当一种语言内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借鉴另一种语言的相关概念来解决。例如,现代汉语对“王冕死了父亲”的解释围绕“死了”的语法性质和概念性质出现很多争论。在这些争论中,“王冕死了父亲”这句话一直被当作汉语特有的语句来整体处理,没有给予英文翻译。试想一下,“王冕死了父亲”该怎样译成英语。译成英语后,原来争论的问题是否还存在。
在大数据时代里,随着概念属性发生时空变化,概念考察工作就要考察那些能够引起概念本身变化的属性是什么,确定属性变化的数据结构,给概念的时空变化予以同步解释。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的基本特征足以说明我们思维中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两个维度:概念整体数量的飞速增加和概念个体属性的不断累积。那么,以概念考察为核心工作的语言哲学研究就要面对因概念变化引起的范式转变。大数据时代的语言哲学研究正在发生范式转变,这范式转变的基本特点就是从静态地追问“存在”“真”“意义”等哲学概念转变到动态地考察“有什么存在”“有哪些真”“意义的累积过程”等这样的研究上来,这正与语言哲学研究的实用主义转向契合(Bernstein 2010:13)。在大数据时代里,追问具体的“存在”不再是假定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追问柏拉图式那种难以企及的理性存在,而是根据相关性特点追问具体存在涉及的概念或者概念属性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关性的概念或者概念属性,它们处于巨大的语义网络中。在这语义网络中,按相关性要求,对活性概念或者说对具有活性的概念属性的追问,这才是大数据时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新课题。概念在大数据时代之所以呈现活性,就在于数据汇聚过程中会出现概念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概念的时空延伸上,这就会出现概念累积的差异。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做语言哲学研究的意义追问,就是要追问意义的累积性质。
大数据时代以其海量数据让一些过去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让人们在意义追问中能够分辨出意义的时空性质和累积特性。大数据带来的不是数据之大所面临的处理压力,而是有大量数据为依托的研究动力。
陈仕伟. 大数据技术异化的伦理治理[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1).
杜世洪. 关于假装的语言分析和概念考察——对中国后语言哲学的一个思考[J]. 外语学刊, 2010(2).
杜世洪. 实用主义语言哲学思想探析——皮尔士的意义理论[J]. 外语学刊, 2014(3).
杜世洪李 飞. “语言分析哲学”的一个新动态——布兰顿意义理论概览[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9).
李醒民. 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下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钱冠连. 后语言哲学参与第二次哲学启蒙[J]. 外语学刊, 2017(1).
唐其敏杜世洪. 关于英语学习者的语言意识与概念充实的思考[J]. 当代外语研究, 2016(6).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文旭. 语言的认知基础[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
徐子沛.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Agerri, R., Artola, X., Beloki, Z., Rigau, G., Soroa, A. Big Data for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 Streaming Approach[J].Knowledge-basedSystems, 2015(79).
Baker, G.P., Hacker, P.M.S.Wittgenstein:UnderstandingandMeaning[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Bernstein, R.J.ThePragmaticTur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Brandom, R.B. Why Truth Is Not Important in Philosophy[A]. In: Brandom, R.B.(Ed.),ReasoninPhilosophy[C].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u, W.M.DataMiningandKnowledgeDiscoveryforBigData:Methodologies,ChallengeandOpportunities[M]. Berlin: Springer, 2014.
Cimiano, P., Corcho, O., Prasutti, V.TheSemanticWeb:SemanticsandBigData[M]. Berlin: Springer, 2013.
Dummett, M.TruthandOtherEnigmas[M].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rl, T., Khattak, W., Buller, P.BigDataFundamentals:Concepts,DriversandTechniques[M]. Boston: Prentice Hall, 2016.
Fodor, J.A. Concepts: A Potboiler[J].PhilosophicalIssues, 1995(6).
Fodor, J.A.Concepts:WhereCognitiveScienceWentWro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ster, I., Ghani, R., Jarmin, R.S., Kreater, F., Lane, J.BigDataandSocialScience:APracticalGuidetoMe-thodsandTools[M]. London: CRC Press,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7.
Frege, G. On Concept and Object[A]. In: Geach, P., Black, M.(Eds.),Translationsfrom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GottlobFrege[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Hurwitz, J., Nugent, A., Halper, F., Kaufman, M.BigDataforDummies[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3.
Jakendoff, R. What Is a Concept, That a Person May Grasp It?[A]. In: Margolis, E., Laurence, S.(Eds.),Concepts:CoreReadings[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Kalil, T. Big Data Is a Big Deal[Z].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2012/03/29/big-data-big-deal, 2012.
Laney, D. 3D Data Management: Controlling Data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Z]. META Group, 2001.
Ji, C., Li, Y., Qiu, W., Jin, Y., Xu, Y. Big Data Proce-ssing: Bi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JournalofInterconnectionNetworks, 2013(3).
Mauro, A.D., Greco, M., Grimaldi, M.WhatIsBigData?AConsensualDefinitionandaReviewofKeyResearchTopics[Z].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2014.
Mayer-Schönberger, M., Cukier, K.BigData:ARevolutionThatWillTransformHowWeLive,Work,andThink[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Olsher, D. Semantically-based Priors and Nuanced Know-ledge Core for Big Data, Social AI, and Language Understanding[J].NeuralNetworks, 2014(10).
Qiu, R., Wicks, M.CognitiveNetworkedSensingandBigData[M]. New York: Springer, 2014.
Shroff, G.TheIntelligentWeb:Search,SmartAlgorithms,andBigDat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mith, E. Concepts and Induction[A]. In: Posner, M.(Ed.),FoundationsofCognitiveScience[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8.
Thagard, P.ConceptualRevolu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Wittgenstein, L.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TLP)[M].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PI)[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