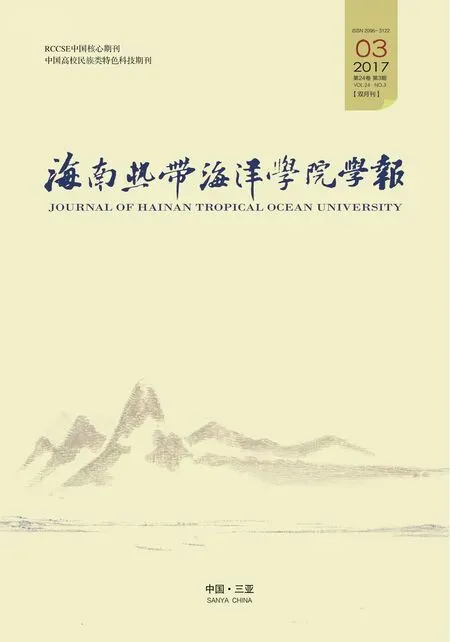黎族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启示
文丽敏,公衍峰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黎族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启示
文丽敏,公衍峰
(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
人们长期对古代黎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存在误解,真实情况表明这恰恰是黎族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形成的生态智慧。这对我们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下,具有深刻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黎族;生态智慧;轮作
长期以来,黎族一直被视为落后和不开化的民族,这个民族曾经的许多经历和传奇成了它不文明的证据。诸如黎族的刀耕火种,黎族女性玩“隆闺”,黎族的女子“文身”,黎族的已婚妇女不落夫家,黎族的敬神怕鬼,等等。当然,被人诟病最多的当然还是黎族放火烧荒的耕作方式,这被认为是给海南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人云亦云的讥讽甚至使许多黎族人自己也疑惑起来,怕谈自己民族的过去,愿意向外人展示自己民族“汉化”或现代化的成就。
黎族的传统文化真的有那么落伍吗?不是。至少与汉民族相比,黎族的许多风俗特征都值得本民族的人们骄傲。以女子玩“隆闺”为标志的两性关系的相对自由平等,比起汉族的节烈贞操观要健康自然得多;对自然神灵的敬畏,比现代人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态度也要好得多。
一、 对“刀耕火种”的再认识
“刀耕火种”一直是原始与落后的代名词,但当我们真正深入黎区去了解黎族人的生活时才发现,刀耕火种不仅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野蛮,而且堪称是一种生态智慧。
“黎族的先民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摆脱了单纯的采集经济,发展了早期原始农业——山地农业亦即烧垦农业经济,便使用加工工具(石器),借助自然的力量(火),向自然环境索取食物,焚山耕种又称‘刀耕火种’,即砍倒烧光的游耕经济。”[1]在明代顾岕的《海槎余录》中,对这种方式也有详细的记载:“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砍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酷烈则纵火,自下而上,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贝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别择地所用前法。”[2]
首先,黎族的刀耕火种(黎族人称为砍山栏),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肆意而为,而是一种有着周全的环境考虑的生产方式。他们会选择离村落有一定距离,坡度较缓,无高大树木的地方(黎族人对古老巨大的树木心存敬畏,不轻易采伐),砍伐灌木,待树枝水分蒸发后点燃,燃烧后产生的草木灰成为天然的肥料。再用削尖的木棍在土地上戳洞,将稻种点播在洞内覆土,即完成了播种过程。早期黎族对所种的山栏稻一般不进行田间管理,待成熟期将至,才派人守护驱赶鸟兽。这种播种方式比起汉族的精耕细作式农业,从生产效率上来说,当然显得相当的粗放和原始。但若从环境影响评估的角度来看,黎族的耕作方式比汉族要好得多。
其次,黎族的播种方法不是大规模垦荒,不易造成水土流失。汉族的大规模垦荒是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也是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这种咽不下去的苦果,至今仍使中华民族如鲠在喉。而且,黎族采取土地轮休方式,在一块土地播种二至三年后即放弃,既避免了因土地肥力下降导致的粮食减产;又可以使土地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自然恢复良好的生态条件,可供再一次循环使用,还可以避免病虫害的大规模发生。今天,我们都听说了一个时髦的概念,叫作“循环经济”。其实黎族先民们创造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简单实用的“循环经济”。现在,欧洲和北美一些国家的大农场,已经重新恢复了古老的土地休耕轮作制度。
现在刀耕火种被诟病最多的就是对森林的损毁。但比起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和历代朝廷为“平黎”“剿黎”而进行的开路焚山对森林所造成的破坏,黎族砍山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我们说砍山栏对环境影响不大的原因除了人口数量少以外,更重要的是黎族对待自然的态度以及与自然共生互惠的关系。笔者曾经到五指山一带做过有关黎族传统文化的田野考察,对黎族人与自然环境的相处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黎族在没有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一直与大自然保持着紧密和良好的关系,黎族人堪称是自然之子。黎族人认为自然界的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都是有情感有灵性的。人只是生灵中普通一员,所有生灵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们要生存就要与自然的生物或自然现象打交道。黎族人就像与族人、与邻里相处一样对待自然万物,他们认为只有人类态度合适谦和,取之有度,才能得到自然界与众生灵的谅解。这就是早期人类自然崇拜的由来。
黎族所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在生态许可的范围内进行,除了极少量的铁制生产工具,黎族其他的生产生活用具,包括所有的建筑全部取自自然物。黎族的许多生产生活用具都是木制或竹制,包括房屋。在它的使用功能被穷尽之后,很方便再化为泥土。以独木制作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具是最有黎族民族特点的器物,并且十分结实耐用。我们在黎村采风时,惊讶地发现很多用了几代人的独木器具仍在使用。这与我们两三年淘汰塑料用具,三五年淘汰金属用具的生活习惯反差太大。
黎族的房屋无论是最初的干栏式建筑,还是后来的船形屋,都是用木桩加竹制框架支撑,用茅草铺顶,用泥护墙。防潮隔湿,冬暖夏凉。今天绝大多数的黎族同胞都已住进由当地政府援建的水泥平顶房子里,可是我们问了许多黎胞,他们仍然怀念茅草作的船形屋。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的回答是水泥房子住着不舒服。这是一个可信的答案。水泥平顶房子的唯一好处是结实。我们到海南后曾经住过水泥平顶房子,堪称是冬冷夏热,极不宜人居。而汉民族营造已久的砖瓦房,其大规模烧制砖瓦的过程对环境的破坏也是很大的,这不仅是指采挖土方对地表的破坏,而且在没有矿物质燃料的时代,这必然要消耗大量的木材。今天,海南蒸蒸日上的水泥、石灰、砖瓦产业已经成为威胁这个海岛环境生态的重要原因。
黎族人的自然崇拜让人印象深刻,但凡是自然界呈现的物象,基本都在黎族人的崇拜范围。这是因为,黎族直到19世纪之前很长的历史阶段都处于生态环境系统之内。他们的所有生存需求,都来自于自然物。他们绝大部分的废弃物,都可以重新回到自然界参与新一轮的生态循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黎族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植物利用史”[3]。我们今天还能查阅到的黎族各种调查研究资料中,有明确记载的自然崇拜就有十几类数百种之多。黎族人普遍认为雷、风、雨云、雾、等天象都有一种神秘的“灵性”在其中,因此有土地崇拜、山崇拜、石崇拜、火崇拜、水崇拜、稻种崇拜、树崇拜等。黎族人认为大树通灵,特别是被奉为神树的大树,不仅不能砍伐,也不能随便折枝攀登。此外,还有牛崇拜、犬崇拜、蛙崇拜、鱼龙崇拜、鸟崇拜、狗崇拜、猫崇拜等动物崇拜,以及木棉崇拜、芭蕉崇拜、番薯崇拜、竹崇拜等植物崇拜。这些广泛存在的自然和自然物崇拜,虽然存在于不同地区,但从其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上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
对“万物有灵”的信奉,使母系氏族社会的黎族在与自然打交道时小心谨慎。“万物有灵”的出发点,有点像今天人们所说的“换位思考”,是一种以己推人的立场。当事的黎族人会从对象物的感受,来想象人的行为可能对其带来的影响甚至是伤害。他们就会尽量缩小和控制这种影响和伤害,并对此作出补偿。
在这种精神制约下,黎族对自然一直是敬畏有加,取之有度。努力寻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相安无事的途径。大大减少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当人心是用信仰的方式自律时,其效果最佳,社会监管成本最低。当人心是用刑法的方式他律时,其效果最差,社会监管成本最高。今天我们为了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不得不供养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包括公、检、法、税务等等。这种外部监管必须依赖缜密的法律和法规体系来运作,但仍不能杜绝违法犯罪行为。”[4]
二、 黎族的所有生活过程融入自然之中
过去黎区也经常发生氏族间的冲突,有时也会爆发反抗汉族官吏的民族起义。但是黎族人不用深沟高墙来防御外敌,他们采用更加生态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村峒,即在居住区周边种植和养护荆棘类植物带,形成高5~6米,宽3~4米带刺的树墙。其防护效果在那个时代,要超过一般的高墙。一个人或几个人要想无声无息的穿越这种树墙是不可能的。
事实证明,黎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对自然环境破坏程度最小的,一个黎族村峒几百年下来,周边的生态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整个海南岛在黎族这个先住民族繁衍生息的数千年时间里,森林覆盖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就是一个明证。公元前110年,海南岛划入西汉王朝版图,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南的统治,进行了多次移民垦荒。开山“平黎”,加上官、商采伐贸易,到20世纪初,海南岛原始森林覆盖率已下降至50%。此后日本入侵海南岛,对森林的掠夺最为严重,致使森林覆盖率从1933年50%下降为解放前夕的35%。相当于元明清三朝森林消失总和。*参见颜家安《海南岛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新中国成立后,海南生态的重大破坏是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为了炼钢和建设用材,海南的原始森林被大肆砍伐。大力发展橡胶事业、发展热带高效商品农业,又使原本所剩不多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今天海南岛的绿色植被大都是近50年来恢复过来的次生林和人工林。真正的原始雨林只残留在霸王岭、吊萝山和尖峰岭的部分地区。
当然,黎族的绿色生存之道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人口密度不能太大。据史料记载,晚清时的黎族人口约25万左右。*参见[清]明宜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如今海南岛黎族人口已经超过127.74万人*参见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载《海南日报》2011年5月11日第A2版。,当然不能再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去了。但是,黎族的生态智慧对于我们应对现实的生态危机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15年,阿尔贝特·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理论*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法国思想家,创立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代表作品为《敬畏生命》等,将伦理学的范围由人扩展到所有生命。,随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核心主张就是:敬畏生命的“生命”不仅是人的生命,而应该是一切生物的生命,即对一切生命都应是“敬畏”的态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施韦泽的思想开始体系化。施韦泽生命观的重要特征是将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他认为:“人类长久以来将自然生命排斥在‘生命意识’之外,这是传统文化和伦理的根本缺陷所在。”[5]因此,人类只有敬畏一切生命——包括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才能最终使自己的生命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尊重和保护。这种学者个人的醒悟,其实就是回到了黎族早期的精神存在状态。现代学者用理性重新认识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想境界,是黎族人早就用生命自然体验到的生存常识。
人类本来是“自然之子”,在其日益膨胀的物欲推动下,人类不仅虐待自己的同类,也开始虐待自然,把自然视为可以肆意掠夺的资源。人原本就在自然万物的网络之中,或主动,或被动调整适应自然的选择,包括人的身体也有适应自然选择的机能。人类只有尊重一切生命,敬畏一切生命,才能从根本上对自己负责。“如果没有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我们的生命来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来自我们的生命,这一生理学上的事实在精神意义上特别重要。”[6]只有当人类能够真正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摆正自己在这个自然万物的网络中的位置,人类才能感受到自然的无限生机与奇妙,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与高贵。“任何事物,不管它自身如何完整,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某种关系中保持其存在的。”[7]
我们在从事黎族的人类学考察之时,曾经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在没有蚊帐、没有蚊香的年代,黎族人怎么应对成千上万的蚊虫叮咬?问过许多黎族人,他们也说不清楚。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黎族老人道破了天机:“咬一会儿就不怎么咬了”。答案其实就这么简单!人的肌体有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与调节机制,会自动分泌出让蚊虫不喜欢的味道或产生其他回避机制。这是人与自然长期磨合适应的结果。今天这样的人体调节机制几乎不起作用了,我们被迫用疫苗、空调或各种药物保护自己。然而,人体的免疫与调节功能因此不断下降,自然界各种对抗人造药物的超级细菌、超级病毒不断产生,人类正在为自己积累日益严重的防疫危机。“SARS病毒”在2002年底开始席卷了半个地球,现在“寨卡病毒”又呈全球传播之势。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身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自然界和其他一切生命之上。因此人类越来越藐视自然规律,不断地违背自然规律。在遭受自然界一次又一次惩罚之后,人们应该认真体味施韦泽的观点和思想。
三、 黎族生态智慧对今天的启示
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误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自然的控制,成为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君主。但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给自大的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能再走这条不可持续的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8]
我们应该放弃将自然资源,特别是把土地视为单纯的可开发利用的对象的那种人类的傲慢态度,转变对土地的掠夺式耕作,注重尊重土地自身的涵养过程,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令人欣慰的是人类对此有了基本的理论共识。“绿色经济”“绿色农业”的口号被各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广泛使用,但是在实践层面,进展十分缓慢。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环境污染加剧的势头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海南是否可以在“绿色农业”领域起示范作用?对于海南这样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省份,种植业提倡“轮耕”“休耕”“轮作”式的绿色产业模式很有必要。例如,对于小型农场和一般农户,应当鼓励他们采取多种多样的“轮作”模式,“小地块,多品种”,同一地块每年更换物种。黎族人早就利用这种方式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概率。这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海南省拿出10%的耕地做“一季草一季粮”或“两季草一季粮”的实验,不仅会提高绿色产品的品质,还会大大促进海南畜牧业的发展,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见得比现行的模式差。我们的城市建设也有应该向黎族学习的地方。比如,用树篱取代围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钢筋水泥使用量,最大限度地增加绿色植物,降低大城市的夏季“热岛效应”,美化城市景观;还可以大幅度降低工程造价。正如有学者所见:“生态特区是海南发展战略的最佳定位。”[9]
当然,对黎族生态精神的借鉴,最根本的是要改变我们对自然的掠夺态度。黎族在海南岛繁衍生息了两千多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黎族聚居区水碧山青,生态环境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森林覆盖率在90%以上。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的生态友好型社会,在黎族千百年来即是。这主要得益于黎族广泛的自然崇拜观。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使过去的黎族人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并在生产生活中着眼于自然资源的恢复。这样的生存策略使黎族在近两千多年的海南岛开发过程中,始终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保持在自然界可自我修复的状态之内。
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以往黎族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特征。过去学者一般认为像黎族这样的原始民族之所以与自然保持着和谐共生的关系,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生产力低下,生产工具简陋。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很片面,忽视了对黎族价值体系的考察研究。问题根本原因还在于黎族并不把自然当成要征服的对象,而是崇拜的对象。这种崇拜与梭罗所说“我希望我们的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那种恐惧”[10]是一样的,是对自然界应有的尊重与敬畏。机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许还将套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天下的普遍规律,从而否定像黎族这样的原始民族价值观的历史传承价值。实际情况是,西方资本主义用暴力加文化灌输,瓦解了世界其他民族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这就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的客观的规律,那人类社会的命运就太可悲了。
“人的发展绝不是占有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也越来越和谐。”[11]今天,当我们从全球性的人为环境灾难中猛醒过来时才发现,像黎族这样的自然观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然而,恢复与重建似乎已经太晚,人类的贪欲已经被从魔瓶中释放出来,好像没有任何办法让其再回到瓶子里去。今天,“绿色和平”和各种各样的生态主义主张,正是黎族人千百年来自觉践行的价值观;如果用是否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来衡量生态主义的价值尺度,那么黎族人曾经达到的高度至今无法被超越。遗憾的是,黎族的生态智慧,不仅为后来的汉族人丢弃,也为现在的黎族人自己所遗忘。
[1] 邢关英.黎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22.
[2] [明]顾岕.海槎余录[M].台北:学生书局,1985:383.
[3] 陈小琼.试论黎族对植物资源的利用[J].琼州学院学报,2016(3):25-31.
[4] 文丽敏.“神意型”社会——黎族上古社会形态再探[J].琼州学院学报,2013(3):45-51.
[5]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
[6] 陈泽环,朱林.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161.
[7]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53.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
[9] 宁清同.生态特区是海南发展战略的最佳定位[J].琼州学院学报,2016(4):59-66.
[10] [美]梭罗.瓦尔登湖[M].李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11.
[11] [美]梭罗.梭罗日记[M].朱子仪,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32.
(编校:李一鸣)
Ecological Wisdom of Li Ethnic Minorit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s
WEN Li-min,GONG Yan-f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toward the slash-and-burn method used by the ancient Li ethnic minority people. However, the reality shows that this is just the ecological wisdom created from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Nowadays, when the world is facing the ever-worsening ecological crisis, this ecological wisdom can give deep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to us.
Li Ethnic Minority;ecological wisdom;crop rotation
格式:文丽敏,公衍峰.黎族的生态智慧及其当代启示[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7(3):27-31.
2017-03-21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14-69)
文丽敏(1974-),女,吉林公主岭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影视人类学;公衍峰(1982-),男,山东临沂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C954
A
2096-3122(2017)03-0027-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