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云论书
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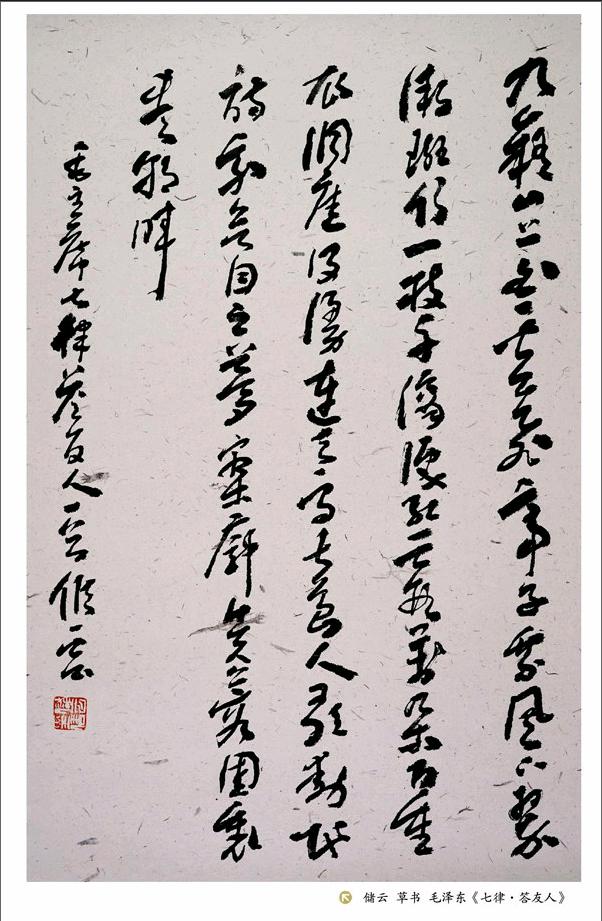
我行草书上手就是《平复帖》,刚开始边都沾不上,临了许多遍之后,手上有了些贯通的感觉,此后学其他章草、行草就不觉得特别难。《平复帖》的字很少,而且也比较简洁。但是它与王字,比如《丧乱》《得示》《初月》以及其他魏晋名家的字是相通的。有了《平复帖》的感觉,学二王就容易多了,因为《平复帖》的塑造性差,而王字的却很强。《平复帖》对我的影响至大至深,我所有作品几乎都有它的味道,有一个阶段,包括参加三、四届全国展的作品,更是直接以章草的面目出现。所以说,学习书法要先扎根于一本帖,将它吃透,决不能东张西望,浅尝辄止,但也不必死守一家。《平复帖》以外,南朝的《瘗鹤铭》我下的功夫也很大,《瘗鹤铭》虽是楷书,但有篆书的用笔和隶书的造型,笔势绵远悠长,艺术性很高,即使是《郑文公》和《二爨》也不能匹敌。和《平复帖》一样,《瘗鹤铭》也只是80多个字,但我反复临写、揣摩,收获很大。像《平复帖》《瘗鹤铭》,我过段时间就要拿出来温习一下,它们是我的根基。通过温习,我可以不断纠正学其他碑帖时带来的一些不能融洽的因素,达到使之混融无迹的目的。
讲到临摹,黄宾虹对我影响很大。在黄宾虹的绘画作品中,他用自己的一套方法,不管线条、意趣、构成,既高级又现代。黄宾虹留下了许多临摹之作,如仿董其昌、邹衣白、恽道生等,但将他们的画放到一起,我发现一笔都不像。但这并不表明临摹没有意义,恰恰是这些原型滋养了黄宾虹。我的临摹也是这样,表面上看似乎在临,其实我是用自己的方法在做,并力图挖掘原作的一些特点。从内在说,完全是我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我从黄老那里得到的启发。我临摹任何一家或是一件作品,只取我需要的东西,比如怀素,他的线条深远度(内质)非常好,苏轼在这一方面不及他,但《黄州寒食诗》中的“锋芒”却十分高级,神态响亮、入味。我学他们,只在乎这些东西。我写字持重,笔不轻易游走,不以外在的气势为得趣,一定要觉得吃上了劲才会行笔,所以相对较慢,不是急风暴雨型的。这样的用笔方法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样写字既能沉稳,又能深入,且不呆板,非常适合我的个性,也符合我的审美观。我不喜欢花哨、轻滑,飘逸的东西我虽然很心仪,但我的秉性办不到,所以只能舍弃。每个人学习书法,都应当学会找准自己的风格定位,这个风格与自己的资质、性格有相当大的关系,勉强不得,否则就会炒杂烩,神情悬隔,徒劳无功。
我研究黄宾虹30年,他的作品既浑厚又华滋。虽然画得很随意,细细体察却相当周密。书法也应该有这样的精密度。呆板的厚度不是厚度,而是迟滞,但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厚度。传说邓石如花几年时间画棋盘、画鸡蛋,所以就写好篆书了。这非常荒唐。厚度不可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所谓厚度,是指一种纵深的东西,线条必须在纸布上给人一种立体的错觉效果。这与笔划的深入浅出有关。许多人写字,只有重轻粗细,而没有深浅(上下)的感觉,因此这还是一个用笔的问题。林散之先生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笔到曲处还求直”,笔曲了还要向前送,必须先还原到直,才能深人纸面,吃到力量。这符合运动学的原理,比如运动员跑外道必须往里侧,打篮球没有人会直挺挺的跑步,必然是有屈体、有下蹲、有伸展。我学过体育,笔的跳跃与走动、点线的结合与人的运动原理是一样的。出手既要有力度又要有准确度,就必须掌握这个规律。另外,不是说用劲了就有力度了、当笔头向下的时候.力量反而要向上提,越是涨墨笔越要向上。纸笔的接触面要小,墨涨出的轨迹才会清楚,才会有神采,有天趣。用力往下按,膨胀出去就是墨猪。书法的章法是不能预先设计的,结字和篇章的形势往往与用笔产生的节奏有关。我觉得自然的书定就是章法,有人擅长引带,我则比较喜欢以字形与墨色的变化来调整行气。
黄宾虹的篆书完全在吴昌硕、齐白石之上,他后期的题画行书更超过了当选的所有的书法家。齐白石的篆书来源太单一,吴昌硕也主要是《石鼓文》。黄宾虹则于三代金石无不肆力。他们的金石无金,黄宾虹却金石俱全:他的篆书渊雅高古,既有金石气,亦饶书卷气。相形之下,吴昌硕老则老矣,内在却很浑浊,有些俗气。徐悲鸿10多岁时随父亲徐达章学书法,我见过徐19岁时父亲去世,他向溧阳亲戚打的一张借条,字已经相当了得,当时是二王的路子。后来他结识康有为,从碑刻化出行书,结字优美,线条凝练,可以称得上无迹可寻,看上溜溜的,但包容量很大。我有一次看江苏美术馆的藏画展,有郭沫若、沈尹默、沙孟海、林散之几位的,其中有一件徐悲鴻的对子,使周围这几位大书家顿时黯然失色。徐悲鸿气度上不及康有为,但内在的凝练、线条的概括力都大大超过,而且康有为失笔多,徐则可称万无一失。康有为的另一位学生刘海粟,气度也很大,还有他题画的行草也是惊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