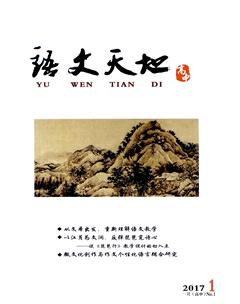从文本出发,重新理解语文教学
袁平梅
人生从来不是孤独的旅行,在意识萌生的刹那,人便开始了与世界、他人的对话。文学作品亦然,作者将自身与世界的对话演化成文,最终将其重新放入世界,以求获得更为长久的生命。文学理论将世界、作者、读者、文本的对话视为文学产生和解读的四要素。在解读端,因读者的参与,文本获得了新的意义。以这样的文学理论为基石,我们不妨重新理解语文教育。
以往我们讨论课堂上师生谁主谁次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纠正原来教育中“一言堂”的现象。但就语言类科目教学的特点而言,“一”和“二”不是关键的问题,“言”才是关键,即谁来说(这即是谁主谁次)、说什么、怎么说。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对话”,而对话的关键不在老师说还是学生说,而在如何有效地发掘文本,以达到让文本自己说的目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一种基于文本解读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师生同是读者。在文本面前,读者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说,教师只需作解读方法的引导,解读的过程则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完成。
从师生共同解读文本的角度出发,语文教学中的对话就主要围绕文本自身的特点展开了。但在此之前,不能忘记,任何文本都离不开语言载体。唯有对语言本身的特性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才有可能进一步解读文本。
从汉语言本身来说,作为仅存的表意文字,汉字的字形便可启发读者,如《种树郭橐驼传》中的“字而幼孩”中的“字”,若按现行的字义理解,根本无法解释;若学生能分析字源,便自然知道这个字有表示房屋的宝盖头和一个“子”字组成,“抚养”的意思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汉语的音律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如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般是直接从叠词的角度進行分析,但若从情感的表达上看,叠词一般是起强调的作用,不能体现出这期间作者情感的变化过程。我们若留意这几个词在音调上是“平仄仄平平仄平”,便可以发现,这恰好符合作者情感的起伏变化。
对汉语特性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之后,我们就可以深入文本本身了。理解文本一般从形式和内容进行分析,但若语文只限于对形式和内容作剖析,毫无疑问,语文课堂就拒绝了与作者的对话,这将导致文本解读最终失去了一个关键的环节。从形式和内容分析,这是为了把握文本写作特色和主旨,但是什么造成了不同的特色和主旨?那是文化、时代背景和作者个性在共同起作用。在以往的语文教学中,时代背景和作者经历会作为解读文本的依据,即所谓的“知人论世”。这种解读的方法固然有其有益的一面,但有“先入为主”之嫌,某种程度上是阅读上的偷懒。最佳的方式应是从文本本身的特点入手,从中看出文化的差异、时代的局限和作者的个性。
我们不妨将《荷塘月色》与《雨巷》进行比较,这两篇文章均写于1927年,时代背景一样,表达的心情也大致相同,均流露出知识分子的迷茫和彷徨。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说基本上把握了文章的内涵,但还不够,因为只看到了文本的共性,而文本背后作者的独特性却被忽略了。为什么表达相似的主题,朱自清选择到荷塘散步,戴望舒却选择了在雨巷彳亍?“荷塘”和“月色”仅是作为一种景物来烘托作者的内心感情吗?在观赏景物之前,作者选择了一条“幽僻”的路,并且用一个“寂寞”来形容,很显然,“寂寞”是一语双关,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写照。那作者的寂寞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文人清高的情怀。
在写完“荷塘月色”之后,作者联想到了古代采莲的习俗,说“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联系到前文“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作者喜爱的热闹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尘世繁华,而是一种文化“风流”;作者喜爱的“群居”也不是没有选择的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说到底,作者喜欢的热闹和群居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一种典型的文人情趣。联系到“荷”在古典文化中的清高意味,我们可以大致揣测作者如古代文人一般坚守清高的情怀。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对蛙声和蝉声“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印证,蛙声和蝉声所代表的尘世噪声显然不是作者喜欢的热闹。面对外部的纷乱,作者选择了“独善其身”,但现实却不断地把他拉回到“兼济天下”:“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雨巷》则不相同,作者在情感上几乎毫无掩饰,用“忧愁、哀怨”等词修饰意象,直接表明这是理想。
从行文上看,《荷塘月色》是节制的,情绪是“淡淡”的,而《雨巷》则是浓烈的,这不能不说跟作者的个性有关。朱自清自视甚高,而戴望舒则忧郁内向,并带着点冲动,这从他三次失败的婚姻中也可以看出。
因此,只有深入了解文本背后的作者,我们才能对文本的差异作出解释,这既是对文本的尊重,也是对作者的尊重。藉此,语文的对话就可以说是非常全面而精准的了。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第三中学(3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