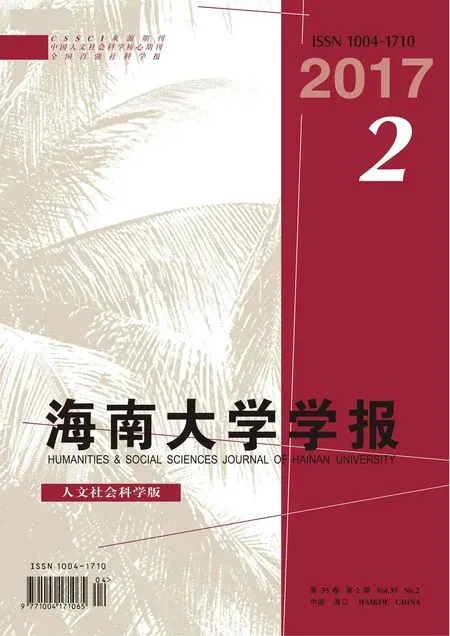超越“经学”“国学”的“古典学”新境
杨天奇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超越“经学”“国学”的“古典学”新境
杨天奇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倡言建立“中西合璧”的“中国古典学”,其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文社科研究者摒弃过多的本土情结和感情色彩,做到学术研究上的价值中立和理性判断,以便更好地到寻找到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的有效途径。“古典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确为我们扬弃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局限、平等对待“经学”和“子学”“中学”和“西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此即不会陷入“中学为体”的拘囿,也不会步“西学为用”的后尘而再遭“牛体马用”之戏谑。如今,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亟需我们以大气谦和的姿态吸收中西文化的优长,尽可能地使华夏文明“走出亚洲”“走向世界”,并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域外文化相互补充、和谐共生。惟其如此,和谐文明才得以构建、和谐世界才得以存焉。
古典学;国学;经学;子学;中西合璧
晚清之际,“西学东渐”之风炽热,张之洞等人曾提出“中学”与“西学”对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体现了文教认识上的中西之争,同时也反映出“中学”与“西学”相互对立却又难以沟通的尴尬境地。如今,强势的西方国家(美国)常常高标其为西方文明传统的担纲者,这意在向人们表明现代国家在政治上的强势应该与该国大学中的古典学强势相同步,即便我们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但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最基要问题,而“我国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垢病,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1]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古典学”的确已迫在眉睫。其实,“古典学”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学术术语,它希冀以全新的视阈探询、复活已逝的历史世界,并以此有效地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缺失与弊端,所以复兴古典并非是对古典学术的全盘接纳,而是通过全新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在古典文明中探询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因此这门学科更多的是一种带有历史性、历时性的体验之学、内省之学和经世之学。发展有本土特色的中西合璧式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文教大业,从而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并立足本土培养出一批‘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1]惟其如此,才能使更多的有志青年成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文明担纲者,这不仅可以让我们作为古老东方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而不致它邦伪纂,也不会使固有传统中绝而为异国接续。
一、古典学溯源及精神实质
有关古典学的定义,在英语著述中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就在维拉莫威兹(Wilamowitz-Mmoellendorff)的德语著作中却有一段比较贴切的描述:“虽然古典学这一头衔不再暗示那种崇高地位,但人们仍旧这样称呼它,可以根据古典学的主旨来定义:从本质上看,从存在的每一个方面看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歌词、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就像每一门知识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或者可以用希腊的方式,用一种完全的哲学方式说—对现存事物并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发点,目标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丽事物的纯洁的、幸福的沉思。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把古典学划分为语言学和文学、考古学、古代史、铭文学、钱币学以及稍后出现的纸草学等等各自独立的学科,这只能证明是人类对自身能力局限性的一种折中办法,但无论如何要注意不要让这种独立的东西窒息了整体意识,即使专家也要注意这一点。”[2]1古典学于西方兴起较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初具规模,尤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曾一举达到鼎盛。西方古典学不仅重视文献、考释、校勘,同时也注重义理、辞章、考据,所以它和中国传统的经学十分相似却又不仅局限于此,是古典语文学、古代史、古代哲学等若干学科的总称。在维拉莫威兹看来,文明是一个统一体,科学方法当然也是浑然一体的,古典学虽然和语言学、文学、考古学有着许多天然的联系,但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诸多独立的学科窒息了文明与文化的整体意识。
其实,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几次比较重要的古典学重建举动,自秦始皇焚书之后,今文经学兴起,但孔子壁经的重见天日,造成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竞争互动,后来郊玄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融合统一,而曹魏正时期“三体石经”的出现和经学玄学化的趋势,也是古今学术整合并发生转变的具体表现。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统一政权的巩固,《经典释文》《五经正义》等官方考订文献的出现不仅表明了政府维护并发扬经典的决心,同时也将古典学术的研究推向了另一个新境,尤其是《十三经注疏》中“义疏”与“正义”之学术方法的成熟,使传统经典再次勃发生机、彪炳千古。可见,上述做法无疑都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和文化思潮所为。所以说,古典学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其当时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深刻反映,今天我们重提古典学建制,恰恰也是对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区文明与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所做出的及时回应。
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 1914—2004年)曾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3]14布洛克的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西方固有的人文传统,其实这也是古典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便人文传统在中世纪曾受基督教教会的“非难”,但在16世纪之后,随着商品工业经济的发展、人本主义的倡导又加强了原有的人文主义传统,以致笛卡尔用“我思”否定了“我在”,接着康德、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福柯都试图用“反理性”的方式来重新评价原有的道德与价值体系,这不得不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次进阶。笔者认为:“人文学科”作为“the humanities”更应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传统,特别是Liberal Education(自由教育)——其目的是希望人能够从世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来抵制职业化、利益化对人类灵魂的侵蚀。其实,Liberal Education的自由理念与古希腊时期的“七艺”教育传统是分不开的。“七艺”源于公元前400前后的“智者运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等智者们首先提出了涵盖辩证法、修辞学和文法学习的“三艺”以满足民众自由辩论、演说的需要。之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人必须学习音乐、几何、天文、算数,如此才能培养和谐发展的完美人格,“四艺”之说便由此开端,并与“三艺”合成为“七艺”。在我国周朝时期,官学虽以“六艺”为主,但“六艺”与“七艺”确有很多相同之处,尤其作为“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也十分注重对君子品格的全面培养。总之,无论是西方的“七艺”还是中国的“六艺”,都将音乐、几何、体育分别视为陶冶情操、锻炼思维、增强体魄的必要手段,但又不把这些当做是人生的最终目的。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Eleutherion epistemon”的论说,其实它是现代博雅教育即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产生的母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liberal education”最终将人分为两种:“自由人”的和“非自由人”。自由人虽然学习技艺,但却出于自身的需求或以培养德性为目的,而非自由人则以领取酬金为目的却也败坏了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应该学习种种必需的和实用的事务,但不是所有实用的事务都是儿童所需要学的。有实用价值的事务很明显可以分为自由人的事务和非自由人的事务两类。任何工作、技术和学识如果导致自由人的身体和思想不适合于德性的运用和实行,就应认为与工匠的营生是同类事物。那种人们称之为工匠的贱业的种种技艺都会败坏公民的身体,领取酬金的活计会使公民劳瘁,而且还会贬抑其思想。”[3]153总之,“城邦应当进行一种教育: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4]154当前在欧美国家,像哈佛、斯坦福这些世界一流大学都在沿用古典学的办学理念。这些年来,随着国内“通识教育”“人文教育”的兴起,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下设的古典学专业、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清华大学新雅学院已相继开办,同时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1]。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为例,开设的毕业学位和专业方向包括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法学,切实贯彻多元化个性化发展的本科培养目标。不仅如此,学生攻读的学科领域分布也相当广泛,有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这些课程皆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必须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同时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要言之,古典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智慧与修养,进而塑造一批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而非不学无术的亿万土豪。
二、传统经学复兴是否可能?
1923年,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曾提到过“古典考释学”的概念,但这大多是受了西方“古典学”其中的文献学、语言考释传统之影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西方古典学的精神实质。很多学者竟以此为由,将古典学重视语言分析的传统与中国“小学”乃至经学划等号,这完全是没有认识到古典学的生命意识和时代担当的急躁表现。实际上,“经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学”,所以复兴“经学”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古典学术以及文化。当前,仍有不少人试图通过复兴古典来复兴经学,这种努力是否能够达到理想的目标,我们有必要从近百年的“经学复兴之路”中去探询。
近代道光以降,国势每况愈下,百弊丛生,而作为官方主流思想的儒学乃至经学逐渐表现得萎靡不振,终究走向了衰落。通常认为,儒学的衰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风俗的败坏、人心道德的沦亡。据此,维新派代表康南海于1895年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名举人于北京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奏陈此番实情:“然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更宜讲求挽救之方。盖风俗弊坏,由于无教。士人不励廉耻,而欺诈巧滑之风成。”[3]43在这些举人的眼里,风俗弊坏的首要原因是因为传统的儒学思想没有得到充分贯彻。鉴于此,康有为继续讲到:“而‘六经’为有孔子为经世之学,鲜有负荷宣扬,于是外夷邪教,得起而煽惑吾民。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吾每县仅有孔子一庙,岂不可痛哉!”[6]43在康有为看来,儒学之所以衰败,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经典没有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为扩大儒学的影响力,康有为建议政府应该派遣优秀的儒生到海外去传播孔子之道,这样不仅可以“察夷情”“扬国声”,甚至还能“以夏变夷”。鉴于此,康有为还著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来为其变法乃至经学的转型与复兴寻找理论依据,但这种做法很快便遭到湖南保守派曾廉的指斥:“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姑平白诬圣造此为名,其处心积虑,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以欲也。康有为之书,亦咸同后经生著作之体例,前列经史子旧说,而后附以己意。盖浅陋迂谬之经生,而出之以诡诞,加之以悖逆,浸假而大其权位,则邪说狂煽,必率天下而为无父无君之行,臣不知其置于皇上于何地也?”[3]492曾廉说康有为“参杂邪说”,的确触击到了问题的要害,不仅如此,梁启超也说恩师康有为“杂引谶纬之言以实之”[3]65。论及“谶纬”“邪说”之言,不得不让我们回顾一下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盛行的公羊学系统,这当然也就触碰到了孔子神圣化、儒学宗教化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汉宣帝时期始立《觳梁》博士,“觳梁学”与“公羊学”开始并立为官学,“《公羊》善于谶,《觳梁》善于经”(郑玄《六艺论》)西汉晚期,谶纬之学风行,儒学遂即被抹上一层神秘色彩。数千年来,很多人会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这其实和西汉末年儒学的发展有很大关联。实际上,康有为并没有认识到,儒学之所以衰败,完全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儒教教会,而全赖国家积贫积弱所致,故空言“兴教”或是杂引谶纬之言无异于效颦学步之下策,这不但有妨外交,还有妨思想进步。后来梁启超对此亦深有省悟:“但使政事修明,国能自立,则学格兰斯顿之予爱兰教会以平权可也,学俾斯麦、嘉富尔教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权在我,谁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说者,吾见其进退无据也。”[3]77-86最终,康有为也就沦为了梁启超所言的“不知宗教之界说”的典型,其对经学的神化改造也以失败告终。但有一点不容否认的是,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同时,也借鉴了风靡一时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并在公羊学“三世”《礼运》“大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进化史观的“三世说”,这不能不说是经学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但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论,康有为等人的努力“是经学时代结束前壮观的一幕,夕照辉煌,晚霞满天,预示着新世纪行将到来”[3]3,故晚清之际的经学复兴看似满天辉煌,实为夕阳残照,终不过是强弩之末。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及至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又会同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光绪三十年颁布《 奏定学堂章程》,是为“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主张学习西方之算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农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贸易学等各个西方先进科学,但依旧重视对传统经学的学习,并单独开设经学一科,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共11 门。洋务派始终认为,西方科学固然重要,但传统的儒家文化负有“慎防流弊”和“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3]289的功效,所以在张之洞等人看来“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瀹(渗透)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1]289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教育不至于舍本而逐末而导致纲纪废弛、道德沦亡。尤其在清朝诸多大臣眼中,西学虽有着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的长处,但儒家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的根袛依旧占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中华所以立教, 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 周公孔子之学术, 今宗旨则不悖经书, 学业则兼通文武。”[11]16可见“不悖经书”是中体西用的最高宗旨,故习经之制在士大夫眼里是不能废黜的。如今我们也时常提到“中体西用”,但它的本质正如上所述,对西学的界定往往局限于西方技艺,在其他方面最多也止于学习西方的商务知识、国际公法,而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哲学理念却持否定之态度:“不可讲泰西哲学……中国圣贤经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3]1488(《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在张之洞看来,中国学生无需学习西方哲学乃至思想,学之则有大患,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洋务派中的保守文人对西方思想的恐惧心理。然而,人类文化原本就有其一体性和相通性,并不能对其进行人为地割裂与分离,张之洞之所以排斥西方哲学,实际上和他并不真正了解西方哲学有很大关系,所以其本人后来也遭到了严复“牛体马用”的戏谑。
不可否认,张之洞等人提倡的“不悖经书”之原则,仍旧没有跳出“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藩篱。传统经学,特别是政治化、章句化乃至神学化的经典解读无疑会严重束缚读书人的思考空间,长此以往,“我”始终不能跳出“六经”,只能在现有的“经”中寻章摘句,士人的思想最终也就失去了其独立的价值而被淹没在繁琐的“注”中。以考据为能事的乾嘉学派不但断送了原有的理学道统,而且与整个现实社会悬隔万里,终究悖离了孔孟之学的本意。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乾嘉学派在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层面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为何只是在最后发展成了一种“学派”而非“思潮”,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对此,侯外庐曾指出:“两汉之学,其弊也‘拘’;魏晋至唐及宋初,其弊也‘杂’;宋庆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党’;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琐’。”*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3页。其实,侯外庐的总结源于《四库总目提要》:“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训诂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陆,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共弊也悍。学脉旁分,攀援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徵实不诬,及其弊也琐。案二千年经学升降得失,《提要》以数十言包括无遗,又各以一字断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以上六字断语虽不皆是准确的,但对清代汉学之“琐”的概括,则是十分恰当的。概言之,自古至今的经学研究往往蔽于词而不知人,蔽于古而不知世。故辛亥以后,国人摒弃了原有的经学传统,开始试图以西方学术的方法来改良固有的经典和文化,“整理国故运动”等方式都是希望以西方学术的研究范式来发扬本土的精粹,这些做法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过分强调西方学术的逻辑演证,完全忽视了儒学本身所蕴含的义理和精髓。
而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早在上个世纪就意识到了西方文明与西方学术的种种弊端,希望以“四书”等儒家经典为基础、以宋明理学为核心来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及其价值,并以期实现传统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终极关切。其实,复兴“儒学”这一举动,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本土文化情结”和浓厚的民族感情色彩,正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中所论:“我们首先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肯定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为忘了这些,便不能把此过去之历史文化,当做一客观的人类之精神生命之表现。遂在研究时,没有同情,没有敬意,亦不期望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能继续发展下去;更不会想到: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此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继续发展下去,因而对之亦发生一些同情和敬意。”[3]8对此,景海峰先生也曾分析到:“当代新儒家有着强烈的续统意识,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被他们的弟子称为‘现代三圣’,便是儒家道统观念的再现,这种自诩为承续慧命的道统观和他们自视甚高而又常怀悲苦的矛盾心境是极为吻合的,徐复观提出的‘忧患意识’概念,既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体认,也是他们本身掉影孤行的最好写照。”[14]2新儒家知识分子们虽有着强烈的“道统意识”,却又“常怀悲苦”“掉影孤行”,造成这种矛盾的缘由并不是因为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愿心是荒唐的,而是“道统”本身就强烈制约着“知性主体”,无法使其确立学术的独立性。
当然,除了考量“续统意识”的民族情感外,我们还要考虑是否有足够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环境来复兴儒学乃至经学。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家约瑟夫·列文森曾在他的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明确指出:“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里已经成为满足情绪需要而未必有实用价值的古董,已经被博物馆化了……这些东西没有很大的生命力,在社会没有起积极的作用。这就叫博物馆化。”[3]504在列文森眼中,儒学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因为儒学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君君臣臣式政治基础,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早已失去其存在的依据。对此,范文澜先生认为既然封建统治已经不复存在,所以经也不该被视为“神圣”的事物,“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宋学系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因此新汉学系堆积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的价值存在,谁说应该丢到茅厕坑里呢?”[3]261在范文澜先生看来,完全可以将“经学”视为古代史、古代哲学史的原始资料,而不该将其视为“权威”。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复兴儒学乃至经学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保证,而这种制度应该是全方位的,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是经济、法律等各个层面的制度。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彻底坍塌,使得固有的传统经学开始瓦解,所以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复兴,不得不关注现有的经济形势及其政治制度,这确实是一个极为复杂、困难的课题,需要我们权衡利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扬弃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局限
中国学术自古就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经、史、子、集皆为治学之圭臬,皆不可偏废,但“经”在古代各家学派都被视为其思想的源头和根据。先秦墨家、兵家、农家等各家虽皆有经典流于后世,但因没有完整、博大而精深的经学体系,故未能成为引导后世文化的主流。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诸子不仅皆出于“王官学”,而且亦有“经传”,“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3]94不仅如此,就连记录日常生活的著作也被称为“经”,“他若陆氏《茶经》,张氏《棋经》,酒则有《甘露经》,货则有《相贝经》,是乃以文为谐戏,本无当於著录之指。譬犹毛颖可以为传,蟹之可以为志,琴之可以为史,荔枝牡丹之可以为谱耳。此皆若有若无,不足议也。”[17]103然在传统士大夫眼中,上述著作虽皆可称“经”,但都为“异教之经”,大多是聊以自娱之作,只能谐戏置之。同样是“经”,为什么要将儒家之“经”视为治学和治国的圭臬,而要将诸子之经乃至“茶经”“棋经”等视为末流呢?其实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得从“经”的源头谈起。“经”,古字为“巠”,《说文解字·糸部》:“经,织也,从糸巠声”,最初是指织布时用梭穿织的竖纱即纵线,这是它的本意,后来被引申为书籍,“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3]54在章太炎看来,古书最早皆由丝线穿联竹简编成,所以古时群书都可称为“经”,由此可见“经”在起初并不具有权威性。要说“经”转变成为具有统治中国思想地位的至圣之书,完全在于孔子的功劳,但这里的“经”已不再是“群书”,而是具有特定范围的“六经”了。通常认为“六经”是儒家一派的经典,其实不然,在先秦时期,“六经”也并不是儒家的“专利”,有述为证: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庄子·天运》
老子认为六经是先王留下的遗迹,但不是先王遗迹的本原。所谓“迹”,并不能达于“道”,只是语言存在的形式,“迹”仅仅是一种“象”,所以要想“迹”发挥其作用,首先必须万物的自然变化相识为友。如何赋予“六经”新的生命力,孔子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的确莫衷一是,按司马迁的看法,孔子删定了诗,编订了《礼》《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以缮《易》,“序《书》传”并编次其事。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六经”已经出现,孔子本人不过是为了更好得使“迹”达于道,故才重新整理六经。但孔子编订“六经”亦有准绳,绝非随意使然,概言之有三个原则,第一是尽量保持原来文辞,即“述而不作”;第二是“攻乎异端”,摒弃一切非议中庸之论;第三是“不语怪、力、乱、神”,删除芜杂怪诞之章节*有关孔子删定“六经”的原则,具体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卷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70页。。孔子整理“六经”的确功不可没,后世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当然这里的“作”应当按编订解),从战国至晚清数千年内,“六经”一直被视为治国的圣典,此后的“七经”“九经”乃至“十三经”虽有所增益,但都未能摆脱“六经”的影响与束缚。然而,儒家“经学”体系的彻底成熟不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汉初曾设儒经博士,始与诸子之学并立。此后,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通过独尊儒术来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于是不久便出现了“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的局面。
通过以上梳理,人们不难发现,经学的形成有一个长时期的积累过程,而非一时兴起、“神化”而成。因此,建立“中国古典学”,必须在自觉继承“乾嘉学统”和“三期儒学”的基础上,“扬弃”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局限*准确地说“扬弃”是一个哲学术语,是德语“aufheben”的意译。黑格尔、康德、费希特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都常常提到扬弃一词。对旧事物的发扬、保留和继承,是一个“扬”的过程,它具有连续性;而对旧事物的抛弃、否定是一个“弃”的过程,具有非连续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小逻辑》等著作中同样认为“扬弃”就是一个从意识到自我意识再到绝对精神的环节,这个环节中即肯定又抛弃否定,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阶段对于前一阶段来说都是一种否定,但又不是单纯的否定或完全抛弃,而是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从而使发展过程体现出对旧质既有抛弃又有保存的性质。,以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这是因为,经学乃至儒家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华夏先民们在没有铁质农具从而私有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政权。尽管夏朝废除了早期氏族社会以推举、禅让来延续权力的民主制度,形成了以血缘因袭王位的世袭制度,但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尚不稳固,其血缘关系也很难渗透到十一支拟姓氏族以外的部分群体。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充分吸取夏、商两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使王室的血缘关系渗透到整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再通过‘制礼作乐’来维护和巩固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亲子血缘关系出发,以‘爱有差等’来论证‘礼有别异’的儒学诞生了。”[3]可见,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也不仅仅是靠汉代儒生援引谶纬之说神化而成的,它的成熟完全得益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如果说,“孔子的成功有赖于周公的铺垫,那么周公的成功则根植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正是由于早熟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完好地保存了早期国人的家族血缘关系,才使得儒学将家族伦理社会化的理论建构成为可能。”[22]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并未将自己的学说付诸于政局混乱的春秋末期,将儒学发展为“官学”的功绩却应归功于董仲舒。汉代政治的大一统急需依赖一种牢固的思想树立威信,而儒学本身具备的思想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或许,汉武帝对儒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出于政治上的需求,不得不在审时度势的情况下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了构建政治与精神层面的话语霸权,“经儒”的形成势必要经历一个政治化、神学化的过程,随之兴起的便是河图、洛书等谶纬之说,于是,传统的儒家典籍成了名副其实的“经”,其不可撼动的权威性只能让学习者在“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而考其分立博士,则有不可解者”[3]77的金科玉律下进行。自此以后,“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而又需为上所定之儒学。于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春秋以后,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3]8故自董仲舒始,“经学时代”开启而“子学时代”终结,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局面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上不复存在,上至士大夫下至黎民百姓,其一言一行都在“经”的框架内,“好像是两腿有病的人用拐杖支着才能行走,离了拐杖,他的腿就不起作用。”[20]187尤其在经学家们看来,“离经”的结果必然是“叛道”,所以无论是古文经学派还是今文经学派,他们都是怀揣着“继承孔孟”“托古改制”的心理进行经典阐释,留给后世的大多是以“传”“注”“疏”“笺”“正义”“训纂”“训诂”“解诂”为主要形式的解读,这不仅没有跳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藩篱,而且将儒生对经典的理解变得繁复化,以致误解跌出,难见真义。
然而,西方古典学对待其经典采用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圣经学”(Sakralsphaere)即对圣经的诠释学,在当时就已凸显了很强的“人文精神”。从基督教产生至中世纪时期,《圣经》一直被神学家们视为至圣经典,虽然也有不少与之相关的注释、翻译、考释、阐证等工作,但大多是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进行的,终究未能摆脱其“经学传统”的条条框框。直至16世纪前后,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的勃兴、自然经济的解体,不但导致了基督教经学传统的衰败,还促成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圣经学”兴起。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已完全不能与之适应,而城市新型资产阶级与君主的“联盟”势必需要一种全新的政体为之服务,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影响下,资产阶级于是提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试图将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也在无形中促进了人文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圣经学”不仅反对教会对《圣经》的垄断,而且还提倡人人皆有学习《圣经》的权利,主张将《圣经》从神坛散播到民间。特别是以瓦拉(Vara)为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主张学习拉丁语以便从原版《圣经》中寻找信仰的真谛,而非埋首于经院学家们繁琐的附会阐释之中,为此他还在1471年出版了《拉丁语的优雅》一书。有学者指出,“人文主义者中与基督教传统分道扬镳的最著名人物是洛伦佐·瓦拉。”[3]306最值得一提的是瓦拉对《君士坦丁赠与》一文的辩伪,他通过逐字校对在这篇文章中找出了4世纪不可能出现的文字,并运用“历史学与颂词不一致”的史学观点证明了《君士坦丁赠与》恰恰是公元8世纪的一篇伪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启蒙时代怀疑主义学术精神的盛行。 此后,有不少学者为“圣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很大努力,但贡献尤为突出的当属伊拉斯谟(Erasmus),他被后世称为“圣经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认为经院学家对《圣经》教条化、神秘化的行径无疑遮蔽了经典中原有的真谛和内涵,所以他极力强调原始基督教的道德精神,并且始终认为基督教授予人类的不外乎虔诚、仁爱、真善、质朴、圣洁等品质,而“博爱”是整个基督教义的核心,所以教会的繁文缛节不但遮蔽了最原始的宗教精神,而且让众人陷入了世俗的泥淖。因此,在伊拉斯谟看来,必须从“人”的内心出发,虔诚接受基督的洗礼,而非依赖那些神乎其神的教会礼仪。可以说,“圣经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诠释学的成熟与发展,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认为文本的视阈理应和读者的视阈达到一种和谐,如此理解才算完成。后来,伽达默尔在此基础上完善了哲学诠释学,并试图从理解、解释、应用、实践四个层面来提升读者对于文本的理解,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传承下来的文本,而且文本是属于整个传统的一部分”[3]403。鉴于此,伽达默尔主张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旧有的文本,“我们只是要求对他人的和本文的见解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这种开放性总是包含着我们要把他人的见解放入与我们自己的整个见解的关系中,或者把我们自己的见解放入他人整个见解的关系中。”[22]366这种开放态度要求读者必须承认、接纳自己曾经某些反对的东西,“把认识者束缚于自己当前视域的特点以及认识者同认识对象之间的时间间隔,作为一切创造性理解的基础,而不是作为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和障碍来认识的。我们的偏见并非使我们与对象相隔,而是使对象向我们开放,它是社会认识得以进行的积极条件。”[3]4在伽达默尔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使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中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可见,从施莱尔马赫开始,经由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再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其内核都是为了突出人的“主观精神”,他们认为“理解”就是人类主观精神的客观化产物,需要我们接纳文本之外的广阔的意义世界,这不仅可以促进神圣文本向世俗文本的转换,而且能够更好地释放读者的主体精神。在诠释学派学者们眼中,理解是一个历史性的“延展”过程,其自身就富含着创造性,向传统经典的“回归”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接纳,而要通过“延展”挖掘其现实意义。
所以对待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也需要一种“延展”。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谱碟学、生态学、两性文化、符号学、系统论、文化冲突、结构主义等多种方法来重新解读古典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我们需要明白,能够自如运用多元的科学方法研究古典并解决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才是古典研究的终极目的,正如陈炎先生曾说:“我感兴趣的儒家,不是经学意义上的儒家,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儒家;不是书本上的儒家,而是生活中的儒家;不是永垂不朽的儒家,而是不断更新的儒家;不是闭关锁国的儒家,而是面向世界的儒家。”[3]291可见,如何将古典上升为一种实践之学、体验之学、经世之学,实现传统对人类生命的最终关切,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经学与子学的轩轾与合流
上古时期,王官文化兴起,至商周之际渐由“神”转向“人”,西周巫官衰而史官兴, 王官文化逐渐摆脱神学束缚, 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然而到了东周“礼坏乐崩”,王官文化不再拘囿于庙堂之上,开始下播民间,钱穆先生认为六艺为“王官学”,这恰与“轴心时代”相符。“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先秦诸子其实是一个系统,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论六家要旨》中讲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
所以在先秦诸子系统中,任何一家、一子都不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和能力:“从逻辑的角度上讲,它既是一种思想的发端、一种思想的终结,又是由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过渡的中介环节;而从功能的角度上看,以孔子为代表的伦理哲学倾向同以老子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倾向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补充关系,以墨子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倾向同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哲学倾向之间形成了相反相成的制约关系。”[24]134晚明时期,李贽就曾清醒地认识到理学家将经学权威化的弊端,故希望能够将经学与子学平等视之来抵制理学对人性的扼杀;傅山也试图通过训诂、比较等方法来激活子学,并提出“经子平等”的主张*傅山认为子在经先,“经子之争亦未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并指出“子书不无奇鸷可喜,但五六种以上,径欲重复明志,见道取节而已。”子不仅先于经,而且还优于经。参见傅山《霜红龛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5页。;近代受西方思潮的碰撞,有不少学者同样做出了打破经学权威的努力,对此章太炎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论”,意在说明经和子出于同一母体;马一浮、熊十力也坚持认为“经子一体”之说并非谬论。其实,所谓的“子”,最初并不是知识分类的名称,它不仅是指古代的一种官爵,也指先秦各派别的思想。“子”彻底演变为一种知识类别是在汉代经学成熟之际,刘歆撰《七略》,以“子”来代称先秦至西汉九流十家的思想著作,并分门别类,子部遂始建。直至清代《四库全书》编纂之时依旧沿袭了汉代这种对经、子的划分方式,“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其中或佚不传,或传而后莫为继,或古无其目而今增,古各为类而今合,大都篇帙繁富,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3]汉代刘歆虽对经、子作了严格意义上的划分,却也曾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的主张*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於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后班固对此加以发挥,以致此说几成定论。近代胡适曾撰《论九流出于王官之谬说》即《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试图通过逻辑演证的方法来否认刘歆、班固等人对于“九流”出于一派的说法,并以此反驳盛名一时的章太炎。表面看来,胡适与章氏的做法完全相反,但其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打破旧有经、子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将诸子之学看成是真正的救世哲学。由此看来,胡适的反驳其实和诸子“出于王官”、不得偏废的倡言者有着同样的鹄的。为突出经、子的平等关系,冯友兰先生则干脆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上篇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由此方面言之则在中国哲学史中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皆中古哲学而近古哲学则尚甫在萌芽也。”[20]8毋庸置疑,董仲舒与康有为都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但在冯友兰看来,传统经学以今文经学“始”亦以今文经学“终”,尤其是康有为以西学付会经学、“旧瓶装新酒”的做法终究会使“至多至新之酒”撑破“旧瓶”。所以,要想促使中国学术的进步,必须跳出经学的框架,打破“酒瓶”,索性用“新瓶”装“新酒”。而古典学作为一门囊括所有古典优秀学术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打消传统文化研究者对于所谓经学、儒学乃至国学研究的固执己见,通过构建经、子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尽可能地使思想文化回到子学争鸣时期的繁荣局面。特别是庄子“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荀子“化性起伪”、墨家“兼爱尚贤”、法家的“综合名实”、阴阳家“辩证析理”,名家的“其正名实”等论说,无不彰显了诸子与生俱来的自由性、独创性、批判性等优秀品质。即便诸子经典也常常引用《诗》《书》等经学典籍中的章句,但其目的皆是为了自立新说,而非依傍旧说、循规蹈矩。
如今,学界对于“经”和“子”的论争,实际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心态,特别是原教旨儒家,始终坚持“经”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地位,他们的“拥护”不但没有引起儒家反对者的同情之心,相反更加激化了“反儒者”的仇视情绪。也许,我们不能否认原教旨儒家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全盘肯定、彻底极端的做法不免让反儒者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迂腐可笑。与此不同的是,“子学”的拥护者即“新子学”派则希望能够在平等自由的氛围中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不仅仅拘囿于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与前两派皆有所不同,“儒学好感者”则认为儒学在今天的主流文化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但又必须通过“子学”乃至“西学”来完善它,这与原教旨儒家的极端态度明显是不同的,但与“新子学”派的主张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无论是“新子学派”还是“儒学好感者”都希望能够运用多元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儒家乃至传统文化,这不仅可以做到“方法多元”,而且很容易保持“价值中立”。在“新子学派”和“儒学好感者”看来经学与子学乃至和西学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并没有孰高孰低。而“古典学”的确为我们扬弃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局限、平等对待“经学”和“子学”“中学”和“西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如此即不会陷入“中学为体”的拘囿,也不会步“西学为用”的后尘而再遭“牛体马用”的戏谑了。
五、超越国别与“中西合璧”
“古典的”的英文单词为“classical”,具有传统的、经典的、历史悠久的、 第一流的等涵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classical”这个单词的词根恰恰又是我们所熟悉的英文词“class”,最初有等级的、阶级的等义,由此可以推断“古典学classics”最早应当是一门划分“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带有阶级标签的学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等级”的差别,人们最初依靠“五行”中的“礼”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礼”作为六艺之一,既是人们所遵守的日常人伦规范,也是判断一个人受教育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不难看出西方的Classics和中国先秦时期的礼乐传统具有很大的相通性。鉴于此,不少人主张可将注重整体研究的“国学”与“古典学”划等号,这个看法是否恰当,尚有待商榷。其实,“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据《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3]94可见,在古代,“国学”仅指传授知识的教育机构,且专注于王宫小学、乐舞之教。《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3]73古时的教学,闾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京城则有大学,在这里“国学”则发展成了有别于乡学、私塾教育的“大学”,是国家的一级学校,相当于汉代的“太学”。贞元年间,唐宗室成员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并增其旧址、建学授徒,号称“庐山国学”。宋仁宗五年,“庐山国学”又改称“白鹿洞之书堂”,实为藏书讲学之所,亦即我们常言的“书院”,此后有关“国学”的概念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层意思。直到晚清转型之际,受西方思潮的猛烈碰撞,最初是由日本发出了构建“支那学”的主张。1902年,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倡议创办《国学报》以发扬“国粹”,“国学史”的创作也很快被提上了日程,但由于各种阻力终未付诸于实践。直至1904年,邓实于上海《政艺通报》发表《国学保存论》,旨在说明建立“国学”的重要性,并于次年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国学”一词遂在学界站稳了脚跟,影响力也愈来愈大,但由此而引发的争议也日益增多,特别是“国学”与“精粹”“国粹”乃至“国故”的区别就很难判分。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切皆“粹”,“国学”在范围上虽占有足够的优势,但其糟粕之处往往为许多新型知识分子所诟病,以致五四运时期的“旧派”与“新派”都偏向使用“国故”一词。当时也有很多人认为“国学”作为“一国固有之学”可与“外国学”相对,故可称之为“中国学”。
在现代人眼中,“国学”不仅包括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还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学等,甚至书法、养生、绘画、戏剧都可纳入国学的范畴,并以此提出了构建“大国学”的设想。对此,不少人竟戏谑到“国学像个筐,古代的东西都往里装”。其实,这一切都是对“国学”界定不当而造成的。胡适曾说:“‘国学’在我们的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包含着‘国粹’; 但又包含‘国渣’。”[3]6所以,当我们钟情于“国粹”的同时,往往又无视“国渣”的存在,以致在“国学热”的大浪潮中“国渣”也沉渣泛起、滥竽充数、忝列其中,使不少民众对“国学”产生了怀疑甚至抵触之情绪。不难看出,传统文化再次面临重新命名的问题且至关重要、不容小觑。要而言之,无论是“国学”“国粹”“中国学”还是日本所谓“支那学”、西方之“汉学”,这一系列命名都将传统文化视为“一国固有之学”,受地域限制比较明显。“如果以‘古典学’来命名中国的传统学术,不仅可避免名称上沟通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由此我们得以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所以,古典学作为“Clasical Studies”,无论在名称上、还是在学术渊源上都比“国学”“国故”“汉学”等诸多称谓具有先天优势。如今我们倡言复兴“古典”,这既指中国古典也指西方古典。上个世纪前半叶,德国人将复兴古典等同于狭义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文化复兴,酿成了世界性灾难,故今日中国亦须防范此危险。
实际上,只要我们一提到“国”字,都难免会渗入不少“感情因素”,诸如国旗、国家、国歌乃至国粹、国学,任何名词只要被冠以“国”字,皆会激起不少人的爱国情愫。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爱国热情,但在学术研究之中如果夹杂过多的感情因素就一定会导致科学的“非理性”,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皮锡瑞曾在《经学历史》中指出:“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 ,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这种注重实证的治学方法是乾嘉学派的主要特征,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得“乾嘉学派”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后来章炳麟则认为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共有六个特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佐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3]1119特别是其中的“断感情”一条,是保障学术研究上科学理性的重要前提,也正是有了“断感情”一条,乾嘉学派才得以保持“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汰华辞”的朴学传统。熟读《纯粹理性批判》的牟宗三本人也明白:“观解理性之活动及成果都是非道德的(不是反道德,亦不是超道德)。因此,遂有‘道德中立’和‘科学之独立性’。”[3]8可见,“科学之独立性”必须以“道德中立”为前提的,否则便会陷入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替代“国学”,不仅可以避免这种狭隘的民族情绪,还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多个瓶颈。由此不难看出,“古典学”的首要目的就是放弃学术上的“一元价值”,进而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做到科学研究上的理性思考与方法多元,这样做的好处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从中西之争回到古今之争,以历史的眼光来判分古今学术上的优点与不足,从而使古典文明与文化更好得发挥其“以察时变、化成天下”的“变”与“化”之功效;其次,“中国古典学”不仅包容了汉学、国学、中国学,同时也包括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这不但适应了当前文化共享的时代要求,也符合全球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潮流;第三,西方很多名牌大学都设有自己的古典学系,就连马克思本人当年也修古典学,而在中国从上古至秦汉,再从秦汉到清末,古典学的传统也一直在延续,故建立古典学不仅可以消弭近代以来文史哲的学科划分,还可以使传统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传续而不致伪纂。
概而言之,倡言建立中西合璧的“中国古典学”,其一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突破经学固有的权威,超越经学、国学原有的束缚与限制,从而平等地对待“经学”与“子学”,再现诸子争鸣时期的思想繁荣局面;其二也是为了让我们以全新的视阈来看待中西、古今学术上的优缺点,平等地对待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寻求建立和谐世界具有普世价值的新型文明。当然,这一切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扬弃其历史性的糟粕,弘扬其民族性的活力,并寻找到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的有效途径。“尤其对待中华文明产生的渊源不仅要从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时间”即“量”的角度上去看,而且要从“义理”这一“质”的角度上判定中华文化产生的原因,从而通过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判定儒家文化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找到传统文化的富矿。”[24]1放眼全球,世界范围内的资源竞争、资本竞争、军事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制度竞争乃至文化竞争正在不断加剧,而在种种竞争中文化竞争显得越来越严重。如此看来,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论调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哗众取宠。毋庸置疑,西方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也在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西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乃至“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集团的兴起,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文明冲突的关注。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避免出现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结盟而对抗基督教文明的局面,又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更好地继承与创新,是古典学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当今社会,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业资本、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等领域都严重缺失群体意识、社群意识和人文主义关怀。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女权主义、宗教冲突等问题下,西方的自由、人权和个人主的论调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同情、正义、礼教、责任、社群等观点恰好能够为我们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化解诸方矛盾提供很多智力上的支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经济的相继崛起,人们开始意识到:“以世俗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文明并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样,是与现代社会无法兼容的一具僵尸,而是潜藏着人们尚未认识的巨大活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国学研究热潮逐渐升温,儒家文明所包含的内在价值正在被学术界重新估量和评判。进而,儒家文明的现代转型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32]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损益”,如何创新出兼得“伦理”“民主”“理性”“智慧”的新文化形态,是我们当前应尽快解决的问题。然而,当前许多传统文化研究在选题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无法将传统的学术研究与现代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在视野方面,缺乏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不能在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中来研究“中学”;尤其在传统文化研究手段上,不少学者仍然习惯于书斋式的考据、训诂等研究方法,既不会做社会学的统计分析,也不愿意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以,要使学术研究实现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就必须联合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协作攻关,并搭建‘文化基因’、‘文化实力’、‘文化转型’、‘文化安全’这四个研究平台。”[3]而建立中西合璧的“中国古典学”正是为搭建这四个平台所做的一次努力和尝试,惟其如此,华夏文明才能更好的“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从而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教文化等域外文化相互补充、和谐共生,也只有这样,和谐文明才得以构建、和谐世界才得以存焉。
[1] 刘小枫,甘阳.古典西学在中国[J].开放时代,2009(1):4-31.
[2] 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M].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姚仁权,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5] 柯小刚.书院作为现代社会通识教育的形式[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6(1):9-10.
[6]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卷[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7.
[7] 翦伯赞.戊戌变法:第2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9] 梁启超.梁启超文选·保教非所以尊孔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10] 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增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2] 范书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3] 封祖盛.当代新儒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9.
[14] 郭齐勇.杜维明文集:第2 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15]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6]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1994.
[17] 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8] 陈炎.儒家文化的历史生成[J].天津社会科学,2015(7):108-119.
[19]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21]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306.
[22]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
[23]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4] 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5] 中华书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6] 吕友仁.周礼译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27] 礼记.叶绍钧选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28] 克川.胡适谈国学[M].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29]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0]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香港:学生书局,1978.
[31] 陈炎.超越国学研究的古典境界[J].中国文化研究,1998(1):17-24:.
[32] 陈炎.问题与思路[N].光明日报,2015-04-14(007).
[责任编辑:林漫宙]
A New Realm of “Classics” Beyond the“Confucius Classics” and “Studies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YANG Tian-qi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he advocate for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the Sino-Western combination aims to help more researcher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bandon their native complex and emotions, and realize the neutrality of value and rational judgment in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so as to better find out the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study of classics” as a new discipline does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to abandon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classical learning based on earlier texts and that based on modern texts, equally treating the “study of Confucius classics” and “study of other schools of classics” as well as “Chinese learning” and “Western learning”. This can not only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fo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but avoid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o as not to suffer from the banter of “mix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s well.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clusively absorb the merit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acilitat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walk out of Asia and towards the world” while mutually complementing and harmoniously coexisting with such alien cultures as Christian culture, Islamic culture and Hindu culture. Only by this can a harmonious civilization be constructed and a harmonious world exist.
classics;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study of Confucius classics; study of other schools of classics; Sino-Western combination
2016-09-11
杨天奇(1989-),男,甘肃兰州人,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15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比较诗学。
B 21
A
1004-1710(2017)02-01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