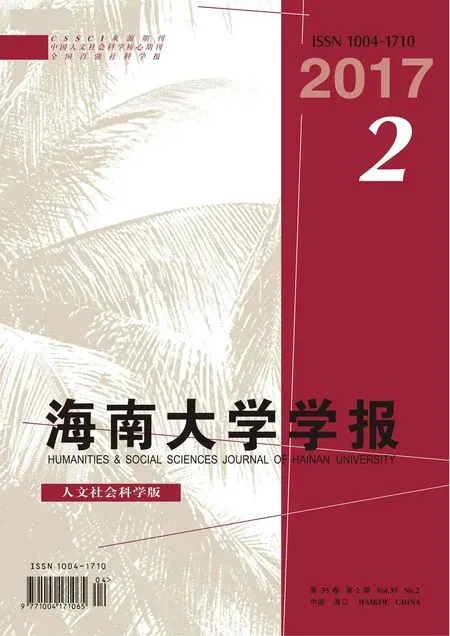从偶性、偶然性到“偶-在”
——对张志扬哲学的一个“地形学”阐释
梅迎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从偶性、偶然性到“偶-在”
——对张志扬哲学的一个“地形学”阐释
梅迎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张志扬的“偶在论”是检讨西方哲学的产物,但这种“检讨”本身已经不再仅限于西方哲学的范围,而是一种有着“文化间性”的新哲学。相对于实在先于偶性的传统本体论,“偶在论”则首先以偶性来颠倒实在,以偶然性来颠倒必然性,并最终指向了一个包摄偶性与实在、偶然性与必然性于其中的悖论性相关的“偶-在空间”。这种“地形学”意义上的“偶-在空间”能够容纳多样性于一个非辩证法式同一的统一性中,因而,张志扬的“偶在论”是一种极具跨文化潜力的中国现代哲学。
偶性;偶然性;偶-在;张志扬
“重新解释了西方哲学史”,这是海德格尔对自己一生思想劳作的定位。相较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哲学,德国哲学则尤为注重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哲学就是哲学史”,此一命题可谓是对德国哲学之精要的一个简明概括,当然,我们应该警惕这个“概括”(Abstrakt),因为概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站在了“历史性”的反面,但另一方面,“哲学史也是哲学”,因而一种兼具历史性的概括也是可能和必要的。在此,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矛盾的、介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临界状态,中国当代哲学家张志扬称这一临界为悖论式相关,也即偶在。德国哲学无疑是张志扬思想的主要来源。与海德格尔的说法相仿,张志扬把“重读西方哲学史”视为其学术活动的一个主要面向。“重释”与“重读”在词义上的细微差异表现了两位哲学家在面向西方哲学史时的不同身位和态度,但更为重要的也许是,这差异本身正是哲学自身之历史性的呈现和展开。作为西方哲学传统内部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奋力要将哲学(形而上学)带向其边缘,而作为西学东渐百余年之后的中国“哲学家”,张志扬则试图在中国思想经验被哲学笼罩和几近吞噬的状况下还哲学以本来面目,揭示哲学在普遍性、世界性和现代性的外衣之下被掩盖起来的特殊性、民族性和传统性,以“中取西学”的姿态来重新面对西方哲学(史)[1]。但必须注意的是,张志扬绝非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并不主张以某种纯粹中国固有的“国故之学”来与西方哲学分庭抗礼,毋宁说,张志扬乃是以接纳西方哲学的方式来批判西方哲学,因而这也与中体西用或“取精弃糟”的文化综合主义不同,因为体、用是无法切割成两片的,精华和糟粕也总是粘连在一起的。所以,建构一种真正的“中国现代哲学”[2]乃是一项重塑“新体”、实践“新用”的活动。在张志扬看来,本源意义上的哲学在任何一个元典文化中都是有的,哲学可以说是一个“共集”或“空集”范畴,或叫“通名”,因西方哲学的特殊性而独霸哲学的通名为专名,让共集或空集中的其他哲学全部退出其实是取消了其他哲学的哲学等级,让西方哲学独享哲学之名,这是西方哲学的一种霸道品性[3]310。但当今我们在思考作为“空集”的哲学时,也必然是无法绕过西方哲学的,因为不管是否情愿,西方哲学早已渗入了我们的历史之中,融进了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历史(世-界)是“一”和“多”相互交织着的悖论式相关,历史的统一性正是在历史的多样性中呈现的。这种“原-历史”(Ur-geschichte)也就是张志扬所讲的既无法在语言中证明其存在,也无法在语言中证明其不存在的“本体”。如前所述,这个“本体”只是一个空集,张志扬亦称之为“偶在”。“偶在”可谓张志扬哲学的核心概念。
一
“偶在”一词来源于西文Akzidens或Kontingenz,从这两个词的拼写上看,并没有“在”(Sein)的词根,故一般将其译为偶性或偶然性。而从义理上讲,偶性恰恰是“在”的对反概念,表示同“实体”或实在(Substenz)相区别的附加属性,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但张志扬认为:
“偶在”与“偶性”没有不同,好比都是“一个人”,只是“身份”变了。原来“偶性”处在附加于“实体”的地位,如今“实体”,凡人为设定的都虚幻不实……所以真正的主角是“偶在”,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偶在”和“偶性”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偶在”本原的是“本体论差异”即悖论,而“偶性”则附属于“实体”即本体论同一”。[3]230
显然,“偶在”一词在词形上已经显示出某种对传统本体论的解构,偶性从属于实体的上下层级深度模式,被转化成了“偶在”自身的非同一之差异性的悖论相关。基于此缘故,本文以下将把“偶在”改写为“偶-在”,因为在张志扬哲学的脉络之下,重要的既非“偶”,亦非“在”,而是两者的相关性本身。换言之,相关性本身是将偶性和实在“内存”于其中的、并使其得以可能的更为原初者,因而可以把“偶-在”理解为某种“元-空间”(Ur-ort),正如张志扬有时也会把“偶在”叫做“偶在空间”一样。
但需要注意的是,张志扬哲学中的空间概念并不意味着本体论式深度模式的回归,“存在本身的直接性,亦是生成的直接性。语言恰恰有层次地完整地体现着这个存在悖论,这里还需引申地作点说明,显即隐,是对生成本身的不确定性的描述,它并不隐喻生成的深度关系,如表层的结果是深层的原因产生的,这不是显即隐的当下性。在此同时的当下性中,显即隐并不必然地承诺对中心的指代,因而不能把它看作一般深度模式具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4]。正如张志扬的悖论式相关的概念深受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思想的影响一样,张志扬所理解的空间也直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的地形学”(Topologie des Seins )。海德格尔的思想一般被认为有一个从早期到后期的转向(Kehre),但海德格尔本人却认为转向并不是从现成的一端移向另一端,他说:
“海德格尔I”和“海德格尔II”之间所作的区分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可成立,即应该始终注意到:只有从在海德格尔I那里思出的东西出发才能最切近地通达在海德格尔II那里有待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I又只有包含在海德格尔II中,才能成为可能。[5]
所以说,海德格尔终生对存在问题(Seinsfrage)的思考并非一条“坦途”,毋宁是有着复杂“地形”(topos)的“纵横阡陌”,从对存在的意义(Sinn von Sein)的追问,到存在之真理(Wahrheit des Seins)问题的提出,再到后来以存在之场所/空间(Ort)来阐释存在之真理,存在问题自身就好像经历了某种“地形学”*Topologie在中文里一般被音译为拓扑学,这是一门研究各种“空间”在连续性的变化下不变的性质的数学分支。考虑到topos在古希腊文中乃是地形、地貌的意思,且本文并非在狭义的数学意义上使用拓扑学一词,因而本文将Topologie译为地形学。的变形,因此我们可将“思想的转向”理解为“转向的思想”,存在之思亦是对“转向”本身的思想。海德格尔在早期力图把时间作为崭露存在之意义的地平线(Horizont),因而有《存在与时间》问世,但后来海德格尔的思考重心不再是时间了,而是“与”本身,这就使得存在问题带上了更多的空间性意象,因为“与”(Und)在德文中不仅有并列之义,也有转向、转入之义。存在向时间的转入本身成为了更本源的事情。因而《存在与时间》最终成了一部残篇。按照转向后的海德格尔思想,存在之空间即空间之存在,换言之,时间并不是存在的地平线,存在反倒是时间的地平线,存在就是元-空间(Ur-ort)。张志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海德格尔的,他认为纯空间即虚无,它渗透一切、吞吐一切,规闭着时间而自身又不可穿透[6]。“偶-在”可以说就是作为“即存在即虚无”的纯空间本身。正如海德格尔经常说存在与虚无共属一体(Zusammengehören)一样,在张志扬的“偶-在论”中,偶性和实在也是悖论式相关的。
二
现在让我们重新从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出发,来思考“偶-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知识都表现为逻辑判断的形式,即将主词包摄于谓词之内。这也就是说,作为一般物的谓词把作为个体物也即实体的主词归属于自身之内了,或者说,特殊者内存于普遍者之中了。沿着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个体物才是终极实在,反映到判断上就是只能作为主词而不能为谓词,这样的个体物是一切一般性概念知识的基础。但这种个体物被包摄到一般者中,主词被归属于谓词之内的做法却面临一个悖谬性难题,即以这种个体物优先的思考方向是无法真正把握个体物的。当主词被归属于谓词之内,作为个体物的主词就在谓词的一般性中失去了个体性,而个体物是超越一切判断的存在,当它在被包摄于作为谓词的一般物之中时,也就被一般物所同化从而消失在一般物之内。换言之,此时个体物反而成了一般物的一部分。因为无论给主词加上多少个谓词,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此时此地的“这一个”(hecceitas)。因而,理性思维在这里便陷入到了一个悖论之中。
与亚里士多德对悖论的消极态度不同,张志扬给予悖论以积极性的肯定。“‘第二实体’对‘第一实体’或‘本体’对‘个体’、‘一般’对‘个别’的存在关系,乃是一个悖论关系,既存在于又不存在于。二者没有辩证法所许诺的对立面可以统一起来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两者是非同一性的。但是,人类思维似乎恐惧这个断裂的事实而力图消除它。”“本体、种、属,终究既不存在于个体之外,也不存在于个体之中,它完全处于中国哲学的一个‘悬’字状态。”[3]112在张志扬看来,概念理性在把握事实时是有限的,悖论并不是因为人的偶然失误而造成的错误,而是事实本身的真实呈现。如果以“偶-在论”的方式去理解这个悖论,那么,原本主词和谓词、个体和一般的矛盾便能够相容了。当然了,这不是一种辩证法式的综合。即是说,可以反亚里士多德之道而行之,不让个体包摄于一般,主词归属于谓词,即不再把个体作为包摄一般的根本空间,而是反过来,把作为偶性的一般看作把握根本空间的出发点。换言之,即从主词优先的逻辑转向一种从谓词出发的逻辑。
但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张志扬对“否定性”(Negativität)做了一个二重区分:递归上升和悖论悬置。所谓递归上升,就是按照种加属差的递归逻辑,从较为低级者一直上升到可理解的最高形式,或成为主宰的“最高存在者”。这就是主词逻辑。此外,否定性还另有一种更基本的含义,“存在-虚无”的“悖论悬置”。“尽管在‘不是’即‘否定’中,‘非存在’和‘不存在’的确与存在相关联着,但只是悖论式的即断裂式的限定着——偶在着,使‘存在’只在自身完整的限定中而不上升为主宰‘多’的最高存在者。”[3]186我们可以将“悖论悬置”理解为一种谓词逻辑。也就是说,把谓词或偶性看作某种有媒介作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作为个体的主词,虽然是独立的并与其他个体没有关联,但却发现自身与其他个体共同处于其中,因而也可以说,此空间乃是使得主词成为能够在一个谓词判断中得以出现的语境。在这个根本的空间/语境中,个体与个体在相互否定中获得肯定,同时这也是作为一般者和谓词的空间的自我否定,且没有失去其普遍性。
举个例子,红、橙、黄、绿作为不同的个体被置入“颜色”这个一般性的空间中,那么红、橙、黄、绿各自得以成立,也即能够作为主词,都是基于颜色这个谓词的自我否定,并且在红、橙、黄、绿之间的相互否定以及它们各自的自我否定中,颜色一般也得到了肯定。因而红、橙、黄、绿各自与一般者颜色就处在一种悖论式的相关之中。在主词逻辑中作为偶性和谓词的颜色(如红是一种颜色),在谓词逻辑中,就成了一种让个体或主词得以可能的“偶-在空间”,因而可以说颜色本身是无色的!也即是说在颜色空间中,颜色本身不具有个体性或对象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偶-在”的悖论空间中,谓词能够在一个更高的谓词判断中成为主词,例如我们可以说“颜色是一种性质”,那么此时相对于颜色而言,性质就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偶-在空间”,但是假设我们沿着谓词的方向不断推究下去,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最为源始的“偶-在空间”就是“偶-在空间本身”!
这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是同理的:最为源始的“存在者”(Seinende)将不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Sein selbst)了,“存在”不是“存在者”。“偶-在”与“存在”是等位的概念,正如“存在”本身就是虚无(Nichts)或无底深渊(Ab-grund),“偶-在”在终极上将不能是主词,更为严格的说,“偶-在”是无法在主词逻辑的框架内可以得到理解的。因为你无论如何去设想一种主谓判断的极限状态,这个谓词都仍然是某种主词,某种对象或某种存在(者),如此将会导致一种无穷后退的“恶无限”,因而终极的谓词不应该是存在者之存在,而是“虚无之存在”;终极的“偶-在”空间就是一个“虚无之空间”或“场所”*笔者对“偶-在空间”的“虚无”(Nichts)之特性的理解受到了日本京都学派哲学家的影响,如西田几多郎的“绝对无”,田边元的“绝对媒介”,西谷启治的“空”。。一切事物都是作为“偶-在空间”的虚无(Nichts)的一种具体化。
三
如果说“偶性”是一个实体范畴,那么“偶然性”则属于逻辑范畴,它只与“必然性”相对。偶性与偶然性虽然都导源于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但两者在使用上还是各有侧重,就像“构成因”与“关系因”的区别一样[7]36。然而,正如通过重新解释偶性和实体的关系可以得到“偶-在”概念,同样,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出发,也是一条通向“偶-在”概念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张志扬深受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soziologischen Systemtheorie)的影响。
与试图以“交往理性”( 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重塑“社会共识”的哈贝马斯不同,卢曼将“偶然性”(Kontingenz)当作现代社会系统运作的样式,即一切事物不再是不可能,但同时,又不是绝对可能。在卢曼这里,“偶然性”已经不再是与“必然性”相对的“偶然性”,而是“偶-在性”了。张志扬也说:“偶在是由对不可能性的否定和对必然性的否定来界定的。据此,凡是虽然可能,但并非必然的东西,都是偶在的。”[7]62哈贝马斯认为,从语言、行动者的交往规则里面可以找到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条件,但在卢曼看来,我们不可能找到这种克服社会之“不确定性”或“偶然性”的配方,因为社会整体不再是能够被定义的,也即是说,对一个社会系统的观察(Beobachten)自身就是社会系统自身运作的一部分,一个理想状态下的观察社会的“阿基米德点”是不存在或“偶-在”的。试图使用一个阿基米德点来观察的行动本身只能由社会本身来推行。社会决定了一切,但自身却是不确定、无法定义的,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也即是“偶-在”的,这种“偶-在性”是社会沟通和自身运作的表现方式和产物。因而“偶-在”作为一个不可观察者就成了一个难题。卢曼认为,宗教就是针对这一难题的,宗教的功能正在于将不可定义的“偶-在性”引向可定义性。“上帝可以看成是一个集中的悖论”[7]203。
卢曼是以其有关“观察”的理论来面对这个悖论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运作(Operation),这个运作乃是以某种“差异”(Differenz)来“标示”(Bezeichnen)某事,并同时把被标示的事情与其他事情“区分”(Unterscheiden)开来。由于观察运作一定会运用某种“区分”*例如:自我与世界,内在与超越,系统与环境都是区分。,也就是说,观察总是要划出某种边界才能够进行“标示”与“区分”,所以任何观察运作本身也是可以被其他观察运作所观察到的,任何观察运作都同时在改变着它所观察的世界。不可能有一个可以被观察而本身却不受观察影响的恒定不变的世界。换句话说,我们永远无法站到世界之外来观察世界,而只能从世界内部,按照世界本身所提供的具体条件来进行观察[8]。因此,在卢曼看来,除了对对象的观察之外,还存在对观察本身的观察,这就是“二级观察”(Beobachtung zweiter Ordnung)。这种二级观察把一级观察所使用的“区分模式”本身作为观察对象。换言之,一级观察总是无法观察到自己正在使用的“区分”,这个“区分”成为系统之所以能够进行观察的“盲点”。
以透视法所绘的图画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观察中的盲点。以透视法所作的画不再仅仅是对实物或对象的描绘,同时,它也将观察者即作画者的位置一并包含了进来。随着作画者所处位置的不同,对象所呈现的景象也会随之变化,绘画的观赏者只有站在与作画者相同的位置,才可以观察到与作画者相同的景象。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能够观察到对象,则必须立足于某个盲点或观察角度之上,必须采取某种区分,即使这个区分只是众多区分形式中的一种,或者说,我们的观察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所以,盲点是观察得以可能的条件,虽然盲点可以在二级观察中成为新的对象,但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新的盲点。只要你还在观察,那么盲点和区分就是无可摆脱的。用卢曼的话说,就是系统本身总是从“无标记的空间”(unmarked space)中进行“标示”与“区分”的观察运作,它自己无法观察到此“无标记的空间”[9]。在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无标记的空间”称之为“偶-在空间”。“偶-在空间”作为元-空间自然是无法被观察的,但它却是观察得以可能的条件,也就是“区分”得以有意义的“元统一”,“区分”和“统一”构成一种“偶-在”的悖论性相关:“区分”以“统一”为前提,但“统一”也只能在“区分”之中才能显示自身。在卢曼看来,我们不能通过外部观察的方式来界定宗教的本质,上帝也非观察的对象,而是悖论本身。
在卢曼的“上帝是集中的悖论”的影响之下,张志扬提出了“开端之悖论”。传统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追求绝对的第一开端(本源/arche),但张志扬认为,开端即是划界,传统哲学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凭着他们所能想象的开端,不是有限的无限(类似由一点出发的射线),就是无限的循环(圆)”,“因而划界的开端首先就是‘有-无’的生成悖论,其表现是不确定/确定、不可说/可说的界面”[7]50。张志扬进而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所许诺过的三大开端——“上帝”“存在”“主体”——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都没有真正成为永恒持存、普遍必然的绝对同一,而是裂变多端。
“上帝”,且不说只是西方犹太教、基督教世界的划界,即便划界之后,“上帝”依然三分,即“三位一体”之后的重点转移、释义繁衍更是多不胜数,但有一个总的趋向,即上帝从君临一切之上严厉主宰生杀予夺的惩罚,转变为十字架下苦肉仁慈宽容和解的赦免。[7]51
“存在”,最初有在“存在”的河流之外与河流之中(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也就是存在即一与存在即变之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存在则呈现为各种形式的最高存在者。海德格尔之后,则有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区分,以及德里达更为激进的将存在抹去的踪迹化。对于“自我”,则早在笛卡尔那里,就因为有着致命的“时间缺口”或“死的根性”,从而使得“自我”具有“点积性”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同一性主体。从康德到胡塞尔的先验哲学传统更为强化了对“时间缺口”的掩盖。以福柯为代表的当代法国哲学家将“身体”引入自我实乃对自我的降解,使身体成为自我的出身或起源[7]52。这一系列的流变更迭实质就是卢曼所言的“盲点”的更迭,用张志扬的话,则是“‘视点’的移动或‘入思方式’的变迁,造成界限内外的差异,结果,从虚到空,唯‘偶在’在”[7]52。
四
以上,我们分别从“偶性”(实体属性)和“偶然性”(逻辑属性)两个角度来思考了张志扬哲学中的“偶-在”概念,并且把“偶-在”规定为一种“地形学”(Topologie)意义上的元空间。张志扬虽然说,“偶在论”是检讨西方哲学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种“检讨”本身已经不再仅限于西方哲学的范围了,而是一种有着“文化间性”的新哲学。张志扬区分了“无形神”和“有形神”,并且认为前者可与中国的“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同层次,后者只是“诸神”即各民族神、宗教神而已,如耶和华或上帝等[1]309。不过张志扬无意于让中国文化一家独大,而是努力探索一个能够容纳多样性的“非同一的统一性”,所以说他所理解的道并非专属于中国,而“偶-在”也并不专属于西方。无形的道与非实体的“偶-在”作为一个根本的空间使得各种特殊文化类型都可以在其中生成。因此,张志扬尤其看重海德格尔哲学,且将其比作西方哲学史中的“白乌鸦”就容易理解了。张志扬的“偶-在”几乎就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悖论性相关也几近于显隐二重性。海德格尔也使用过“地形学”的术语“敞开之境”(Gegnet)来指称“存在”,“敞开之境”环绕着我们所有可理解的“地平线”,只有在这些“地平线”中,事物才能得到理解。这就像是只有在“偶-在”的空间中,偶性和实体才能获得意义。在“偶-在论”的视野下,并没有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截然划分,它们的差异仅仅是由于历史世界在形构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不同道路和方向的选择而已。
真正的哲学只是永远去重塑“开端”而非去占有某种开端,只有在不断地对开端的塑造中,才能不断地打开“偶-在空间”。一切开端并不本来就是开端,在这些开端之前,我们一定已经找到了结束。开端与结束是同时确立的,正如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一经确立,就已经走向了终结。张志扬说:“我不得不放弃曾经立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哲学’的现世书写。……临到,一切都为它准备的开始,骤然发现,‘已经没什么可写的了’——站在这几个字面前,心为之惊悚!——意识到我的路已经走完。”[3]363实际上,在走完/结束之前,结束已经发生:“偶-在论”既标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也同时就预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结束。因为中国现代哲学本身,永远需要重新开端,重新结束。
[1]张志扬.西学中的夜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张志扬.创伤记忆[M].上海:三联书店,1999.
[3]张志扬.偶在论谱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4]张志扬,陈家琪.形而上学的巴别塔[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270.
[5]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1278.
[6]张志扬.语言空间[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146.
[7]张志扬.偶在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0.
[8]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M]. Frankfurt:Suhrkamp,1992:75-82.
[9]Niklas Luhmann. Die Religion der Gesellschaft[M].Frankfurt:Suhrkamp,2000:29.
[责任编辑:孙绍先]
From Accident and Contingency to Occasional-being——a topological interpretion of philosophy of Zhang Zhiyang
MEI Ying-Qiu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Zhang Zhiyang’s theory of occasional-being is the product of reviewing Western philosophy , but this “review” itself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Western philosophy , but a new philosophy with “intercultural nature”.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ontology,the theory of occasional-being undermines substance with accidents, necessity with contingency, leading to a paradoxical occasion-being space as its final point, which incorporates and includes contingency and necessity.Even this “topological” occasion-being space could accommodate the diversity in a non-dialectic unity. and therefore ,Zhang Zhiyang’s theory of occasional-being is a great cross-cultural potential Chinese Modern Philosophy .
accident;contingency;occasional-being;Zhang Zhiyang
2016-10-10
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资助项目(201306360108)
梅迎秋( 1982-) ,男,山东淄博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国哲学和现象学。
B262
A
1004-1710(2017)02-0108-06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