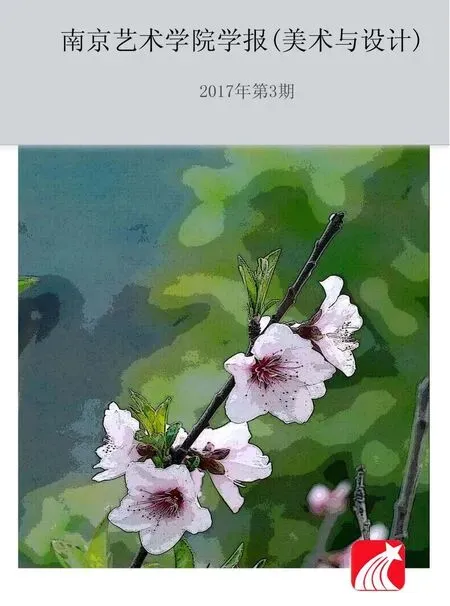傅山:从“甲申国变”到惨淡治生
郑付忠(长沙师范学院 书法系,湖南 长沙 410100)
傅山:从“甲申国变”到惨淡治生
郑付忠(长沙师范学院 书法系,湖南 长沙 410100)
1644年明朝灭亡,对于像傅山这样的儒者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一来要他们要为衣食而忧,二来改换门庭后的傅山失去了精神的寄托,找不到自我身份定位。加之他拒绝参加博学鸿儒“恩科”,经济条件急转直下。由于生活没有着落,他的交往和应酬均带有极强的谋生色彩,情急之下的傅山甚至动过从商的念头,不得不通过鬻书卖画、行医等方式治生。傅山主要面临的尴尬在于如何看待治生之道,书画自古被视为文人遣兴排志的雅好,他以此谋生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傅山;治生;鬻书卖画;身份
傅山(1606—1684),山西阳曲人,字青竹,号朱衣道人。出身书香门第之家,博学多才,于书画、诗文、医学等诸多方面皆颇有造诣。祖父傅霖是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山东辽海道参议。其父傅之谟乃明代万历年间贡生,博学能文,未入仕途,以教授生徒为业。由于出身官宦之家,祖上殷实,傅山自幼饱读诗书,遍览历代图籍、书画、碑帖,还精研医术,也为国变之后半生落寞、以书画文事治生埋下了伏笔。
一、身份迷失与精神归宿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军推翻大明王朝,随后清朝入关,入主中原。明朝顷刻间巢倾卵覆,中国历史完成了由大明到大清统治的转变,即所谓“甲申国变”。明朝灭亡对于傅山这样的儒者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衣食之忧,更为重要的是,改换门庭后的傅山失去了精神寄托和身份定位,②开始了他纠结挣扎的谋生之旅。明亡之前,傅山家境殷实,在老家忻州及太原一带有多处地产。[1]明亡后,由于他失去了经济来源,并且在甲申、乙酉年间典卖家产筹资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因此经济条件急转直下,不得不通过鬻书卖画、行医等方式谋生,且时常寻求朋友的帮助,勉强度日。这还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困难,更令其痛苦的是精神上的虚无。明亡后,部分文人出于种种原因投降了新朝,但也有部分人坚守节操,决不出仕清廷。如李傲机便视名节如生命,《皇明遗民传》卷一载,李氏国变后隐居汉阳,遇有达官求见,“即跃入江中,俟其去乃出”,[2]一时传为佳话。这类遗民不仅洁身自好,而且往往对“变节”者施以道德批判,如归庄便说:“只恨这些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帽,金带横腰,今日里一个个稽首贼廷怀揣几篇儿劝进表。更有那叫做识字的文人,还草几句儿登极诏。”[3]这样的舆论环境对出身儒者的遗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道德枷锁。傅山在国运更迭之际站在了大明王朝的一边,称病拒绝参加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儒“恩科”。且作《病極待死》诗以表明决心:“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4]句句可见其视名节如生命、誓不与清廷合作的决心。但由于康熙帝驳回了托故请辞的奏折,最后各地督、抚不得不强行把傅山抬往京师。从《续修四库全书》的记载看,傅山此行充满了戏剧性:“……固辞,有司不可。先生称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床以行,二孙侍,既至京师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上闻诏免试,许放还山。”[5]政治立场的坚定和文人节操的固守由此可见一斑。
傅山在明亡后由于一时难以找到精神归宿和身份定位,故常有反常之论。或许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故这些振聋发聩之声常以艺术评论的形式出现。比如他在《作字示儿孙》一诗中说∶“作字先作人, 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 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 笔力不专主。一臂加五指, 干卦六爻睹。难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遡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 毛颖足吞虏。”并紧接着附有一段详细论述:
贫道二十岁左右, 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 无所不临, 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 遂临之, 不数过, 而遂欲乱真。此无它, 即如人学正人君子, 只觉觚棱难近, 降而与匪人逰, 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 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 痛恶其书, 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 而苦为之。然腕杂矣, 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 不亦伤乎! 不知董太史何所见, 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 贫道乃今大解, 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 令儿孙辈知之, 勿复犯此, 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 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 只缘学问不正, 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 危哉! 危哉! 尔辈慎之。毫厘千里, 何莫非然? 宁拙毋巧, 宁丑毋媚, 宁支离毋轻滑, 宁直率毋安排, 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6]
以上材料有两个核心含义,一是傅山认为,“书品”如“人品”,并把做了“贰臣”的赵孟頫当作一个反面教材警示子孙。这是因裹挟了政治情绪而发出的偏激言论,傅山本人显然也深知此中道理,因此我们在《霜红龛集》中又看到这样的描述:“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无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7]这种对赵孟頫前后评价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反映的是傅山在国变后政治情绪的波动及其与新王朝敌对人生态度的微妙变化,本质上并不是对赵书的负面看法。因此有关这段论述以“四宁四毋”作终的说法,由于忽略了“四宁四毋”的语言环境,在书法史层面做过度阐释也就没有意义了。关于此论,清代学者全祖望给予了“君子以为先生非只言书也”[8]的评价,可谓不虚。傅山早年学赵书,“甲申国变”使得他对改仕新朝的赵孟頫颇为不满,故有此反常之论。蔡显良说:“其实这一思想观点就是在傅山政治观影响下, 才在甲申之变这一历史的特殊时机到来之后生发演绎而成的……但这只是特定思维下的特定选择, 是以人论书观念的一种延伸性、极端化的表述, 而并非正常书法审美思维过程中的产物。因此,‘四宁四毋’只有放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特殊的表述场合, 才能产生特定的审美内涵, 而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常规审美与艺术宗旨来对待, 否则将有失偏颇。”[9]有关“四宁四毋”在书法史层面的过度解读屡见不鲜,①按,贾宗赤曾指出“四宁四毋”在书法美学层面的过度阐释:“我们如果不从傅山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和傅山的思想、性格, 以及宁丑毋媚这种语句在语法上的使用特点去全面分析, 只是片面而主观地把‘四宁四毋’当作傅山在书法中艺术境界极高的审美追求……这种评价是欠妥的。”(见贾宗赤:《“四宁四毋”之我见》, 载《书法》1991 年第 2 期)确系忽略了文章的整体语境,有断章取义之嫌。与其说“四宁四毋”是一种艺术观念,倒不如将其视为特殊时期的一种政治诉求更为准确。当“舍身取义”与“卖国求荣”的两难摆在傅山面前的时候,两害相较取其轻,他只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极端方式。
国变之后,傅山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尴尬在于如何看待身份转变之后的治生之道。这里所谓的身份转变是傅山变成了“遗民”,而作为一个传统文人的身份他始终未变,矛盾也正由此出。由于国变后生活落寞,情急之下的傅山甚至动过从商的念头。据载他曾合计和朋友开一家酒楼,但由于灾荒短粮政府禁止酿酒而搁浅,[10]77-78这似乎触碰到一个传统文人的思想底线,一个宁死不仕新朝的文人,居然要为了生计而染指商业,傅山的身份给其治生留下的空间少之又少。今按,傅山对商业领域的涉足有其特殊时代背景,明代中期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社会风气逐渐转变,士商相杂的现象十分突出。特别是明亡后,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择业观念逐渐转变,传统意义上对“四民”观念的固守也有所松动。但士人从商的现象也只能在普通士人中较多的存在,而不可能在有影响、有名望的士人中间普遍存在,因为后者鄙视经商的观念往往要强烈得多。[11]傅山自然属于名士,所以他对通过商业治生势必比普通人更加审慎。国变后与其有类似遭遇的许多遗民均对从商表示出抗拒的姿态如著名遗民屈大均(1630—1696)便说:“予于治生之道,靡所不知,而不能一一见诸施设,则以家无资财而性好恬淡,终日漠然无所营。美利在前,视之如有所染。故凡有以货物来言者,皆一笑谢之。”[12]屈氏表示出对商业的鄙夷,这种情绪在清初遗民中较为普遍。清代儒士王夫之(1619-1692)在《传家十四戒》中说:“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13]尽管商业氛围已经较为浓厚王夫之依然把“商贾”排到了末位,这与其儒者的身份不无关系。又如理学家张履祥(1611—1674)也表示,以“贸易之事”为“心害”,[14]且对儒者卖文为生的谋生方式不以为然:“白沙言:‘昔罗先生劝仆卖文以自活,当时甚卑其说。据今事势,如此亦且不免食言。’愚谓卖文亦不可,惟康斋先生躬耕为无害于义。”[15]可知卖文谋生的方式在当时士人中是有争议的,而张氏的主张是宁愿务农。他的这种观点在其致吕留良(1629—1683)的信中同样得到了呈现:
兄禀赋之高明,嗜善之饥渴,与夫择道之不惑见义之勇为,种种溢美,何难尽造比肩于千古之人豪顾将久与昏浊之日苟盗浮名之辈流动,若絮长角胜者某虽志行不立,私心不为兄甘之。往时尝止兄之学医实惧以医妨费学问之力。今去此又几春秋矣!自兹以往,少壮强力,更有几何?试虑行年即若卫武,已去其半。中夜以兴,虽若横渠,犹将不及。堪为若此无益身心,有损志气之事,耗费精神,空驰日月乎!昔上蔡强记古今,程子尚以为“玩物丧志”;东莱日读《左传》,朱子亦以其守约恐未。何况制举文字,益下数等,兄岂未之审思耶?[16]
从张履祥的叙述中可知,他不仅认为吕留良卖文“有损志气”,而且还曾规劝吕氏不要学医,因为学医“妨费学问之力”。甚至吕氏自己也曾一度反思自己的鬻文谋生之举,并深觉不妥,直至临终仍作诗表达羞耻之心:“坐计耦耕犹未得,卖文乞食总堪哀。”[17]对于文人而言,卖文、鬻书、卖画、行医都是无奈之举,有夺志辱身之嫌,由此不难想象同为遗民的傅山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屑于经商治生,认为这有乖士大夫避世全节的志愿,但由于失去了经济着落,所谓保全志节对于大部分遗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事实上,包括傅山在内的诸多遗民或多或少都曾染指商业,艰难维持生活。对于明清之际士人的谋生方式,赵园曾给出这样评价:“……几乎没有讨论余地,因而也往往不被讨论的,是商贾……对谋生手段的衡量,所持非‘效益’尺度,而是道德尺度。”[18]一方面是生计所迫不得不接触商贾,另一方面又要正视他人的非议,毕竟这些遗民的偏见部分地展示了当时的世道人心,这便是傅山等人所面临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对于那些鬻书卖画的遗民而言,由于书画自古被视为文人遣兴排志的雅好,所以以此谋生者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如明亡后徐枋(1622-1694)以卖画谋生,便遭到了他人的非议。以至于他在《答友人书》中自辩道:“仆作画三十年,而卖画未及数载……比年以来,物力日艰,人情日素……故不得已而卖画,聊以自食其力,而不染于世耳。然非我求,蒙迫而后应,且卖者不问其人,买者不谋其面,若百年采筹,探箬桃,椎纤屦,置之道头,需者随其所值,亦置道头而去,仍不与世相接,而与物交关也。”[19]尽管徐枋想通过“自置街头”的方式避免买卖双方的“谋面”,规避与市井为伍的风险,但仍旧担心世人的误解。徐枋试图自我辩解以保全名节,然而这种托词即便能够搪塞世人悠悠之口,也难以经得起徐氏的自我推敲。作为传统文人,他内心甚至把鬻书卖画等同于卖鞋席:“避世之人,深不欲此姓名复播人间也,则仆之佣书卖画,岂得已哉?仆之佣书卖画,实即古人之捆屦织席,聊以苟全,非敢以此稍通世路之一线也。”[20]这种定位显然是出于对商贾的鄙夷而发出的。在儒者看来,游幕、卖卜、行医、处家馆等皆为堕落之举,如明末诸生方文(1612——1669),入清不仕,常卖卜自给,招致朋友的非议和劝诫。他作诗答朋友说:“江市聊为贸卜行,敢言踪迹类君平,所求升斗供饘粥,不向侏儒说姓名,四海同人惟道合,一生得意是诗成,何当日暮垂帘后,共奏商歌金石声。”[21]尽管卖卜自给,方文仍旧不忘自比汉代隐士严君平,一来严君平也卜筮为业,二来想以“市隐”自慰。但他分明又不能无视朋友的非议,否则也不至于作诗自辩了。
简而言之,明末清初的整体社会氛围并没有给这些落魄的文人以充分的谋生自由,傅山自然也就很难放开思想枷锁融入到商业社会中去。且不说经商,即便是靠处家馆、卖文、卖卜等为生,也属无奈之举,而沦落江湖鬻书卖画就更不值得提倡了。
二、交往与酬应
傅山的交往与酬应,很大程度上与其在国变后的拮据生活有关,因此他的社会交往多与其鬻艺经历有关,其应酬也多夹杂着各种利益交换。白谦慎先生在谈及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强调:“凡创作时不是为抒情写意、旨在应付各种外在的社会关系——或出于维系友情、人情的往还而书写的作品,广义地来说,都可以视为应酬作品。”[10]86对于一度生活无着落的傅山而言,艺术的遣兴托志与为斗米而忧是交织在一起的。傅山交往和应酬的对象十分复杂,有清政府中的一些官僚,也有学界投缘的同仁,甚至还有普通百姓。无怪乎他发出这样的慨叹:“无端笔砚业缘多,不敢糊涂说换鹅。这为世情难决绝,鹜书终日替奔波。”[22]一方面如傅山所说是出于人情世故难以推诿,另一方面,傅山在这种交往和应酬中何尝没有获得利益呢?比如他与清政府官员魏一鳌的交往,便夹杂了寻求经济上的帮助和政治上的保护的因素。[10]14傅山曾多次写信给魏一鳌请求帮助,如1652年前后,他曾致书魏一鳌,请求免去他的土地赋税,①《丹崖墨翰》第十七札:“寒家原忻人,今忻尚有薄地数亩。万历年间曾有告除粮十余石。其人其地皆不知所从来。花户名字下书不开征例已八十年矣。今为奸胥蒙开实在粮食下,累族人之催此,累两家弟包陪,苦不可言。今欲具呈有司,求批下本州,查依免例。不知可否?即可,亦不知当如何作用?统求面示弟山。弟甘心作一丝不挂人矣。而此等事葛藤家口,不得了了。适有粮道查荒之言.或可就其机会一行之耶。其中关键,弟亦说梦耳。恃爱刺之。”(引自齐峰主编《傅山书法全集》第8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2页)又写信给魏氏请求经济帮助:“天生一无用人,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不得,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盐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静活命乞食之优婆夷及一比丘为顾,同作莲花眷属。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信中傅山以“口腹累人”相乞,甚至把自己说成了清心寡欲的出家人,以请求经济帮助。而魏一鳌也果然不负众望——1653年,魏氏花30金在太原郊外为其购置了房屋,[23]解决了傅山国变后到处寄宿的难题。
傅山耻于出仕,但又不能全然不食人间烟火,于是不得不进行各种社会应酬,或者谋求其书画经纪人的帮助。前面提到由明入清的徐枋,他卖书画采取了较为传统的方法,即“自置街头”以避免与屠沽世俗的接触。其实唐宋时期便出现了所谓“牙人”这一行当,有点类似于后来的经纪人。比如专门负责书画交易的中间人称为“书侩”,①按,据唐人李绰记载:“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着。……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逃焉。王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其时急切减而赈之,曰:钱满百千方得。”(见李绰:《尚书故实》,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167页)牙人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买卖双方提供供需管道,并以其专业性保证商品的质量。二是避免了买卖双方“谋面”,顾全了儒者的颜面。傅山的谋生之道自然也少不了要寻求“中间人”的帮助,比如戴廷栻(1618—1691)。戴氏与傅山同为明遗民,国变后,相同的故国情结和遗民态度使得二人交往密切,成为岁寒之友。傅山在《叙枫林一枝》中说:“枫仲髫年,受知与袁山先生,许以气节文章名世。丙子,拔晋才士三立书院课艺。枫仲声燥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字。余因其蚤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助,竟成岁寒之友矣。”[24]367所谓“古道相助”,即谓戴氏常为傅山代卖书画,助其度过生活困难。故宫博物院藏有傅山致戴廷栻的一些书信,言及傅山的生活求助:“穷而无聊,颇欲结三椽之菴,以字画为卦谋也。记室或有善缘, 一劳指示。枫老仁丈。弟山顿首。”[25]信中谈到傅山盖房无资, 请托戴廷栻为其代卖字画。傅山没有仿效徐枋“自置街头”而是寻求戴氏等经纪人的帮助,恐是他放不下身段,以至于此。戴廷栻是傅山的老朋友,因此常见到傅山在信中向他诉苦:“老人听着写字,生头痛矣。勉强写后,两眼角如火烧,少选胶膏餬之,径不能开一缝,其苦如此,非诳言也。即以字论,尚成半个字耶!有命即书坏扇二柄,非弟罪也,若有人非,请分任之。”[24]479写字作画本自娱,对于傅山而言却成了谋生的工具,恐为人耻笑,信中诉出其难言之苦。此外,傅山鬻艺还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他喜欢旅行,有时也写信给戴氏请求帮助:“……弟欲理前约,为嵩、少之游,称此老病未死,略结此案。求兄一脚力度我,临时并欲求劳一得力使者帮之也。……盘费欲以一二字画卖而凑之,不知贵县能有此迂人否?先此问之。”[24]477言辞说得极委婉,且不无自我调侃。从中还可以获得更深一层的解读,即傅山卖字非为发家致富,因此他对朋友的请托也没有遵照商品和市场规律,按照通俗的说法——不是你想买我就卖。鬻书总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为交游而卖字对于读书人来说倒显洒脱。此外,傅山晚年写信给戴廷栻说:“……欲结庐茅丹崖之下,送此残年,而苦无芟苍凿翠之资,未免有待于我辈。而我辈之可烦者,莫过我兄。而吾兄此时之囊政复羞涩,可当奈何!自过河西分单破梵,外景内情,逐处不堪,无聊派遣,作得绢画数副,烦枫仲道丈为我作一风流头陀代为韵募……”[26]卖画不为别的,只为做个隐者,倒有点陶潜的“结庐南山下”的意味,要在物质生活难以保证的前提下保全一丝文人的志节,傅山的确有点狼狈不堪。当然,对于戴氏、魏氏的帮助,傅山也不会白白接受,他能做到的回报就是为他们作书画、治印,为其家人看病,[27]这也算是一种变相的交易行为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治印,傅山向来少把治印作为私人应酬,除了其治印水平所限外(非关主旨,暂不展开),白谦慎先生认为出于两种考虑,一是“耗时(有时刻铜印),不似书法可迅速完成”,二是印章“不像书画那样可以悬挂展示”。[28]笔者认为,当以前一种原因居多,治印自古乃工匠之役,且耗时费力,相较书法而言,更有为人作苦役之嫌,由此也可见戴氏魏氏对傅山的帮助非同一般。
与傅山有过书画交往的还有一位叫做荃老的人傅山在与之的书信中谈及以书换米之事:“庽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24]496-497从写信口吻来看,傅山应当不止一次与荃老以书易米了。“留而发之”当是托其卖字之意,傅山打趣说,这种交易将成为大陵(太原附近文水县)的一桩笑话,实际上是一种慨叹和自嘲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自古有之,避免了买卖双方对质于市肆的尴尬,是文人常常采取的一种谋生之道生活困难还迫使傅山学会精打细算:“闻祁县米麦价颇贱于省城,欲烦兄量米八两、麦六两者”。[29]傅山从前朝富家子弟一落而转变成需为斗米操劳者,听说祁县米价比较便宜,他专门委托朋友代买,此中心酸可想而知。由此也让我们对其交往酬应中的诸多尴尬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和宽容。
三、治生之道
傅山出生于官宦之家,明亡后家境一落千丈,谋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看病”,“二是卖字画”他是士大夫,对卖字这件事是很不愉快的。[30]关于从医的问题,明清之际不少遗民确实是以此谋生的傅山的医术系家传,清人全祖望说:“先生既绝世事而家传故有禁方,乃资以自活。”[31]傅山卖书鬻画之余还兼职行医,傅家还一直开着药铺, 由傅眉经营。②案,关于傅家开药铺一事,清人戴本孝(1621-1691)于 1668 年在太原拜访傅山时提及傅家药铺,可知至迟在 1660 年傅家还在开药铺(见(清)戴本孝《迂道太原, 造访黑松庄傅青主不遇, 冒雨返邸次, 怅然赋此却寄》、《赠傅寿髦》, 载《余生诗稿》,康熙年间刻本, 卷3)但儒者行医谋生历来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之举,有辱斯文。如吕留良曾以行医自活,就遭到友人张履祥的批评:“儒者之事,自有居广居、立正位而行大道者,奚必沾沾日活数人,以焉功哉?若乃疲精志于参苓,消日力于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酬应之烦,不逾鄙俗,较其所损,抑已多矣。复挈长短于粗工,腾称誉于末世,尤为贤者所耻乎?”[32]可能是有鉴于此,傅山并没有放下身段做一个全职的医者,就像他偶尔鬻书卖画一样,囊中羞涩时就主动寻求自活之道,稍稍富足后便又极为自诩。作为一个文人,傅山骨子里的孤傲很难被磨灭,他有一段话颇为经典:“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可得知也!”[24]863-864这里所说的“俗物”,白谦慎认为。“很可能是那些有钱但缺乏文化修养的地主和商人。”这些人明明腰缠万贯,却还要斤斤计较,又担心买到代笔之作,时常对傅山“面逼”。[33]世俗之人只在乎傅山的签名,并不关注作品的质量,因此会有在傅山看来的愚蠢之举,令其不堪其扰。对于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作品,傅山称之为“死字”、“死画”:“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酢请祝,编派催勤,机之远矣。天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耳!”[24]819古人历来注重政治理想,似这般为人役使之事,历来被视为消磨意志之举。《旧唐书•阎立本传》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的记载,[34]说的是唐高宗李治的两个宰相,左相姜恪驰骋疆场,屡立战功,右丞相阎立本却以书画见称,为后人所讥诮。这种矛盾在傅山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他的诗文中常提及为了谋生而作书的矛盾:
鹜书有何好?此谬由诸君。
作意见不见,制心闻不闻。
所希在斗米,岂敢望鹅群?
自笑悭贪甚,吾能去几分?[35]
说的是傅山为了生活而与世俗周旋,自觉已经偏离了艺术本旨。又作《村居杂诗》与此旨趣相近:
无端笔砚业缘多,不敢糊涂说换鹅。
这为世情难决绝,鹜书终日替奔波。[36]
这两首诗道出了傅山的无奈和疾苦,正如他所慨叹的那样:“笔墨事本游戏自适一着,而径为人役苦恼,乃知亦是恶姻缘也。”[24]866正因为如此,傅山在看到儿孙学书有长进时便陷入矛盾:“且吾几为此事死,尔复欲造此三味耶?万万不可开此门户。传语后人,勿复学书,老夫痛惩之矣。”[24]863这话恐怕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傅山并没有能力摆脱尘世的烦扰:“因无贷之难,遂令老夫役人之役。凡来人,不忠厚者多。 ”[24]866他分明知道来者别有所图,因此从内心对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充满愤懑,但究竟还是难以摆脱世俗的纠缠,这种心态正体现了文人与书画商业文化的博弈。
结束语
在巨儒名士看来,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意味着一份殊荣,靠商业治生为他们所不齿。对于有些遗民以商业谋生,黄宗羲(1610-1695)慨叹说:“江河日下,生死休戚,惟财乎是系。小人习观世变之机,而知其势之所重在于此也,于是惟货力是矜是尚。”[37]社会名流的价值观念对傅山形成了巨大的舆论约束,与普通遗民相比,傅山等社会精英入清后在择业方面思想包袱较重。尽管当时社会的商业氛围已经愈发浓厚,但对于傅山等儒者来说,传统“重农轻商”思想仍旧极大的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因此傅山以鬻书卖画为生,但他却留有底线。白谦慎先生说:“虽然傅山迫于生计而鬻书卖画,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10]207这种相对的自由当然是由于傅山所具有的强大的文化资本而获得的。因此傅山鬻艺也并非完全被动,他的“应酬策略”体现为其在书写内容、是否题上款、是否钤印以及书体选择等方面所具有的相对自由。[10]195-206直至他临终前的1684年5月,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傅山留下了绝笔《辞世帖》:“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38]生前为了名节、为了生存,傅山始终不能放下思想包袱,《辞世帖》使得他彻底卸下了重担,对其无奈的治生之道作了完美告白。
[1]丁宝铨.傅青主先生年谱[G]//.霜红龛集(影印丁宝铨宣统年间刻本)[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1353.
[2]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M].巴蜀书社,2009:334.
[3]孙静庵着,赵一生标点.明遗民录·归庄(卷三十六)[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273.
[4](清)傅山.病極待死[G]//.霜红龛集(卷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5]《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429 集部别集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97.
[6](清)傅山.霜红龛集(卷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7](清)傅山.霜红龛集(卷二五)[G]//.家训(影印清宣统三年山阳丁宝铨刊本)[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8](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六)[M].影印嘉庆九年史梦蛟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蔡显良.坚守信念与尴尬实践---论傅山“四宁四毋”书学观与创作的矛盾[J].文艺研究2008(3).
[10]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1]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2]欧初等主编.屈大均.屈大均全集(三)[G]//.翁山佚文辑(卷上)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30 .
[13](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5册)[M]. 岳麓书社,1995:923
[14](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六)答陆孝垂[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8.
[15](清)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备忘录遗[G]//.北京:中华书局2002:1212.
[16](清)张履祥.杨园先生诗文(卷七)[G]//.续修四库全书(第1399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08-109.
[17]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3:103.
[18]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97.
[19]汪宗衍.艺文丛谈[M].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64-65.
[20](清)徐枋.易堂集(卷二)[G]//.四部丛刊三编(第75 册)[M].上海书店,1986.
[21](清)方文.嵞山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2]林鹏.丹崖书论[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94.
[23]尹协理编.新编傅山年谱[G]//.傅山全书(第7册)[M].,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5289-5290.
[24](清)傅山.傅山全书(第1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5]白谦慎.关于傅山研究的一些问题[J].文物世界2007(6).
[26]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11)[G]//.卢辅圣等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3册)[M].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329.
[27]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77-78.
[28]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8.
[29](清)傅山.傅山全书(第7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476.
[30]白谦慎.文人艺术家的应酬——从傅山的应酬书法谈起[N].中国文化报2015.10.25(6).
[31](清)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G]//.郝树侯.傅山传[M].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110.
[32]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3:164.
[33]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94.
[34]欧阳修等撰.旧唐书(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2680.
[35](清)傅山.起用杜句戏作(之三)[G]//.傅山全书(第1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174.
[36](清)傅山.村居杂诗(之十)[G]//.傅山全书(第1册)[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272.
[37](清)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奠高董君墓志铭(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842.
[38]侯文正.傅山传[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312.
(责任编辑:夏燕靖)
J209
A
1008-9675(2017)03-0034-06
2017-01-20
郑付忠(1982-),山东人,长沙师范学院书法系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