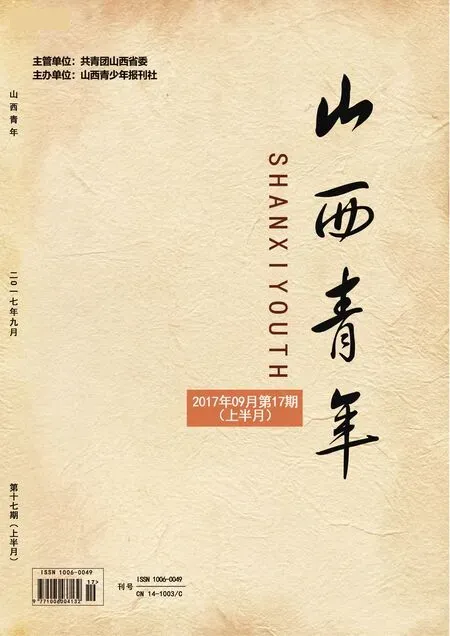浅析《呼兰河传》“瘟疫”社会整体意识下的个人悲剧
江 浩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浅析《呼兰河传》“瘟疫”社会整体意识下的个人悲剧
江 浩*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从《呼兰河传》作品本身的故事上,它不仅仅是部小说,同样是部人物与社会矛盾冲突的戏剧。“瘟疫”的社会如同一方死城,它的死气并非来源于人的身体,而更多地指向社会群体意识,人们愚昧麻木、精神腐朽,活着时却已经死了,却要留下这“死尸”在活人的世界传播“瘟疫”,因此,呼兰河小城里游荡着的鬼魂,早已使大多数人变成没有灵魂的傀儡。而个人的遭遇,终也在这场“瘟疫”蔓延中走向悲剧,个人愿景在腐朽的社会意识下丝毫没有依托,只要轻轻一下,就彻底毁灭!
“瘟疫”;社会意识;挣扎
一、“瘟疫”由心生,再侵蚀人心
呼兰河是一座小城。小城里的人,生活呈现着反复、反复、再反复的过程;城中的大泥坑,人们深受其害,却常因其发生的一些事而津津乐道,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两条福利:一是常常抬轿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是居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又经济、又不算不卫生的瘟猪肉。因此,人们倒也不去填了。似乎小城的人已经彻底沦为麻木不仁的木头。
为何成为一堆木头?因为人们没有生存的意义,他们生来就是等待死亡的,这使得他们对生命极其漠然。呼兰河的人生来是卑微的,漫无目的的,这群人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不知道谁创造了自己。他们的心中没有敬畏,没有对美好的向往,一场心灵的“瘟疫”便渐渐在这世代死寂的城中滋生。
究其原因是人们心中缺乏美,因此“瘟疫”便放大了人性之中理所当然的恶。“作为抒情小说的《呼兰河传》,通篇弥漫着凄婉寂寞的情绪。”[1]这种理所当然的人性恶体现在“大泥坑”、“跳大神”和“洗热水澡”,人成为一种深受封建社会毒害的毒物,他们理所当然地散播着罪恶。“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如此振振有词,如此“善心”洋溢,所做之事,却渐渐都是“吃人”的事,而他们也仅仅是小城中的区区几个典型而已。这群被毒害而扭曲的心灵的人成为了呼兰河的主体,如此,呼兰河便已成为“瘟疫”横行的人间死地。
二、“瘟疫”泛滥,集体无意识下的罪恶行径
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由于活泼开朗,婆家便将她视为怪物,遵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古训,进行残酷的规训。毒打、“跳大神”、“热水澡”。而那些东家的婶子、西家的大娘等“善心”的“看客”乐此不疲地将小团圆媳妇折磨得死去活来。“看客”们“于是人心大为振奋,困的也不困了,要回家睡觉的也精神了。他们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结果小团圆媳妇被活活烫死了。这群人正践行着“吃人”的行径,却对此感到无比的正义,无比的欢愉,殊不知,当整个社会成为一所精神病院时,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悲剧。
小人物之有二伯,是长工,在“我”家一做就是30年,而且没有工钱。他是个老实质朴的人,代表一种单纯老实,然而有二伯身处被奴役的地位,十分可怜,但他毫无觉悟,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东北阿Q。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埋葬了小团圆媳妇之后,他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如有二伯这般的人也终于因为无所依托而被整个“瘟疫”所侵害,变得没有追求没有善恶之分,变得虚伪。
这一群看客就是这城中最主体的行尸走肉,最为扭曲的群体。当社会意识终成为了毒物,小人物的美与善最终无奈地被侵蚀,毫无反抗之力!
三、挣扎无力及美与善的寄托
以小团圆媳妇和有二伯为例的小人物一方面拥有善与美,另一方面由于整体意识病态而显得挣扎无力最终不得不沦为悲剧;当整体显得死寂的时候,呼兰河中还是否有美与善呢?
美与善的寄托体现在了儿童与老人身上,祖父与“我”。祖父是个慈祥友爱的人,“我”从祖父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俗世之外的家的温暖,平静、安宁。可是祖父毕竟是年老之人,即使代表了美与善,却为这世俗所隔离,这种美与善不会持久,对整体意识不会有冲击。另一方面体现在“我”的身上,我是一个童真的孩子,并以孩子的视角来目睹着呼兰河城内所发生的一切,“我”天真、活泼、可爱、顽皮,所以在众人都说小团圆媳妇有病的时候,只有“我”说她没有病,也只有我跟小团圆媳妇玩,人们说小团圆媳妇是妖精,睡一觉头发就掉下来,“我”也说这是剪刀剪的。“我”的话揭露得是事实,“我”的身份却是一个孩童,所以一切的言语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矛盾也是一种无力。同时孩童的天真虽然是天赐的,却同样有着有二伯那种无法冲出群体心理病态现状不得不妥协的遭遇,这种童真也许并不长久。“然而正是由于运用独特的儿童视角,在表现快乐幸福的童年生活的同时,才更加反衬出萧红内心深藏的悲凉与寂寞。”[2]
当整体的心理病态麻木扭曲的时候,是否还有唯一幸存者呢?
冯歪嘴子的最后出场是个人意识觉醒最后寄托,是挣扎者典型形象的体现,他不搅和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事情,即便邻里拿他开心,他也根本不介意。他安静地选择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即便生活再艰辛,也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与这个病态的群体保持距离。他朴实善良,会偷偷给“我”吃免费的黏糕,好好照顾老婆尽着丈夫的责任,对嘲笑他的邻里也丝毫不介意。冯歪嘴子并不是与群体格格不入,他是入世,一方面又维持着自己的清醒,他的形象是个人意识在这个小城内唯一的代表,同时也是觉醒着的典型。
小城里的人大多都是死了的,他们没有了灵魂,甚至是“吃人”封建制度的代表,而最终的悲剧在于整个社会群体的意识都已经麻木不仁,深受毒害,当所有的地方都被“瘟疫”所笼罩,那些仍然保有几分清醒的人该是何去何从呢。那些仅存的善与美就成为了这些“吃人”者攻击的对象,成为一个个悲剧。呼兰河小城成为了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斗争的剧场,在这一部记叙性的戏剧中,群体意识的主体病态毁灭着那些仅存的善与美,却又呼吁了个人的挣扎永不停止,哪怕牺牲也要反抗的觉醒意识。
[1]谢海平.一串凄婉的歌谣——论萧红的呼兰河传[J].理论学刊,2004(5):114-115.
[2]杨秀江.论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儿童视角[J].泰山学院学报,2010,32(1):68-72.
江浩(1994-),男,四川凉山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I
A
1006-0049-(2017)17-026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