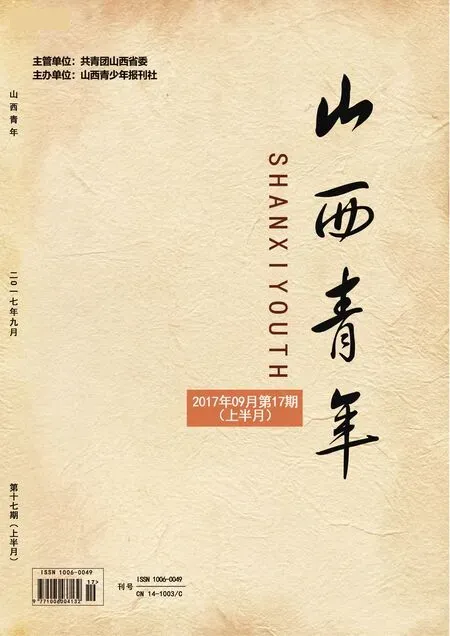性别差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状况研究*
徐莎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广东 东莞 523808
性别差异: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状况研究*
徐莎莎*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广东 东莞 523808
本文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访谈了7名女性6名男性社工,发现其各有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状况,女性社工的倦怠感受多源于对工作有效性的失望,男性社工则比较多来源于自己的男性身份在社会中承受的压力;女性比较主动使用来自家庭、同事的支持,而男性应对职业倦怠状况的支持来源比较单一。在以上发现的基础上,文章还对社工机构提供组织支持提出了建议。
职业倦怠;女性社工;男性社工;社会支持
职业社会工作在内地的发展已经超过十年,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服务从基础到层次丰富,这与奉献爱与热情的社会工作者密不可分。在高强度的情感付出和压力工作下,社会工作者已成为职业倦怠的易感人群,而这一现状也已引起业界的关注。
一、文献回顾
Freudenberger在1974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这一概念,指当工作者因为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强度大而感到情绪枯竭、筋疲力尽时,就会产生职业倦怠。Maslach认为这是一种症候群,包含三个方面:情绪衰竭——在助人工作中投入过多情绪,透支后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工作热情完全丧失,这也被认为是症候群的核心;去个人化——个体以一种麻木、冷漠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事或受助者;低个人成就感——个体对自己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都评价很低。Hansung Kim(2011)等提出,职业倦怠程度高的社会工作者更多地发生头痛、肠胃疾病等身体不适,Farber指出,有强烈的离职意向是倦怠的典型表现之一。
国内近年来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也多有关注,黄文斌(2011)在调查研究中指出,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程度较为严重,李静静(2014)在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武汉、重庆等七个城市的250名社工为样本的研究中,认为社会工作者出现轻度职业倦怠。对于造成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的原因,李静静认为性别因素与职业倦怠状况无关,而孙铁、黄文斌在各自的研究里则认为相关,且都是男性社工的职业倦怠得分高于女性。任云霞(2013)提出,相较于本科生,研究生学历的社工去个性化程度最严重;工作资历久的工作者,倦怠状况相对低。社工缺乏社会支持也会增加职业倦怠(石亚、史天琪,2013)。
现有的研究,多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年龄、资历、学历、性别等人口学因素都被讨论,但其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有不同的定论,尤其是性别因素,本文在其后将重点分析。社会支持对于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有干预作用,而男女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支持的获得上会否有不同,与其职业倦怠状况有什么关联,本文也会探讨。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来了解不同性别的社会工作者在情感衰竭、去个人化、低成就感三方面的感受,及其获得社会支持状况,对其职业倦怠状况产生什么影响。
从15年11月至17年4月,笔者共访谈13人,7名女性,6名男性,访谈对象工作年限从半年到七年不等。
三、研究发现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男女社工都存在或轻或重的职业倦怠状况,在情感衰竭、去个人化、低成就感三方面各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男性社工和女性社工在职业倦怠状况上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
(一)整体状况
13位访谈对象中,除一位社工表示还未有倦怠症状外,其他社工都表示自己曾有过或正被职业倦怠症状困扰。
德力,项目社工,男性,工作五年。他表示自己算是职业倦怠症状的康复者。“两年前的时候最为严重吧,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想上班,坐在电脑前,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做不出来,感觉很焦灼。不得不做的工作就随便应付。”德力觉得自己很糟糕,工作没有意义,想要逃离。但因为“没有想明白离开去干什么”,德力留了下来,捱过倦怠症状最为严重的时期后,情感衰竭和去个人化状况减轻不少,“工作中我会主动地考虑项目发展的许多问题,比如执行,比如成效。”
陈及,女性,是某家综的中心主任。“我感觉倦怠是一直都有的。工作方法可能就简单粗暴一点,像上一次跟那个志愿者急起来了。”对待服务对象方式缺少温情关怀、冷漠、粗暴是职业倦怠症状中去个人化的表现。
达哥,男性,从事社工服务半年,他表示工作很开心,和服务对象相处也很融洽,专业能力上还有很多想要学习的地方。他是访谈对象中唯一一位表示没有任何倦怠感受的社工,除此外,男女社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情感衰竭的折磨,去个人化及低成就感带来的挫败情绪。
(二)男女社工的倦怠特点
文意,女性,社区社工,做妇女儿童服务已经六年,经历了很多对社
工行业的失望。“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社工服务真的很乱,上面的制度设计,下面的服务执行……其他项目点跟我们分享经验都是说如何把文书写得漂亮一点,但实际上对这个服务对象有什么帮助什么影响,没有人关心。”文意说社工理想的火种在心中逐渐熄灭,也许还会残存一个星点,其余的热量都已被现实耗尽。在服务中,经历了情感衰竭后她也开始变得敷衍应付,出现去个人化症状,进而出现对自己成就低评价。
小甲,女性,项目社工,做儿童教育服务三年,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担忧让其对自己的工作也产生怀疑。“我觉得自己做得越来越不像社会工作了,我也常常觉得强调的那些理念、方法…真的有用吗,在实际的服务中,用不上。”对工作成效的怀疑也让她萌生离职的想法。
男性社工不同的是,他们在提及倦怠症状时,都会说到自己经济上的压力。新一,男性,从事社区服务七年,他说自己是把社工当做一份工作来做,七年间他有过两次离职计划,希望能去到有更多薪资回报的地方。“很巧这两次都没有走,因为机构也都及时给了一些(薪酬)支持……我们在社工这个圈子里可能感受还不多,出去外面社会,就能很明显感觉到(经济地位)差异。”新一说近年不太愿意春节回家,因为不想被亲戚盘问工资,“这个社会的评价标准还是看钱的,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性”。
小李,男性,司法社工,从业两年的他直言自己感觉很辛苦很累,尤其是每个月的工资不够用时,就更加觉得疲惫烦躁了。“我会努力去考到社工证,看能不能晋升,多一点补贴,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不做了。你要是一个女孩子一个月这点钱其实都没所谓的,我一个男生,肯定不行的。”
女性社工的倦怠症状主要源于对社会工作助人成效的怀疑,进而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个人成就持负面态度,产生倦怠情绪;男性社工以一个“社会中的男性”的身份去衡量自己的工作成就,而男性这个角色被赋予的期待和要求,加重了他们的负面情绪,使其倦怠症状更为严重了。
(三)男女社工应对倦怠状况的社会支持
职业倦怠会让社工感觉到精力透支、情绪低落,失去热情,面对这一症状的影响,社工们在一开始也会寻求自己身边的支持资源,在这一方面,男女社工也有不同的表现。
阿玉,女性,为外来务工群体服务,她的丈夫也是社工,两人同属一个机构,她有感受到来自家庭的很多支持。“我婆婆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她觉得很好啊,也很支持……她现在也有帮我们带小孩(六个月大);我老公,我们平时就是互相吐吐槽咯,抱怨发泄完就再继续工作。”与其相似的是林一,她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跟家人科普社会工作的内容,丈夫和公公婆婆都觉得很有意义,对她的工作表示赞赏,这也是她在有倦怠感受后还能继续坚持的原因。同时,女性社工这一身份也给她们带来社会认同感。比如从事残疾人服务一年的安妮,“大家会觉得你很有爱心,也比较稳定,好像是政府工,社会地位还可以。”她有轻微情感衰竭,但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也给她一定的安抚力量。
男性社工在应对倦怠症状时,家人并不是其寻求支持的首选,因为“跟他们说了,也不懂,也不了解”(德力),以及“跟她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她又会担心,我又要反过去担心她”(新一)。男性社工与家人的沟通不如女性社工主动,家人对其工作的了解比较少,不能充分理解其倦怠感受;因为主流文化中对于家庭角色的期待,男性社工们都对自己有承担压力的要求,因而选择不跟家人谈自己的倦怠感受。另一方面,男女社工在是否寻求同事支持上,也有差异。星哥,从事流动人员服务,工作七年,“跟朋友说比较好,因为有些时候你的倦怠感受就是来源于你的同工……社工这个圈子很小的,你跟同行讲一讲别人就知道是什么了”,男性社工在遭遇情感衰竭症状时,会愿意向与社工无关的朋友寻求支持,在放松娱乐的互动中获得能量。而女性社工则非常愿意跟同事表达,“很累的时候,就跟同事说一说,就感觉心情好一些……至少感觉有个伴,还一起(奋斗)的”(文意)。
在访谈中,社工都表示,机构/组织没有特别为缓解他们的职业倦怠感受提供帮助。
四、结论及建议
笔者通过对13名社会工作者的访谈,了解到大部分社工都存在或轻或重的职业倦怠症状,如感觉到异常疲惫、抗拒工作、强烈的离职意向、怀疑工作成效等;而男女社工职业倦怠症状则各有特点,女性社工多因为对社会工作这一助人服务成效的怀疑,而对自己的工作价值、工作意义持负面态度,产生倦怠情绪;男性社工因为自身的性别身份,感受到社会文化的压力,使其倦怠症状更为严重了。在寻求社会支持以应对倦怠状况上,女性社工能主动使用来自家人和同事的支持,而男性社工则回避向家人、同事寻求支持,支持来源局限于朋友。
职业倦怠会对社会工作者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其工作服务质量,对组织和行业发展都具有一定威胁,这也是当前社工机构需要直面的问题。从缓解社工职业倦怠的角度,笔者据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有帮助:1、加强组织支持:社工机构、行业组织应重视给予社工精神慰藉关怀,主动进行筛查和帮助,尤其是对于男性社工,使组织支持、同工支持成为其缓解职业倦怠症状的有效资源;2、对女性社工:可多组织有关社会工作内涵、价值的同工探讨会,以回应女性社工因成效质疑而产生的倦怠感受,丰富其应对倦怠症状的资源;3、对男性社工:可多组织家庭联谊会,促成男性社工家人对其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并缓解其性别角色带来的压力,从而减轻其部分职业倦怠感受。
[1]Freudenberger,H.J.Staff Burnou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74(30).
[2]Christina Maslach,Burnout:The Cost of Caring.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c,1982.
[3]Kim H,Ji J,Kao D.Burnout and Physical Health among Social Workers:A Three-Year Longitudinal Study.Social Work[serial online],2011(7).
[4]李瑶.社区工作者职业倦怠表现与原因研究[D].兰州大学,2015.
[5]孙铁.西安市一线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D].西北大学,2015.
[6]石亚,史天琪.社会支持视角下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01):150-152.
[7]任云霞.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倦怠状况的调查——以深圳社工为例[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40-45.
[8]李静静.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评量、因素鉴别与干预策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9]黄文斌.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1.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15d03)的研究成果。
徐莎莎(1988-),女,四川达州人,硕士,东莞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会性别。
C
A
1006-0049-(2017)17-0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