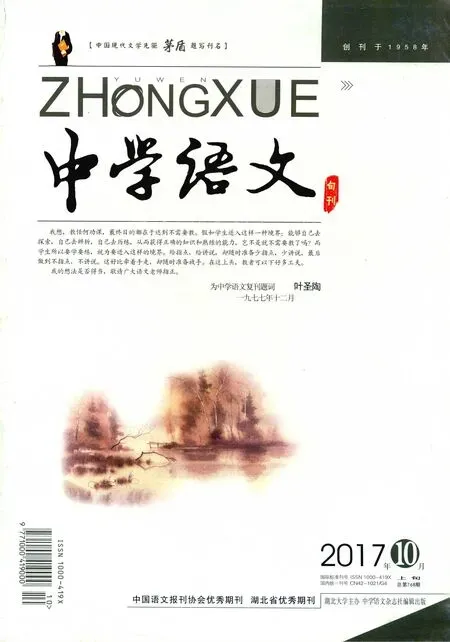试析白居易《琵琶行》的叙事性
刘自歆
试析白居易《琵琶行》的叙事性
刘自歆
白居易《琵琶行》(以下简称《琵》)自产生以来,便声誉鹊起,从唐宣宗所赞“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至清人张维屏感叹“开元法曲无人记,一曲琵琶说到今”,并且成为后世戏曲题材的重要选择,可谓流传广泛,影响巨大深远。不仅如此,它也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传统经典篇目,被选入人教版教材必修三中,足见其地位和价值举足轻重。但是,很多教师对其应该怎样解读并实施教学,特别是对它的叙事性缺乏自觉的认识,常常陷入解读误区和偏狭之中。倘若沿着叙事性的角度,在我国传统叙事理论基础上,借鉴符合《琵》文本要求的西方叙事学理论给予整体审视和细读,更深层次地挖掘曾被忽略的叙事内涵,那么,或许会发现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和解读途径。
一、文体特征和叙事性弱化
《琵》中的“行”,源于汉乐府与古诗,是古诗中的一种体裁。《琵》又被称为《琵琶引》和歌行体叙事诗。南宋姜夔较早的阐释过各诗歌题名意义:“守法度曰诗,载始末曰引,体如行书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①明代徐师曾《诗体明辨》解释道:“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也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他们都共同指出这种“歌行体”的诗歌,具有兼容叙事性和抒情性的特征;至于在一篇中孰轻孰重,则应具体文本具体对待,而《琵》具有借事传情、因情传事的突出特点,即使叙事,也是在抒情下的叙事。《琵》称“长庆体”是始于宋人,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其特点是叙事性的律化的长篇七言歌行,但并非是单纯的叙事,而是在抒情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抒情风格的叙事诗。美国学者王清献将《长恨》《琵琶》与《孔雀东南飞》比较后说:“文人作诗看来更多地倾向于根据他的情趣与哲学事件作出解释,而不是通过严谨详实的情节来复述故事。”(王清献 《唐诗中的叙事性》出自《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可见,《琵》的重心在于表达诗人的情感,白居易曾旗帜鲜明地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诗歌矣。”(《策林》六十九)
正因为如此,在语文教学中,本该与抒情性同等重要的叙事性,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弱化),甚至被漠视,即使对叙事性有所涉及,也仅仅停留在粗糙的勾勒概括上,严重缺乏在叙事视野下的情节结构、故事人物以及音乐描写、景物描写和故事人物的关系诸方面的整体细读和深入探究。这种现象除上述文体原因外,还存在着种种复杂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从《琵》的接受史和批评史来看,学界始终注重其抒情性和社会政治意义,而轻视其叙事性和系统的叙事学理论建构。我国叙事诗并不发达,到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才集中出现了一批叙事诗,“中唐诗坛开始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就是正统文学的趋向终结和市民文学的兴起。于是诗歌从内容到语言上都出现了新的转变。”②事实上,真正确立和形成《琵》叙事诗地位的标志是明代戏曲评论家何良俊的评论:
初唐人歌行,盖相沿梁陈之体,仿佛徐孝穆、江总持诸作,虽极其绮丽,然不过将浮艳之词模仿凑合耳。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五《诗》二)
直到清初贺贻孙《诗筏》方认为,如《琵》诸篇“才调风致”“描写情事,如泣如诉”,“长庆长篇”这一文人叙事歌行体才得以公认。但是,这些评论只是宏观性的且十分注重其抒情性,至于《琵》的叙事性有何具体特征庶无评说。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至叙事的文学,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③《琵》叙事性得不到足够重视的原因由此可窥一斑。
其次,之所以弱化或忽略《琵》的叙事性,与语文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有关。《琵》的教学目标和重点,在于识记背诵、语言理解、思想情感把握及艺术手法鉴赏,乃至从作品的社会背景出发,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当然这些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客观上冲淡了对其叙事性特征的认识与把握。强调它的抒情性,并不意味着舍弃其叙事性,相反,要把抒情性与叙事性相提并论,也就是说一定要确立关于叙事性的教学目标,这才是语文教学对待《琵》解读的科学态度。
第三,在叙事学和文体学理论指导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教师在研究和实施《琵》教学时,难免会弱化或忽略其叙事性。《琵》的叙事性首先体现在“序”上,诗序是故事梗概的单纯叙述,而“歌行”则是对故事梗概的铺展曼衍,描写委曲周至,叙事抒情错综兼容。诗序的原初功能正是为了弥补诗歌在叙事上的不足,所以要研究《琵》的叙事性,务必把诗序切实落实在“歌行”中。另外,还可以把《琵》与白居易同题材的《夜闻歌者》比较,与其他作家同题材的叙事诗相比较,从而提出诸如以下问题:《琵》是不是情节平淡单纯?如何通过叙事手段刻画人物形象?它的叙事结构有没有独特的地方?极古今才人之力的音乐描写只是为了突出歌女的技艺高超?景物描写在叙事中有何意义和价值?对于这些问题,如果给予一线教师实质性的科学指导,恐怕叙事性和抒情性将会成为同等重要的诗教两翼。
二、视角转换与叙事结构
申丹教授在考察西方叙事视角的分类和部分代表性作品之后,纠正了当代西方叙事学界关于“叙述类型”的偏误,给叙述类型作了四大类的划分。(1)无限制型视角(即全知视角);(2)内视角(包含热奈特提及的三个分类);(3)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以及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视角);(4)第三人称外视角(同热奈特的“外聚焦”)④。根据申丹教授的界定与划分,结合《琵》文本叙事事实,《琵》有两种叙事类型:全知叙述视角和人物限知视角。但要特别说明,《琵》中歌女属于人物限知视角很好理解;《琵》是叙事诗,不是小说,它排斥虚构,追求“言直而切”“事核而实”,即叙述的是真人真事;那么,诗人作为全知叙述者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又有故事中江州司马的人物身份,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追述自己被贬后的经历与体验,这样,江州司马的追述当属于人物限知视角,也就是第一人称外视角。为了避免混乱,暂且把诗人对整个故事的叙述作为全知视角,而文中以江州司马身份出现追述往事的作为人物限知视角。所以,《琵》具有了双重叙述视角的特点,那么它是如何运用双重视角安排叙事结构的呢?这种结构在文本叙事中究竟有何意义和价值?
现代诗学认为,叙事诗的核心是事件,完整的事件和情节是其艺术生命之所在。《辞海》(文学分册)就认为叙事诗“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有故事就有开始、过程和结局,就有人物、情节和环境,就要连贯一个或一系列的事件。《琵》也正是如此,它有以下故事情节组成:送客盆浦口;邂逅琵琶女,使快弹数曲;琵琶女自述身世经历;江州司马自述“出官”情境,并“歌以赠之”;歌女感我此言再演琵琶。《琵》开头以全知视角叙述盆浦口送客,于“惨将别”之际,忽闻琵琶声,“客忘归”,“寻”“问”“移船”“邀”“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这些外部行为全知叙述者自然知道,歌女弹奏“曲调含情”,象说尽“心中无限事”,全知叙述者尚且作了交代。紧接着全力外聚焦大段的音乐描述,共有20句,然后突然转换为人物限知视角,包括歌女自述和江州司马自述,诗歌结束又转换为全知视角的叙述,歌女感我此言,再演琵琶。毫无疑问,诗歌具备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这个情节不但不平淡单纯,反而是波澜起伏,跌宕有致,其原因正在于两处人物限知视角的叙述。琵琶女“自言”身世经历,叙述从才、色、被捧、自我狂态,到被弃;不但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而且人物形象逼真丰满,栩栩如生。再看江州司马自述,三处“我”即故事中人物,追述谪居以来的情境与内心感受。地势“低湿”“黄芦苦竹”“鹃啼猿哀”“山歌村笛”,这是内聚焦于人物所处环境;“叹息”“取酒独倾”直至“青衫湿”,此乃人物情感的流露,何尝不是层次分明、结构严密、波澜起伏呢?迁谪之人的苦况,还能用什么方式比这样表达更真切的呢?再把这种人物限知视角置入全知视角叙述中,事件连贯完整,叙述起承转合,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琵》“为古今长歌第一”当之无愧矣。
不仅这样,同白居易《夜闻歌者》、元稹《琵琶歌》、李绅《悲善才》相比较,更见《琵》视角转换和叙事结构的独特性。这三篇完全是以全知视角的方式叙事抒情的,故事平面化,缺乏变化,而且人物始终是“被聚焦”的对象,总不如《琵》那样“事核而实”。特别是陈寅恪先生对先于《琵》的元稹《琵琶歌》的一段论述,极为精辟深刻,他说:《琵》“则既专为此长安故倡女感今伤昔而作,又连绾己身迁谪失路之怀。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岂微之泛泛之作所能企及者乎?”⑤陈先生虽然强调《琵》是借歌女之事表达诗人专一的情感,批评元稹一诗两用,情感不如《琵》真实;但也明确地提示了人物限知视角在叙事结构中的暗合性。他对李公垂《悲善才》一诗评价,“但若与乐天之作参互并读,则李诗未能人我双亡,其意境似嫌稍逊。”⑥意境是要靠叙事来营造的,同样,《悲善才》的叙事也是逊于《琵》的。
最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在《琵》叙事结构中,有三处景物描写,它们分别是: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明月江水寒。通常人们强调以动衬静的表达技巧和各自的表达效果,如果从叙事性的角度加以考量分析,还可作如下补充。申丹教授在分析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一个插章中的景物描写时说:“描写停顿,即从身处故事之外的叙述者的角度进行景物描写,这种描写仅仅占据文本篇幅,而不占用故事时间,因此被视为故事时间的‘停顿’。”⑦《琵》的景物描写当然也可以这样界定,但又有其独特个性:一是前二者是处在全知叙述视角下的景物描写,第三者则是处于人物限知视角下的景物描写,三处景物描写所在文本位置各不相同;二是都有暗示故事或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三是都有景中寓情的特点。第一次景物描写既表现送客离别时的空阔环境和怅然之情,又暗示将有新的故事发生,下文“忽闻水上琵琶声”中“忽闻”则暗示了事件突然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而引出“主人忘归客不发”直至“千呼万唤”的一系列情节,景物描写兼具造成悬念和叙述过渡作用。第二次是在大段音乐描写之后,“唯见”说明琵琶声停,万籁俱寂,人们沉浸在音乐营造的虚幻缥缈的巨大空间里,这样的情景终不能永久,下文聚焦歌女“沉吟”的神态,“放拨”“插弦”“整顿衣裳”“收敛”的动作,然后是人物自述。此处景物描写在故事叙述中具有既收又转的作用。歌女自述中的景物描写,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暗示歌女的孤寂、冷落、悲苦伤感,在结构上有前后照应的作用,下文“夜深忽梦”事则是沿着“守空船”叙述的,“梦啼”不正是景物描写所暗含的伤感吗?
总之,语文教学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意识到这种描写停顿的叙事结构意义,忽略景物描写的暗示性,即忽略描写停顿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三、双重暗合与音乐兴寄意义
《琵》的第一重暗合是指“同是天涯沦落人”,即诗人与歌女“沦落”之相似点,这一点极其显而易见。不但诗序交代清楚,而且文本也是循着诗序的叙述加以呈现的。《唐宋诗醇》所评:“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极为确当。袁行霈先生说:“琵琶女和诗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同,两人的遭遇也各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属于不同的社会问题。但诗人还是把她引为同调,引为知己,说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深挚的话来。”⑧“洪迈引白诗另一篇《夜》作比较,说明《琵琶行》盖取相类事件以‘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不为无见。”⑨所谓“相类事件”乃同是“沦落”之意。这种暗合主要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的,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两人身世遭遇的仿佛性,歌女昔日艳盖群芳,艺压京城;白居易早年进士及第,授翰林学士,关心并参与国家大事。歌女命运转折在年老色衰,继而远离长安,漂泊在外,独守空船,在生活上被抛弃;诗人以诗讽谕政治,得罪权贵,又因越职言事,被贬江州,抑郁愁苦,在政治上被抛弃。二是音乐作为媒介使两人情感得以沟通,歌女以音乐表达情感,诗人以听众身份感受到音乐所寄托的情感,从而,音乐使诗人和歌女处于平等相怜的知音位置上。
不管读者从哪个角度赏析,都对这种暗合给予了高度关注,语文教学同样重视并落实了这一教学重点。一方面音乐描写的表现手法和表达效果,例如,比喻、拟声词、以无声衬有声、渲染等;另一方面注意音乐情感的传输。当然这些鉴赏是十分重要而准确的,但值得引起关注的还有,音乐描写在文本叙事结构中处于突出而重要的位置,它究竟与歌女的“自述”有什么关系?继而与主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什么关系?这也许是被人们无意忽略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细绎文本,笔者认为,音乐描写使用兴寄手法,与歌女自述构成第二重暗合关系。
陈子昂的“兴寄”说强调内容上言此意彼的寄寓目的,不仅有深厚的寄托,还要有广泛的意义而不专指某一具体内容。白居易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在《与元九书》中称新乐府诗是有关“美刺兴比”的,《唐宋诗醇》评《琵》曰:“比兴相纬,寄托遥深”,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专指第一重暗合,“兴寄”内涵的价值判断总是倾向于社会政治的理性批评,其实,“兴寄”在表现手法上不拘泥于一定要用比兴,内容上也不一定受儒家讽谕美刺观念的局限。那么,《琵》又有怎样的兴寄内涵呢?这20句音乐描写可分为四个乐段,饱含深厚的兴寄意蕴。“转轴拨弦”六句,其特点是旋律低沉、苦闷抑郁,又“似诉平生不得志”,又欲“说尽心中无限事”,与歌女当前心情吻合,暗含歌女当前不幸遭遇。“轻拢慢捻”七句,乐曲特点是激越而欢快,顺势暗含了歌女因才高貌美而被宠的人生经历。“幽咽泉流”五句,乐曲变为“冷涩”“凝绝”直至“暂歇”,恰好寄寓歌女年长色衰、门前冷落、嫁做商人妇、悲苦孤守的经历际遇,以至于愤懑无语,悲戚无声。“银瓶乍破”四句,乐曲突然爆发为刚劲雄壮的旋律,正寄寓了歌女当前的不平之情,回应第一乐章。而且这些描写是置于“歌女自述”的前面,先叙音乐,再言人生际遇,岂不是“兴”的形式体制?因此,音乐描写不仅表现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巧和音乐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不仅表现了诗人描摹音乐无人超越的技巧和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音乐描写采取兴寄手法,在叙事结构中形成第二重暗合关系,托寓遥深,树意丰厚,文理细密,毫发俱应,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琵琶女借助音乐的叙事语言和音乐形象,暗合身世经历,兴寄自我情感。白居易作为叙述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感悟来欣赏音乐,并对音乐产生了强烈共鸣,继而进行再创作,以诗化的语言叙述关于音乐的故事且借此寄寓迁谪之意,使歌女身世经历暗合诗人迁谪经历,从而着重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喟。
①姜夔.《白石道人全集(诗说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林庚.《唐诗综论》.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1页。
③王国维.《文学小言14》.《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上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0-221页。
④⑦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263页。
⑤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9、50页。
⑧袁行霈.《〈琵琶行〉 赏析》.《教师教学用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⑨谢思炜.《白居易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作者通联:安徽太和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