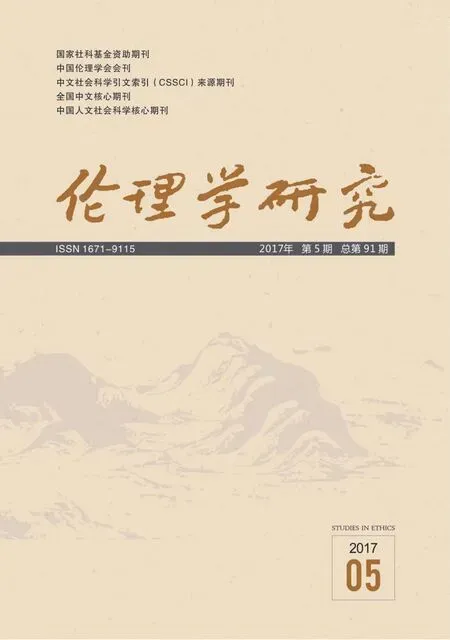论法律服从的多重辩护
张 秀
论法律服从的多重辩护
张 秀
在现代国家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服从法律是一项政治义务,而不是单纯的法律义务。公民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律,而是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辨认和确认法律的正当性,在服从法律的过程中推进法治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在现代国家推进法治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公民的政治义务,公民对法律的服从至少需要思考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公民的自愿性,如何提升公民的守法意识;其二是法律的正当性,即法律必须是正当的,符合正义的要求。
法律服从;自愿性;法律正义
在传统的治理形式中,特别是人治模式或者宗教统治下,受教权观念或君权神授观念的影响,公民(准确地说,臣民)对教会或国王颁行的法律服从被视作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至上原则。但随着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教权和君权的至上性被质疑进而被否决,相应地,对之的服从至上性也就瓦解了。而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特别在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公民守法问题?公民对法律的服从是一种绝对法律义务还是可辩护的政治义务?在现代国家的法律服从问题上,怎样才算合格的现代公民?这些问题成为近年来政治哲学讨论的热点问题。
一、法律服从:现代公民人格的基础
约翰·密尔说:“文明的第一课是学会服从”。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宪政法治为基础的政权组织形式特别重视培养公民的守法精神,公民服从法律成为公民一项基本义务,守法即是服从政治。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服从法律即是对公民自由的最大保障。法律如果不能体现公民的意志,不能为公民服务,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那么,法律就失去了规范的价值基础,公民可以要求重新修订法律。随着近代社会契约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公民对法律的服从成为现代公民的标志。然而随着政治哲学家对二战深入的反思,人们发现公民对法律的服从不应该是盲目的服从,而应该是审慎的服从,或者说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项法律义务,还需要考察公民法律服从背后的道德问题。
为什么说公民法律服从的义务不是一项简单的法律义务,而是一项具有道德意义的政治义务?很多人习惯地将公民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等同于“服从法律的义务”。譬如:美国学者理查德·泰勒认为政治义务即指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义务[1](P75)按照泰勒的说法,讨论政治义务就不具备独特的必要性,我们只需要辨明法律义务即可,但约翰·西蒙斯很不赞同。他指出“服从法律的义务”与“法律义务”有很大的分别,“服从法律的义务”是一种动态的价值表述,而“法律义务”只是一种静态的事实表述,其区别就在于前者涉及义务的道德性问题,而后者是与道德义务相对应的概念[2](P23)。他在《道德原则和政治义务》一书中指出“政治义务是阐述这种特殊的道德纽带(如果存在的话)之性质与范围的问题”[2](P2)。“服从法律的义务”是一种政治义务,是道德义务的一种,是要审查服从的道德性问题,就像社会义务和家庭义务是道德义务的一种一样。为“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提供辩护,并不是在法律意义上提供辩护,而是追问公民在政治共同体(国家)中负有的道德义务[3](P8)。道德性是政治义务的一个重要特性,具有构成性特征,缺乏这种道德性谈论政治义务会偏离“义务”的本质特征。单纯的法律义务并不是这样,单纯的法律义务关注的是实体法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法律要求我们不可偷盗,我们就有不偷盗的法律义务。所以,作为政治义务的法律服从追问的是履行法律义务的义务,如果从逻辑学的角度,这是一个二阶(second-order)义务,而公民对具体法律条款的遵守则是一阶(first-order)义务,二者是有分别的[2](P23)。
西蒙斯对公民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与服从法律的法律义务之间的等同关系的否定是非常必要的。西蒙斯说:“政治义务一直以来总是与公民观念紧密联系,也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在最低意义上成为‘好公民’的义务。显然,这个义务所包含的东西,要比仅仅服从法律来得多;它也包括以另一种方式支持国家的政治制度。”[2](P3)政治义务概念并不囿限于“服从法律的义务”,西蒙斯对政治义务概念做了“一般化”处理,从而使得“服从法律的义务”成为政治义务的部分内容,但是不能指代政治义务整体。在西蒙斯看来,政治义务与两种职责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是法律义务,它是一种针对“领土范围内的人”的职责;一种是公民义务,它是一种针对“国家中具体公民身份的人”的职责。认清楚这一点才能健全现代公民的内涵,全面认识现代公民为什么要服从法律?什么情况下公民有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公民如何对待非正义的法律或法律判决?
二、法律服从与公民守法自觉
服从国家的法律、缴纳税款以及保卫国家被视为现代公民基本的政治义务。公民具有服从法律的政治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公民不能为守法精神进行反思和辩护,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公民的守法是盲目服从。对公民法律服从义务最初的反思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但他却坚决不越狱,其理由是他认为作为雅典公民,他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国家、法律给予他出生、成长、受教育的环境,他应当尊重国家的法律。如果公民不经过国家、法律的同意就擅自逃离,这是对国家、法律的破坏。任何人都不能以不正当的方式生存,即使可以生存,也是不值得肯定的。
从苏格拉底的反思中,近现代的政治哲学家在法律服从问题上产生两个重要理论:其一是同意论;其二是公平游戏理论。同意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洛克,洛克指出人民的自愿服从源于主权取得的方式——人们相互达成的协议,这份协议是建立在公民同意的基础上的,“任何政府都无权要求那些未曾自由地对它表示同意的人民的服从”[4](P192)。法律是国家权力的体现,法律的运行是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方式,国家通过立法,建立法律秩序,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个人生活,实现个人自由权利的最大化,公民表达同意的重要方式就是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但法律是外在的规范,很多人守法的理由源于对法律惩罚的惧怕,如何将法律服从内化为内在的守法自觉呢?洛克希望通过同意这一形式实现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自我支配,自主立法,自愿守法。具体体现在:公民同意国家制定法律,维护公共秩序,并自觉遵守自己所定之法,这样公民在表达对立法的同意和守法的承诺后,服从的政治义务就应运而生。
对于同意理论,有人提出这样的质疑:法律是由公民制定的,公民有服从的义务,那么,如果法律不是公民自己制定的,公民就不需要服从了?比如:当立法者去世或者立法机构解散,所立的法律还存在,后继的公民有没有服从的义务?或者说除了公民自己立法产生服从的政治义务外,公民还基于什么样的道德理由服从法律?洛克说公民法律服从的同意表示也可以表现为公民对国家、政府所颁布的法律的认可,通过公民认可法律作为国家权力的体现而获得公民的服从。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每条具体的法律都需要征询每个公民的同意,这样的立法成本太高,也很难实现,但在组建政治共同体之初,“假定至少是有过一次全体意志的同意”[5](P18)。这“一次同意”就是建立政治共同体,产生公民认可、信任的政府,组建政治共同体后,建立在公民同意基础上的具体法律制度,就可以通过具体的立法程序产生效力。
洛克的同意理论把公民法律服从的道德理由建立在公民自愿性的基础上,这种自愿性基础并不以你实际表示同意为基准。如果你认可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权形式,而国家也维护最初契约所约定的公民自由、社会稳定,那么服从法律就是公民的政治义务,公民应该自觉守法。可是,也有人会提出疑义:我可以不同意吗?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在同意理论中,不同意的唯一途径就是退出政治共同体。如果你不愿意退出政治共同体,公民守法又是一种当然的政治义务,那么,你同不同意都应当守法。显然,这种解释让人觉得很无奈。于是,有学者希望从另一种角度来论证即使公民没有同意,但是国家很好地履行了国家职能,生活于其中的其他公民也很好地履行了维护政治共同体的义务,公民因基于公平的原则同样具有守法的义务,这项义务不以你的同意为前提,这种理论被称为“公平游戏”理论。
“公平游戏”理论最早由H.L.A哈特提出来,他说,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如果A按照规则,限制自己的自由,为共同事业做出贡献,且共同事业中的B、C、D……因为A对共同规则的维护而受益,那么基于公平的原则,处于共同事业中的B、C、D……同样负有服从共同规则的义务[6]。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这个共同规则就是法律。这个理论受到质疑,也同样备受关注。哈特之后,罗尔斯撰文《法律义务与公平游戏义务》试图修善哈特的“公平游戏”理论,将“公平游戏”理论与“正义论”联系起来。罗尔斯对哈特“公平游戏”理论最大的修改体现在[7](P118):
(1)罗尔斯将“公平游戏”理论与“正义论”联系起来,用“互利和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替代哈特理论中的“共同事业”。
(2)罗尔斯对合作者和不合作者或搭便车者(free rider)进行了细致的区分。
(3)罗尔斯强调公平游戏理论必须在一个“理性和民主的政治共同体”,一个“互利并且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中才能实现。
“公平游戏”理论主张公民之所以具有法律服从的政治义务,是因为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或共同事业)中,每个公民有自觉维护社会公平的义务。当我们的守法行为,维护了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安居乐业,那么作为受益的其他公民也同样负有自觉守法的义务,否则就是社会的搭便车者,就会破坏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会影响社会公序良俗的有效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是要制止这种搭便车行为,将社会秩序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显然,“公平游戏”理论不需要公民的同意表示,也不是基于对政府感恩图报,而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理由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不做搭便车者,因为搭便车者最大的道德问题就是对其他做出牺牲者的不公平。与哈特不同的是,罗尔斯的“公平游戏”理论将公民法律服从的义务从公民对国家、政府之间的服从,转接到公民与公民之间公平原则的考量,对这一转换,有学者提出质疑。譬如:周濂在《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一书中指出罗尔斯的这个转换很可能让国家和政府成为最大的“免费搭便车者”[8](P92)。这种忧虑是成立的,至少在公民和国家、政府间关系不明确的状态下是值得忧思的。但是,周濂所忧虑仍然是抛开公民与国家是依据契约关系而建立起来这个前提,在罗尔斯所讲的“互利而正义的合作体系”,这种状况是可以通过制度的设计而避免。当然,公平游戏理论仍然有理论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诺奇克的思想实验中提到,如果一种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体能够自愿并主动接受的(并非所有的公共利益都具有选择性),而只是恰好享受了其他公民法律服从所带来的好处,碰到这种公民选择的自愿性和公共利益的不可选择性相冲突怎么办呢?或者说,仅仅基于公平的理由够不够构成公民法律服从的道德理由?在法律服从的政治义务的争辩中,我们还需要特别重视法律本身的正当性及其规范效力的问题。
三、法律服从与法的正当性
自愿性特征只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法律服从的必要条件,并非充要条件。在上个世纪,德国纳粹时期的法律同样经过公民的同意,并受多数公民自愿服从,但这种法律服从行为却是一种“恶”的行为。因此,当我们反思极权主义的法律服从时,我们还需要认真考察法律服从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即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
什么样的法律被认为是正当的?哈贝马斯的主张备受关注。他指出考察这个问题需要严格区分法律的事实有效性与规范有效性[8](P37-38)。法律的事实有效性是指实体法在具体的运用中其作用效力来自规则自身或源于被接受的事实,这种事实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强制人们遵守而无需道德基础性价值的支撑,也被称为合法律性。法律的规范有效性则指实体性法律的效力不仅仅取决于法律存在的形式,还取决于法律的内容以及内容规则所包含的道德等实体性价值,也被称为法律的正当性①。考察法律的正当性主要是从后面这层意思来考察,即考察法律的规范有效性。那么,具有规范有效性的法律如何生成?哈贝马斯提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商谈法律程序,认为“只有那些产生于权利平等之公民的商谈性意见形成和意志形成过程的法律,才是具有正当性的法律”[9](P507)。一旦法律脱离这个程序,法律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就很难得到保障,法律容易滑向专制主义的深渊。当然,哈贝马斯诉诸的是一种严格的法律商谈程序,他对商谈的基础性条件作了系列的规定,公民通过反复商谈,充分论辩,逐步增强公民对法律的认知,法律在公民的充分商谈中,既不会曲解公民的意愿,也不会歪曲立法目的,同时还能让公民充分了解法律,使法律得到更普遍的服从。
尽管哈贝马斯非常重视商谈程序对法律正当性的辩护,但罗尔斯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在《答哈贝马斯》的书信中指出[10](P428),纯粹公平的程序只存在于理想的原初状态中,也只有在原初状态下,严格的商谈程序正义才能导出法律在结果上的正义。如果把这种理想的商谈程序运用到现实规则中,如何确立程序的有效,最终仍然需要诉诸“多数决”的原则。可是“多数决”原则本身是有缺陷的,多数是相对于少数而言,少数群体的正当诉求如何保障就是“多数原则”的最大问题。罗尔斯指出,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程序上的“多数决”,而应该充分论证正义本身,通过对正义的规范论证来辨别法律的正当性。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系统论证了正义二原则②,并指出法律只有满足正义二原则的要求才具有正当性。在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中,第一原则:自由、平等原则又是重中之重,第一原则必须在宪法中得以贯彻,违背第一原则的法律是不应当被服从的。因此,任何法治国家的宪法都是根本大法,程序最严格,内容最根本,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同时也必须得到最大多数公民的同意确认。宪法的正义性是确保整个法律体系规范有效的基础,但即使“宪法被看成是一种正义,法律仍然有不完善的程序”[11](P353-354)。法律的不正义在不完善的程序中很容易发生,如何对待这种情况下的不正义法律?罗尔斯的回答是:服从它,不从其缺陷中牟取利益,这是公民的自然责任。罗尔斯试图论证维护正义宪法是所有人的自然责任,而不是由自愿行为所引起的义务,这就是他所说的在一个接近正义的社会中,也很难避免不正义的法律和政策的发生,但只要这种不正义的法律不超过某种不正义的限度,我们维持正义的自然责任就约束我们仍然应该服从不正义的法律和政策,或至少不运用非法手段来反对它们[11](P343)。
四、西方法律服从理论的问题与启示
在人类法律发展历程中,对公民法律服从的辩护一直没有停止。公民是法律生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公民的自觉守法对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政治哲学家对公民法律服从的政治义务进行的多重辩护,不仅丰富了这个主题的辩护理由,同时也凸显出这个主题重要的学术价值。当罗尔斯极力证明公民有法律服从的自然责任时,这种自然责任理论也面临其他学者的追问。譬如:杰里米·沃尔德伦认为自然责任理论并未严格区分不同群体之间责任的大小和殊异。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具体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并非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身份、角色都是一样的,正如政治社会中会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在政治共同体中也会有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之别。从内部人员的角度,他们对共同体的诉求主要体现在政治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的冲突、合作、资源分配等问题,而内部人员更愿意自觉遵守共同体的规则、接受共同体的制约来维护共同体,但对于外部人员来说就不一样了。外部人员并不认同政治共同体价值和必要性,虽然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他们也未必认同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但迁徙并非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不能说如果你不认同政治共同体的价值,你就可以离开政治共同体。因此,对外部人员的基本要求仅仅是不从外部对共同体的规则运转进行干扰与破坏,而并不要求他们参与共同体规则的维护。所以,沃尔德伦认为外部人员并不具有法律服从的自然责任,内部人员有法律服从的自然责任也是因为其内部人员这一特殊身份产生公民与共同体之间的自然责任。即使在一个接近正义的宪政民主国家也无法证明所有的公民都自然而然就负有法律服从的政治义务。
虽然西方法律服从的理论争辩还在继续,但对于正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全民守法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关于公民守法义务的争辩与法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难题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公民自觉守法的道德意义与价值。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公民的自觉守法为前提,在一个复杂的政治共同体中,公民在自觉守法的行为选择上会变得异常复杂,这种复杂性一方面来自公民主观方面自愿主义的道德性难以完全展现;另一方面也来自客观方面对法的正当性的追问机制不够健全,实际可操作性仍有待加强。在西方的法律服从理论中,尽管辩护的理由不一样,但是对公民法律服从义务的辩护大多强调公民有服从国家法律的政治义务,同时也有审慎思考法律正当性与正义性的自然责任。在我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公民更应该认真对待守法的政治义务。一方面,我国一定程度上缺乏规则意识和法治传统,需要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让公民意识到公民自觉守法是公民基本的政治义务,也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初期,立法、执法、司法都可能出现程序上的纰漏和实质上的非正义性,作为现代公民在服从法律,特别是服从不正义的法律时需要认真思考服从不正义法律的限度、边界,并对健全法制、完善法治做出公民应尽的义务。公民在维护共同体的完善和发展时,对待正义和不正义的法律不能等量齐观:
(1)如果经过公民立法或公民认可的法律是正义的,公民有服从的义务,这是基于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与承诺而形成的对公民的道德约束。对于正义的法律,公民法律服从的政治义务是普遍的、毫无例外的。苏格拉底用生命捍卫的也是在他看来是正义的雅典法律秩序。如果一项法律本身是正义的,而司法部门却给出了错误的判决,这不能成为公民逃避惩罚的理由,公民所应做的是通过法律的申辩程序来修改判决。
(2)如果基于正义宪法前提下,由于程序本身的缺陷,所立之法是不正义的法律,虽然公民没有服从不正义法律的道德理由,但公民仍然不能像一个“搭便车者”一样逃避违法的惩罚和制裁,而是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矫正不正义的法律,这是公民维护政治共同体的自然责任。
总而言之,提升公民法律服从的政治意识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法治目标需要从公民守法的主客观要件入手,通过公民对法律的商讨、共议来增强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使法律贴近生活、深入人心;同时也要重视客观方面对法律正义性的审查,使法律的制定、执行和实施不仅符合正当性的程序要件,而且符合正义性的实质要求,体现公民的意志,维护公民的权利,促进公民自觉守法,建设法治国家。
[注 释]
①在以下的论述中,Legitimacy都被译作“正当性”而不是“合法性”,以区别合法律性(legality)。
②正义二原则:第一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第二原则是机会均等和差别原则。
[1]Richard Taylor,Freedom,Anarchy,and the Law: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Philosoph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3.
[2]A.John Simmons,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Obligation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3]R.M.Hare,Political Obligation,Essay on Political Morality[M].Clarendon Press,1989.
[4]乔纳森·沃尔夫.政治哲学绪论[M].香港:牛津出版社,2002.
[5]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H.L.A.Hart,Are there Any Natural Right[J].Philosophical Review,1955(64):175-191.
[7]J.Rawls,Legal Obligation and The Duty of Fair Play,in Collected Papers [M].edited by Samuel Free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8]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0]J.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11]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张 秀,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
上海市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民众对乡镇干部认同的差异与取向研究”(15BZZ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