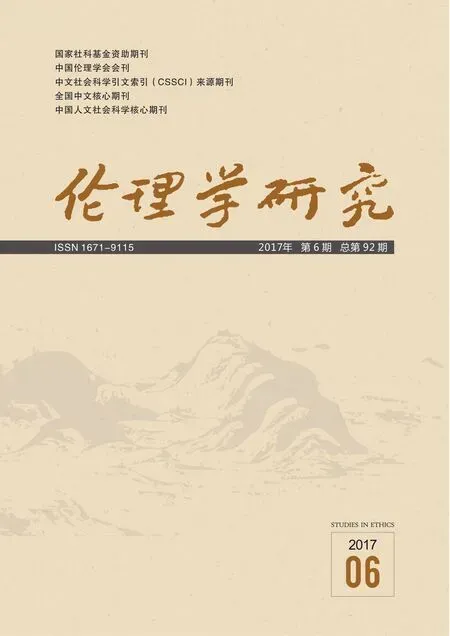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学锋
王船山义利之辨中的公私取向
王学锋
王船山义利之辨是与公私之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船山不仅对利作出了公利、私利的区分,而且对义也作出了公义、私义的区分,整体上要求重公义、轻私义,重公利、轻私利,故此提出了“循公废私”“存公抑私”等命题。与此同时,船山对个人私利亦作出了完全有别于理学的独到性分析,承认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尚公崇私”的伦理学命题,体现出一种早期启蒙的伦理倾向。船山这种“尚公崇私”论蕴含着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起来的因素,是对理学“贵义贱利”以及否定个人正当利益的批判性超越,而其公私论与义利论的结合则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
王船山;义利之辨;公私取向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议题,相对于其他议题而言,“义利之辨”具有提纲挈领之意义,亦是引起社会变革之强大思想引擎。王船山在民族兴旺、社会稳定、人民生存这样的核心问题意识引导下,对“义利之辨”这一传统议题表现出了一种“接着讲”的积极态度。我们知道,公私之辨历来就是与义利之辨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议题,甚至形成了以公私辨义利的思想传统。王船山并未像传统儒家那样简单地将公私作为判定义利的标准,而是主张在义利框架下重构公私观念,讲究公私与义利互训,“公私之别,义利而已矣”“公私之辨,辨于义利”[1](P300),对公与私的内涵作了较为深刻的甄别与剖析,因而在公私取向上也就呈现出了多层面的立体性价值表达。王船山的公私之辨思想十分深刻,既有对传统的合理承继,又有立足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特质,体现出一种“集千古之智”与“推故而别致其新”于一体的深厚历史价值,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一、“循公废私”的价值确证
从义利公私之辨的角度,王船山提倡“循公废私”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点看似与传统儒家主流价值观一致,而事实上又存在着本质区别。
传统儒家“循公废私”的价值观对“公”“私”有两个层面的理解。一个是超然性的价值层面,这一层面的公私范畴主要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公具有“大义”的至善伦理价值,私则是指与义决然对立的“私欲”“自私”,是从心底生发出的一种个体性私欲或贪欲。孔子所讲的“大同”世界是指人人有公正心、讲大义而没有奸邪心的世界,君王以一种“公平无偏私”的原则为国家选拔贤能,人民以“平等无差别”的态度对待身边每一个人;荀子所谓的“公察”“公道”“公义”也是接着孔子而讲的。从伦理价值这种超然性层面讲,“公”即具有了“大善”“至正”“至善”等伦理意义。超然性价值层面的“循公废私”具有本体论根据,“大公”是天和自然的天然本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又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人作为“天道”化生的产物,自然应当效仿天道之大公至正,做到“循公废私”,乃为“圣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周子通书·公》)。
另外一个是实然性层面。从实然性层面理解公私,主要是指赋有身份或者挺立主体意义层面的不同实体,如“公”是指对“公家”或者“国家”利益的价值追求,“私”是指对“个人”“私人”利益的价值追求。“公家利益”相对于“个人私利”而言亦具有“绝对善”的伦理价值,“个人利益”“一己私利”则具有绝对意义层面“恶”的属性。
王船山承继了传统儒家“循公废私”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对公私内涵做出了明确的超然性价值层面的确定。这主要体现在对“为政者”的品德要求方面,“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2](P519),不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天下,也不能把天下视为一己之私。“王者以公天下为心,以扶进人才于君子之涂为道。”[3](P427)作为君王应该把天下视为“公”,为天下黎民百姓公平公正地选拔贤才。船山认为公平与偏私、奸邪绝对对立,这里的“私”是指一种反社会、反天下的私心。之所以强调“循公废私”就在于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然则义利公私之别,存亡得失之机,施之一家而一家之成毁在焉,施之一国而一国之兴废在焉,施之于天下天下之安危在焉,岂有二理哉?”[1](P97-98)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公私,则“私心”要无条件地服从“公心”,这种公是一种境界,一种豁然大公的境界。当然这种“循公废私”的价值取向也是有本体论依据的“天不偏阳,地不偏私,所以使然者谁也?曰:道也”[4](P822)。“天道为公”的根本法则决定了大公是每个人都先验具有的内在品质,“公者,命也,理也,成之性也。我者,大公之理所凝也”[2](P418)。
但当王船山在论述实然性层面之“公”与“私”时,则表现出了极强的辩证意识和启蒙性质。如船山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互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3](P535)船山从义利公私之辨的角度,把“义”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即“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一人之正义”指国君之正义,“一时之大义”指一姓之正义,“古今之通义”指“民族存亡”“生民生死”,三者的依次排序具有价值递进意义,前两者的“公正性”“公平性”“普遍性”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只有代表民族存亡、生民生死的“古今之通义”才是一种“大公”,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善价值。“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3](P535)忠诚于自己的国君,这是指“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但这个“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是否属于“大公”“通义”的范围,则要看其侍奉的君主是一个怎样的人,“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3](P535)。如果君主暴掠成性、荒淫无度、自私狭隘,以天下私一人,这个时候的“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则会成为一种“私”,君主的兴亡则只是“一姓之兴亡”。所以船山评论子路为卫辙而死,算不得“义之公”,而是“一己之私”,因为“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3](P535-536)。在船山看来,民族大义要高于君臣之义,生民之生死要高于一姓之兴亡。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统治者“私天下”的缘故,以公天下的名义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这种导致败亡的治国方针“始于嬴秦,沿于赵宋,以自毁其极,推初弱丧,具有伦脊”[2](P539)。
由此可见,王船山从实然性层面对义利进行公与私的甄辨,进而辩证地指出“生民之生死”为“公”,而“一姓之兴亡”为“私”,在辩证的义利公私观基础上,强调循公废私,“显示出走向近代义利观的启蒙意义”[5]。
二、“存公抑私”的理性证成
从理欲公私之辩的角度,王船山提出了“存公抑私”的观点。天理人欲之辨主要繁荣于宋明时期,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学派,即程朱学派和以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在朱熹看来,“天理”是义,是公,具有绝对“善”的价值,而“人欲”则是利,是私,具有“恶”的道德属性,故提出“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论断。与朱熹相反,李贽则把人的自然欲望“完全”等同于“天理”,充分肯定人欲的正当性、正义性,“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卷三十二》)把“心”等同于“私”,“有心”则必然“有私”,“无私”则“无心”,并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激进命题(《焚书·答邓石阳》)。人们穿衣吃饭等基本欲求就是“天理”,除此之外别无“天理”,这就将“人欲”“私欲”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将“人欲”视为“真”与“善”的化身,由对人欲的“全盘”肯定,进而走向了纵欲主义。
王船山则是在辩证批判程朱禁欲主义和李贽纵欲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关于理欲公私之辨的伦理构建,确立了“存公抑私”的辩证理欲观。
王船山从根本上反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苦行主义价值观。他既充分肯定“理”的伦理本位价值,又从本质上、本体上论证“人欲”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主要体现在“人欲”是“天理”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天理”的彰显途径。“天理”必然通过“人欲”而得以体现,“天理”是“人欲”之“天理”,离开“人欲”而谈“天理”,那是废人伦的,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必将导致人的主体性失落,造成对人性的歪曲和否定,“它在否定人欲之合理性的同时也使天理落入了空无的境地”[6],故曰“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7](P913)。正是在“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为对垒”的立场上[7](P756),王船山不仅反对“禁欲”,亦反对“薄欲”,“吾惧夫薄于欲者之亦薄于理,薄于以身受天下者之薄于以身任天下也”[9](P374),王船山指出,那些薄欲之人往往也是不能以身任天下的“不义”之人。由此可见,人欲是根本上的,是体,而天理是依附于人欲的,是用。“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7](P641)船山通过对朱熹理欲观的批判,将“人欲”提升到了“公共”“普遍”的层面,并因此使“人欲”具有了“公利”“公义”的属性。
但王船山并不赞成李贽将“人欲”完全等同于“天理”“公理”的说法。在对“人欲”的伦理判断上,船山与李贽一致,即都肯定了人的吃穿住行等生理欲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2](P128),声色臭味之欲是人们的生活所必需的,是厚生的必然要求,仁义礼智之理,是人们精神生活所必需的,是正德的必然要求,它们构成健康人性的两个方面或二重性,二者“俱可谓之为性”。但王船山批判李贽视“人欲”为“天理”的观点。但船山对“人欲”进行了“公私”“善恶”的价值甄辨,曰“欲字有褒有贬”[7](P757),“欲者,己之所欲为,非必理之所必为也”[7](P763),人欲包括理所必然的正当欲求,也包括为理所排斥的非正当的欲求,只有“理之所必为”者才“可欲”,只有“可欲”者才能称之为“善”。那么何谓“可欲”者呢?“合于人心之所同然,故人见可欲。而其但能为人之所欲,不能于人之所不知欲、不能欲者”[7](P757),根据此,那些声色臭味之人欲则是每个个体都有的欲望,因此是一种“公欲”“共欲”,具有“普遍”“共同”的伦理意蕴,这种声色臭味之“公欲”是与“天理”完全一致的,因而也是正当的,具有“善”之属性;而那些“纵其目于一色”“纵其耳于一声”“纵其心于一求”等“纵欲”,则是“贪欲”“奢欲”和“私欲”,之所以给予这些欲望以“恶”的道德评价,是因为它们会带来“天下之群色隐”“天下之群声闷”“天下之群求塞”的恶果[8](P439)。
质言之,船山对“人欲”进行了公私甄辨,将“人欲”分为“公欲”与“私欲”,“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7](P641)。
但船山也深知,纵算是“私欲”也是人性生成的一部分,企图依靠确立伦理规范来压制“私欲”是很难做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是通过保存和发扬人性中“公理”部分的引导作用,将“私欲”抑制在一定的程度内,即“以理制欲”,“以理制欲者,天理即寓于人欲之中。天理流行,而声色货利皆从之而正”[4](P356)。“君子节之,众人任之,任之而不知节,足以累德而损物。”[3](P1151)有学者指出“人性的伟大和尊严在于人不只是一般地应用天性,而是在于在应用天性的过程中发展起人所特有的人性。天性向人性的转化在于人能应用自己的知能开掘和光大自己的天性,人竭尽知能开掘和光大天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人性的生成过程”[9]。而人性中的“天性”部分即是合乎“天理”的“人欲”部分,人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充分保存人性中属于“天理”具有“善”意义的部分而抑制属于“私欲”的“恶”部分。
综上所述,船山在批判程朱与李贽理欲观的基础上,通过对理欲进行公私诚伪的甄别区分,提出了“存公抑私”的伟大理论。对人欲的肯定,使船山的理论具有了人道主义的近代特质,“王夫之的理欲观既继承了传统理欲观的合理因素,又反映了走向近代的开新特质,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包含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的价值元素”[6]。
三、“尚公崇私”的理性论证
王船山在义利与公私互训的理论视阈中,还彰显了一种“尚公崇私”的价值取向,这既体现在义利论中,也体现在公私论中,这一倾向十分有力地佐证了王船山作为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理论特色。对黎民百姓“个体正当利益”的维护,是通过“合私为公”的路径来完成的,体现了对宋明理学“贵义贱利”“贵公贱私”思想的突破、超越。
在义利论中,王船山对“利”的议论体现出一种“崇私”的伦理特质。所谓“利”即是“生人之用”[10](P277),把“利”一般地解释为“生人之用”,这一点是对孔孟至宋儒传统的继承,利是人生存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财富等,没有利,人将无法生存,“出利入害,人用不生”[10](P277)。船山在“利”范畴上超越前人的贡献在于,他是从与“害”相对立的角度提出的,进而认为要求人不要“谋利”,那就是置人于“有害”的处境,因为人完全不要私利,将会无法生存。有学者指出“王夫之提出了两种‘利’的概念:一种是‘益物而和义’意义上的‘利’,另一种则是‘滞于形质’意义上的‘利’;前者为善,后者则为恶。‘益物而和义’意义上的‘利’,是一种与人民大众的福祉相一致且能够促进人民大众福祉实现的‘利’,也是国家人民之公利。”[5]由此可见,船山强调利的重要性,但这种利是“益物合义”之利而非“滞于形质”之利,即个人的正当利益。
在船山的公私论中,公与私从理论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个相对立的概念,这从前面两点的论述中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为了论证“私”的合理性,他将普遍性的“私”进行了“公”的伦理属性构建,将“私”化为一种普遍性的“公”,从而使“私”在某种层面具有了“善”的道德价值。从辩证法讲,“公”与“私”只是一对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从本体论上讲,“公理”天然地蕴含着“私欲”;从认识论上讲,“私欲”是“天理”的彰显。
我们在分析船山公私论时,从实践层面要将公、私的具体义与其所指向的实体性事物联系起来,那么船山公私观的实质就是船山如何看待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在国、君与黎民个体之间的合理分配关系。如果不拘泥于字面的“利”字,仅从“利”的具体内容来看,王船山讲“利”的地方颇多。
首先,王船山首要重视的是黎民百姓的个人“私利”,如生存权和财产权。
王船山十分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利。王船山指出,“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灭,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2](P128),对照传统理学对社会大众基本生理需要的遏制甚至扼杀,王船山对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肯定就显得弥足珍贵。在理欲观中,王船山将“私”即每一个个体都有的“声色臭味”等基本需求提升到“普遍性”“共同性”的高度,从而赋予了“民之私以公的形式”[11](P23),体现出一种“崇私”的倾向。
基本生理需要权得到保障,那么进一步需要保障的生民权利即是财产权。船山在很多地方大谈为民谋利,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愿。在王船山看来,优秀的统治者应该把富民摆在首位,主张“裕民以政”,唯有养民、裕民,“裕民则民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所以他为商贾辩护也是因为“大贾富民”。王船山尊孔孟仁学为圣学,在“王天下”与“霸天下”两种治平的方式中,他极力主张“王天下”,而实现“王天下”的工具性手段不外乎两端:即先富之,后教之。故曰:“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井田、学校,二者其大端也”[12](P311)。那么,为何要“富之”?为何要先富之?船山回答道:“民无恒产,亦无恒心。”[12](P311)并进而提出国家应该“取民产而定恒制”,“是故欲求民心而使之有恒,必先取民产而定其恒制”[12](P313)。要制定稳定、正义的财产分配制度来保护人们拥有长久、永恒的财产所有权。为保障和实现社会民众的财产利益,船山有许多制度方面的设计,包括土地、粮食、商业等方面。在土地制度方面,船山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传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所有制,认为土地是自然之物,它属于“自然之公”的状态,但它依靠力量才能耕种,使之发挥应有的“资生”之物用,因此就土地的这个特性来说,只有拥有开垦土地从事稼穑能力之人,才可以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并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的光辉命题,“若土,则非王者之所得私也。天地之间,有土而人生其上,因资以养焉。有其力者治其地,故改姓受命而民自有其恒畴,不待王者之授之”[2](P551)。土地历来而且永久地是私有的,“人各治其田而自收之,此自有粒食以来,上通千古,下通万年”[7](P45-46)。王船山一方面揭示了历代君王将普天之下的土地据为己有,是一种“假公济私”的违伦理性行为,另一方面又将“有其力者治其地”的土地私有普遍化为一种“共同”的法则,从而使之具有了“公”的道德属性,并予以高度的价值评价。可以说王船山对土地私有的道德辩护具有极高的价值,影响了中国清末以来一大批的有识之士,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基本政治走向。关于粮食,王船山反对苛捐杂税对农民的盘剥,“民之所为务本业以生,积勤苦以获,为生理之必需”[3](P512),粮食是满足“生人之用”的主要物质资源,“匹夫匹妇以之生,而天子以生天下之人,故贵”[3](P725),进而把是否重视百姓的粮食生产视为辨别明君与否的主要标志。关于商业,船山指出“金粟之死生,民之大命也”[3](P165),从百姓个人私利满足方面论证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并因此制定了“利便一听之民”的贸易原则。天下的财富应当用来满足天下黎民百姓的正当物质需要,君王将之据为己有必将祸国殃民。总之,王船山认为国家(公家)应该为庶民谋取正当私利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当然,国家也可以通过赋税等方式从庶民私利中获得“公利”。
其次,王船山肯定国家之公利亦不可忽视,但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船山虽然多处谈到满足庶民百姓的个人私利之重要性,但也并不因此否定国家之公利的重要性。民众需要国家的秩序管理,因此民众也应该凭借自己的力量效劳于国家,为国家提供赋税,但国家也要把握分寸,不能敛待命之粟,这是国家之公利的正义所在,过犹不及都是不合理的。
在封建社会,不少的官宦家族往往以“公家”之名牟取个人之暴利,王船山给予辛辣的批判和讽刺,“其甚者,若李待问加派练饷,每秋粮一石至二三钱,重剥民资,付州县官练乡兵,何尝有一卒之用!徒充墨吏囊橐,为害愈深”[2](P634),他主张“唯轻徭薄赋,择良有司以与之休息,渐久而自得其生,以相忘而辑宁尔”[3](P194)。他更反对大臣们鼓动君主以公家的名义牟取一己之私利的行为,他以秦朝为例,“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3](P68)秦朝之所以得罪天下苍生最后走向灭亡就是因为以“天下之大公”的名义而“私己”的缘故。对于“公家”,他反对传统理学“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的君国至上论,也与同时代思想家黄宗羲的无君论迥然相异,而是主张公私兼顾。
由此可见,王船山“尚公崇私”的价值取向是通过两条“化私为公”的途径来完成的,或者论证“私”具有普遍“公”的属性,或者论证“私”对国家民族之“公”有利,而这种论证方式与宋明理学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运用的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以“公”的目的性包容了“私”的过程性,从而确立了“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构建了一种符合新兴阶级意愿的公私关系。王船山对个人正当私利进行前所未有的肯定,对天下为公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反对天下为公名义掩盖下的天下为君论,提出一种具有近代启蒙价值的“合私为公”新型公私观。正是在这一点上,王船山的公私观体现了道义论和功利论的统一,并进一步走向了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追寻。
四、王船山公私之辨的镜鉴及当代价值
与传统儒家长期以来以“公私”论“义利”不同,王船山则主要在义利的框架内,对“公”“私”进行辩证地甄别和深度地剖析,既坚持重义轻利的基本价值取向,又坚持在义利框架下,对“私”的不同部分进行了不同的伦理评价,从而从根本上解构了“私”的纯利己的属性,赋予了“私”以“善”的道德价值,体现了船山公私观的近代启蒙意义,彰显出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而朝向义利并重、公私兼顾的价值目标。王船山的公私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首先,王船山公私观开创了宋明以来公私之辨的新范畴和新境界。王船山生活在社会政治形势跌宕起伏、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重大转折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促使王船山对传统儒家的许多范畴、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与崭新解读。为促进民族国家的存续和发展,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大无畏精神与开拓精神对传统的义利观、公私观等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哲学范畴进行了新的功利主义诠释,以适应新经济时代新兴阶级的利益需要。传统儒家将公与私作为判断义与利的唯一标准,故曰“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王船山则对“公”“私”进行了辩证考察,揭示了“公”“私”范畴的层次性与相对性,既大胆揭示了“公”在某种程度上的虚伪性与恶的道德属性,也公开地为宋明以来臭名昭著的“私”进行“正名”,指出“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善的价值和属性,并进而提出义利与公私互训的思想主张,倡导以“古今之通义”统领“一时之大义”“一人之正义”,从而开创了宋明以来义利公私之辨的新范畴和新境界,正如梁启超所言“(船山)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可谓发宋、元以来所未发”[13](P735)。
其次,王船山公私观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王船山义利框架下对公私观的重构,彰显了对个人、个体等私人利益的价值肯定和追求。对个体利益的肯定和宽容为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王船山颇具近代启蒙性质的公私观深深地影响了近现代以来一大批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如魏源、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等。魏源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的地位,有学者指出是“开风气”的领军人物[14],魏源继承了明清之际以王船山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为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图谋富国强兵之策,魏源主张要扫除传统社会腐朽的重义轻利、重公轻私的道德风尚,对“功利”进行了“公天下”与“私一身”的辩证区分,大胆地提出“以实事呈实功,以实功呈实事”的近代功利主义思想。王船山的公私义利观“对毛泽东产生过特别巨大的影响”[15],青年毛泽东在挽救民族于危亡的民主主义革命中,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了王船山的义利公私观,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行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16](P450),强调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再次,王船山公私观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公与私、义与利的选择提供了合理的边界。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公”观念一直是主流的意识,但让人们感觉困惑的是,在历史生活中,主导人们行为或者在人们行为中发生深刻作用的却是“私”的意识,而且“公”“私”两种观念分别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并行不悖地大行其道,更可悲者,还有很多人在“公”的名义下从事者谋“私”的勾当。质言之,传统“公”的价值观念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并未真正内化为人们的内心道德准则,究其原因,就在于传统“公”“私”范畴厘定不清,且形成以“公私论义利”的狭隘传统。王船山公私观则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正确地指出“公私”“义利”范畴的相对性和多层次性,从而使“假公济私”的行为、“以公谋私”的行为无法立足;王船山为“私”正名,则为人们合理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伦理辩护。尤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浪潮中,弘扬船山公私之辩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公与私、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正确对待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与解决民生问题的并行不悖,均具有镜鉴和重要启示价值。
[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7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5]王泽应.王夫之义利思想的特点和意义[J].哲学研究,2009(8).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7]王泽应.论王夫之的理欲观[J].哲学研究,2013(6).
[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9]王泽应.王夫之人的尊严论及其深远影响[J].船山学刊,2014(4).
[1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1]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M].郑静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
[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8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4]唐凯麟.试论魏源的伦理思想[J].求索,1983(3).
[15]王泽应.船山思想对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与启示[J].船山学刊,2016(4).
[1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王学锋,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省交通厅副研究员。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王船山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YBA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