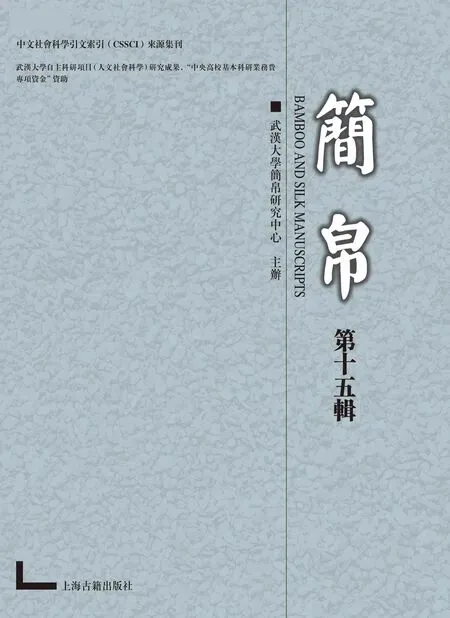上博竹書《魯邦大旱》篇及其形成探索
顧史考
壹、前 言
《魯邦大旱》篇,爲《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的重要文獻之一,記録的是孔子與魯哀公及弟子子貢兩場相次的、有關魯國遭遇大旱及魯君所當採取之對策的對話。如整理者馬承源先生所述,本篇長短簡共六支,而其中最後一支有墨節當作篇末終結記號。①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馬承源對本篇的“説明”,第203頁。《魯邦大旱》圖版及馬承源釋文注釋見該書的第5、49—56及201—210頁。此篇原與《孔子詩論》及《子羔》兩篇是合編爲一册的,整册書題爲《子羔》,寫在整理者所原列爲《子羔》篇第5簡的簡背上。《魯邦大旱》應是全册的中間篇,位於《孔子詩論》後、《子羔》前,篇名則爲整理者摘取首句而題的。②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馬承源的“説明”第183頁;及李鋭:《試論上博簡〈子羔〉諸章的分合》;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5—96頁。完簡約55.5公分,有上、中、下三道契口,其間上道契口離頂端約有8.6公分的距離,下道契口離末端約7.9公分距離,而中道契口則正位於此兩道契口中間,與之均有約19.4—19.5公分的距離。③見馬承源對本篇的“説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第203頁。完簡約55.5公分之説則見《孔子詩論》馬承源的“説明”;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頁。因爲《春秋》哀公十五年有“秋八月,大雩”的記載,整理者推測本篇所指大旱爲當年夏秋時事,然則其叙述背景即可定爲公元前480年,亦即孔子逝世的前一年。①廖名春亦主此説,見其《試論楚簡〈魯邦大旱〉篇的内容與思想》,《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第9頁所述。針對此種推測,楊朝明則認爲儘管其發生在此一年的可能性較大,但《春秋》書“雩”亦不見的即是由於該年發生旱災,不如保守地説此事發生於哀公時孔子在魯的六内之年,亦即前484至479年間。見其《上博竹書〈魯邦大旱〉管見》,《東嶽論叢》2002年第5期,第113—115頁。然如曹峰所言,同樣的故事既然又見於《晏子春秋》而彼講的則是齊國之事,因而“從思想史上的角度,這種確認性的工作其實没有多大意義”;見其《〈魯邦大旱〉初探》,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1頁。
如其他學者已指出,本篇最堪玩味的是,整個故事及對話内容與《晏子春秋·内篇諫上》第十五章“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所載記極其相似,甚至可謂乃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儘管其主要人物完全不一樣。然而除了主角之不同外,内容上亦有些微言大義的區别,而仔細探究其所以致此之緣由,或將有助於説明一些思想史上的問題。此外,與《魯邦大旱》同載一册的《子羔》篇亦有一些不可忽視的相同點,本篇對此亦將略加以分析。
貳、《魯邦大旱》釋文集釋
《魯邦大旱》篇的六支簡當中,第3、4兩簡均爲完簡,其他四支則僅剩上面的大半,第1、2、5等三簡似各缺19到20字左右,第6簡所缺的則全是篇後的空白處而并未損文字。簡1至簡5應該連讀,而簡5與6原連讀的可能性亦大。②廖名春謂簡5與簡6之間尚缺一兩支簡的可能性雖不能排除,然依照其上文的對話情況可知孔子此處的話“也不會太長”,所以此兩支相接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筆者亦是如此看之。廖氏説見其《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年第1期,第8頁。《魯邦大旱》篇整理者釋文所定的編聯順序并没有什麽可疑之處,今以此原序直接排聯而加以若干意補。
以下的釋文中,凡未加注者皆以整理者原釋文爲準,而與原釋文不同之説則放入注腳内。在此,“‖”表示殘簡的殘端,“▌”則表示完簡的界限。“()”表示所採讀法,“〈〉”表示訛字之更正,“[]”表示漏字,“{}”表示衍字。“【】”則表示筆者意補的部分(意補文字祇聊以作參考之資)。
▌魯邦大旱,哀公胃(謂)孔=(孔子)曰:“子不爲我(圖)之?”③“”:對此種“圖”字,裘錫圭有進一步的説明,可參(裘錫圭:《〈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文注釋》,2006年手稿;後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85—492頁)。孔=(孔子)(答)曰:①“”:如整理者指出,此字一般讀爲“答”;陳偉則認爲讀爲“對”較恰當(陳偉:《讀〈魯邦大旱〉札記》,簡帛研究網[http://www.bamboosilk.org,後改成http://wwwj.ianbo.org]2003年1月27日;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115—120頁)。“邦大旱,毋乃(失)者(諸)型(刑)與惪(德)(乎)?②如整理者指出,“刑與德”蓋指刑罰與慶賞兩種政治手段。以儒家而言,“失諸刑德”或偏指刑罰過重或失當。林志鵬以“刑”通“型”,即“法度”,亦通(林志鵬:《〈魯邦大旱〉詮解》,《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78—483頁);或亦可以解爲君主之“模範”。關於“德”的一面,羅新慧(第89—90頁)亦指出《禮記·檀弓下》記載魯遇旱災而穆公問對策於縣子時縣子贊成“徙市”之舉,“含有穆公自責以修德的因素”,因而認爲“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普遍做法是既有修德之舉,同時又希冀借助巫術習俗以爲己所用”(羅新慧:《從上博簡〈魯邦大旱〉之“敚”看古代的神靈觀念》,《學術月刊》2004年10月,第85—90頁)。唯(1)‖【型(刑)惪(德)皆當者,天其佑之。願君善(圖)之!”公曰:“若然,則女(如)】▌之可(何)才(哉)?”③此處缺約十九至二十字,今且意補如此。秦樺林亦補其末字爲“女”,而讀爲“若”(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簡帛研究網2003年2月14日)。廖名春《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則試補“‘正刑與德。’哀公曰:‘庶民以我不知以説之事鬼也,若’”等二十字,認爲此處該是哀公對孔子“理性主義的意見”提出疑問,才將引出孔子下面“妥協的方案”。林志鵬《〈魯邦大旱〉詮解》則從黄人二讀“唯”爲“雖”而後又試補“然,君尚無玉帛。哀公曰:既正刑德,又以玉帛事神”等十九個字。“才”:整理者原讀“在”,此則如李鋭等學者讀“哉”(李鋭:《讀上博館藏楚簡(二)札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523—531頁)。孔=(孔子)曰:“(庶)民(知)敚(/説)之事(鬼)也,④“敚”:整理者讀爲“説”,當求雨祭名。李學勤則解作“祝詞”,在此當“禱祝”之意(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第4—7頁;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97—101頁)。范麗梅綜括有關記載,進一步説明“説”祭是“有災變時……可以作爲號呼告神以請事求福的方式之一,其具體的做法是陳論其事以責之或以祠説於上帝鬼神……對象包括了昊天上帝、先祖父母、山川鬼神等等,而祠説的内容則由反省自我到責求天地鬼神”(范麗梅:《上博楚簡〈魯邦大旱〉注譯》,《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163—180頁)。羅新慧《從上博簡〈魯邦大旱〉之“敚”看古代的神靈觀念》讀“敚”如字(通“奪”),意即“解除憂患”,作用在於消災救難,與記載中的“説”當爲同一祭祀:其“主要内容之一爲以强取的方式迫使神靈聽順人意,向神靈陳論事實并以言辭相責讓,另一方面則又以珪、璧、币、帛或犧牲等祭品陳列於神前,以禮順迎神靈”(第87頁);其説亦有理。康少峰則讀爲“悦”;毛慶亦讀“悦”,然以標點改爲“庶民知、悦之事,鬼也”(康少峰:《〈魯邦大旱〉歧釋文字管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第140—144頁;毛慶:《〈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字釋句獻疑》,《南通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154—157頁)。不(知)型(刑)與惪(德)。女(如)毋(愛)珪璧(幣)帛
“”:整理者釋爲“視”;黄德寬改釋爲“”而讀“鬼”,李守奎之釋讀亦如此,今從(黄德寬:《〈戰國楚竹書〉(二)釋文補正》,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21日,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34—443頁;李守奎:《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雜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78—483頁)。范麗梅《上博楚簡〈魯邦大旱〉注譯》認爲此“鬼”具體指的可能就是所謂“旱魃”。顔世鉉則讀此“”爲“畏”而以“畏也”屬下當解釋語(顔世鉉:《上博楚竹書補釋二則》,簡帛研究網2003年4月29日)。於山川,①“女”:整理者讀爲“如”。季旭昇則讀爲“汝”(季旭昇:《上博二小議(三):魯邦大旱、發命不夜》,簡帛研究網2003年5月21日)。然如康少峰《〈魯邦大旱〉歧釋文字管見》已指出,稱君爲“汝”實乃不敬,今不取。“”:整理者讀“薆”,解作“隱蔽”。今則如劉樂賢而讀作“愛”(劉樂賢:《讀上博簡〈民之父母〉等三篇札記》,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10日;亦見其《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文物》2003年第5期,第60—64頁)。毛慶《〈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字釋句獻疑》則改釋爲“态”,即“忲”亦即“奢侈”義;然而如此讀之則子貢下面反對此一舉的話語如何解釋,毛氏并未加以説明。政(正)坓(刑)與(2)‖【惪(德),②“政”:整理者讀如字而以“政坓”連讀爲一詞。今亦如劉樂賢《讀上博簡〈民之父母〉等三篇札記》及《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而讀作“正”。下簡讀同。則民蟼(將)歸君而邦乃治矣。”公曰:“諾,(吾)蟼(將)厚祭之。”孔=(孔子)】▌出,③此處亦缺二十字左右,今且意補如上。廖名春《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則於“孔=”前試補“‘德以事上天。鬼神感之,大旱必止矣’哀公曰:‘善哉。’”等十九個字。廣瀨薰雄則試補其頭十個字作“德以事上天,其幸而雨乎”(此後五字從《晏子》本末尾之語),而疑其後十個字左右可補如“哀公不悦而退之。孔子”之類的句子(廣瀨薰雄:《關於〈魯邦大旱〉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第507—510頁)。史傑鵬則疑“正刑與德”後講的大概即“等把這件事應付過去再説吧”一類的話,意即先以祭祀爲要,而“正刑與德”則可以待他日(史傑鵬:《小議楚簡〈魯邦大旱〉》,《中華文化畫報》2007年10月,第38—40頁)。遇子(貢),曰:“賜,而(爾)昏(聞)(巷)(路)之言,毋乃胃(謂)丘之(答)非與(歟)?”④據廖名春《試論楚簡〈魯邦大旱〉篇的内容與思想》的分析,孔子提出此問所擔心的不是社會輿論將“非”其“毋愛”於山川祭祀之策,而是“非”其“正刑與德”之策。筆者之説則見下節。子(貢)曰:“否。(抑)(吾)子女(如)蔞(重)[丌(其)]命{丌(其)}與(歟)?⑤“”:整理者讀“也”而屬上。何琳儀讀爲語首助詞“繄”而屬下(何琳儀:《沪簡二册選釋》,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14日;後收入《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44—455頁)。俞志慧亦屬下,然讀爲“抑”,以“否”一字爲子貢之答詞,“抑”以下爲孔子省略了“曰”的追問(以下的對話當中亦多如此讀)(俞志慧:《〈魯邦大旱〉句讀獻疑》,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27日;此文内容後亦收進其《〈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二題》,《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511—519頁)。廖名春亦如俞氏而讀“抑”,然而在此視爲相當於“豈”,表示反詰語氣;廖氏又指出“否”是子貢對民情一問的回答,而接下的話才是表示其自己的看法(廖名春:《〈魯邦大旱〉的“重命”和“寺乎名”》,簡帛研究網2003年)。裘錫圭亦從俞氏讀“抑”,而視爲轉接連詞,其下面的話仍歸子貢(裘錫圭:《説〈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丌歟”句》,《華學》第九、十輯(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5—287頁;後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31—534頁);今亦從此説,以“抑”當“然而”、“但是”義來解。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疑可讀爲“偕”而亦屬下。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則贊同整理者“否也”之原讀。俞志慧認爲“吾子”祇能是孔子對弟子之稱;秦樺林亦從之,而認爲此處之“吾子”本身亦已足以表示説話者已换爲子貢的作用。然其實弟子稱孔子爲“吾子”亦不乏其例,劉樂賢《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及康少峰《〈魯邦大旱〉歧釋文字管見》已詳之;今仍從整理者之歸屬。 “女”:整理者讀“若”;顔世鉉則讀爲“乃”,季旭昇《上博二小議(三):魯邦大旱、發命不夜》亦從之(顔世鉉:《上博楚竹書散論(三)》,簡帛研究網2003年1月19日)。今讀爲“如”(或“若”)而當“如果”、“假如”義來理解。“蔞命”:整理者讀爲“重名”,以義爲“重視巷路的反映”。顔世鉉《上博楚竹書散論(三)》讀“命”如字而理解爲“重視百姓生命”。季旭昇則理解“命”爲“天命,上天的旨意”,康少峰略從之,當“重視天命神意”來解,亦指出此與下文子貢之强調“正刑與德以事上天”堪稱是緊緊相扣的;今亦大致從此思路來理解。廖名春《〈魯邦大旱〉的“重命”和“寺乎名”》及《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則認爲此“命”與前面之“説”義近,即一種祭祀之名,或亦可(從陳劍向廖氏提所示)讀爲“禜”,“重命”即“看重禳除旱災的祭祀”,亦是“子貢指責孔子迷信鬼神祭祀”。秦樺林謂“重命”即“尊名”之義,“蓋指在祭祀活動中向鬼神敬致美‘號’以示尊崇之意”(秦樺林:《楚簡〈魯邦大旱〉“重命”解》,簡帛網[http://www.bsm.org.cn]2006年1月9日)。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讀作“踵”,以“踵命其與”當“往來告其親友”之意。劉信芳亦讀“踵”,然訓“踵”爲“追尋”而解“命”作“稱名”,意即“追尋‘山川’之所以稱名”(劉信芳:《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踵命”試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5年1月第1期,第12—13頁)。廣瀨薰雄《關於〈魯邦大旱〉的幾個問題》讀“蔞”爲“重複”的“重”,以“重命”爲“重複命令”的意思;毛慶《〈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字釋句獻疑》亦提出類似的説法,以爲“重複”孔子的“意見”。裘錫圭《説〈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丌歟”句》亦採取相類的解法,以“重命”義爲孔子對哀公“累加”上“毋愛圭璧幣帛於山川”此種無必要的“囑咐”。“丌(其)與(歟)”: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認爲“若……其歟”此種句型“很可能是加强測度語氣”;或是,然此種語序頗爲反常。范麗梅《上博楚簡〈魯邦大旱〉注譯》略從之,而謂在此是“省略了中心詞”。秦樺林《楚簡〈魯邦大旱〉“重命”解》則以“其”當代指“山川”的代詞,實不可取。廖名春《〈魯邦大旱〉的“重命”和“寺乎名”》認爲“如其”或表示强調語氣而本句相當於“吾子如其重命歟?”俞志慧《〈魯邦大旱〉句讀獻疑》則將“重命(名)其”,當“重其命(名)”之誤乙,而以“重其命”當“重天命”來理解。廣瀨薰雄則訓“其”爲“乃”而以“與”當支持義;曹峰《〈魯邦大旱〉初探》採取類似的解釋,譯爲“[如果您重視人的生命,]他們都會聽從您的”。裘錫圭《説〈魯邦大旱〉“抑吾子如重命丌歟”句》則讀“丌”如句末語氣助詞用的“忌”,以“如……丌歟”當作類似“如……也歟”的某種語氣較緩和的、相對客氣而有疑問氣味之句。今且從俞氏誤乙之説,而姑將“歟”視爲某種强調假設語氣之詞(或亦可以考慮讀如字而屬下句)。女(若)夫政(正)坓(刑)與惪(德),①“女夫”:整理者讀此爲“如夫”,而讀下一次爲“若夫”;今如劉樂賢《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及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而統一讀爲“若夫”。又秦氏認爲此處“若夫”足以表示説話者已换爲子貢之用,如此乃支持俞志慧之句讀;今不取。(以)事上天,此是才(哉)■。女(若)天〈夫〉毋(愛)珪璧(3)▌(幣)帛於山川,毋乃不可∠?②俞志慧《〈魯邦大旱〉句讀獻疑》以爲子貢此次之答至此爲止,以下當孔子對子貢釋疑解惑之語;今不取。廣瀨薰雄《關於〈魯邦大旱〉的幾個問題》支持此處俞氏之讀,然似以“毋乃不可”當肯定之語,與筆者之理解相反。毛慶《〈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字釋句獻疑》亦支持此處以下换爲孔子語之説,又謂此處的小鉤形符號正是暗示説話主角已轉换;然下面“䓫”字後亦有同樣的符號,無論如何也似乎祇能解釋爲句讀標點符號,并非如毛氏所云。夫山,石(以)爲膚,木(以)爲民,①“民”:《晏子》本作“髮”,乃比較合理。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認爲此“民”可能即“毛”字之訛。女(如)天不雨,石蟼(將)䓫(焦)∠,木蟼(將)死,丌(其)欲雨或甚於我,②“或”:如陳偉《讀〈魯邦大旱〉札記》已指出,此“或”很可能在此該讀爲“又”。但陳氏又謂讀如字則不好解釋,筆者則不以爲然;今且如整理者讀如字。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王志平讀“有”(王志平:《上博簡(二)札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第495—510頁)。或(又)必寺(待)(吾)名(命)(乎)?③“或”:整理者在此讀“何”,今則如何琳儀《沪簡二册選釋》而讀爲“又”。如陳偉《讀〈魯邦大旱〉札記》指出,此“又”在反問句中有强調語氣的作用。“寺”:整理者讀“恃”,以“恃乎名”解作“恃名傲世”。劉樂賢《讀上博簡〈民之父母〉等三篇札記》讀“寺”爲“待”,以“待乎名”爲“等到叫名字”的意思;顔世鉉《上博楚竹書散論(三)》亦然其説而申論之。今亦如之讀此字爲“待”,然接下讀法則不同。廖名春《〈魯邦大旱〉的“重命”和“寺乎名”》及《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讀同整理者,然以“恃乎名”之“名”讀爲“命祭”之“命”,認爲此句意略相當於《晏子》内篇本的“祠之何益?”陳明(據劉樂賢《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引)則直接讀“寺”爲“祠”,劉樂賢所採新説之一亦從之;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亦讀“祠”。“”:此句頭一“”字,整理者讀“乎”。今如陳偉《讀〈魯邦大旱〉札記》及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而讀此爲“吾”、讀下一例爲“乎”。“名”:整理者讀如字,今如陳偉《讀〈魯邦大旱〉札記》而讀爲“命”,對句義的理解大致與陳氏相同,即“難道必須等待我們的呼唤嗎?”如前注已示,廖名春《〈魯邦大旱〉的“重命”和“寺乎名”》及《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以此“名”讀爲“命祭”之“命”;今雖不從,然亦可略依其思路而理解此“命”爲命祭中的“命神”之詞。如廖氏所舉的([宋]王與之《周禮訂義》卷四十三載)鄭鍔所言解釋得好:“命者,述其意以命神,如‘命龜’之‘命’。蓋有指使之言……乃所以命之也。”劉樂賢《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所採新説亦從陳劍之讀爲“禜”,與廖説亦近。康少峰《〈魯邦大旱〉歧釋文字管見》則讀如字,然當作祭祀的代稱;林志鵬《〈魯邦大旱〉詮解》則以“名”指“禮”儀之名號而言。裘錫圭《〈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文注釋》亦讀如字,當“稱名”來理解。夫川,水(以)爲膚,④“膚”:《晏子》本相應之字作“國”,亦比較合理。魚(以)(4)▌爲民,女(如)天不雨,水蟼(將)沽(涸),魚蟼(將)死,丌(其)欲雨或甚於我,或(又)必寺(待)(吾)名(命)(乎)?”孔=(孔子)曰:“於(嗚)(呼)!(5)‖【賜也,而(爾)通乎天人之際,而未能達乎民心。女(如)不厚祭,⑤此處亦缺二十字左右,今且意補如上。廖名春《上博藏楚簡〈魯邦大旱〉校補》則試補爲“賜,我告爾:命也者,君子以爲文,庶民以爲神。如不命,王”等二十字(以“君子”爲合文而算)。陳侃理則認爲孔子的意思應即“以山川比國君”,因爲旱災對老百姓與國君的影響不同,要表達的意思是“天不下雨,草木魚蝦没有生路,但山川依然會存在,因而山川對下雨的希望并不會那麽急切”,來反駁子貢的比喻(陳侃理:《上博楚簡〈魯邦大旱〉的思想史坐標》,《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6期,第75—78頁);或可以備一説。】▌公剴(豈)不飯杒(粱)飤(食)肉才(哉)?⑥“飯”:整理者釋爲“”而讀爲“飽”,而徐在國對此讀法從“攴”、“包”通假上的可能加以進一步 的説明(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學術界》2003年第1期,第98—103頁)。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疑乃“飫”之誤;毛慶《〈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字釋句獻疑》則認爲可釋爲“養”。李守奎《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雜識》則改釋爲“飯”,俞志慧《〈魯邦大旱〉句讀獻疑》亦提出釋讀爲“飯”的可能(其修改本亦言及施謝捷也改釋此字爲“飯”),而高佑仁又對此一釋讀加以進一步的證明(高佑仁:《論〈魯邦大旱〉、〈曹沫之陣〉之“飯”字》,簡帛研究網2005年2月20日)。今從此後説。“杒”:整理者讀爲“粱”;如其已指出,“粱”是一種精美的糧食。毛慶則認爲此字無法讀爲“粱”而實從“刃”聲,在此讀爲“任”而訓爲“佞”,指佞人;然陳嘉凌及李守奎則已指出,“刅”、“刃”混訛的例子不少,仍該讀爲“粱”(陳嘉凌:《〈魯邦大旱〉譯釋》,季旭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讀本》,萬卷樓2003年,第41—52頁)。“飤”:今如整理者讀爲“食”;毛慶《〈戰國楚竹書(二)·魯邦大旱〉釋字釋句獻疑》則提出異議而從《説文》釋爲“糧”。殹(抑)亡(無)女(如)(庶)①整理者將“才殹”連讀爲“哉也”。何琳儀《沪簡二册選釋》讀“殹”爲語首助詞“繄”而屬下,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從之而謂用法同“唯”。今則讀爲“抑”而亦屬下(俞志慧第3簡同字已讀爲“抑”,然彼讀并未言及此簡)。秦樺林《上博簡〈魯邦大旱〉虚詞札記》認爲此處讀“抑”并不合適,因爲以爲“豈……哉?抑……何?”無法當選擇問句;然依筆者理解,此兩句正當默認的選擇問句,意思即“[你既知魯公將如何,那你究竟要依我意而讓魯公進行求雨祭],還是根本不採取幫助百姓之策呢?”廖名春《〈魯邦大旱〉的“重命”和“寺乎名”》亦已讀爲“抑”,然而視爲相當於“豈”用,表示反詰語氣。民可(何)?”▂①(6)
叁、《魯邦大旱》通讀及概述
現在先依照以上的釋文而以通行字及自然分段來列出《魯邦大旱》全文以方便讀者,接著乃對全篇的内容加以簡略的分析:
魯邦大旱,哀公謂孔子曰:“子不爲我圖之?”
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唯【型德皆當者,天其佑之。願君善圖之!”】
【公曰:“若然,則如】之何哉?”
孔子曰:“庶民知説(/敚)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如毋愛珪璧幣帛於山川,正刑與【德,則民將歸君而邦乃治矣。”】
【公曰:“諾,吾將厚祭之。”】
【孔子】出,遇子貢,曰:“賜,爾聞巷路之言,毋乃謂丘之答非歟?”
本簡殘去一半,而終篇的墨節符號與殘斷處之間尚有約十四字長短之空白。
子貢曰:“否。抑吾子如重[其]命{其}歟?若夫正刑與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天〈夫〉毋愛珪璧幣帛於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爲膚,木以爲民,如天不雨,石將焦,木將死,其欲雨或甚於我,又必待吾命乎?夫川,水以爲膚,魚以爲民,如天不雨,水將涸,魚將死,其欲雨或甚於我,又必待吾命乎?”
孔子曰:“嗚呼!【賜也,爾通乎天人之際,而未能達乎民心。夫如不祭,】公豈不飯粱食肉哉?抑無如庶民何?”
此蓋言魯國大旱而哀公乃求孔子來幫他出對策,孔子首先提出“正刑與德”以作爲“事上天”的上策。哀公大概問之具體該怎麽辦時,孔子乃解釋因爲庶民祇懂得祝禱祭祀之爲所以安撫山川之靈而使之解旱,而并不瞭解刑、德之政策與大旱的關係,所以最好要一面以豐厚之祭品執行求雨之祭,而另一方面又得矯正刑、德之不平衡才行。儒家對於“刑與德”,亦即德治與强制的問題上,一向强調以德教爲主、以刑罰爲次,後者祇可以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用之,因而“失諸刑與德”所指,簡而言之亦即刑罰過重,失其正當的平衡。①對於先秦儒門及儒門外對德治與强制的辯論,見拙著《從禮教與刑罰之辯看先秦諸子的詮釋傳統》,《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3期,2000年,第1—32頁。楊朝明《上博竹書〈魯邦大旱〉管見》對此一問題亦有所論述;亦見其《上博竹書〈魯邦大旱〉小議》,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9—146頁。曹峰則對此有不同的見解,認爲《魯邦大旱》中的思想并“不是以‘德’爲主,以‘刑’爲輔”,反而是兩者并重,“似乎與早期儒家思想不相吻合”,見其《〈魯邦大旱〉初探》第133—136頁。
等到孔子退朝而遇到其弟子子貢後,就問他説:“賜,爾聞巷路之言,毋乃謂丘之答非歟?”
對此一問的情形,諸位學者皆解釋如“孔子由哀公處出來,遇見子貢,問他在城内道路上聽人談話,是不是説自己對哀公的回答不對”,或如“孔子從魯哀公宫出來,在路上碰到他的學生子貢,詣問社會輿論對他的彌災之策的反映”等等,②分見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第6頁;廖名春:《試論楚簡〈魯邦大旱〉篇的内容與思想》第10頁。學者對此種理解一無異議。然問題是孔子既然才剛從魯公那裡走出來而遇到子貢,社會焉能來得及對其剛才講的(或且亦私下講的)話有什麽“輿論”可言呢?因此,筆者乃理解此“爾聞巷路之言”爲“你聽過最近路上的輿論,[因而該理解庶民對大旱及國君的態度如何]”,然而因爲孔子深知子貢之習以理性來辦事的性格,知其心中對己之對策肯定有所不以爲然,因而又加了一句:“你難道不認爲我對哀公之回答是不對的嗎?”即是説“毋乃謂”之主語并非“巷路之言”(儘管如此讀之似乎是很自然的),而實乃“賜”,即子貢。如此理解之,整個段落才能順利解釋。
子貢回答時,先很客氣地講“不會”,乃又接以“不過,如果您是看重天命的話,那麽採用像‘正刑與德’此種措施以事上天,這就對了;而至於‘毋愛珪璧幣帛於山川’此一舉,難道不是不可以的嗎?”然後接著乃拿出生動的比喻來説明山川對雨水的需求可能比我們還大,所以假如山川真能控制天氣,那又何必等到我們通過雨祭來使唤之才將願意下雨呢?因爲斷無此理,所以子貢深信執行此一豐厚的祭祀完全是違反理性之事。
孔子最後的回答,可惜有缺文而無法確知,然所歎息的大概就是子貢考慮問題之不周全。孔子此處的回答似乎比較簡略,可能祇是舉其一以待子貢自反其三。他説魯公難道不會一天到晚吃得好好的,你寧可讓他這樣奢侈下去而對人民之痛苦不採取任何對策嗎?意思是説他如此回答魯公至少能讓公將國家資源用在求雨之祭此種積極的活動上而不是光用在讓自己吃喝玩樂而將人民置之不理,這樣至少能給人民一種心理安慰,而同時仍是勸魯公採取矯正其刑罰與慶賞此種有實質用處之策,豈不是最好不過的辦法?若反依子貢之意而與魯公説求雨之祭實無用,則魯公既將用大量資源來吃喝玩樂下去,而又將缺乏使他正刑與德之動機——亦即其對山川之神威性的信仰。孔子深達人心,而其口才靈巧之弟子子貢則并未對人心加以考慮,而光是以事理言之。①確如劉樂賢已言:“據前文推測,孔子可能會批評子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懂得自己提出祭祀求雨的用心。”見其《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第62頁。全篇的重點,似乎即在於此一治道周全的問題之上,即理性、禮儀及人情之不可不兼顧。
肆、餘 論
《魯邦大旱》中的孔子對進行求雨祭的態度究竟如何,學者持有不同的意見。如劉樂賢説:“簡文中的孔子,一則對旱災與政治相聯并强調‘正刑與德以事上天’,二則對祈神求雨之俗表示肯定。這種相信鬼神乃至天人感應的觀念,爲《論語》、《孟子》、《荀子》等書所無,值得引起注意。”②劉樂賢:《上博簡〈魯邦大旱〉簡論》第62頁。劉氏此説基本上是没錯,此簡書中的孔子的確肯定祈神求雨之俗的作用,而“正刑與德”之後特加“以事上天”等字,則至少表面上稍有天人感應的意思在内。然而此種天人感應之意究竟多深?因爲仔細看全文,孔子的重點并不在此。
李學勤分析此文時,對簡5至6孔子之歎息有缺文的内容猜想:“原意是講即使拿出了珍貴的玉帛,哀公還是照樣過他豪奢的生活,如果只改正政治的刑德失誤,不行祭祀禱祝,民衆是没法對付的。”①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第6頁。此説基本可從,然對孔子的思路似乎付予過於現實的態度,没有凸出“正刑與德”的重要性。然而李先生接下去强調,“孔子主張玉帛向山川禱祝的原因”是因爲“是一種傳統的禮儀,爲民衆所習知”,而“孔子答魯哀公説大旱是由於施政刑德的失當,這也不能簡單地指爲天人感應的思想……孔子的‘天’没有‘神’與‘權’的性質,但‘天’對孔子仍存有一種精神寄託的作用。由此不難理解:孔子建議哀公祭祀山川,只是爲了給民衆安慰;而要求哀公正刑與德,也不過是乘機在政治上進諫而已”。②李學勤:《上博楚簡〈魯邦大旱〉解義》第6—7頁。此言非常中肯。
廖名春亦謂:“孔子的這一意見,既照顧到了民情,又利用天災作政治文章”,“君子只是將”祭祀“作爲一種文化現象,作爲一種文飾政治的手段——禮,并不是真的相信”,亦大致即此意。③廖名春:《試論楚簡〈魯邦大旱〉篇的内容與思想》第9、11頁。廖氏亦提出若干文獻證據來説明:簡本中的孔子此種傾向,亦即“重人事,輕鬼神”然又對祭祀鬼神“採取容忍”態度,也是他文所習見的(包括衆所周知的相關《論語》章句),而關於子貢敢於責問夫子的習慣性,亦見於許多相近之記載,《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或即其例。④范麗梅亦有類似的詮解,見其《上博楚簡〈魯邦大旱〉注譯》第177—179頁。廖氏特舉馬王堆帛書《易》傳《要》篇,其中子貢責問孔子“何以老而好易”?,而孔子答以“我後其祝卜,我觀其德義耳也”,指出與簡文的對答極其相似。⑤廖名春:《試論楚簡〈魯邦大旱〉篇的内容與思想》第11—14頁。廖氏所舉之文例,確實值得思考。
然而最可注意者,亦即其他學者似乎尚未留意的一點,即《魯邦大旱》的情節與同載一册的《子羔》篇有極爲相似之處。《子羔》最顯著的特點,即孔子經過子羔的一問便即肯定禹、契、后稷等三代始祖的奇妙誕生故事,以其母感天而生子的傳説當作實有其事;號稱不言“怪力亂神”的孔子何以向弟子叙述此種怪事,比起其支持舉行求雨之祭,乃更加令讀者難以置信。然與本篇同樣的,其重點并非在此:經過子羔的不斷追問,乃知孔子所要强調的實即生爲人子的舜,因爲其從幼好學而一直修養自己,且後來爲明君堯所欣賞而付以重任,因而最後竟成爲彼三“天子”事此“人子”的局面;其重點在於儒家所恆言的修己以待時的概念上,就如本篇是將重點放在刑、德適當及順民情以行事的治道之上。兩篇均以并非理性的傳統禮俗或神秘信念當作可以包容甚至肯定之事,然其所以肯定之并非肯定其神秘本身,而純是爲了顯示出某種更高一層的孔教理念。由此可知,此兩篇之所以同載一册,確有可能并非偶然。①參拙著《上博楚簡二〈子羔〉篇新編及概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論文,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陳振傳基金漢學研究委員會主辦、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協辦2016年(本論文集即將由中西書局正式出版)。
再説“大旱”的故事,先秦至前漢的文獻中亦并非罕見。有的“大旱”故事的情節是君主欲殺主祭之“巫”、“祝”、“史”等以當作代罪羔羊,而明臣提出敏鋭的分析以止之。如《左傳》僖二十一年: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②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390—391頁。楊朝明《上博竹書〈魯邦大旱〉管見》亦已引此文,可參。亦見曹峰:《〈魯邦大旱〉初探》第131—132頁。
臧文仲的對策即强調要“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以減緩災情,而以理性的分析完全否認焚巫之用處。雖未對祭祀本身提出看法,然亦顯然是將重點放在以現實之政策來減緩旱災所帶來之害。又如《新序·雜事》第十章:
梁君出獵,見白雁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無異於虎狼。”③[漢]劉向編著,石光瑛校釋,陳新整理:《新序校釋》,中華書局2001年,第219—222頁。
公孫襲所引用的故事純是以一種對人民之仁愛作爲出發點,并没有反對天意的因素,不過將此天意視爲與傳統的概念不一樣,强調的是天愛其人而并不愛其祭。
這些故事與《魯邦大旱》雖有若干相同點,然而其側重點均有分,難以等同看待。與《魯邦大旱》最可比較者,固然莫過於《晏子春秋·内篇諫上》第十五章“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的故事(亦見《説苑·辨物》),即: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
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
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
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爲之柰何?”
晏子曰:“君誠避宫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
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①吴則虞編著:《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1962年,第55—59頁。此一“版本”與《魯邦大旱》的“版本”有如下的基本不同點。1)主要人物即齊景公與晏子,而非魯哀公、孔子與子貢,且亦有“群臣”之沈默以爲晏子陪襯;2)講出對祭祀的理性否定者即晏子,而説出最後結論者亦即晏子,可以説是兼當子貢與孔子的角色;3)晏子明言“祠此無益也”,并不支持對山川的祭祀,與孔子之態度有明顯的不同。此外亦有若干叙述上的不同點,今不一一指出。
乍看之下,這兩種版本有根本上的不同,亦即其主要説理人物對求雨祭的支持與否。然而細察之,此二本之結論并非相背而馳,反而從某種角度可以説是大同小異。晏子最後所講出之對策,即勸景公欲“誠避宫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亦即要景公對自己的豐富生活作一定的犧牲,哪怕等於祇是象徵性的,仍要與山川之神靈(乃至與人民)表示“共憂”,此蓋亦與孔子之欲哀公少吃點“粱”與“肉”同理。晏子言“其幸而雨乎”,或乃意味著他并非真的相信天人感應,儘管其言在三天後確實即“幸而”得驗。然重點在於晏子之言,“其維有德”,與孔子一樣强調的是“德”上的表現,以誠心與人民及神靈共憂共樂。然則此兩個版本於精神上其實也可以説是相當一致的。②曹峰亦曾對此兩個大旱故事的異同進行過詳細的比較,不過因爲他採取了廣瀨薰雄對孔子與子貢對話的斷讀(亦即俞志慧的部分斷讀),認爲孔子是輕視向山水之神靈進行豐厚祭祀的行爲,因而與筆者的理解全然不同。詳情見曹峰《〈魯邦大旱〉初探》。曹氏既認爲孔子是輕視厚祭的,則如何解釋其先前對魯公説“如毋愛圭璧幣帛於山川……”,似乎尚未予以交代。陳侃理亦曾對此兩種版本的異同提出想法,認爲子貢的觀點與晏子幾乎一致,而《魯邦大旱》即是以反駁《晏子春秋》彼章中“晏子”的立場而寫的;見其《上博楚簡〈魯邦大旱〉的思想史坐標》第75—78頁。筆者雖亦認爲《魯邦大旱》是在《晏子》彼章後産生的(見下),然對兩者間關係的理解則亦與陳氏不同。
然而兩者畢竟亦有其微言大義上之分歧,不得不對此加以思索。究竟孰先,孰後?孰爲原版,孰爲改寫版?改寫之目的何在?此種問題固然見仁見智,難以拿出鐵證來牢固地站在一邊,再説兩者均爲某種前文的改寫版此種可能性亦無法完全排除。然依筆者之見,此一故事,從兩版的共同特徵考之,顯得與《晏子春秋》其他章節有共鳴之處,因而其原屬於《晏子》資料而後乃爲儒者所借來改寫的可能性仍是比較大的。
何以知其然?今且舉《晏子春秋》中的另一章以爲例。《晏子春秋·内篇·諫上第一》的第十二章,舊題爲“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叙述的是齊景公患了一種痼疾,請教對策於兩位嬖臣以至於晏子的一則故事。同一個故事又出現於《左傳》昭二十年(彼版亦與《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第七章“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的版本幾乎全同,可視爲同版)以及上博六的所謂《競公瘧》篇,然三種版本間頗有異同。①筆者曾對此三種版本進行比較,詳情見拙著《從出土文獻看先秦版本間的關係:以齊景公病久的故事爲例》,“簡帛文獻對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啓示”工作坊論文,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將收入拙著《上博等楚簡戰國逸書縱横覽》;上海:中西書局)。相對之下,因爲《晏子·内篇》本最短且扼要,今且選此本以全録於下:
景公疥且瘧〈(痼)〉,②竹本此字作“”。該字雖然亦可視爲“瘧”字或體,然筆者曾推論過其實該視其“”爲聲符而讀爲“痼疾”的“痼”,而《晏子》内篇的“瘧”是早期抄手誤讀此種“”字的結果;詳情見拙著《楚文“唬”字之雙重用法:説“競公‘痼’”及苗民“五‘號’之刑”》,《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2008年,第387—393頁。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説于上帝,其可乎?”
會譴、梁丘據曰:“可。”
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
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
公曰:“然。”
“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
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③吴則虞編著:《晏子春秋集釋》第42—48頁。此不但如同本篇所分析的大旱故事一樣是有關某種禍患的向神求解法,而且晏子此章用來揭發其荒謬之面的那種極其理性且思路清晰的邏輯推理方法,簡直是如出一轍的。再説此一類的故事及其推理方式在《晏子春秋》一書中處處可見,而於孔子資料的其他篇當中似乎是完全看不到的,實乃足以説明本篇之來源出於晏子類資料的可能性遠比其出自孔子類資料大。①其實此種可能性,曹峰於其《〈魯邦大旱〉初探》已指出過(且在注腳中亦已曾舉過此久病故事之例[《左傳》本])。他説《晏子春秋》既“有相當多的篇章談到天災,談到人事和神事孰重的問題”,又比起孔子類資料“晏子對君主毫不留情的批評幾乎比比皆是”,因而“毋寧説《魯邦大旱》整體風格更接近於《晏子春秋》,而與傳統文獻所刻劃的孔子形象有距離”(第129—131頁)。此種觀點,筆者自然是很贊同的。
誠若如此,則《魯邦大旱》版本之改寫有何用意?首先,加入子貢此種第三人物來强調其理性主義的一面,即能讓主要人物(孔子)通過對其弟子思想之偏重的糾正來更加凸顯出禮之爲貴(即使是違反此種理性的傳統禮俗)以及人情之不可不顧。禮本來即是所以節情,强調此二者本即儒者之特色,而晏子版即使除了强調理性之外亦是兼顧人情的,然晏子無法如孔子教訓弟子般地教訓自己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而《魯邦大旱》之情節方能真正顯出禮儀及人情之重要。此如同荀子之批評墨子相類,如其言“樂”乃“人情所必不免也”,而墨子一律以現實主義爲尚而完全忽略禮樂對人情之熏陶作用。從某一種角度看之,子貢之以理性解釋彼求雨之祭,亦頗類於墨子之蔽於一隅而不知道之全也。然晏子既非純儒亦非墨,與其説《魯邦大旱》是針對晏子思想而隱約加以批評,或不如説是戰國儒家採用此已有之故事而加以儒家色彩,使之能爲孔門之道服務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