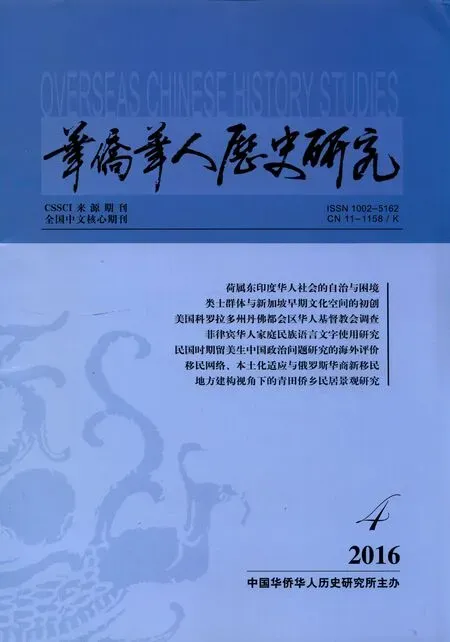社会整合视阈下的制度建构:二战前新马“华校会考”研究*
社会整合视阈下的制度建构:二战前新马“华校会考”研究*
王玉娟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新马华人;华侨教育;华校会考;侨务工作
20世纪30年代,新马华人社会兴起举办华校联合会考的热潮。论文对二战前新马华校会考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建设进行了考察梳理,分析了新马华校会考的影响力。新马华校会考从“民间肇始”到“中英官方主导”,其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在当时殖民地社会华校帮派化、各自为政的大背景下,新马华校会考成为促进各华校之间合作与交流的创新教育机制,同时亦是一种“分”中求“合”的教育措施,激励彼此间的竞争,促进了新马华文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华校会考制度作为华侨教育整合的重要内容,不仅有利于华文教育自身的发展,亦为侨务工作的管理提供了新思路。
华侨教育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新马华人研究的重要范畴。新马华侨教育经历了早期的私塾教育、20世纪前期会馆办学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时期,华校的分散化、帮派化一直是新马华侨教育的特点。但随着新马华人社会的逐渐整合与成熟,华社内部如中华总商会、怡和轩俱乐部、同济医院等跨帮派组织的不断出现,反映出新马华社内在统一的向心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此背景下,新马华校联合会考这一跨帮派的教育活动亦孕育而生。纵而观之,新马华校会考历经1930年福建会馆举办之“民间肇始”、1934年中国驻新总领事馆之“中国官方主导”及1935年被英殖民政府强制接管而具有“英方烙印”的历史嬗变过程。
有关华校会考这一概念已有学者论及,如在颜清湟所著《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叶钟铃、黄佟葆所著《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的研究中,考察了福建会馆主导时期的华校会考,肯定了福建会馆在华校会考初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囿于各种因素却未能对二战前新马华校会考的历史演变与制度建设进行整体系统的考察。[1]此外,当前关于新马华侨教育的研究中,主要涉及华侨教育的兴起、发展革新、华校管理运作等方面。①参见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1998年;吴华: 《新加坡华文中学史略》,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6年;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唐青:《新加坡华文教育》,台北:华侨教育出版社,1964年;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 Toronto : Royal Kingsway Inc,1992年;颜清湟: 《战前新马闽人教育》,《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年;刘宏: 《论二战后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视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颜清湟:《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汤锋旺:《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尽管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细究之下,大多华侨教育之研究主要是对社群会馆办学制度下华校帮派化、分散化的探讨,而对新马各华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机制则着墨不多。华校会考是华文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体现的是华文教育在社群化发展基础上的超社群、整合发展的趋势。反观现有华文教育研究,主要关注华校“分”的社群化特性,忽略华文教育的整合性发展,因而探讨华校会考这一“分”中求“合”的教育措施,有利于更完整地呈现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貌。因此,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思考华校会考如何在华校帮派化、各自为政的背景下促进新马各华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探讨新马华侨教育发展的力量源泉和制度内涵,及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华文教育的整合并促进其发展,这是华文教育管理的制度创新。
一、民间肇始:新加坡福建会馆改革与华校会考(1929—1933)
20世纪初,新加坡许多华校是由华商或会馆创办,会馆办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办学的主要模式,[2]其主要特点是,学校管理、经费筹措等基本上是由学校所属的社团来负责。这一特点决定了各会馆所属的华校之间是相互独立、畛域分明的。
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亦步入进一步整合改组时期。以福建帮为例,1929年陈嘉庚当选为福建会馆主席后,以该组织不够严密为由,着手改组福建会馆。他将福建会馆由总理制改为执监委员制,执行委员会下分设教育、总务、经济、建设、慈善五科。[3]其中,教育成为陈嘉庚改革的重要方面,其目的是“希望新加坡的华侨教育能够统一”。他认为“要统一全侨教育,要先从统一闽侨教育着手,而统一闽侨教育,最要紧的是经费问题”。[4]当时新加坡闽侨学校约有35间,大部分由社团及闽商所创办。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一些华侨学校因经费困难被迫关闭的问题,陈嘉庚提出闽侨教育由福建会馆统筹统办。他将馆业常年利息及公筹捐款赞助闽侨学校,将道南、爱同、崇福三校由会馆直接资助,其余通德、光洋、中华、丹诏、崇德、彰德、益励、钟声、慧群9间学校为辅助学校,其董事职权仍然独立,不敷经费由福建会馆酌量补助。可以说,陈嘉庚对福建帮教育的改革使华校管理更加统一化和制度化,经费来源更加稳定。
在改革闽侨教育后,陈嘉庚即开始落实统一华侨教育的目标。面对殖民时期新加坡各华校散漫不振、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机构的现状,陈嘉庚为谋求华侨教育的统一,提出由福建会馆发起主办新加坡华校会考。1930年,在陈嘉庚的支持下,福建会馆任命林庆年为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会考委员会委员长,开始有序实施华校会考。①此为新加坡华侨林庆年在推进新马华文教育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与创新之举。林庆年就任新加坡福建会馆教育主任后,首倡在华校采用华语教育,继而倡议中小学实行华校会考制度。
第一,设立会考总机构“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1930年11月13日,林庆年召集南洋工商补习学校校长林则扬、南洋女学校校长刘韵仙等10余名华校代表,在发起成立华校会考筹备会及“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该委员会共由15人组成,包括林庆年及各校联席会议推举的9名委员;同时,还聘请当地热心教育人士,共同筹划华校会考事宜。②委员会发起人为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林庆年、工商补习学校校长林则扬、爱同学校校长何欣农、树人学校校长郑鼎新、南洋女学校校长刘韵仙、启发学校校长钟岳南、应新学校校长丘孑夫、振东学校校长林深、道南学校校长郑玄珠,再推定6名热心教育人士加入,即傅无闷、黄俊昌、汪颂鲁、普圣提、李振殿、黄肖岩。这些华校会考委员不仅是新加坡各华校的董事、管理者,亦是所属社群的帮派领袖或重要人物,他们的倡导与支持为新加坡华校会考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第二,发表《新加坡华侨小学校学生会考宣言》,呼吁各华校摒弃地域偏见,积极参加华校联合会考。《宣言》呼吁“以集合许多学校之学生于同一之地点,而考验其学力;察已往之所得,激未来之潜心;启华侨教育一贯方针,系当轴集中情绪;期量质均等,俾收效于宏者也”,其目的是通过各校之间的考试竞争以提高华校的总体教学质量。为此,华校会考委员会宣称,“此举为全侨公开,非任何团体之独断,固造鸿沟,虚约一己,逢场作戏,道谋于渐者也。呼吁,愿有改进华侨教育之志者,进而教之;或未加之学校,踊跃参加,有厚望焉。”[5]可见,该宣言期望通过各校间的竞争提高新加坡华校教育的总体质量,从而实现陈嘉庚统一新加坡华侨教育的最终目的。
第三,制定华校会考详细规则,审议通过《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简章》。《简章》规定会考委员会分设总务、考试、监试、文书、调查、事务六部门,并对各部门具体职责予以详细规定:总务股主要职责是筹募经费、对外交际,公布与考学校及学生名数。具体规定会考学生年级以初小四年级上下学期、高小二年级上下学期为限;会考科目包括国语、英语、算术、常识四科;会考学生所有经费均由福建会馆赞助,每名考生发给车资四角钱,中午期间还有茶点招待。[6]考试股拟定考试规则、考试标准、测验方法。为保证考试的严肃性与公平性,委员会专门聘请外埠华校负责命题,“国语”为峇株巴辖爱群学校,“常识”为柔佛宽柔学校,“算术”为麻坡中华学校,“英文”为马六甲培风学校,但因各校采用教材不同,对出题范围无明确划定。[7]评阅试卷推举非现任教育官员而富有教育学识之人担任。成绩评判以80分以上为甲等,70分以上为乙等,60分以上为丙等,60分以下为丁等。监试股维持考场秩序、监视考生、处分舞弊考生、审查考卷。监试股成员主要由参加学校每校推出教职员一人任之,以示公平。文书股办理本会文书、登记与考学生、监制考卷。调查股邀请各校参加会考、调查各校与考学生名数、学级。事务股职责是购买奖品、布置考场、购买考场文具等。[8]总体看来,华校会考委员会各部门能各负其责、协调合作,最大限度保障华校会考顺利实施。
1930年12月13日,由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各帮派华校参与的新加坡首次华校会考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举行。参会华校有振华、怀德、彰德、南洋女学校、爱同、道南、崇福、崇正、浚源、应新、益励、启发、中华男校、光洋、民正、化南、光亚、丹诏等共计22所。[9]虽参加华校数量有限,未涵盖新加坡全部华校,但参与学校大多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华校,总体上能够代表新加坡华校的水平。根据1931年1月17日揭晓的第一届新加坡华校小学会考各校会考成绩:报考学生共达475名,其中初小四年级(包括上下学期)考生322名,及格者107名,占33%;高小二年级(包括上下学期)考生148名,及格者64名,占43%。[10]总体来看,华校会考总成绩不太理想,但在各华校各自为政的局面下,新加坡华校首次会考能顺利实施已属不易之事。
综上所述,福建会馆的改组和新加坡华人帮群社会进一步整合等外部因素为华校会考的初步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加坡福建会馆内部则通过成立会考委员会,发表会考宣言,制定华校会考具体规则,对华校会考的调查统计、经费筹措、考试规则制定、试卷评阅评判、成绩奖励等予以详细规定,为华校会考顺利实施奠定内部制度基础。同时,华校会考以最大程度凝聚新加坡华人社群力量,破除华社会馆办学畛域分明各自为政的局限性,使新加坡华侨教育突破帮派局限,是华侨教育自发自觉的合作行为。新加坡学者叶钟铃认为,新加坡华校会考开启华侨教育界合作的先声,是新加坡华侨教育的“自主性”或“本土化”的表现。[11]概言之,华校联合会考这一跨帮派的教育活动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外部发展和内部建构整合的重要内容。但是,此次华校会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制度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各华校是否参加联合会考无强制性,致使参加会考的学校数量有限,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华校自由散漫的现状;各校所采用的教材至为纷杂,出题无明确范围,致使第一届会考总体成绩不太理想;在成绩竞争的压力下,造成部分华校只选派优秀学生参加考试造成无序竞争,等等。
此后,福建会馆主办的新加坡华文小学会考实际共举行两届。①由福建会馆主办的华校会考从1930年至1933年本应举办四届,1930年和1931年的前两届华校会考顺利举办,但1932及1933年的两届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致使新加坡经济不景气而停办,因而实际只举行两届,直至1934年由国民政府接手承办。第二届会考于1931年12月14、15日举行,而第二届华校会考闭幕礼,由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副领事李仁主持颁奖,并发表演说,可见中国领事对当地华侨教育的关注,此举实为后来领事馆接办新加坡华校会考之先声。[12]而至1932及1933年两年期间因经济原因停办,直到1934年由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接办华校会考主办权。
同时,随着新加坡华校会考的成功举办及其影响不断扩散,马来亚部分地区有条件的华校也开始组织毕业会考。其中,以1931年马来亚雪兰莪巴生树胶公会和吉隆坡福建会馆两个民间团体发起的毕业生联合会考影响较大,参与者有中华学校、国民学校及中华女校等15所学校。[13]会考资金一部分由巴生树胶公会从会员树胶买卖中抽收捐款,一部分为有经济实力、热心教育的学校董事之捐款。会考命题阅卷及监考,由聘请的教育界名流担任。[14]虽然马来亚参与的华校有限,但此举为华校会考扩展至马来亚地区,进而实施新马华校联合会考奠定基础。
二、中国官方主导:中国驻新总领事与1934年华校会考
从国民政府海外华侨教育的目的来看,华侨教育第一要务是保持华侨的民族性,促进海外侨民对国民政府的向心力和支持力。新加坡华校会考在海外的成功实施,引起了国民政府官员及侨务研究者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海外华侨教育各自为政,成绩良否,不易判明,各校会考,优劣立分,校长教师,不易冒滥,家庭校董有所是从;不比较无竞争,不竞争不进步,各校会考,为最光明之竞争,必收最优良之效果;学生程度参差,升学最有妨碍,欲求整齐划一,只有会考一途;举办各种比赛,促进各侨校联合举办活动,如联合运动会、成绩展览会、演说竞进会等。”[15]因此,如何将海外华校会考纳入国民政府海外教育政策范畴内成为其所考虑的问题。
为此,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华校会考的政策法规,试图由国民政府在海外的常设机构驻外领事馆或侨民教育团体,来主办或直接参与华校会考的整个过程。193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侨务委员会公布《侨民教育实施纲要》,首次提出在海外各地实行华校联合会考,并随时举办各种比赛。[16]1934年2月20日,教育部与侨务委员会公布修正《侨民中小学规程》,规定侨生修业期满,除由各校举行毕业考试外,“应将毕业考试及格之学生,于十日内造具名册及成绩表,呈报该地领事馆,听候会考。会考委员会组织华校会考规程及办事细则。而对有特殊情形,及未设领事馆、距离领事馆过远地方,得由当地或附近曾经教育部及侨务委员会立案之侨民教育团体,代表会考职权,召集会考,若侨民教育团体亦未成立,或该地及附近仅有侨校一所,得免会考,但准免会考之中学毕业试卷须汇送侨务委员会复核。会考或复核及格者,由各该校给予毕业证书,均须呈经该管领事馆或会考委员会验印,中学毕业证书并须送侨务委员会验印。初级小学修业期满、成绩及格,由各该校给予毕业证书,可免会考。”[17]此外,南京国民政府为避免海外华校会考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从1934年起,侨务委员会除了对已立案侨校每月平均补助8400法币元外,还对成绩优良而经济确实困难的立案侨校发给毕业侨校会考奖励金,每月平均883法币元。[18]这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从制度和经费上对参与中小学毕业会考的华校予以指导和帮助。
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中国驻新总领事馆正式介入新加坡华校会考。1934年5月23日,新加坡总领事刁作谦召开华侨教育会议,到会者有华社著名领袖林庆年、林文田、李伟南及各华校代表等。会上,刁作谦提议举办华校会考。为防止英殖民政府阻挠,刁作谦提前与当地英提学司接洽,英殖民政府表态“亦不反对也”;曾主导新加坡华校会考的林庆年亦表示“本人能力所及,自当追随刁总领事,以尽职责。”[19]在获得英殖民政府的默许与华社的支持后,刁作谦提议组织会考委员会,在总领事馆的指导下,召集各华社侨领及所属华校校长等共同筹划新加坡华校会考,负责指导华校会考考试地点、题目拟定、试卷评阅等。
相比福建会馆主办的华校会考,1934年由新加坡总领事馆举办的华校会考在学生年级、教材选定和成绩评定等环节更加规范和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增加初中年级的会考,严格规定各校参加会考学生的范围。根据总领事馆发布的会考规则,考生不仅有各校小学毕业生,还首次将初中毕业生纳入会考的范围;规定测验题目范围应依会考各校初中三年下、小学六年下、四年下之程度拟定;国语、英文、算术、常识各题不应过深亦不过浅。[20]第二,统一考试教材。因会考出题是以各参加会考学校所呈报课本为依据,为严格考试题目和内容,新加坡总领事馆在5月24日即发通告:“本届毕业期间为时已甚迫近,请所有自愿参加本届会考之各中小学校,将学级程度、毕业人数、应试科目所用教材,逐项列明,以便选择地点,定期命题会试,并筹备一切。”[21]根据各校教科书种类编制之不同,最终选定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中文教材为考试内容之依据。[22]第三,严格考试计分标准。根据总领事馆发表的华校会考测验题标准计分法,采用“不扣分”、“不给负分”的计分法,成绩评定分为甲、乙、丙、丁四等。[23]所有试卷由会考委员会考试委员阅卷。第四,组织中华教育研究会,以期改进下届华校会考。6月25日,新加坡总领事刁作谦在华校会考结束后不久即召开教育会议,组织中华教育研究会。[24]其目的是将学识丰富、热心教育、富有名望的华侨人士如胡文虎、陈延谦、李振殿、林世魁、李伟南等聘请为名誉会员、特别会员,从人力和财力上对华校会考予以资助。[25]
经总领事馆和各会考委员协商,由新加坡总领事馆举办的华校会考于1934年6月16、17两日举行。参与华校主要有中华女学校、爱同学校、应新学校、启发学校、端蒙学校等18所华校;①《华校会考名单已公布》,《总汇新报》1934年6月14日。参加学校主要有中华女学校、南洋女子学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爱同学校、应新学校、启发学校、端蒙学校、崇本女学校、崇正学校、育英学校、养正学校、振华学校、兴亚学校、道南学校、新华学校、侨星平民学校、励新学校、光洋学校18所华校。与考实际人数为377人,其中初小学生219名,高小学生123名,初中学生35名。[26]从6月21日华文报刊登载的华校会考成绩来看,初小组112人及格,高小组65人及格,初中组14人及格。[27]具体到学校,初中组第一名为中华女学校,高小组第一名为工商学校,初小组第一名为兴亚学校。[28]总体来看,在自愿参与的原则下,会考学校学生数量有限,但与以往相比,华校会考学生成绩达到及格水平的总体接近半数,实属进步之事。6月25日,新加坡总领事刁作谦召集各考试员、参加各校校长及监考员,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华校会考闭幕总结表扬大会。[29]至此,1934年由新加坡总领事馆谦主导下的华校会考顺利结束,虽然学生数量、成绩未达到理想目标,但其增加初中生会考、统一会考教材、严格考试标准等措施弥补了以前华校会考之不足,并将华校会考的影响力不断向外扩散。
在马来亚,1934年中国驻吉隆坡领事吕子勤在之前巴生和吉隆坡会考的基础上,有意将会考制度扩充到全雪兰莪州。他认为:“像巴生及吉隆坡这两个小规模的会考,可以对于教与学有所促进,极有意义。不过花了双重的人力物力,所影响的范围那么狭小,实在可惜,最好由华校人士,联合起来,举办全雪兰莪州华校小学毕业会考,那就意义更加重大了。”[30]经过他的多方努力,两次召集当地教育界著名人士举行座谈会,最终决定于1935年底举办由领事馆主办的雪兰莪州华校小学毕业会考。但是,在当时殖民地社会背景下,中国领事馆主导的华侨会考遭到了英殖民当局的猜忌和阻挠,“英殖民地政府对于这件事极不满意,认为雪州华校小学所以要毕业会考,是由于中国领事鼓动而促成的,有损害当地的教育权。曾由视学官出面,向诸位筹备委员施行压力,要他们停止工作。”[31]1934年8月底,英殖民地政府突然强行宣布将由英政府提学司署负责主办新马地区华校中小学毕业会考,并强制要求所有华校都参加。由此可知,1935年殖民地政府所以要举行华校毕业会考,乃是“基于政治的意味,与中国领事争夺教育权”。至此,新马地区华校中小学毕业会考主导权已被英殖民地政府强行接管。
纵观1935年新马地区华校会考主办权更迭这一过程,英殖民地政府强行取得华校会考主办权,更多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夺取华校会考主导权作为控制和笼络华侨的一种手段;而中国驻外总领事馆实际管理海外侨务,在控制华侨教育的发展方面要求大部分华校需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接受国民政府派人视学、督查,因此,中国驻新总领事馆努力介入和主导华校会考。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由新加坡总领事馆主办的华校会考仅仅举行了一届,即遭到英殖民地政府的阻挠甚至扼杀。而新马华校会考主导权变更的过程表明,国民政府在海外执行侨务政策时受到殖民地政府和当地社会环境的制约。
三、英方主导:马来亚七州府华校联合会考与1935年后华校会考
1934年新加坡总领事馆主导的华校会考,获得华社的支持与好评,但同时也深为英殖民政府所忌惮。因此,到1935年,华校会考被英殖民地政府强行接管,并被推广到马来联邦,举办新马华校统一会考,即“七州府华校会考”,使华校会考成为英殖民政府华侨教育的三大政策之一。①厉行华校注册制度、发给补助费及举办华校会考制度,是英殖民地政府对华侨教育的三大政策。参见姚楠、关楚璞等:《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年,第645页。
同时,为减少中国政府的阻力,英殖民政府邀请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参与其中,使华校会考由双方共同协商筹办。[32]1935年9月初,英殖民政府华文副提学司署发函征求各华校意见,希望其积极参加英殖民政府主导的华校会考。各华校对于此问题的看法,因顾虑中国政府的态度而有所迟疑。经新加坡总领事与各华校进行磋商与研究,在已经失去华校会考主办权的情况下,总领事馆被迫同意各华校参加英殖民地政府华校会考。[33]在获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各华校遂与英殖民政府联系会考事宜。以端蒙学校为例,该校于9月22日第七次教务会议讨论参加会考事。[34]10月7日,端蒙学校派代表参加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华校会考第一次会议,并商量与考学生人数。[35]会后端蒙学校代表亲赴提学司署缴纳登记与考学生姓名、籍贯、年龄、照片等表格共35份,并带回考生座位号数及会考须知等。[36]
此后,英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华文教育当局统一制定更加完善的全马会考规则,并增加许多新的会考规定。除了小学生、初中生会考外,七州府华校会考最重要的内容是增加师范班参加会考。会考科目小学有华语、英语、算术、史地,[37]初中有华文、英文、数学、史地等科。师范班在三年级时参加会考,四年级时参加教育学科会考,考试科目有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校行政、教育测验、小学教材、教学法。[38]为避免出现为提高竞争而只派优秀考生的情况,考试规定凡是有毕业班级的华校均须参加会考,无论是接受政府津贴还是非政府津贴的华校,不容学校仅选派成绩优良者应考,致成绩统计欠准确。同时,为便于统计及方便学生参加考试,英殖民地政府将华校会考分各区同日及同试题执行考试,各州根据实地情况分设考场。会考考场分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吉隆坡、巴生、英蓉、怡保、金宝、太平、实兆远等地区。因各校所用课本不统一,极难采取统一考试标准,故试题不在任何课本内采取,而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之初中、高小、初小课程标准为华校会考标准。[39]此外,会考监考人员由殖民地政府教育部官员及各地视学官担任,会考各科题目由英教育部制定撰拟。[40]试卷由教育部聘请各州视学员评阅,以示公正,以杜流言。考试各科成绩统计均以50分为及格之最低限度,75分以上为优等。考生有三科及格者,即认为会考及格,及格学生将被英殖民政府教育部授予及格证书。[41]概言之,相比早期小范围的、分散的华校会考,英殖民地政府举办的华校会考扩散到马来亚七州府,在参与学校、考试地点、试题标准及考试监考评阅等规定更加统一完善,效果亦更加明显。
1935年12月2日,由英殖民地政府组织在新加坡和马来联邦两地同时举行的华校总会考如期开考。其中新加坡参加会考22校,包括崇正女校、端蒙学校、养正学校、道南学校、应新学校等,总计学生人数345人。考试地点是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由英殖民地政府副提学司魏坚士与中国驻新总领事刁作谦主持。[42]马来联邦地区雪兰莪有33校,考生418人;森美兰10校,考生97人;彭亨2校,考生33人。[43]考试地点分别是:吉隆坡借用尊孔学校,巴生为树胶公会,芙蓉为锡商公会,彭亨为启文学校等。[44]总体上看,英殖民地政府主导的新马华校总会考在增加参与华校数量和扩大区域方面,最大程度上确保了英殖民地政府动员能力和华校会考影响力的发挥。
然而,从1935年起,名义上由英殖民政府教育当局与中国驻新总领事馆联合举办的华校会考,由于国民政府参与程度较低,华校会考实际上由英殖民政府主导。此情况在南京国民政府《1942年教育部关于华侨教育过去状况与今后改进要点的报告书》亦予以承认:“会考出题的标准虽依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初高中课程标准,但试题由殖民政府教育部出示。南京国民政府参与华校会考的程度较低,各侨校学生之程度,未经国民政府严密考核,仅仅是将华校会考结果,由各领事馆报告(包括试题)到国民政府教育部。”[45]下表为南京国民政府统计的海峡殖民地历届华校会考成绩。[46]

表1 海峡殖民地历届华校会考成绩统计表(1936—1939)
表1显示,1936—1939年,初中和高小会考成绩逐年提高,但总体上及格率尚不及50%,反映出新马华校教育总体水平有待提高;表2显示华校会考各科成绩以英文为最优,史地、国文次之,算术最劣。其原因在于,殖民地时期的各华校重视知识学习的实用性,表现在注重英文教育,有的华校小学一年级就有英文课。而英文总体水平较高将有利于学生毕业后在当地找工作,这是教育本地化的反映。部分学生国语程度较低,甚至“初中国文成绩大部分程度不过等于初中一、二年级,而劣者且未必优于高小生所作”。可见若无国文等成绩的改善,则学生总体教育水平程度仍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表2 海峡殖民地华校历届会考各科成绩统计表(1936—1938)
据统计,战前英殖民地政府共举办6届华校会考,直到1941年日本侵略东南亚,新马两地沦陷,华校会考遂告停顿。1945年9月,马来亚光复后,华校陆续复课,但经过战争的破坏,一切因陋就简未上轨道,因此,华校毕业会考直到1947年才恢复举行。1935—1951年(除去中间日本侵略东南亚而耽误的4年)新马华校会考共举行13届。[47]总体而言,英殖民地政府主办的新马华校会考,持续时间长,规则制定完善,真正使华校会考在考试规则制定、考试时间地点、试卷标准评判等一系列过程中实现统一化、标准化;同时,这一时期新马华校会考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许和华校的大力支持,举新马两地之力量为华校会考的举办、管理和实施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以确保华校会考能正常、有序地进行。
四、新马华校会考影响之分析
20世纪初以来,对新马华侨教育的争夺与控制是中国政府与殖民地政府争夺华侨认同的一个重要措施,二者都把华侨教育作为控制和笼络华侨的一种手段。[48]南京国民政府为控制南洋华校,先后颁布约50项侨民教育的政策法规,规范海外侨教,要求华侨教育宗旨、侨校管理、课程学制、注册立案、教科书选用等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而大部分华校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侨务委员会、驻外总领事馆的实际管理与视学督查,这就很大程度上使南洋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与此同时,新马英殖民地政府则运用国家权力,以立法的方式控制华校的发展。如采用强制立案注册法令限制破坏侨教,或是采用奖励津贴、支持办校等形式同化华侨,其最终的目的是控制华侨教育,削减中国政府对华教的影响力。因此,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前的华校会考是中英两国争夺与控制新马华侨教育的重要措施。尽管华校会考主导权不断变更,期间各方或竞争或合作,亦或停办,然而新马华校会考的意义及影响不容忽视。
首先,新马华校会考从“民间肇始”到“中英官方主导”,其管理制度不断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会考主导权几易其主。最初时福建会馆担负起举办华校会考的使命,是新马华社民间的自发行为,而随后的中国官方和英殖民地则是政府行为,并且三者彼此间存在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表明华校会考受中国政府、华人社会以及殖民地政府三方面的制约,正是这三方的互动最终不断塑造和完善了华校会考制度。第二,华校会考制度规则不断完善。华校会考在选择委员会成员、考生年级、出题改卷标准、监考评定等各环节逐步完善,不断克服以往管理混乱的弊端。第三,华校会考效果明显。其成效不仅表现在参加会考人数不断增加,学生成绩逐步提高,更表现在新马华社对全体华校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视。总之,新马华校会考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对华侨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
其次,华校会考推动了新马各华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激励彼此间的竞争,促进了新马华文教育的统一化、规范化。二战前新马华校办学形态主要是“会馆办学”,其被人诟病之处在于帮派观念根深蒂固,彼此之间缺乏交流。华校会考则以超社群结构为基础,最大程度凝聚华人社群力量,使新马华侨教育真正意义上突破帮派局限,促使华文教育发展到新的阶段。此外,海外华侨教育自产生以来各自为政,侨校水平和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成绩良否,不易判明。而新马华校毕业会考,则通过统一考试和各华校的竞争,提高华侨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换言之,“一可整齐学生之程度,二可激励学生之竞进,三可养成学生严肃之纪律,四可祛除各别考试时所发生之种种流弊,其方法之良,用意之善,莫过于此。”[49]当华校会考的成绩一经发表,“报纸便大事宣传,往往不惜花费精神,统计某校与考生若干名,及格率所占比例,优良的成绩,谁占第一位,谁占第二位等。”[50]如此公开成绩并大肆宣扬便给成绩相对靠后的学校带来极大的压力和进步的动力。因此,《南洋商报》发文《马来亚华校会考揭晓》,称赞华校会考制度是提高海外华侨教育的良策。[51]但华社对华校会考并非一致的赞扬声音,1937年新加坡《爱同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发表文章《会考制度应废止》,引用国内教育大家陶行知、陈衡哲等批评会考制度的言论,称华校会考因循国内模式,未考虑当地教育现实状况,甚至有华校为提高成绩而逃避规则,从而造成不良无序竞争等弊端,违反了华校联合会考的初衷。尽管华校会考引起某些批评,但华校会考的优势却不容忽视,华校会考制度对统一华校教育水准和提高华文教育的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华校会考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华侨社会,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侨务工作发展。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曾告诫:“世界之进化无尽,我同胞事业之进步,与之无尽。盖今世商战、工战,无非学战。”[52]而海外华侨教育是争取华侨认同的一个重要措施。新马华校会考凸显国民政府和英殖民政府,都“积极”参与华侨学校教育的管理与监督,试图控制与争夺新马华校会考主导权。然而,就新马华侨社会而言,其虽认同中国政府为祖籍国,但现实环境是处于英殖民当局的统治下。新马华侨教育一方面受中国教育制度的影响,传承中华文化和保持民族特性是其教育宗旨;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适应其所居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法律,如对英文教育的重视。可见华校会考虽是华文教育发展的制度创新,但受中国、华侨社会以及殖民地政府三方面的制约。换言之,对新马“华校会考”的探究基本上诠释了华侨社会在殖民地环境下生存、发展与妥协的历史事实,实为研究海外华侨与中国政府及殖民地国家关系的生动写照。概言之,政治因素成为影响新马华校会考及海外华侨教育的重要因素。就华文教育及侨务工作发展来说,中国政府的侨务工作与海外华侨社会结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侨务政策的制定需要注重华侨社会结构的双面性,即“分”与“合”,并把握其中的度,妥善处理与利用各方力量而达到最终目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侨务工作的开展。
五、结语
华校会考是华文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华文教育社群化发展基础上整合趋势的体现。在现有华文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社会整合视角来探究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以更好呈现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全貌。通过对华校会考制度的发展演变、制度完善及其影响,来思考中国政府、华侨社会结构与华文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华校会考制度从民间到官方的发展轨迹,显示出华侨社会自主性发展与外部因素之间的关联。华侨社会的自主性既需要注重华侨社会内在规律,也受到外部客观环境的制约。唯有在平衡各方因素基础上,才能保障其自主性的良性发展。第二,华校会考制度的研究显示出华侨社会解构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双重性影响,华校会考制度正是在这种“分”“合”并存的社会结构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华校会考制度作为华侨教育整合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利于华文教育自身的发展,亦为侨务工作的管理提供了新思维。
[注释]
[1] 参见颜清湟:《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庄国土、林忠强:《东南亚的福建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页;叶钟铃、黄佟葆:《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21页。
[2] 汤锋旺:《二战前新加坡华人“会馆办学”研究》,《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4期。
[3] 《福建会馆第一次委员会议昨晚在怡和轩开会记略》,《叻报》1929年3月6日。
[4] 叶钟铃、黄佟葆:《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20页。
[5] 《新加坡华侨小学校学生会考宣言》,《新国民日报》1930年11月19日。
[6 ] 《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规则》,《新国民日报》1930年12月16日。
[7 ] 《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通告》,《新国民日报》1930年12月12日。
[8] 《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简章》,《新国民日报》1930年11月26日。
[9] 《新加坡华侨小学学生会考委员会通告》,《新国民日报》1930年12月12日。
[10] 《华校会考成绩公布》,《南洋商报》1930年12月13日,1931年1月19日。
[11] 叶钟铃、黄佟葆:《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29页。
[12] 叶钟铃、黄佟葆:《新马印华校教科书发展回顾》,新加坡:华裔馆,2005年,第28页。
[13] 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Toronto : Royal Kingsway Inc,1992年,第249页。
[14] 《教总33年: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1951.12.25—1985.4.8)》,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年,第544页。
[15] 《为华侨教育敬告侨胞》,《南洋研究》第四卷第三期,1932年7月1日,第422页。
[16] 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04页。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档案出版社,1994年,第934页。
[18] 《中政会议决补助华侨学校经费》,《华侨半月刊》,1934年第49、50期合刊,第34~35页。
[19] 《刁总领事昨晚召开华侨教育会议》,《总汇新报》1934年5月24日。
[20] 《华校毕业会考之测验标准及规则》,《总汇新报》1934年6月6日。
[21] 《总领事馆通告一则,为华侨学校毕业会考事》,《总汇新报》1934年5月25日。
[22] 《总领馆为华侨会考事,催促各校速填两种调查表》,《总汇新报》1934年6月8日。
[23] 《领馆通告会考计分法》,《总汇新报》1934年6月15日。
[24] 《端蒙校刊》1934年第3辑第4期,第78页。
[25] 《侨务月报》1934年第7—8期,第123页。
[26] 《本坡华校会考今日在工商学校举行》,《总汇新报》1934年6月16日。
[27] 《本坡华校会考昨在商会举行闭幕礼》,《总汇新报》1934年6月26日。
[28] 《华校会考得第一名者》,《总汇新报》1934年6月22日。
[29] 《端蒙校刊》1934年第3辑第4期,第78页。
[30] [31]林连玉:《回忆片片录》,吉隆坡: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出版委员会,1963年,第41~46页。
[32] 颜清湟:《福建人在马新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林忠强、庄国土主编:《东南亚的福建人》,2006年,厦门大学出版社,第14页。
[33] 《新加坡端蒙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第35页。
[34] 《第七次教务会议议案》,《端蒙校刊》,1935年第4辑第5期,第82页。
[35] 《举行参加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华校会考第一次会议》,《端蒙校刊》1935年第4辑第5期,第90页。
[36] 《华校会考报名》,《端蒙校刊》1935年第4辑第5期,第91页。
[37] 《会考要点》,《总汇新报》1935年9月3日。
[38] 周聿峨:《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4页。
[39] 《全马来亚华校将举行总会考》,《总汇新报》1935年9月3日。
[40] 《七州府华校总会考已截至报名》,《总汇新报》1935年10月17日。
[41] 《会考要点》,《总汇新报》1935年9月3日。
[42] 《七州府华校总会考今日一律举行》,《总汇新报》1935年12月2日。
[43] 《七州府华校总会考已截至报名》,《总汇新报》1935年10月17日。
[44] 《吉隆坡芙蓉彭亨华校会考地点决定》,《总汇新报》1935年11月7日。
[4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档案出版社,1997年,第280页。
[4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237页。
[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第238页。
[48]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5页。
[49] 《星洲日报半月刊》第12期,1938年12月15日,第13页。
[50] 林连玉:《回忆片片录》,吉隆坡:马来西亚联合邦华校教师总会出版委员会,1963年,第41~46页。
[51] 《1937年新加坡爱同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第6页。
[52] 黄炎培:《关于菲律宾华侨教育意见书》,《东南洋之新教育》,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06页。
[责任编辑:密素敏]
·书讯·
《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出版
美国布朗大学民族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胡其瑜(Evelyn Hu-Dehart)教授著、周琳翻译的《何以为家——全球化时期华人的流散与播迁》一书,于2015年6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龙登高教授主编的《社会经济史》译丛之一。
全书约20万字,由《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华工与华商》《移民与发展中的社会——墨西哥北部的华人》《北下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1910—1934)》《自由劳动力抑或新型奴隶制——19世纪古巴和秘鲁的中国苦力》《鸦片与社会控制——秘鲁和古巴种植园的苦力》《“黄色贸易”与大西洋中央航线(1847—1874)》《假想敌还是替罪羊?——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排华运动的检视(1870—1930)》《唐人街与边境——亚裔移民的交往与冲突》《西属马尼拉——穿越太平洋的海上冒险与美洲第一个唐人街》等9篇论文组成。这些论文讲述在全球化进程中,华人移民在拉丁美洲、加勒比、东南亚等地区迁徙与谋生的曲折故事。这些流离播迁的人们,在改写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参与塑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至今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世界。(乔乔)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Joint Graduation Exam in Chinese Schools of Singapore and Malaya before the World WarⅡ
WANG Yu-j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Chinese education; Joint Graduation Exam in Chinese School;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n the1930s, joint graduation exams became popular in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his paper traces back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joint graduation exams in Chinese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nd analyzes its influences. Lacking of standardization among Chinese schools, the joint graduation exams foster collabora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schools, stimulate positive competi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e standardization. As an important propor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joint graduation exams not only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but also provide new idea for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G749.33
A
1002-5162(2016)04-0019-11
2016-09-23;
2016-11-06
王玉娟(1984—),女,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
*本文为云南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新马地区华校会考为例》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