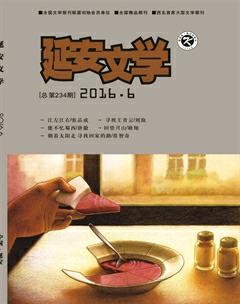江左江右
张品成,湖南浏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红刃》《北斗当空》等二十余部。曾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十四届冰心文学奖。
一
书童崔工利那时不知道他已经做了人家的书童,他坐在破屋前的大石头上看天。他哥崔工胜一脸的心事重重的样子,灰褐色的天空和蝗虫弄出的满地狼藉,让他心上更塞满乱草。哥哥心里惦着的是弟弟今后的日子。那天,吕大每说跟了他去当兵吃粮,他还觉得事情很遥远,当兵吃粮呀,饿不了肚子哟。搁过去,队伍上招兵买马那是个难事情,要抓丁。可现在不一样,这一年先是涝,后是旱,然后是蝗虫。你看蝗虫把粮弄了个精光,队伍上也没粮的,还多添那么多嘴?鬼信!人都挤破了头想去队伍上。当兵有衣穿有饭吃,总比逃难要好。
崔工胜不知道蝗虫漫天飞舞那天,洪天禹站在窗前得意地笑着。
许世魁那些天陪了他的长官。谭副官死后,许世魁一直陪伴在洪天禹的身边。除了洪天禹上窑子他不随身外,基本就贴身做陪同和保镖。
许世魁看见洪天禹莫名的笑,说:“要死人的,这蝗虫过去皇帝都怕,你还笑?”
“是我洪天禹走运的时候了。”洪天禹说。
许世魁后来明白他说的是人马。
洪天禹趁了天灾扩充了他的人马,是他开心的理由。崔工胜也因此入了队伍从此衣食无忧,也是他开心的理由。
不开心的是想到弟弟。
崔工利十一岁,但人长得瘦小,看去不到十岁样子。人小心却大,镇上有说书的来,挤进去听,恨不得每一个字都不漏了。说三国说水浒说薛仁贵征西,心上一些芽芽就冒呀冒的,常常幻想了从军做元帅将军。
富前来了队伍,他亢奋了几天,天天看人家操练。
他哥崔工胜和富前的一帮后生入了队伍,崔工利的脸黑了有几天。有人说:“哎哎!是谁欠了你的米还的是糠吧?”
他说:“没人欠我米谷我也没欠人米谷。”
“那你脸拉成这样?”
崔工利朝人翻白眼,“为什么队伍上就不要我呢?”
有人牵过那匹马,指了指马背,“你骑上去我看看。”
崔工利试了好几回,他没法骑上那马背,不仅没骑上去,连那马都欺他,扬起蹄子扎实地给了他两下,害得他屁股痛了近半月。出门,走路一瘸一拐,身后就有许多指戳嘻笑。他羞丑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了。他恨死了那个人恨死了那匹马。后来他知道,他不该恨那人那马,没有他们,也没有他崔工利后来的一切。
他真的入了队伍,事情像做梦一样。他哥跟他说,你给我记住了,从今后你要管住你那张嘴,师长要找个石头嘴的书童,你嘴多话多,你不管住你这差事就丢了,不仅差事也许命也丢了!崔工利很坚决地给他哥说,就当我的两片嘴皮叫刀割了哟,我会管住的。他哥说,你要管不住,信不信我真割了你嘴皮。
他们给了他一套小号军服,他穿了还耷拉出好长一截。他哥要给他剪裁下,说你这么的不好看。但崔工利不肯。说师长给我的衣服我不能改,我要好看干嘛?我要我是个兵。
他成天穿了那身衣服走上窜下的,屁股眼里三把火烧了,坐不住。忙上忙下,拎了水烟壶,说:“师长,我给你点撮烟。”拎了水壶,壶嘴上热气腾腾,说:“师长,我给你泡杯茶。”拎了酒壶则说:“师长,来一口来一口!”
然后就是去找书。师长说:“工利,你要多费点心思给我找书。”
崔工利就屁颠屁颠地四处跑,走村串户给师长收书。
很多人大眼小眼地看了他,“当兵打仗,抢地盘,攻城略地称霸一方,要书干什么?”
“我们师长他要。”
“噢?!你们师长也不识几个字,他读什么书?”
他朝人家噘嘴翻白眼,“谁生来就认字的?”
人家看他那架势再说下去就要发飙使性,收住了嘴。有人就把一些闲书散页敷衍了塞给他。崔工利当然也不识字,分不清书高低好坏,有成册的纸,纸上印有字就是书。就全尽收到匣子里,他总是满载而归。他挑了那两只书匣,大汗淋漓却兴致冲冲地把担子撂到洪天禹面前。
洪天禹一脸的灿烂,拣起几本书翻了翻,朝他的书童竖起大拇指:“好小子!”
柜顶上有包枣,洪天禹抓过来抛给崔工利,“周长官送给我的山西交城骏枣,赏给你吃吧!”
崔工利打开,红红的枣色泽鲜亮。他不吃,他把枣包了一层又一层,用麻绳缠绑了挂在胸前,晃荡了到处走。
人说,“你脖上挂了什么?”
“师长的枣,师长给我的枣。”
“师长的枣也是枣,难道能是金子?”
“那不一样!”
“来,拈颗我们尝尝,看一样不一样?”
崔工利不肯,他脖子上吊着那包东西晃荡了一天,把富前角角落落全走了个遍。黄昏的时候,他坐在场坪处废石磨嚼食枣子。有人过他就会递上一颗。“哎哎!洪长官的枣喂!”
又说:“你不是要尝尝师长的枣的吗?来你拈一颗。”
大家都那么嚼了,崔工利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觉得大家都嚼出滋味,心里花就开了。还剩了一把,他抓掌心里不肯给人。
“我要留了我哥尝。”他说。
他哥崔工胜去了火车站,他要送下二舅潘耕晨。到天黑人才回来,他弟那把枣一直捏在手心,递给崔工胜时,那枣软成了泥。
二
师长的屋子里堆满了书。这让崔工利很开心。他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人不识字,辨不出书的好坏,只有新旧之分。
师长说:“初八要开拔了,你把书给我装箱了。”
崔工利就一心一意整理那些书,新旧的分开,新的用木箱装了,旧的呢,能装箱的装箱,不能装的就用草绳随意捆了。
他做得很认真,一丝不苟。
崔工利做的另一件事是去遛马。他永远记得那马的事。第一次他想亲近那马,那马却扬起蹄子扎实地给了他两下,害得他屁股痛了十几天,重要的是让他丢人现眼。他想着有一天要好好地教训那畜牲,但那只是想想,他知道那一切遥不可及。马是师长的马,打狗还欺主哩,他敢动那马?另外,那马很机灵,说不定还没等他下手,又会给他来那么两下,他有些害怕。
他没想自己能做师长的书童,书童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师长做马夫。师长的马夫老了,师长说你也到了该休歇的年纪了,让别人来做这些事吧。
崔工利又一次要走近那匹枣红马。他小心地往那马身边挪步,但很奇怪,那马很本分,他抓住了那根缰绳,小心翼翼地靠近,眼睛盯着马的那两条后腿。那两条腿很安静马也很安静。他拍了拍马背,“伙计……”他说,“原来你也是个势利眼的呀,也知道我做了师长的书童就另眼相看了吗?”马打着响喷,很友好的样子,他们成了朋友。
成了朋友就无话不说,那当然说的是人,和马就是真成朋友也不能无话不说的嘛,马又听不懂人话,马更不会说人话。
崔工利牢记了他哥给他说的话。在师长身边,把两片嘴皮管得牢牢的,把那些话憋在肚子里。他想,憋了憋了话就烂了变成了空气,烟消云散。但事情却不是那样,那些话像些小鬼,关在他肚子里也不安分,他常常觉得憋得难受。他想,他得想办法,不然,他真的会被话憋死。那些话一天一天在他肚里堆了积了,他感觉自己要被什么撑成一坨老树蔸。
那不成,工利是做将军的料,有一天会成张飞关云长赵子龙,他跟自己说。
我还能让肚里那些闲言碎语坏了我事情?他想。
他找他哥说,他哥没接话,直接就刮了他一巴掌走了。
崔工利去遛马,脸上还挂了他哥的掌印,红胖起一片。
他们不让我说话!他们都狗东西不让我说话……人又不是马,长了嘴光用来吃东西,人长嘴除了吃东西得说话。
我又不是哑巴,我得说,我不说这张嘴就坏了废了。嘴坏了将军就做不成了,这不成,我得说!不能跟人说我跟你说总成,我以后就跟你说吧!
那天,他终于找到办法了。他想,跟人不能说我还不能跟马说吗?
他跟马说,他只能跟马说。
他对那匹枣红颜色的马说:“他们说队伍要往南边去哩,可是一直就没动静……,我看这两天该动了哟……为什么?你问为什么?哈,这不明摆了么?没吃的了,蝗虫把一切都毁了,队伍上这么多人喝西北风呀……”
队伍确实在第三天开拔的。
崔工利跟那些大人们想的不一样,他脑壳里没塞麦秸棉秆,塞的是那些梦境一样的想象,是那种战火硝烟枪林弹雨里自己各种冲杀的想象。那么一大片的麦田,两军对垒,互相大瞪了眼,一片寂静,但却弥漫了杀气,杀气腾腾。将军举了令旗,当然洪长官,人高马大的师长骑在那匹枣红马上,手里的令旗在风里张扬,急不可耐。突然,师长一挥手,军令如山呀,将士奋勇。崔工利想象中的自己也夹在队伍里。拿了刀,一抡扯一道光,对方脑壳就落了地,西瓜一样滚;拿了枪,一抠火子弹就在对方身上穿胸而过。天兵天将呀,千军万马,那呼啸而涌的哪是兵马?是一团风,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然后,是那片场坪,戏台前一块场坪,队伍里的人都齐整整列队那地方。师长坐着,还有那些军官站在师长的身边。然后是一些士兵,衣服当然齐整,风纪扣什么的一丝不苟,不一样的是他们胸前都戴了花,大红的花。他们是英雄,当然戴花。他想他得把胸脯挺得高高,他得让那大红花更醒目,他想,他哥看得到吕司务长看得到队伍里的兄弟都看得到全镇的老少都看得到,不仅活了的看得到,就是墓里的爷娘也看得到。他们看到的是两朵花,一朵在胸前,一朵是自己的脸,自己的脸笑得跟花一样……
吕大每终于贴着崔工利的小耳朵说:“就这几天的事,队伍要有动静了。”
崔工利说:“鬼晓得,叫给书装箱已经半个多月了也没动静。”
“你看就是,就这几天。”
那两天,崔工利给枣红马加了些料,“说你多吃点,吃了有力气,要行远路了。”
果然,三天后,师长集合队伍下了开拔的命令。可师长骑上那马没多久就下来了,队伍也行军没多久就用不了那双脚了。他们上了火车,还有那匹师长的坐骑和那些书。
崔工利一直噘了嘴。
“哦!你哥骂你了?”崔工利摇了摇头,“他们不让我上前线……”
“那是,那地方也不是你们毛孩子去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
“要死人的嘛。”
“你们死得我就死不得?”
吕大每侧过头认真地看了看崔工利,“你小嘛!”
“小就怕死?!”
“没人说你怕死……是你太小,不适合去那种地方。”
“那我是兵不?”
“是呀,你穿了军服在队伍里吃喝怎么不是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这话没错呀。”
“没错长官不让我去?”
“还有一句你也知道的……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崔工利翻白眼了,他朝吕司务翻了好一阵子白眼。“我知道了……你们是怕我抢功,你们怕我做英雄好佬,风头盖过你们……”
吕司务笑了起来,手里那箩筐砰然落地,他笑得前仰后合的,“你个鬼工利哟,你要笑死我了,你脑壳里塞的是什么哟……”
崔工利满脑子想的是能征战沙场,满脑子是战马啸啸杀声震天的刀光剑影火光冲天那些场面……到队伍里的第一天,他脑子里就装满了这种想象。那些东西,像酒一样发酵,越来越浓烈。他以为到了这地方,怎么说洪长官也会带了他在身边。他是随从嘛,随从当然形影不离。可他们真把崔天利当成书童,书童应该在书房,而不应该在战场。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但不管崔工利怎么想,他还是和几个伤病留在了后方。
队伍是清早出发的,没有带上炮,一是因为没有路,那炮就不能动弹,不能动弹就成了一堆铁没了用场。不拉炮,那些马还是有用场的,拉别的东西。装备和粮草多多益善。枣红马当然是洪天禹的坐骑,马走险路安稳,在山里,马是好东西。
三
他哥和谭多年几个在喝酒。他们经历了一场战事,虽说没放一枪,连对手的影子也没看见,但到底是上过战场了。他们觉得很走运,没像那一营人一样被红军截了生死不明,也算是大难不死吧,看起来必有后福。然后他们就聚一起打平伙凑份子买酒买菜,他们正喝着酒。
听崔工利说那些事,听来听去的也听不明白。他们说:当兵的管那么些事干什么?当兵吃粮,一条命吊在裤腰带上,长官说东往东,长官说西往西,死了一堆黄土埋身,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不死,拼出点名堂论功行赏……都看命,是不?
他们说喝酒喝酒,操心那些事干什么?管他谁鹬谁蚌谁渔翁呢。
崔工利有些憋闷,“就知道喝酒,长官的事不是你们的事吗?”
崔工胜和几个兄弟对视了一下,觉得这个弟弟话来得突然。他朝他弟瞪眼睛,但他弟不惧他,他弟不朝他看,崔工胜知道吕大每在,他弟就敢和他对了来。崔工胜说:“你个娃,你管那些事?”
崔工利说:“我没管,我只是问问。”
崔工胜说:“你要我撕你嘴皮子揪你耳朵吗?”
吕大每护住崔工利,“你个工胜哟,你就晓得拿你弟出气!”
“我出什么气?!”
“他们说你今天手气背,输了钱……”
“那是……但我没什么气,牌桌上的事,有输有赢那没个什么哟……我是说工利他没记性,他把你的话忘脑后了。”
吕大每和崔工利都看着崔工胜。
“你没记住吕大哥过去是怎么跟你说的?”
“说什么了?”
“在洪长官身边,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看了,就当眼前云,不要在脑里过;听了就当耳边风,不要在肚里藏……这话你忘了?”
吕大每说:“是哟是哟……工利呀,你真把大哥给你讲的话忘了?”
崔工利脸就白了,他知道这一次,他将失去吕大每对他的保护,他确实犯了错不是一般的错是大错。他想,他这一回在劫难逃的了,他要挨他哥那么几下了,不是一个耳光就是一个“栗子”,他们管捏紧了拳头在脑门或者后脑上猛敲那么一下叫给你一栗子。他沉默了,把眼闭了,就是说他默认了。人倒霉盐缸也生蛆。我忍了哟,我下次再也不这么了。
有人在他头上磕了一下,没那么疼。
崔工利睁开眼,给他一“栗子”的不是他哥,是吕大每。
吕大每黑了脸,“你要是还想在洪长官身边呆了你记住了!”
泪从崔工利两眼里涌出来。
“我……不,不想走的哟……”
“那你听好了……还是那句!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的不要听……看了,就当眼前云,不要在脑里过;听了就当耳边风,不要在肚里藏!”
“我记住了!”
书童崔工利不太爱读书,但他是书童,所以必须陪了洪长官读书。
因此,他不喜欢读书,但还得有模有样地读,有板有眼咿呀地吟。手里捏着一卷书,眼睛盯在书页上,但那些字如蝌蚪,总在那小小的一方纸上游,没有一个能游进他的眼里。
崔工利找他哥崔工胜,他说:“哥,你手里的枪都要成烧火棍了?”
他哥瞪大眼睛看他,“成烧火棍成烧火棍了嘛,你操心个什么?”
崔工利想跟他哥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句话,他先前也曾跟他哥说过,得到的是一记耳光。他想他要再说那句话的话,他哥那只巴掌会风一样掠过来在他脸上开花。他没跟他哥说出那话,但他跟吕大每说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说。
吕司务长笑了,“用呀,谁说没在用?”
“哪用了嘛?哪交火了嘛?”
“哦!非得交火才算用?你看大家守着这条防线,你看大家不是都在忙,也没看有人闲了……”
崔工利说:“是没人闲了,玩牌九也是忙吗,喝酒逛窑子也是忙吗?还有人上山打猎,下河摸鱼……都是忙吗?”
吕司务抬起手张开巴掌,他没抡过去,他伸过去轻抚了一下崔工利的额头。
吕司务长说:“你看你这小脑壳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哟?”
“我说错了吗?”
“你不该想这事的……”
“我怎么就不该想这事了?我穿了这身衣服就是士兵了,士兵就该想这事。”
“洪长官都不操心,你操心个什么?”吕司务说。
崔工利没把心里所想说出来,他不是操心,他是急切,没有仗打,没有刀光剑影,哪来的英雄?崔工利满脑子都是将军梦,也许男孩都这样,好斗尚武,喜欢冲冲杀杀的事儿,喜欢冒险逞能。不知道天高地厚,更不知道忧愁滋味……
没人理会崔工利的话,并不代表没人理会他。大家觉得这娃儿小,就想带了他去船山玩。他们说,去船山赶集哟,那是个好地方。
崔工利常听吕司务和他哥崔工胜那些队伍上弟兄说起船山,他们说那里的烟好酒好人更好,他没听出他们说的“人”有具体的含意,他们注意到那些士兵说“人”字时脸上有隐晦的什么显现,有莫名的笑。崔工利弄不懂,他只觉得他们怪怪的。船山是个镇,当然有人呀,不仅有人,而且是有很多的人。镇子是个大镇,镇子上住了很多人。还不时有四面八方来的客商,他们随水而来。还有那些山里的农人,男女老少逢墟赶集而来,那天人就更多了,人山人海。
他弄不懂他们说“人”,不懂不懂吧,人并不是什么都要弄个水落石出。而且,他看出或者说感觉到,吕司务他哥他们那些队伍上弟兄总是对他隐瞒了什么。隐瞒什么呢?他不知道,但隐隐感觉。
他只知道吕司务他哥他们那些队伍上弟兄喜欢去船山,开始他没想去那地方,但吕司务他哥他们那些队伍上弟兄对那地方说得多了,崔工利就上心了。
他跟他哥说,“你带我去船山。”
他哥说,“你去那地方干什么?”
他说:“你们去得我就去不得?”
他哥不理他了,绷了脸。他最怕他哥崔工胜绷脸,就不吭声了。
他不明白他哥为什么不愿意带他去。崔工利找到吕大每。
他说,“叔,我为什么不能去船山?”
吕大每说,“谁说你不能去船山了?”
崔工利说,“我哥他不带我去,为什么你们去得我去不得?”
吕大每笑了,“你哥是担心洪长官不给假吧,你是洪长官的书童,你得陪了洪长官。你没看洪长官他不去船山的吗?”
不说,崔工利还真没留意这事,吕大每一说,他真就注意到了,是的哟,没见洪长官去过船山的呀,而且,洪长官挑了那么个地方做团部。谁都大惑不解,那里离船山很远。吕大每说,人家长官,人家不会把指挥部放在防线上。这么说,大家就释然了。但远是远了点,可洪长官有马,路途不是个事。就是步行,走也就两三个钟点的事嘛。
洪长官为什么就不去船山呢?
崔工利搞不清楚,那些士兵也搞不清楚。
崔工利跟长官洪天禹说起这事,他想请一天假去那地方耳闻目睹。洪天禹侧过头眉头皱了一下,说:“你个娃儿去那地方干什么?”
长官洪天禹没准崔工利的假,崔工利后来发现长官洪天禹自己从不去那个叫船山的地方。为什么不去,他弄不明白。但长官不去,自己要去那地方的想法就有些非份了,他是长官的书童,他就是长官的影子,长官不去他当然不能去。
长官洪天禹没再说什么,起身往那边拱了下下巴。崔工利心领神会,他走过去取下挂在墙壁上那支匣子。
洪天禹一直喜好火器,也就是喜欢收集各类枪。当然,火器中包含有炮,也是他所喜欢,但他只弄了门迫击炮,别的炮搬不动,那些山炮他格外青睐,可他没办法。他只有收集枪。在他看来,枪炮是天下最好东西。他有句口头禅经常挂嘴上,人说话不如枪说话炮说话。他有间存放枪支的屋子,里面摆满了枪,四壁都挂有各类枪。有洋的也有土的,那有几杆铳,有打鸟的也有打兽的土铳,有长铳也有短铳。有人说那几杆铳就算了吧,放在洋枪堆里扎眼。他说铳也是火器呀。其实他没把内心的真实想法与人说,他拉人进山时使的就是一杆铳。就是说起家时用的就是铳,他怎么能把铳忘了呢?
那些枪都是从四面八方收集来的。也有别人送的,那些乡绅知道洪天禹嗜枪如命,都想了法子到处弄枪作为礼物送给他。送钱送物的洪天禹司空见惯也就点个头作个揖淡淡的一个谢。但送枪就不一样了,洪天禹眉开眼笑,无论长的短的,都要拿了在手里把玩好一会儿,然后说:好东西!谢谢了噢!
因此,书童崔工利的另一项工作是给长官洪天禹擦枪。开初他觉得做那事有点那个,枪干净得很嘛,干嘛要擦?弄两手油乎乎的,有时还沾在脸上身上。但听洪天禹跟他讲枪,看长官洪天禹拆枪装枪,就看出兴致来了。觉得事情很玄乎神秘,就那几砣铁,拼装了就能成一支枪,就能射出子弹把活跳跳一个人的命给收了。他也喜欢上那些火器,有事没事他就想摆弄那些长枪短枪。
枪放在屋子里也难得沾上灰,崔工利擦枪总要找理由。“你看你看……”他跟洪长官说,“天落了几天雨哟,那些枪得擦下上上油,不然就锈了嘛。”
“擦嘛!”洪天禹说。
天要是不下雨,连了大晴天,崔工利一样有话说。
“我听到老鼠在那屋子里唱戏哟还打架嘛。”
洪天禹很淡定,说:“那也没米谷,老鼠要在那疯让它们疯好了。那一屋子的枪,难道老鼠能咬铁?”
崔工利说:“老鼠咬不了铁,但老鼠到处屙尿的嘛……”
洪天禹依然没当回事,说:“屙尿让它屙就是。”
“你看你说就是……你以为呀?”
洪天禹又那么睁大眼看他的小书童,“哎哎……以为什么?!”
崔工利说,“老鼠尿坏东西,铁沾了长锈生斑……”
洪天禹一听就急了,“擦枪!快去擦枪!”
崔工利就钻进那间屋子,他擦枪是假,但在里面玩枪是真。
四
洪天禹喜好火器,潘普昭当然投其所好,保卫局也好边贸局也好,诸多的任务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弄来枪支弹药。白军方面的封锁,于军火来说不言而喻,严密防查,滴水不漏。这给潘普昭他们带来很大困难,有不少同志因此而牺牲性命。长官喜欢枪,给洪长官弄枪也就成了个最好借口。所以,潘普昭常常在洪天禹面前谈枪,有时带一本两本关于枪械的书来给一大一小两个学生讲枪。
崔工利也是从潘普昭的嘴里知道枪还有那么多的名堂。比如花机枪,潘普昭说那是莫辛纳甘;比如撸子,在他口里说是勃朗宁。还有什么曼利夏,卡尔卡诺,毛瑟什么的。其实不就是汉阳造老套筒?潘普昭说那可不是。他跟洪天禹崔工利说枪,说得头头是道。他说,知道不?什么汉阳造三八式,元年式、四年式、辽十三式、巩造98式和中正式,都是仿照外国的枪械制造的。什么苏俄的莫辛纳甘,奥匈的曼利夏,意大利卡尔卡诺什么什么的,照了人家的样子做的。还有我们说的枪牌撸子马牌撸子花口撸子其实说都是勃朗宁嘛,只是枪的型号有别……
说得洪天禹眼前天花乱坠,说得崔工利心里山摇地动。
洪天禹说:“你别尽是洋名儿一串一串,你就说枪吧。”
崔工利说:“是呀是呀,说枪……”
潘普昭就说枪,他见多识广,也博览群书,关于枪,他能说出很多洪天禹和崔工利没听说过的名堂。
洪天禹心花怒放,“你给我搞几支来看看。”
潘普昭于是就去了香港。
枪械一般是从香港进货,虽都是黑市买卖,但那地方各种新式武器都能找到,且还便宜。潘普昭珍惜这种机会,洪天禹要找某种枪,设在香港的苏区边贸局的同志迅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要尽快找到这批货,重要的是要找到红军所需的零配件。红军在苏区有兵工厂,但因条件所限,只能修理一般的枪械。对于一些关键零部件,还得想办法从别处弄,尤其是一些洋家伙,那更是物以稀为贵。潘普昭当然珍惜这种机会,以洪天禹的身份弄些紧俏的枪和重要零部件。
每回潘普昭取货回来,洪天禹总要在师部摆一桌酒席,把手下那几个重要军官请了一起喝酒。先是夸枪,说:“好枪好枪!”
潘普昭说:“洪长官,这是最新一款自来得了,当然好!”
洪天禹接了夸他的曾经的副官,“潘副官手眼通天,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哟。”
潘普昭笑,大家都笑。
洪天禹说:“别笑别笑!我还是要数落你潘副官的……”
潘普昭收起笑,大家都收起了笑,盯盯地看着洪天禹。
“你名堂多嘛……”
“我玩什么名堂了?长官,我怎么敢跟你玩名堂?!”
“你看你……叫盒子炮也行叫驳壳枪也行大不了你叫匣子枪叫二十响呀,你叫什么自来得?”
“噢噢,香港那边这么叫来着……叫盒子炮叫盒子炮……叫什么它都是条好枪。”
洪天禹说:“大家喝大家喝,我忙点事去了。”他把崔工利扯了起来。大家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一提好枪,洪天禹坐不住了,他要试枪。
他们去了靶场。
洪天禹在镇子后面的山里找了个地,叫手下平整了,做了靶场。平常供士兵练习用,但一有新枪到手,洪天禹就扯了崔工利去那地方。他要试枪。崔工利往那把匣子压子弹,压了很多颗,朝长官喊:“还要不?还要不?”洪天禹说:“压满压满!”崔工利就一直压满,是整整二十粒子弹。他压得指头生痛,放嘴里吸吮了。
那边。洪天禹已经打了一匣子子弹,枪口冒了青烟,他往枪口吹着气。崔工利听得枪声停歇,拔脚往那边跑,回来时扛了那只靶。数了那上面的枪眼。“二十枪,枪枪都在八环内。”洪天禹不吭声,也往匣子里压子弹,压好,把枪丢给崔工利。
那时候,崔工利就不是书童了,他绷了脸,模仿了洪天禹的样子。他想,好汉都应该是那么种样子。脸上得有威严。他不知道那东西叫杀气,在洪天禹,刀枪在手,那杀气就腾现脸上,人说杀气腾腾。洪天禹据说天生就这样,所以他能在众好汉里出人头地做了头目,现在又做了长官。他想,崔工利人小小,就当儿子待,老子英雄儿好汉。我带个传人。
所以,洪天禹有意无意都跟崔工利讲杀人的事。他说:“大刀杀人最痛快,斩人者痛快,受死者也痛快。”
“怎么就痛快了?”
“一刀劈去切萝卜样,血飙出几丈远,人还笑笑的,魂飞魄散……矛就不一样了,矛和子弹戳一洞洞,戳到地方那痛快,一口凉气进去,一股热血出来人就没了。戳不到地方那就生不如死受尽苦痛。”
崔工利起初听到背脊处还透了凉气,手心汗津津的。听多了,觉得那些生生死死的事就跟儿戏一样,他信洪天禹那句话,生当做豪杰,死亦为鬼雄。死不算个什么,但要死得轰轰烈烈,不枉人在世一场。
人死灯灭,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洪天禹真就改变了崔工利,人虽小小,读书是正事,却还被洪天禹扯上“武”,他陪长官读书,也陪长官习武。每到洪天禹在靶场要试枪练枪,崔工利就忙上忙下。
有一回洪天禹跟他的书童说,“你就不想玩玩枪。”
崔工利说,“我帮你擦枪就把枪当玩耍东西了哩。”
洪天禹说,“是说叫你试下打枪。”
崔工利第一次用枪就是拿的盒子炮。他想单手举,那枪有些沉。
洪天禹说,“你两只手握呀!”
崔工利就两只手握紧。
“你瞄准靶心……”
崔工利睁大眼看着那边的靶,看成了一片糊影,他努力地扣着扳机,枪响前竟然紧闭了双眼,然后,他扣动了扳机。他没想到枪声那么响,他更没想到那枪竟然有那么大的后坐力,尽管他两只手握了,还是没抓住。那支盒子枪从他手里飞了出去,重重地掉在崔工利身后的石头上,在那砸出个小坑。
他以为长官要骂他,没有,长官捂了肚子蹲在那笑得天翻地覆昏天黑地。他觉得长官的笑像一只无形的巴掌,狠抽着他的脸,抽了一下又抽一下。他看见长官洪天禹站了起来,拈起地上那把匣子,在衣襟上揩了揩,又对了枪口吹几口气,说:“这枪给你了!”
“给我!”
“嗯,给你!”
崔工利带了哭腔,“又没摔坏,那么摔下就能摔坏?”
“是没摔坏,摔坏了给你?”
崔工利小心地接过那只匣子,他说,“谢过长官了。”
洪天禹丢下一句话,“有一天,我要看见你那个坑是个洞洞出现在靶心上。”
那以后,崔工利一天除了日常的事务外,基本就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练枪。读书,读得进读不进是另一回事,但却有模有样地在读了。其实崔工利读书天资很好,潘普昭教什么几乎都进了耳里,从耳里走到了心里,就烙在心上的那块大石头上了。但每每崔工利在读书什么的都得心应手,洪天禹脸色就不好看。惭惭,崔工利明白其原因,明白原因后,在读书上就再不那么上劲了,看书里把那些字当成蝇虫,任了在眼前飞。洪天禹毕竟爱面子,一个娃儿,读书都比你强,你个长官在人前没脸子啦。
崔工利学枪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尽心尽力。练枪他拜了两个老师,一是洪天禹,长官枪法了得;二是潘普昭。潘普昭也有一手好枪法,起先大家都不知道。有一天洪天禹扯着潘普昭进山打猎。闲着没事时洪天禹会起打猎的兴致,所以隔三差五洪天禹就要带了几个进山一趟。这一带的山里有野猪麂子豪猪豺狗……。那是冬天,下雪后的第三天雪要融不融时候,洪天禹说,我们打猎去弄点好吃的去!
赣南就是冬天也难得下雪,下了雪也就三两天就融了。雪困了山里的兽,饿了几天,融雪时候就出来觅食。这时候是最好的打猎时机。
客家人猎兽的办法很多,多是安置机关,做各种的套套那些野物。他们管走兽飞禽都叫野物。用铁做铁夹,用木头和竹子做出许多的机关,总能套住野物。
但最难的却是做踩弹,其实就是制了硝掺了碎瓷片用浸了香猪油的布扎成一种炸弹。这种特制的炸弹对于饥饿的野物来说很见效。炸弹也就鸡蛋大小,但制作很讲究,先是选了上好的木炭,磨成粉末。赣南农户大多住土砖屋,放置尿桶的角落往往会长一层白毛,隔些日子就会成粉,掉下一层层来的浮土。有人就看上这些末末了,小心地扫了,在自家屋檐下搭个土灶,土灶上支一口大锅。灶台边几口大缸,上边架着筛子,硝水就从那些土里滤到缸里了。然后,生火熬硝。有了硝,就有了点眉目,所谓“一硝二黄三木炭”,黄就是硫磺。这三样东西掺和一起再加以碎瓷片,然后就是包扎的功夫了。一般人不敢做那事,这踩弹包扎太有讲究。不能包太紧,太紧了会在扎制时就爆炸。也不能包太松,太松了那野物咬嚼了不会爆炸一切都是空的。不紧也不松恰到好处。然后包裹了猪下水,有野物叼咬了,以为是块美食,咀嚼间那瓷片摩擦了起了火星那东西就炸了。
洪天禹喜欢用枪。
五
师部有很多报纸,有从南京来的也有广东上海和省城南昌来的,甚至有从香港来的。五花八门。有军方派定的,也有洪长官指定要订的。反正洪长官的师部不缺报纸和书,这两样,让洪天禹的师部与别处格外不一样。
每隔几天,就有人从船上捎来大堆的报纸。那个邮差不是由驿站送信送邮件,是由船捎了来。船也并不必停靠码头。报纸里包上一块卵石,一扎扎地往岩上抛。那哨卡的沿岸,都七零八落的遗有“报纸”。
那一天只要不下雨,崔工利总会出现在那条岸堤上。他捡报纸,这是他分内的事。
他把那些报捡了,就会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把报纸一张张铺平,把皱巴巴的地方弄平整。那弄出一大叠的报纸被风吹得欢欢地跳。他会抓一张报在手,拣几块卵石把那叠报纸四角压了,然后,悠然自得地坐在那棵香樟树下看报纸。他并不急了回镇上。
我为什么要急了回呢?他想。
这里很好,非常好。我多呆会儿。他想。
那地方离哨所不远,他摆了姿势给那些士兵看。他当然是故意那么,他觉得自己很吸引人,他觉得那么弄一下脸上光亮亮的神采奕奕。
有时候,真会有三两个哨兵会走过来跟他说话。他们都认得这个小兵,不要说做师长的“书童”早就在师里成了名人,就是作为崔工胜的弟弟,这些士兵对崔工利也格外熟悉。他们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
他们很爱跟他开玩笑,有人说,“看喽看喽,船上那漂亮妹子在睃你哩……”
崔工利不往河里看,他心无旁骛读报纸。
他们说:“今天船山墟集哩,一会跟我们去那地方?”
崔工利说:“我不去!”
他们会掏出烟秆,在那抽烟,也摆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说起船山的新鲜事,他们也故意那么说,让那些话语钻进那个少年的耳朵。他们说那些铺子,铺子里琳琅满目的货;他们说起那些作坊,说那些手艺人了得;他们说那些窑子,说得若隐若现欲说还休;他们说听戏,说那些角儿那些唱词还有那种气氛……
崔工利终于抬起头了,他听到他们说戏。他在老家里就爱听戏看戏,那大小的戏班子走村串镇,崔工利从无遗漏,不管风呀雨呀霜呀雪的,他会缠了他哥带他去看戏。其实也不是缠。崔工胜也是个戏迷。他也那么痴戏,逢戏必看。但他不喜欢他弟看戏时嚷嚷,所以,常常抛了那条尾巴。他弟精了,他弟总能制服崔工胜的摆脱。对戏的爱好是自幼开始的。他记得娘在世时爱抱了他去看戏,他们那地方唱的是豫剧,崔工利在娘怀里时看不懂剧情也听不懂唱词,但那曲调却种子样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有很长一段日子就是睡梦里他也听到那些曲调流星雨一样在他脑子里蹿飞。
崔工利坐在那,翘了个二郎腿,把报纸翻得哗啦哗啦地响。他故意那么。士兵跟他说话,他爱理不理那么。他看报纸。嘴里呢喃了,时不时跳出个“啊”“呀”什么的,眉动眼眨。
士兵大多不识字,那叠报纸对他们来说都是废纸,和脚边的落叶差不多。
士兵看崔工利惊惊诧诧那么,心上难免起了好奇。
问,“报上说什么呢?”
他说:“要交火了!还有……还有……”
“噢!?”
“你看你们噢?!这有什么好噢的?”
有人甚至唉了一声。
“你看你叹气?!叹个什么鬼气嘛……”
还是一声长长叹息。
崔工利得意了,他说:“想知道吗?”
士兵说:“当然当然!……你个工利短命的哟,你跟你大哥们卖关子呀!”
他们那么说,心里却觉得自己很那个,这个娃,一起入的队伍,才多长时间呀,崔工利竟然跟家里财主少爷样能识文断字了。他们这时候不能跟崔工利较劲。一较劲他蹿起就一走了之,身都不回。那他们就不知道报上那些事情了,他们每回都让崔工利读报,报上有世界各地的消息,什么新闻都有。他们很爱听,他们听出了瘾。所以,一有机会就来缠了崔工利。
他们显得很那个。说:“工利工利,你读来听听?”
有人就掏出一块两块点心或者糖果给他,说:“报上说个什么呢?”
“还有什么?”
“蒋委员长到南昌了。”崔工利说。
“到南昌到南昌呀……蒋委员长是什么人,皇上呀,皇上来来去去都坐飞机,他到哪不是一句话的事?”有人说。
“报上说蒋委员长到南昌不是说开火的事,是成立了个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要搞个运动……”
“那不打仗了?要搞新生活了?”有人问。
崔工利白了那人一眼,“要么你来读?”
那人不吭声了,脸上挤一丝笑又挤一丝笑,他不敢再多嘴,没人敢再多嘴,他们担心崔工利卷了报纸拍拍屁股走人,已经发生过好几次那种情形,一句话对不上崔工利脾气,他就发飙走人。当然,他哥崔工胜在他不敢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哥崔工胜在他从不读报,早早地卷了报纸找个借口回师部了。
“蒋委员来南昌建行营,不打仗建行营做什么?”
没人回答,周边很安静。崔工利抬头看大家一眼,没人说话他又觉得很那个了,他拿眼睛横人家。“没听到我说什么吗?”他说。
有人点了头,轻轻的那么。
“哑了呀哑了呀?!”他朝那些男人大声大气说。
“蒋委员来南昌建行营,不打仗建行营做什么?……我读这段你们没听到?……”
“听到了……那是那是……不打仗建行营做什么?”有人小声附和。
崔工利翻着报纸,他抖动了一个那张报,报纸发出“哗啦”的响声,显然,报上有什么吸引了他。
“日本人进军承德,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失守……”
“他娘的!”
崔工利说:“你骂我?!”
那人说:“你看你,怎么会骂你?我骂日本人。”
“狗日的日本人!”大家就都骂了起来。
后来,他们想起些什么,他们有些愤怒,有些沮丧,也有些莫名的忧伤。崔工利把报纸卷了起来,“洪长官等了我的报纸哩,我得走了。”
然后,他们又等了十天半月,虽然五天来一次报崔工利也到这取一次报,但不是每一次他都会读报。
今天不是一块两块点心糖果了,有人备了一大捧炒栗子,板栗很香。他闻到那股清香了,那人从提箩里拈出几颗,朝崔工利扔了过去。崔工利接了剥一颗放嘴里又剥一颗放嘴里,连嚼了三颗。但那个男人手不动了,崔工利心领神会,他得读报了,不读那板栗没他份了。
他咳了几下,算是清清嗓子,开始读报。
六
这一天,崔工利终于读出兴奋,整个早晨,他的脸眉开眼笑就像那轮秋日。
洪天禹去临川开会,崔工利没跟了去。他以为洪天禹当天能回,却沒有,凌晨时分,听得长官屋里有响动。心想,长官半夜归屋了?翻身起床,去洪长官屋边探动静。却是一只猫。赶了猫,关好门窗。却是再睡不着。
想到是取报纸的日子。我取报去。他想。
天未亮不亮时分,就飙起,往江边去。到江堤正好山窝里日头要拱出一线边缘。他站在雾岚里,看着那些小舟梭一样在江里顺流而下。一些是渔舟,在河流弯道处漂悠。河湾处有旋流,天长地久就旋出处深潭。深潭中藏有各种各样鱼,清晨,鱼也爱起早觅食。渔人清晨往潭里撒网,每有收获,鱼不在多,在于新鲜。总能卖出好价钱。
有一条扁舟却不载客不载货,是专门送报送信。自古有驿车驿马,但很少听见人说驿舟。枯水时节,入秋时分,雨水少了,大船走不了,但报纸和信依然要定时送,驿舟就应运而生。其实可以有驿车甚至驿马的。但似乎船山一带贡江两岸书信报纸一直是由商船运送,所以驿舟随流而走,轻便快捷。信是送往驿站,洪长官的报纸依然那么往岸堤甩拋。
洪长官不读报,但要的却是某种张扬,三五天来一次,起初士兵不大理解为什么要这么,邮差有义务直接把报送到镇上,但洪天禹说你丢岸堤上就是。洪天禹的理由很简单,邮差一周送一回,等读到报也没个意思了。
起初村人也不知道那些纸捆是什么,人说是报纸。有人就捡了一扎,那是个放牛的老倌。老倌觉得纸好,裁成巴掌大小小纸片。
人说,“薄老倌,你裁了做票子么,这票子能买栋楼的吧?”
姓薄的老倌说,“我卷烟哩,我也抽个纸烟哟。”
在乡人看来,抽纸烟是体面人上等人,是那些富人官家抽的,乡下人只有抽烟丝。有人就想也用纸卷一根两根的试试,其实并没有烟斗用起来方便,也有股纸味和油墨的杂味。但薄老倌一类人,要的是那架势作派。
崔工利取了报,天还早,士兵们在堤上操练,横成一排,先是喊了口令小跑,还有哨子声音,堤岸边林里的鸟已经适应了那些噪声,在枝叶间蹿跳鸣叫,相安无事。
但士兵听到了一串的笑声。
看去,是崔工利哩。
这么早崔工利竟然出现在堤岸那块石头上,手捧了报,笑出了哈哈哈的一串声音。士兵们的操练就进行不下去了,探头探脑地往那边睃望。执勤官就说:“看什么看的呀!”也往那边看,看见崔工利读报,就知道操练要黄弄不下去。说了声:“立正,稍息……解散!”
士兵围住了崔工利,他甚至没抬头看他们一眼,聚精会神的样样。
士兵嚷嚷了,“哎哎!工利哟……你看你来这么早,没备糖果糕点的嘛,这么早,集还没开张哟……”
崔工利抬起了头,“谁讨要糖果糕点了?!”
“没有没有!……根了你胡说哩!”
肖根了说:“是喔是喔!我胡说!……我是想知道报上有什么好消息嘛……你看你工利那么笑?”
“是有好消息……这里有好消息……我说我怎么鸡还没叫就醒了……”
“读来听听读来听听……”
崔工利清嗓子了,崔工利很响地读了,“二十三日,蒋委员上庐山了……”
“天气热,蒋委员长上庐山避暑。”
“何止避暑嘛……”
“那干什么?”
“部署呀……”
“你看你个娃……说话咬文嚼字的……”
崔工利咳了几下,又捧了报读着:“……蒋委员长携各军事将领云集庐山,商议围剿赣闽之境红军之策……”他抬起头,一脸的欢天喜地,他灿灿地那么笑。
肖根了说:“你看你笑?!”
“有仗打了呀,要交火了呀!”
“要交火你看你乐成这样?”有人愤愤地说。
崔工利看那些脸,那些脸阴沉了。他想,养兵千日呀,养你们干什么的?就是打仗上前线的嘛。但他没说,他觉得有些扫兴,站了起来拍着屁股。以往,士兵们会求他多呆一会,今天却没有。
他想,他们怕死哩,一说打仗就沉了脸。
他没再看那些士兵,他拍拍屁股走了。
崔工利给那些士兵读报,添油加醋,他似乎这方面很有才能,他把那些事渲染得神乎其神。他读了会抬起头看那些面孔一下,那些脸,齐齐地凑到他的跟前。听到精彩处,有人会情不自禁啧啧几声。也有不识趣的,忍不住问这问那。崔工利都不作答,问得多了,他会皱了眉头一脸的不耐烦神情说:“哎哎,你问个什么?有话等我念完了问不行?!”有时会说,“这也问这也问?你看你……”有时也会回答人家几句。说什么话,全看他心情。
但他有时也笑笑地回答每个大哥的话,拒绝人家的点心糖果。
那时候,士兵们就会知道崔工利一定会说那句话,“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戏呀,你们都答应多少回了。”
士兵们说:“好的,一定!”
崔工利说:“你们又答应了一回,一共三十二回了哈!”
最后带他上那地方的还是吕大每。不是那些大哥不带崔工利去船山,是他哥崔工胜不让他去。
七
对于崔工利来说,船山充满了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哥和那些队伍上兄弟口中的印象,何况他们跟他说时说得很含糊。在崔工利心目中,船山是若隐若现一个谜。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