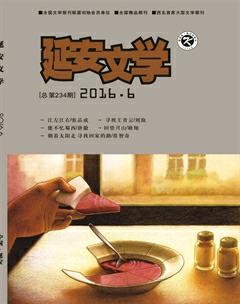我的第一次高考
张润生,陕西志丹人。延安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延河》《延安文学》等。
一
我们知青点来了三个上大学名额,可是谁也不上。
那是1976年9月的一个傍晚,我们知青吃过饭后,都坐在硷畔上的一摊麦秸上歇乏。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在院灯下撒着欢儿,突然向硷畔下狂吠,一看,是生产队长来了。队长一上来就喊:“学生娃娃们,好事来啦。”
我们立马把队长让坐在麦秸摊上,问他有啥好事?队长从上衣兜里掏出三张表格,向三个插了两年多队的知青抖了抖,说:“上大学。”
这个“好事”和我没戏,我才插队三个月,只有看人家上大学的份儿。
队长向那三个知青说:“来了三个名额,正好,插队两年以上够资格的就你们三个人,都有份。”他把一张表格递向其中一个知青,让他填表。可这个知青说他不上。他把表格又递向另外两个,那两个也是连连摆手。队长兴奋的脸一下子变得灰塌塌的。
那时上大学不考试,就是考也很简单。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说的是一所大学与文革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决裂的事。影片里,这所大学的招生考试,会写个“毛主席万岁”,招了;会写个“共产党万岁”,招了。不会写字不要紧,看手上的老茧,谁的老茧厚就招谁。实际情况虽不是这样,但也差不多。考试很简单,人人都能过。只要自己填表队里上报,几乎全招。
即便这样,队长又动员了一阵儿,还是没人填表。他叹了一口气走了,边走边说:“日怪,叫上大学还不去。都是叫烂怂‘社来社去闹的。”
社来社去中的“社”,指的是人民公社。社来社去意指从哪个公社来上的大学,上完后,还回到哪个公社去。说白了,就是上完大学还要回到农村,继续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当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除个别的,如当了我们队驻队干部的北京女知青秦佐,我们公社赵家湾生产队的北京知青王强,“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外,大都是为了镀金,等插够两年后,被社员推荐,跳出“农”门,或当工人,或当兵,或上大学。在这三条出路中,当工人最好。那个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各个大学、各个中小学,都进驻“工宣队”,大老粗管起了知识分子,工人的地位前所未有地高。再说当了工人马上就有工资,那时的工人牛得很。所以,知青们跳“农”门的上选是当工人,次之是当兵。至于上大学,由于是“社来社去”,所以大都不去。
谁知,这种潮流和理念,在1977年8月彻底翻转。
二
1977年8月,高考制度改革,9月开始实施,并于当年冬季就招收第一批学员。其中有条文:插队够不够两年都能考,成绩优先者录取。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就是这一条,改变了知青们的理想和信念。
北京女知青秦佐,是知青中的大人物。她留着短发头,常穿一身绿军装,一副“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派头。她已经在我们队插队六个年头了。秦佐刚来的时候,清瘦清瘦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社员们心疼地说:这个碎女子真可怜,快早早地推荐她当工人去。秦佐却豪迈地说她不走了,她是来农村扎根的,要用科学知识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秦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一有空就看书,边看边往本子上记,记下一沓子后,就给他们上一次夜课,讲得头头是道。社员们说,按她讲的去自留地里伺营菜水瓜果,长得还就是比原来强。他们还举了一个秦佐推广科学种田的例子说:有一年麦苗返青的时候,公社给队里拉来一拖拉机尿素,让社员们给麦子追肥。可社员们说尿素是化学品怕把麦子蚀死,不用。这时,秦佐就拿了一个脸盆,扛了半袋子尿素,上到对面山上的麦地里,用尿素洒了大大的“化肥好”三个字。半个月后,“化肥好”三个字上的麦子绿油油地窜得比别的麦子高出一截,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化肥好”三个绿色大字。这一下,社员们亲眼看到了化肥的好,都积极地使用起来。社员们说秦佐有好几次当工人的机会,她都不走。后来,公社看秦佐是个人物,就把她借调到公社,然后又返任到我们队当了驻队干部。驻队干部和队长平起平坐,这样,就更便于她搞科学种田了。他们说这一下秦佐“扎根农村,用科学知识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信心就更坚定了。他们说和秦佐一起来插队的五个北京知青,当工人的当工人,当兵的当兵,都走了,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就是这样一个要把“扎根农村,用科学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人物,高考制度一改革,就立马着手考大学了。
再说赵家湾的北京知青王强。王强是在1968年冬天一个雪花飘飘的下午,来他们生产队插队的。当时只有16岁,长得胖墩墩的,中等个,理一个小平头。他们说王强人小志气大,一直嚷嚷着要扎根农村干革命。王强不但苦水好,还有理发的手艺。一直坚持义务为社员们理发,一分钱都不收。社员们说王强插队两年后,来了一个招工名额,社员们一致推荐他去,可他把名额让给了别人。后来每次来招工、招兵还有上大学的名额,社员们推荐他,他都不去。他们说王强为了不让社员们再推荐他,居然在他们村找了一个对象,就是现在所说的女朋友。对象叫赵小珍,长得不咋的,可王强选中了她。当时一个陕北农村女子能攀上一个北京知青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赵小珍当然心花怒放,对王强很好。他们说有一年冬天,王强作为知青先进分子,去公社开表彰会,得了一张奖状和一双丝绒手套。奖状倒是常见的那种,可那双手套在当时可是高级货,贵得很,一般人根本买不起。公社为了叫得奖的人拿到喜欢的颜色,就叫他们到供销社里自己去挑。王强一开始也兴高采烈地挑着,挑着挑着,他就挪到一个摆着塑胶手套的货柜前端详起来,端详了一会儿,对售货员说不要那种手套了,拿上两双塑胶手套行吗?售货员满脸疑惑,他解释说这种手套隔水,给他的对象用,大冬天的洗涮不会把手冻坏。可见王强确实要在农村结婚扎根呀。可高考制度一改革,这个在农村找了拴马桩的知青青年,也着手考大学了。
知青中的大人物都这样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都一窝蜂地着手考大学。这下,一年前那三个拒绝上大学的知青傻眼了。据说那批被招的学员,不再“社去”,与以后招下的学员一样对待,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他们的肠子都悔青了,直骂自己是个笨怂不长前后眼。
于是,我们知青点的六个知青集体向队里请假,进城回家复习,准备考大学。假,是要请的,因为,如果考上,也要靠队里填写美言的政审表;如果考不上,还要靠他们推荐当工人或当兵呢,成败都不敢惹他们。我们都是在本市农村插队,我插队的生产队离城也就七八十里地,骑上自行车半天就可进城。
三
一进家门,我妈对着我就嚷嚷:“咋才回来?人家考大学都考成一窝蜂了。你们的同学张丽琴、薛生辉,反正你的好几个同学到咱们家寻了你几趟了,说是要和你商量怎个考大学呀。”
我赶紧出门去找张丽琴。张丽琴在我们班里学习成绩很好,和我一样也爱好文学,常来常往,所以我决定先去找她。
走在大街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高考气氛的浓烈,都在议论考大学的事情。张丽琴一见我就一脸笑,我却有了一种恐怕辜负她的不安,就说:“你学得比我好,我是搭你这个强伴来了。”
她说:“什么呀,我三顾茅庐都没有见到你,到底是谁搭谁呀?”
我说:“谁搭谁先不说吧,咱们先商量一下这高考怎弄呀。”
最后我俩定下:我们俩,再叫上以前学习靠谱的薛生辉、刘延才及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一个六人复习小组,以人多智慧多的方式共同复习考大学。第二天,我们的六人复习小组成员聚齐在我家,然后就商量怎样复习?想来想去还是找我们原来的老师!于是,我们估摸着下午放学了,就去找我们高中时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张老师和语文老师惠老师。
四
好家伙!放学了校园里还一片热闹。一打听,原来是学生走了,社会上的人来了。有工人,有农民,有我们这些插队知青,都是为考大学来找老师的,老师一下子从原来的臭老九被尊为文曲星。
我们走到张老师的办公室前,啊呀,里面被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排着一长串人在等候。我踮起脚尖向里面看,看呀看,也没看见张老师,只好也排在门外等候。在等待的时候,我听见人们用神秘和崇拜的口气议论说:张老师是个老牌大学生,数学可厉害呢。我感叹世事的无常,我们上高中那阵儿,张老师就是因为“老牌大学生”这块牌子,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教育出来的黑苗子,有企图在下一代身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倾向,屡受压制,被人下看。我们还曾经为他“抱打不平”过一次呢。
那是高二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教育局要把张老师调到农村去教学。张老师要被调走?我们的心里一阵空落,一下子想起他平时对我们的好来:他讲课水平高,平时对学生也嘘寒问暖。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要被发配到农村中学?凭啥?我们愤愤不平起来。于是我们十几个“激进”的学生,其中就有我们六人复习小组的成员,就直接冲进市委“请愿”。那时的市委门好进,畅通无阻。一个干部问明我们的来意后,就把我们领进一个会议室,接着他去给领导汇报。我们等了一会儿,管教育的市委副书记就来了。她让我们谈情况,我们先说了张老师的好,然后说了我们认为的不公,最后表达了不要把张老师调走的心愿。副书记听完后,一脸微笑着说情况知道了,市委会考虑解决的,然后让我们回去。不知是不是我们找市委起了作用,最终张老师没有被调走。后来张老师没有明说什么,但话言话语中流露出了对我们的感谢之意。
张老师现在地位高了,但我想,他会念在我们曾经为他“抱打不平”的份上,对我们另眼相看。
直到天黑,才轮到我们。果然,张老师一见我们,热情程度明显地比别人高。不用我们说,他就知道我们干啥来了。他立刻从书柜给我们一人拿出一份他自己刻印的复习题。那时候,这可是宝贝。一般人刻印不出来,买又没处买,奇缺得很。旁边的人羡慕得不行。张老师把复习题给我们后,说:“这里人多,没办法给你们细讲。晚上八点半,我在高二(3)班教室讲课,你们来听吧。”
晚上八点多,我们到了学校。每个教室都灯火通明,人头攒动。这种全民学习的阵势,震得我们一愣一愣的。高二(3)班的教室里人挤人,我们正瞅着看往哪里坐的时候,一个学生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过去,他指着四个空位说:“这是张老师叫留给你们的,快坐。”到底是张老师,就是不一样。于是我们六人就挤在四个空位上等着开讲。八点半,张老师进来了,他拿着厚厚的教案、三角板、圆规什么的,看来是经过精心准备的。那时的老师特别能奉献,精心准备教案,黑天半夜上课,都辛苦成那样了,也一分钱不收。张老师一开讲,我就懵了。讲的是三角函数的诱导公式。什么正弦函数,什么余弦函数,还有平方关系……不要说懂了,就连字母也认不全。我们上学那阵儿,就解个一元一次方程,再就是勾股定理。像这种带着一串字母,又小写又大写,还带着括号,有的头顶上竟然顶着一个尖儿的公式,从来没学过,一见就懵了。我瞄了一眼张丽琴,见她两眼茫然,一头雾水的样子,估计也懵了。一堂课云里雾里什么也没听懂。
数学没听懂,我们却天真地想,多听几回就好了,毕竟一年多没拿书本了。第二天,我们按计划拿上自己的习作去找语文老师惠老师讨教写作文的技巧。惠老师,我在上学那阵儿,就听人说他在报社当过记者,文章写得很好。果然,他的办公室门口排着长队,排队的人都拿着自己的习作,一边蹙眉咂嘴地议论着作文是如何如何地不好写,一边等待着向惠老师讨教秘笈。队列在向前慢慢蠕动,终于轮到我们了。惠老师见是我们,虽不像张老师那样两眼放光,但毕竟带过我们,也是热情有加,尤其是对我和张丽琴更是另眼相看。他叫我俩坐到跟前,说:“说你们的习作我就不看了,我知道你们的水平不错。你们现在主要是要创新,使文章有新意,让人一看觉得耳目一新就行了。”接着他给我俩说了一些现在已进入新时代,要树立创新理念什么的。他给我俩指点罢后,看了我们那另外四个人的习作,笼统地对他们进行了集体点评。
办公室里面挤满人,外面还排着长队,人人都焦急等待的情况下,惠老师能对我俩“一对二”地指点那么长时间,可以说给了我俩很高的待遇,我俩不但信心大增,还有点沾沾自喜。
创新,怎么创?我绞尽脑汁地写出一篇自认为很创新的作文,里面有好几个我自认为是很创新的词,如“让我们的祖国光速前进”一句中的“光速”,别人都用“飞速”,我用“光速”,够创新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