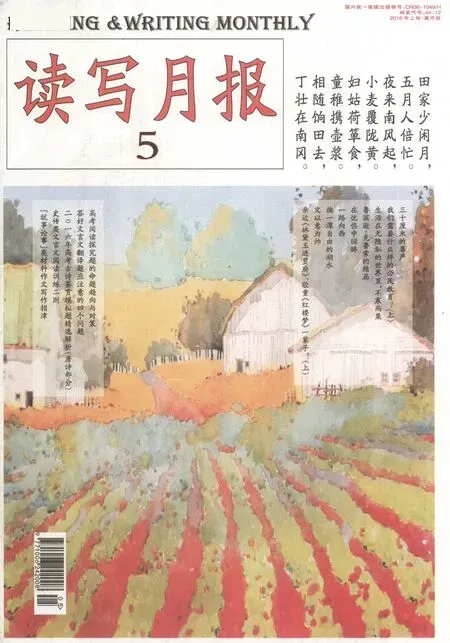亲近《林黛玉进贾府》,敬重《红楼梦》一辈子!(上)
●浙江省镇海中学 魏建宽
亲近《林黛玉进贾府》,敬重《红楼梦》一辈子!(上)
●浙江省镇海中学 魏建宽

一
《红楼梦》是高中课程标准规定的高中生必读的十部中外名著之一,高中教材只节选了《红楼梦》第三回的大部分,并将回目的标题改为“林黛玉进贾府”。
一篇 《林黛玉进贾府》,最多也就教学四课时吧,如何通过这四节课的欣赏,让学生亲近与敬重《红楼梦》一辈子呢?
我之所以将 《林黛玉进贾府》的教学期待定为让学生“敬重《红楼梦》一辈子”,而不是“爱读”一辈子,是因为我的教学定位必须清醒,必须面对现实。学生的年龄、阅历、文学理解力、文化积淀、审美鉴赏力及巨大的应试压力,都决定了仅通过一篇课文的教学就使每一个学生高中毕业之后“爱读《红楼梦》一辈子”并读懂《红楼梦》有点不切实际。
《林黛玉进贾府》授课完毕,我布置了一篇几百字的小随笔作业,题目为“听老魏讲 《林黛玉进贾府》之后”,学生金鸿飞这样写道:
诚然,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我原来最不喜欢的是《红楼梦》,用作家梁晓声先生的话来说,的确是“脂粉气太重”。不过,若真正“一本正经”地欣赏起来,也能对心灵产生触动。有言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红楼梦》也是这样,不同的人能读到不同的味道,能读出不同的林黛玉。老魏引导我们读《红楼梦》时,他提出的阅读高度是应该读到能与作品与作者的灵魂对话的层面。
张爱玲认为读《红楼梦》的最普及的方式是偏爱大观园的某一个少女,所以我阅读时试着偏爱林黛玉,这并不是因为课堂上仅接触了“林黛玉进贾府”这一片断,而是真切地被黛玉的人格魅力所打动。
一开始老魏在课堂上讲《林黛玉进贾府》时,讲到“复旦投毒案”中的林森浩,讲到临刑前的林森浩向自己的好友赠送《红楼梦》,并对朋友说《红楼梦》值得读一辈子,对此我是不相信的。直到看到老魏分发的资料中的林森浩的遗书图片,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对于一个将死的人,把一本书列在向朋友推荐的一生必读的四本书之中,可见《红楼梦》是怎样的一本能对一个人的一生起重要作用的书啊!
我也会记得老魏的那句话:《红楼梦》是本应该读一辈子的书。抛开课业压力,当我闲暇时,必愿抛开手机,捧上《红楼梦》,感悟人生。
感谢我的学生,他们让我很欣慰!他们认同了我的“文学作品阅读的四境界说”——文字、文学、文化、灵魂;他们认同了我推荐的张爱玲读《红楼梦》的方式;他们认同了我以“复旦投毒案”中的研究生林森浩后悔没读《红楼梦》为例而得出的推论——不朽的文学名著对一个人的灵魂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在应试压力巨大的当下,他们也愿尽量摆脱手机的消遣式浅阅读,“捧上《红楼梦》,感悟人生”!
二
怎样让学生对《红楼梦》与曹雪芹产生亲近感与敬重感呢?
我先以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的一幅与《红楼梦》“林黛玉进贾府”情节相关的彩绘国画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入手——
我向学生提问:熟读《红楼梦》第三回,说说戴敦邦先生的这幅画存在哪些问题?
经过讨论,我总结说这幅国画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1.林如海身为兰台寺大夫、钦点扬州巡盐御史,一位如此高级别的官员送女远行进京,后面竟只有几位仆从,而且是远远地立着,竟然如当今扬州平民百姓于码头送子女远行,这在一个“礼制社会”,让人不可想象。
2.小说原文明白写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遂同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对照原著,戴敦邦的画缺了什么?——只有一只船,且船太小,小如绍兴的乌篷船,且缺了一只船,还缺了荣国府来接林黛玉的人。有人可能会问,接林黛玉的“老妇人”先上船了,这就更说不通了。礼制社会中,荣府的来接黛玉的“三等仆人”,在林姑娘还没上船之前,他们这些仆人还竟敢先上船?
3.贾雨村虽是林府的家庭教师,由于“男女有别”,他必须“另有一只船”,由于他对林府的“依附”关系,他仍是“仆从”,林黛玉没上船,林如海没上轿回府,他怎能端坐船中不起立行礼?
由此可见,这幅画表明戴先生一是没有细读原著,忽略了原文情节中的细节,二是阅读《红楼梦》所必具的“文化”层面的学养还不够深厚!
对此,给《红楼梦》画了一辈子插图的戴先生早于1983年就撰文 《攀爬巅峰画〈红楼〉——为〈红楼梦人物百图〉作后记》一文,坦承自己文化层面的学养不足:
吾把《红楼梦》比做一座艺术上的珠穆朗玛峰,而自己只是个没有多少实力的爬山汉,也没有征服世界最高峰的雄心壮志,只想试试自己有多大能耐就爬多少高度。第一次 “攀爬”(英文版《红楼梦》插图创作)暴露了吾这个民间艺人的本事、教养的不足……这次又经前辈的鼓励和红学界同仁的怂恿,进行了第三次“攀爬”,画了绣像一百零八图红楼人物。在整整两年的绘制中,吾深感一个工匠式的艺人,要改变自己的匠俗,要高雅些,是何等不易……吾感到吾国所有的文学名著中,最难画的要数《红楼梦》!越是艺术性高和完美的作品,越难以再现和再创造。
学生读完戴敦邦的这段话,不由得以敬重的口吻感叹:仅从文化层面上说,读懂《红楼梦》,就是一辈子的事!
三
由戴敦邦对《红楼梦》的敬重与敬畏,我再顺势讲到《林黛玉进贾府》中的贾母见黛玉的细节,向学生提问:林黛玉“方欲拜见”外祖母,为什么就 “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为什么外祖母“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这个问题已不仅仅涉及到“文学”与“文化”层面,而且涉及到学生能否与作品及作者的“灵魂”相遇的问题!
从“文学”层面来读,只要理解这是一个细节描写,只要由“文字”中的“方欲”“一把”“搂”“心肝儿肉大叫”,读出林黛玉的聪慧敏感与贾母怜爱孤女的慈爱性格,就不俗了。不过,从“文化”与人物的“灵魂”层面阅读,就必须理解:在等级森严、封建礼教思想禁锢着每一个人的贾府,贾母为什么不让外孙女行完“拜礼”再将黛玉“搂入怀中”呢?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讨论之后,我让学生阅读了台湾作家、画家、美学家蒋勋先生的与此相关的文章片断——
黛玉第一次见到贾母,看到她头发都已经白了,这个时候贾母应该是接近六十岁的年龄。因为第一次见外祖母,要行跪拜大礼。这时贾母立刻把她抱在怀里,不让她跪,大叫心肝儿肉。“心肝儿肉”是老人家最喜欢叫孩子的语言。我们在这里看到贾母那种心痛的感觉。她此刻见到的不仅是黛玉,也是她的女儿贾敏。她在这里疼的、哭出来的其实是对女儿和外孙女很复杂的感情。作者在这个地方写得非常精简,但很动人,你几乎可以感觉到那个画面。贾母生了几个男孩,贾敏是独生女,是她最爱的女儿,可是早早就死掉了,临终都没有见到,她把对女儿的感情转移到外孙女的身上了。
再让学生阅读《清史稿》(卷九十一)中关于“宾礼”的文字——
卑幼见尊长礼,及门通名,俟外次,尊长召入见,升阶,北面再拜,尊长西面答揖。命坐,视尊长坐次侍坐。茶至,揖,语毕,禀辞,三揖。凡揖皆答,出不送。
由《清史稿》学生明白林黛玉见贾母,是 “卑幼见尊长”,入门之后必须“再拜”,“命坐”之后方能“视尊长坐次”再琢磨自己该坐哪个位置才能“侍坐”。而贾母见林黛玉,省去了繁复的礼节,“一把”就将黛玉 “搂入怀中”,蒋勋先生告知我们阅读这一“精简”的片断时,要读到其“动人”之处。“动人”之处在哪呢?这就是人情之美,人性之美——陷入礼教制度与人情、人性矛盾冲突中的贾母将人情置于礼法之上而流露出的可亲与可敬!
四
人们不禁要问:位于贾府这个封建礼法制度下等级森严的家族“金字塔尖”的人物贾母,本应成为谨遵礼法的榜样,为什么不压抑自己的情感呢?为什么反倒如此率情任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曹雪芹要这样写呢?
对此,我觉得众多的品红楼的读者中,鲁迅先生是在灵魂层面与曹雪芹距离最近的人,他写于《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为我们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参照——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我向学生介绍了自己读上一段文字的体会——
宝玉看到了他所爱的人——美丽如秦可卿,纯真如秦钟,卑微却善良决绝如金钏,美丽善良而相信真爱的尤二姐,身处下贱而又想孤傲地活出人格美的晴雯,一个个地消逝!
鲁迅从美或丑的毁灭中,去参悟人生的悲剧与喜剧背后的内核,这是生命哲学、人生哲学的第一要务——思考这个世界对于人来说,什么最重?什么最轻?人为什么活?怎样活?人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姿态?有的人为什么活不出自己的姿态?
让学生读完上述文字,我向学生发问:贾母难道不想活出自己的真实的符合人性的姿态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贾母见到因丧母而来投靠她的病弱孤苦的外孙女之后,再联想到她病亡的女儿贾敏,她身上的母性完全被激发出来了,她再也顾及不到那些礼法,在这一刻“礼教”的枷锁被她弃置一旁!面对死去的贾敏,面对眼前孤弱的外孙女,贾母面对的就是死神的能吞噬一切的巨大的黑色羽翼,在这一刻贾母知道有比礼法更 “重”的,那就是人应该还要有一颗柔软的心!
从文学的角度上看,这是人物形象折射出的丰富性的闪光;从文化层面上看,这是礼法向人情、人性之美的撤退;从灵魂层面上看,这是曹雪芹为我们画出了一个问号——面对尘俗世界层面的禁锢,你会活出一个怎样的精神姿态的你?
五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继续向学生发问:“为什么 《林黛玉进贾府》中,对王熙凤与贾宝玉的服饰描写那样地泼墨如水,而‘众人’‘王熙凤’‘贾宝玉’看林黛玉的描写中,却只字不见林黛玉的服饰?”
讨论之后,我展示了张爱玲的论述——
通部书不提黛玉衣饰,只有那次赏雪,为了衬托邢岫烟的寒酸,逐个交代每人的外衣。黛玉披着大红羽绉面、白狐里子的鹤氅,束着腰带,穿靴。鹤氅想必有披肩式袖子,如鹤之掩翅,否则斗篷无法系腰带。氅衣、腰带、靴子,都是古装也有的——就连在现代也很普遍。
唯一的另一次,第八回黛玉到薛姨妈家,“宝玉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便问:‘下雪了么? ’”也是下雪,也是一色大红的外衣,没有镶滚,没有时间性,该不是偶然的。“世外仙姝寂寞林”应当有一种飘渺的感觉,不一定属于什么时代。
宝钗虽高雅,在这些人里数她受礼教的熏陶最深,世故也深,所以比较是他们那时代的人。
学生读后,首先是感到惊讶,张爱玲因不认同一般读者只会浮躁地 “站着读”《红楼梦》,竟然“坐着读”《红楼梦》读至如此沉醉的境界,读到了“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的地步。
学生读后,还发现张爱玲读《红楼梦》真是读到了与作者以及与作品灵魂相通的境界,因为张爱玲读到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超越时代、超越 “受礼教的熏陶最深,世故也深”的薛宝钗所不可企及的精神层面的价值——“世外仙姝”的审美价值!
对于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美学家、哲学家刘再复先生阐述得最为透彻——
林黛玉她是一个只能在天际星际山际水际中生活而不宜于在人际中生活的生命,从根本上不适合于生活在人间。她到世间,是为情(还泪)而来,为情而生,为情而抽丝(诗),为情而投入全部身心,唯有她,才是真正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孤独者。
类似的对林黛玉的评价,也出现于王昆仑先生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黛玉之死》中——
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完全是背驰的。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
王昆仑先生注意到 “诗意”的、渴望有着精神与灵魂层面的充盈生活的林黛玉与世俗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又何尝不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时代的人之间所存在的?只要你渴望拥有 “诗意”层面的生活,就必然会与身边凡俗的现实世界产生冲突。
大学毕业后的学生融入社会,难道不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吗——除了努力挣得“面包”之外,还需不需要拥有如林黛玉那样的 “灵魂生活”?而恰恰在面对这个选择上,《红楼梦》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个参照,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红楼梦》是值得陪伴我们一生的书。
曾任“中国《红楼梦》研究协会”会长的冯其庸先生,也谈到林黛玉作为大观园中的“诗魂”的意义及价值,并揭示了生活中“在作诗”的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对于我们选择做一个怎样精神层面的人的意义及价值,冯先生的观点可与张爱玲、刘再复、王昆仑先生的观点互为映衬——
从诗的人物个性化来说,“诗魂”不正好是诗才横溢的林黛玉个性的呈现吗!再者,在《红楼梦》第五回《金陵十二钗》正册里关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诗是:“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曹雪芹特意将谢道韫敏捷的诗才比黛玉,这说明他是用诗人的品格来塑造黛玉的,所以,这个“诗魂”,当然非黛玉莫属。
曹雪芹笔下最最动人、最最哀感顽艳、最最万劫不磨的,自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及其毁灭。这一对爱情典型的深刻的描写,包含着曹雪芹种种的社会理想,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的理想,对爱情和青春的理想,对人的自我造就、自我完善的理想,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理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