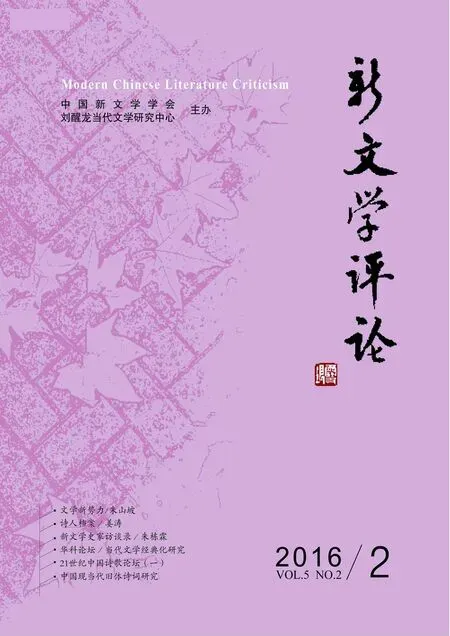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草根性”与文学写作的本源
———也谈新世纪的新诗
◆ 荣光启
“草根性”与文学写作的本源
———也谈新世纪的新诗
◆ 荣光启
一、当代诗的“自赎”
2015年诗歌界目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余秀华的走红。像另一个湖北人一样,走红之际,他们的名字,即使在出租车上,也被师傅聊到。当年的易中天老师,多少出租车司机接受了他关于“三国”的品位;而今天的余秀华,则向世人出示了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面貌。出身于武汉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其对历史与经典的品位,在另一些教授看来,有浅薄之嫌;而余秀华这位出身低微、身体残疾的农村妇女,其诗作在许多大学教授读来,却是刻骨铭心的感动。被《诗刊》推出、被微信推广的余秀华的诗作,我最早读到,是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张箭飞教授的微信朋友圈里,她自己也极为推崇。我心里的震撼是与后来读到的美国教授沈睿女士的感受一样的,虽然我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权主义倾向。
据沈睿自述,2015年1月12日,她在微信上看到一个朋友转的《诗刊》推荐的一个诗人的作品,题目是《摇摇晃晃的人间——一位脑瘫患者的诗》,极为震撼,这位言语向来锐利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毫不吝啬地写道:“这么清纯胆怯美丽的爱情诗!我被震动了。我接着往下读,一共十首诗,我看了第一遍,第一个感觉就是天才——一位横空出世的诗人在我们的面前,她写得真的好。我又再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了,我在床上坐直了,立刻在微信上转这位女诗人,并写: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她的诗,体验语言的力量与感情的深度。对她实在好奇,在网上查她,我查到了她的博客,博客里全是诗歌,我开始读,一发不可收拾,好像走进了斑斓的秋天的树林,每一片叶子都是好诗,都凝聚着生活的分量,转化成灿烂的语言,让你目眩,让你激动得心疼,心如刀绞,让你感到心在流血——被诗歌的刺刀一刀刀见红。我一篇一篇地读下去,我再也无法睡觉。本来就是常常失眠的年龄,我被余秀华的诗歌——她的永恒的主题:爱情、亲情、生活的困难与感悟,生活的瞬间的意义等等感动,震动,读得直到累了,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她的新闻。……这样强烈美丽到达极限的爱情诗,情爱诗,从女性的角度写的,还没有谁写出来过。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丽·迪肯森,出奇的想象,语言的打击力量,与中国大部分女诗人相比,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而不是写出来的充满装饰的盛宴或家宴,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你目瞪口呆,感情的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①
2015年5月22日,在湖北省作协召开的“余秀华诗歌研讨会”上,诗人张执浩的发言耐人寻味,他说:这两年来,我一直愿意为余秀华“站台”,作陪衬,除了认可余秀华的诗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余秀华的诗歌为广大读者关注,“这是多年来中国诗坛为人所关注、但却是第一次以正面形象为人所关注的一个事件……”这几年来,当代中国诗坛出了许多事件,比如“梨花体”、“羊羔体”、“鲁奖”、“啸天体”,以及最近的“乌青体”……但是,历次事件,几乎都是负面的,一次次让人远离诗歌、鄙视文学。甚至有人说,新诗写作,只要会回车键就够了②。而余秀华,这一次在当代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新诗形象:原来,新诗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面目!《诗刊》编辑刘年如是写道:
几千年来,诗歌在中国,有类似于宗教的教化作用。
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也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可是,进入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个民族开始疏远诗歌。这当然与我们以经济建议为核心,唯物、唯钱、唯快、唯新的时代潮流有关。诗人本身,也难辞其咎。海子的自杀,顾成的杀人,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诗歌行为层出不穷,让诗人成了阴暗变态的代名词,更加上诗歌的晦涩难懂,变成了让人难以接近甚至反感的文体。何况还有下半身,梨花体,乌青体,一次又一次对诗歌的戏谑和嘲弄。以至于诗人一再地边缘化,以至于,在人们的聊天中,有人敢承认自己赌博自慰甚至嫖娼,但不敢承认自己写诗的地步了。
经济发展了,物质满足了,人们发现,幸福还没有到来。人们在反思中发现,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不是粮食、石油、住房和钱,而是缺乏真诚的诗意。于是,在这个曾经以诗立国的国度里,人们开始往回找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能力。所以,余秀华走红,有其偶然,也有其必然。是汉语成熟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新诗自发地回归传统、回归现实、回归大众后,必然的结果,是诗歌本身的走红。我觉得作为诗人和诗歌从业者,都应该感谢她,她让诗歌以一种比较有尊严的方式,重回到国人的生活中。她的诗歌读者,应该感谢她。
甚至,这片土地,也应该感谢她。
这话极像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的当代版:“……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分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④千年后,照耀张若虚的月亮,照到的是一个叫余秀华的中年农村妇女抽搐的左手。那落在余秀华手上的月光,是张若虚的月光,也是当代汉语诗坛所稀缺的一种诗意的光芒。2015年第2期《长江文艺》,诗人张执浩在他主持的“诗空间”栏目,推荐了余秀华的组诗《在横店》,张执浩的推荐语说:“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行走了几十年,当她找到诗歌这支铁拐时,才终于真正站立了起来。我关注她的作品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从自发地书写和表达,到逐渐自觉地对命运的理解和宽宥,当她迈过这条沟坎之时,她的作品便呈现出了一种惊人的爆发力。”余秀华诗歌的发表与获得广泛认同,不是她个人的事,而是当代汉语诗坛的事。如果以前面那些使人远离新诗的一系列事件为背景的话,也许我们也可以说,余秀华和她的诗,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次“自赎”。
二、“草根性”: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在诗人、《诗刊》副主编李少君看来,余秀华的崛起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脉络——“草根性”的发展必然。诗歌的“草根性”是什么呢?——“……2003年,我当时做《天涯》杂志的主编,当时和一帮诗人,就是杭州的潘维他们搞了一部车,我们就开着车从杭州到苏州,一路上随便转一转,就不断地碰到一些诗人,有的诗人甚至在村里面的,有的诗人可能就是一个县城里面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什么的,当时很奇怪的就是这些人我完全没听说过,见面就送上诗稿,那个时候诗稿都是打印的。我看到这些诗吓我一跳,我说这个诗写得蛮好的。最后见到了杨键、江非,他们当时已有一定诗名,生活很清贫,但诗歌别开生面。杨键当时是一个下岗工人。江非当时的身份就是一个农民,是农村户口,在务农。我们以前认为诗歌、诗人都是高高在上,像早期的诗人北岛、芒克这样的;但突然发现这样一批诗人,写得这么好,身份却不符合我们对诗人的想象。当时我就感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到常熟后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当时就比较冲动,想到一个词,就叫‘草根性’。江浙这一代当时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乡镇企业认同草根,我就用‘草根性’命名这样一种诗歌,从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带着本土的、地方性的经验,而且很有个人的那种特性的诗歌。以前的诗歌传统是从上而下的,诗人要启蒙大众,朦胧诗实际上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你看一批高干子弟,比较早地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现在过程反过来了,是自下而上的。”⑤
在另一个地方,李少君谈到了与“草根性”诗歌写作的一个对立面——“深入地区分一下观念性诗歌与草根性诗歌的不同是非常重要且必需的。我常常说其实区分‘草根性’极为容易,‘草根性’是指一种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写作。 比如同是‘口语诗人’,韩东几乎没有‘草根性’,只是擅长制造观念。于坚的‘草根性’却很明显, 且非常深厚, 无论是其早期的 《尚义街六号》、《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还是晚期的《零档案》、《事件系列》等诗歌。来自个人经验与生命深处的激情,云南特有的地域背景以及诗人自然的生存环境以及对唐诗等传统之根的继承,汇成汹涌的源泉横贯其中,打动一切有血有肉之人。于坚常年的历练已经逐渐‘诗成肉身’。而韩东的诗,完全不能达到如此境地,不过一些小技巧、小诡计,所以即使在民间内部,与沈浩波相比,韩东也被称为‘伪民间’。但恰如一位诗人所说:‘你们以为一点小诡计就真的能蒙骗世人吗?’当然,韩东本身是学哲学出身,擅长学习西方观念,只不过阴差阳错误入了诗坛。当然,观念性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占主流位置,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可能是所谓追赶意识导致的。这是所有后发国家的通病,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 而观念、思潮是最容易学的,但要学到根本的东西还需要漫长的岁月和足够的时间。当然, 虽然这样,但也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西方发展积累了几百年的现代诗歌的技巧、理念演习了一遍,为逐渐涌现的可能的新的转型做了某些准备。”⑥
观念性的诗歌往往来自一个时代有责任的文学家追赶世界文学潮流的努力,这种写作的理论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文本在即时的诗歌审美形态上,往往滞后或者不忍卒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观念”有时能够刺激新的诗歌美学的发生,从长远的角度,未必不能带来诗歌审美形态的革命。
不过,我觉得,“草根性”诗歌观念的意义道出了文学的一个本质:文学写作的变化往往并不依赖于一个时代那些有责任的文学家以及他们的努力,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文学写作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是文学写作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才能,是一个有语言表达能力的人的基本需要,人若自觉地以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觉、经验和想象,这就可能形成文学。文学真正的生命力在这里,这是文学不会灭亡的基础,这个生命力是不管文学史的喧嚣和观念革命的复杂与宏伟的。如果文学是草木的话,使之旺盛使之生生不息的那根与本——正是个体的人以文艺的方式言说自我的冲动、渴望,与语言、形式上的有意识的寻求。
李少君说的那种“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是“草根性”的基础,这是文学写作发生的前提。而“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则构成了“草根性”诗歌写作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必要元素,它们决定着这种个人写作能否为更多人接受。举例来说,余秀华的写作,在个人的表达诉求之外,或者之内,是她的乡村经验、忧伤的个人气质以及她在知识方面的“传统”之影响(比如你在她诗歌里能读到海子和雷平阳的风格)。经验上的疼痛感,忧伤、抒情、以自然意象为主的语言风格等等因素,构成了整体的余秀华诗歌,在读者接受中,由于人们共享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和文化模式,这种诗歌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三、作为文学写作本源之一的“草根性”
在余秀华给人签名的那个时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她的第一本诗集的名字是“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艰难的签名——“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的平衡,并用最大力气让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⑦,在另一个场合,我见她用右手压着左手,用左手写下了“某某某雅正——余秀华”,这一行歪歪扭扭的文字,所付出的努力,估计是我潇洒的签名的一百倍。这才是真正的余秀华,一个在人间活得非常艰难的人,她幼时的疾病使得她走路摇摇晃晃,她说话吐字不清,声音摇摇晃晃,她的手不停抖动,写字摇摇晃晃,她在自己的人生中感到生存的艰难和命运的可怖、在内心对生命和生活长期提心吊胆……“摇摇晃晃”的形体、声音,“摇摇晃晃”的生存隐忧,这才是她真实的人生。有人问余秀华,在你看来,诗歌是怎样一种东西?她说,写诗是掏心掏肺、把灵魂掏出来的过程……余秀华说话吃力,这个“掏……”,是一个艰难发出的声音,它突然使你感觉,“掏心掏肺”这个词,也许只有从她口里说出来才有点像真的。
《圣经·新约》记载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关乎人对上帝的态度。“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12:41—44)有钱人拿出一堆钱,奉献于圣殿,觉得自己很对得起上帝了,同时觉得自己多么虔诚;而一个穷寡妇,也许只是投了两个硬币,但耶稣说,她“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里谁是最虔诚的,一目了然。大多数人对于文学,只是爱好者,业余的怡情养性,如果有名声,当然好,没有,也不强求,这种态度是对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而有些人,文学——这种用语言文字来感觉自我、想象世界和陈述经验的精神活动,却是他的全部,是他生命的中心,就像法国批评家莫里斯·布朗肖在谈论卡夫卡的时候说:
卡夫卡不顾一切地想成为作家。每当他认为他的愿望受到阻拦时,他都会深陷绝望当中。当他被派去负责他父亲的工厂,他觉得他在两个星期里将无法写作的时候,他恨不得了结自己的性命。他《日记》里最长的一段写了他每天如何挣扎,如何不得不上班做事、不得不应付别人以及不得不对付自己,以便能够在他的《日记》里写几个字。这种着狂状态虽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知道,这并非不寻常之事。就卡夫卡的情况而言,倘若我们看到他如何选择在文学中实现他的精神和宗教命运,那么这种着狂状态似乎就更加自然了。由于他把他整个的存在都放在了他的艺术上,当这一活动不得不让位于另一种活动时,他看到他整个的艺术面临危险:因此,他停止了实际意义上的生活。
…………
“用血写作,”查拉斯图拉说,“你会知道血就是心智。”⑧
在莫里斯·布朗肖看来,卡夫卡是那种“用血写作”的作家,这里的血,更是象征的意义上的。在西方语境中,血即意味着生命⑨。这里是说卡夫卡是那种以整个生命在写作的人,除此之外,他没有做任何事。文学是他的宗教与救赎。李少君提到的杨健、江非、雷平阳等诗人,还有这里的余秀华,曾经恐怕都是将诗歌视为救赎的一种言说自我的行为,写诗不为什么,只是为了言说自我的感觉、经验和想象,在一个文学的世界里自我得到慰藉,当然,如果有他人也为这些文字感动,那便更好。
“草根”一词,直译自英文的grass roots,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把grass-roots单列为一个词条,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在文学的领域,“草根”的活力其根源在于文学的本质: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其手段是以感觉化、有想象力、经验性的语言,给读者带来在感觉、想象和经验上的具体性感知;从这个意义上,有语言能力的人可能都有文学表达的能力,而对于有些人,他在生命的过程中,执着于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在文学创造的那个世界中获得安慰,至少那个世界能否获得他人的认同,那是另外的事。卡夫卡的作品,是生命的需要,他不写作,可能会死,他临终前,期望朋友将他的作品付之一炬。余秀华的写作,是一个残疾女孩从小到大的与孤独和恐惧相伴的行为,在文学写作中,她获得了一些安慰。杨健的写作,表达的是一个月工资不足三百元的下岗工人对宇宙苍生的悲悯,这是多么荒谬但又多么有意味的事。我也想起我的同乡魔头贝贝(安徽枞阳人,后随父母迁居河南南阳),他是一个油田的看仓库的工人,但他却一边看守仓库,一边拿着啤酒瓶默念合适表达自己的文字,这些分行的文字成了当代很多人喜欢的诗歌……
我觉得文学的“草根性”在这里,文学写作因这种与个体生命连接的特性(它是一些人生命中自发的需要),其生长状态不一定与时代的节奏、历史性的那些革命段落构成对应关系。你说这些从“草根性”里冒出来的诗人是“精神贵族”,也可以。这两个词在这里有共通之处。在我的理解中,对于文学写作而言,“草根性”不一定是写作者所属社会阶层方面的意义,这个词道出的其实是文学写作的一个本源。这种从文学源头而来的“草根性”,往往给气喘吁吁追赶世界潮流而常常活力匮乏的主流诗坛,带来新的面目与新的激动。曾经的雷平阳、江非、杨健、魔头贝贝等,近期的余秀华等,恐怕就是例子。
四、热闹与忧思:新诗在新世纪
应该说,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诗歌似乎也开始了新景象。“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两大阵营的对抗,网络论坛、博客等新媒体,多种因素刺激了当代汉语诗歌的表面繁荣。除了正式出版发行的十余种主要诗歌刊物和十余种刊登诗歌的主要综合性文学杂志之外,诗坛不断涌现的大量的民间刊物令人目不暇接(有些民刊也慢慢转正,成了非常漂亮的正规出版物)。这是一个诗作空前繁盛诗人无比繁多的时代,除了那些早已成名的诗人在继续写作之外,无数新的诗歌写作者借着网络、民刊、官刊和各类奖项不断浮出水面。
“诗人”,这一特殊的称谓和身份,在今天也变得含糊不清。诗人们大多不再是为了诗歌含辛茹苦的落魄才子,也少有为了诗歌而献身的文化英雄,在市场经济的风云中游刃有余同时诗写得也不错的大有人在。今天绝大多数诗人,有自己的职业和收入,在现代化的生存体制当中爬行或游弋,诗歌只是工作之余的精神追求和自我慰藉。诗人在自我表达的同时,也因着诗歌获得了许多陌生人的爱戴与仇恨、来自远方的祝福和攻讦。在特定生存模式的挤压当中,许多爱好文字的人惊讶地发现诗歌还可以帮助我们寻求心中潜在的光荣和梦想。诗歌作为一种“事业”和诗人作为一种“身份”在这个时代被空前边缘化。诗歌不再抒写一个宏伟的社会或文化的想象共同体,而只是抒写个人的情感经验,时代的主题和景象只是在个人的经验表达中得到可能的“折射”。诗人不再是专门写诗的人,他只是在生活的某个时间回到诗歌写作当中。但也可以说正是这种边缘化,诗歌才可以从附着于种种意识形态的状态中回复到个人、回复到诗本身。诗人作为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个体,才可以真正拥有写作的自由,获得写作的可靠资源和能力。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时代,每个人至少可以在写作中尽情地对自我进行想象性的表达。这似乎也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除了特定的政治命题我们不能触及,我们的想象性言说似乎可以无所不至。这种“过剩”的个体精神独立性和思想自由的幻觉,衍生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极为繁盛的诗歌话语。在连篇累牍的诗歌文本和不断涌现的诗歌写作者面前,新世纪新诗的真实情形如何?一位诗人、批评家在回顾近十年的诗坛时写道:
……与十年前相比,大部分诗人写得无疑更好了,从乡镇到都会,诗歌界整体的技艺达到了水平线上。十年前的重要诗人,如今仍然乃至更为重要,少数人能够持续地掘进,写出了一批又一批可信赖的代表作,并将风格严肃地发展成各自的轨范……
与十年前相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诗歌的人口无疑更多了,诗歌的门槛也更低了,似乎先于教育、医疗,实现了真正的平民化,诗歌地域的分布也更为均衡,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冒出一两个欣欣向荣的诗人团伙。原本恶斗的“江湖”越来越像一个不断扩大的“派对”,能招引各方人士、各路资源,容纳更多的怪癖、偏执、野狐禅。出于对传统诗歌交际的反对,新诗作为一种“不合群”的文化,曾长久地培育孤注一掷的人格,放大“献给无限少数人”的神话。近十年来,诗之“合群”的愿望,却意外地得到报复性满足,朗诵的舞台、热闹的酒桌、颁奖的晚会、游山玩水的讨论,从北到南连绵不断,有点资历的同仁们忙于相互加冠加冕。这当然是好事,虽然加重了诗人肠胃的负担,但带来了心智和欲望的流动。
与十年前相比,批评的重要性降低了,集团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各方都在无意识中规避,但批评的社会功能却取得长足发展,有时候让人联想到某一类服务行业……这种服务甚至不需预约,可以随叫随到。另一部分批评,则立足长远,忙着在当代思想的郊外,修建规模不大的诗人社区,好让德高望重的诗人集体地搬迁进去,暗中获取长久的物业经营权。影响之下,名气略逊一筹的诗人们,一定会自动在附近租住青年公寓,期望能够联动成片,成为郊外逶迤的风景之一种。……
似乎,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十年后的诗歌的生态似乎更为健康、从容、平稳,诗歌界的山头即使还林立、丛生,但那只是衬托出文化地貌的多样性而已。唯一让人略略吃惊的是,诗歌写作的“大前提”较十年前,没有太大改变;诗人对自己形象的期许,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诗歌语言可能的现实关联,没有太大改变。真的,没有太大改变。如今,大部分诗人不需要再为自己写作前提而焦灼、兴奋,也不必隔三岔五就要盘算着怎样去驳倒他人,或自我论辩。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无非是丰富自己的前提,褒奖自己的前提,并尽可能将其丰富。从“20世纪”的角度看,从充满争议的新诗传统看,这倒是件新鲜事。
…………
或许是上世纪末的论争,透支了诗人的体力,最近十年诗坛虽然不缺少攻讦和斗嘴,但早已没有了整体的“抗辩”,这显示了空间挣脱了时间后的轻盈。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主体弱化的时代,是一个需要辨认危机、补充钙质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在现场扎根、掘井、张网捕兔、乱吃草药的时代,但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诗人主体形象的普遍高涨。……没有困境和难度的主体,缺乏临场逼真感的主体,他没有创造价值的贪念,实际上却做到了被通用价值牢牢吸附。……⑩
此文对新世纪新诗作整体评价非常精彩,我喜悦于其文字的漂亮,更珍惜其中的自省与警醒。置身于热闹的当代诗歌现场,很多时候,我们是否只是在消费诗歌?而对诗歌本身,无论从创造还是从批评的角度,我们其实并无多大的建设性?在一些人看来,这是“最好的时代”,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最糟糕的时代”……思想和抗辩、谦卑与渴求、困境与历险、激进与牺牲……这文学写作的应有品质,似乎不多见;或者,这些品质一直是潜流,是地火,依然在运行,只是尚未浮出水面;或者,早已显露峥嵘,甚至蔚然成风,只是你孤陋寡闻……
目前余秀华现象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意味着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复兴。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草根性”写作为整体平庸的新诗偶尔赢得一点脸面,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其意义不在于给文坛带来新奇的谈资,也不一定意味着期待中的那个“黄金时代”就已经到来,而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因为这样的诗人少,所以他们很耀目;由此,我们也知道:当代文学在文学写作之本源上的一种迷失和诗坛那种用生命在写作之品质的缺失。

2015年6月于珞珈山
注释:
①沈睿:《什么是诗歌:余秀华——这让我彻夜不眠的诗人》,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b7c5b80102vf0z.html?tj=1;沈睿:《余秀华:让我疼痛的诗歌(代序)》,第3~5页,《月光落在左手上——余秀华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2006年,从9月26日至10月4日,韩寒连写6篇博客文章,对当代诗人与诗歌冷嘲热讽:“现代诗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现代诗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回车”,“诗人本身就有点神经质,再玩下去就要变成神经病了”。
③刘年:《多谢了,多谢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184页。
④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闻一多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⑤朱又可:《社会在搞笑诗歌的时候,说明什么?》,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804。
⑥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南方文坛》2005年第3期,第25页。
⑦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自序)》,《摇摇晃晃的人间——余秀华诗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⑧莫里斯·布朗肖:《卡夫卡与文学》,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174143/。
⑨比如《旧约·利未记》17:11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⑩姜涛:《拉杂印象:“十年的变速器”之朽坏?----为复刊后的〈中国新诗评论〉而作》,《飞地》2015年第十辑,海天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6页。
⑩里尔克著,冯至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