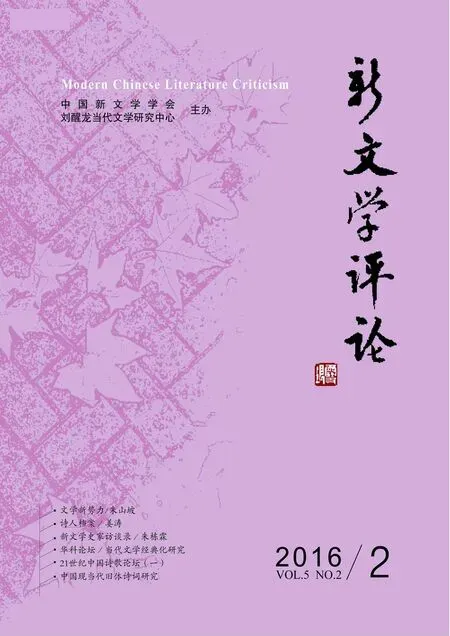新世纪的诗歌师徒群体现象
———以保定河北大学为例
◆ 周伟驰
新世纪的诗歌师徒群体现象
———以保定河北大学为例
◆ 周伟驰
最近几年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诗人留在高校任教,在创作上对他们的学生形成影响,产生互动,仿佛古老的师徒制得到了复苏。
“诗歌是不是可教的”这个问题,跟苏格拉底的问题“美德是不是可教的”一样,恐怕是可以持续讨论下去的。平静地考虑,诗歌有可教的因素,也有不可教的因素。对于传统诗歌来说,格律、用韵等等形式的规范是可教的,技巧的要素通过解剖经典也是可以教的,但是诗歌所体现的遭遇、气质、人格是无法教的。虽然无法教,但是有些精神的品质是可以模仿和景仰的。对于现代诗歌来说,也许在欧洲人看来,诗更多地事关天赋,因此难教,而在美国人看来,诗在于训练,熟能生巧,并非不可教。但是诗歌大师的出现,是否能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却是值得细想的。美国高校中创意写作班的成批涌现,确实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诗人,整体上繁荣了美国诗歌,成绩有目共睹①。至于有无大师,则或许可另外讨论。因为大师的出现不只是牵涉教育的问题。在民国时期,中国新诗的第一代(胡适、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卞之琳、废名等)在高校任教后,已经成功地培养出了第二代(穆旦、郑敏、臧克家等),可惜这个进程后来被政治粗暴地打断了。八十年代的诗人可以说是通过自我教育成才,限于当时的整个文化环境,他们的起点并不高,在对中西诗歌的了解上都不够深入,主要通过翻译作品来学习写作。八十年代的活泼和浮泛是一体两面,九十年代诗人们被逼得沉下心来做学术,一部分人开始进入高校,新世纪后新老诗人们集中到高校任教,出现了跟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相似的现象。虽然其中有一些专业分工上的差异(比如中国诗人一般在中文系任教,教的是文学批评而不是创意写作),但教师的诗歌观念和实践对学生的写作实践发生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然迟早会发生的现象。
据我的了解,目前在高校任教的知名诗人有多多、王家新、西川、萧开愚、张曙光、柏桦,稍年轻些的诗人中很多本身在学术上是科班出身,大部分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在高校任教,如雷武铃、臧棣、姜涛、胡续冬、冷霜、汪剑钊、谭五昌、伊沙、陈均、荣光启、魏天无、胡桑、余旸、张伟栋等,还有一些是因为留在高校工作(行政)而对诗社发生影响,如肖水等人。这些诗人对学生的影响和纯粹做文学批评的教师(如张桃洲、敬文东、江弱水等)尚有不同,因为后者只从事理论的指引工作,而诗人则以其写作实践对学生的创作予以实实在在的影响。只在纸面上读到一个诗人,跟这个诗人成为你的老师指导你写作或被你摹仿,可视为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个诗人作为体制的一部分,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时,诗歌受到的重视就会大为不同。当然我所说的“师徒制”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的师徒制,因为现代师生关系跟中国古代书院制、私塾制和西方中世纪修院制不同,师生并未生活在一起,严格说来只有知识传授的关系,至于课外是否有密切的交往,则完全看师生个人是否投契了。
这种现代的师徒制能否产生一个好的诗歌写作上的传承?我想这也是因人而异。同样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壤上,有的萌芽结果,有的一芽不发,都有可能。也可能有的教师更用心一些,有的更粗心一些,因此而有不同的结果。时间有先后,教法有巧拙,学生有聪明愚拙的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诗歌这个东西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诗歌本身是否能教就一直争议不断,哪些因素可教也可以讨论,诗人的教育也许只是激发起了学生创作的热情,却不一定对学生具体如何创作构成教导……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诗歌教育都能结成正果。
不过以我有限的见闻,还是知道一些诗人在诗歌教育上取得了成果。以我这两年读到的一些年轻诗人的好诗为例,都跟这个师徒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敬文东和冷霜对中央民族大学诗社的学生(如李海鹏等人)的创作会有影响,臧棣、姜涛对北大一部分写诗的学生的影响——北大学生比较自信,个性强,承认自己受影响的恐怕不多——但我相信通过文本的分析和感受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当然学生的写作受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一定就只来自老师。比如,这两三年写出了一批相当优秀的诗歌的范雪②,她的诗歌语言我就认为受到了作为老师的姜涛的很深影响,当然同时也可能接受了萧开愚和席亚兵的影响。
由于个人交往的原因,我跟雷武铃和他的弟子接触较多,因此作为一个“当代诗歌师徒制”的旁观者,我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地位,可以在比较充分地了解上谈论他们师徒之间、学生同门之间的互动。
在北大写诗的朋友中,我跟雷武铃、杨铁军、吴畏都是研究生1992级(席亚兵要晚一级),1995年毕业。杨铁军毕业后去美国读书,我留在北大就学,继续读博,吴畏去了武汉大学读博,后来放弃写诗。1995年雷武铃毕业后,可能因为要调动爱人工作的缘故,去了当时被当作“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保定的河北大学任教,条件相当艰苦。1996年我曾去保定看望他,看到保定马路上的灰尘是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灰扑扑的楼道里堆满了大白菜,河大旁边的一条干沟渠是菜市场,令我很悲伤,武铃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还写诗。无论从城市外在的生活条件,还是学校的整体水平、学生的分数来说,河北大学都跟北大、复旦等发达地区重点高校无法相比。可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武铃以一个诗人的热忱,以自由、民主和真诚的作风,使学生对诗歌产生了热爱——热爱是最好的教育——培养出了好几拨诗人学生,里面我认为写得优秀的有不少。我现在能记得他们的诗作的,就有王长才、王志军、谢笠知、张国晨、王以琳、刘巨文、李俊勇、傅林、李君兰、王强、杨震、赵星垣、曹亚楠、郭溪等人③。其中,以质和量的综合水平论,说王志军、王强可列入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诗人的行列,是毫不为过的。
尽管在随后的写作过程中这些学生发展出他们各自的个性差异,但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武铃对于观察力的强调,因此,这让他们的诗歌写作从一开始就跟青春期写作的天马行空、感伤滥情区别了开来。武铃本人的创作,我认为其特点就在于观察与描述,而且是老式慢镜头式的、细致的扫描,这要求描述者沉住气,浑然忘我,全神贯注地移情于对象中,克制自己的情感,达到一种客观性。如果有感情的表露,那也是通过形象的移动似乎不经意地流溢出来的。比如,在《黄昏出门看雪》④一诗中,28行共花了约27行写作者在林中湖边徘徊,看到这个景那个人,但你会觉得纯是客观描述,但末尾有一句“我最终没打电话”却使看似无意义的零碎的场景一下子统一了起来,原来这是一个心乱如麻的人在对自己是否要做一个决定性的动作(打电话)犹豫不决中所见之景,这样写景越多越散,感情也就越激烈。但他不会像自白派或浪漫派那样大喊大叫。再比如在《远山》⑤这首较长的诗里,作者用了大段的笔墨描写和朋友垂钓聊天所见之远山和白云,偶尔也透露了自己的苦恼,看似冗长散漫,但最后一句“你的孩子刚做完心脏手术,必须赶回去给他换药”却使整首诗收敛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使前面所有的冗长散漫的描写都有了归宿和意义,得到了理解或谅解,而且可能更有力量。这就是慢性子的描述所获得的力量,打个比方,有的诗人擅长写短诗,相当于一百米冲刺,他可以先声夺人,但你让他长跑他就泄气了,底气不够了。有的诗人擅长写长诗,相当于马拉松或长途散步,开头看上去貌不惊人,但越跑到后来越有后劲,非常人所能及。武铃用笨重的描写组织起来的诗常常是后一种效果。如果说诗歌中用大段的描写可能会令读者分散注意力,觉得不够跳跃,那么在散文中,就能够更淋漓尽致地展现纯客观观察及描述的好处。《观云》是武铃的一篇文章,写他跟几个学生在傍晚观看天空云朵变幻的情景,我认为完全可以作为中学或大学“观察课”的范文。它对于训练学生如何拥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是颇有示范效果的。
在武铃的学生中,王志军、杨震、谢笠知、郭溪较多地继承了这个重视观察,通过描述来写人情的特色。王志军的诗集《时光之踵》中的大部分诗,都具有坚实的观察的功夫。比如《老房子》⑥,在镜头缓慢的摇摆中,老房子里陈旧的物什逐一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可是它们只是单纯的事物吗?它们是跟“往昔”这样的时间感受连在一起的,所以它们不只是物,它们令人想起人和人的感情,特别是亲人之间的亲情。通过“旧物”来念“旧情”,诗中的观察非常细致,如果用古典绘画来比喻,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全景壁画。谢笠知《一朵白云》⑦详细地描述了一朵白云的出现与消亡,这朵云跟普通的云相比,更有自己的性格。“它从容、谨慎,/抵抗着四面八方的撕扯,/它抓紧自己:这轻逸的偶然的形体。”可是,这朵云在存在的偶然中,实际上是一朵充满剧烈的紧张感的云:“蓝天后面绝对的黑暗,/这空无,是渗透在它每一根/棉丝般纤细的神经里,/那激烈的恐惧,让它抓紧自己,/保持完整。让它充满力量,越过狂风。”这样的云已经突破了“云”的所指,而带上了缘起和存在、维持同一性和存在的神秘了。再如王强《树影》⑧一诗,不仅写出了一棵树在风中死劲挣扎的样态,而且写出了它的“内心”的那种紧张。这些诗里都有一种耐心“观看”的艺术。
我从大学起参加过各类诗歌团体,知道要维系一个诗群的写作,需要办刊、交流,持续地保持成员诗歌阅读的兴趣和写作的习惯,还要有热心人张罗各种集体活动,否则随着各人毕业、出国、工作、结婚等生活变动的发生,有的成员很容易“脱团”,整个团体也很容易“散团”,过几年大家对写诗的热情就淡漠下来,直至完全不写。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诗歌毕竟是人生的奢侈品,是“无用之物”,它无法带来养家糊口的资粮,甚至带不来名义上的光荣。但如果诗友之间的友谊还在,也许也可以作为写下去的一个理由。就武铃和他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早些年武铃自由时间还比较多,课后也多和学生玩在一起,可以经常聊天,创作的感受和倾向自然而然地得到传播和交流,近几年可能比较忙碌,但假期一有空,他仍会跟学生一起出去郊游、聚会,通过微信、手机、办刊(他们办有一个诗刊《相遇》,大约两年出一辑)等跟学生在一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武铃和他夫人小廖热情好客的性格优点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换了一个内向的老师或缺乏耐心的老师,或家人不好客的老师,可能就不会乐意花这么多功夫跟学生聚在一起了。在诗群联系中,起到一个加强友谊的工具是“献诗”。在八九十年代,诗人们一度热衷于写“为某某而作”的诗,这可以既献给某某朋友,同时诗里所谈的内容也不限于某某朋友,但写得多了,也会出现所写内容跟所致朋友毫无关联的现象。你完全可以写一首“为胡适而作”的诗,而诗里根本没有胡适的影子,或者他跟你的关系完全不明。我注意到武铃诗里很多“献诗”与此不同,他的这类诗有时主标题就出现朋友的姓名,有时副标题是“给某某”,诗如其人,就是对两人或多人的共同经历或活动的直接回忆、描述或感想,因此,这些诗本身就是友谊的产物,它也起到了加强友谊、增进理解的作用,我们可以将这类诗称为“交谊诗”。在王志军、王强、叶鹏等人的诗中,也有大量这样的诗。如果将他们师生之间、同门之间、诗友之间这样的“交谊诗”罗列出来,恐怕足以构成一个复杂多边的、既有核心又有开放的分叉路径的圈子。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其实这类诗也是非常之多的,常发生在诗友之间,无论馈赠的一方还是接受的一方,双方都对诗中所说的事情是了解的,对于其中的情谊是清楚的,它本身有一个产生和壮大的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机制(语言的社会功能本来在先于“私人语言”),它是值得研究的一个主题。在新诗中,我不清楚是否有人对新诗的“交谊诗”有过专门的写作和主题化,以及是否有人对“交谊诗”作过专门的社会学或文艺学的研究,总之我觉得这是随着当代“诗歌师徒制”的出现,为了维持诗歌友谊和写作,而自然地在诗友圈子里出现的一个“副现象”。
就我的观察所及,目前雷武铃的诗歌师徒群的特色,就是上面所说的两个,一个是以“观看”和“描述”为底子,一个是以经常的联络和“交谊诗”维持诗群的创作热情。学生在河大接受教育的年份一般都是有限的四年(个别七年),因此在校期间主要是发生了对诗歌写作的兴趣,热爱上了这个“事业”,开阔了视野,至于具体的写作风格的形成,那要等到他们在社会实践、在自身生活的展开和命运的遭遇中,在各自的感受、磨砺、碰撞中产生,由于各人的性格、气质、遭遇、精神境界不同,因此会发展出不同的诗歌类型。对原有诗歌信念的加强、巩固、纠正、偏离,甚至反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王志军、王强都已离校多年,他们的写作路向就各不相同。王志军的近作加强了想象力的一面,王强则注意到诗歌的音乐性,对雷武铃有时过于散文化形成纠正。虽然如此,但他们的诗歌从一开始都以侧重“观看”为出发点,使他们跟同龄人相比,诗歌拥有一个坚定的基础,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同时“交谊诗”的写作,使他们对人性更多地持“同情的理解”,更加富有人性。我觉得从这两点来看,雷武铃作为一个诗歌教师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诗歌写作的师徒制也会有它的弱点。跟着一个强势或气场强大的师傅,学生方面可能会略有压抑,一方面在发表上和获得承认上占一些优势,但同时有可能成为导师的一个“副本”。因此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要学到老师的长处,另一方面也要“吃百家饭”,开阔写作视野,吸取众家之所长,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另外,对老师自身写作的一些盲点,如果学生对之没有明确的认识,并在写作实践中加以克服,反而加以放大,则可能成为诗群写作中的软肋或集体盲点。这只能寄望于学生将来随着水平的提高,予以纠正。
在别的高校诗歌师生群那里,可能发展出了另外的写作特色和交流方式,希望将来能看到更多的实例。我这里仅仅举了一个我本人接触到的例子,不能代表这个新现象的全部,可能叙述有不周全之处,还望大家谅解。希望能看到更多高校诗歌师徒群的相关报告和研究。
注释:
①如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坊成立于1936年,培养了诸多优秀诗人,马克·斯特兰德就曾在那里学习和教学。
①范雪:《诗十八首》,萧开愚等编:《中国诗歌评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③广东《橘州文艺》2014年第1、2合刊(总第五十一期)刊出了一个包含了这些诗人的专辑《河大诗选》。杨震的诗可见于《2009》(民刊),山水印作2012年版。刘巨文的可见于其自印诗集《北方》2016年版。
④雷武铃:《赞颂》,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
⑤雷武铃:《赞颂》,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⑥王志军:《时光之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⑦谢笠知:《花台》,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⑧见王强诗集《风暴和风暴的儿子》(民刊),广州副本制作2014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