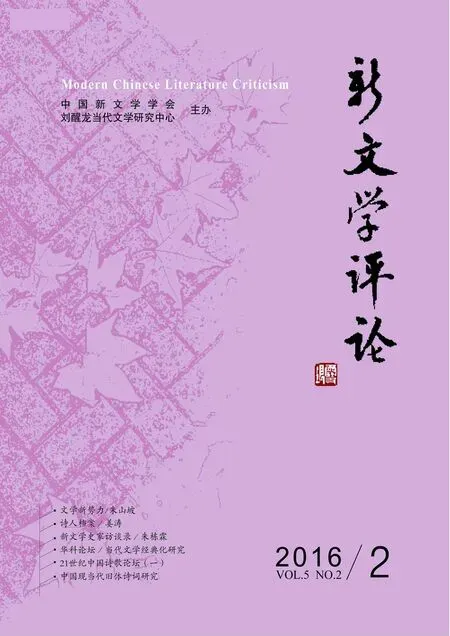新诗的大众化与历史想象力
———新世纪诗歌印象
◆ 师力斌
新诗的大众化与历史想象力
———新世纪诗歌印象
◆ 师力斌
2015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旗帜性刊物《新青年》创刊100周年,是胡适第一首白话新诗《蝴蝶》发表99周年。新诗眼看就一百年了,迈入新世纪也已15年。15年在中国诗歌史上并不算长,但在百年新诗中却不算短。15年来,诗歌与我们身处的国家一样,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伴随“诗歌边缘化”、“诗歌死了”的各种唱衰、担忧,是诗歌界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天,以及优秀诗歌的沉潜。各种命名不断出台,标志着诗歌无尽的活力:新世纪诗歌、21世纪诗歌、打工诗歌、网络诗歌、新红颜写作、下半身、口水诗、丽华体、乌青体、中间代、“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诗歌小鲜肉也已经上场。奥运诗歌、抗震诗歌、抗战诗歌的大规模新闻性出现,体现出诗歌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一马当先的快捷优势。多如牛毛的诗歌活动,这个诗会,那个朗诵,线上征集,线下联谊,江南首发式,江北研讨会,诗集、诗选、诗刊、网刊的出版,诗歌大展、诗歌方阵的亮相,展示着诗歌旺盛物质生产力。驻校诗人、诗歌研究院、诗歌中心、翻译中心等新事物的出笼,则是诗歌研究机制与时俱进的明证。随着时光的流逝,尽管诗歌的大部分繁华都已落尽,但仍有一些被我们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库、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等一系列诗歌丛书,杨克的《新诗年鉴》,程光炜的《岁月的遗照》,黄礼孩的《诗歌与人》,谭五昌的诗歌年度排行榜,伊沙的微博“新诗典”,柔刚诗歌奖,以及一系列沉着坚毅的诗歌团体、出版、活动、奖项等诗歌品牌,都依然在我们眼前闪耀。
新世纪15年是网络诗歌的黄金时代。雨后春笋般的诗歌网站、论坛、社区,鱼龙混杂,活力无限。不管有多少质疑,旺盛的人气不可阻挡。网络是诗歌零门槛的技术支撑,丽华体是诗歌低起点的样板,免费阅读、即时互动、一键搞定,是诗歌消费零成本的有力证明。不花钱不出门就能把最高雅的消费品搞定,诗歌已经成了21世纪最便宜的文化消费。诗歌虽然经常以打酱油的方式进入网民的生活,但很可能与阿里巴巴双十一的天文销售数字一样,将迈入历史。
新世纪15年是诗歌选本的黄金时代,民刊的黄金时代,诗人小群体、诗歌NGO的黄金时代,他们殊途同归地在政治禁忌稀释的诗歌领域喧哗与骚动。
新世纪15年的诗歌,将来在诗歌史上应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原因在于,由全球化、社会转型、网络技术、和平年代等多重因素造就的诗歌大众化潮流。“每一片树叶的正反面都被写过了”。诗歌生产、流通、消费、评价的平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校的BBS、网络社区、诗歌网站,然后是博客诗歌、微博诗歌、微信诗歌、“新诗物”接连涌现。说诗歌神话未免夸张,但诗歌奇迹却时有见证。余秀华仅是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奇观之一。丽华体、乌青体、诗歌春晚、汪国真争论、余秀华走红,这些大众化的诗歌事件,都是诗歌大众化浪潮中的浪花。
与前述事实相关联,一个以“草根诗歌”崛起为代表的诗歌大众化时代到来了。诗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全唐诗》一共四万来首,当下一年诗歌的产量至少是唐诗的十倍。无数草根网友散布在祖国各地。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但见君写诗。不同于1958年诗歌“大跃进”的体制性推动,新世纪诗歌大众化更多的是市场推动和草根属性。“国家”在诗歌中似乎是缺席的。两大身份不同的诗歌群体,打工诗歌和女性诗歌,格外引人注目,与“草根诗歌”纠缠在一起。如果说女性诗歌的崛起,是消费主义、女性主义双重语境的产物,那么,打工诗歌则是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乡差别日益加大的历史后果。他们的出现,都与这个时代息息相关。
秀诗,秀图,秀生活:女性诗歌新常态
新媒体的普及,极大激发了女性诗人的表达欲望。秀诗、秀图、秀生活,成为女性诗歌的新常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前沿情况,在女性诗歌这里表现得最为鲜明。言论自由往往被置换为文学表达的自由,文学表达的自由往往又置换为诗歌表达的自由。“五四”时期如此,1980年代如此,今天的女性诗歌(包括男性诗歌)也如此。以诗歌为投枪也好,为鸦片也好,为选票话筒也好,都不外乎是一种文化策略。如果网络被取消,我相信,至少会有一半的诗人灵感消失,创作减退。在网络化时代,一首诗要大于一首诗。一首诗在博客上贴出来,至少也包含了以下用意:一是“我贴故我在”的主体性宣示;二是“我写故我能”的向传统文学生产体制的挑衅。我也会写诗,诗歌并不神秘,并不高雅。三是“我写故我自由”的顺手牵羊式的文化诉求,我爱写就写,你爱看不看,爱谁谁。一个女性诗人的写作,不管标明还是隐藏身份,都会增添一种含义,“我和男人有区别”,“我理解的诗是这样的,而不是你们男人理解的那样的”。“我的生活是这样的,而不是你们那样的”。
女性诗人的急剧增加,绝对是新世纪诗歌的历史性事件。李少君的观察非常敏锐,他在2010年与张德明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中说,“最近,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网络上出现的女诗人越来越多,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有一些已经被主流诗歌界逐步接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情况。因为在朦胧诗和第三代中,女性诗歌似乎更像点缀,比如朦胧诗和第三代中,女性诗人数量就不多”。这篇对话提到了几十位女诗人的名字,都是我非常陌生的。然而,这些女诗人仅是沧海一粟。周瓒提供了更多佐证:围绕在《女子诗报年鉴》、《翼》、“女书诗社”周围的女性诗歌群体,黄礼孩等编辑出版的《诗歌与人》、《2002中国女性诗歌大扫描》、《中国女诗人访谈录》,晓音主持的《女子诗报年鉴》等。周瓒估计,“新世纪十年中活跃的女诗人总数超过了20世纪后半叶(亦即当代文学五十年)的女诗人的总数”。娜仁琪琪格主编的《诗歌风赏》丛书,汇聚了从王小妮等60年代诗人到“90后”新诗人,各种年龄段女诗人一百多位。新世纪以来活跃的女诗人,从1940年就开始写诗的老诗人郑敏,到1960年代出生的王小妮,还有大量的“70后”、“80后”、“90后”诗人,直到近两年的“00后”小诗人,组成了中国两千年来最壮观的诗歌合唱队。
中国古代女诗人比例非常小。 《全唐诗》九百卷中,妇女作品有十二卷,占1.34%①。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是一本女性研究权威著作,据该书统计,自汉代以来各代的女作家如下:汉魏六朝32人;唐代23人(包括五代蜀的花蕊夫人费氏);宋代46人,元代16人;明代238人;清代3571人。三千不是小数,但平均到三百年中,每年也就10位。当下的女诗人每年岂止10位、100位!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的大型诗歌选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全书30册,共选诗人349位,女诗人58位。1980年代之前成名的女诗人仅有6位:冰心、林徽因、玲君、陈敬容、郑敏、林泠。52位是1980年代之后成名的女诗人。在第二十六到三十卷,这以“60后”、“70后”、“80后”为主打诗人的五卷中,女诗人大多占到将近一半。这样的选择绝不简单是厚今薄古,还有女诗人创作丰富、质量之高不容随意舍弃的缘故。
诗歌生活化是女性诗歌的首要特征。写诗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主要用以纪录行迹,抒发感情,寄托理想,朋友交流。安琪的一句诗“当我死时,诗是我的尸体”,就是最极端的说明。在新浪博客首页“主张”一栏,金铃子写的是:简单生活,简单写诗。施施然的新浪博客,贴了不少画作,呈现诗画同源的主体形象。她的画中经常有一位古典女性,带有明显的自画像色彩。舒丹丹的新浪博客,贴有她的油画作品,与她的诗歌形成某种互动关系,展现诗人生活的多侧面。
女性诗歌受消费文化的浸染非常深,突出地体现为四种模式化:身体依恋、佛寺朝拜、小资情调、古典想象。下面提到的女诗人是我从大量阅读中筛选出来的,她们非常优秀,诗歌技术娴熟,因此,她们存在的问题也就更具有问题代表性,必须严肃对待。
身体依恋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最近的源头是1980年代翟永明、伊蕾等女性诗人对身体的爆炸性运用。三十年后的今天,身体已经被本质化、程式化,异常契合消费文化的逻辑。余秀华的“去睡你”即是典型。大量的女性诗歌暗含如下判断:写身体就是写真实;身体大于天;身体等于地气;身体是日常生活的核心。身体仿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社会历史间的复杂关联被取消了,成为与时代、社会脱节的空洞肉体,就像网络上的美女头像一样。来看几个例子。 “一条流向暮晚的河,/它平静,忧伤。/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比如真实。/真实的东西需要用手去抓开,/像弯曲的子宫,/它痉挛,/它流血,/它经过一个人的身体。//像一条河流向暮晚。” (红土《现状》)“她的体内蓄着湖泊 蓄着一条江/但还没有女性的温情/还不懂得那将不断沉沦的深渊/就要在她的身体上耸起高高的忧愁/和不眠的甜蜜 与绝望”( 陈小素《青春期》)。“作为养女,我从来都没敢碰过/它们,即使在它们最饱满的时候”(离离《乳房》)。 “年轻女士的衣领低了,露着/女人平常的胸脯,肉色的乳沟向下/天然的箭头指向/决定她骄傲性别的火山,幽谷,/罂粟花。它羞闭。”(郑皖豫《放蜂》)“在夜里/有时,她会把手/轻轻放在乳房上/那儿肌肤的柔嫩和白皙/有如珍藏的月光”(扶桑《手与月光的谈话》)。太多啦,可以点出一长串名字:蓝蓝《诗篇》,衣米一《时光》、《对话》、《春》、《听鸟》、《他们在教堂,我们在床上》……百分之九十的女诗人都受这方面的浸染。
佛寺朝拜是一个宽松的说法,主要想描述女性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佛、佛陀、禅、塔、寺、经幡等与佛寺相关的语汇这一现象。马克思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个判断非常深刻。市场化生活的压力,社会转型带来的创伤,价值观的巨变等等,使一部分人将精神寄托转向佛陀等宗教领域,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南怀瑾、星云大师、释永信、仓央嘉措等公共化的佛教名人的鹊起,就是其表征。最令人瞩目的是,不断有高学历精英人士出家修行的消息。很多社会名流信佛,如李嘉诚、刘德华、李连杰、王菲。佛寺符号在诗歌中的大量出现,正是这种社会思潮的反映。女性诗人常常将佛想象为一个清净、超脱的世界,在这里求得内心安宁、解脱和对罪恶的饶恕。“一座佛塔,一本诗书,是流水的两岸,是人生平等的两极。”(清荷铃子《蜕变》)。“我曾去庙里,小半天呆坐,看池中锦鲤,鱼戏莲叶。/也曾孤自一人,登那九级浮屠,塔阶上的足音让我宁静,/那渐行渐窄的阶梯,又令我生了恐惧,莫名孤独。//从前我去庙里,是为了姻缘或好儿女/而今我仍常去,只为在菩提树下坐一坐。”(舒丹丹《我曾去庙里》)余小蛮的《收割》、《凉水寺》,李云《佛光之夜》,想象自己的另一重境界,借佛出世,超脱现实。没有市场的功利、钻营、压榨、巧取豪夺,也没有世俗的尔虞我诈、利益喧嚣、心灵浮躁。一句话,现实中所有的丑恶庸俗,在佛的世界里都消失了,只剩下清净、安宁、祥和、幸福。由此可见,女性诗人们能够想象到的理想社会,不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或者其他的大同世界,而是佛界净土。染香的《安卡》通篇渗透了对于佛的领悟和感受,佛在这里已经不是只言片语的引用或者点缀,而是贯穿全诗的思想支撑:“有时候,你是一页并不深奥难解的经文,被长至脚踝的咖色衲衣深情拜读——那暮烟一样的眼神哦,那金属色的音质!”“你是行者,也是风中的童话,安卡。”这首诗,染香调动了视觉、听觉等全身心的感受,来描绘“你”带来的幸福体验,塑造出一个综合、丰满而光辉的形象,写得深情投入。如此崇敬的心怀,之前仅存在于对领袖的敬仰之中。这真是莫大的历史性变化。
小资情调在这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称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二是指称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忧伤、孤独、疲惫、软弱、拥抱、温暖、叹息、梦、流水、大海、草原,成为此类诗歌的高频词。你、我二人天地,构成这些诗歌的人物关系(天地间别无他人)。“你来,我的世界温柔似水。”(素素《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我愿意在秋雨中自刎。/为你,瘦出原始的峭壁。/和峰峦。/我与你交换这间山山水水……” (水晶花《大地情人》)“小兽,无辜一样纯洁的小兽,昨晚我突然想起你,也许今天是立冬的缘故,我想起你皮毛上的光,羽翎里的色,唤醒前世般温暖的记忆。”(李见心《可能之诗》(组章))“爱上一个冥想的人,叹息着,将时光打发,又不舍,再拥抱入怀。”(苏若兮《音乐》)吻是小资情调的必备佐料,在这个针尖上,已经跳出了千百种舞蹈。“放纵是一种快乐,胜过你送我一万个亲吻”(朱巧玲《雅歌:乌鸦》)。宇向《我真的这样想》是她的代表作,整首诗就一个愿望,我想拥抱你。说实话,这是我看到的关于拥抱的最动人的诗歌之一,将它放在这里进行批判有些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对于一个怀抱的渴望之外,这首诗真的无法再提供更多的东西了。
古典想象是流行文化安在诗歌身上的一条猴子尾巴。孙猴子主要在影视界翻跟头。宫斗剧、格格戏提供了大量元素,唐朝控、古装恋、闺怨情比比皆是:“她曾对着镜子理云鬓,贴花黄/微笑和喘息”(王妃《铜镜》) “我坐在兰花凳上 想念那些旧时代的女人/ 罗裙绣袜 纤手弄云/ 低声跟从自己的命运/陷在这园林里 美丽得让人掉眼泪”(冯娜 《园林》)。“波心荡,杀死人的月光啊//那时,我醉卧云端,御风而行。/二十四桥箫声骤起,纤手素花,/一声“公子,请——”(莫卧儿《扬州·白》)。翩然落梅是典型的古典控,她自己承认对古典诗词的偏爱。她说,“我一直对于美丽的汉语非常迷恋,喜欢摆弄那些精致、古典的词语。倾听她们的音韵,沉迷她们的意境”。“此地离长干十里溯溪而上/一重又一重的桃花/小桥流水浸入粉嫩的胭脂水彩”。“倚着栏杆远望/身上散发着千年石头的寂寞与寒香”(翩然落梅《长干曲》)。她的《与君别》、《大堤曲》、《胭脂痣》都是此类。诗中的这些文化符号都是八百年前的,与今天几无瓜葛。民国范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颇为流行的大众想象,为诗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趣味。“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当当作响的电车,从默片里开出来/灰色长衫和月白旗袍礼让着上下/不远处的钟楼,是夕阳中的诗人。”(施施然 《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霍俊明在《变奏的风景:新世纪十年女性诗歌》中,看到了网络对女性诗歌的强大影响,也看到了与消费文化的合谋。在大量阅读当下女性诗歌的过程中,我明显地体验到霍俊明所言的这种合谋。总在祈求佛、主、天使、上帝;常常碰到林徽因、萧红、张爱玲、林黛玉、上官婉儿、小燕子、武媚娘(其实是穿了唐装的范冰冰)。然而,我们看不到李双双、银环、白毛女、江姐的影子。流行文化成了诗人历史记忆的血栓和情感消费品批发市场。
并非所有女诗人都如此。另有一批女性诗歌向社会现实延伸触角。郑小琼、刘虹、阿华、横行胭脂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诗人,诗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关系,在她们那里得到更加宽泛的理解。王小妮是新世纪以来书写中国情绪强有力者。她的诗歌超越了性别的范畴,站在“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既细腻也宏阔,生动也深刻,在反映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的精神难题和心灵困惑方面,走在了诗歌的尖端。用陈仲义的话说,她由女性走向了母性。王小妮是最少用身体做文章的诗人之一。她的写作中心始终是历史中的人。怕、恐惧、担忧、清醒、知足、平常,构成王小妮诗歌的关键词。她在所有的诗歌中都写到了那个“看见当下”的主体形象,日常生活在她这里获得了精神的高度。这是王小妮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活在新世纪、全球化、市场化、现实中国的“社会女人”进入了诗歌写作。与以前虚幻、抽象的黑夜女性、卧室女性完全不同。“社会女人”这一路的诗人有很多,安琪、郑小琼,吕约、横行胭脂、尹丽川、巫昂、阿华、青蓖等。郑小琼的“载道式的阶级抵抗与性别争取”,为新世纪诗歌增添了“打工兄弟姐妹”的主体经验。青蓖以纪录片式的眼光去看生活。在“公共水管洗衬衣”的小先生,私下里爱着美丽少妇(《情人》),试胸衣的女人(《女子会所试衣间》),办公楼的白狐精,耍官腔的男人,都是职场上常见的普通人物,具体,有质感。有些诗人明显受到了当下思想论争的感染。李小洛的《偏爱》就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自己的偏左的习惯:“我只是偏爱左边一点/左眼看报,左手写字/用左边的眼球积聚光线”,“我固执地保持着这种习惯/其实和道听途说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无关”。
打工诗歌:粗暴的美学和历史呼喊
打工诗歌是群体意识的历史性表达,拓展和矫正我们对诗歌的理解。新世纪以来,打工诗歌与“底层文学”的讨论相联系,复活了业已消失的阶级记忆。它与小说界的《那儿》(2004年)、《马嘶龄血案》(2004年)《命案高悬》(2006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2年)、《地球之眼》(2015年)等一系列“底层”叙事相呼应,共同建构当下文学的历史想象。
打工诗歌往往集体亮相。有人不完全统计,在“珠三角”,写诗的打工者已达千人,有诗作发表的则在几百人。从2001 年至 2009 年底他们还出版了 《打工诗人报》、 《中国打工诗歌报》、《中国打工文化报》、《中国打工诗歌精选》等出版物,2002年创办了打工诗人网络论坛②。2001 年 5月 31 日《打工诗人》试刊号(第 1 期)标明的办报宗旨是:“我们的宣言:打工诗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打工诗歌,与命运抗争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心愿:用苦难的青春写下真实与梦想,为我们漂泊。”③最近有人估算,“目前在一线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应在万人以上,其中以‘70后’和‘80后’为主力,分布在不同的工种和城市间”④。这仅是工人文化的一小部分。北京皮村的打工者连续举办了三届打工春晚,崔永元、杨锦麟做过他们的主持人,影响巨大。新世纪初,《天涯》、《文艺争鸣》等杂志都发起过“底层文学”的讨论,打工诗歌是其焦点。2015年打工诗歌再掀高潮。2月15日,北京皮村进行了一场打工诗人朗诵会。“五一”期间,工人诗人邹彩芹、田力在央视新闻“工人诗篇”中出现。5月23日、24日“我的诗篇”草根诗会在天津大剧院小剧场举行,引发文艺界震动。农民诗人余秀华也现场念了她的诗《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⑤。工人诗歌+余秀华,似乎表征了“工农文化”的奇迹般历史苏醒。《北京青年报》、新华网等媒体报道了这两次工人诗歌朗诵会。加上此前对余秀华的地毯式报道,媒体对“工农”“诗歌”的呈现,抓住了这个时代的奇观。最穷困的人最需要诗歌。新诗成为最便宜的文化消费。工人诗歌重申了“诗言志”的属性,重申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优秀传统。“活着,我活在内心腻子粉的白!/活着,我活在皮肤被晒成油漆的底色!/……如今它站在我的扳手上,从扳手的孔里我活着!/如今它站在我的老虎钳上,从老虎钳的口里我活着!/……我活在甲醛的尖叫声中!/我活在电转悲鸣的速度中!/我活在内心荒芜的工棚里!/我活在不由自主的流浪中!”(程鹏《活着》) “刘汉黄男 26 岁土家族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人/身高1.7 米瘦小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东莞市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操作工人/2008 年 9 月 22 日入职 9 月 28 日下午/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冲床机器砸碎/……” (蒋明《杀人犯刘汉黄》)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的诗《流水线上的雕塑》广为流传:“手头的活没人会帮我干/幸亏所在的工站赐我以/双手如同机器/不知疲倦地,抢,抢,抢/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茧”。郑小琼、柳冬妩、谢湘南、郭金牛等一大批打工诗人的诗歌,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另类感受,呼号与呐喊,穿透力和刺痛感,对于以光滑、柔软、无力、空灵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美学为主导的诗坛,是有力的冲击,它以一种粗暴的不舒服感,强行扩大着诗歌的历史想象。诗歌古老的现实主义传统正在被唤醒、恢复。张清华说,他们的作品不一定能够成为最好的诗歌,但正是这些诗歌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它们比一个专业诗人的作品还要重要一些”⑥。
不只打工诗人写打工诗歌。伊沙《中国底层》,谷禾《宋红丽——1月16日〈××时报〉》,翟永明《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打工诗歌重要的不是它的美学形态,而是它唤起的美学原则。
写什么和怎么写:诗歌的历史想象力
新媒体革命带来的诗歌变革是巨大的,诗歌的大众化程度前所未有。但是,我们对此并不满意。原因何在?繁荣不等于强大,高原不等于高峰。经典短缺,气象偏小,或许是重要原因。
从丰富性来讲,新世纪诗歌已经广阔到完全能够容纳完全相反的诗歌实践和诗歌观念。有口水诗的嚣张,就有书面语来反驳它;有高雅玄虚的学院派,就有大大咧咧的民间派来修正它;有忧郁的小资,就有粗犷的莽汉;有下半身,就有上半身;有言志,就有载道;有纯诗,就有不纯;有审美,就有审丑;有隐逸,就有介入;有个体,就有群体……诗歌领域自身的对话、质询、辩驳、诘难就已经够热闹了。在新媒体撑开的大网里,谁都可以做齐天大圣,但谁都似乎露着猴子的尾巴。女性诗歌的个体表达也好,打工诗歌的群体诉求也好,女性诗歌内部的揽镜自照也好,还是放眼社会也好,诗歌最终还是要靠诗歌说话。与媒体掺和在一起的各种体、各种热、各种火、各种秀,这些“体热火秀”,于好诗,于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最终都是无效的。杨远宏的一个说法尽管极端,却切中要害:坦率地说,有的是更加恶俗的喧嚣和泛滥,比如,从唯口语到口水诗、废话诗、垃圾诗,从个体生命体验/日常生活审美到官能展览/下半身写作,从案头孤寂面对、沉思到现场裸奔作秀、热炒等等。应该承认,所有这些离经叛道的诗歌恶作剧,对现行强势的腐朽、专横秩序和规训,有一种痛快的社会学意义的挑战、解构和反叛;同时更应该指出,如此走火入魔或江郎才尽、诗歌的末日疯狂,在根本上与诗歌无关,它们只是以践踏、羞辱、摧毁诗歌为代价的“诗歌小品”、“诗歌散打”⑦。
这里,我想起了陈超先生的一个重要概念——历史想象力。2006年,他在《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一文中指出,“历史想象力”,不仅是一个诗歌功能的概念,同时也是有关诗歌本体的概念。“写什么”和“怎么写”,在历史想象力的双重要求下,是无法两分的。简单地说,“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历史想象力”,应是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深刻融合后的产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锐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当代又具有开阔的历史感,既捍卫了诗歌的本体依据又恰当地发展了它的实验写作可能性。这样的诗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诗,它不仅可以是纯粹的和自足的,同时也会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它不仅指向文学的狭小社区,更进入广大的知识分子群,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
面对陈超先生“历史想象力”这一诗歌标准,我哑口无言。我觉得符合这一标准的典范诗人就是杜甫。“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的统一”,“诗性幻想和具体生存的扭结”,“有组织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经验的深刻融合”,“把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在这强大的标准面前,一切口水、书面、学院、民间、女性、男性、下半身、上半身、打工诗歌、女性诗歌、草根写作、神性写作,是不是会一碰即碎?因此,我认为,对于真正优秀的诗人来讲,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实际上早已经解决,这是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最大收获。沈浩波一度被认为是下半身写作的代表,而近几年的诗歌实践表明,他不仅不是下半身,反而颇多上半身的“神圣”。臧棣早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典型,语言缠绕,修辞繁复,而当下的臧棣,口语用得比口水诗还溜,比如2015年的《劳动节丛书》、《取材于月亮的偏见》、《雾霾时代入门》。
尽管诗歌的大众化带来了新一波诗歌普及与诗歌热潮,诗歌的零门槛、零审查、零成本、低起点是诗歌“祛魅”、“去神秘化”的有功之臣,但它绝对不能代替或取消“历史想象力”这一最高标准。诗歌最终需要处理个人与社会、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想象、介入与超脱诸多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恰到好处的分寸感是经典产生的必由之路。优秀诗歌既需要广阔的视野,也需要精致的细节。诗和好诗之间的距离要大于十个太平洋。诸多诗人、诗评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罗振亚对新世纪诗歌观察的结论是,“过于纯粹的操作有悖于诗歌的个性,太贴近世俗的鸣唱也难以获得更多的青睐。理想的诗歌状态是生发于现实和心灵、但又不为其束缚、而能在贴近的同时又有所超越”⑧。杨庆祥“重启‘我’与‘我们’对话式的写作”的呼吁,张执浩“处理个人与时代、个人与民族(国家)、个人与公众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的期待,都与陈超的“历史想象力”异曲同工。这些观点,该是怎样的精细!这越发说明新世纪诗歌已经达到的高度。令人欣喜的是,如果认真阅读当下新诗,就会发现,优秀诗人正借“历史的想象力”向诗歌的高峰冲刺,大解、张执浩、陈先发、树才、臧棣、伊沙、雷平阳、沈浩波、郑小琼、安琪、路也等一大批诗人,都让我们期待。
2015年12月21日于和平门
注释:
①参见浙江大学俞世芬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女性诗歌研究》。②何轩:《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10年3月,第31卷第2期。
③何轩:《新世纪打工诗歌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10年3月,第31卷第2期。④参见《打工诗人首参加“打工春晚”:为3.1亿人立言》,新华网2015年2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5-02/15/c_127497618.htm。
⑤参见《暗夜淹没了他们的声音遮蔽了他们的身影》,《北京青年报》2015年5月26日。
⑥参见《“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网2015年2月10日,http://www.chinawriter.com.cn。
⑦《新世纪诗歌的新》,《诗歌月刊》2009年1期。
⑧罗振亚:《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北京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