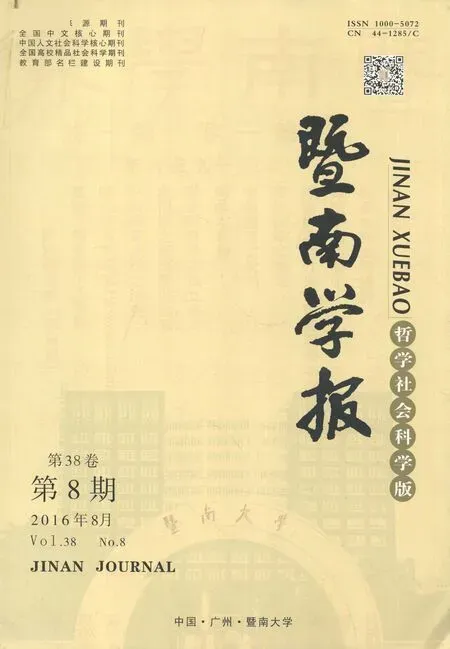东京审判侵略战争责任追究中的制度逻辑——以荒木贞夫审判为中心
邹皓丹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抗日战争研究】
东京审判侵略战争责任追究中的制度逻辑——以荒木贞夫审判为中心
邹皓丹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根据东京审判文献资料,在追究荒木贞夫是否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负有侵略战争责任时,为了弥补证据证明力的不足,被告、检方、辩方各自以明治宪法体制的不同面相作为逻辑前提进行立论,进而得出了有关侵占东北四省责任归属的不同结论。被告荒木试图将枢密院紧急会议的国家意志最高决策权作为论证集体责任的前提,认为应该由内阁和枢密院承担集体责任。检方的立论逻辑着眼于枢密院免责基础上的军部专制,据此起诉荒木贞夫的个人责任。辩方的立证脉络建立在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原则基础上,认为荒木的行为是遵循外务省外交方针的结果。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认定“反和平罪”司法实践中的需要,制度逻辑可以视为从追究国家责任过渡到个人刑事责任的桥梁。第二,源于东京审判面临证据文献缺乏的困境,制度逻辑有助于检方在起诉中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第三,源于明治宪法体制的复杂性,它为三方从制度的不同面相出发进行立证提供了便利条件。荒木的案例表明,审判各方对明治宪政体制制度性因素的认识对于理解东京审判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荒木贞夫;“九一八”事变;侵略战争责任;反和平罪;明治宪法体制
一、引 论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检方立证第Ⅲ方面,即“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它作为日本侵华的一个阶段,受到国际检察局的独立举证并提起诉讼。其中,对导致“九一八”事变①“九一八”事变的称谓日文对应满洲事变。它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它是指1931年9月18日当晚,日本关东军铁道守备队蓄意炸毁奉天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给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于次日占领东北军首府奉天的军事行动。广义上,它指的是1931—1933年期间,以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为开端,中日之间产生的一系列军事对峙对抗和政治外交危机。有关该事件的时间下限划分标准,中日学界有三种见解。中国学界一般将1932年9月日本承认“满洲国”作为“九一八”事变的终结;不过臧运祜认为,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出发,“九一八”事变的下限定为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比较合适。而日本学界通常将其下限定为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参见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段的认识,与日本学界的通常认识相一致,即从1931年9月18日—1933年5月31日期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全过程。(参见1946年7月1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北京、上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5页。)1947年2月24日庭审记录中更是明确记载:“满洲事变以塘沽协定作为终结。”(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28卷,第292页。)爆发和扩大的问题进行责任追诉是检方起诉的重点之一,而荒木贞夫则成为该阶段受到指控的八位被告①其它7位被告分别为: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冈洋右(病殁而免于起诉)、南次郎、大川周明(患有精神病而免于起诉)。之首。②在“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的起诉阶段,检方将荒木贞夫列于八位被告之首,并非随意为之。它反映了国际检察局对于荒木贞夫的重视程度。1946年1月21日,国际检察局A组组长伍德科克(W.W.Woodcock)(专门负责日本对侵略中国东北的起诉准备工作)对季南(Joseph Berry Keenan)的报告中,即将荒木贞夫列为该阶段的第一位被告。参见[日]粟屋憲太郎、豊田雅幸、永井均编:《東京裁判への道——国際検察局·政策決定関係文書》第2卷,東京:現代史料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另外,有关国际检察局起诉准备工作的分组问题,参见[日]粟屋憲太郎:《東京裁判の被告はこうして選ばれた》,《東京裁判論》,東京:大月書店1989年版,第83—84页。在1947年7月9日的庭审中,检方指控他在担任陆军大臣(1931年12月13日—1934年1月23日)期间,对1932年初日本以武力占领锦州、哈尔滨,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即对占领中国东北四省③所谓的东北四省,是指中华民国时期的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的政策决定——负有侵略战争责任。④国际检察局以“反和平罪”(诉因第27:1931年9月18日—1945年9月2日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对于荒木贞夫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所负的侵略战争责任进行追究。在法庭判决中,庭方认同了检方的起诉内容,判定荒木“对于(日军在)满洲和热河所作军事上政治上各种政策的进展与实行,他曾负担显著的任务。对于占领中国该部分领土所接连采取的军事步骤,他曾尽力加以支持。”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9页。
能够如此定谳,国际检察局对荒木贞夫的审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⑥国际检察局在1946年准备起诉阶段,共对荒木贞夫进行过12次审讯,并获得口供。时间分别为:1月18日、1月19日、2月5日、2月7日、2月8日、2月11日、2月13日、2月15日、2月21日、3月7日、3月8日、3月11日。参见荒木贞夫讯问笔录(case 58),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14卷,北京、上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检方立证阶段,检方指控荒木在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军事行动中负有领导责任,即是以国际检察局对荒木贞夫的讯问结论⑦有关国际检察局对荒木贞夫的讯问结论,参见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720—722页。为立论依据,并以荒木贞夫审讯笔录摘要作为主要证据获得法庭采纳的。⑧检方提交并获得法庭采纳的相关证据包括:PX188-A同盟国实施被告荒木贞夫讯问笔录(1946/2/15):被告荒木就任陆相后占领东四省决定时期。PX188-B同盟国实施被告荒木贞夫讯问笔录摘要(1946/2/19):为整肃满洲与首相、藏相、书记官长商量。PX188-C同盟国实施被告荒木贞夫讯问笔录摘要(1946/2/7、8、11):1.占领范围从东三省向东四省扩大;2.枢府本会议(1931/2/17):通过战领东四省军事预算。(此处枢府本会议的时间有误,应该为1931年12月17日。)PX188-D同盟国实施被告荒木贞夫讯问笔录(1946/2/8):荒木承认东四省的主权归中国。PX188-E同盟国实施被告荒木贞夫讯问笔录摘要(1946/2/13):为达成占领东四省之命令。与此同时,在辩方反证阶段,辩方律师则试图以荒木贞夫自辩陈词为依据⑨辩方提交的荒木贞夫自辩陈词共有两部分,分别是:DX3161被告荒木贞夫宣誓供述书、DX3162被告荒木贞夫其他陈述书(1946/2/11)提交检察方。,佐以文献证据,反击检方。无论是检辩双方相互攻防的过程及其附属证据,还是荒木贞夫本人的审讯笔录和自辩陈词,这些文件资料皆保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证据和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中,构成了回顾当年审讯的文件资料。
如果仔细阅读这些档案,可以发现,基于荒木贞夫是否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负有侵略战争责任,被告、检方和辩方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形成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叙述。而三个叙述的矛盾之处,恰恰以对明治宪法体制不同面相的理解为认识前提。本文试图对这段有关荒木贞夫审讯所形成的三个版本进行制度分析,希望以此为切入点,揭示出由明治宪法体制所构成的制度逻辑,在理解东京审判中所具有的价值。⑩有关东京审判日本、西方和我国的研究现状,参见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东京审判再讨论》第一章“东京审判研究的由来和展望”,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页。其中,并不存在相关研究,探讨制度逻辑在理解东京审判司法实践中的价值。
从制度逻辑的视角出发深入发掘东京审判的复杂性,亦是对日本国内保守学者、右翼势力所谓“胜者的审判”观点的有力批驳。日本保守学者往往以东京审判中事实认定的疏漏,证明审判不过是胜者的“政治权力工具”,被告确定、适用罪名均服务于美国占领政策。本文将证明,在检方立证起诉的过程中,事实认定背后隐含着其对明治宪法体制的制度认知。尽管这种对制度的认知受制于当时的知识水平,不可避免在司法实践中有所疏漏;可是,不能据此否认东京审判中蕴含的客观性、公正性。
二、荒木的版本——“九一八”事变扩大是内阁和枢密院集体决策的结果
在东京审判中,针对荒木贞夫在“九一八”事变扩大中是否负有领导责任,被告、检方、辩方之间形成了三种版本的叙述。其中,被告荒木贞夫的叙述是三种版本的核心,检方、辩方在庭审中皆围绕着荒木的版本展开攻防而形成其他两种版本。基于此,要对这三种版本进行分析,首先要从荒木的版本开始。
(一)荒木贞夫对“九一八”事变扩大问题的叙述
根据东京审判文献资料,荒木贞夫曾经接受过国际检察局12次审讯,也曾经提交过2份自辩陈词①根据当日的庭审记录,辩方声称其实存在3份自辩陈词,检方认为仅存在2份,对于第3份的存在“一无所知”。在辩方反证阶段,辩方也仅提交了2份自辩陈词作为证据,皆被法庭接受。参见1946年7月9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第306页。,它们是分析荒木贞夫对于此问题叙述的核心资料。
在自辩陈词中,荒木贞夫指出,他在1931年12月13日担任陆军大臣不久后,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的犬养毅对他提出了自己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政策:
(a)自卫和不扩大是处理目前形势的基本政策,但在此政策的基础上,应该意识到立即恢复法权和秩序,结束在满洲敌对状态的重要性。
(b)应该了解到破坏法权和秩序的人是张学良,他是需要对目前形势负责的人。因此,就这点而论,军事行动的战场必须严格限制,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出他的统治范围。
(c)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以应对现在锦州地区发生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尽管要如此行事,但在这样做之前,还是要发表声明,要求张学良撤兵,离开锦州地区。只有这样,才能清除将来的罪恶根源。②DX3161被告荒木贞夫宣誓供述书,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68页。在1947年9月10日的庭审中,该部分被辩方当庭宣读。
这段叙述表明,尽管犬养内阁认为,应该延续前任内阁处理“九一八”事变时所采取的、自卫和不扩大政策,但这项政策已经无法应对现任内阁所面临的、锦州的敌对形势。而造成此一敌对形势的罪魁祸首是张学良。在必要的情况下,只有以武力占领张学良治下的首府锦州,一举歼灭张学良的势力,才能彻底根除敌对隐患。鉴于此,在犬养内阁看来,出兵占领锦州可能是内阁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必要选择。这意味着,在荒木看来,正是犬养毅明确提出建议,认为内阁应该下定决心,以武力侵占锦州、扩大“九一八”事变。
接着,荒木在自辩陈述中论述了犬养将该观点上升为阁议的政治过程,并指出他本人的一切行为都是遵照内阁阁议施行的。
总理的这些观点在内阁会议中经过讨论,并形成了犬养内阁的基本政策。与这个决定相配合,我(荒木)与藏相、海相进行了必要的联系,并着手进行必要的准备,并命令陆军省执行相关职责。我同样将(总理)的意见转达给参谋总长,并要求他遵循执行。③DX3161被告荒木贞夫宣誓供述书,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69页。在1947年9月10日的庭审中,该部分被辩方当庭宣读。
根据荒木的叙述,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策经由内阁会议讨论,成为“犬养内阁的基本政策”,而且这项政策的具体实施并非仅由陆相一人承担,藏相、海相、参谋总长皆分担了该政策的执行任务。鉴于此,无论从政策决定过程,还是从政策执行过程来说,如果要追究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战争责任者,该负责的应该是内阁全体,而非他陆相一人。
审讯记录中,荒木贞夫也持此一相同论点①根据1946年2月7日审讯记录,检方曾就扩大“九一八”事变的责任者的问题讯问过荒木贞夫的看法,荒木明确回答,在他看来,是内阁决定了这项政策。(参见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294页。)该部分在1946年7月9日的庭审中,被法庭接受为证据PX188C,并当庭宣读。,而且在审讯官的反复确认中,荒木还补充了有关此一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更多关键性细节。
问(海德审讯官):内阁在12月17日批准了这项政策的一部分,该部分内容是由日本军队占领这四个省吗?
答(荒木贞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能说政策的一部分是不是获得了内阁的批准,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首相和其他所有的大臣都同意这个政策,否则它就不能被执行。
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同意的?
答:政策实际上是在枢密院会议上决定的,所有该院成员、内阁代表或许还有天皇都出席了会议。②1946年2月8日,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303页。在1946年7月9日的庭审中,该部分作为证据PX188C被法庭接受,并当庭宣读。
根据荒木补充的细节,内阁在做出侵占东北四省的政策决定后,尚进行了两步政治行动,才将该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第一,内阁批准了军事支出,只有如此,军方兵力调动才有可能实现。第二,内阁将此一政策付诸枢密院审议,并在1931年12月17日获得枢密院会议的认可。
关于12月17日枢密院会议的性质和具体内容,荒木的审讯记录中仅保存有如下一段叙述:
问(海德审讯官):将军,为什么说这是一次非常规会议?
答(荒木贞夫):这实际是一次紧急会议。军费支出要求通常需要在议会中被通过,但是当时议会并不在会期。
问:要求什么样的军费支出?
答:要求平定张学良治下东北四省的军费支出。当时事态非常紧急,就好比发生火灾时无暇讨论或争辩应该使用哪种水泵一样。③1946年2月8日,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304页。在1946年7月9日的庭审中,该部分作为证据PX188C被法庭接受,在7月10日的庭审中被检方当庭宣读。
根据荒木的叙述,12月17日枢密院会议是内阁希望在不经过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为获得占领东北四省的军事预算,而将该预算议案付诸枢密院审议的枢密院紧急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中,内阁和枢密院一致决定,同意军部以武力占领东北四省,扩大“九一八”事变。
(二)荒木叙述的制度依据: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枢密院紧急会议
荒木对这次枢密院紧急会议的描述仅有上述寥寥数语,并不足以全面理解所谓枢密院会议的“紧急性”。荒木认为,内阁及枢密院在扩大满洲事变中负有责任,此一判断是否成立?要了解这个问题,则有必要从明治宪法体制的制度性规定中对这次会议的性质进行进一步分析。
明治宪法体制下,紧急状态可以视为政府获得特权的一种状况。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8条(法律的紧急敕令)④《大日本帝国宪法》第8条,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代法律之敕令。此敕令应于下次会期提交帝国议会,若议会不承诺时,政府应公布其将失去效力。([日]伊藤博文:《憲法義解》,宮沢俊義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31页。)和第70条(财政的紧急敕令)⑤《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0条,为保持公共安全,有紧急之需用,因国内外情势政府不能召集帝国议会时,得依敕令以为财政上必要之处分。在前项规定情况下,须于下次会期提交与帝国议会,以求得其承诺。([日]伊藤博文:《憲法義解》,宮沢俊義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116页。),当国家遭遇到突发情况,政府需要通过只有议会有权审议的议案,获得只有议会有权批准的预算⑥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7条,凡法律须经帝国议会之协赞;根据第64条,国家之岁入岁出须经帝国议会之协赞,每年列入预算。帝国议会拥有“二大特权”,即立法权和预算审议权。([日]伊藤博文:《憲法義解》,宮沢俊義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70、105页。),而议会在此时却无法行使其职能(或适逢闭会,或无法召开时,政府有权通过一种特殊的法律程序,将自己的议案上升为临时法律,或者让自己的预算要求获得暂时批准,事后再请求议会的认可。在这里,所谓的特殊法律程序,即政府首先需要将该议案上禀天皇,请求天皇允许将其付诸枢密院审议后,经过枢密院审议,获得枢密院的批准方可施行。
这意味着,在紧急状态下,政府的议案和预算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枢密院的态度。在这里,枢密院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昭和时期著名宪政史家铃木安藏总结了枢密院在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几大职能:
1.立宪政治体制下,枢密院作为宪法承认的国家机构与责任内阁并存。与此同时,作为最高的辅弼机构,枢密院在政治上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
2.与内阁不同,枢密院在施政中无须负任何责任。
3.虽然以不参与施政为原则,但是付诸枢密院咨询的事项却包罗万象,使得枢密院拥有相较于内阁来说,独立且对等的地位。而且枢密院顾问官的任免不需要受到任何来自议会的掣肘,因此得以强有力地牵制和左右内阁。
4.决定国政事宜方面,比之议会,枢密院拥有更强有力的决定权。
5.皇室的机构。①[日]鈴木安蔵:《太政官制と内閣制》,東京:昭和刊行会1944年版,第214页。
引文中所言枢密院秉持“不参与施政”的基本原则,这是来自于《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第8条中的规定,即“在立法行政方面,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顾问,但是不得参与施政”。②[日]法学講究会编:《大日本帝国憲法·憲法附属法令:学說法令判例一覧》,東京:清水書店1904年版,第83页。但是,正如铃木安藏所言,在国家政治的运行过程中,枢密院虽然表面上“无须负任何责任”,但是它作为宪法中规定的正式国家机关,其实际职能却与上述原则背道而驰。作为天皇的咨询机构,它拥有凌驾于政府、议会之上的超然地位。特别是一旦政府认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决定启用特殊程序通过议案和预算时,枢密院就取代了议会的职能,成为最高的国家意志决定机关,拥有最终决策权。
根据荒木的叙述,1931年12月17日召开枢密院会议,其目的是为审议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预算请求,在此次会议中,最终决定了侵占东北四省的政策。从制度出发,这次枢密院会议开设的合法性即来自《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0条。在这种情况下,枢密院实质上即成为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会议则成为可以证明荒木贞夫叙述的最重要证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被告荒木试图以枢密院紧急会议的国家意志最高决策权作为论证集体责任的制度前提。在他看来,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紧急会议通过了增加军事预算的议案,以此为标志,枢密院确认了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决策。故而,侵占东北四省的政策是内阁和枢密院集体决策的结果。
三、检方的版本——“九一八”事变扩大,荒木贞夫需承担个人责任
根据对荒木叙述的分析,可以发现,他认为内阁和枢密院应该承担集体责任,依据在于犬养内阁会议和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会议。要知道,内阁会议从来不会留下笔录,而枢密院会议的笔录是存在的,东京审判中,检方也有多次使用枢密院会议记录作为文献证据的经历。③检方使用枢密院会议记录作为证据共有21次(同一证据号算一次),证据号分别为:PX479和PX484(1936年11月20日)、PX485(1936年11月25日)、PX491(1939年2月22日)、PX492(1937年11月6日)、PX550(1940年9月10日-26日)、PX551(1940年9月16日)、PX552(1940年9月26日)、PX589(1938年11月22日)、PX649和PX650(1941年7月28日)、PX660(1941年6月16日)、PX687和PX687A(1942年10月12日)、PX787和PX787A(1940年12月18日)、PX909和PX909A(1937年1月20日)、PX911和PX911A(1930年10月1日)、PX1182(1941年11月21日)、PX1266和PX1267(1941年12月10日)、PX1275(1943年8月18日)、PX2205和PX2205A(1930年12月9日)。在追究扩大“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上,检方有没有查阅过这份枢密院会议记录,在检方看来,这份枢密院会议记录是否能够证明荒木贞夫所论证的集体责任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将开始检方版本的分析。
(一)检方对于“九一八”事变扩大问题的叙述
在东京审判庭审中,检方对荒木贞夫在扩大“九一八”事变问题上的侵略战争责任检控是由海德(Elton M.Hyder,Jr)①埃尔顿·M·海德检察官来自美国,于1943年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服役于海军,在一艘位于巴拿马的坦克登陆舰上担任少尉,后因身患疟疾而退役。1944年,他在德克萨斯州能源部担任首席检察官助理。1945年,因美国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Tom Clark)的任命,海德成为东京审判美国检察官团队的助理检察官,是美国检察官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负责的。在国际检察局审讯过程中,他作为审讯官之一,参与了对荒木贞夫的整个审讯。
1946年7月9日的庭审中,他向法庭提交了荒木贞夫讯问笔录的摘要作为证据,起诉他在担任陆军大臣后不久,“很快即决定了平定和占领东北四省”②1946年7月9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第308页。的政策。根据审讯笔录,当审讯官问道,“什么时候你做出决定,认为应该平定和占领张学良治下的4个省?”荒木贞夫正面回答道:“在我成为陆军大臣以后不久。”③1946年2月15日,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478页。在1946年7月9日的庭审中,该部分作为证据PX188A被法庭接受,被检方当庭宣读。据此,检方认为荒木贞夫在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决策中负有首倡责任。
至于荒木贞夫在讯问记录中所提到的内阁会议和枢密院会议问题,却未能引起海德的足够重视。他仅将其解读为:这项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是如何在荒木主导下,经过一系列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首先,“荒木与首相、海相、藏相以及内阁书记官长就他所提出的关于平定和占领这些省份的军费预算进行了商议,在这次预备会议上所有人都表示同意”。④1946年7月9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第310页。进而,“首相向天皇提出预算请求,天皇转而请枢密院讨论并加以认可与通过”。⑤1946年7月9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第311页。
为了证明荒木贞夫是推行此一政策的主谋,海德其实还必须论证一个问题,即内阁和枢密院主观上并无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意图。麦肯锡检察官(Walter I.Mckenzie)替海德弥合了这一逻辑缺失的一个方面,即内阁责任问题。在第二天(7月10日)的庭审中,他引用了1931年12月22日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William Cameron Forbes)致国务院的电文,其中记录了福布斯与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的对话:
犬养向我保证,日本决不会允许这样一种局面出现,也决不会损害中国主权。他重申日本仅仅希望保护日本人民和利益,并且表达了随着秩序的恢复和满洲交通方式的改善,会大大增加中国居民迁入满洲的期待。⑥PX191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致国务院电文(1931/12/22):会见犬养毅、保证不侵害中国的宗主权。参见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第348页。
基于此,检方否认了在以武力侵占东北四省的政治决策中犬养内阁所负有的责任,仅追究荒木贞夫的个人责任。
该电文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或许可以作为间接证据得到认可,事实上最终也被法庭接受为证据PX191。有趣的是,在1946年2月7日的审讯过程中,海德审讯官曾经就同样一封电报讯问过荒木的看法。荒木认为,这份电报内容只能称之为犬养“在访问中的一次声明,而并不能将其称之为一则官方声明”。“外务大臣所说的一切话都不能称之为官方声明,有的时候他必须那样说。”⑦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292页。也就是说,在荒木看来,这份无意损害中国主权的声明不过是犬养外务大臣的外交辞令。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犬养毅对福布斯的保证究竟是外交辞令,还是有感而发,尚且值得有待进一步推敲。不过,这份电报并没有从实质上反驳荒木所言的、内阁军事预算与关东军以武力侵占东北四省这两件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布斯的这封电报恐怕并不能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文献证据。
而且,如上文所言,荒木对犬养内阁和枢密院责任的阐述皆集中在1931年12月17日那次极为关键的枢密院会议上。需要指出的是,在庭审中,检方对此并未给予只字回应。而且,在当年东京审判中,除了荒木的叙述能够证明这次会议的存在,检方也并没有特意去寻找有关这次会议的文献证据。但是,检方还是选择相信它的真实性。在1946年7月10日的庭审中,麦克马纳斯(Lawrence J.Mcmanus)律师①劳伦斯·J·麦克马纳斯,从1946年6月开始担任荒木贞夫的美籍辩护律师。他毕业于曼哈顿学院和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1935年至1949年于纽约曼哈顿担任助理检察官。参见The Tokyo War Trial Digital Collection,http:∥imtfe.law.virginia.edu/contributors-34,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10日。曾经问过检方,“不知道检方手中是否有这次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如果有,是否打算提交法庭作为证据?”海德检察官回答道:“据我所知,检方并没有这次会议的记录。荒木在讯问中曾经提到过,而我们也相信他的陈述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记录在1945年末被销毁了。”②1946年7月9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卷,329页。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检方选择相信荒木的叙述,认为1931年12月17日确实召开过枢密院会议,其中也确实讨论过占领东北四省的军事预算,并同意军部以武力扩大“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叙述印证了被告荒木贞夫的观点,即内阁和枢密院在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军事行动中负有责任,他本人的所为仅是执行政府的政策而已。另一方面,检方在并未给予任何回应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起诉荒木贞夫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承担个人责任。难道检方立证逻辑冲突、前后自相矛盾了吗?
(二)检方对明治宪法体制的制度认知:枢密院会议免责基础上的军部专制
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是出于检方立证的疏忽,引发这个看似逻辑矛盾的处理方式的根源在于海德检察官对明治宪法体制的认知问题上。海德将枢密院会议视为御前会议的一种特殊形式,没有意识到它作为宪法规定的正式国家机构,在紧急状态下可以成为最高国家决策机关。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意识中,潜藏着军部专制的逻辑,据此来解读扩大“九一八”事变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海德对于明治宪法体制的上述两项认知在1946年2月15日的审讯记录中明显体现出来。
在国际检察局荒木贞夫讯问笔录中可以发现,检方对于1931年12月17日枢密院会议的称呼,其翻译前后并不一致。在1946年2月8日的讯问笔录中,该会议被翻译为“the Privy Council”③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302页。1946年2月8日讯问记录的一部分被作为检方证据188C,在庭审中宣读。,即枢密院会议;而在同年2月15日的讯问笔录中,同一次会议又被翻译为“the Imperial Conference”④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479页。,即御前会议。2月15日当天,在继续因这次关键性的枢密院会议接受审讯时,荒木贞夫针对检方将这次会议称作“the Imperial Conference”,还特别做出解释:
问(海德审讯官):将军,在1931年12月17日的御前会议(the Imperial Conference)上,除了内阁和枢密院成员之外,还有其他人参加了吗?
答(荒木贞夫):它不是御前会议(Gozen Kaigi)⑤Gozen Kaigi,为审讯记录中原文标示,对应日文汉字:御前会議。,虽然天皇出席了该会议。它仅是一次枢密院全体会议(Sumitsuin Honkaigi)⑥Sumitsuin Honkaigi,为审讯记录中原文标示,对应日文汉字:枢密院本会議。。所有内阁成员按照等级依次坐在天皇的右手边。枢密院成员按照爵位依次坐在天皇的左手边。在总理大臣背后,内阁局长依次排座,他们分别是陆军省军务局长、海军省军务局长、外务省政务局长等。我不能确定局长们是否全部出席,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可能都在。根据情况,有些次官也会出席会议。一些情况下,会议需要这些年轻人汇报一些特别的问题,如果不需要,他们就不会出席。这取决于特定的情况。
问:两位参谋总长和参谋次长参加这次会议了吗?
答:没有。因为有关军事行动的事项没有在这次会议中予以讨论。
问:将军,你曾经出席过御前会议吗?
答:没有。在我担任内阁成员期间,召开御前会议是罕见的,我怀疑是否在那段时期召开过御前会议。我认为如果有召开过,我会记起来,因为召开御前会议一定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记不清了,但是召开御前会议一定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我不觉得在我担任内阁成员时期,发生过如此重要的事情。在那段时期,倒是召开过军事参议官会议,天皇有出席军事参议官会议。军队组织机构的废立等重要的军事事项的决策是需要天皇同意的。只有经过天皇同意,某个军事机构才可以被裁撤,某个新机构才可以被设立。
问:军事参议官会议可以决定政策吗?
答:只能决定与军事相关的政策。
问: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是否决定过要平定张学良治下的领土?
答:这种事项不是由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的。
问: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答:我觉得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肯定,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决定权。
问:军事参议官会议是否就满洲问题建议过内阁?
答:该会议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只有需要时才召开会议。并没有就平定满洲这种问题召集过会议。①1946年2月15日,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479—480页。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发现,在1946年2月15日的审讯互动中,海德检察官与荒木贞夫的关注点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荒木的叙述一直围绕着枢密院会议与御前会议的差别而展开,而海德则始终着眼于是否有军方人员参与了这次枢密院会议。
1.海德的制度认知:广义御前会议中的枢密院会议
有关枢密院与御前会议区别的讨论,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即荒木说他自己担任陆相期间并没有参加过御前会议,因为当时没有发生过特别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荒木贞夫会这样说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需要额外提及的是,在1947年3月6日东京审判的庭审中,辩方出示了基于东条英机讯问记录的证据DX2348,其中明确说明了御前会议的性质。对比荒木贞夫的言论可以发现,二者对御前会议的理解是一致的。
东条英机解释说,御前会议并不是正式的官方会议,而是日俄战争以来发展出的“一种政治惯例”。它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宪法,而是来源于皇权。只有在面临重大政治决策时,才会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内阁成员和军部首脑组成。“重要的国务大臣会参加御前会议,都有谁参加取决于与所讨论问题的相关程度。有时,还有经过特别授权的军事长官、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而且,御前会议的最终决定在形式上也无法作为正式的官方决定,它“不承担政治责任”。“不过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如参谋总长、内阁大臣、枢密院议长等,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责任,他们并不承担身为御前会议一员的责任。”②1947年3月6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29卷,第543页。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很可能是因为荒木贞夫并没有像东条英机一样,明确指出枢密院会议与御前会议的本质区别,而海德检察官也并没有深入追究过这个问题。尽管从荒木口中了解到了枢密院会议不是御前会议,在庭审的检方陈词时,海德检察官也最终正确地采用了“枢密院会议”的表述;可是,在被提交的庭审证据PX188C和PX188E③2月11日口供被作为证据188C提交,2月13日口供被作为证据188E提交,并当庭宣读。中,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会议仍被翻译为“御前会议”,而身兼审讯官与检察官职能于一身的海德并未特别予以纠正。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庭方同样将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会议称之为“御前会议”。参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4页。也就是说,在庭审过程中,海德检察官一直混用“枢密院会议”与“御前会议”的表述。这意味着,在他看来,“枢密院会议”不过是“御前会议”的一种特殊形式。
这样一来,御前会议就有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上讲,天皇亲临的枢密院会议、大本营会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官方会议都可称之为御前会议。狭义上讲,它是指为类似于开战和终战这样的重大事件而召开的,由天皇、元老、政府和军部成员组成的非官方会议。①参见[日]田村安興:《日米開戦前の御前会議と帷幄上奏に関する書誌的研究》,《高知論叢:社会科学》(107),2013年7月,第1—75页。如果按照这样的区分,很显然在荒木贞夫的审讯过程中,海德检察官时常将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会议称之为“御前会议”,是从广义上去理解;而荒木贞夫则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御前会议”一词。而二者对“御前会议”理解上的差异,在1946年2月15日的审讯中,荒木与海德对此已经沟通过。但是显然这次沟通并不成功,二者对此一问题的认识差异在庭审中依然存在。
海德从广义上理解御前会议的内涵,即意味着在他看来,枢密院会议不过是御前会议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对于并不十分了解日本帝国政治实践的海德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6条规定:“枢密顾问依枢密院官制规定,应天皇之咨询审议重要国务。”②[日]伊藤博文:《憲法義解》,宮沢俊義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90页。与此同时,《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第8条规定:“在立法行政方面,枢密院是天皇的最高顾问,但是不得参与施政。”③在1946年6月13日庭审中,《大日本帝国宪法》被检方提交为证据,作为PX68被法庭接受。《枢密院官制及事务规程》被检方提交为证据,作为PX83被法庭接受。鉴于这些文件都是昭和日本最基本的制度性规范,海德检察官应该了解它们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如果单从法条出发,不考虑实际的政治运营过程,是可以认为,枢密院仅仅是天皇的咨询机构,并没有最高决策权的。尤为重要的是,枢密院会议背后牵扯到皇权。既然国际检察局已然决定不追究天皇的责任,那么很可能在海德看来,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追究枢密院的责任问题了。
2.海德的制度认知:军部专制逻辑中的枢密院会议
在1946年2月15日的审讯中,海德检察官还一直追问荒木贞夫,试图确认军方人员是否参与了1931年12月17日枢密院会议,是否军政部、军令部全体军部人员都参与了枢密院会议的政治决策,是否军事参议官会议与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决策相关。这背后隐藏着检方立证的主要线索,即军部专制的逻辑。
在准备审讯荒木贞夫的过程中,海德审讯官在审讯记录中读到过如下一段话:
格鲁先生评价1932年的形势,指出“军人正在明显地支配着政府,非经他们同意,一步也不能动”。(审讯注意事项:荒木贞夫在这段时间担任陆军大臣)④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第13卷,第275页。
这里的“格鲁先生”即从1932年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十年间、一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C.格鲁(Joseph Clark Grew)。引号中的引言来源于他的日记选集《使日十年》⑤[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蒋相泽译,陈宏志、李健辉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本书的英文原版名称为Ten Years in Japan,日文译名为《滞日十年》。。作为日美关系恶化的见证,《使日十年》以军部的失控为线索,记录了“军部极端分子进行鲁莽的、自取灭亡的侵略”⑥[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蒋相泽译,陈宏志、李健辉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历程。该书1944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日本败迹暴露无疑。正如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邀请完成《菊花与刀》一样,《使日十年》的出版也是意在为美国处理战后局势提供参考。故而,它被国际检察局视为认识昭和历史的最佳书目,⑦在1945年12月10日的国际检察局工作人员会议上,萨盖特(Henry R.Sackett)检察官指出,“要了解他们(日本人)的特点,最佳的方式是阅读《使日十年》。”([日]粟屋憲太郎、豊田雅幸、永井均编:《東京裁判への道——国際検察局·政策決定関係文書》第1卷,第271页。)也成为国际检察局以军部专制为线索认识明治宪法体制的主要认知来源。
具体到扩大满洲事变的侵略战争责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检方能够起诉荒木贞夫负有个人责任,尚需要将军部专制的制度认知落实到犬养内阁的政治实践中。犬养健的证词在这里发挥了关键性作用。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有关犬养内阁政治政策的历史叙述皆是以犬养健的证词为基础。参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54页。作为犬养毅之子,在犬养内阁时期,他曾担任其父的秘书,应该了解整个内阁的政治决策过程。在证词中,他将因五·一五事件遇刺身亡的父亲犬养毅叙述描述成一个致力于中日和平的外交使者②根据后来的历史学研究,犬养毅的政治主张并不是那么单纯。他作为政友会的党首,刚上台即确定了推动所谓“自主外交”路线——基于传统的对外强硬立场,不惜无视国联及各国干涉,采取积极政策解决满洲事变。1932年12月12日,犬养内阁即以马贼猖獗为理由,批准关东军向辽西开进,并将此一责任归咎于张学良。参见[日]绪方贞子:《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李佩译,胡连成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182页。,曾经建议天皇撤兵遭到拒绝、与蒋介石秘密谈判受到军部阻拦、甚至遭受军部支持者内阁书记官长森恪的威胁③参见PX161犬养健宣誓供述书,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3卷,第196—198页。,由此反衬出军部的侵略本质。1932年,面对犬养首相的遇害,格鲁也曾在日记中评论道,“军部简直就像脱缰之马,正在横行无忌,显然是想建立法西斯制度。”④[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蒋相泽译,陈宏志、李健辉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页。由此可见,《使日十年》中的观念与犬养健的叙述不谋而合,将犬养内阁时期侵略政策主张的形成归咎于军部恐怖主义。这恐怕也是犬养健的证词缘何获得检方和法庭完全采信的原因。
沿着军部专制的逻辑,以确认犬养内阁的和平主义倾向为背景,再加上在1946年2月15日审讯中,从荒木贞夫处获悉,1931年12月17日这次关键的枢密院会议仅仅由文官政府(内阁和枢密院)组成,无论是军令部成员,还是军事参议官会议成员,都没有参与到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决策中,海德自然失去了深究这次枢密院会议的理由。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在历史事实认定方面,海德完全相信荒木的叙述,即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紧急会议通过了增加军事预算的议案,以此为标志,枢密院确认了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决策。以这一政策为指导,关东军出兵锦州、哈尔滨,实施了侵占东北的军事行动。第二,在立证逻辑上,与荒木贞夫将枢密院紧急会议视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不同,海德以枢密院免责基础上的军部专制作为对明治宪法体制的制度认知基础。
以被告和检方拥有不同的制度认知为前提,即使在事实认定相同的情况下,海德检察官仍然能够起诉荒木贞夫,认为他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负有个人责任,乃是出于如下理由:第一,依据军部专制的逻辑,检方断定,陆军大臣荒木承认他首倡了以武力侵占东北四省的政治决策。第二,以军部专制的逻辑为认识前提,检方采信了证人犬养健的供词,又找到了福布斯的电报作为文献证据,认为犬养内阁在主观上并不希望分割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第三,有关枢密院的责任问题,一方面,枢密院作为天皇的咨询机构,是御前会议的一种特殊形式,背后隐藏着天皇大权。因不追溯天皇而可以不予追究。另一方面,枢密院不同于大本营会议和大本营联络会议,它与军部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是完全由文官所组成的会议。基于军部专制的逻辑,则完全不需要追究枢密院的责任。鉴于上述逻辑,即使事实上,内阁和枢密院曾经通过决议,同意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军事行动,而且该决议导致关东军侵占东北四省。但是,还是可以推论出,这一结果完全是由荒木为首的军部力量所推动而造成的。
四、辩方的版本——扩大“九一八”事变是陆相服从外交方针的结果
根据对检方版本的分析,不难发现其逻辑严谨下,文献论据的不足。第一,是否能够以福布斯大使的一封电报作为文献证据,犬养健的证词是否可靠,以上述二者来证明犬养内阁无意侵占中国领土,这个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二,在自身的立证逻辑下,检方并没有对1931年12月17日枢密院会议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辩方是否发觉了这个问题?是否利用其作为反证的武器?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将开始对辩方版本的梳理。
(一)辩方对于“九一八”事变扩大问题的叙述
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庭审进入辩方反证部分的个人辩护阶段。荒木贞夫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位接受个人辩护的被告,麦克马纳斯律师是其美方辩护律师。1948年11月12日,荒木贞夫在写给菅原裕①东京审判中,菅原裕是荒木贞夫的本国辩护律师。的信中表达了接受外国律师辩护的无奈,“而来三年的法庭论争中,我需要克服搜集证据、与证人交涉、言语不通、审判形式不同等几多困难,尤其还要克服与美国律师协调不同意见的困难,其中充满妥协等复杂的事情”。②[日]菅原裕:《東京裁判の正体》,東京:国書刊行会2005年版,第275页。由此可见,辩方反证逻辑并不一定与荒木的观点相一致,它的成立是被告与律师妥协的结果。
事实也是如此。有关扩大“九一八”事变的责任问题,虽然根据审讯记录,检方认为荒木贞夫在决定侵占东北的政治决策中负有首倡责任,但是在自辩陈词中,荒木贞夫不承认这一点。他抗辩指出:“在第187号和188号证据中有一断言,意思是我制定了占领东四省的计划。这是不合格译员的翻译引起的错误,与事实全然不同。”③1947年9月10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69页。而且,他坚持认为,这是遵循犬养内阁政策行事的结果。与此同时,麦克马纳斯律师在庭审中,却并没有论证荒木的所为是否遵循了犬养内阁的决策④辩方之所以另辟蹊径,选择辩护策略,与当时个人辩护阶段的庭方定调有关。1947年9月10日,检察官柯明斯-卡尔(Arthur S.Comyns Carr)对荒木贞夫的自辩陈词表示疑虑。他认为,这份陈词中“包含了纠结编造的论点和引文。其中声称,(业已被法庭证实的)许多其他证人的观点和文件尚需进一步证实。故而检方郑重地建议法庭,这种内容不可成为其他(被告)证人撰写自辩陈词的先例”。庭方认同了检方的观点,表态道:“没有受到指控的证人不可以被指控。如果我们允许(被告)指控其中一个(没有受到指控的)证人,那么我们就要容许所有这些事件的存在。我们不会允许任何(身为被告的)证人随意发表自己的论点。”这意味着,在个人辩护阶段,辩方的反证逻辑就不能超越检方立证线索的界限,只能在检方立证的框架内寻找突破口。这作为检控双方在个人辩护阶段的共识,在当天被法庭所确认。参见1947年9月10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60—61页。,反而另辟蹊径,试图论证“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荒木完全遵从外务省当局的决定”。⑤1947年9月16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543页。
在1947年9月16日庭审中,麦克马纳斯辩护律师提交了1932年1月30日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并被法庭接受为证据DX3174。⑥辩方将1932年1月30日的枢密院会议记录作为呈堂证据,实质上是利用了检方没有深入发掘荒木所言的、1931年12月17日枢密院会议记录的检控漏洞。根据现有的枢密院会议记录,1931年12月17日确实召开过枢密院紧急会议,其讨论的主题为《有关纸币与黄金兑换的相关方案》,并非荒木贞夫所言的、审议军费支出的议案。整份会议记录都没有丝毫内容涉及到军费开支的问题。参见《銀行券ノ金貨兌換ニ関スル件》,《枢密院会議筆記》(昭和六年12月17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档案号:A03033725800。事实上,荒木贞夫所言的、那次决定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枢密院会议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它并不发生在1931年12月17日,而是发生在1932年1月30日。这份记录正是在1947年9月16日庭审中、被辩方作为证据提交、并为法庭所接受的证据DX3174,即枢密院议事录(1932/1/30):被告荒木陆相、芳泽外相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答辩。(参见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第41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161页。)笔者查验了国立公文书馆亚细亚史料中心所藏的本次会议的原始资料,与证据DX3174一致。参见《満洲事件ニ関スル経費支弁ノ為公債発行ニ関スル件》,《枢密院会議筆記》(昭和七年1月30日),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档案号:A03033726900。律师不但当庭宣读了其中荒木的发言,而且也宣读了外相方泽谦吉的发言内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荒木在此次会议中表达的论点与他在自辩陈词中所言犬养毅的观点一致,即认为以武力侵占东北四省是内外局势所迫、张学良对日本敌对态度所引发的必然结果。第二,根据芳泽外相的发言,也可以发现,在他看来,在劫匪众多、良民匪化、完全丧失秩序的满洲,日本帝国为了获得和平,使用武力似乎是政府的必然选择。⑦芳泽外相的发言如下:“我确信,我们在满洲行动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和平和安宁,这一直是我们对满洲的基本政策。当然,在那块劫匪横行丛生的土地上维持完美的秩序是很困难的,在那里,即使普通人都会变成劫匪。但是,在我看来,维护那块区域的和平是帝国所绝对必须的。”1947年9月16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546—547页。这份辩方证据显示,无论是被告荒木,还是外相芳泽,他们都表达了要以武力侵占东北四省的企图。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这份证据的文本内容,能够直接证明荒木的行为不过是执行外务省政策的论据,仅在于荒木贞夫评价出兵东北的政策时所指出,陆军省与“外务省的关系非常和谐圆满”。①1947年9月16日庭审,载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第46卷,第546页。
(二)辩方的辩护逻辑: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
辩方仅凭证据文本中的一句话即试图论证外务省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辩护策略乍一看可能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如果联系明治宪法体制下的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其辩护逻辑就一目了然了。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5条②《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5条,国务大臣辅拥天皇而负其责任。凡法律、敕令及有关国务之敕诏,须有国务大臣之副署。([日]伊藤博文:《憲法義解》,宮沢俊義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84页。)规定了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度,根据《宪法义解》,“大臣责任在于以其各自的固有职责辅弼天皇”。③[日]伊藤博文:《憲法義解》,宮沢俊義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40年版,第87页。这意味着只有天皇有权辞退国务大臣,总理大臣无权辞退任何一位国务大臣。该条款赋予了各位国务大臣独立制定其职权范围内政策的可能性,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总理大臣的干涉。④仅从宪法文本的角度出发,认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第55条规定了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这种观点只是对于该条款的一种解释,它源于明治藩阀对政党内阁出现的防范。此种解释至今仍然存在争论。其争论点参见[日]坂野润治:《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第3章,崔世广、王俊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不过从内阁制度中有关总理大臣权限的规定出发,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宪法第55条所规定的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1885年的内阁官制学习的是德国的“大宰相主义”,而1890年明治内阁官制改革,参照的则是英国的内阁制度。自此之后,内阁制度“极大限制了从前内阁总理大臣的各省统制权,所谓的首相的地位堕落到仅止于内阁议长的位置”。([日]山崎丹照:《内閣制度の研究》,東京:高山書院1942年版,第114页。)“一言以蔽之,内阁制度改革的本质,可以认为是导入了‘主任大臣副署主义’,否定或者说缓和了‘大宰相主义’。”([日]永井和:《近代日本の軍部と政治》,東京:思文閣1993年版,第37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欲追究扩大“九一八”事变的个人责任,则首先需要明确,哪位国务大臣负责该事件的处理。
上述问题的解决涉及“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第二次若槻礼次郎内阁对该事件性质的认定。在我们今天看来,“九一八”事变是约定俗成的称呼,可是,在这起冲突发生的当下,这样一个称呼却是内阁通过商议决定的。它代表了政府对于这一冲突性质的认定。1931年9月21日,第二次若槻内阁通过阁议,决定“将9月18日夜,因中国士兵爆破满铁而引发的事件称之为事变”。⑤[日]《海軍制度沿革》第17卷,東京:海軍大臣官房1944年版,第588页。这份阁议被下发给关东军各部,同年9月23日陆满普第4号电文即写道:“此次时局被视为事变,特别将其称之为“九一八”事变。适用于事变发生相关的规定,特此公示。”⑥《今回の時局を事変と看做す件》,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档案号:C01002650400。这意味着内阁将这起事件定性为非常态的冲突和骚乱,但并非战时状态。基于此,对“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方式即适用于平时的政策,而不启用战时的规定。由于“九一八”事变被定性为适用于平时政策的冲突,且而该事件发生在境外,根据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制,理论上它应被视为外交事件,由外务省负责解决,由其他省配合外务省进行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外相对于满洲局势的判断就成为是否需要以武力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决定性因素。
正是基于以上的制度逻辑,辩方才能够得出结论,荒木对于东北四省所进行的一切行为,不过是执行犬养内阁中、专门负责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外务省所制定的政策决定,从而起到为被告辩护的目的。
五、结 论
根据东京审判的文献资料,在追究荒木贞夫是否在扩大“九一八”事变中负有侵略战争责任时,检方、被告本人和辩方形成了三种不同版本的叙述。三方分别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的侵略战争责任归属。通过对三个版本的分析,可以发现,三方的不同叙述并非建基于对历史事实认定的基础上,即三方皆没有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献证据,有关这个问题的个人责任追究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证人证词。被告荒木叙述中所提到的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紧急会议并非如他所声称的内容。检方提出的福布斯电报,是否可以证明犬养内阁确实无意侵占中国领土,其效力值得怀疑。而辩方所提出的1932年1月30日枢密院会议记录,其中恰恰含有被告荒木贞夫有意以武力侵占东北四省的内容。
为了弥补证据证明效力的不足,三方各自以明治宪法体制的不同面相作为逻辑前提进行立论,进而得出了有关侵占东北四省责任归属的不同结论。
被告荒木试图将枢密院紧急会议的国家意志最高决策权作为论证集体责任的前提。在他看来,1931年12月17日的枢密院紧急会议通过了增加军事预算的议案。以此为标志,枢密院确认了扩大“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决策。故而,侵占东北四省的政策是内阁和枢密院集体决策的结果。
检方海德检察官的立论逻辑着眼于枢密院免责基础上的军部专制。第一,在他看来,枢密院会议首先是天皇的咨询机构,其责任不在东京审判的起诉范围之内;其次它由文官组成,与军部毫无关联,更加无须追究。第二,依据军部专制的逻辑,他采信了犬养健的证词,并认同福布斯电报的内容,认为犬养内阁对中国领土并无侵占意图。以上述两项为前提,他得出结论,侵占东北四省的首倡者是荒木本人,内阁和枢密院只是迫于军部的压力,认同了他的主张。故而在扩大“九一八”事变的问题上追究荒木的个人责任。
辩方的立证脉络建立在国务大臣单独辅弼原则的基础上。以此为前提,麦克马纳斯律师依据内阁对“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判定,将其视为外交事件,将外务省视为负责解决此次事变的机构,试图将芳泽外相对满洲局势的判断作为荒木在侵占东北四省过程中的行动依据。据此,他论证外务省主导了“九一八”事变的解决过程,荒木在“九一八”事变扩大中的言行完全是遵照外务省的外交方针。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状况,第一,源于追究“反和平罪”的司法实践需要。从法理上来说,可以认为“反和平罪”的逻辑结构由两部分构成,“即战争违法观与领导责任观”。①姜津津、季卫东、程兆奇:《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光明日报》,2014年9月1日,第16版。这意味着,判定个人是否犯有“反和平罪”,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要从法律上确认侵犯主权国家已构成犯罪,但并不能由此就自然而然地推定卷入的那些领导人构成了犯罪;因此还必须佐之以证,确认被告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这也是惩治罪犯的关键所在。”②朱文奇:《东京审判与追究侵略之罪责》,《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第9页。这意味着,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要追究“反和平罪”的个人刑事责任,则需要遵循两个步骤:首先确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然后才能追究其中的个人领导责任。其中,国家制度则成为由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过渡的必要桥梁。
第二,源于东京审判司法实践中的客观无奈。国际检察局草创之际,即意识到这次庭审所面临的困难,即文献证据的严重不足。这是由德日两国占领政策的差异所导致的。正如1946年1月4日,检察官季南在《与美国陆军部长交谈的备忘录》中写道:
据我所知,纽伦堡法庭很大程度上依靠文献证据来进行审判,在这些审判我们不能期望有这样的条件……欧洲崩溃,实质上允许我们得到广泛的犯罪证据。在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占领日本主要岛屿之前许多天就已经传播开,为有效隐藏或者毁灭这些文献证据提供了足够的机会。③[日]粟屋憲太郎、豊田雅幸、永井均编:《東京裁判への道——国際検察局·政策決定関係文書》第1卷,第53—54页。
为弥补证据文献的缺失,国际检察局尝试了很多方法。例如,之所以在起诉内容中追加“刑事不作为”的法理,即是因为“国际检察局无法确保拥有足够的证据文献来根据直接责任的法理立证被告们的个人责任”。①[日]户谷由麻:《東京裁判——第二次大戦後の法と正義の追求》,東京:みすず書房2008年版,第159页。而以制度逻辑为立证前提,对被告进行起诉也是弥补文献证据不足的一种方法。以制度逻辑进行立论,有助于检方将证人证词和文献证据组织起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完成起诉的工作。
第三,源于明治宪法体制本身的复杂性。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由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明治藩阀订立的。他们在起草该宪法时即怀有一定的自保心态,“一方面,藩阀希望宪法作为共通的规范得到有效的利用,得以根据宪法的规定实现分权,得以令政府在运用和解释宪法时不至于陷入独断恣意当中;另一方面,鉴于藩阀指导者们自维新以来即担负着构筑近代日本国家的责任,其身上还残留着希望将自身置于法令、制度之外的风气,他们希望以维持自身政权的方式来实现日本持续的独立和近代化路线,并对此拥有欲望和使命感”。②[日]佐佐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東京:吉川弘文馆1996年版,第1页。这导致明治宪法自成立之日起,即充满争议,一直摇摆于君权与民权之间,引发“天皇主权说”和“天皇机关说”之间的学术论争。从这种意义上讲,明治宪法体制本身具有诸多面相。它不但可以为检方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提供制度依据,也有可能为辩方所利用,使其可以针对检方对明治宪法体制的个别认识缺陷,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甚至,被告也有可能凭借自身对明治宪法体制的谙熟,想方设法为自己减轻罪责。
鉴于认定“反和平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需要、东京审判客观上文献证据的不足,再加上明治宪法本身的复杂性,在追究扩大“九一八”事变的侵略战争责任时,才会出现检方、被告本人和辩方三方分别从明治宪法体制的不同逻辑出发进行立证,确认侵略战争责任归属的现象。
它提醒我们,在东京审判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检方在审判中犯了这样那样的事实性错误。东京审判是在历史情景中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既包括历史当事者对历史事实的掌握程度,也涉及到他们对日本政治制度的认识。回过头来,我们今天想要重新介入这段历史,理解东京审判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番面目,审判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东京审判司法实践在案情纷繁驳杂背后所蕴含的理性逻辑,这样诸如此类的问题,制度逻辑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媒介。
本文写作承蒙程兆奇老师的悉心指导;承蒙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各位学友对文章初稿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在2016年5月3日“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青年学者研讨会”上,承蒙吴景平老师的细致点评;承蒙匿名评审专家的指点,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李晶晶]
K265
A
1000-5072(2016)08-0027-14
2016-05-31
邹皓丹(1982—),女,辽宁大连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中日关系史、东京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