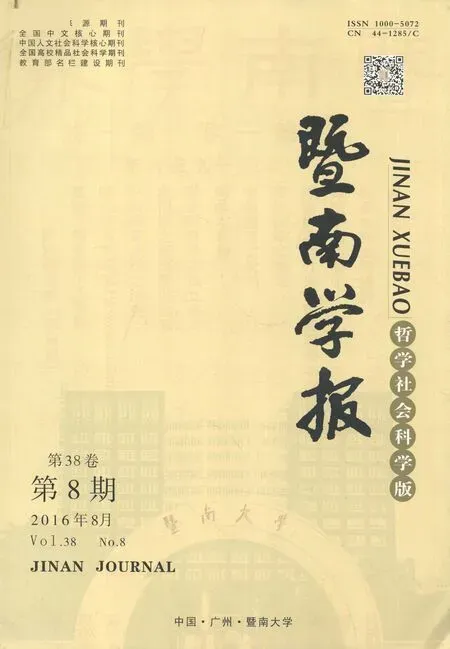《邵氏闻见录》与南宋初年政治——以其中有关王安石的记叙为讨论中心
叶 菁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邵氏闻见录》与南宋初年政治——以其中有关王安石的记叙为讨论中心
叶 菁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邵氏闻见录》是邵伯温在南宋初年创作的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载了北宋士人的对话与交游。本文以《邵氏闻见录》中记载的《辨奸论》所引发的一桩公案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邵氏闻见录》是如何反应南宋初年的政治状态,进而从中探讨政治与文学的生态关系。全文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其一,研究《邵氏闻见录》对于王安石的多角度批判,以达到全方位攻击王安石的目的;其二,研究《辨奸论》一文是《邵氏闻见录》批判王安石的核心依据;其三,受政治影响的《邵氏闻见录》写作手法的转变,对于王安石及新法的描写往往采用歪曲事实、伪造事实和曲意理解、引申发挥等写作手法。通过分析南宋初年批判王安石的主流政治背景和洛学的兴起,来探究《邵氏闻见录》是如何多角度地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从而达到与主流政治思想保持一致的目的。
《邵氏闻见录》;邵伯温;王安石;政治;洛学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包括诗、词、小说、话本在内的各种文体形式均得到蓬勃发展,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7页。而笔记小说的发展尤应引起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宋代笔记小说至少有五百多部,其中大多数保留至今。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前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数量如此之多的笔记小说绝大多数出自宋代士大夫之手,多为案边随笔记载,内容主要包括当时的政治、史实、名人轶事等。文学离不开现实的创作背景,笔记小说的创作也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本文拟以南宋初年的一部笔记小说——《邵氏闻见录》为中心,从一个侧面来考察现实政治是如何影响文学创作的,以及在政治的影响下,文学特别是宋代文人笔记,是如何依据政治走向来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从而代表了宋代笔记小说的一种创作类型。
导言:由《辨奸论》引发的一桩公案
《辨奸论》为宋人攻击王安石的一篇文章,指斥王安石为致使北宋亡国之祸的奸邪,有“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③(宋)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以下所引版本相同。之语。《辨奸论》原文在《邵氏闻见录》中被首次提及,并称其著者为苏洵,为批判王安石之作。自宋至明代,《辨奸论》的作者一直被认为是苏洵。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江西人李绂在《书〈辨奸论〉后二则》一文中,开始对《辨奸论》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认为此文为赝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围绕《辨奸论》的真伪及作者问题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讨论,按照对于《辨奸论》的作者是否为苏洵可以分为两派,即“肯定说”和“伪作说”。如邓广铭先生持“伪作说”认为:“炮制了一部《闻见录》的邵伯温,也就是假冒苏洵之名儿写《辨奸论》的那个人。”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3页。此书系邓广铭先生所著《王安石》的修改本。到目前为止,有关《辨奸论》真伪及作者问题的讨论尚未结束,已然成为了学术界的一桩公案。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有“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②方勇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9页。孟子倡导的知人论世的文学评论方法,抓住了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生活的反映的基本特征,主张只有了解作者的时代,才能知其人,进而正确评价其作品。最先也最全面录入《辨奸论》的《邵氏闻见录》是南宋邵伯温创作的一部笔记小说。邵伯温为理学家邵雍之子,受到其父影响,早年出入富弼、司马光等名臣之门。《邵氏闻见录》创作于南宋初年,书中记载了大量前贤的对话,如与邵氏父子关系密切的司马光、程颢、程颐、吕公著、富弼、文彦博等。其中,对于北宋时期新旧党争论述很多,尤其是对于王安石及新法的论述十分详细,且多引前贤议论及当时评价,自发感慨是《邵氏闻见录》一书所议论的主要论题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史学家的重视。然而,《邵氏闻见录》中对于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论述有很多偏颇之处,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其中对于王安石新法的批判是与南宋初年贬低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其书亦受到南宋初年学术斗争的影响,进而改变了文学创作的正常轨迹。
一、《邵氏闻见录》对于王安石的多角度批判
《邵氏闻见录》成书于绍兴二年(1132),此时高宗回到临安(今浙江杭州),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在政治上,宋高宗为笼络人心,而打击徽宗、蔡京政治集团,以撇清自己与北宋亡国之祸的关系,笼络人心。对于王安石多角度的批驳在高宗朝愈演愈烈,胡寅在建炎三年奉旨撰《追废王安石配飨诏》,在这封诏书里,已经明确把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变法认定为“实慕非、鞅,以聚敛为仁术,以法律为德政,排摈故老,汲引憸人,变乱旧章,戕毁根本”;把其在学术上的创立认定为“祸乱相踵,率兽食人,三纲五常,寖以堙灭”。③(宋)胡寅著,尹文汉点校:《斐然集·崇正辨》,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86页。这种对历史全盘翻案的做法得到了宋高宗的认可,他在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时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商鞅、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④(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73页。继而彻底否定了王安石的作为。从学术上而言,随着对新法的批判,士大夫们也逐渐开始攻击王安石的学术。士大夫中反对王安石最积极的当属邵伯温的门生——尚书右仆射赵鼎,他在《论时政得失》中说:
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自余童贯、王黼辈,何曾足道。今贯、黼已诛,而安石未贬,犹得配享庙庭,蔡京未族,而子孙饱食安坐。臣谓时政阙失,无大于此。⑤(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7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12页。
赵鼎彻底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并由于其是邵伯温的学生,在学术上属于洛学一派,因此,赵鼎的言论对南宋初年洛学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南宋初年这种学术氛围之下,王学衰退,洛学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因此,当时的政治舆论是偏向于认为王安石致亡国之罪,在加上洛学学者需要打击王氏新学以抬高洛学的学术地位,作为洛学著名学者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打击王安石其人及其新法的中坚分子。在《邵氏闻见录》中,有多段记载论及王安石,这些论述只有一个共同目的——论证王安石是导致北宋亡国之祸的主谋。
《邵氏闻见录》成书之时,朝野上下已经形成了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之势。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也多有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从政治、学术乃至私人生活等方面对王安石进行了批判。这些记载,有的不尽真实,李绂《穆堂初稿》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已作了一些辨析①李绂在《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中认为:“唐人好为小说,宋元益盛。钱氏之私志,魏泰之笔录,圣主贤臣动道污藏,至《碧云碬》《焚椒录》而悖乱极矣。其若可信者,无过《邵氏闻见录》,由今观之,其游谈无根,诬枉而失实,与钱魏诸人固无异也。”见于《穆堂初稿》卷四十五,《清代诗文集汇编》232—2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9页。,更有近代及今人学者称《邵氏闻见录》为一部“谤书”。②如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认为《邵氏闻见录》“不屑辨,不屑述也。”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邵氏闻见录》对于王安石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论新法之失。
《邵氏闻见录》中多有论及王安石新法之失,如论太皇太后向宋神宗诉新法使民间疾苦,“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卷三);论其兴兵,“元丰变法之后,重以大兵大狱,天灾数见,盗贼纷起,民不聊生。”(卷十一),“今乘舆播越,中原之地尽失,天下之人死于兵者十之八九,悲夫!一王安石劝人主用兵,章惇、蔡京、王黼祖其说,祸至于此。”(卷五)等等,对于新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其二,贤者不用,任用小人。
邵伯温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王安石不用贤者,而任用小人,继而对王安石提拔上来的吕惠卿、章惇等人,也有批判之意,如论吕惠卿时说:“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卷十二),并用司马光的上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今观安石引汲亲党,盘踞要津,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吕诲远矣!”(卷十一)然而此上章不见于司马温公集,今仅见于清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六③(清)顾栋高著,刘光胜点校:《司马温公年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闻见录》卷十一据此夹杂大段议论,不知是否为司马光原文,或为伯温自作,存疑之。
其三,论及王安石私德不佳:性格执拗,奸诈,喜怒无常,强词夺理等。
除了在政治上批判王安石之外,《邵氏闻见录》还多次从王安石私德处下笔,批判其性格执拗,奸诈,喜怒无常,强词夺理等等,有八条之多。如论及王安石的奸诈,记载了一则王安石误食钓饵之事,并引用宋仁宗的话加以批判:“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卷二)论及王安石性格执拗,则援引了司马光所说王安石不饮包拯酒的故事一则,司马光认为“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卷十)。然而其中最典型的是论及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恶事件,并批判王安石气量狭小,喜怒无常: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洗。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故荆公《熙宁日录》中短魏公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尔。”作《画虎图》诗抵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罢新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条例司疏驳,颁天下。又诬吕申公有言藩镇大臣将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自草申公谪词,昭著其事,因以摇魏公。赖神宗之明,眷礼魏公,终始不替。魏公薨,帝震悼,亲制墓碑,恩意甚厚。荆公有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犹不忘魏公少年之语也。(卷九)
此则因论及王安石与韩琦交恶的过程,使王安石的私德最为人所诟病,认为其气量狭小、喜怒无常。
其四,在《邵氏闻见录》中,除了大量论及王安石之外,邵伯温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王安石之子王雱。比较著名的是卷十一中关于王雱性格险恶的一则记载:
一日盛暑,荆公与伯淳对语,雱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以出,问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数为人沮,与程君议。”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则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儿误矣。”伯淳正色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故退。”雱不乐去。伯淳自此与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雱为从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罢相,哀悼不忘,有“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之诗,盖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①(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1页。
文中称王雱推行新法,意欲“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这一条记载并不符合史实。然而就是这条不合情理的记载,被《宋史》编纂者所采用,收录在《宋史·王雱传》中,遂成为王雱受人诟病的依据,可见《邵氏闻见录》在当时影响之深。
二、“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邵氏闻见录》批判王安石的核心依据
《邵氏闻见录》从多角度批判王安石,有一个核心的依据,那就是邵伯温认为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和宋高宗朝主流的社会舆论一样,邵伯温也导致北宋靖康之难的全部罪责推在了王安石的身上,并在《邵氏闻见录》中引用苏洵写的所谓的《辨奸论》来阐发。其实,《邵氏闻见录》中所引的苏洵《辨奸论》中的思想,很大一部分源于吕诲在熙宁年间上章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监;一言近诬,万死无避。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②(宋)吕祖谦编著、齐治平点校:《宋文鑑》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64—766页。吕诲这篇奏疏论述了王安石十大罪状,全文洋洋洒洒,认为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好比唐代卢杞之奸邪,最后得出一个预测性的结论:“误天下苍生,必斯人矣”。在熙宁年间的政坛上,吕诲连上三次奏疏,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预测性的结论。但是,吕诲的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发挥作用,吕诲本人反而被贬官下野。不仅宋神宗没有采纳吕诲的意见,当朝士大夫也不认同吕诲的看法。如司马光曾说:“窃见介甫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矣,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③(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与王介甫书·第一书》,《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550页。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大多数都认为王安石可致太平,这正与吕诲认为王安石可致亡国的观点相对立,因而我们可以推测,吕诲的言论在当时并不是主流社会舆论,也不会对政治格局造成影响。
但是,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却叙述了吕诲有关王安石可致亡国的观点,并进行多角度的阐发,这当然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与学术环境的影响。在《邵氏闻见录》中,有多段记载论及王安石,这些论述只有一个共同目的——论证王安石是导致北宋亡国之祸的主谋。《邵氏闻见录》中有多处批判王安石导致亡国之祸的论述:
上即位于宋,迁淮扬,虏逼,上渡江,甚危,兵民溺水死驱执者不可胜数。今乘舆播越,中原之地尽失,天下之人死于兵者十之八九,悲夫!一王安石劝人主用兵,章惇、蔡京、王黼祖其说,祸至于此。(卷五)
至熙宁初,王荆公为相,寝食不暇,置条例司,潜论天下利害,贤不肖杂用,贤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独留,尽变更祖宗法度,天下纷然,以致今日之乱。(卷六)
邵伯温不仅直言王安石导致亡国之祸,更用南人不能为相的说法,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上的依据:
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人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呜呼!以艺祖之明,其前知也。(卷一)
宋太祖是否真有“不用南人作相”的禁令,待考。但是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朝,则分别有两位南人作过宰相——王钦若和晏殊,也没有使宋朝遭遇亡国之祸。此种说法不过是为了批判王安石而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以上《邵氏闻见录》中种种论及王安石亡国之祸的观点,不一而足,其中,批驳的最直接最锋芒毕露的无过于那篇著作权尚存争议的《辨奸论》。在《辨奸论》中,猛烈地批判了王安石的亡国之罪,比之吕诲的奏疏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挚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请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儿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
《辨奸论》不仅批判王安石在政治上“收召好名之士”,“阴贼险狠”;更批判王安石在生活上“不近人情”,乃至于“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种批判为旁人所质疑,南宋朱熹就认为《辨奸论》中的批判不合情理:“老苏辨奸,初间只是私意如此,后来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说。然荆公习气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喫物不知饥饱。辨奸以此等为奸,恐不然也”。①朱杰人主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0—4051页。朱熹认为,《辨奸论》只是抒发了苏洵个人对王安石的不满,况且王安石是一个不注重个人生活小节的人,人所共知,《辨奸论》多从他人私处入手,恐不尽然。无论《辨奸论》的作者是谁,《邵氏闻见录》全文引用《辨奸论》,可以看出《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也认同《辨奸论》的思想观点,多从王安石私德入手进行批判,谓其奸诈、气量狭小、喜怒无常、不近人情,以达到全方位攻击王安石的目的。
三、受政治影响的《邵氏闻见录》写作手法的转变
宋代笔记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以记录当朝史实为主,兼记名人轶事、历史考据、诗话、琐闻等,内容丰富而繁杂。正因为一部笔记小说中往往兼有笔记、小说、故事、诗话、考据、历史琐闻等众多内容,笔者以为,宋代笔记同时兼有笔记和小说两种文体的性质。①关于“笔记小说”的概念和所辖范围,学术界尚未有一致的界定。例如刘叶秋认为历代笔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第三是考据辩证类的笔记。但同时指出,这样分作三大类,仍难周密。因为笔记一体,历来以“杂”见称,一书之中,往往见有各类。(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目前学术界对于“笔记小说”的概念尚未有一个明确且公认的界定范围,这也是由于笔记小说内容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正在陆续出版中的《全宋笔记》拟收录近五百部宋代笔记及笔记小说,定书名为“笔记”,采用较为宽泛的说法。宋代笔记小说往往同时兼有笔记和小说两种文体的性质,这是因为宋代笔记小说中笔记与小说的分界并不明显,一部笔记小说中往往兼有笔记、小说、故事、诗话、考据、历史琐闻等众多内容。笔者在整理宋代笔记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宋代笔记是否能称之为小说加以区分,即笔记中小说故事所占比例较多、文学色彩较浓的才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从而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相对于史书而言,笔记小说能较生动、具体、全方位地描述党争情况,这一点为正统的史书所不及,应予以重视。
但是,有些宋代笔记小说在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偏离了记录史实秉笔直书的写作手法,特别是涉及到北宋新旧党争的问题时,有些受到打击新党的主流政治思想的影响,小说故事往往以打击新党为目的的小说故事,以便与当时的主流政治思想保持一致的目的。宋代笔记小说和政治的联系十分紧密,这是因为:其一,宋代笔记小说的作者,多为党派中人,如苏轼、苏辙、范镇、孔平仲等,自身的政治党派意识会或多或少左右他们的文学创作,在笔记中多攻击敌党人士,以笔记小说作为他们议论时政的宣泄口;其二,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笔记小说在政治舆论的导向下偏离了正常的创作轨道,如本文论述的在南宋高宗批判王安石新法的政治舆论下,包括《邵氏闻见录》《铁围山丛谈》等笔记小说对王安石群而攻之,成为宣扬政治舆论的帮手。就《邵氏闻见录》而言,受到南宋初年批判王安石及新党的主流政治思想的影响,这部笔记小说中包含了以《辨奸论》为代表的多处批判王安石的小说故事,主要采用歪曲事实、伪造事实和曲意理解、引申发挥等三类写作手法。
走在故乡的土地上,听友人讲黄骅特别是黄骅农村这些年的变化。湛蓝的天空、色彩缤纷的田野,映衬着那些甜甜的枣儿,只要细心,一草一木都可以看出历史的痕迹。我用凌乱的脚步在家乡捡拾起那些破碎的历史,就像在时空隧道穿行,一会儿明、一会儿暗,让整个身心都如此清澈,清凉。
邵伯温为了突出王安石私德的缺陷,不惜在《邵氏闻见录》中歪曲历史事实,以造成读者的误解。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邵氏闻见录》中王安石与韩琦交恶一事,真实的情况是否如《邵氏闻见录》中所说的一样呢?王安石确实作有《韩忠献挽词》二首,其词曰:
心期自与众人殊,骨相知非浅丈夫。独斡斗杓习亭座,亲扶日毂上天衢。锄稷万里山另竖,衮绣三朝国有儒。爽气忽随秋露尽,谩凭陈迹在龟趺。
两朝身与国安危,典策哀荣此一时。木稼曾闻达苣白,山颓果见哲人萎。英姿爽气归图
纵观此词二首,充满了对韩琦的赞扬之情,赞扬其在政治上系国家安危于一身,“独斡斗杓习亭座,亲扶日毂上天衢。锄稷万里山另竖,衮绣三朝国有儒”,“两朝身与国安危,典策哀荣此一时”;赞扬其在个人风度上英姿飒爽,风度翩翩,“英姿爽气归图画,茂德元勋珀毳彝”。末句“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是王安石有感而发,追忆自己年轻时曾在韩琦幕府,表达了对韩琦的缅怀之情,看不出有含怨影射之语。《邵氏闻见录》则专论荆公诗末句,歪曲地认为这是王安石对韩琦含怨之作,未免断章取义,引导读者误解原意。
《邵氏闻见录》中与之类似的采用引申发挥等写作手法描写王安石的小说还有一例:
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始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
这段记载描述了苏轼由黄州过金陵时,王益柔守江宁,苏轼与之同游蒋山,因得以拜谒王安石并与之谈话的过程。但是文中对于王安石的表情神态刻画十分细致,仿佛小说作者身临其境,正如蔡上翔所说:“其语言状貌,如‘介甫色动’,‘介甫色定’,‘介甫举手两指’,‘介甫厉声’,殆如村庸搬演杂剧,净丑登场,丑态毕出。”①(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2页。苏轼确实在金陵谒见过王安石,但相与谈论如何,则无他人可知,《邵氏闻见录》中不仅有记载,且精于细节,如蔡氏考辩所云所记王安石神色多变,则纯如小说家言,可见邵伯温在小说中采用了引申发挥的写作手法。又如《邵氏闻见录》中谈到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关系时说:“王荆公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卷十二)邵伯温认为王安石写“福建子”三个字,就是悔恨于吕惠卿。然而“福建子”三个字,并不一定就是指吕惠卿。与王安石同时代的有不少福建人,如曾公亮、陈升之、吴充、章惇等,甚至连王安石的两个女婿蔡卞和吴安持也是福建人。可见“福建子”三个字并不能确指某个人。其次,王安石并没有对“福建子”寓于褒贬,所谓王安石“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是《邵氏闻见录》一书采用引申发挥手法的体现,只是邵伯温自己的猜测而已。
至于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采用虚构的写作手法伪造事实之处也有不少,前文所述王雱为推行新法意欲“枭韩琦、富弼之头于市”即是典型的伪造事实。清人李绂称:“由今观之,其游谈无根,诬枉而失实,与钱、魏诸人固无以异也。邵氏所录最骇人听闻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②(清)李绂撰:《穆堂初稿》,纪宝成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89—590页。其实,文中所述王安石、王雱与程颢会面的时间、节气等都与史书不合,是典型的伪造事实。文中其后写到王安石在钟山时,恍惚看见王雱荷铁枷杻如重囚者,则纯属鬼魅之妄说,尤不足辨。然而就是这些伪造、虚构事实的记载,被《宋史》编纂者所采用,收录在《宋史·王雱传》中,遂成为王雱受人诟病的依据,可见这些笔记小说在当时影响之广。
余 论
文学离不开现实的创作背景,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换句话说,“从文学反映论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③沈松勤:《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页。《邵氏闻见录》虽然是一部文人笔记小说,也离不开其创作的时代背景,而与当时政治紧密相连,对王安石全方位的批判与主流舆论保持一致。宋代笔记小说数量很多,内容繁杂,很难做出定量分析,但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可以作为文学与政治生态的一个侧面考察,从中探讨笔记小说思想内容和写作手法的转变。
除了《邵氏闻见录》之外,在南宋高宗时期,也有几部笔记集中批判王安石,体现了政治影响文学生态。《铁围山丛谈》为蔡京之子蔡絛于靖康元年以后流放白山时所作的一部笔记小说,蔡絛在此书中,对于北伐之繇和靖康之祸,皆推诿他人,为蔡京文饰。因此,蔡絛在《丛谈》中于三苏尤极意推崇,深诋王安石新法,甚至丑诋王安石为野狐、貛等,认为王安石是天上的野狐下凡,所以不得有后代。④(宋)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页。《铁围山丛谈》中这种为了替蔡京文饰而丑诋王安石的做法,与当时蔡京失势的政治格局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直接影响了士人对于王安石的正确评价。南宋以后,随着王安石及其新学的失势,士人对其评价有所回落,因此,其间出现的笔记小说中时有讽刺、揶揄之语,如岳珂《桯史》中有关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的一则故事,描述了庙庭之中孔子正坐、颜孟与王安石侍侧,然而孟子和颜子都公推王安石居上,甚至连孔子都不能安席,为王安石避位。①(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0页。笔记小说中出现这种虚构的故事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的。岳珂乃岳飞之孙,生于宋孝宗淳熙十年,主要生活在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在此期间,王安石已被罢黜了配享孔子庙庭,新学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不再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官方文本。因此,岳珂可以在《桯史》中编造故事,以讽刺王安石及其新学,这也是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南宋初年从政治和学术上批判王安石的社会风潮的影响下,文人的笔记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因为政治的导向而改变了创作的初衷。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对王安石的形象多有所歪曲,目的是为了说明王安石是导致靖康之乱的罪魁祸首,从而贬低新学,抬高洛学,并与当时政治主流保持一致。除了《邵氏闻见录》之外,尚有《铁围山丛谈》《桯史》等笔记小说,也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对王安石进行了歪曲的描述。以上这些笔记小说都可视作政治环境影响文学生态的具体表现,代表了宋代笔记小说的一种创作类型,应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I207.41
A
1000-5072(2016)08-0019-08
2016-06-27
叶 菁(1985—),女,浙江宁波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