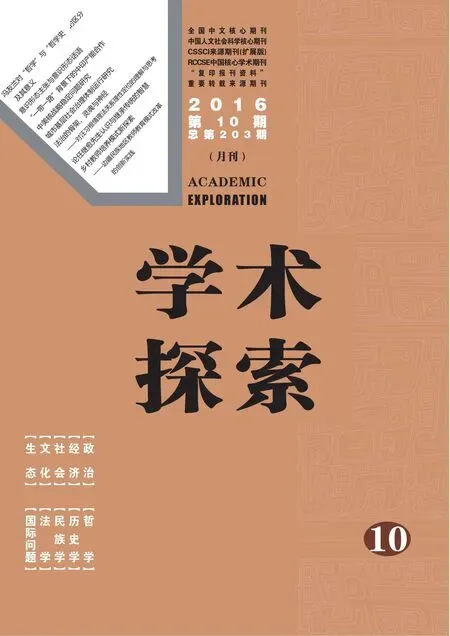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面临的困境及治理路径
黄绍文,黄涵琪
(红河学院 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云南 蒙自 661100)
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面临的困境及治理路径
黄绍文,黄涵琪
(红河学院 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云南 蒙自 661100)
哈尼梯田具有“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景观组合特征,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21世纪以来,哈尼梯田却面临着一些困境,主要表现在:生态系统的变化,导致涵养水源功能下降;在开发利用遗产区资源中出现梯田景观被毁坏的情况;杂交稻的“绿色革命”导致多样性传统水稻品种流失;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导致梯田面积萎缩;传统观念改变导致文化传承断代及民居传统文化元素缺失等。面对这些困境,我们应树立以下治理观念:一方面要坚持梯田自然生态环境改变最小的原则,尽量不去改变梯田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以法制建设为保障,以文化自觉促使哈尼梯田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统一,并且传承下去,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困境问题;治理路径
历经了13年的申遗,2013年6月22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以元阳县为代表的哈尼梯田核心区,以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对于哈尼梯田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保护的终结,恰恰是挑战的开始。作为本乡本土的社科工作者,我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带着深厚的感情、强烈的忧患意识来研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面临的困境和治理路径的。
一、哈尼梯田在全球梯田中的影响
梯田在全球分布广泛,作为一种沿等高线构建的阶梯式农地利用方式,它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南方的丘陵地带,在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南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小巽他群岛、印度的阿萨姆山地也有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群落,其中以种植水稻的梯田为大多数。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南方或者印度半岛上有一支移民队伍南渡重洋,在吕宋岛登陆,之后进入了山区,逐渐形成了如今的菲律宾伊富高梯田文化。剩余的移民则继续南下到了爪哇岛和小巽他群岛繁衍生息。从梯田的分布现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梯田在世界上主要存在于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中国的梯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山岭地区,其中以云南、广西居多。位于滇南红河州南部山区的哈尼梯田,是哈尼族人民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岭雕刻。广西龙胜的龙脊梯田、湖南新化的紫鹊界梯田、浙江云和的梅源梯田、贵州丹寨的高要梯田等也颇为独特。在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的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一个“环太平洋梯田文化圈”。[1](P7~9)
整个环太平洋的梯田姿态各异,各有特点。其中,菲律宾科迪勒拉山区高山水稻梯田奇观,以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造灌溉系统最先被列入梯田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它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伊富高祖先完全凭借肩扛手扶在海拔1500多米的山间雕刻出的大规模的高山梯田。然而,这一神奇的文化景观由于环境的恶化和人为的忽视,以及伊富高年轻人价值观的改变,也正逐渐遭受“灭顶之灾”。目前一半左右的梯田已经不复存在。伊富高省省长巴格雷特悲观地认为,这一世界奇迹将在未来的15年内彻底消失。[1](P17)
哈尼族的梯田分布在滇南哀牢山脉中下段的元江(红河)流域、藤条江流域、把边江(李仙江)流域。主要集中在元阳、红河、绿春、金平、元江、墨江、宁洱、江城等县域。据统计,总面积达140多万亩。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据晚唐樊绰的《蛮书·云南管内物产》云:“蛮治山田,殊为精好。” 自唐代以来“蛮”就已经在红河流域的元江、墨江、红河、元阳等地形成了哈尼族文化核心区,而梯田(山田)恰好又在此间分布集中。故此“蛮”当是哈尼族先民。
哈尼族人在梯田生产活动中以自然生态为依托,在生活方式上以自然环境为根本,在宗教活动中以自然万物为神明,创造出“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景观组合特征,展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人居生态环境,在中外梯田中“独领风骚”。在现代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如何传承农耕文化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在全球变暖,中国西南连续干旱的气候环境下,灌溉梯田的水资源逐年减少,如何保持梯田波光粼粼的水土平衡?为此感叹:申遗难,守遗更难!守护像哈尼梯田这样的活态文化遗产难上加难!
二、哈尼梯田的困境与成因分析
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变暖,农村体制的变革,西部开发力度的加大,全球化、科技化、产业化、城镇化等现代文明的影响,与申遗之前相比,哈尼梯田所依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的传承机制都面临着困境。归结起来为:生态系统变迁,导致涵养水源功能下降;在开发利用遗产区资源中出现梯田景观被毁坏的情况;杂交稻的“绿色革命”导致多样性传统水稻品种流失;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导致梯田面积萎缩;传统观念改变导致文化传承断代,以及传统民居的变迁等,*2008年笔者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云南哈尼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已结题),2012年国家环保部南京环科所又资助了《红河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研究》(已结题)的项目,2013年又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云南哈尼族梯田文化核心区元阳梯田稻作品种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资助。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材料,均属于上述课题的田野调查。其困境及形成原因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生态系统变迁,涵养水源功能下降
21世纪以来实施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等生态工程之后,元阳县森林覆盖率上升很快,至2015年森林覆盖率达44%,特别是哈尼梯田遗产区的森林覆盖率达67%。但由于遗产区50%的植被属于次生退耕还林,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下降,水源减少,导致枯水季不能保证梯田水源。
从哈尼梯田分布来看,梯田在海拔1600米以下均为保水田,即一年四季波光粼粼,也是哈尼梯田的主体部分,但由于环境的变化,每到枯水季节,离沟水源较远的部分保水田也变成干田,导致栽秧时令也无法移栽秧苗。
从自然环境来看,哈尼梯田灌溉水源减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雨水季节分配不均。元阳县虽然素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季节差异显著,每年11月至第二年4月为干季,降雨量少,河流溪水为枯水季。每年5月至8月为雨季,洪涝、地质灾害时有发生。二是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改变水源林的生态结构。为了追逐经济林木的高效益,许多村寨的旱地、荒山,砍伐灌木林后大量栽种了杉木林,从涵养水分功能来讲,杉木是吸水多的植物之一,其林下的地面较为干燥,从而导致水源林涵养水分功能减退。三是水利建设投入不足,工程性缺水严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之中国西南地区近年来连续严重干旱,灌溉哈尼梯田的“绿色水库”水量大减或枯竭,难以满足梯田灌溉的需要。元阳县灌溉19万亩梯田的上万条大小水沟密如蛛网,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投入不足,水库、沟渠等水利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梯田灌溉沟渠90%以上是土沟渠,沟渠渗漏,导致工程性缺水,有的水沟由于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堵塞后年久失修,导致栽秧季节无水流,雨水季节泛滥洪灾,水资源平衡被打破,造成部分梯田得不到有效灌溉,面临干涸危机。
(二)资源开发与保护梯田环境问题
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延续的主要威胁之一就是现代旅游经济的商品开发。为了配合旅游发展,满足游客需求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成为影响遗产地景观的重要因素。这类设施本不属于哈尼梯田农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一旦建设过度,带来的将是对原始景观的极大损害。如遗产区内箐口村西南面的“哈尼梯田小镇”休闲旅游度假村的建设就是典型的案例。
箐口距元阳县城老城区6千米,由于箐口地处元阳哈尼族梯田风景核心区,村落四周被绿树竹林和层层梯田环抱,蘑菇房与梯田合二为一,民风淳朴,具有典型的哈尼族传统村落生态文化。箐口村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哈尼山村,森林—村寨—梯田—河流四素同构的哈尼梯田生态文化系统景观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凡是来元阳旅游的人都要在箐口村西南面的公路边停下来远眺东北方向的箐口村落:每到冬春早晨,白雾缭绕的远处高山上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的下方是一个村落和层层延伸的梯田,错落有致的蘑菇房在白雾中时隐时现,偶尔有几缕炊烟在黄墙青顶上飘过,如同人间仙境。到了中午云雾散尽,村寨周围的层层梯田,就像千万面的镜子将蓝天映入其中,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2](P4)
箐口村祭山神的地点位于村西南4千米处的一座小山包丛林中,森林核心面积约10亩,缓冲区小灌木林50亩,其周边还有500多亩的荒地植被,是村民的放牧场,其下方有层层梯田分布。因此,这片森林及其周边牧场实际上既是宗教活动地点,又是一片生态系统良好的水源林。林中有一棵直径为1米多的乔木,说明这里曾经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现在植物群落结构仍然明显:顶层乔木,中层灌木林、下层草本植物,地面层苔藓。树冠荫蔽度密,地面阴暗潮湿,枯叶堆积层厚,地表为腐质土,草本茂盛,乔木树干上生长地衣、苔藓,树藤发达。林中树种以麻栗树、丝栗树为主,神林的外围生长2米多深的蕨类植物。[2](P14)
由于箐口地处梯田美丽的地带,2013年元阳县实施“美丽家园”建设的“哈尼梯田小镇”选址就在村民神山林周边,给梯田与森林层层围绕的村落自然景观造成破坏,哈尼族长期以来宗教祭祀的神林也难逃厄运,神林缓冲区外围生长2米多深的蕨类植物早已不复存在,神林外围已盖起了一栋栋“蘑菇房别墅”。实际上这座神林及缓冲区的牧场植被就是下方梯田的水源林,由于生态系统被破坏造成下方的梯田干涸。我们可以从“开发”前后的中得到印证。
遗产区内“旅游休闲景点”的建设不仅破坏了梯田自然景观,而且面临着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蘑菇房别墅”建立在缓坡地带,房屋地基、村内通道路基等经过人为大型挖掘机开挖松土,原有的植被和土层结构被破坏,坡面的地层变成了脆弱的松土质,加之其地处山坡上,降雨量大,雨季持续时间长,有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到时座座别墅及下方的梯田会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二是“旅游休闲景点”的排水系统不完善,排污系统解决不好,大量游客进入小镇别墅休闲度假,大量的排污会造成下方梯田的污染;三是“旅游休闲景点” 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将会引发与当地居民资源分配利益的纷争、社会治安等一系列新矛盾。
(三)杂交稻的推广,导致传统稻种丧失
20世纪90代初期开始,哈尼梯田引进了外地品种,其中杂交稻以产量高的优势,推广面大,经过实践海拔在1300米以下的梯田都适宜种杂交稻。到2013年杂交稻推广的面积增加到13.5万亩,占元阳县梯田总面积19万亩的71%,由此栽种传统品种的面积不足30%,且这部分梯田之所以幸免的原因是杂交稻不能适应高海拔高寒地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哈尼梯田曾经培育出上百种传统品种,但在政府倡导种植新品种的背景下,传统品种不断消失。1956~1982年,元阳县曾先后进行4次子种普查,其县域内有196个品种,其中籼稻有171种,粳稻25种;另有陆稻47种。[3](P119)在以杂交稻为代表的现代品种的冲击下,25年的时间里传统品种不断消失,而且传统品种流失的速度还在加快。哈尼族梯田文化核心区元阳县,20世纪80年代尚有200多个传统品种,至2015年整个县域内还种植的传统品种不足100个,*2012~2013年国家环保部南京环科所资助的《红河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研究》项目在元阳县内采集了100个传统水稻品种。从一定意义上讲,杂交稻成为哈尼梯田稻种生物多样性的“杀手”。
(四)梯田面积萎缩,改变传统利用方式
21世纪初期以来元阳梯田环境的另一大变迁是水田改旱地。元阳县海拔1200米以下的土地水热条件好,适宜发展热带经济作物,其中,香蕉、杧果、荔枝、龙眼、菠萝是传统热带经济作物。香蕉是元阳县的水果支柱产业,2004年元阳县水果种植面积10万亩,其中香蕉4万亩,占水果总面积的40%。其他水果种植较为分散,规模小。2004~2008年的香蕉种植面积基本维持不变,原因:一是香蕉市场价格在2元/千克左右波动;二是适宜种植香蕉的热区土地有限。到了2009年香蕉市场价格回升到4元/千克,由此热区部分梯田成为开发香蕉基地的对象,到2013年香蕉种植面积增加到6万亩,占元阳县水果种植面积的60%以上,增加的2万亩大部分是梯田,涉及黄茅岭、黄草岭、俄扎、新街、马街、逢春岭等乡镇。如俄扎乡2000多亩哈播梯田,当地农民经营了数百年的梯田如今变成一年四季都是一片葱绿的香蕉基地。
2010年以来受西南大干旱影响,高山区的部分梯田也改为旱地,种植玉米、黄豆等作物。最典型的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区攀枝花乡的保山寨梯田和老虎嘴梯田先后有1300多亩梯田改为旱地,种植玉米、黄豆。
老虎嘴梯田是哈尼梯田世界遗产区三大主要景观之一,2009年以前每当秋收之后至第二年春季栽秧之前都是波光粼粼的梯田景观,连片梯田中有一块造型远望形如奔驰的骏马,特别是在晚霞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观,是所有游客必看的一个精彩绝伦的景点,无人不为天工神造的骏马艺术而惊叹不息!如今由于水田改旱地,在骏马的胫部、腹部等许多地方出现了斑痕,晚霞映照下神奇的骏马失去了往日的特色。2009~2014年元阳县梯田改变利用土地的情况见下表:*涉及梯田遗产区新街、攀枝花、黄茅岭乡的梯田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的5118亩,占元阳县改变梯田利用面积14.85%。如此下去,遗产区梯田保护不容乐观。

2009~2014年元阳县梯田面积变化表(单位:亩)
梯田面积萎缩除了水源不足导致干旱的自然原因外,在市场经济的驱使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重要因素。传统种植水稻的经济效益太低,村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一旦有了经济价值更高的农作物时,人们往往放弃传统的水稻种植,选择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替代。以水稻种植计算其经济收入,如果种植一般的老品种,亩产约300千克谷子,5元/千克,不计人工成本,毛收入1500元/亩。如果种植新品种杂交稻,虽然亩产能达到500千克谷子,市场价2元/千克,毛收入仅为1000元/亩,加上新品种杂交稻必须得扣除谷种、化肥、农药等成本价约300元/亩,收入只剩700元/亩,其经济效益就更低了。据调查,种植香蕉,不仅有市场,而且价格稳定,一亩梯田种植130株香蕉,每株产20千克,以4元/千克计,亩产毛收入可达10400元,经济产值远远高于传统的水稻种植。
(五)传统民居的变迁,导致梯田与村落和谐景观的消失
村落是哈尼梯田景观人与自然和谐的标志,在元阳哈尼族传统民居最有特色的就是蘑菇房的建筑形样,这是哈尼族迁徙到亚热带哀牢山区为适应高温多雨的半山地带而改进的“碉式”建筑民居,在垫基石上采用木夹板定型泥土筑墙或土坯砌墙,从地面一层起有3层,顶层上面覆盖四斜面茅草顶,有利于排水,村落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半山腰间,远望其形犹如朵朵蘑菇,故称“蘑菇房”,在层层梯田环抱的自然景观中显得神奇美丽、生机盎然,青色的蘑菇草顶与连在一起的青色石灰平顶晒台,在夕阳余晖下闪闪的梯田和早晨哈尼山寨炊烟袅袅的蘑菇房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美景!但是,21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建筑用材山茅草逐年减少,梯田推广杂交稻后,稻草秆短小,不宜做屋顶覆盖的材料。人们开始将屋顶稻草层掀掉,搭起人字木架固定双斜面的石棉瓦,个别农户新建或重建房屋时,虽然不改变蘑菇房的内部结构,但以石头砌墙,顶层做成水泥平顶。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蘑菇房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在当地政府彻底消除蘑菇房的号令声中,哈尼山寨变成了一片白花花的石棉瓦房,失去了往日蘑菇房村寨的特色。
传统蘑菇房与梯田的和谐分布,显现了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哈尼梯田景观在“森林—水系—村寨—梯田”四素同构的组合特征缺一不可。基于这样的认识,2001年起元阳县政府在箐口村进行了乡村旅游景点规划建设,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改造村内道路、排水沟、村内广场,并对61户已建成砖混结构的水泥房和水泥瓦顶恢复成蘑菇房草顶的造型,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2008年元阳县又启动实施哈尼梯田旅游特色村建设,提出了“一镇六村”规划建设,即打造新街镇老县城的国际旅游城市,以箐口村为借鉴先后改造普高老寨、大鱼塘、全福庄小寨、牛倮普等,努力将梯田核心区的“一镇六村”打造成旅游基础设施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民族文化旅游特色村。但是,由于改造蘑菇房没有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只是在房顶上覆盖一层薄薄的稻草,风一吹就飞了,故老百姓称其为“戴帽”工程。与此同时,随着遗产区人口的不断增多,家庭分家带来建房需求逐年增加,遗产区内群众提出建房需要的就有3740多户,而遗产区又无宅基地安排,难以满足群众需求,导致农户在自家农田、耕地、林地里建盖第二栋,甚至第三栋房屋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新建的房屋都是钢筋水泥混合的现代建筑,不仅影响了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而且破坏了遗产区的生态环境。
(六)文化传承断代,梯田文化面临危机
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云南哈尼稻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4]习总书记的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哈尼梯田非物质文化人文生态系统变迁的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
乡土性逐渐消失是哈尼梯田文化遗产价值延续的极大威胁,外来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对乡土的传统知识冲击很大,由此导致乡土文化系统的破裂,也是文化传承断代的危机。梯田农耕乡土知识是哈尼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治家本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至20世纪末,年轻人一丝不苟地学习前辈的耕作技术。按哈尼族衡量年轻人的传统人才标准,小伙子帅不帅,不是看他的相貌身材,而是看他的耕田技术如何,如果小伙子是犁田、耙田、筑田埂的能手,就会得到大众的称赞,也就会赢得姑娘们的青睐。同样,姑娘美不美,就要看她栽插时蜻蜓点水似的栽秧技术。[5]通过10年家庭联产承包后,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背景促使青壮年外出打工,由此引发传统梯田农耕管理观念的改变,梯田文化的传承面临断代的危机。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梯田耕作技术,他们对传统古歌、情歌、舞蹈也不热衷,而是追求时尚的流行歌、交际舞,他们虽然也会参加传统礼仪活动,如丧礼、婚礼、祭寨神等,但他们脑子里没有多少传统文化内容。男的不愿去学耕作技术,女的不喜欢学纺织、绣花等传统服饰工艺。因此,今天劳作在梯田里的大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甚至70岁的人还不得不犁田、耙田。
三、哈尼梯田困境的治理路径选择
破解当前哈尼梯田面临的困境,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但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路径是:推广多样性水稻品种植,实现梯田可持续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传承保护哈尼梯田文化;加强法制建设,为保护梯田提供法律支持。
(一)推广多样性水稻品种,实现梯田可持续发展
从全球稻作生产粮食作物主产区来看,选育品种的大面积单一化种植,是导致稻作品种遗传基础狭窄,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带来水稻抗病力下降、土壤酸碱结构被破坏等环境问题,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在元阳哈尼梯田,尽管在杂交稻“绿色革命”的冲击下,传统品种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但是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保护了当地的水稻资源,高度的多样性依然存在。多样性品种可持续的水稻种植是梯田活态遗产的标志。从梯田的活态性和文化遗产价值的持续性来,水稻种植是保护梯田的必由路径。
科学研究证明,哈尼梯田稻谷品种多样性是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的。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教授主持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项目)“农业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和保护种质资源的原理方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元阳梯田传统农业中的可持续要素”。课题组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哈尼人民世世代代连续种植的水稻地方品种问题”。根据哈尼人民的口头传说,现在元阳梯田种植的水稻红米品种已经连续种植了上千年。“这一情况在世界上同类梯田中实属罕见……元阳梯田红米品种成为研究农业作物品种可持续利用最为宝贵的材料。” 该品种内部有丰富的基因多样性,多样性指数是现代改良品种的3倍。这种基因多样性使得该品种有良好的适应性,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他自然因素变化,它都能发挥出良好的适应缓冲作用,能长期保持产量稳定和阻止病虫害的暴发流行。鉴于此,朱有勇教授指出:“元阳梯田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可持续农业不可替代的研究基地。我们对元阳梯田传统农业瑰宝的研究,仅仅是冰山一角,还有太多的科学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还有太多的可持续要素需要发掘,为人类造福。”[6]
梯田红米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不但具有传统品种的基因价值,而且还有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具有超越百年历史稻种的唯一性。哈尼梯田品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病虫害的扩大和蔓延,即使遭遇病虫害,多个品种有与之抗衡的功能。因此,哈尼梯田传统稻种从来不施化肥、农药杀虫剂等。这一切大大降低了农民经营梯田的成本。虽然传统品种产量相对低,但它具有生物多样性,基因也多样化,适应性强,耐寒,米质优良,口感好的特性,是名副其实的绿色食品。地方政府应该加大梯田传统红米的选种、育种和种植的保护力度,从而实现梯田红米优质优价的目的,让梯田的主人看到希望的田野,从而更好地保护好梯田,杜绝弃耕、抛荒现象。优质的传统品种,既是绿色食品,又能体现经济价值,梯田的主人在水稻种植中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之后,就能传承梯田农耕文化,自然就保护了梯田文化遗产,也就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二)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传承保护哈尼梯田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存在着内在相互依存关系。”[7](P443~444)以族称命名的“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更加凸显了“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在各种复杂背景下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梯田主人能否传承农耕技术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本质上看哈尼梯田属于维系区域稻作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层级的物质文化遗产,但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哈尼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梯田农耕技术、农耕程序、农耕管理、农耕礼仪等一系列农耕文化无一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增强民族文化自觉是哈尼梯田文化传承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哈尼族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曾经让人梦魂牵萦的梯田故土,纷纷走出大山,把到各地城市谋求发展作为首选目标,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要让他们看到希望的田野,留住梯田的主人,要大力发展以红米为代表的梯田无公害产业,同时要通过学校教育和各种途径培训,提高他们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对他们自己文化特质和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觉醒。随着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到各级党政机关工作、到外地求学、就业的人员日益增多,这部分群体有着较强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回到自己家乡后,对民族群体和特定社区的人们调适外来文化的行为必然会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
2014年7月在红河县作夫村“矻扎扎”节田野调查时笔者亲眼目睹了这样一幕戏,在节日的那天下午,经常出外打工的一群年轻人,背着现代音响来到村寨中央的球场上,想施展现代迪斯科舞,球场的另一端是村民自唱自跳的哈尼族传统乐作舞,*乐作舞:哈尼族传统集体舞,男女老少皆宜,多则万人里外围圈舞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时迪斯科舞的音响压过乐作舞的歌声,但随着参与乐作舞人员的增多,舞圈的扩大,歌声和传统舞的欢呼声超过了现代音响,最后跳迪斯科舞的年轻人也融入了传统乐作舞圈里。
(三)加强法制建设,为保护梯田提供法律支持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于2012年5月31日经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实施。本条例对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的保护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是目前对元阳梯田保护最权威的法规。当下哈尼梯田遗产区的建设存在一些不协调的问题,如“哈尼梯田小镇”建设是为了发展旅游业而做的一项民生工程,但这一工程不仅破坏了梯田景观,而且破坏梯田水源的生态系统。恢复传统民居蘑菇房也是修旧不如旧。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借助法律手段,促使梯田保护责任化的结果。因此,健全法律法规,重在落实,政府应该带头遵守,克服长官意识,使哈尼梯田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能够有效地统一起来,并且传承下去,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珍贵遗产。
对哈尼梯田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要坚持梯田自然生态环境改变最小的原则。也就是说,尽量不去改变梯田的自然环境,在梯田遗产景观区域不要大兴土木。哈尼族梯田对水的循环利用,靠的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森林植被蓄水功能,从高山森林孕育的溪水河流被盘山而下的水沟引入村寨,梯田连接水沟,泉水顺着层层梯田,由上而下、长流不断,最后汇入谷底的江河湖泊,又蒸发升空,化为云雾阴雨,贮于高山森林之中。如此巧妙地利用自然、变自然生态为梯田农业生态正是哈尼梯田生态文明的智慧杰作。
梯田是哈尼族最具特色的文化代表,是哈尼人民用若干世纪的生命和血汗创作的人类文化遗产,是哈尼族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主要载体。其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上,而且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价值。申遗以来,哈尼梯田虽然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是,哈尼梯田仍然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活态遗产”,是当下云南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的典范,蕴含有丰富的传统技能和传统知识,是全人类宝贵知识遗产。这份遗产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而且是属于全人类拥有的共同财富。保护好这一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全体哈尼人民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1]闵庆文.大地之歌——哈尼梯田的世界影响[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0.
[2]黄绍文.箐口:中国哈尼族最后的蘑菇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3]元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元阳县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
[4]尹朝平.时不我待积极传承农业文明[N].云南日报,2015-05-05,(1).
[5]黄绍文,廖国强.农村体制变迁对哈尼梯田及生态的影响[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6]朱有勇.元阳梯田红米稻作文化——一项亟待研究和保护的农业科学文化遗产[J].学术探索,2009,(3).
[7]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李 官〕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of Hani Terrace
HUANG Shao-wen, HUANG Han-qi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661100, Yunnan, China)
Hani Terrace, with the combined features of the four elements isomorphism of “forest-water-village-terrace” as well as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standards, was included in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Hani Terrace is facing the following difficulties: decreased function of water conservation caused by the ecosystem changes; the destruction of terraced landscape du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the loss of the diversity of traditional rice varieties brought by the “green revolution” of hybrid rice; the atrophy of terraced area caused by the change in land use patterns; and cultural heritage dating and loss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culture induced by change of traditional concept. On the path selec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Hani Terrace cultural heritage,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minimization, so as not to chang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terrac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protection of terraced field and arousing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unify and pass down effectively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e of Hani Terrace to make it a truly precious heritage of human culture.
Hani Terrac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3XJA850001);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WX15160)
黄绍文(1965— ),男(哈尼族),云南元阳人,红河学院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遗产与民族生态文化研究;
G112
A
1006-723X(2016)10-0131-07
黄涵琪(1989— ),女(哈尼族),云南绿春人,红河学院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助教,主要从事新闻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