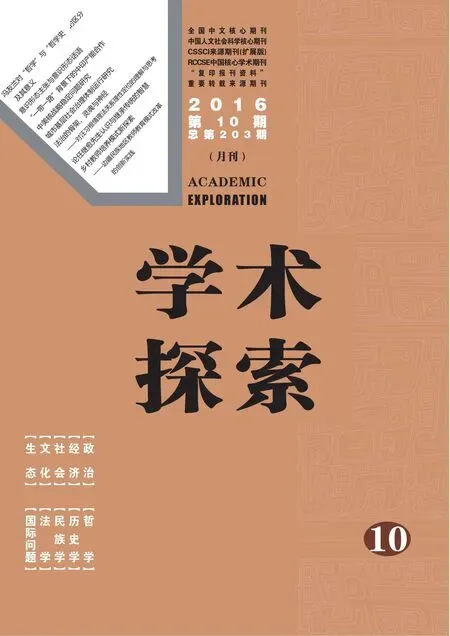帮助侵权涵摄下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
陈存款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0031)
帮助侵权涵摄下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
陈存款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0031)
建立在网络自然搜索基础上的竞价排名行为有其自身特点,究为广告还是技术信息服务,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规定并未结束其争议。其与推广用户行为结合造成损害过程中,侵权要素及形态均较复杂,帮助侵权不失为私法上分析该种行为的有力工具。帮助侵权之主观有故意和过错之争,以包含过失为妥。服务商过失的判断应从严把握,以实现公平正义之宏旨。整个过程中,司法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双重属性;帮助侵权
继2008年“屏蔽门”事件之后,魏则西事件再次将百度搜索引擎竞价排名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引起人们广泛讨论和质疑。*魏则西因身患滑膜肉瘤而四处寻医。经电视媒体报道和百度搜索及魏父实地考察等多方了解后,魏则西入住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治疗中心治疗。2016年4月22日,魏则西因医治无效死亡。此事件折射出了广告虚假宣传、医疗广告、医院(包括部队医院)监管改制等问题,还引发了人们对搜索引擎竞价排名问题的深思。
一、竞价排名是一种兼具广告属性的信息技术行为
关于竞价排名的性质,理论界及实务界有广告说、信息服务说之争,还有少数人坚持公共产品说、中介属性说等观点。持广告说的学者不管是从推广公司自身的定位还是其他角度出发,一般都将《广告法》第二条作为论述基点并落脚于此,对技术特征重视不够。《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也将付费搜索结果明确为广告。持信息服务说者更加重视搜索引擎的技术特征,多将之视为信息检索或信息提供行为而对广告属性有所忽略。其他学说都只重视了其中一方面的特征。国家网信办的《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并未结束竞价排名行为的性质之争。该规定第11条也只是规定了付费信息提供者的义务,对竞价搜索排名的行为性质仍未予以明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意义不大,因任何人提供商业广告信息都应守法。*第十一条 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提供付费搜索信息服务,应当依法查验客户有关资质,明确付费搜索信息页面比例上限,醒目区分自然搜索结果与付费搜索信息,对付费搜索信息逐条加注显著标识。服务商的推广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行为,兼具广告的部分属性。
(一)搜索竞价排名的信息技术本质
搜索引擎竞价排名,是指排名服务商根据企业出价高低和质量度等网站指数确定相同关键词在展示结果中位置的一种行为。百度公司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步骤进行:首先,注册开通百度推广账户;其次,服务商审查企业资质,*根据百度推广官方网站,“帮助中心—申请百度推广需要准备什么材料”介绍,企业资质一般包括营业执照、ICP备案、行业资质等材料,且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了不同的客户资质审核要求。http://e.baidu.com/help?subsite=cq.访问时间:2016年6月1日。签订推广服务协议,企业给付预存费用。预存费用一般包含技术服务费和点击费两部分。目前,百度推广的开户预存费用为6000元,1000元为专业服务费,5000元为预存点击费用;再次,推广人设定关键词、标题、链接地址、文字描述等内容;最后,服务商审核通过后为之设链,进行推广。结合自然搜索原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行为具商业属性,推广企业与提供商之间是服务合同关系,服务商从该行为中获益;第二,竞价服务商只设链,关键词及企业网站的各种信息均由企业自行设置,但排名行为可能影响搜索人;第三,自然搜索结果也包含了企业的网站链接,排名服务商干涉并改变了自然搜索结果的显示顺序,将链接在搜索结果中予以置前展现。
《广告法》虽然明确互联网广告适用该法,但互联网广告有弹窗广告、电子直邮、横幅广告、及时聊天等多种方式,未明确网络搜索竞价行为是广告。一方面,如果无竞价因素,自然搜索引擎则根据关联匹配度、人气指数等算法规则进行计算。搜索排列结果也是根据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的算法规则而排列出现的。故服务商欲改变搜索结果的排列出现方式,只需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改编其计算程序法则,对数据库进行搜集整理分析即可。获得报酬只能说是服务商干预搜索结果的一种动机和目的。自然搜索的信息技术本质并未因人为因素、有偿性地介入而改变。因此笔者总体上赞同北京市高级法院信息检索行为之观点。*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第39条、第40条。实践中不少法院亦持有相同观点。*见本文实证部分表1。但亦不能因此完全否定其中所具有的广告成分。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关键词、句、标题、图片等内容均由推广用户自己编辑选择且可随时变更,服务商本身并不参与。
(二)竞价行为具广告学之部分广告特质
“广告是一种有偿的、经由大众媒介的、目的在于劝服的企图。”[1](P6)再结合其他经典广告学著作,[2](P2)广告实际上是一种以不特定人为对象的传播活动,有偿性是否为必备要素尚存争议,但一般都具有偿性、大众媒介性及劝服性三要素。广告活动通常有广告主、广告公司、辅助性组织(外援性机构)、媒介目标受众等主体参与。
竞价排名明显蕴含有偿性特点,但大众媒介性及劝服性要素则难以准确涵射其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广告形式比较明显,易于大众辨识。相比之下,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虽以“推广”字样标示,但其混杂在所展示的搜索结果中间,区分度较小。搜索者依兴趣或所需进行搜索,再根据搜索结果进一步查找信息,具有较强的自主选择性,传统媒介受众则是被动接受广告信息,当然也可以选择看或不看广告信息。竞价搜索结果展示的是商品、服务还是链接信息尚存争议。实际上大部分的链接都包括文字、网址、图片等信息,如果从记载及显示的内容来看,有些具有说服诱导之成分。而仅从链接来看,则难观此信息。大多数的竞价搜索结果其劝服性因素并不明显,且展示的信息内容不具体,但有的推广标题和描述中也具有介绍引诱消费者的内容。
(三)《广告法》第二条之阐释
《广告法》第二条第一句规定了广告的主体、形式、目的及调整对象。为维系整个法律秩序的统一性,自德国萨维尼“规则的联结”始,至卡尔·拉伦茨“法律意义的脉络”,再到波恩·魏德士的“内外法律体系”,及至杨仁寿“内部法律体系”说,虽然对体系的认识有所不同,均认为体系为解释的有力工具之一。对《广告法》第二条第一句地理解首先应放到其内部体系中看,考虑上下条文之间的连接及逻辑关系;还要进行《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司法解释、规章等法秩序统一下的综合考察。从内部体系来看,本法规定了广告内容、行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故应将该法的调整对象“商业广告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行为来看待,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包括广告的内容准则、监管、经营、发布行为规范等,不能将之理解为静止的、名义上的广告。从整个法秩序来看,该法属经济法范畴,主要规制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为,同行政法、刑事法及民事法一起调整广告行为,尤其是责任的衔接上。
平义理论认为法律无须解释,指示理论认为文义解释优先,两种理论自身欠缺明显。解释始于文义,终于文义,但也不能囿于文义。文义以明白无误的意义为核心,至四周则为模糊地带。文义解释应参照语文语法结构、词句关系、日常用语与专业术语等,当结果为复数时,还应结合历史解释等方法确定文义结果。该句中若忽略“商业广告活动”及后半句,则其半句也能构成句子。“直接或者间接地”一起构成方式状语,用以修饰谓语“介绍”,“介绍”后则为宾语。“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均具有模糊性,需解释。媒介是扩展信息的工具,依存于信息传播而存在的;形式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概念,相对于内容而言,指事物内在要素的结构或表现方式。互联网搜索引擎虽然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不同,改变了受众被动接受信息的特点,但本质上仍为扩展信息的工具,虽然大多时候仅为指引链接,只不过指引链接是间接地扩展作用。故,其属媒介的一种,信息是本质,互联网搜索引擎为形式载体。而竞价排名则是服务商利用搜索引擎这一媒介间接传播信息的行为。
二、司法实践论
(一)八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北大法宝进行与本文主题相关之搜索,筛选出2010年之后的八个案例为样本,用以观察实务部门之观点及处理模式,以资参借。

案件编号定性主观状态主观判断依据裁判逻辑或理念1网络服务提供未明确不明确以他人行为构成直接侵权为前提,不构成共同侵权2网络搜索服务,非网络传媒过错,对于明显侵权可能性应知未知。未分故意或过失百度公司应知晓知名度却未审查用户资质构成帮助侵权3信息检索技术服务,非广告无过错主动审查关键词是否涉嫌反、黄等法律禁止性内容;是否侵权驰名商标;推广合同中要求相对人不得侵权;设置投诉及权利救济渠道八百客公司构成侵权,但百度无责4未明确无过错,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与侵权人无共同的意思联络和过错提醒服务合同相对方不得侵权;公示了投诉及救济方式;遵循了通知移除规则注意义务较低,限于明显违反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每个都详细审查难以做到5网络付费推广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并无过错,不构成教唆、帮助侵权原告企业名称知名度不具导致事先审查的注意义务;审查了相关资质;约定、提醒用户不得侵权;设置了救济方法一般无全面、主动、事前审查义务,仅对明显违法尽审查义务;有高于自然搜索的一定审查及警示义务。逻辑为不知、也不应知侵权存在6广告经营主体(未明确是广告行为)缺乏明知,无故意推广网站与跳转网站域名不同,对跳转网站百度无法知晓和控制第三方网站是欺诈人和责任主体,推广服务商无欺诈故意,原告损失与其行为间无直接因果关系7未明确有过错“加V认证”比一般推广具较高注意义务,明知“人证一致”认证存有漏洞及打零钱认证法可以弥补却未采用;服务商接获权利人通知后未对冒名网站进行筛查因加V认证而具较高注意义务8涉案链接属广告不明确不明确非虚假广告,推广链接与被链接网站无关
为行文方便,表中未列出案由,其中1、2号案件案由为“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3号为“侵犯商标权”;4、5号为“不正当竞争”;6、7为“财产损害”;8为“虚假宣传”。关于承担责任方面,本表所列的1~8个案件中,只有2、7案件承担责任,法律依据分别为民通第134条第1款第7项、民通意见第148条;民通第134条第1款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从比例来看,法院裁判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为25%,75%的不承担责任。
从本表中可看出以下几点:*案例1~8编号分别为:北京市高院,(2013)高民终字第1620号判决;上海高院,(2008)沪民三(知)终字第116号裁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终字第2779号判决、(2015)一中民(知)终字第860号判决;深圳市福田区法院,(2015)深福法知民初字第106号判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06709号判决、(2015)一中民终字第05826号判决、(2013)一中民终字第9625号判决。第一,从对推广服务的定性来看,认为属于信息服务或技术服务的占比50%,未明确定性的占25%,认为属于广告的12.5%,认为属于广告经营主体但未明确其是否属于广告行为的12.5%;第二,承担责任的规范依据一是《民通意见》148条的帮助侵权,承担相应责任,一是依《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三款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从裁判证成方式看,案中法院大都从间接侵权的角度进行论证,在论证第三方构成侵权前提下,再分析服务商的主客观方面,第三方侵权前提下,服务商才有可能侵权(除表中第8个案例外,均是此分析路径);第四,从推广服务商主观状态来看,有的法院具体到故意,但基本上都停留在主观有过错而未有故意和过失之辨;第五,注意义务问题,一般来说服务商并不存在较高的注意义务。法院判断违反义务俱结合案例而定,并无一成不变之标准。一般包括较低的注意义务(即对涉反、黄等法律禁止性及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情形的注意),因合同行为产生的义务(提醒、告知、约定相对人不得侵权),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加V认证行为,增加了公众的信赖),法定义务(设置权利救济渠道、通知后采取必要措施等)等。
(二)两种不同性质案例的展开
1.判决定性为广告的不当性
此八个案例中,只有田某诉百度公司虚假宣传纠纷案中二审法院明确将百度推广定性为广告。该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百度推广本质上属于信息检索技术服务,同时认为,即使认为百度推广属于广告,也不能认定百度公司是关键词的广告制作者或者发布者。二审法院在(2013)一中民终字第9625号中认为,推广链接属广告,但也以广告不属于虚假宣传而维持了原判(原审驳回了田的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中,法院认识到了竞价排名与纯搜索引擎二者间存在差异,搜索结果在某位置地出现有人为的因素。但二审判决也存在一些不当之处。
第一,关于造成差异的人为因素及目的问题,前文已述,不再展开;*详见前文“搜索竞价排名的信息技术本质”部分所述。第二,从“设置者”来看,二审法院笼统地用设置者这一称谓指代不明。结合语义,可以理解成是广告主,似乎也可以理解成包括百度公司在内。如属于前者,其目的顺理成章;若理解成包括后者,则难以自圆其说;第三,正如一审判决所述,如果推广链接属于广告,服务商的主体定性将存在困难。根据《广告法》第二条,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中的广告设计、制作者显然不符。广告学中的代理一般指辅助机构进行的调查、咨询、策划等活动,显然也不是广告代理人。发布是将广告资讯通过媒体或形式向社会大众传播的行为。竞价推广服务中,服务商只是将第三方网站予以指引,并不发布具体内容,大多缺乏劝服意图,搜索者根据自己兴趣和搜索结果进一步访问所需网站。因此,认定为广告发布者也存在不妥。
2.定性为信息技术行为的妥适性
此八个案例中,认定排名推广行为是信息技术行为的占比50%,此种定性之法院,认识到了搜索排名的技术本质及区别自然搜索的特性。结合判决,理由如下:第一,提供商仅通过平台和技术进行竞价排名,不参与第三方关键词、描述及网址等地选择和设置,其内容和形式由第三方自主决定,详细过程参见本文第一部分;第二,从结果来看,仅改变推广用户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缺乏推介商品服务之功能;第三,因其收费或加V认证,不同于一般的自然搜索,具较高的注意义务;第四,竞价推广是企业提高竞争力,增加商业机会的手段和方式。法院此种定性虽未明确竞价行为所具有的部分广告属性,但亦赋予不同于自然搜索的较高注意义务。
三、帮助侵权为百度竞价行为的私法规范
(一)《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作用
企业用户通过搜索引擎服务商推广商品或服务的行为,涉及较多的是侵犯知识产权中的著作权和商标权、商业利益,当然也存在侵犯人身权或财产权之情形,如虚假陈述引起的责任及产品质量责任。从侵权法的范畴来看,知识产权、商业利益、产品质量及消费者权益领域均有特别法予以规定。据普通法(《侵权责任法》)与特别法之适用原理,二者均有规定时特别法优先。当然,认为属广告的学者,应按《广告法》确定提供商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搜索排名行为侵权样态的多样性和法律规定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却始终存在。更何况,特别法关于民事侵权的规定多为转介条款,仍需借助《侵权责任法》最终确定民事责任方式、范围的承担等。为此,有必要从侵权法的基本原理来审视其行为。
据前文对该行为之分析,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其能否与推广企业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尤其是能否构成帮助侵权,从而承担连带责任。搜索排名中,服务商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当然是法律规定,除非事人另有约定。侵权法范畴内,承担连带责任以共同侵权及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者较多。多人侵权包括共同加害、共同危险、教唆、帮助侵权及分别侵权几种类型,主要规定在《民通》第130条、《民通意见》第147条、《侵权责任法》第9~12条等。若提供商与注册用户双方存在意思联络,双方故意侵权构成共同加害自不待言,也易于辨识。教唆者也较易判断,承担连带责任即可。因普通意义上的帮助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较难区分和定性,不能抽象地认为帮助者知道其行为可能造成侵权就认定为帮助侵权,此不利于助人为乐公序良俗之维护,也为日常生活所不允。因之,应该具体分析其行为与被帮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排名服务商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侵权,须仔细辨别,详加斟酌。
(二)帮助侵权构成
一般只有在通谋的数人侵权形态下,按照分工之不同,整个行为中存在教唆行为、实行行为和帮助行为。相对于个人侵权来说,共同侵权本质上在于形成了多数人的共同意志,有一定的组织和分工。主观状态是区分共同侵权的重要因素,不得不辨,帮助侵权亦然。
1.故意与过错
帮助即为以积极的或消极的行为,对实施侵权行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权行为之实施者。[3](P506)通常以物质、方法、精神等方式助之。关于帮助侵权的构成有故意说和过错说两种观点。
关于故意说,有学者认为,“帮助”与刑法中的同义,即故意。[4](P761~763)(P365~366)还有学者认为,双方为共同故意,过失不构成帮助侵权。[5](P320) (P374~375)更有学者认为,帮助人和被帮助人要为直接故意且有意思联络,意思联络发生在实行行为前的为共同加害,发生在中则为帮助型共同侵权行为。[6] (P109~111,118)也有学者则认为双方为故意即可,不必共同故意。[7] (P180~182)虽然王利明教授认为,“尽管帮助者主观上可能不存在故意,但是其已经认识到行为的后果并参与了此行为”。[8] (P551)从此论述看出,既已有所认识仍为帮助主观上实为故意,故其也持故意观。
持过错说的学者认为,帮助者的主观不但包括故意还包括过失。史尚宽先生认为,帮助之意义与刑法略同,与刑法不同者,不以故意为必要。亦得有过失之帮助。[9](P174~175)持此观点者也不在少数,“过失帮助也可构成帮助侵权。客观上对加害行为起辅助作用,亦构成共同侵权”。[10](P1026)
2.帮助不以故意为必要
对共同侵权的理解不同,对帮助侵权认识也会产生差异。双方为共同故意或相互知晓而为之者,自行为产生时始为共同加害。至于双方主观均为故意,结合帮助行为的认识对象,显然为帮助侵权。对于被帮助人不知帮助行为的存在,帮助人故意提供且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客观上起到作用的形态,一方面,此种情形是帮助人在利用被帮助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具有道德的可谴责性;另一方面,帮助人不直接实施侵权行为,受害人对帮助人及因果关系较难证明,为发挥侵权法功能,理论上也易认为构成帮助侵权。至于过失能否构成帮助侵权,笔者同意过失亦能构成的观点。
第一,认识的对象是厘清帮助者心理状态之前提,即“被帮助行为”还是“帮助行为”。通念之侵权认识是对自己行为之认识,进而是意志因素的判断。应知的判断又常参照注意义务的违反。注意义务是为避免给他人造成损害而对自己行为的限制,其来源主要有法律规定、约定、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及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等。如果法律在普遍意义上让自己对别人的行为也承担如此的义务并承担责任是法律的苛刻和不公,也与自己责任不符,不但会严重限制行为人的行为自由,在客观上也是不合理和不可能的,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规定且有充分的理由,如替代责任。因帮助行为通常依附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而发生损害后果,故对被帮助人行为与帮助行为二者的认识是统一的。即,帮助人的认识对象应为“帮助与第三方的侵权行为结合起来可能发生某种损害后果”。如果认识到了仍提供帮助,为故意无疑。在帮助侵权中,因被帮助行为本身已是侵权行为,具有违法性和应谴责性,帮助人理应存在一定注意义务,故,帮助人的主观态度也可能为过失。
第二,帮助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帮助者的主观应包括过失。帮助行为具有依附于第三人侵权行为的特征,以其他侵权行为的存在为前提,帮助行为不能脱离前行为而单独造成损害后果。若帮助人过失帮助发生损害后果,不按照帮助侵权处理将难以找到合理的法律依据。有人认为可以按《侵权责任法》第10条共同危险或第12条分别侵权进行处理,虽共同与分别均属相对,界限也并非明显,但此做法仍不妥。一方面,共同危险以择一的因果关系为基础,通常适用于侵权人不明的状况,侵权人确定则转化为单独侵权。帮助侵权中的侵权人通常是确定的,以单一因果关系为基础,故共同危险难以包括过失帮助行为。另一方面,即使将帮助行为看成是分别侵权行为之一种,因果关系也难以符合。第12条规定的因果关系为共同因果关系且每个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一。帮助侵权中,帮助一般只起到加速、鼓励或促进作用,缺乏第三人的行为有时仍可单独发生侵权后果,只是发生的快慢问题。只有帮助行为和因果关系具有独立性和可分性时,第12条才有适用的余地。共同加害行为显然更不合适。
第三,帮助侵权中,帮助在不同类型中的侵权中发挥的作用不同。虽然教唆、帮助在同一条款中规定,但仅是承担责任的方式相同而已,不能理解成构成要件也相同。二者明显存在不同之处。教唆为造意行为,以故意为限,但帮助则可理解成包括过失在内。帮助行为的从属性特点并不能否定其参与实施侵权的性质。帮助的方式人的帮助可表现为直接参与、提供工具、言语激励、有作为义务时不作为等多种方式,在帮助侵权中可起主要,甚至重要作用。此时,过失提供帮助者存在主观过错情况下,不予承担责任对受害人显属不公。故,帮助人的主观状态应包括过失。
第四,从美国及中国台湾的司法实践来看,帮助已突破故意的禁锢。美国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876节是关于协同行为人的规定,根据(b)、(c)项可知帮助也包括过失在内。*第876节 (b) 行为人知道他人之行为构成对义务的违反并且对该他人的此类行为给与实质性协助或鼓励;或者(c) 行为人对他人完成一侵权结果给与实质性协助,并且其自身行为,如果单独考虑,构成对该第三人的义务的违反。虽然王泽鉴先生认为过失构成帮助有讨论的余地,但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亦承认过失帮助构成侵权。“帮助人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而为帮助行为,致受帮助者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除帮助人能证明其帮助为无过失外,均应与受帮助之行为人连带负损害赔偿之债。”[11] (P493)虽将帮助之主观扩大到过失,但对过失之判断应坚持严格标准,不能过于宽泛和放松。参鉴美国在产品领域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准则,搜索排名行为的用途和作用较为显著,不能因提供者知道该行为可能用于侵权就认为构成帮助侵权。
第五,从刑民关系来看,刑法是民法的保障法,民法重过错,刑法重故意。刑法处罚的是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程度的行为,较为严苛且以打击故意犯罪为主,过失帮助者的主观恶性较小,往往难以达到应受惩罚的程度,承担民事责任即可。相比之下,民法强调的心理状态是过错,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只在特定的侵权情形下才具有意义。为平衡和分散社会风险,实现《侵权法》补偿及预防功能,我们发展了保险制度。网络无处不在的今天,虽网络内容服务商通常不造成工业产品之风险,但其工具性使网络侵权更易发生和难以控制且具传播迅速、影响大等特点。在此过程中网络服务商往往起帮助作用且多为过失,故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有必要将帮助理解成包括过失在内。
综上,在主观方面,被帮助人的主观方面可为故意或过失,包括对帮助人的帮助行为没有认知,帮助人的主观状态一般是故意,但也包括过失在内。客观方面,帮助行为对实行行为的发生及损害结果的出现客观上起加速作用。因果关系方面,单独来看,帮助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发生之间通常具有使损害结果更易出现或扩大的因果关系,但帮助与被帮助行为结合作为整体来看则与损害结果之间具相当因果关系。有些学者所说的甚至没有因果关系的说法也不可取,若无因果关系,责任就与行为之间就会失当,与法律责行相当的基本原则不甚相符。当然,帮助型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有损害结果,此无争议。
搜索推广行为服务商明知被推广企业存在侵权他人民事权益的可能性依然提供服务造成损害后果,那么就构成帮助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提供商主观上有过失,即应知而不知,则须探讨应知或注意的来源及标准。此种认识亦符合《侵权法》第36条第3款之立法意图。据该款,提供者“明知”构成帮助侵权,承担连带责任;应知的(过失的),自应知时与用户承担侵权责任。[12] (P218~219)服务商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后,再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4条等法律进行内部的责任追偿和分担,此时应参考其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所起作用等确定最终的责任承担。
(三)衡量服务商过错之参酌因素
实践中,故意的判断较难,但避风港规则是一很好的平衡手段,服务商自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即为明知。按照帮助侵权理论,此时服务商始具备帮助侵权的主观要件,如果不采取相关措施就构成帮助侵权,且该行为对损害的发生起辅助作用,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该与侵权人一起负连带责任。
竞价推广是在自然搜索基础上进行的,涉及三方主体。一是提供服务的人(供方),二是需要提供服务的人(需方),三是社会公众。三方因竞价排名服务发生关系。供方提供的搜索结果包含公共信息和推广商业信息,因此提供商要对搜索结果进行区分。公共服务的角色就决定了其最低的注意义务。网络环境下推广用户可随时变更关键词、句、标题、图片等内容,面对不断变换更新的海量信息,法律强加竞价排名服务商以真实、主动、瞬时、全面的审查义务显然苛刻,其客观上也难以做到。相比之下,注册推广企业对自己编制发布的信息更易控制和审查,这也是法律克以经营者、服务者责任自担的基础。有偿推广又使其具特殊性,应负比自然搜索情形下较高的注意义务,否则也是不公。故服务商的义务包括自然搜索和竞价排名搜索的双重义务,此也为《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所确认,但新规定仍然很抽象,许多语词内容难以判断,不好操作。因此,判断义务之来源还应结合民法的基本理论。民法上过失的通用判断标准为相同群体内的普通人标准,受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因此,互联网信息搜索竞价服务商通常的行为是参考标准之一,还应考虑搜索推广行为兼具广告属性的有偿信息服务行为的性质并结合个案而进行最终判断。
在以上几点的基础上,竞价排名提供商的注意义务有以下几点。
第一,较低的法定义务,如对涉反、黄、赌、毒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的注意等;还要遵守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行业准则和制度。第二,红旗标准,如驰名商标、广为人知的侵权事实等,所谓显著性可参考常识、常理、常情进行判断;第三,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及逻辑能够推出的应知事实;第四,合同产生的义务,根据权义对等原则,提供商收取推广用户费用,对推广用户理应尽资质审核、保存记录、提醒、通知等较高的注意义务。当然,其资质审核为形式审核,如果为实质审查明显加重提供商义务,主管机关有时也难以做到,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更是如此;大众创业情形下,提供商更应该进行技术创新,发现形式审查方式有漏洞时应尽力创制新的审查方法,及时采用并堵塞漏洞;第五,广告的部分属性要求提供商对公众公示权利救济渠道并为信息用户维权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帮助等;同时,应增强竞价排名结果在搜索显示结果中的可识别性。假如提供商还有其他先行行为,也要考虑是否引起信息消费者的信赖及产生相应的义务,如服务商加V认证是对推广企业主体信息的确认就产生用“打零钱认证法”进一步核实资质的义务等。
[1]托马斯.C.奥吉恩,克里斯.T.艾伦,查理德.J.塞梅尼克.广告学[M].程坪,张树庭,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2]威廉·阿伦斯,迈克尔·维戈尔德,克里斯蒂安·阿伦斯.当代广告学[M].丁俊杰,程坪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
[3]涉台问题101年度台抗字p493号裁定.民法债编总论[M].台北:郑若溪,2015.
[4]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M].杜景林,卢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5]杨立新.侵权责任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杨会.数人侵权责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张铁薇.共同侵权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
[8]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9]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0]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11]台湾最高法院99台上1058号判决.侵权行为法[M].王慕华,2015.
[12]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3]王泽鉴.侵权行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4]程啸.侵权责任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15]许传玺.侵权法重述第二版:条文部分[M].石宏,育东,译.法律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黎 玫〕
Pay-Per-Click under the Subsumtion of Helping Tort
CHEN Cun-kuan
(Th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400031, China)
Pay-Per-Click based on the network search engine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bout it there are disputes of whether it belongs to advertisement,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or both. And the new regulations do not end the debate. The elements and forms of tort are complex in the damage process of combing with the promotion of user behavior, and helping tort is a powerful tool of civil law in analyzing this kind of behavior. There are intention and fault opinions about the subjective of help infringement, and thus it is proper to include negligence. To realize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negligence judgment of service providers should be strict. The judicial practic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u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Pay-Per-Click of search engines; dual attribute; helping tort
陈存款(1983— ),男,河南通许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法学研究。
DF41
A
1006-723X(2016)10-0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