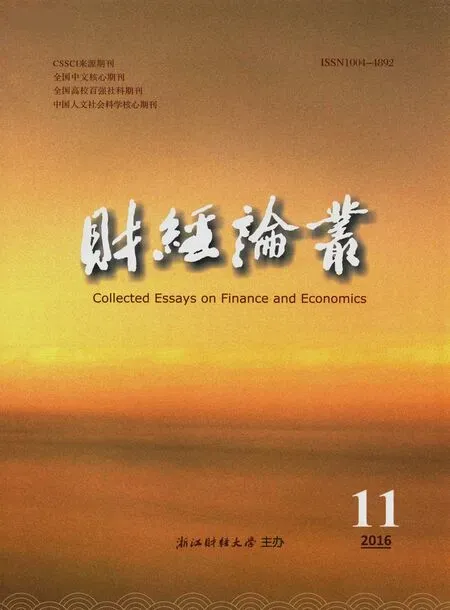网络建构视角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企业间领导力生成研究
——基于“大淘宝”网购平台案例
吴昀桥,郝 斌
(1.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83;2.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237)
网络建构视角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企业间领导力生成研究
——基于“大淘宝”网购平台案例
吴昀桥1,郝斌2
(1.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083;2.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7)
通过对单一企业网络纵向案例研究,本文探讨了企业间网络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企业间领导力的动态变迁。研究发现:核心企业在网络拓展中形成了网络权力,这种权力会随着生态企业网络的发展而逐渐演化,且这种动态网络权力配置较好地维系了企业间协调机制的有效性;过于强大的网络权力降低了核心企业行为对伙伴企业的意义建构性,进而影响到企业间领导力的提升。为此,核心企业只能通过正式权威的建立,在不同时期分别形成技术、平台和制度层面的领导力。本研究较好地弥补了依托对称性网络结构而形成的关系管理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引导非对称性网络结构下企业间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化。
企业间网络;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企业间领导力;商业生态
一、引 言
联盟合作与企业间网络的日益盛行,驱使网络管理成为企业抢占市场机遇、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大量研究聚焦于此,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企业网络管理策略及其效能机制[1][2][3]。其中,企业间网络管理的关系视角强调持续性、嵌入性网络关系在协调网络资源、管理网络活动中的作用,企业之间通过信任、承诺、依赖等方式相互联结,关系规范和市场信誉进而成为约束伙伴企业行为的主要手段[4]。与之相对应的契约理论视角则质疑非正式关系的约束效果,认为私利会成为企业打破关系平衡的诱因,企业只有通过缔结正式契约,才能够有效管理其伙伴企业[5]。而从网络知识管理与分享的角度看,协调与沟通作为即时互动机制,能够促进企业间知识共享与利益整合,进而培植合理有序的网络关系[6]。网络管理的伙伴选择视角则认为,伙伴企业的管理不应该是一个单纯的事后行为,需将网络管理的内容嵌入到前期的伙伴选择中[7][8]。这些研究视角往往基于不同的立场,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逻辑体系,但却共享同一个隐含假设,即企业间网络是基于资源交换或能力互补而催生的平等合作机制。
然而,在产品内分工日益细化、企业间协作动机愈加多元化的背景下,企业间网络中的平等关系开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非对称性的关系结构及其催生的企业间网络权力[9]。其一,企业间资源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开始成为跨企业边界合作的常态;其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抢占网络中心位置来赢得结构性优势和利益分配权;其三,市场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少数大型企业成为中小企业赖以依托的竞争领导者。在非对称性网络关系下,传统的网络管理理论显然难以解释核心企业的网络行为及其管理策略,故对企业管理实践也难以提供有效指导。此类问题的出现,引发了少数学者的关注,并开始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核心企业的网络构建与管理[10][11]。诸如,Dhanaraj和Parkhe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将核心企业的网络管理总结为三方面的活动:管理知识流动性、管理创新可获取性、以及管理网络动态性[2];Paquin和Howard-Grenville基于核心企业能力与行为的演变,分析了非对称性网络管理的动态性[3];Perrons则通过对Intel的案例分析,展现了核心企业利用网络权力来协助合作伙伴开展技术创新的动态过程[9]。但较为遗憾的是,由于相关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主流文献还未能形成一致而清晰的逻辑分析框架与理论体系。
通过对当前相对较为有限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作为网络的领导者,核心企业需要利用网络权力来管理跨边界的业务活动,其在整个网络中的影响力左右着合作伙伴的利益和企业间网络的价值创造。此时,核心企业具备了引导、控制和协调其他网络成员企业的领导者权威和非正式权力,即企业间领导力[12]。具体而言,企业间领导力是指联盟网络中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的影响力,核心企业通过探索联盟发展方向、整合联盟资源与目标、协助解决成员企业困难、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与声望来引导和影响联盟其他伙伴企业,并促进联盟成功。为了更好地探索核心企业利用网络权力培育并管理企业间领导力的内在机制,本文引入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案例企业的历时性分析,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核心企业如何通过网络建构来强化自身网络权力?网络权力如何作用于核心企业的网络地位,进而催生企业间领导力?
二、理论基础
从关系交换的理论视角来看,网络伙伴企业之间是基于持久交互作用的资源交换关系,关系双方均拥有彼此需要且有价值的资源[13]。资源的相互依赖会促进企业之间的关系性嵌入[14],并催生企业在维系彼此之间资源可获取性过程中的信任、承诺以及交互作用(reciprocity)[15][16],形成企业之间因关系性嵌入所产生的网络内知识沉淀,进而诱发网络外知识溢出效应,呈现出双重网络嵌入,推动网络发展与升级[17]。正是在此理论逻辑下,近年来主流文献从二元层面和网络层面分别对企业间合作关系的运行与协调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18][19][20]。但是,此理论逻辑所蕴含的隐藏假设是,合作企业之间的资源交换与业务交互作用是在一种对称性网络关系下展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使得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也存在着进一步完善与深化的空间。
最近几年内,少数学者开始打破以往理论建构中所依托的对称性网络假设,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合作中,试图探究非对称网络关系下企业间知识管理与整合。总体分析,这类研究大体遵循两条路径:其一,基于小企业的立场,探讨小企业如何在合作中避免大企业的知识侵犯、维护自身利益、开展知识探索[21][22][10];其二,基于大企业和整个网络关系的立场,分析大企业如何更好地管理网络价值创造并带动小企业的发展[23][2][3]。
由于市场地位或能力不足,小企业在与大企业合作中往往具有先天的劣势。大企业所具备的强势技术学习能力和资本优势对小企业的技术知识形成了威胁,Katila等将此形象地描述为“陪鲨鱼游泳”[21]。然而,这种威胁还取决于“鲨鱼”本身:其一,“鲨鱼”是否具备了侵占知识的能力;其二,“鲨鱼”是否有知识侵占的动机[10]。实际上,大企业知识侵占的能力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具备的网络权力及其运用方式[9]。大企业可以选择基于强势网络位势转嫁内部成本,例如供销关系中的附加报价(add-on pricing)[11],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网络能力和地位来更好地协调和管理跨边界的价值共创。在以大企业为核心的非对称性网络内,成员企业的角色完全不同于对称性网络,企业之间的依赖也由对等性转变为非对等性[4]。大企业的市场地位和技术主导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形成强势的网络权力,进而提升小企业的单边依赖性。
在非对称性网络中,核心企业由于占据了较成员企业更具优势的位置,其个体行动在网络的形成、成长和成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4][25]。然而,仅单独的网络位置并不能创造出利益,核心企业会利用其位置优势,通过保护、探索和管理网络,去获取网络利益的更大份额。除了占据中心位置以获取网络利润的更大份额,中心企业也应承担其责任,使得整体网络的生产既有效率又有效果。因此,公司在评估其通过联盟网络所创造出的价值时,首先要判断公司在网络中的位置。
Ibarra在研究个人权利时,认为权力除了来源于个体属性和正式权威,同样来自于纵向的劳动分工[26]。对于资源和不确定性的控制可能来源于跨边界的位置或者组织工作的核心位置[27]。而在产品内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网络中核心企业,例如Intel、Dell和Cisco等,负责向市场供给最终产品,并承担产品价值的实现,而其他生产与服务企业则围绕最终产品业务链条从事价值创造活动。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致使网络成员企业更加依赖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能力,核心企业也随即成为网络的中枢。因此,可以说,这些处于价值网络高位环节的核心企业的业务拓展与市场开发能力显著影响整个价值网络的价值创造和整体竞争力[28]。正是由于非对称性网络中这种企业在价值网络中进行的劳动分工,可以将个人权力的结论引申至网络层面,即企业间的权力同样来源于网络中的分工,换句话说,处于价值网络中高位环节位置可以为企业提供权力的来源。例如,模块化技术结构的发展,不仅使得主导设计成为技术结构的核心要素,而且还使得成员企业对于主导设计的模块集成商的依赖性增强,模块集成商也从而获得对于成员企业的权力,而升格为平台领导者[28]。
非对称性网络下的权力结构突显了核心企业的异质性角色,也赋予了其网络协调与管理职能。核心企业作为网络的“守门人”[29],不仅要承担自身的业务发展,还肩负着整个网络价值共创的使命[30]。尽管核心企业享受着优势网络地位及其衍生的网络权力所带来的收益红利,但也会受到诸多挑战。第一,核心企业需要与网外的同业企业竞争以吸引优质业务伙伴。战略伙伴选择理论强调通过关系建立之前的有效伙伴选择以促进合作成功[31][7]。虽然企业间网络中大多数非核心结点上往往因技术门槛较低而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相应的伙伴选择也相对较容易,但也有少数结点在技术上具有较高的要求,对应的市场厚度也较小,要选择并建立有价值的伙伴关系并不容易。此类供应商在业务合作与交易上往往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为了吸引这一类优质供应商,核心企业需要与其他同业企业展开争夺。第二,核心企业承担着网际竞争的重担。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和网络化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将业务重心下移(系统→模块),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竞争的重心上移(企业→网络),企业间网络成为最终产品市场竞争的基本单位。核心企业在网络间竞争中的表现无疑会影响到成员企业的追随意愿,因为较强的竞争力对成员企业来说意味着持续、稳定的合作机遇和可预期的未来收益。第三,核心企业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还需兼顾企业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根据商业生态系统理论[32],网络成员之间存在互赖、共生的利益联系,彼此之间通过知识流、物流、资金流紧密相连。在长期的业务协作中,利益分歧在所难免。如何协调网络成员间的利益、建立包容性的利益整合机制,无疑是对核心企业的挑战。
核心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彰显了网内协调与管理的重要性,近期的主流文献也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33][30][34]。诸如,Dhanaraj和Parkhe指出,网络成员企业并非仅仅对网络诱因和约束做出反应的惰性实体,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会主动开展价值搜寻与联合互动的自发性主体[2]。在另一项历时性研究中,Paquin和Howard-Grenville发现,在网络建构早期,核心企业会随着技能和资源的积累而逐渐形成网络管理能力,而随着网络的发展,核心企业在努力为不同成员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会遭遇越来越多的困境,网络管理也相应从偶发性的成员选择转变为持续而紧密的关系互动[3]。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没有超越企业间关系视角的束缚,将核心企业的网络管理视为基于关系治理机制的知识获取与业务协调。由于关系治理机制需要建立在持续性、反复性的互动和行动可预期的假设基础上[35],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间利益协调与整合问题。
在外部挑战和内部管理的双重压力下,以松散耦合结构为依托的关系治理机制已经难以满足跨边界价值共创的要求,核心企业需要借助更强的掌控力,以实现对成员企业的规制和整合。可以说,核心企业基于依赖非对称性所形成的网络权力为网络管理奠定了结构性基础。核心企业可以利用结构优势对成员企业决策施加影响,并在全网范围内推行既定的网络规则。然而,Shulman和Geng的研究发现,网络权力的过度使用有可能引起新的管理困境[11]。从Hogg等的关系认同视角来说,网络权力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企业对既定关系的价值性、战略性、公平性等方面所形成的认同[36]。这种认同的产生并不依赖于核心企业是否运用网络权力,而在于网络权力实施的方式和情境。核心企业的角色不能仅满足于权力的实施者,更应该体现出网际竞争下的领导者和探索者。在既定的网络管理行为和策略下,核心企业不再依赖于强权管理,而是逐渐培养和塑造企业间领导力[12][34],以此来引导成员企业之间积极有效的互动与融合。在此理论逻辑下,核心企业如何利用网络权力开展管理,以培育自身的企业间领导力?随着网络权力的实施,核心企业的地位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研究将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关注核心企业如何通过网络权力的建构和运用来提升企业间领导力,是一个较新的领域,基于现有文献还难以形成系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适合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37]。通过对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深化对同类问题或现象的理解[38],在研究过程中不预设过多的框架限制,使研究者可以发现更多的理论关系[39]。本文依据案例典型性、数据可得性、数据获取便利性等三个标准来进行案例企业选择[40][41],最终选定“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以下简称“大淘宝”)为案例样本,即以淘宝、天猫、聚划算等个人网购平台为核心的商业体系(不包括阿里巴巴B2B平台)。
(二)变量测定
在变量测量上,努力保持相对宽泛的概念范畴,以确保变量能够从数据中析出[42]。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选择文献中已有的分类及测量方式,以保障研究的可复制性。创新模式主要引用Henderson和Clark的框架,划分为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43]。架构创新是指企业对整个生态系统与网购平台的打造与调整;而模块创新即基于既定业务或服务的改进行为,属于局部性调整。网络权力的测度在网络中心性概念基础上,结合核心企业的异质性角色,主要基于核心企业在网络管理中所依托的优势点。意义建构衡量核心企业在多大程度上与成员企业共享学习经历、并对重要战略问题持有共同理解[6],相关测度如服务共享、业务扶持等。企业间领导力包括技术、平台、制度等三个方面[28],重点测量核心企业如何从这些角度去引领、影响或管控伙伴企业的行为与战略选择。
(三)资料收集
根据Miles和Huberman“证据三角形”观点,资料收集渠道必须多样化,以实现不同资料之间的相互验证,避免因资料的片面性而降低理论构建的有效性[44]。同时,多渠道的资料收集有利于避免共同方法变异问题,进而提升案例研究本身的建构效度。为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访谈、文献资料、内部档案数据等三种方式收集研究所需资料。实地访谈包括对“大淘宝”内部人士、中小网上卖家、平台服务商、行业专家等15人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方式进行,配以主问、辅问和记录人员,以确保充分挖掘研究所需信息,每次访谈约持续1至1.5小时。访谈结束后,研究人员与受访者交换名片,以便进一步的跟踪核实。文献资料收集途径包括:(1)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收集主流媒体对“大淘宝”相关业务、战略或高层人员的新闻报道、专访等资料;(2)通过EBSCO、AB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优秀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数据库收集与“大淘宝”有关的研究文献资料;(3)通过上海市图书馆、浦东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收集与“大淘宝”及其主要高层管理人员相关的图书资料。内部档案数据包括:(1)阿里研究报告,指通过阿里网站平台收集的阿里研究中心在不同时期发布的研究报告;(2)平台运行相关内部资料,主要包括各个时期阿里制定的网商规则相关资料、各类业务的相关宣传与分析材料、淘宝论坛中的相关信息发布和评论等;(3)高层讲话和公司报告,主要包括阿里集团高层在公司内部、网商论坛、企业家论坛等场合所做的报告,以及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年报等。
(四)数据整理与编码
本研究采用深度内容分析法,在对案例数据分析之前不预设理论偏好和初始假设[45]。为分析不同时期“大淘宝”开展的网络建构与管理行为,我们将案例企业所经历的发展时期划分为培育期、成长期和拓展期三个阶段。根据不同时间阶段,对“大淘宝”网络构建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关键事件的确定原则主要依据Ring和Van de Ven的界定,即“这一事件影响到合作双方关系的发展”。整个数据整理与分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步[46]。第一步,通过初步内容分析识别关键概念及其潜在关系。基于此,将研究团队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对资料进行通读并展开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注重采用表格来予以辅助[47]。随着分析过程的推进,安排两个小组一起开展讨论。经过多轮的资料阅读与讨论,确定了以下变量为本研究的关键变量:创新模式、网络权力、意义建构、企业间领导力。第二步,基于前述所明确的关键概念,对资料进行编码。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团队根据本文的主题及关键变量进行渐进式编码。创新模式按照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进行编码,网络权力按照强制性和柔性编码,意义建构按照强、弱编码,企业间领导力按照技术、平台、制度编码。整个编码过程由研究团队共同讨论确定,最终形成的编码关键词及条目数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测度关键词及编码条目数
四、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首先通过时间序列展开,剖析“大淘宝”生态网络的成长及其企业间领导力形成的基本过程;其次,开展跨阶段的比较分析,以揭示企业间领导力生成过程中各相关要素的演变路径;最后,对案例分析中所揭示的实证证据进行理论总结与讨论。
(一)基于时间阶段的“大淘宝”生态网络成长分析
1.“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培育期。2003年5月,以C2C业务为核心的淘宝网正式上线。尽管淘宝网的建立为阿里巴巴集团在网购生态系统中赢得了较好的网络位置,但在平台流量大量集聚之前,其并不具有显著的网络权力,淘宝网仍然需要通过大量的广告来吸引中小网店和网购消费者的注意。为了迅速赢得中小网商的关注,淘宝网推出了一系列的架构创新措施。在互联网业界普遍倡导商业模式赢利导向的环境中,淘宝却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双边平台定价模式创新特性[48],采用完全免费方式来引导网店和网购消费者的汇聚,并很快获得了大量人气的积累。该战略的成功实施至少有赖于淘宝两方面的能力:其一,强大的资金实力,来自集团层面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使得淘宝团队能够将免费战略执行到底;其二,淘宝团队卓越的战略视野,这可从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的演讲中得到充分体现,“淘宝选择免费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因为对手是收费的,我们为了与他们竞争,所以就采用免费的方式……我们最后选择免费,完全是因为市场……在这个时候,市场的培育是最重要的。”淘宝网在第一阶段所推出的另一项架构创新举措是诚信系统的建立,包括卖家评级、在线评价等。诚信系统的建立为淘宝网提升其服务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淘宝网一系列的网络建构行为构成了其网络权力的基础,体现在中小网商对淘宝平台的认可与追从。正如一位网店经理所说,“早期的淘宝网尽管在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上不能与今天相提并论,但在人气的集聚能力上,的确明显超过了同时期的竞争对手”。利用早期市场竞争相对较小、网购文化尚待培育的历史时机,淘宝网迅速通过架构创新占领了行业高端,在短时间内大量争取网站流量,培养用户体验。正是由于淘宝网网络权力的作用,中小网商对这一平台产生了深度的非对称性依赖,很多网商开始增加对淘宝网店铺的人力和资金投入,也越来越受到淘宝平台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过程中,淘宝网的强制性网络权力得以逐渐建立起来。
对于很多网商而言,这一时期淘宝的架构创新策略使其在诸多方面受益,即较强的意义建构性。其一是低成本的网店运作。由于淘宝网完全减免前六年的平台服务费,为中小网商节省了较大的成本支出。其二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淘宝网推出的一系列网商培植计划如淘宝大学、在线互动社区、论坛等,使得中小网商可以获得大量的网店经营知识,这在网购行业发展的初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三是人气集聚的优势。由于淘宝网成功的模式创新,淘宝当时成为网购的代名词。大量的网购客户被吸引过来,使得在淘宝网上开店成为网上销售的主要渠道。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培植网络平台,淘宝网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低门槛、宽松管理的策略,为网商的创新管理和迅速扩张提供了契机。
2.“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成长期。进入“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生态系统构建”开始成为网络发展的核心目标,最为标志性的事件无疑是“大淘宝”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在这一阶段中,阿里巴巴集团主要从两个方面丰富和拓展其电商网络:一是“大淘宝”内部资源协同与功能拓展,二是平台物种多样化与生态链打造。
从“大淘宝”内部来看,阿里巴巴集团一系列的战略性举措确保了其网络功能逐步增强,这些创新为中小网商的业务拓展提供了较好的资金、信息、业务配套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在自身平台功能日益强大的同时,“大淘宝”注重通过引入外部的多样化生态物种来拓展网络的服务功能和水平。正如《2010大淘宝生态圈百年合作伙伴发展倡议书》中所指出的,“在大淘宝商业生态圈建设中,合作伙伴作为重要的生态角色,其价值不可或缺”。这方面的举措包括用以引入第三方程序开发者的淘宝开放平台和涵盖物流、营销、渠道等方面“淘宝合作伙伴计划”的“淘拍档”平台。这些平台用以整合发展各方面的电子商务外包供应商,在IT、渠道、服务、营销及仓储物流等电子商务生态链的各个环节为淘宝卖家提供个性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
“大淘宝”的模块创新策略将其自身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显著提升了其强制性网络权力。利用此权力,“大淘宝”开始考虑自身的赢利模式,包括一系列的业务性收费和强制性规则。同时,“大淘宝”对于规则的设计越来越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越来越大。强制性网络权力的提升一方面强化了“大淘宝”在网络管理中强制执行的空间,提升了网络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部分的抱怨和不满。例如一位网店经理指出,“在阿里巴巴第一次的店家清退中,我们竟然因为属类问题被清退出了天猫平台…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花费了几十万,才再一次进驻”。由此,强制性网络权力的提升对于“大淘宝”网络创新行为的意义建构性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日益发展的生态体系为中小网商的成长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另一方面,过大的费用压力和维护成本大大挤压了中小网商的赢利空间。
从这一阶段的网络建构行为来看,由于网络拓展所赋予的日益增强的控制力及其对中小网商的约束,“大淘宝”的强制性网络权力得以进一步强化;柔性网络权力仍然在发挥作用,但相较于第一阶段效果略有减弱,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强制性网络权力所取代。由于“大淘宝”对市场把控能力的逐渐增强及其对网络生态系统的日益丰富化运作,其平台领导力得以显现。
3.“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拓展期。在经历了网络功能的丰富化之后,“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的第三阶段开始立足于新一轮的架构创新,包括物流骨干网“菜鸟”网络计划、余额宝、移动社交通讯工具“来往”、基于手机的在线网购平台“手机淘宝”、作为C2B(customer to business)先行者的“天猫预售”,等等。此外,“大淘宝”在这一阶段中所推出的“双十一”购物节活动较好地推动了平台的整体性升级。从网络建构的角度来说,这一举措至少在三方面使“大淘宝”受益:实现了很好的平台营销效果;进一步发展和培育了网购客户;更为最为重要的是,“大淘宝”通过此活动的展开对其平台的数据处理、信息沟通、物流配送等整个系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演练,显著提升了其大规模网购业务的综合处理与协调能力,实现了“大淘宝”、物流企业、网店、第三方服务商等不同角色之间的协同。
“大淘宝”在这一阶段的架构创新策略进一步强化了其强制性网络权力,特别是服务于全网的物流体系构建,无疑增强了中小网商对平台的非对称性依赖。同时,“大淘宝”在这一阶段利用其结构优势所开展的一系列创新行为,也再一次体现了其能力上的优势,特别是对于新市场领域和新服务模式的探索。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淘宝”的网络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而就“大淘宝”权力运用的意义建构性而言,则体现出了截然相反的趋势。换言之,“大淘宝”网络发展策略对于中小网商而言的意义建构性进一步降低了,主要体现在:其一,各种收费项目进一步增加再一次挤占了中小网商的利润空间;其二,整个平台上的超竞争状态使得中小网商难以获得快速成长的机会;其三,“大淘宝”的重心已经由网商的培植转向了自身势力范围的圈定。日益降低的意义建构性无疑会影响“大淘宝”企业间领导力的提升。为此,“大淘宝”在第三阶段主要通过对制度体系的建构来提升其领导力,即所谓的制度领导力。一是自身平台制度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对规则体系的修正和升级;二是共享的价值观和理念;三是参与行业标准和立法的制定。
(二)企业间领导力生成机制各要素的跨阶段纵向比较分析
1.创新模式。在第一阶段里,“大淘宝”的网络建构策略侧重于基础架构的搭建,力图通过全新的平台架构和服务体验赢得市场关注。这一过程中,推出了诸多架构创新,包括以网络评价和信用评级为核心的诚信体系、以支付宝为依托的网上支付体系、以免费为主要手段的营销服务体系等。这些架构构成了网商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成为“大淘宝”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在形成主体架构的同时,“大淘宝”也完成了功能性的模块创新,进一步拓展了“大淘宝”企业网络的服务承载能力。进入第二阶段,“大淘宝”架构创新的步伐有所放缓,对原有架构的升级工作主要包括“大淘宝”战略设计及天猫平台的搭建、基于O2O战略所推出的“淘一站”线下实体平台、致力于提升“大淘宝”综合信息处理与计算能力的阿里云等方面,而基于主体架构所开展的功能拓展成为这一阶段中“大淘宝”网络优化的主要手段。大量模块创新使得“大淘宝”在保持主体架构基本稳定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网络的综合服务和价值创造能力,同时,也为“大淘宝”在第三阶段升级主体架构奠定了基础。进入2011年以后,“大淘宝”开始将战略视角聚焦于新业务平台拓展,在原有基础架构上对“大淘宝”网络做了根本性的变革。相比较而言,“大淘宝”在第三阶段所开展的模块创新则明显减少,这主要源于第二阶段所开展的大量模块创新工作很好地丰富了企业网络的服务功能,同时也体现了“大淘宝”在平台构建策略上的战略性调整。
2.网络权力。与一般电商平台相比,“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在建立之初就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平台能力。特别是在投资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大淘宝”在营销推广策略和效果上明显优于同期其他对手,在构建有效的网上交易机制上也体现出了显著优势。这种能力上的优势使得“大淘宝”可以向中小网商施加积极影响,从而赢得中小网商的主动追随和遵从。
3.意义建构。在2003年淘宝网成立之初,“大淘宝”主要立足于新市场的培育,试图通过让更多的网上卖家赢利来形成流量优势。在这一阶段中,“大淘宝”采取了有效的网络构建策略,也推出了一系列让卖家受益的服务。而对于“大淘宝”本身来说,并没有过多考虑自身的赢利问题。正如马云所说,“你向每个会员收取费用,一定要给会员创造远远多于他付出的费用的价值,这是每个阿里巴巴人都应该牢记在心的”。显然,这样的做法对于“大淘宝”的伙伴企业具有很强的意义建构性,彼此之间在持续的互动中能够形成共同的认知和理解。进入第二阶段以后,如何丰富和完善已有平台、为网上卖家及配套服务商提供更多机会仍然是“大淘宝”重要的战略方向。而与此同时,“大淘宝”也开始考虑自身的赢利模式问题,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收费工具或规定。在这一过程中,过分地追求利益反而给网上卖家带来了较大的经营成本压力。相应的,网络构建行为对网上卖家而言的意义建构性也有所减弱,因为过分追求自身利益必然会降低有关企业间关系需求的共同认知,也不利于在网络拓展与协调上形成一致性认知。正因为如此,“围攻淘宝”事件才得以发生。而在第三阶段中,“大淘宝”网络拓展行为对于网上卖家的意义建构性进一步减弱。网络关系上的共享利益和关系性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大淘宝”的卖家很可能会因此而遭受较大的利益侵害。
4.企业间领导力。在第一阶段中,“大淘宝”企业网络正处于培育期,还不足以对网上卖家、配套服务商等形成直接影响,因此这一时期并不具备明显的平台领导力。而在技术层面,“大淘宝”通过推出网上支付平台和信用评级系统,很好地完成了对伙伴企业的引导和培植。实际上,网购平台本身的技术架构并不复杂,但信用体系、支付宝等关键业务相关技术架构的搭建,从根本上奠定了“大淘宝”技术领导力的基础。进入第二阶段后,不断增加的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使得企业网络架构日趋完善,对于网上卖家、配套服务商等伙伴企业的影响力也因此日益强化。基于“大淘宝”企业网络,越来越多的中小网商获得了经验和利润,也乐于追随“大淘宝”的战略步伐。此时,“大淘宝”所表现出的是平台领导力,即通过建构完善的网上交易平台并有效整合企业间网络信息与资源而形成的对其他伙伴企业的影响力。在第三阶段里,尽管平台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大淘宝”的网络管理与协调策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平台、规则、行为规范等诸多要素组成的系统共同作用于伙伴企业,由此形成一种制度性约束和影响。其一,平台作为基础保障支撑着伙伴企业之间的协调行为;其二,“大淘宝”所塑造的网络规则、规范与行为准则确保了稳定的网络关系并推动企业间价值共创。为此,这一阶段“大淘宝”所形成的企业间领导力可界定为制度领导力,即通过建构和利用网络制度来推动企业间价值协同创造而形成的对成员企业的影响力。
(三)结果讨论
核心企业通过网络构建来强化自身中心性位置、赢得控制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学界共识[49][34],“大淘宝”的发展历程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印证。网络权力作为核心企业赖以开展企业间管理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管理的方式和策略选择,这也是Dhanaraj和Parkhe(2006)[2]等研究的隐含假设。尽管网络权力并不具有与企业内部职位权力相类似的强制性,但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伙伴企业行为和网络价值分配[9]。基于此,“大淘宝”在初期采取了免费策略,借此大力提升其网络权力,当网络权力足够强大时,才开始引入赢利机制。从核心企业生成的角度来看,网络权力的提升是一个由能力向结构转化的过程,核心企业作为网络资源的整合者,在内部需要协调不同伙伴企业之间的利益,在外部则需要领导伙伴企业参与跨网络的市场竞争,能否具备较强的企业间领导力因此显得至关重要。类比于个体在企业组织中的情况,本文认为网络权力构成了企业间领导力的基础,“大淘宝”的经营实践也对此进行了印证。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大淘宝”还不具备足够的控制力,其网络权力相对较小,只能通过免费等方式来吸引潜在伙伴的加盟,所以在这一阶段,其企业间领导力还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随着平台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网络权力的提升,“大淘宝”逐步实现了对整个网络的控制,潜在伙伴也开始主动追随“大淘宝”的业务战略。此时,其平台领导力开始显现。进入最后一个时期,日益完善的平台制度体系赋予了“大淘宝”更加强大的网络权力,也使其逐渐体现出制度领导力。这里,从技术到平台再到制度的跃迁,体现了“大淘宝”企业间领导力边界的拓展,而非强度的提升。就观察的结果来看,“大淘宝”在其发展历程中并没有塑造出较强的非正式影响[12],其企业间领导力更多来源于正式网络权威和创新能力。
从另一方面来看,网络权力向企业间领导力的转化会受到意义建构的影响[6]。网络权力的使用只有在具有较强联合意义建构性的前提下,才能够获得伙伴企业的认同和追随,进而衍生出企业间领导力。就“大淘宝”的发展历程来看,意义建构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强制性网络权力的使用则日益频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大淘宝”已经牢牢把控终端网购消费市场,现有合作伙伴很难轻易脱离淘宝阵营;第二,悬殊的规模差异使得伙伴企业很难向核心企业发起有实质意义的挑战;第三,经营中的能力和资源惯性使得伙伴企业对“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产生了较强的依赖性。较低的意义建构性意味着伙伴企业与核心企业之间在诸多战略问题上难以形成一致的理解,核心企业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诉求势必引起伙伴企业的不满甚至叛逃。鉴于由此引起的潜在危机会一直存在,企业高层无疑应该提高警惕,并制定与采取预防性措施。
企业间领导力的生成不仅仅有赖于既定情境下的网络控制和价值共创,更体现在突破现有情境或制度束缚,为新业务的拓展赢得合法性,即非正式经济向正式经济的转化[50]。强势的核心企业往往能够将非正式经济正式化,为伙伴企业赢得新的市场机会,进而提升自身的企业间领导力。“大淘宝”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例如,原来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的余额宝,经过“大淘宝”的持续经营和广泛协调,成功演变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形式。非正式经济作为新的业务形式,充分体现了核心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将非正式经济转化为正式经济,再一次验证了核心企业的市场领导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非正式经济正式化彰显了核心企业的制度领导力。
五、结论与启示
核心企业到底如何获取网络权力并形成企业间领导力?“大淘宝”的发展实践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鲜活的实例。本文通过对“大淘宝”生态企业网络三个阶段发展实践的深入分析和纵向比较,揭示了核心企业网络构建中的创新策略调整、网络权力演变和企业间领导力生成的动态机制,明晰了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向企业间领导力转化的理论逻辑。探索性案例研究结果显示:核心企业在网络拓展中逐渐形成网络权力,这种权力会随着生态企业网络的发展而增强;过于强大的网络权力降低了核心企业行为对伙伴企业的意义建构性,进而影响到企业间领导力的提升。为此,核心企业只能通过正式权威的建立,分别在不同时期形成技术、平台和制度层面的领导力。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通过探索成员异质性在网络构建中的作用,拓展了企业间网络相关研究。本文从核心企业和伙伴企业之间的网络位置与分工差异出发,梳理和识别了成员异质性下企业的网络构建策略和地位变迁,能够对已有文献形成有效的补充和拓展。特别地,本研究强化了成员异质性所引起的位势差在企业间协调与信息分享中的作用,有利于深化Lipparini等关于核心企业与伙伴企业之间信息流动的相关研究[23]。具体而言,核心企业与伙伴企业之间的信息并非自由流动,而是会受到网络结构及地位差异影响,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会运用其能力或结构优势来干预网络信息流动。第二,通过剖析企业间领导力及其转化机制,发展了核心企业生成的相关文献。企业间领导力问题不仅凸显了网络成员特质作为研究对象的必要性,而且回应了近期有关对核心企业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呼声[49]。特别在核心企业生成的问题上,主流文献始终没能取得突破。本文有关企业间领导力的探讨,为理解核心企业从能力提升、规模扩张到地位演变的动态过程提供了一个替代性视角,有利于弥补当前企业间网络理论在论述非对称性问题方面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本研究揭示了为何某些企业在联盟或平台战略的实施上远胜其他企业的原因。
本文的结论对管理实践同样具有启示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为止核心企业在如何管理联盟网络的问题上还缺少可参考的理论,更多的理论解释都集中在信任、关系、契约等协调问题上。而实际上,大型企业高层对联盟网络的管理不仅是外部协调的问题,同时也是利用位置优势所形成的权力来开展管理的问题。网络权力在大型企业管理其联盟网络中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在更短的时间内、利用更少的资源来组织起有效的协作。然而,过分地透支网络权力有可能导致大型企业丧失其优质合作伙伴,从而在长期的联盟管理中得不偿失。此时,与伙伴企业协作以培育共享的战略体系或能力架构无疑能够促进企业间利益最大化。要想打造跨企业边界的整合性优势,大型企业需要培育自身的企业间领导力。为此,大型企业应更加关注伙伴企业的利益,发展包容性的协同战略,并将伙伴整合到长期发展的战略图景中。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仅仅通过单一案例对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及其企业间领导力问题进行了讨论,在理论归纳与构建上难免存在不足。进一步研究有必要通过更加多元化的经验分析来弥补这一缺陷。
[1]Capaldo, A.Network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The leveraging of a dual network as a distinctive relational capabilit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pp.585-608.
[2]Dhanaraj,C.,Parkhe,A.Orchestrating innovation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pp.659-669.
[3]Paquin,R.L.,Howard-Grenville,J.Orchestration blind dates and arranged marriages:Longitudinal processes of network[J].Organization Studies,2013,34(11),pp.1623-1653.
[4]Xia, J.Mutual dependence, partner substitutability,and repeated partnership:The survival of cross-border allia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pp.229-253.
[5]Ding R.,Dekker H.C., Tom G.Risk,partner selection and contractual control in interfirm relationships[J].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13,24(7),pp.140-155.
[6]Revilla,E.,Villena,V.H.Knowledge integration taxonomy 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Trade-offs between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12,140,pp.854-864.
[7]Li,D., Ferreira,M.P.Partner sel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4(1),pp.308-319.
[8]Shah,R.,Swaminathan,V.Factors influencing partner selection in strategic alliances:The moderating role of alliance contex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29(8),pp.471-494.
[9]Perrons,R.K.The open kimono:How Intel balances trust and power to maintain platform leadership[J].Research Policy,2009,38,pp.1300-1312.
[10]Diestre L.,Rajagopalan N.Are all ‘sharks’ dangerous? New biotechnology ventures and partner selection in R&D allia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33,pp.1115-1134.
[11]Shulman,J.D.,Geng,X.Add-on pricing by asymmetric firms[J].Management Science,2013,59(4),pp.899-917.
[12]郝斌,任浩.企业间领导力:一种理解联盟企业行为与战略的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1,(3):109-118.
[13]Uzzi,B.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pp.35-67.
[14]McEvily,B.,Marcus,A.Embedded ti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petitive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11),pp.1033-1055.
[15]Folta,T.B.Governance and uncertainty:The tradeoff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ontrol and commit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pp.1009-1028.
[16]Schreiner,M.,Kale,P.Corsten,D.What really is alliance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how does it impact alliance outcomes and succes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pp.1395-1419.
[17]彭伟,符正平.创业导向、双重网络嵌入与集群企业升级关系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3):71-80.
[18]Gulati,R.Alliance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pp.293-317.
[19]Powell,W.W.,Koput,K.W.Smith-Doerr,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pp.116-145.
[20]Zaheer,A.,Bell,G.G.Benefiting from network position:Firm capabilities,structure holes,and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5,26,pp.809-825.
[21]Katila,R.,Rosenberg,J.D.Eisenhardt,K.M.Swimming with sharks:Technology ventures,defense mechanisms and corporate relationship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8,53,pp.295-332.
[22]Vandaie,R.,Zaheer,A.Surviving bear hugs:Firm capability,large partner alliances,and growth[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pp.566-577.
[23]Lipparini,A.,Lorenzoni,G.,Ferriani,S.From core to periphery and back: A study on the deliberate shaping of knowledge flow in interfirm dyad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35,pp.578-595.
[24]Goerzen A.,Beamish P. W.The effect of alliance network diversity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erformanc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26(4),pp.333-354.
[25]Goerzen A.Managing alliance networks: Emerging practic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19,pp.94-107.
[26]Ibarra H.Network centrality, power, and innovation involvement: Determinants of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ol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3,36,pp.471-501.
[27]Astley W. G,Sachdeva P. S.Structural sources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A theoretical synthesi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1),pp.104-113.
[28]郝斌,刘石兰,任浩.企业间领导力理论和实践溯源与层次结构探讨[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5):50-59.
[29]Munari,F., Sobrero, M.,Malipiero, A.Absorptive capacity and localized spillovers:Focal firms as technological gatekeeper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J].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2,21(2),pp.429-462.
[30]Provan,K.G.,Kenis,P.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Structure,management,and effectiveness[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18,pp.229-252.
[31]Hitt M.A.,Ahlstrom,D.,Dacin,T.M.,Levitas,E.Svobodina,A.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strategic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China vs.Russia[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2),pp.173-185.
[32]Moore,J.F.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5,pp.75-86.
[33]Suarez,F.F.,Lanzolla,G.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cs in building a first mover advantage theory[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2),pp.377-392.
[34]Sydow,J.,Lerch,F.,Huxham,C.Hibbert,P.A silent cry for leadership:Organizing for leading (in) clusters[J].Leadership Quarterly,2011,22,pp.328-343.
[35]Oliver,C.Determinan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grat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0,15(2),pp.241-265.
[36]Hogg,M.A.,van Knippenberg,D.,Rast,D.E.Intergroup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Leading across group and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2,37(2),pp.232-255.
[37]Eisenhardt,K.M.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pp.532-550.
[38]Pettigrew,A.M.Longitudinal field research on change:Theory and practice[J].Organization Science,1990,1(3),pp.267-292.
[39]Dyer,W.G.,Jr.Wilkins,A.L.Better stories,not better constructs,to generate better theory:A rejoinder to Eisenhard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3),pp.613-619.
[40]彭新敏,吴晓波,吴东.基于二次创新动态过程的企业网络与组织学习平衡模式演化——海天1971~2010年纵向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4):138-149.
[41]Yan,A.,Gray,B.Bargaining power,management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United States-China joint ventures:A comparative case stud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6),pp.1478-1517.
[42]Laamanen,T.,Wallin,J.Cognitive dynamics of capability development path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9,46,pp.950-981.
[43]Henderson,R.,Clark,K.Architectural innov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 35(1),pp.9-30.
[44]Miles,M.B.,Huberman,M.A.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An Expanded Sourcebook[R].SAGE, Thousand Oaks,CA,1994.
[45]侯杰,陆强,石涌江,戎珂.基于组织生态学的企业成长演化:有关变异和生存因素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1,(12):116-130.
[46]Ring,P.S.,Van de Ven,A.H.Developmental processes in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1),pp.90-118.
[47]Glaser,B.G.Strauss A.L.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Aldine Transaction,1967.
[48]杨文明.互联网平台企业免费定价反垄断规制批判[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1):104-113.
[49]Müller-Seitz,G.Leadership i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A literature review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2,14,pp.428-443.
(责任编辑:闻毓)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Power and Inter-firm Leadership in the Process of Network Building ——A Case Study of the“Big Taobao”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WU Yun-qiao1,HAO Bin2
(1.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200083,China; 2.Business School,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Big Taobao”ecological network,this study explores hub firms’ power and inter-firm leadership in the context of inter-firm networks.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types of network power are formed from the extension of inter-firm network: structure-driven power and capability-driven power;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firm network,structure-driven power and capability-driven power firstl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with a subsequent tendency of co-evolution, thereby maintaining the efficacy of the inter-firm coordination mechanisms;network power lowers the effect of joint sense-making between the hub and partners,thus affe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firm leadership;consequently,the hub firm has to foster technological,platform,and 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in different phases by introducing formal authority.By extending literature of network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hip asymmetry,this study helps to enhance the explaining power o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heory which was originally built on the basis of symmetric network structure, and contributes to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nter-firm relationship under asymmetric network structure.
inter-firm network; hub firm; network power; inter-firm leadership; business ecology
2016-04-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15ZDA0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71102067)
吴昀桥(1984-),男,湖北公安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博士;郝斌(1981-),男,安徽安庆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
F270.7
A
1004-4892(2016)11-008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