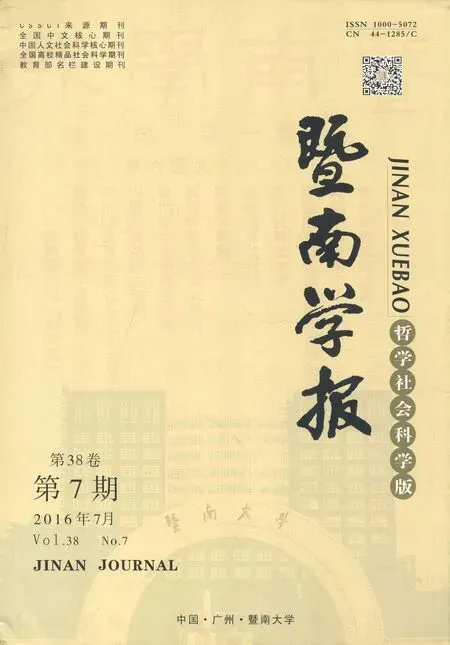主体间诗学: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特质
王毓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东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海外中国学】
主体间诗学: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特质
王毓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东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主体间诗学。研究者既没有把刘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视作一个完全异己的、另类的他者,也没有以本体地位自居,俯瞰它,而是高度尊重并认同它的身份,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把它视作另外一个话语主体,并基于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主要采取边译边释的话语方式,以另一主体的方式与其进行平等对话。双方话语之间真正的意义和交织,不仅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性和类似,而且在于它们之间的比较,也即发现每个传统内相对于另一个传统的差异性,其最终目的和意义是理解而非判断对方。
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主体间诗学;他者
日本是海外《文心雕龙》研究大国。尽管中日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它们都同属于汉文化圈。因此,若从直接的历史文化渊源上进行身份认同,严格说来,日本不是中国的他者。与之相反,那些不属于汉文化圈的国家或民族、文化就是中国的他者。其中,比较热衷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心雕龙》研究,且成果较丰硕的国家是美国。美国《文心雕龙》研究者的身份大体有三类:一是华裔美国人;二是美国本土人;三是汉文化圈以外的美籍外国人。很显然,只有后两类是中国文化的他者。他们的《文心雕龙》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
此类研究的数量虽然不多,但特色鲜明。从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它始于20世纪,大致可以分为40年代之前、50—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很零碎,主要包括在人们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中,戈登(Erwin Esiah Gordon)1945年完成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论文“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早期观念”最具代表性,其中的第三章专论刘勰及《文心雕龙》;第二个阶段出现了以《文心雕龙》为专题的论著,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1970年完成的华盛
顿大学博士论文《〈文心雕龙〉里的文学理论》最具代表性;第三个阶段的成果较多,皮特·威(Peter Way)1991年完成的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中国和欧洲的古典主义:亚里士多德〈诗学〉与刘勰〈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以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92年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学思想解读”具有代表性。后者翻译并解读了《文心雕龙》里的 18篇。本文拟主要通过对上述各阶段代表性成果的分析,探讨美国《文心雕龙》研究的跨文化特质。
一
他者是相对另一个主体而言的概念。无论是从客观现实、历史文化渊源,还是身份上来说,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于美国人都是一个外在的、遥远的、陌生的他者。然而,他们并没有把它视作完全异己的、另类的东西,更没有敌视、排斥它,而是以巨大的热情和宽厚的胸襟尊重、包容它,并努力尝试理解、欣赏它。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对《文心雕龙》所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品质的认同上。
由于繁多的版本、骈体古语等因素,中国人读《文心雕龙》尚且有一定难度,何况汉文化圈外的他者!因此,戈登感慨,20世纪40年代,用西方语言撰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论著非常匮乏。存在于中国这个史料里的大量内容仍然没有被系统整理,该领域研究尚处于早期。这对那些想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外国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文学领域,刘勰的著作不为人们所知。对此,吉布斯在其论文“导论”里分析指出,这部分原因是由于中文及《文心雕龙》本身之于他者是个挑战。首先,正如许多中世纪文本一样,《文心雕龙》不是一个“完美”的文本。漏字、误字、个别句子晦涩,不常见的典故和不熟知的人名,以及骈文形式都给阅读带来了困难;其次,许多章节之间缺乏连贯性,有的甚至矛盾。最后,与之交流最大的障碍是其所使用的特殊术语。它们隶属于一个更大的、不同的整体思想系统(即中国文化),于是他者很难对其作出判断。皮特则从自身寻找原因,在其论文最后总结部分,他认为,即使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文心雕龙》研究依然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对其进行跨文化研究——如果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人们首先固守的是民族中心论和少见的超越原因和结果概念的文学影响论,以及类似的主题平行论。
从实际研究情况来看,对《文心雕龙》进行身份认同,找到一个能允许他们与之平等对话的平台,是美国人不畏艰难开始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首要任务。虽然戈登没有明确说明,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研究刘勰的。因为他最早把刘勰与亚里士多德并提,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文论是“最深刻的文学哲学”,它的存在使中国文学(也许世界文学)显得更辉煌。戈登之后,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形成了一大传统:大凡研究刘勰,几乎无人不提亚里士多德。
宇文所安、梅尔(Victor H.Mair)、迈尔(Victor H.Mair)、普拉克斯(Andrew H.Plaks)等都程度不同地对二者进行了论述,皮特更是直接以此为研究课题。与戈登相比,吉布斯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论证了对话平台之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博士论文“第一章”里,他在指出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所面临的困境的同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遵循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里所说并实践了的“一个对话平台”(a single plane of discourse)的理论和方法。此平台就是世界艺术理论。吉布斯明确声明,他研究《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力图显示艾布拉姆斯理论的实用性和普遍性,最起码能把《文心雕龙》这个中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论著,以及中国文学思想和欧洲文学思想,如艾布拉姆斯所希望的,带到一个世界艺术理论的对话平台上”。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艺术理论”里的“艺术”是包括“文学”在内的西方传统上美的艺术概念。他解释道,他之所以不直接用“文学理论”而用“艺术理论”,是因为他的研究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以及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和发现,尤其是他不断从过去的18世纪美学看浪漫主义美学,描述英国批评理论和外国思想之间的关系,追溯各种批评观念和美学思想的起源,目的是通过广泛深入的比较,强调以英国为中心的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在整个世界文学批评史上的枢纽地位。吉布斯非常推崇艾布拉姆斯所说的这个广阔平台。在博士论文里,他完全采用艾布拉姆斯从世界艺术理论里总结出来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分析《文心雕龙》,并主要以刘勰对文学的态度,即实用和美学关怀为切入点,将他与柏拉图、朗基努斯相对比,在整个人类范围内高度评价刘勰,指出:“作为文学理论家,刘勰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古典时期世界的伟大理论,尤其是由于刘勰,我们有了人类天才关于‘适应’(adaptation)原则的智慧之花——他从过去文学中抽绎出来,并在《通变》里建构起来的。”
戈登、吉布斯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具有示范作用。其后,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些程式化的东西,诸如平台、基本思想、基本思路以及基本视域等。人们往往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认同刘勰,不断从哲学、艺术,尤其是美学视域审视他,并在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世界其他艺术理论家的比较中考察他,认为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是世界艺术理论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除皮特外,标题里点明对刘勰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非常罕见,但是,研究者特殊的身份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比较的不可避免。除亚里士多德外,人们还普遍将刘勰与柏拉图、朗基努斯等西方著名的艺术理论家相比较。如解读《物色》篇时,通过与朗基努斯崇高理论(尤其是他对萨福抒情诗的评论)、黑格尔语言观,以及席勒“素朴的诗人”观点的比较,宇文所安阐释了刘勰有关语言为情感的外物的思想。罗纳德·伊根(Ronald Egan)则在与柏拉图的幻影(illusory images)、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复制图像(reproductive images)、文艺复兴时期的低级摹仿(inferior counterpart to imitation)、浪漫主义时期的灵感(spiritual sensation),以及现当代的直觉(intuition)、精神表现(psychic expression)、心理迹象(mental sign)和符号(symbol),这些西方传统上内涵
复杂多变的概念相比较的过程中,阐释了刘勰的“神思”概念。至于那些聚焦于探讨刘勰与其他学科关系的学者,也是在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从事他们的研究。例如,刘勰与佛教关系是世界“龙学”研究里的一个经典话题。美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跨文化研究特色鲜明。他们不是仅从印度和中国大的历史时代背景或其他人的论著出发,论证刘勰及其著作所受佛教影响,也不是仅从《文心雕龙》文本中摘出个别语词,考证它们是否是佛教用语,而是在世界艺术理论的平台上,或者像戈登、吉布斯一样,比较考察佛教影响下的刘勰文学思想、方法和写作技巧;或者在深入解析印度诗学和《文心雕龙》的基础上,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如迈尔(Victor H.Mair)在《〈文心雕龙〉的佛教》一文里,首先对世界范围内有关《文心雕龙》与佛教问题的主要论著进行了评论,然后把深受佛教影响的印度诗学与《文心雕龙》相比较,原创性地提出了“《文心雕龙》里的印度原型”说法,并认为佛教在《文心雕龙》里起着重要作用,这不在于刘勰所使用的个别佛教术语,而在于他的思想模式和系统性的组织方法。尤其是在论述《文心雕龙》与印度诗学之间的关系时,迈尔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佐证的。
在与世界其他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中,美学始终是人们在此平台上审视《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视域。例如,皮特明确从美的艺术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刘勰对文学形式的系统论述及其所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与亚里士多德的形成对照。前者通过暗示表明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有关系,后者则明确在艺术的逻辑分类里(如绘画、音乐等)区分了文学。于是,二者在方法论和批评视角上存在着差异:刘勰关注文学的美学性质,亚里士多德关注艺术行为——摹仿。与皮特相比,宇文所安则直接用美学思想或理论进行批评,如他认为“章句”篇里的“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是刘勰的整体结构模式,与亚里士多德基于各个相互需要的整体概念相比,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模式,类似西方美学里“多样统一”思想,尤其贴近浪漫主义的有机理论。
二
一个共同、稳固的平台之于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旦承认《文心雕龙》是美的世界艺术理论里的一部分,研究者就不再把它视作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者,而是另外一个与自己相对的“你”了。一个和他们已经熟知的世界其他艺术理论相似的存在者,一个分享或部分分享他们自己文学或世界其他文学特征的文学文本。于是,出现了歌德所说的“两个主体”:一个是作为第一意识主体的“研究者”,另一个是作为第二意识主体的“别人的话”,即《文心雕龙》。它不是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单纯的物,而是另一个有意识的主体。作为说话者,它总是在言说,并向
一切人或文本敞开。因此,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本质上是两个主体间的对话行为。这种对话总是由于彼此之间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而交织在一起。这集中体现在研究者总是就世界艺术理论里最具普遍意义的东西,与《文心雕龙》展开对话。
世界艺术理论形形色色、纷繁复杂。“一个事实是许多艺术理论一点都不容易比较。因为它们缺乏一个能相遇并碰撞(to meet and clash)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于是,如何找到一个像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非常简单,易于操作,但却非常灵活的参照框架(a frame of reference),从而不会过度歪曲任何一种艺术理论,它将在一个单一对话平台上(a single plane of discourse)尽可能多地被转化为多种形态”,便成为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任务。在博士论文“导论”里,吉布斯对此有专题性论证。他赞成艾布拉姆斯四要素观点,并以此为工具分析《文心雕龙》,认为艾布拉姆斯从世界艺术理论里区分出来的这四种基本要素,即“作品”(work)、“作家”(artist)、“观众”(audience)和“宇宙”(universe),也存在于《文心雕龙》中。正是这种“普遍性”(literary universa),吉布斯进一步举例解释说:一方面使他易于发现《文心雕龙》与世界其他文学理论之间哪里一致,哪里不一致,甚至问题的症结是什么,理解了《文心雕龙》中一些对他者来说,似乎是模棱两可或矛盾的东西(主要由误字、漏字现象导致);另一方面使他发现了刘勰批评的主要倾向(即实用而非表现),明白了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主要贡献。因为普遍存在于《文心雕龙》和其他世界艺术理论中的这四个基本要素,既奠定了它们之间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也避免了对话中的任何一方把自己的哲学强加于另一方”,从而使二者之间平等的对话成为可能。吉布斯把这种研究称为“客观的《文心》研究”(objective Wen-hsin studies),并声称,毫无疑问,它会使一般世界文学的研究者看到,刘勰是一个重要的具有广泛理解力的严肃批评家,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不是超出世界文学范围之外的另类。
吉布斯治学理路和研究方法,以及得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影响了后来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者。大多数人都在论著里直接或间接引用他的言论,或者继续深入研究他曾经探讨过的一些问题,如皮特、宇文所安进一步阐发了他有关刘勰诗学的实用性、“通变”等思想,安特耶(Antje Richter)接受他关于佛教影响刘勰“孝”的观念思想,撰有《空梦及其省略》一文。当然,对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吉布斯所继承并实践的艾布拉姆斯“四要素”的治学理路,即基于世界艺术理论里一些普遍存在的因素展开研究。例如,皮特和安特耶聚焦“作品”研究体裁,宇文所安从“作品”与“读者”关系出发解读《文心雕龙》,罗纳德·伊根(Ronald Egan)就“作家”与世界关系探讨“神思”等。20世纪后期,以皮特为代表的一些人看似另辟蹊径,但其实质与吉布斯“普遍性”思想一脉相承。如在其博士论文“导”论里,皮特从语言的视域认同中国文学,区分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认为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学批评都属于文学话语。他明确论证指出:“绝大多数印欧语言借助于一些形态模式区分名词和动词音素,中文并不代表一个基本源自其不同历史事实的另类。……如果文学不仅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事实,而且是语言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性质将独立于任何个别的历史。呈现于中西两个最具历史独立性的文学之间的有关形式、观念和价值的批评,将最能揭示文学作为语言历史的本质因素。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批评和欧洲批评都区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而且在文学话语内部,同样的术语被用来表示独立的文学历史事实。”于是,它们之间便有了可供比较研究的共同基础。皮特进一步论证说:“如果不顾它各种差异的历史,考虑到世界——用维特根斯的话来说——作为各种事件的总和,文学也是作为其中客观真
实存在的事件的一种形式,那么,各种文学就具有某种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可限定的性质”,继戈登简短评论之后,皮特在世界艺术理论研究范围内最先系统比较研究了刘勰《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诗学》,并在追溯柏拉图、郎基努斯等世界主要美学理论家思想,以及分析世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实用主义、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同时,首次使用哲学话语、辩证的话语、批评话语和文学话语等概念,探讨了以二者为代表的中西古典主义诗学的特质及其在世界艺术理论史上的地位。他之后,普拉克斯、宇文所安也主要聚焦于话语层面考察《文心雕龙》。如后者曾明确宣称,对刘勰的论证,我考虑的不是已经完全成型并固定的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对此的加工处理,也即作为表达者的骈文修辞。这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话语机器”,它通过它本身的规则和需要言说。《文心雕龙》是表达者刘勰与骈文之间的对话。
而从“四要素”、“文学话语”类普遍存在于世界艺术理论里的基本因素出发,人们不难发现《文心雕龙》属于世界艺术理论里的一部分,它与世界其他艺术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性。例如,吉布斯研究证明:“宇宙论既是刘勰文学起源也是他文学理论的基础。他在《原道》篇里有关‘光’等的隐喻,我们在艾布拉姆斯提到的欧洲浪漫文学批评家或世界早期批评家那里也能看到类似说法”。宇文所安亦认为,《文心雕龙》的修辞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诗学》,以及其他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些文本。而中西传统文学思想的共性更多表现在文学作品与文学思想之间不是一种简单,而是一种张力关系。皮特在博士论文的“导论”里甚至认为以刘勰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中西古典主义诗学在方法和思想方面存在着“同源性”(homologies)。他论证道,刘勰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有关文学性质和功能等基本问题,代表着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复杂形式。他们经常不仅用同样术语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提供了同样答案。尤其是双方各自代表的中西古典主义揭示了二者在方法和思想方面的同源性。正是基于这种‘同源性’,我们才能着手界定并分析它们各自代表的文学批评”。皮特进一步举例展开论述道,刘勰文学进化概念令人惊讶地契合亚里士多德对同一问题的思想,即文学史揭示了一个目的性的发展。刘勰最早共时与历时地详细分析了文学体裁,这可以与亚里士多德有关喜剧和悲剧体裁发展与演化的讨论相比较,双方都把他们各自尊重的体裁置放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它们发展中的革新或与过去的接合。《诠赋》里刘勰对赋的论述,是他分析体裁历史演变的最好例子。这最易于与亚里士多德对“喜剧”和“悲剧”术语的起源与演变所做的分析相比较。
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所以,有人怀疑刘勰熟悉亚里士多德。皮特在博士论文里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以刘勰、亚里士多德都在形式和历史之间,分别对赋、喜剧和悲剧的考察为例,分析指出:这是因为文学有它自身内在的原则和结构,如果批评家尊重文学话语事实,他们往往会对同一问题采用同样方法论述或得出同样结论。
三
然而,探寻“普遍性”或“同源性”只是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一方面的内容,其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辨别差异性、揭示独特性。而且,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吉布斯在“导论”里公开宣称自己的博士论文是“推进探寻分享一个共同基础的各种理论内部的差异性的一个初步的尝试”。依他之见,“比较方法最重要的用处是发现任何艺术理论里的独特性(没有比较,就不能发现独特这一品质)”。皮特不仅明确指出,《文心雕龙》与世界其他文学思想之间“真正的意义和交织,不仅在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源性和类似,而且在于它们之间的比较”,而且进一步引法国学者于连(Francois Jullien)评论《文心雕龙》时提到的差异性“alterite”观点论证说,这种“比较”的性质和意义就在于“发现每个传统内相对于另一个传统的差异性”。“若在《诗学》和《文心雕龙》两部文本所使用的术语内进行比较,则以二者为代表的欧洲和中国文学传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不明显的相同性”。总体来看,美国跨文化研究所探寻到的这种“明显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历史文化与批评话语
无论具体研究对象是什么,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每个研究者几乎都对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有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这种被吉布斯称为“充分背景”(sufficient background)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文心雕龙》不是在任何诗学影响下产生的衍生物或派生物,它有自己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和传统。在博士论文里,吉布斯和皮特都两章,专门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前者重点探讨了六朝之前的中国古典诗学和刘勰生平,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植根于自己特殊的文学历史,面向过去特殊的作者,指导自己当代及未来文学,所有这些都是其内在固有的趋向”;后者主要论述了《文心雕龙》与中国古典主义、批评传统,认为《文心雕龙》与《诗学》“是两部杰出但拥有完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的文学批评著作”,它们表明“存在着中国和欧洲两个独立的文学传统”。
这种“独立”性鲜明体现在中西批评话语的差异性上。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辨性西方批评话语相比,皮特在“导论”里明确指出,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学批评话语是一种个性化的、具有多重所指的、隐喻的“文学话语”,一方面“中国文学思想以一种带有鲜明个人色彩和悦耳声音的文学批评话语呈现出来,这与西方的非个人的话语形成了突出对照。刘勰呈现出来的批评性质的文学话语魅力,我们在亚里士多德话语里鲜能看到”;另一方面“刘勰的隐喻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形成鲜明对照,结果,精湛的思想和批评经常似乎由于它们的表达而变得歧义”。宇文所安亦认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一个品质是一个术语几重所指,这常常造成了一些无法解决的困难。”
(二)术语及思想观念
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家怀素(Haun Saussy)以《原道》篇“文”为例,认为“雄辩、微妙并融合着语源学热情和交感想象的术语,是导致20世纪欧洲人和美国人喜爱中国文学的原因”。的确,术语是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重心。大多数人都对“文”、“道”、“诗”、“赋”、“神思”、“风骨”等刘勰所使用的主要术语,以及由此表达的相关概念、范畴和思想等有程度不同的分析,尤其是单篇论文,基本上都是以此为题,诸如安特耶的(《〈文心雕龙〉“书记”概念》)确良、普拉克斯的(《〈文心雕龙〉“骨”的骈俪修辞》)、吉布斯的(《中国文学批评里的术语“风”》),以及伊根的(《诗、心和世界:“神思”反思》)等。而由考察术语深入到理论探究是他们惯有的思路。例如,戈登整个硕士论文就是由对“文章”、“文”、“学”、“教化”等术语的分析开始的,他明确指出:“分析术语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因为语词构成了理解人们思想和概念的基本媒介,术语毫无疑问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因素。”吉布斯也如此。基于刘勰有“自己特殊的表达思想的术语集”的认识,他的很多研究都是由解析术语开始的,如他对刘勰创作论思想的论述,就是由深入解析“情采”、“气”、“志”、“才”和“神思”等术语入手的,而他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阐释则是基于对“风骨”一词的剖析,认为“刘勰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复杂的中国美学术语词汇”。
至于他们由此所揭示出来的中西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性则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基本的,如皮特认为:“中国和欧洲文学的基本差异是,孔子及其之后的刘勰明确把诗歌视作最完美的语言,而柏拉图及其之后的西方传统哲学倾向于把依据真理的辩证话语置于文学之上。当刘勰谈论完美语言时,毫无疑问,他正谈论文学”;有些是特殊的,如吉布斯认为“神思”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内,“通变”观念独特。宇文所安和皮特亦赞同他的这一看法,后者解释道:“据我所知,在索绪尔现代理论(即形式主义地考察艺术置换和传递我们现实的能力)诞生之前,西方文学批评里没有与之等同的概念。社会的基本问题是转换或文化革新的需要,它的演变是通过文学的(艺术的)持续革新,这是我们在中国批评里发现的最特别最深刻的观念。”
(三)功能、原则和方法
不同社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导致了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学独特的一些功能。如吉布斯论证说:“从最初的中国文明开始,文学与政府和政治就有着不寻常的密切关系。中国文人是官员,或至少被训练成官员,政治权力的中心通常也是文学作品和品鉴的中心。政府选择文人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中国文学的时期经常与政治时期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文学缺乏独立的地位,它服务于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即所为政府的附属品。当然,人们主要根据它的实用功能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人们更多关注它服务的、交流的功能而不是美的。”皮特亦持有类似观点,认为以刘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原道”思想暗示了文学只是一种传递道德、政治或宗教的手段。
与这种特殊功能相配套的是一些特殊的文学批评原则和方法。早在20世纪40年代,戈登就
对此有所探讨,他议论道:“人们经常说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有意义的贡献,或许不是他一两个具体的发现,而是他所建立的一个探索人类文明成就的系统方法。以此类推,人们今天之所以还记得刘勰等中国早期一些批评家,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提出了一系列文学评价的原则和方法,为后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皮特继而在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诗学的比较中,展开探讨了刘勰易于在美学秩序和最高的现实“道”(人们认识到的时间的和空间的)之间类比推理的方法,以及分析文学与音乐关系时所运用的主观与客观结合的方法。尤其是以大量实例探讨了刘勰分析体裁的方法。如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直接谈论文学中的共时和历时因素”。而刘勰在《明诗》篇最后对诗有这样的综述:“同时高度密切关注文学的共时和历时因素,是批评分析的范例,具有方法论上意义,是任何整体批评的前提,甚至今天,这一观念的意义在比较研究中也只有一半被理解。”
四
对差异性的强调与深入探讨,充分证明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者对他者的尊重——他没有以本体地位自居俯瞰《文心雕龙》,从而忽略、低估甚至贬损它,而是把它视作有内在的、固有的规定性和文化传统的另一主体,以另一主体的方式参与到与之的对话中。从他们对物质化文本《文心雕龙》的态度和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这一点。
几乎对《文心雕龙》有过专题性研究的人都兼具译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无论具体对象是什么,无论采取何种方法,他们的研究都是从翻译并且细读《文心雕龙》文本开始的。例如,四位重要研究者,即戈登、吉布斯、皮特和宇文所安都翻译并详细解读了“原道”和“序志”篇,此外,吉布斯还基本细读了《风骨》和《通变》篇,皮特和宇文所安翻译并解读的数量更是多达7篇以上。与一般译者相比,他们的翻译是有针对性的,也即当他们研究的问题涉及哪一篇或某段文字,他们就翻译之。例如,安特耶两篇论文分别探讨文学体裁“书记”以及刘勰的写作动机,与之相应,她便翻译了《书记》和《序志》篇。同样,为探讨刘勰关于创作思维、对偶问题,伊根、普拉克斯分别翻译了《神思》、《丽辞》篇。在有英译本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做法既出于对《文心雕龙》独特性的高度尊重,也是为了能更深入、内在地相互了解。如吉布斯明确指出:“刘勰的批评判断和描述,是以中国惯有的、和谐的修辞形式呈现出来的,作为一种客观研究,这些必须被视作物质信息,且要求我们必须广博且尽可能仔细地阅读刘勰的文本。”皮特亦从语言角度论证说:“文本的意义取决于上下文的逻辑,语言固有的这一基本品质在古典骈体韵文结构里体现得更强烈。与古希腊和拉丁文学批
评文本相比,上下文的顺序在古汉语中具有更多意义。”因此,如果“聚焦于对《文心雕龙》和《诗学》所代表的中国和欧洲传统内那些最有意义、最有力的批评进行比较,力图提出存在着两个批评思想和方法。这种并置对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最高要求,即彻底重新细读两部文本。”
于是,宇文所安所倡导的“力图展现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便成为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共识,而其手段就是边译边释。且不说宇文所安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解读中国文学思想》,就是伊根、普拉克斯和安特耶等的专题论文,以及戈登、吉布斯和皮特的长篇学位论文,莫不主要以解读的方式出现。这种批评话语的特征主要有三:
1.解释的客观性。文本的翻译内在于研究者的论文而不是游离在其之外。他们通常是先翻译一小段,然后便从对字与句的训诂、词义的辨析,以及意义的解读开始剖析之,类似中国传统上对经书的注疏。尽管他们往往在广阔的世界艺术理论平台上展开这种分析,但是,文本的翻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他们分析的客观性。吉布斯明确宣称自己的研究“不是高度主观性设计的美学评估,而是客观文本分析”。皮特和宇文所安等都认同吉布斯所说的这种“客观研究”。宇文所安认为这种“客观的文本分析”迫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是试图证明一个先行的观点,而是分析手头上物质化的文本,看看它会产生什么结果”。于是,我们发现他们的研究论著大都属于细读文本类,其间鲜有纯主观的空泛议论。即便是按某种分类分析刘勰的思想,他们也往往在文章里作出明确说明。如当吉布斯从“写作背景”、“创作经验”以及“准备和写作问题”三个方面阐释刘勰“神思”理论时,他特意点明,这是他为了论述方便起见划分的,不是刘勰。
2.比较。没有什么比翻译更能显示出两种语言意义之间的界限。而语言的边界即是思想的边界。在论述刘勰本人可能翻译佛经时,戈登指出:“可以想象,翻译另一种外语会给他提供一个更广阔的比较文学的视角,便于他证实他有关文学‘普遍性’的思想。”同理,翻译《文心雕龙》使得他们常常不得不比较。如吉布斯在翻译《风骨》篇里的“风”时说:“英语里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传达刘勰所说的‘feng’。这要通过比较的洞察才能判断。”安特耶甚至以这种比较为目的。她声明,她依据自己的理解重新划分了《书记》篇句段和文本结构,目的是便于在翻译和原文之间比较。在对该篇开头一小段翻译之后,她分析道:“刘勰在此引用《法言》中语,最好说明了书记是一种个人信件的写作体裁。因为对西方书信文学学者来说,古希腊人关于书信的惯用说法,即书信是灵魂到心智的形象或镜子,是保留至今的西方书信理论的核心要素。”与安特耶的认同感相反,宇文所安则认为:“不像系统性论述,解说方式不断强迫我们尊重刘勰文学话语范畴和我们的差异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处,宇文所安明确提出了“尊重差异性”(to honor the difference)。
3.对话性。无论“证实文学的普遍性”还是“尊重差异性”,这种跨文化的比较都是一种典型的、双向对话活动。因为当人们立足于语言本身内在的现实,特别是聚焦于探讨原文和译文各种成分之间的语言对应时,他们的思想不得不往来于二者之间:斟酌字句、作出选择。在这种双向性的对话活动中,主体(即译者)“目既往还,心亦吐纳”:一方面要认真倾听并尊重另一主体(即原文)的言说,另一方面要在自己语言中积极寻找恰当的语词应答。于是,两个主体内在地、潜在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既基于他们之间的相同性,也出于彼此的差异性。这是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翻译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其研究的最显著特色。
因此,我们以上分开论述的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里的两方面内容——认识普遍性、辨别差异性,在实际的研究论著里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在谈到文学起源问题时,刘勰和亚里士多德不仅都通过逻辑分析认同文学的属性,而且论证都用最抽象的术语。前者首先以严格说教方式,把它归于天才—艺术领域,然后再对其进行逻辑分析,后者虽然不是直接论证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但是,正如刘勰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里也暗示了这样一个大的最高秩序概念”。此段话里,刘勰与亚里士多德之间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我们很难将其分解开。研究者通常或者在发现相同性的同时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如宇文所安有“既然假定的世界次序和阐释它的语言优先是由对偶构成的,那么,话语机器的任务就是解析之。在这一点上,它(按:刘勰话语)与亚里士多德的话语相当相似:同样基于自然逻辑。其论辩程序本身是思想的形式,而非仅仅只是思想的表达。……尽管刘勰的‘辩’比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具有更多的语义学内容”之论;或者在相同性的基础上发现了双方的差异性,如吉布斯在肯定刘勰文学理论与世界其他一些艺术理论一样,也存在着实用性问题之后,主要探讨了刘勰对文学实用性关怀的独特方面,如追求论争力量的写作意图、超文学之外的作家及其表现的关怀等。
批评话语中被比较双方之间相同性与差异性的交织,从另一个方面彰显了作为他者的《文心雕龙》在美国跨文化研究过程中的价值。正如镜子一样,它的存在既有助于研究者反观自身,也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洞察世界其他艺术理论。如在对以刘勰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中西古典诗学比较研究之后,皮特认识到:“从《文心》和中国诗视角审视,则欧洲诗学存在着一个基本裂缝。亚里士多德忽视了抒情诗传统或只把它作为一种早期未发展的叙事形式解释它。很明显,这不是因为希腊诗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没有发展成一种完美复杂的抒情传统,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不能把抒情声音从叙事中识别出来。结果,欧洲批评整体上人为地区分出了虚构与非虚构,从来没有真正处理抒情诗的理论问题。与之相比,中国批评,尤其从《文心》可以看到,基本聚焦于抒情诗,从没有把它孤立出来,或分析情节因素、时间和特征,尽管从汉代开始中国诗发展出了一种复杂、成熟的叙事模式。”当然,借助于世界其他艺术理论这面镜子,研究者亦更好地发现了《文心雕龙》的价值。如皮特认为:“在松散、缺乏批评的印象主义式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语境中,《文心雕龙》的性质和它的一些论点不为人们所知,然而,当与《诗学》以及现代欧洲形式主义里那些精确和形式主义的论点并置在一起,它们就突显了。”因此,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两个话语主体地位平等。双
方各以对方为镜子,既发现对方,又反观自身。二者之间不仅不存在孰高孰低或孰优孰劣之分,而且,“只有借助于比较中另一方详细的历史和美学的批评之光(the critical light),每个传统才能被考察,文学批评需要这种历史和美学事实的比较,达到它的目的”。否则,“我们既不能理解欧洲批评传统也不能理解中国的。孤立起来看每个传统,我们只能一知半解”。
这种双方各以对方为“批评之光”的思想,鲜明地昭示出了美国跨文化《文心雕龙》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意义。这就是理解而非判断。因为“只有当我们同时看到他者的独立和差异性时,其文学事实和理论才能变得完全被理解”。正是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人们抱怨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所指多重、概念模糊时,宇文所安议论道,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每个传统都有它自己伟大的概念体系力量。双方都是正确的。在上下文的解说过程中,比较是难免的,但其目的是寻求理解而非比较价值:每个传统遵循它自己的一套理论,并试图用以阐释一个与他者完全不同的文学文本传统。同样,基于理解而不是苛求或评判其优劣高低,有的学者提出了从文本出发的物质化标准,如安特耶指出,“一般来说,《文心雕龙》整体上术语模糊阻碍了人们对文本的充分理解。然而,至少就第25章而言,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责备刘勰”;有的学者甚至为刘勰辩护,如皮特指出:尽管刘勰的语言与推理经常令他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坚持认为,刘勰的批评思想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一样,是连贯的、可理解的。……所有传统里最好、最伟大的思想家,往往能超越其文化的局限。很显然,这种努力尝试以理解为最终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当然不是一种排他的诗学(exclusionary poetics),而是一种相互包容的主体间诗学(intersubjective poetics)。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I206.2
A
1000-5072(2016)07-0049-12
2015-09-16
王毓红(1966—),女,安徽芜湖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西方人文学研究”(批准号:GD14WW1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研究项目“美国《文心雕龙》研究与翻译”(批准号:13G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