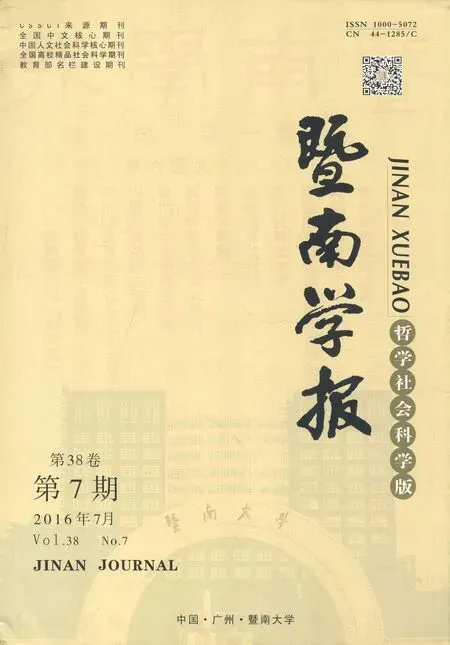北美明清妇女文学研究的理论策略
梁晗昱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北美明清妇女文学研究的理论策略
梁晗昱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北美汉学界对中国明清时期女性写作活动的关注覆盖了女性书写的表情方式、叙事方式和性别表述等方面。该领域研究的兴起,离不开西方世界各种思潮的涌动。同时,中西女性文学环境和女性形象本质上的差异,也是引起汉学界对明清女性书写兴趣的重要原因。
北美;明清妇女著作;理论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孙康宜在《明清妇女诗集及其编选策略导读》开篇就提出“与中国明清时期相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拥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女性诗歌选集或别集”。这一论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其文中提到的“女性写作”(women's writings)被广泛生发开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和女权主义社会运动的推动下,中国文学史上历来被忽视的女性文学被发掘出来,女性文学的价值也吸引了多方目光。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全面的观照,以“边缘”呼应“中心”,以发现的眼光看待传统女性的书写活动,用新的解读和阐释来激活未被发现的传统成为了学术热点。本论文拟就此一学术热点的主要问题进行清理,并评析其成就和不足。
国内学者一贯认为汉学家的西学思维方式容易对中国文学过度阐释,但在女性文学方面,汉学家对材料的挖掘和文本解读的视角总有创新之处,例如从写作主体的历史体验去考察,以文学文化史的方法解读文本;从诗词常见的意象和关键词入手,阐释其间深层内涵,进而进行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从社会性别和两性关系角度剖析出当时的文学风貌等。以下则从表情、叙事和性别三个方面对北美汉学的明清妇女书写研究进行分析。
一、关于明清妇女文学的表情方式
康白情在《读王卓民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时指出,旧时女性诗歌的主题内容大多表达得是脱离实际的闺怨和悼亡情感的。现在看来,康白情的论述不完全准确,北美明清妇女研究表明,女子的情感表达并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悲愁哀怨和苦难情怀,她们的悲情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脱离现实的闺中感怀。
对于明清妇女著作中的情感表述,雷迈伦首先提出了 “文学中的女性”(literati-feminine)和“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即男性书写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自我书写下的形象表达,这两个概念提出从理论上对“女性诗歌的主题内容大多都是表达脱离实际的闺怨和悼亡情感”提出了质疑。雷氏认为女性诗歌的情感表述脱离实际,主要是误将男性笔下的“文学女性”等同于女性的情感表现。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典型女性形象由于出自男性想象书写,期间的情感表述不能作为女性表情模式的客观体现。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建构不乏实例,但男性笔下的女性多是符号性的寄寓,通过语义的差别和两性间陌生化的差异达成的一种书写。宋汉理和魏爱莲都指出,女性的书写首先有赖于女性自身的经验体会,这种体会是迥异于男性想象中的闺情离怨。女性作者或使用男性话语习惯中的文学、文化符码,但却因视角和经验的不同,直接改写了传统符码的意义,通过基于“女性经验”的符码改写,表达自身细腻丰富的情感。
“文学中的女性”和“文学女性”概念的提出,使明清女性文学表情方式的研究,可以通过不同身份女性作家的书写,探索她们情感的类型和情感抒发的方式,重视她们作为“女性”的切身经验情感。
首先,就闺内女子而言,“穷而后工”和“发愤著书”的写作动机使她们的情感表述更贴近现实生活而超越了世俗想象的风花雪月,如孙康宜通过研究明清寡妇诗歌,解读出寡妇诗人实际生活中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和单独抚育子女及赡养公婆的凄苦;魏爱莲以清代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折射出明清女性的忠君爱国情怀,马兰安通过女子悲歌和哀苦吟唱,看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悲叹和对悲剧命运的抗争。从情感的种类和表达方式而言,“女性文学”情感表述的现实主义特色浓烈。相比之下,那些脱离实际的柔弱女性形象、女子闲情的表露,主要体现为男性文人笔下的“文学中的女性”,亦即男性自我情志反映的女性化表达。其次,就闺外女子而言,青楼女子的情感表述或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女子闺情,罗博洛认为明清才子佳人交往的风气滋养了青楼女子的文学创作,李惠仪也通过文人妓女的交往风气和他们交游中创作的诗歌词本,窥探到其中爱恨纠葛的叙述,和青楼女子卖笑生涯的凄苦和屈辱。与闺阁女子的现实主义情感表述的不同的是,青楼女子的表情方式是通过与文人情感呼应实现的。一方面,男性将自己的政治热情折射到与之交往的青楼女子身上;另一方面,青楼女性也通过男女之情和爱国之情的相互隐喻来表达自己的巾帼之志和身处烟花之地的苦楚。
不论是闺阁女子对现实问题的无奈,还是青楼女子对身世飘零的感慨,女性书写中的表情方式都是基于其自身遭遇和经历的,表情种类也是超越闺情别怨的。女性诗词写作中的情感表达并非只有闺情和悼亡,这种情感表达多样性的发掘,客观上揭示了男性文人对女性的误解,也矫正了传统文学观念中对女性单一的认识。
二、关于明清妇女文学的叙事方式
明清女性文学中,有不少记叙个人经历和遭遇的叙事文本。这些文本记载了明清女子的日常生活和旅途见闻,为我们更确切地描绘明清女性生活图景打开了一扇窗户。明清女性书写中的叙事文学,是以叙述为手段、抒情为目的的,就其种类而言,主要有创伤叙事和身体叙事两大类。
以叙述为手段、抒情为目的是明清妇女文学的叙事方式,以叙事为主体表达情感,在叙事中传达浓烈的抒情因素,同时在浓郁的情感表现中又述说和描绘了事件,表达了作者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使诗歌在抒情的熔炉下形成了叙事的风格模式。这种叙事方式,一方面来自女性主体的社会参与感,是她们见证历史的“文化记忆”的文本化,一方面来自女性身体语言在文学表述上的特定作用,身体的书写帮助女性实现其社会身份的认同。由此便也形成了明清妇女文学中的创伤叙事和身体叙事。
创伤叙事主要是“闺外叙事”,是女性对闺房之外世界的描述,多以明清之交的社会动乱为背景,描绘记叙了动荡年代的颠沛流离和国恨家仇。孙康宜、李惠仪、曼素恩等人都聚焦于明清之际的女性创作,认为特殊环境下的女子将乱世的经历化为历史的记忆,展现出时代环境和普通人家的生活遭遇,也从这种特殊的经历中领悟出人生无常和生命的价值。这种写作以文学的叙事配合历史的发展,将二者用语言绾合于文本之中,形成叙事客体(历史)与叙事主体(诗人)的互证,不但通过书写使历史的时空真实再现,也还原了历史背景下诗人的情感心境。从叙事层面上说,个人情志和公共意志交织在一起,使个人记忆融入到历史潮流中,使个人抒情上升到政治的关怀、历史的高度。通过对人生困顿时艰苦卓绝经历的想象和叙事,把一己之经历铭刻成集体的记忆。在客观事实上,女性从叙事中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偏向,展现了女性的坚韧和气节。由于叙事主体会受到文化和社会需求的影响,例如明清乱世中的女性虽然经历动荡和困苦,但仍多以观察者的身份记录这段历史,而男性则更有可能参与到动乱的平叛和修复中,所以在明清女性的创伤叙事中,在记叙和复现创伤事件之外,也会以见证者的视角来评判动乱的始末和参与者的行为。
身体叙事则出现在记叙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品中和依托虚幻的鬼魅身份进行的想象文学中,属于“闺内叙事”,是以女性第一人称亲历视角呈现的明清时期女子生活实景和内心实感。以身体作为媒介,借助身体的描写来抒发生命体验,表现日常生活和闺阁情趣,这在女性诗歌中甚为多见。方秀洁认为闺中女子,尤其是妾,常以身体书写作为欲望和闺情的象征,隐喻传达出女子日常生活中的闺房之乐,同时也通过身体的病痛描述控诉着家庭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折磨。另一方面,身体也是关乎女子忠贞最重要的载体,守身如玉的女子往往成为道德模范被舆论夸耀,卢苇菁在明
清贞女的诗文中发现她们从对自己身体、身份的维护上,捍卫着自己的名节和权利;柯丽德也发现身体是女子保护名节身份最有效的因素。而对于中国文学特色之一的女鬼狐妖,身体的忠贞则是她们道德优劣的直接评判标准。明清女性写作中的身体叙事除了文本内部的身体描写,更多反映出来的是文本外的身体符号——身份。写作中不同类型和笔法的身体描绘,是基于女作者不同的身份类型完成的,例如疾病的身体叙事多是作为家庭成员的良家妇女的日常生活记录、守身如玉的身体隐喻多见于贞女节妇这类道德模范、作为欲望象征的身体描写多出于妓女或侧室姬妾。当个体的身体被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时,其社会性将战胜自主性,从而表现出与其社会身份相呼应的身体特征,此时的身体叙事实则是身份认同的。明清妇女著作中的身体叙事,正是从不同身份角度展现时代女性生活图景的书写策略。
三、关于明清妇女文学的性别表述方式
从性别角度入手,引进“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关注明清妇女写作中的性别呈现,发掘明清时期妇女文学表现上的性别特征和性别界限的日渐模糊化,有利于消解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考察社会对女性性别身份构建、生存方式的影响,同时审视社会性别在家庭、国家间的复杂关系。
明清时期的社会文化大变革对明清的妇女生活环境和价值意识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局变迁打破了女子原本封闭的闺阁,使她们的生活环境陡然变化,因此该时期不少女子诗文的话语环境和表现空间扩大,展现出她们在乱世中生活的勇气和气节。孙康宜、李惠仪、曼素恩等关注于该时期的女性文学特色,认为在风格与主题上,动乱时期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一种刚健有力的话语姿态和男性化的文学兴趣。而到了清末民初,越来越多的女子接受教育,李惠仪认为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妇女写作对时政针砭和社会性思考的涉足,由此表现出对闺阁之外“男人事务”的敏锐认知,和对
家国命运的责任意识。除了女子自身经历了闺阁之外社会变迁的冲击,男女之间交往的松动使女子接触到更多男性社会的东西,男性的英雄主义等思想情感在此也影响了女性的精神空间,使女性写作中的男子情怀得以彰显。富有男性情怀的还有一群特殊的女子——出家女尼。管培达通过对出家女性的观察,发现选择宗教生活的重要原因也是来自于社会的动荡,而出家修行的行为本身具有打破性别界限的冲动和欲望,而女尼们也在她们的宗教生活中践行着非典型女子气质的生活,书写着非典型女性化的文学。
明清女性文学中的性别表述,是基于性别话语和场域空间进行的。汉学家认为,从话语形式到内容题材,再到写作空间,女性书写都表现出男性化的倾向。由此,他们将这种男性化的写作视为“双性性格”(Androgyny)。
书写活动是将生活的物质空间转变成主观认知空间,构建自我对世界认识的过程。当女性的生活空间和交际范畴跨越了闺阁的门墙,视野和观念上的冲击对她们原本的认知构建和传统书写思维都会造成影响。如果把稳定的生活环境视为文学写作的基础,传统的书写活动将此基础变成想象的记录,那么突变的环境使既有的物质想象和现实的真实存在之间产生差异,从而让主体在不自觉中超越原有的认知意识。正如传统视域下的女性集中于家内事务,各种社会身份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形成的:妻子、女儿、母亲、姐妹等,其文字书写的亦以家庭生活为中心。当明清社会的大变革撞击了女子原本固定的生活环境,她们不但要担任好家内角色,一定程度上还分担了男性的社会身份,如养家糊口、针砭时政等。生活基础和角色身份的悄然变化,使得女性现有的价值意识和原
先潜在的认知空间产生摩擦,表现在文字写作中,既保留了女性文字特有的阴柔婉转,又汇入了男性话语的刚劲直露;既叙述家庭遭遇动乱的颠沛流离,又以这些记叙笼括针砭世变的政治得失;既表现家人和自身的苦难,又抒发对故国的黍离之悲。物质生活的变化丰富了女性的社会身份,使得原先男性的性别和话语特色融入到新的女性性别构建之中,然而,不同性别之间这种跨差异的“间性协商”,正是明清妇女书写中“双性性格”的始作俑者。
简言之,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扩大了女性的生活空间,促进了女性社会身份的多元化,传统男性题材和男性话语融汇到女性写作之中,形成了性别交叉的“双性性格”的特色表述方式。
四、小 结
北美汉学界的明清书写女性研究成绩可观,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三十年中,明清女性书写何以引起了北美汉学界的兴趣?
首先,明清女性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妇女著作蔚为大观,涌现了诸多诗文集;另一方面其时之女性生活场域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地方,那就是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非常高,如女子间结社交游、才媛与文人间的文学交往、女子随同丈夫或儿子羁旅上路,甚至有女子为了生计外出谋求工作的,在明清社会,女性的生活空间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闺阁,看到了更多闺阁之外的世界,这也为她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素材。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女子参与闺阁内外的各种文学活动一度成为一种风尚。精英家庭的女性通过亲属或邻里关系建立了自己的文学网络,她们组建诗社或朋友圈,形成了家居式、交际式、公众式等女性文学群体。同时,文人将与闺阁女子唱和交游视为人生韵事,他们不但与能诗会文的女子有诗文往来,还广泛招收女弟子,其中袁枚、陈文述、钱塘等便是代表。闺秀才媛彼此和与文人之间的社交,以文学为纽带,在外出交游和闺中唱和中,扩展和丰富着自己的人文视野和精神领域,构建了妻子、女儿、母亲之外的一种新角色——女诗人。更有甚者,一些女性公然在公共领域中谋求职业,她们通过售卖诗词字画,或者到官宦人家教授女性家眷来获得经济支持,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形成了另一种新的社会性别角色,即闺塾师。不管是女诗人还是闺塾师,这种新的性别角色的形成,无疑来自于前所未有的跨越闺阁的社会生活参与度。
其次,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起,离不开20世纪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动。两次世界大战冲击着传统的性别关系和生产关系,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的比例大为增加,直接导致了女性追求自我实现和权利意愿的加强。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男女婚姻中的性别平等,随后欧洲各国也都将男女平等写进宪法,这也为后面的女性主义二次革命打响了头炮。作为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1976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如本(Gayle Rubin)明确提出“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使女性研究在学理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发展;1986年,美国学者琼·斯科特(Joan W.Scott)在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标志着英语学术界对女性研究的概念上的转变:对“社会性别”的关注和传统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瓦解;1990之后,社会性别研究逐渐与种族、阶级、权利关系等结合,女性在社会性别中心理和文化上的能动性研究慢慢取代了女性被动受迫论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汉学界的中国女性研究也逐渐走出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思想牢笼,开始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探索“社会”这一重要因素对男女性别、权力、生存等各方面的影响,审视社会性别在家庭、生产、国家间的复杂关系。
再者,明清女性书写领域的研究发掘有赖于北美各种思潮的涌动,同时也是中美学术交流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已经意识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史并不是历史上文学景观的真实反映,
而只是在政治选择下经过修饰的符合时代意识形态的“文学史文学”。“文学史”作为一个关于权利关系和权力斗争和一个不均衡的呈现,不能代表真实历史上的文学状况,而“文学”应该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集合而成的,只是这些声音,有的单薄弱小,处于边缘,也有的占统治地位,强大无比。但即使是边缘性的,我们也不能将之驱逐出文学的边界。正如传统观念对中国文学的概括总是“汉赋、唐诗、宋诗、元曲、明清小说”,尤其对于明清两代而言,其诗词作品不可谓不多,但对这些作品的关注度和评价远不及前朝。然而,要更客观和全面地审视中国文学,明清诗词自然应当走入学者视野,成为填补这一时代文学缺口的“五彩石”。与此同时,20世纪 80年代中期,大陆学者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再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华裔汉学家孙康宜的兴趣,之后于1993年在美国耶鲁大学主持召开了“明清妇女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开启了这一领域的系统性研究。从明清诗词到明清女性文学,这一“边缘的边缘”领域的发掘,无疑是对解构中心论和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热烈回应。
最后,与西方女性文学中“天使—荡妇”二元对立的传统不同,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并非只有“天使”或“荡妇”两种。相反,借用女性的语气来抒情言志的例子和实践屡见不鲜,明清女性书写又展现了英豪的男性笔触。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男女双性特质在写作上相互渗透和模糊不定的性别界限,对于西方世界泾渭分明的文学领域和截然对立的女性形象传统,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这30年来汉学界的明清书写女性研究中,这种性别越界和文学中双性性别的探讨自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性别界限的提出受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启示,认为外在服饰只是自我的伪装,同一个人身上总会出现性别的两级差异,衣服之上的表面性别或是截然相反与衣服之下被覆盖的复杂心态。女性写作中男子语言习惯和阳刚意象的选取,或是男性文人在政治失意后以闺怨等女性素材写作的自我解压,则类似于伍尔夫说的“衣服”,都是主体被压抑的性或者说摇摆不定的性别因素的外露。既成的性别规约限定了两性主体的行为方式和意识形态,但主体内外的性别先天具有一定矛盾性,即单一性别模式不能准确表达主体的所思所想,所以主体性别本身就模糊不清,而这种模棱两可不自觉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上的等级和压抑女性的规约束缚,客观上给女性书写及女性作品的接受提供了发挥空间,也使女性的男性化创作得到肯定。
快感和兴趣往往作为衡量标准,来回报艺术的存在价值,北美汉学家以他们对明清女性书写现象的兴趣和热情,对该领域进行着深刻的探索和实践,在材料整理、主题建构、情感表达、双性性格和文学社交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回应了明清书写女性的文艺价值。
[责任编辑 闫月珍 责任校对 池雷鸣]
I206.2
A
1000-5072(2016)07-0061-07
2015-12-31
梁晗昱(1987—),女,广西桂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