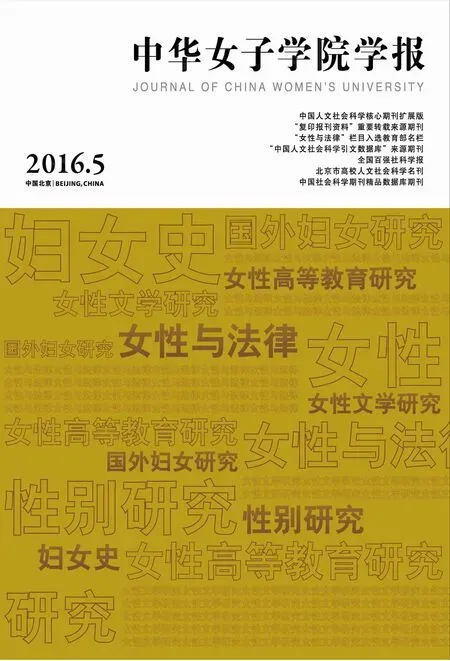浅析当代日本女性职业劳动的困境
金海兰 肖巍
浅析当代日本女性职业劳动的困境
金海兰 肖巍
女性问题,从来都是涉及社会整体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文化的女性面临的问题虽然各不相同,但是由于生理性别的制约及由此衍生的社会性别分工,而给女性生活所造成的羁绊以致苦痛,却具有跨时代、跨区域的相似性,究其根源是对于女性劳动——生育劳动及家务劳动的不平等、不公正对待。消除女性所遭遇的不平等、不公正境遇,是解决社会整体性别正义的问题,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根本动力所在。当代日本女性在职业劳动中的处境与诉求,与日本社会的对待女性职业劳动的制度结构,特别是企业劳动制度设计密切相关,这一矛盾的揭示,对面临着相似困境的中国女性乃至中国社会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日本女性;职业劳动;就业致贫
一、“男主外,女主内”家庭结构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并不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上多数民族地区无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如何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是,在工薪劳动尚不普遍的传统社会,家庭结构基本上是大家族制度,女性生理特性决定的生育劳动和女性所主要承担的家务劳动虽然同样是苦痛与繁重的,但还不足以成为女性贫困的原因。众所周知,世界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无论是英国、日本,还是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都依赖大量无产者女工的长时间劳动。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日本社会,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女性劳动者逐渐退出生产线,与之相反,男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不断延长。现代版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模式逐渐形成。日本的企业文化也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其较长时间加班的劳动时间设计、下班后与同僚的饭局酒肆交流,使男性不参加家务劳动及不与家人共进晚餐变得普遍而理所当然。这种职场劳动不仅没有考虑承担生育劳动的女性的身体生理特性,甚至是以“家有承担全部家务劳动的妻子”的男性为前提的。女性在性别上被作为全盘接过家务劳动的角色而对待,其结果就是被剥夺了从事薪酬劳动的时间。这样的劳动环境及社会结构对于女性来说是致命的。在职场中女性试图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晋升提拔机会,如果不牺牲婚姻或家庭生活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失去男性劳动力的单身(亲)女性家庭则不可避免地陷入困窘境地。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竹信三惠子在回顾自己在报社工作的岁月时这样写道:
1976年进入报社工作,五年后生子。母亲说:“我来帮你带孩子,你努力坚持工作吧。”(竹信父亲早逝由母亲靠个体经营抚养长大——本文作者注)母亲是希望在自己这一代切断套在女性身上的因家务和育儿而羁绊手足,致使其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发声能力处于劣势的枷锁吧。母亲深刻理解女性一身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和有偿的职业劳动的内中艰辛,而我则更期待丈夫分担家务。同窗恋爱结婚的丈夫对于做饭育儿并不排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同样在报社工作的丈夫被分配在早晨六点出门、深夜两点、三点归宅的部门。不久又被派往海外留学、工作三年之久。……当时的报社女性记者比例不足1%,在记者大多“家有负责家务和育儿的太太”的环境下,如果我以家有幼儿为由不参加下班后的饭局等交往,会被嘀咕“没办法,女人”等……有时候醉晕晕地回到家,环抱着哮喘的儿子坐在灯下的母亲正在疲惫地等着我……[1]4-5
这是当时日本职业女性的真实写照。不仅仅是媒体行业,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行业,长时间加班的状态很普遍。这迫使育儿期的女性难以外出工作,全职主妇逐渐增多。
仿佛为了证明这些人的存在似的,在家庭里,家务和育儿也变得越来越费事儿。虽说随着家电产品的普及家务,劳动负担理应轻减,与母亲的那个时代让孩子帮忙照看店铺粗放式育儿方式相比,家务劳动变成了高度的料理、精湛的手工,越来越烦杂。[1]6
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社会到处出现这样的全职主妇的时代。职业劳动与家务劳动难以兼顾的女性,为了持续工作而推迟生育的现象逐渐增多。1989年是刷新日本战后出生率记录的一年,即所谓的“1.57冲击”。为了工作而推迟生育的女性,还有照顾老人的苦恼,最后大多放弃工作,从而依靠丈夫的收入生活的女性有增无减。其结果是挣钱养家的男性不得不接受更长时间的劳动,以致日本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过劳死”频繁发生。对于人的身体来说家务和休养是不可缺少的,而日本企业界无视家务时间和休养的劳动时间设计,终归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日本社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全职主妇的大量出现,是日本社会在高速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劳动时间设计无视女性的生育劳动和家务劳动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这种家庭结构又加重了日本男性劳动的负担,而一旦经济出现低迷,男性收入下降,其弊端就会暴露无遗。
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与“女性贫困元年”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将制定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①这个法案的正式名称为“雇用の分野における男女の均等な機会及び待遇の確保等女子労働者の福祉の増進に関する法律”,中文译为《关于确保男女在雇佣领域均等的机会及待遇以增进女性劳动者福祉的法律》。的1985年称为日本的“女性贫困元年”。[2]招致女性固有贫困的制度性建构自此法案开始。在“女性的贫困”制度化的这一年,有三项标志性的措施:一是《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制定,二是《劳动派遣法》的制定,三是“第三号被保险者制度”的导入。下面分别进行概略介绍。
1.《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
这项法规是逐步取代此前的《劳动基准法》中关于“禁止女性深夜出勤及节假日出勤等保护女性”等措施而制定的法规。其理由是来自日本经济界的“如果希望与男性同等待遇的话那么应该和男性同等劳作”的强烈要求。而以“挣钱养家”的男性为主体的日本企业工会大多不在意法案对加班的限制。当时日本工会妇女部门虽然提出了仿同欧洲的“男女同等的劳动时间限制”的要求,考虑到只要求限制女性加班的话,会成为企业排斥女性的把柄,若男女双方都同样受到限制,则在避免排斥女性的同时也使男性按时回家并加入到家庭生活中来。但是,在几乎没有女性身影的日本政经界,针对这样的意见是无法予以通过的,因此此法案的制定将女性卷入了对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的时间不做丝毫考量的长时间劳动的职场之中。《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制定后,又相继出台了“弹性劳动时间制”②所谓“弹性劳动时间制”,指在一定期间内的日平均劳动时间在8小时以内,即使日劳动时间超过8小时也是被允许的。及针对某些特定职业的“裁定劳动制”③所谓“裁定劳动制”,是对于某些特定的职业种类的从业者能够不受劳动时间规定限制的制度。等实质上容忍长时间劳动的措施。女性能够持续工作,是在必须保证每天从事家务和育儿劳动时间的基础上的。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和其后的各项措施无疑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从事与男性相同的职业、接受与男性相等的劳动条件的女性,必须有家人亲属的帮助,或者有足以支付雇人做家务的高额工资收入,或有配偶可以承担家务劳动。在日本企业想成为正规员工,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接受长时间劳动,而这种长时间劳动若没有配偶的支持是难以承担的,女性也需要有“家庭主夫”的支持。所以,大多数肩负家务和育儿劳动的女性难以坚持下来,一般不得不因产子而退职。育儿告一段落后再次作为非正规劳动者而重新就业。
2.《劳动派遣法》
这项法规的制定使“派遣劳动”成了这些从正式员工“掉队”的女性的接收处。日本政府出于“女性如果和男性参加同样时间劳动的话,有家庭的女性员工难以留存。短工(小时工)因为劳动时间短、工资低和专业性弱而缺乏成就感,为了使女性能够维持家务、育儿与工作的两立,并作为可以保证适当薪酬待遇及职业专业性的另一雇佣方式”的考虑而设计出“派遣劳动”方式。但是,这就带来了在同一个企业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派遣员工的工资比正式员工要少很多。贴着家务劳动承担者的标签而被迫加入到短工(小时工)及派遣员工行列中的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幅度增加,到了2004年前后成为大多数就业日本女性的选择。不仅如此,在90年代后期的经济低迷状态下,派遣劳动几乎被应用于所有职业类别并逐渐向男性蔓延,到2004年派遣员工占日本青年男性就业劳动人员的4成左右。
3.第三号被保险者制度
这一制度也被称为“主妇退休金制度”,即作为就职人员的配偶,被抚养者可以不缴纳养老保险而享受基础退休金的制度。这曾被作为“优待主妇”的政策,却被企业与女性短工的收入关联起来,因为被认定为“被抚养者”的条件是“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从事短工劳动的主妇收入必须在这个标准之下,因此反而成为提高女性薪酬待遇的障碍,无疑是导致主妇贫困化的诱因。
上述1986年开始实施的三项针对女性职业劳动的法案,看似为了促进男女职业平等,但是在不同层面上将女性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和育儿劳动排除在职场劳动的时间设计之外,使女性(特别是已婚育女性)越发处于就业劳动的劣势地位,导致女性的贫困化加剧。因此将1986年称为“女性的贫困元年”,而女性贫困也是日本社会整体贫困化的体现。
三、“Gender Free”意识启蒙运动与《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Gender Free”一词在日本政府主导的女性机构及学校教育中流行起来。“Gender Free”这个用语最初被公开使用的是1995年东京女性财团①东京女性财团,是1992年成立,由东京都政府资助的“公设民营”机构,1995年在涩谷设立“Women's Plaza”,旨在官民携手建设丰富的“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因其大力推广的“Gender Free”意识启蒙运动而遭到日本保守势力的抵制,2001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未经协议,便宣布停止对“东京女性财团”的资助。东京女性财团虽已解散,但“Women's Plaza”活动仍在继续。的手册《为了Gender Free一代的教师们——你们的班级是性别平等的吗?》(1995a)及其项目报告《为了性别平等的教育》(1995b)。在报告书的第一章这样写道:“战后五十年的今天……日本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及男女间的制度不平等现象逐渐解消,表面上的男女不平等大大减少。”“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处于统治——被统治、优势——劣势的关系中的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制度性的平等而瞬间消失。”②参见东京女性财团:《为了性别平等的教育》,1995年。“Gender Free”(性别平等)一语的含义是“不拘泥于性别、不为性别所缚地行动。”这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内心及文化层面的问题”。在该手册中将“Gender Free”(性别平等)与以前的“男女平等”区别开来,认为后者主要指向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日本已经基本实现,而前者则是呼吁触及“人们的意识与态度层面”,意在个人意识的改善。这个概念的提出,偏重于人的意识启蒙,而不是制度变革。大多数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参与了政府主导的各项课题,积极促进了“Gender Free”一语的传播。为了推广这一概念,东京女性财团主办了各种讲座,编写出版了各种研究报告、启蒙影像、宣传资料等。其内容也从最初的主要面向学校教育而渐次地扩大到面向职场和生活社区。通过市民团体使更多的人受到“Gender Free”的意识启蒙。
尽管日本社会的保守层对于“Gender Free”意识启蒙运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但是日本政府受国际社会关注女性问题动向的影响及面临日本国内长期经济低迷、薪资水平下降所引发的对新型劳动力的迫切需要,认识到解决女性就业问题的重要性。1998年日本国会全票通过了《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1999年开始实施。关于“男女共同参加社会”是这样定义的:“是确保男女作为构成社会的对等成员,拥有根据自身的意志参加社会所有领域的活动的机会,能够均等享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利益并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自2000年制定了《男女共同参加基本计划》后,各地方政府分别成立了关于推进男女共同参加的地方条例。促进女性走向社会从事职业劳动,不仅仅是性别公正的问题,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经济的状况所迫。
四、经济低迷与日本女性就业状况
众所周知,自1989年开始日本的泡沫经济出现破裂,经济成长进入低迷状态,主要表现在伴随着日本国内薪酬的上升,日本企业顺应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纷纷到海外设立工厂,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的“空洞化”,日本社会所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开始动摇,男性就业者的正规就业率逐年下降。此前依靠丈夫收入的主妇不得不出去工作以补贴因丈夫收入下降而出现不足的家计。但是因为承担家务劳动,日本已婚女性大多从事按时计酬的短工劳动。对于日本的经营者来说,自然欢迎这种薪酬低并可以随时终止雇佣合同的短工,随后出现的“契约社员”(合同制员工)及“派遣劳动”等都是前者变形的劳动型态,这些与终身雇佣制的“正规雇佣”有别的雇佣形式,后来也普遍波及青年及已婚男性,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及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出现了所谓的“NEET”族①英语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的缩写,是指没有就学、就业、参加职业培训的状态,在日本指15—34岁之间的非劳动人口中没有就学、也不从事家务劳动的“青年无业者”。、不婚族,等等。前面也提到,1989年刷新了战后日本年度最低出生率,日本人口的减少预期,人口的超老龄化,使日本社会面临着劳动力减少问题。继1986年《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实施之后,到1999年《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的颁布,日本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及女性自身的社会参与意愿的增强,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女性就业的方针政策。安倍内阁推出“女性辉耀的日本——提高女性就业率的政策”,具体的目标有:到2020年女性在企业的管理岗位上所占比例提高到30%,让所有等待进入保育园的孩子得以依托,出台了“产休法”支持女性结束产假后的岗位恢复和再就职等等增大女性职业活动空间的措施。如下的数据图表也显示出女性就业率自1990年以来在逐年上升。1980年的日本,夫妻双方以男性为主要家庭收入来源的单方就业家庭占大多数。此后,夫妇共同劳动的家庭数持续增加。1997年在数量上夫妇共同劳动家庭数超过单方就业劳动家庭(见图1)。
日本女性就业率呈上升趋势的背景之一,可以认为是女性就业积极性的提高。在关于自身理想生活形态的调查中,一般描述为“两立型”(结婚生子,但是一直坚持就业)和“再就业型”(结婚生子,中途退职,育儿结束后再就业)的两个选项中在2010年的时候分别超过30%,特别是选择“两立型”的女性受访者自1992年以后一直保持增加的趋势,可以看出女性挑战家庭与工作两立的积极性保持高涨。按照年龄段来看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可以得到大家所熟知的25—34岁这一结婚生子阶段劳动力激减的“M字弯”(见图2)的形状。尽管“M字弯”的底部依然体现为此年龄段女性就业率低迷的状况,但是底部至逐年上升趋势。这可以理解为由未婚或晚婚、结婚生子年龄的变化及伴随结婚生子辞职动向的变化、雇佣形态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

图1 日本夫妇共同劳动、单方就劳动家庭数量变化

图2 日本女性不同年龄阶段就业率的变化
在考察就业女性的雇佣形态的变化时可以发现,“M字弯”处就业率呈提升趋势的25—29岁及30—34岁的年龄阶段,1985年与2014年相比,这两个年龄段的就业率都有所提高。而分别统计“正式员工”、“短时工、临时工”、“派遣员工、委托员工、其他等”项目的变化时,发现与“正式员工”相比、“短时工、临时工”、“派遣员工、委托员工、其他等”项目的增加更为显著。反映出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的就业形态主要以短工、派遣员工等不稳定、低福利、低报酬的岗位为主。因此,大多数的就业劳动女性并没有获得职业发展方面的性别平等,反而是出于经济窘迫而不得不在承担繁重家务劳动的同时,从事低薪劳动。
五、日本女性的精神健康困境
在日本政府迫于经济社会需要而推行的促进女性就业政策、日本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女性关于职业发展与婚育关系的观念的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下,日本女性的就业率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在经历了高速经济成长后进入安定弛缓阶段的日本社会,其国际竞争形势更为严峻。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裂后的长期经济低迷中,日本劳动市场也发生着剧烈变化。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也难以持续,男性劳动力的雇佣形势日趋不安定。男性家庭成员的收入下降,不得不外出从事低薪短时劳动的女性,特别是丧偶或离异等的单亲母亲越发陷入“Working-poor”(就业致贫)的状态。
经济低迷引发激烈的职场竞争,其危及的不仅仅是男性和具有职业成长志向的管理岗位女性,也蔓延到置身于职业晋升之外的普通女性劳动者,所有的职场中人都与精神性苦痛比邻而居。造成职场精神苦痛的因素很多,诸如,职场欺凌、性骚扰、人际交往困难、伴随升职升薪的纠纷,都被视为引起精神疾病的因素。其中,女性就业人员面对激烈的雇佣市场竞争,竭尽全力实现工作与女性自身特有的负担,如产子、育儿等生育劳动、家务劳动的两立,给女性造成紧张和焦虑,由此带来的精神病痛日益凸显。
从下面图3中,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女性的精神焦虑程度普遍比男性高。而20—60岁的年龄阶段的精神焦虑程度无论男女都是极高的。这些问题在于,上述表格中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区分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按照当时20—40岁年龄阶段女性就业率的最高值70%来推察,包括30%的专职主妇在内的女性的精神焦虑程度远高于接近100%就业率的男性。

图3 不同性别及年龄精神焦虑自觉症状调查
而下面表1中的数据是实际到医院的精神健康门诊进行诊疗的男女患者数据。统计当年的整体就医人数,女性远远多于男性,其中的就业人数及比率男性高于女性。而就业人员的就诊人数,女性比男性高出13%,考虑到就业人员在总数上男性比女性多出四成,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女性的精神健康程度整体上比男性低。
日本女性经历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实施后的三十年,在就业竞争中与男性面临相同的强度,还需要承担结婚、妊娠、产子、育儿等家务负担,处于来自职业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来自家庭内的压力同时爆发的境况。从事专业性、技术性、管理型岗位的女性,所在的企业规模越大,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概率越高。而市场营销岗位则企业规模越小,个人的压力越大,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的概率越高。在日本,选择专业性、技术性、管理型岗位的女性更倾向于进入大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抵抗与男性同样的压力获得晋升,若非特别坚强的女性实难胜任。轰动一时的“东电OL被害事件”①“东电OL被害事件”,是指1997年发生的东京电力公司39岁的女性员工庆应在东京都涩谷区某破旧公寓被害死亡、现金4万日元被劫的案件。引起关注的是被害女性庆应作为日本大型企业的精英员工生前曾频繁从事卖淫活动。被害女性庆应大学毕业后,作为第一批综合性岗位的女性员工进入著名企业——东京电力工作,工作业绩不输于男性而顺利升职涨薪。但是,下班后几乎每天到遇害的涩谷区圆山町站街招客。收入丰厚的她缘何从事卖淫活动,似乎令人匪夷所思。在调查中得知,被害女性还罹患厌食症。推想可知,39岁未婚的精英女性员工,在与男性同僚的竞争过程中所积累的无法排解的焦虑和压力,是促使她以卖淫行为寻求精神释放的原因所在。是对日本职业女性这一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

表1 精神健康基础数据:男女就诊人数差别(2014年)
六、结语
综上所述,围绕着日本女性职业劳动的问题,对日本政府相关法案及其对女性就业的实际影响、日本女性就业率的上升及其背景、就业女性的精神健康状况等根据实际数据资料进行了简单梳理。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女性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日本企业的长时间加班劳动时间设计将女性驱逐出职场,使其作为家务和育儿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支撑“挣钱养家”的男性,而当日本社会进入经济低迷、男性薪资下降、劳动力缺乏的时代,日本女性又不得不走出家庭从事低薪的短工或派遣劳动。由于日本政府的各项法案及措施虽然打出消除“性别歧视”的旗帜,但是在根本上并没有把女性承担的生育劳动、家务及育儿劳动作为与职场劳动等价的劳动对待,使女性不得不承担双重的负担,造成了女性整体的精神焦虑和健康困境。如何改变经济界的“厌恶家务劳动”的资本市场逻辑,是解决当代日本女性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资本市场逻辑,重视的是每位员工的工作效率与业绩,而将女性的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作为个体的私人领域的事项,完全由个体或家庭承担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而日本政府的诸项法规和政策归根结底还是在日本企业界的这种逻辑惯性上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从社会观念的变革入手彻底解决日本女性的就业困境。这也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所极力批判和试图扭转的症结。当然,我国的女性问题与日本相比,在层次上更为复杂,但是与日本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也有很多共同点,希冀本文的内容对于思考我国女性劳动问题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借鉴。
[1]竹信三恵子.家事労働ハラスメント[M].東京:岩波新書,2013.
[2]藤原千沙.贫困元年としての1985年——制度が生んだ女性の貧困[J].女たちの21世紀,2009,(3).
责任编辑:秦飞
Analysis on the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Women’s Working Life
JIN Hailan,XIAO Wei
Women’s issues have always been the whole society’s issues,rather than the women’s own.Although Women are facing different issues in different cultures,times and countries and regional areas,there are still similar pains and sufferings due to sex difference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of women.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ituation is that reproduction and housework are not given equal and fair treatment.Therefore,to eliminate the inequality and injustice women have suffered is the key to pursue justice in the whole society,which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motivation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women’s situation and their demands in working life,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the labor system of Japanese companies.Such an analysis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ese women in the same predicament.
Japanese women;working life;working and poverty
10.13277/j.cnki.jcwu.2016.05.013
2016-06-24
C913.68
A
1007-3698(2016)05-0085-07
金海兰,女,满族,清华大学哲学系2013级伦理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劳动、政治哲学等;肖巍,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性别哲学、生命伦理等。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