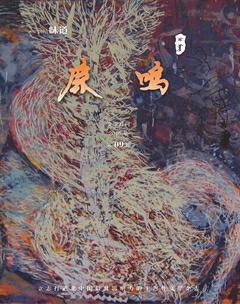无事且饮太平猴魁
项丽敏

春夜是一枚回形针
把我别在窗前
扫雪煮茶,剪灯初话
月光如一架订书机
把制度、门和我都订在一起
我像按图钉似的,把头按进风景里
胡兰成一红,就俗了
有些书需躲起来读
人老腿先老,宛如局部麻醉
生活即请君入瓮
无事且饮太平猴魁
——杨典《太平猴魁》
几年前常去一个诗歌论坛,在论坛里读诗,也把自己新写的诗贴到论坛。那段时间是我的诗歌狂热期,打开电脑,最先做的事就是点开收藏夹里诗歌论坛的网页,浏览过后才能安心做别的。
有天,记得是下过春雪的早晨,点开页面就读到《太平猴魁》,重庆籍诗人杨典的新作,心跳骤然加快,仿佛意外撞见写给自己的情诗。
太平猴魁是我的家乡茶,仅看见这个标题就叫我眼眶发热。
我的出生地就是太平猴魁的产地——黄山市太平湖上游的新明乡。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乐园就是屋后的茶园,我最早认识的植物是茶树,最为上瘾,或者说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味道就是茶之味。
至今仍记得第一次采茶的情景,是在母亲教书的一个名叫夹坑的村子。坑在本地方言里是河谷的意思,新明乡有很多村名都带个坑字,荷花坑、猴坑、箬坑、招坑、桃坑、芦溪坑……那时的茶山归集体所有,村里人全听队长分派,赶大清早在晒场集合,到指定的山头去采茶。差不多快到中午时下山,把装得满满的茶箩送到茶厂过磅,记上斤数。茶季结束时,再按统计的斤数由队长分红。
每到茶季学校就不上课了,有半个月的茶假,学生回家帮大人干活,老师则留在生产队,和茶农们一同上山采茶,采下的茶叶同样交到茶厂过磅。我最喜欢放茶假的这段时间,仿佛这是一个集体的隆重节日,村里男女老少全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采茶、拣茶、制茶,从天亮忙到天黑。这样忙碌,大家看起来却都是很开心的样子,手里干着活,嘴里也不闲着,说笑打趣逗闷子,连我那性情严肃难得一笑的母亲也松开了眉头,对我的管教也没有平常那么严厉了。
第一次采茶时大约六岁,还没有上学,当母亲把一只小茶箩系上绳子,挂上我肩头后,不等她吩咐我就蹦出了门。
夹坑是隐藏在深山腹地的小村,从山顶往下看,隐约可见的房舍真像是落在绿色的坑洞里。二十几户人家,呈L型分布,中间巴掌大的一块平地,供村里晾晒东西。因为山的遮挡,日头在村里逗留的时间也就短了,像急着赶路的客人。一条涧流沿着山根缓缓流淌,弹拨着悦耳的曲子,到初夏的梅雨季时,涧流会在一夜间改变性情,变得泼辣甚至疯狂,发出轰然的激流声。
涧流对岸就是茶山坡。我背着茶箩,摇摇晃晃走过独木桥,到了对岸。说是对岸,其实还是在村子里,可以看见我和母亲借住的小屋子,听见屋后的鸡啊猫啊狗啊闹出的动静。我在和我差不多高的茶树下停住,学着大人的样子,将衣袖挽起,开始采茶,没多一会儿就把这棵茶树的叶子摘得干干净净。
母亲已收拾好家务活准备上山了,在屋子里叫我,没人应,又跑到门口叫:丽敏,丽敏。我赶紧应了一声,放开手里的茶树枝,呼啦一下就出现在母亲跟前,得意地举起小茶箩,期待从母亲脸上看到欣喜的表情。正好队长也走过来,伸手从茶箩里掏了一把,大笑道:小丫头采茶是片甲不留啊,新叶子老叶子一把捋来了,厉害厉害。
队长有个爱好,每次看电影总要学几句新词,茶季前村里来过放影队,估计“片甲不留”就是他刚从电影里学来的。
很快我就知道,采茶看起来简单,却是有讲究的,不能夹带老叶子,不能留太长的叶柄,每支茶的长度要均匀,有虫眼的叶子不能要,发黄发红的叶子不能要,小小的托叶也不能要,炒出来会发焦,没卖相。
在茶季,最热闹也最有趣的地方还是茶厂。
茶厂是每个村子都有的,也是村里最大的房子,可容纳几百人。茶厂不止是制茶的地方,也是全村人商讨事务和娱乐的地方,队长召集开会、村里人家办红白喜事、电影队过来放电影、过年过节请戏班唱戏——偶尔还有玩杂耍和说大鼓书的走进村,都把场子摆在茶厂里。
茶厂也是孩子们的游戏场,在水泥地上划出线格玩跳房子,在粘满蜘蛛网的角落玩躲猫猫,或模仿电影里的情景玩“好人和坏人打仗”的游戏。到茶季孩子们就玩得更起劲了,晚饭一落肚便跑到茶厂。茶厂里吊着七八盏灯泡,大得像葫芦,把平日里黑咕隆咚的屋子照得亮堂堂。孩子们个个变成小疯子,相互追赶着,在地上厚厚的鲜叶堆里翻跟斗,滚成一团儿。大人不停地过来驱赶:死小鬼,看把茶叶都弄脏了,出去出去。可是没用,孩子们刚被赶走,一眨眼又滚进去了。我喜欢把头扎在茶叶堆里闻茶叶的气味,新鲜茶叶的气味浓郁到可以触摸,可以大口大口地吃进肚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除了父母的体味,给我强烈感官记忆的就是茶叶的味道,只要闻到这味道就感到安宁,说不出的舒坦和快乐。
孩子们终于还是被大人们赶回家睡觉去了。茶厂的灯光通宵亮着,炒茶机也不停地翻转着,直到后半夜村庄才陷入万籁俱寂的宁静中。
在我十岁的时候,热闹的茶厂忽然就沉寂,人们不再把采下的茶叶送到茶厂,交给“公家”制作,因为茶园不再归集体所有,而是包产到户分到个人头上。
这一年我和母亲已离开夹坑,回到自己家所在的村子——招坑。招坑也是藏在深山腹地的村子,和夹坑一样山多地少,住户却要比夹坑多得多,有七十多户人家,大多姓项,论起来也都算是亲戚。
从这年开始,茶叶的采制就变成各家各户的事。每户人家在屋后都砌上了专用来炒茶的大灶台,请竹匠到家里来编制烘茶叶的成套器具——茶箩、簸箕、竹匾、烘圈、烘顶。在茶季开始前就准备好足够的柴禾,足够的木炭和食物。
童年的记忆里,除了过年就数茶季吃得最为奢侈——这也是我喜欢放茶假的原因之一,冬天腌的咸鱼腊肉这时都搬出来了,挂在屋檐下,做饭时割一大块,切成薄片蒸在饭头上。春分前腌制的鸡蛋鸭蛋到这时也已入味,洗去外面裹着的一层黄泥,煮熟后切开,红艳艳的蛋黄冒着油脂,看着就流口水。
为茶季准备的食物里少不了的有清明粿和蒿子粑粑(类似青团),做好后用加了盐的冷开水泡着,隔三五天换一次水,可以存放很久,吃的时候捞一只,在烘茶叶的炭火上烤一烤,烤到表皮发鼓,散发出米食特有的焦香就可以吃了,不费时间。在茶季,时间会变得很宝贵,茶叶跟疯了似的呼啦啦地生长着,稍微耽搁一下就老了。
在茶季除了这些还得准备便于携带的干粮,锅巴、炒米,花生糖和冻米糖。家境好一些的人家还会特意买些麻饼存在家里,上山时带上,饿了就拿出来垫肚子。
我家五口人,分到三块茶园,一块在自家屋后馒头形的矮山坡,几分钟就走到了,一块在离家五里地外的深山坞里,另一块在海拔四百多米的高山上,从山底沿着弯曲陡峭的小路爬到茶园,得花一个多钟头的时间。
茶叶的品质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长的环境。我家这三块茶园的地势差异大,味道也有明显的区别。屋后的茶园几乎算是落在村子里,与人烟同居,山头低矮,日照长,长出的茶叶偏于薄瘦,味道清寡不耐泡。但是这块茶园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光照充足,生长期比另两块茶园要提前好多天,等另两块茶园的茶叶到了需要采摘时,屋后山头的茶叶已摘过头茬,不至于挤到一起让人手忙脚乱。
深山坞里的茶园沿着狭长的山谷生长,是三块茶园里地势最低的,两边簇拥着密密的竹林和灌木林。立春后,林子里的野花一茬接一茬地开起来,兰花、樱花、杜鹃、紫藤、野蔷薇、瑞香、金樱子,还有长在溪边大片大片的白水仙,芬芳溢满山谷,浸润着还在酣睡中的茶树。清明前,茶树终于被春野迷人的气息唤醒,毛茸茸的芽尖从枝头心形苞叶里钻出,像刚出生的孩子那样,出于本能地吮吸起来,把密布空气无处不在的香气吸纳到自己的身体里。
三块茶园里,生长得最为迟缓的是高山岗上的那块,这里的茶叶也是三块茶园里味道最好的。
茶树是很有意思的植物,生长在低处或离村庄很近的地方,它的味道里就会多一些苦涩,而若是长在“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云雾深处,它的味道也就沾了世外的仙气,脱胎换骨,苦涩是一点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浓酽的茶香和缭绕舌尖绵长的回甘。
高山岗上的茶叶枝条也是最为肥壮的,叶片厚,色深,多白毫,可能是日照少生长缓慢的缘故吧,使得它们有时间充分汲取地下的养分,吸收自然万物吐纳的精华。
包场到户后,茶叶的出售也是茶农自己家的事,制好的茶叶要么送到茶站的收购点,要么就留在家里等茶商上门收购。尽管高山岗上的茶叶味道最好,卖价却并不好,因为采摘得晚——我们村有个不成文的惯例,茶叶的价格和时令紧密相关,最早采制的茶叶价格通常是整个茶季最高的,随后便以递减的方式,一天一个价地降下来。
高山岗上的茶叶卖不上价还有一个原因,我父母虽是农民出生,对农事却并不十分精通,尤其是制茶的技术——他们只会做普通的奎尖,不会做讲究的猴魁。好原料得不到精细制作,自然就得不到与之匹配的待遇了。
奎尖的制作也是传统的绿茶制作,先在炒锅里杀青,再揉捻,然后摊进烘顶里用炭火烘干。这三个步骤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也是需要一定功夫的,比如杀青,就是用手当锅铲,在高温的铁锅里翻炒鲜茶叶子,性急的人很容易把手指触到铁锅上烫出燎泡,经验不足也不行,要么把茶叶炒过了火,杆子焦了,叶子起泡了,要么炒得过嫩,鲜叶子的青气还没有去掉就捞出锅了。
揉捻茶叶要简单一点,把炒好的茶叶捞进小竹匾里,双手将茶叶拢成堆,以顺时针的方向,揉上几个来回。揉捻茶的功夫主要在力度的把握上,不能轻,也不能过重。小时候不明白茶叶炒好后为什么不直接烘干,而要如此这般的揉压一番,后来看书,才得知这其中有着类似于化学反应的奥妙,书上说“揉捻时茶叶的细胞壁被压破,促使部分多酚类物质氧化,减少炒青绿茶的涩味,增加浓醇味。”
制茶的窍门别人是没办法教的,只能在不断的操作中自己去体会。制茶也是人与茶叶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过程,制茶者只有把整个心思用上去,去细心感受和领悟,茶叶才会慢慢地向你吐露它们的秘密,展示给你它们最好的状态。
在我家,制茶的前两个步骤——杀青和揉捻是父亲干的活,母亲负责的是烘茶这一步。
烘茶也分三个步骤,一烘、二烘、三烘。地上摆三个烘圈,三盆炭火摆在烘圈里,上面支着烘顶。揉捻好的茶叶先摊进第一个烘圈的烘顶,烘至半干再倒入第二个,这中间要适时地给茶叶翻面,使茶叶受热均匀。等茶叶烘至大半干时再倒入第三个烘顶,这只烘顶下的炭火盖的灰要厚一些,不至于把茶叶烘过火候。
母亲在三只烘圈前弯腰弓背翻烘着茶叶,一点也不敢大意,烘干的茶叶最后会变成苍绿色,倒进一只大竹匾里。
我的父母都属羊,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从年轻时候起就爱抵角,动不动就吵起来,在我的记忆里家里很少有和平安宁的时候,但是整个茶季里,父亲母亲像是忘记吵架这件事,只是不停地干着活,两个人言语不多,配合却十分默契。
不吵架可能也是两个人的全部精力都放在茶叶上,没心思理会别的事,再说整个茶季人都是又忙又累的,到半夜往床上一倒就困得像团瘫泥,哪里还有工夫生气吵架呀。
也不止是我的父母,村里以往隔三岔五便要吵架的婆媳妯娌,一到茶季就自动讲和,平安无事地相处着。如此看来忙碌也是很好的事情,尤其是全家人齐心合力地忙着同样一件事,彼此之间的合作、相互需要,会使关系变得更为融洽。
半个月的茶假很快就过完了,母亲回到学校教书,我和哥哥回到学校上课。父亲也到了该去上班的时候,家里只留下奶奶看守着屋门,有茶商来村里收购,奶奶就把做好的茶叶拿给他们看。茶商抓一把,闻了闻香气,伸出手指报了一个价,奶奶一听便摇头,对方又报出一个价格,奶奶还是直摇头。见价格谈不拢,茶商也不再多啰嗦,起身走了。
奶奶摇头的意思其实是表示没听清茶商在说什么。奶奶快九十岁了,听力不好,跟她说话要像打雷那样才有效果。
眼看着就要立夏,我家的茶叶还有不少在屋里搁着。好在我家不靠茶叶过日子,父母都有工作,工资虽不高,维持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没卖掉的茶叶搁家里也不是事,父亲干脆拿它们做人情,买来一摞印有“新明奎尖”字样的茶叶袋,装好封口,作为土产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们。
村里茶叶卖得好的就是那些会做猴魁茶的人家。住在我家隔壁的春生就很会做猴魁茶,为了掌握制茶的技艺,春生刚满十八岁就背着自己的铺盖,到猴坑和猴岗当了两年茶工。
猴坑和猴岗是两个紧邻的村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顶。这两个村子就是太平猴魁的核心产地。
猴岗离夹坑很近,不过一山之隔的距离。母亲到夹坑教书前就是在猴岗教书的,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在夹坑教书后,母亲曾领我去过一次猴岗,看望曾照顾过她生活的老房东。
我对猴岗的记忆是,那条上山的路弯来绕去,似乎永远也爬不到尽头。母亲背着我走一段,然后把我放下来,让我自己走一段,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石头上歇一歇,喝两口水壶里的凉茶,拿出一只麻饼,掰半块给我吃,另半块仍用油纸包好塞进布包里。
在我吃麻饼的时候,母亲很警惕地听着周围的动静。母亲说这山上有很多野猴,会和人抢东西吃,我一听吓得不得了,三口两口就把麻饼吞进肚子。
幸亏在路上遇到个熟人,和母亲聊了两句话便在我面前蹲下,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就将我揽到背上,噌噌噌大步往前走,那么陡的山路,在他脚下仿佛就是平地,一点儿也不当回事。后来听母亲说,以前她在猴岗教书的时候,每次上山都要走半天。在她离开猴岗去夹坑时,老房东拉着她的手大哭了一场,说你走了这村里的小鬼们怎么办啊?谁愿意到这么高的山头上来教书啊?
母亲离开猴岗也是迫不得已,她在这个村子里教了三年书,到第二年的时候就得了关节炎,膝盖痛得打不得弯。住在猴岗的人大多患有风湿性疾病,并且不管大人小孩都是罗圈腿,这和猴岗的高山气候有关,村庄长年笼在云雾中,空气湿度大,很少见到太阳。
这样的地方其实是不适合人长期居住的,但是对茶树来说这里就是风水宝地了。也正是因为舍不得这么好的茶,人们才把家安在这里,世世代代守在这原本只有猿猴生活的高山之上吧。
春生在猴岗待了两年也得了关节炎,不过他这两年可没白待,不仅学到了制作猴魁的技艺,还把猴岗最漂亮的姑娘娶回了家。姑娘过门不久便从娘家带了一批茶树苗过来,春生说这茶树苗叫“柿大茶”,抗寒性好,是制作太平猴魁的最佳品种。
从采摘上猴魁就比奎尖讲究的多,要赶大清早上山,在浓雾散去之前采摘。若是碰到雨天就不能采了,雨天的茶叶过湿,不能炒制,搁着又会发酵变色。大日头下的茶叶也不能采,茶叶经日头一晒就失去了水灵气,没精打采,制出的干茶也会逊色很多。
茶叶采回来后要“拣尖”,这是个精挑细选的过程,去掉瘦弱的、弯曲的、色淡和有虫眼的,只留下叶片肥厚、有光泽且茸毛细密的。经过“拣尖”后的猴魁鲜叶一律是两叶抱一芽的形状,枝条也像尺子量过般一样长。
接下来便是炒制了,先杀青,再捻揉,最后烘干。猴魁和奎尖的制作工艺最大的区别在捻揉这个环节。猴魁的捻揉里还有一道理茶的工序,就是把杀青之后的茶叶一根根整理成形,摆放在浸过冷水的布网上,放进特制的压茶机里,用滚筒来回滚动,捻压。
仅这一道工序的区别,就使猴魁和奎尖有了完全不同的外观。奎尖茶的枝条是弯曲的,叶子各自婀娜地分开着。而猴魁茶则像经过严格训练守在岗哨的士官,手脚并拢,腰板挺得笔直。
母亲回到招坑教书后,就没再去过猴岗,也没再见过待她如女儿的老房东。不过每年母亲会买一些布料糕点什么的,等春生老婆回娘家时托她带给老房东。老房东也总是要回赠一两斤自家做的猴魁茶。
老房东家的猴魁茶被母亲装在一只四方形的洋铁筒里,放在家里最高的柜橱顶上,偶尔来了客人,母亲才拿一只板凳垫脚,从柜橱顶上取下洋铁筒。
母亲把洋铁筒放在那么高的地方是防止我和哥哥乱动,殊不知这样的防范反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家里没人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取下洋铁筒,掀开盖子看一看。洋铁筒的盖子非常紧,掀开时会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每次我都被这仿佛故意吓唬人的声响弄得又心慌,又兴奋。我总觉得洋铁筒里可能装着别的东西,比如桃酥、顶市酥、麻饼,我甚至已在自己的想象里看见它们,闻到它们特有的酥香。但是洋铁筒并没有给我变出这些来,在我费了好大力气掀开盖子之后,不由分说钻进鼻子里的味道告诉我,这里面确确实实是老房东家给的猴魁茶。
尽管没有想象中的美味,我还是被这股浓郁的茶香摄去了魂魄,为之所迷。很多年以后,我仍然无法找到准确的词语描绘这种香气,它只属于秘密的山林,属于春天有灵性的万物,属于上天赐予人间的神奇、喜悦,与无尽的抚慰。
不记得是哪一年开始,那只放在柜橱顶上的洋铁筒突然就空了。一年、两年、三年……它就那样空在那里,没有装进老房东家的猴魁茶,也没有用来装别的东西。
再后来,我家的三块茶山也转让给亲戚家采摘侍弄了。父母仿佛一夜之间变老,老得我不得不重新适应他们的模样。奇怪的是,当我试图回想他们年轻时的容颜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仿佛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这么老。
他们曾经爬过家乡最高的山,肩上还负着沉重的担子。如今,他们连自家的楼梯也爬不上去了。
去年回家,整理房间时,我又看见那只洋铁筒,盖上落着灰尘,摆放在壁橱上。我拿起它,用手托了托,很轻。我知道它仍然是空的,用抹布擦去灰尘后,出于惯性,还是掀了一下,“砰”的一声,随着盖子的打开,一股熟悉而又久违的味道扑鼻而来。
这么多年,空了的洋铁筒仍然还保留着很久以前的茶香,丝毫没有改变,仿佛是故意储存着这味道,等着我回来打开,与过去的岁月重逢。
几乎一瞬间,我被这股奇妙的醇厚香气运送回童年,回到背着小茶箩第一次采茶的时候,回到在灯光明亮的茶厂追逐、翻跟斗撒欢的时候——在香气里我又看见当年的父亲和母亲,都还那么年轻,腰板挺直,额头没有白发,也没有斑点和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