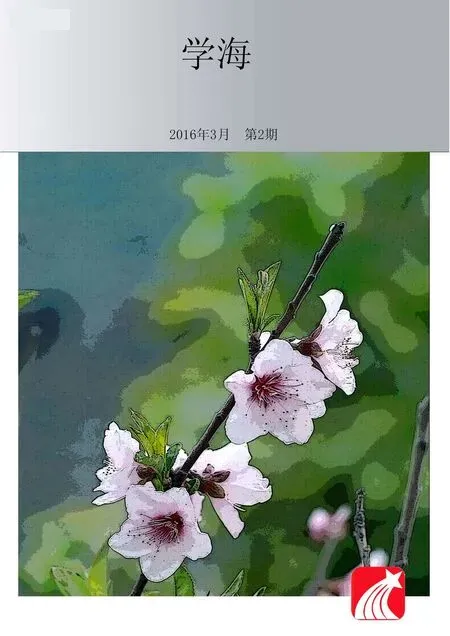儒家丧礼“饰死者”析义
张寿安
儒家丧礼“饰死者”析义
张寿安
内容提要一般讨论儒家丧礼,多专重在谈“丧服”,也就是生者如何为死者服丧;而忽略了死者。其实,儒家的丧礼有二方面。一方面是“生者自饰”:生者依其与死者的身份关系进行自饰,包括服饰及丧期,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丧服”。另一方面是“饰死者”。《荀子·礼论篇》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 就是为死者进行装饰。这方面谈论的人比较少,本文拟就儒家如何“饰死者”略加述论,同时也藉由饰死者的“仪式”来观察讨论儒家“慎终追远”之“慎终”的礼文化意义。
丧礼饰死者儒家的生命信仰
前言:“丧礼”的两个面向
一般讨论儒家丧礼,多专重在谈“丧服”,也就是生者如何为死者服丧,而忽略了死者。其实,儒家的丧礼有二方面。一方面是“生者自饰”:生者依其与死者的身份关系进行自饰,包括服饰及丧期,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丧服”。另一方面是“饰死者”。《荀子·礼论篇》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①就是为死者进行装饰。这方面谈论的人比较少。本文拟对儒家如何“饰死者”略作述论。同时,也藉由饰死者的“仪式”来观察讨论儒家“慎终追远”之“慎终”的礼文化意义。
首先说明,儒家的丧礼并不是在人死之后才开始进行,而是在人之将死即已展开。这就是第一步:疾病。
弥 留
《礼记·丧大记》:“疾病,外内皆扫。君、大夫彻县,士去琴瑟。寝东首于北牅下。废床,彻亵衣,加新衣,体一人。男女改服。属纩以俟气绝。”②
古人说的“疾病”,是指病入困境无可救治,③就是今人说的“弥留”。当病者进入弥留状态时,家人应做的事有:(1)外内皆扫。扫门庭及燕寝,把屋子内外打扫清洁。这个礼仪意指:整肃居室内外、静候事情发生。表示将办丧事。(2)彻县、去琴瑟。撤去各种乐器。《礼记·丧大记》:“君、大夫彻县,士去琴瑟。”古时,自天子至士,家中都有乐器,以备行礼之用。这时候,天子、诸侯、大夫、士都得把乐器撤去,无论这乐器是天子所赐或自家购置。这个礼仪表示有人将亡,家中将长时间不举乐。(3)弥留者应睡在卧室北墙下、头朝东。这种卧法和平时是一样的,因为北方较幽暗适合寝息;头朝东,表示人需要吸收东方的生气。这个礼仪代表家人仍然以“生人”之礼对待弥留者,不因将亡而荒废养生之礼。(4)废床、彻亵衣、加新衣、体一人。这是说把弥留者放在地上。儒家相信人始生于地,放在地上是希望其“生气”回来。其次,脱掉身上的内衣,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次,为了不使死者手足卷曲,所以由四个人分别护持其手足,使其平卧。(5)男女改服。这时候虽然弥留者尚未死亡,但家中男女即应改易服饰,脱去养疾时所穿的吉服,改穿“深衣”。“深衣”是一种吉凶之间的服装,人未死,故不可遽然改穿“凶服”,但“吉服”此时已不恰当,故着深衣。(6)纩以保气绝。拿一些新绵,放在弥留者的口鼻之上,观察气之有无。敬候气绝。
从以上的礼仪,我们看到儒家对丧礼的敬慎态度,一切都在整洁、严肃的气氛下有秩序的进行。对将亡之生命以肃穆静候来面对。这当中有部分礼仪在今日已经废弃,有些礼仪略加转化仍在某些地区实践着。如:死在家中,而非他处。今日医院每每应家属要求为弥留者施打特殊针剂为了使弥留者得以平安回到自己家中、亡于正寝。又如:为弥留者换衣,勿须待死亡之后。这些礼仪中较为人质疑的是“废床”。人之将死,肢体苦困,为何要置之于地?清人孙希旦的解释是:废床的意义和“复”一样。他说:人之生是因为有“魂”与“魄”相系,若魂魄相散则人亡。魂阳而魄阴,人死则魂升于天,魄降于地。人始死,身体僵硬,是因为魄散了,所以以尸就地,希望魄能“依尸而还”。人气绝,是因为魂散了,所以得使人“持衣而复”,希望魂能回来。所谓:“人之魂魄聚则生,散则死。魂阳而魄阴,人死则魂升于天,而魄降于地。始死体僵者,魄之散也,故废床而以尸就地,冀魄之依之而还也。既而气绝者,魂之散也,故使人持衣而复,欲魂之识之而返也。废床与复,同一义也。”④
气 绝
“气绝”之后的礼仪有以下两种:迁尸于寝。复。
《礼记·丧大记》:“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士之妻皆死于寝。”⑤
1.迁尸于寝。意指“死者必皆于正处也。”⑥寝是正寝,指诸侯、士大夫等命士的正寝。《仪礼·士丧礼》于“既卒”后,“设床笫,当牅”,然后“迁尸”。这是说人,若非死于不道,皆应迁尸于正寝,以明死于正处。上引“君夫人卒于路寝”一段,正说明:凡妻之死,皆与夫同处。孙希旦说这是为了办丧事时,诸侯大夫等前来悼唁,不可在夫人内寝行礼,故先迁尸于正寝,以备礼仪。至于何时迁?据孙希旦言大概是“疾病”,也就是病甚时,已迁矣。只有地位低下的女御,则于气绝之后,才迁至正寝。⑦这些阶级差异今日早已废弃,唯死于他乡者,迁回老家;悼唁者行礼于正厅;丧家讣闻也每每注明“寿终正寝”,以区别“死于非命”。仍留存古意。
2.复。招魂,招魂复魄,目的是希望气绝者苏活。
《礼记·丧大记》:“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赪,世妇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荣。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而复。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妇人复,不以袡。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唯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⑧
招魂仪式,得等气绝者迁入正寝之后,才能进行。“招魂”是丧礼中十分重要的一个仪式。一般而言,负责招魂者,都是“近臣”或“亲近之人”。招魂者,得穿着朝服,表明他的身份,意指他仍“奉事君之魂神”,与生时一般;招魂者手中则拿着气绝者的礼服,表示有求于神。招魂是以“三招三号”为竟。招魂者从东南面的檐角爬上屋子,在屋脊的正中央最高的地方,用竿子揭起气绝者的礼服,大号三次。一号于上,希望死者之神由“天”而来;一号于下,希望死者之神由“地”而来;一号于中,希望死者之神由“天地中间”而来。“号”时口中念的句子是“皋某复矣”。⑨三招竟,招魂者卷敛“所复之衣”向屋前投下,司服者以箧待衣于堂前,然后把复衣覆盖在气绝者身上。最后,招魂者,从西北屋檐下来。三招之礼,说明若三招之后气绝者仍未能苏活,表示神明不听家人的诉求,魂魄离散已是肯定,所以招魂者从西北幽暗之处下来,表示此屋凶,不可居。
在招魂礼中还有一个小节,寓意很深却每每为人忽视的,就是那件用来招魂的“复衣”。《礼记·丧大记》:“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郑玄解释说:“不以衣尸,谓不以袭也。”⑩这是因为,“复”礼的目的是“冀其生”,若是用“复衣”入敛死者,就成了“用生施死”,把“生”之礼用到“死”之礼上,“冀其生”的礼意,就被扭曲了,意义完全相反。所以这件“复衣”是得丢弃的。

沐浴与饭含
进入“死事”,施于死者的礼仪有数种:正尸,沐浴,饭含,袭冒,冰尸。
1.正尸。端正尸体。

刚死,就把原来放在北牖下的尸体迁至南牖下已铺好的床上,并且头朝南。前言弥留“废床”时,仍东首;至此,始以“死”待之,所以正其首于南。同时,死者的众亲(包括:世子、父、兄、子姓等)亦依丧服远近序位而列。再拿大敛将用的被子盖着尸体,脱去死时穿的衣服,近臣用角质的匙撑开死者的牙关,拿平日用的几拘限住双脚,使其端正,避免痉挛。
2.沐浴。包括洗身、洗头、修(趾)指甲、修胡须。

儒礼对浴尸之水是十分讲究的。首先,由官人汲水,不必解开瓶上的绳索(表示匆遽)就捧上阶,交给堂上的侍者,端去浴尸,由两名侍者为尸体洗澡。由四个近臣高举起盖尸的被子,另两名侍者为死者浴身,洗澡水先装在盆子里,然后用杓子取水把水淋在尸身上。洗澡巾是细葛的巾,揩身用浴衣,就像生前一样。然后近臣为死者修趾甲。浴尸的水不可随地流弃,得倒入阶下坎里,这个“坎”是临时掘来倒脏水的。洗头水就更讲究了。洗头水不能用清水,而是用洗过五谷的水,称为“潘水”。君是用洗粱的“潘水”洗头,大夫用洗稷的“潘水”洗头,士亦用洗粱的“潘水”洗头。官人先汲水交给侍者,陶人就在西墙下筑个土灶,管人就倒水入瓦罐煮开,再交给侍者,为死者洗头。洗头水用盘盛着,洗毕,用巾揩干头发,就和生前一样。再由近臣修剪指(趾)甲和胡须。洗过头的脏潘水也倒入坎里。
此下有三个步骤:饭含、穿衣、迁尸于堂。





小敛与大敛



除了上述的礼仪,还有二项颇值得一提:

2.敛葬时,置于棺侧的敛物。

(2)温明。汉俗则多在棺盖内顶悬一“温明”。“温明”形如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悬尸上,大敛并盖之。


“大敛”礼毕,其下即开始葬礼,从“饰棺”始,但已不是“饰尸”之礼。
儒家的饰尸之礼,至此告一段落。从以上的礼仪,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儒家对死者的态度是“事死如生”,对待死者和生时一样。最明显的就是“招魂”之后,不把招魂时所用的衣物加覆在死者身上,不袭不敛,以明确表示“复”是希望召回魂魄令气绝者苏活。但“敛”礼表明死亡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两者的目的是相反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荀子所反对的饭含用“稻”“贝”,因为稻是生米,贝是槁骨,完全没有生命象征。
结语:儒家的生命信仰



①[清]王先谦:《荀子集解˙礼论篇》,收入《诸子集成》第2册,上海书店,1987年,第243页。

③郑玄注:“疾困曰病。”,[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三《丧大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1128页。
⑥郑玄注:“言死者必皆于正处也”。出处同前注。
⑦孙希旦:“盖丧事有卿大夫之位,君夫人则天子诸侯吊焉,大夫士之妻则君夫人、卿、大夫吊焉,皆不可于妇人之寝亵之,故其死必皆于夫寝也。内子未命者,既死而迁尸,则凡卒于夫寝者皆于疾病而已迁矣。”《礼记集解》,卷四三,第1131页。
⑨孙希旦:“复者北面,求诸阴之义也。三号者,一号于上,冀神在天而来;一号于下,冀神在地而来;一号于中,冀神在天地之间而来也。”同书,第1133页。
⑩郑玄注,见《礼记集解》卷四三,第1134页。





































〔责任编辑:蒋秋明〕
张寿安,[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soan@gate.sinica.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