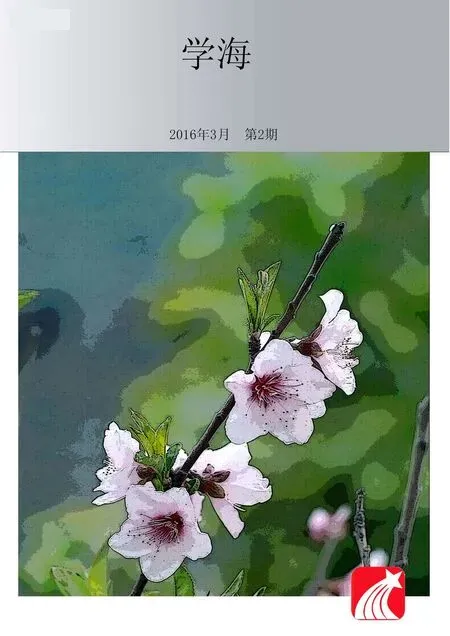“同情”的政治哲学诠释:定义、性质与类型
黄 璇
“同情”的政治哲学诠释:定义、性质与类型
黄璇
内容提要同情,是指看到或想象到他人的不幸经历或处境时,由于感同身受而引起的难过情感。从定义上看,同情与怜悯、同理心、移情、伙伴感等近义词不尽相同。从性质上看,作为一种政治美德的同情是一种善的情感;从类型上看,同情大致能划分为情感的、意志的与德性的三种类型。作为德性的同情,是作为情感与意志的同情的升华。它强调同情的内心私密体验与外在共同道德经验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包含了对善的动机与实践的共同考量。作为自然情感与社会道德结合的载体,成为美德的同情具有重要的正义指向。
同情善情感意志美德
同情是扭转现代理性政治路向的重要突破口。要了解这一被卢梭誉为天然美德的道德情感,需要从厘清同情的基本定义、基本性质和具体类型出发。除了“为他人感到悲伤和痛心”这种最直观的意思以外,同情还有哪些内涵?另外,同情可以是一种情感本能、一种道德心理、一种意志、一种德性,而作为政治美德的同情究竟属于同情的哪个范畴?这些都是在界定同情的过程中需要说明的问题。
概念辨析
在分析同情的定义与内涵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同情”与“怜悯”的差异。《现代汉语词典》对“同情”的解释是:“对他人的不幸遭遇或处境在情感上发生共鸣,并给予道义上支持或物质上帮助的态度和行为”。《现代汉语词典》对“怜悯”的解释是“对遭遇不幸的人表示同情”。从意思上看两者没有明显区别。但是从词语的常用语境来看,怜悯给人的感觉更多地是强者对弱者、地位优越者对地位卑下者、男性对女性所表达的同情感,如“怜贫惜老”、“怜香惜玉”等。而“同情”更多地是一种平等的双方在偶然地位不对等情景中的情感认同与情感联系,也更富道德蕴涵。
阿伦特这样区分同情与怜悯:“同情(compassion)是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似乎痛苦是会传染的;怜悯(pity)则是毫无切肤之痛下的悲痛”。①与此同时,阿伦特把卢梭视为将同情引入现代政治的第一人。在卢梭的文本语境中,法语pitié表示的是:任何有感知的生物在看到同伴遭遇苦难时,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同身受的自然情感。不管后世的研究者如何评价,卢梭始终没有表示过同情是建立在优越感和不平等地位上的情感。他把同情视为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地位的重要“武器”。因此,用“同情”而不是“怜悯”来作为pitié的中文解释似乎更为妥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卢梭所有著作的大陆中译本中,pitié都被翻译成“怜悯”,而在几乎所有研究卢梭的国内外文献及其中译本中,都没有将卢梭的pitié与英语中的compassion进行区分,也没有明确说明pitié更多地符合汉语中“怜悯”的解释,而不符合“同情”的解释。
在英语中,与同情相关的概念就有好几个,像compassion, pity, empathy, sympathy, fellow-feeling。将它们分别列举并解释其内涵,有助于使本论题中的“同情”获得确切而恰当的定义。
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对具有同情涵义的几个英语概念作出了辨析,它们分别是compassion, pity, sympathy与empathy。Compassion(中文一般译为“同情”、“怜悯”)是由于意识到他人不该遭受的不幸而引起的一种痛苦的情感。Compassion有着独特的认知结构,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对不幸程度(size)的判断——即相信或估计到一件非常严重的而不是微不足道的坏事发生在某人身上。第二,对非免责(nondesert)的判断——即遭遇不幸的人们并不是由于他们自身原因而致使不幸发生的,他们不该遭受如此不幸。第三,对幸福(eudaimonistic)的判断——即遭遇不幸的人物,在同情施动者的人生目标与计划中是具有重要意义,是一种善的目的。遭遇不幸的人的善应当得到增进。②
关于pity(中文一般译为“怜悯”、“同情”、“可惜”),纳斯鲍姆指出,它的原意与compassion相同,但现在它已经演变为具有以高傲和优越的态度对待正在遭受痛苦之人的涵义。而这种微妙的涵义变化无论是在古希腊时期的戏剧文本语境中,还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类文本语境中,都是没有的。这也许正是后续研究卢梭的各种文献难以明确说明,卢梭在使用pity时究竟是表示同情还是表示怜悯的原因所在。相比而言,compassion并没有产生这种语义变化。事实上,自法国大革命以后,希望延续希腊罗马政治理论传统的卢梭,他所使用的pitié已经很少被作为具有现实指向的口号性概念广泛传播,取而代之被广泛使用的是由pitié延伸出来的fraternité——博爱。这与此前提及的pitié语义产生一种基于不平等关系的转变不无关系。③
empathy(中文一般译为“同情”、“共感”、“共鸣”、“同理心”)是对他人经历的一种想象性重构,不论他人的经历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愉悦的还是痛苦的,又或者是不好不坏的,也不论想象者把他人的情况想成是好的、坏的还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一种“同理心”、“共感”的empathy,要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全盘移情的心理状态。这就与compassion所强调的是对他人痛苦经历的感同身受有明显不同。也就是说,empathy并不像compassion那样包含着对他人状况的一种判断,它不注重对他人的经历做出特定评价。④亚当·斯密的同情概念似乎就采用了empathy的涵义,尽管他用sympathy来表示同情。斯密认为,sympathy的原意与pity、compassion一样,都是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fellow-feeling)的词语。但sympathy的含义在斯密的伦理思想脉络中得到了扩展——“现在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比如快乐、高兴与激动)的同感也未尝不可”。⑤换言之,亚当·斯密的sympathy更倾向于具有empathy的涵义——无论是他人高兴的还是悲伤的、好的还是坏的经历都应当引起人们的同情。所不同的是,empathy并没有对他人的经历做出价值判断,而在斯密的sympathy中,价值判断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斯密强调:旁观者在产生同情心时是需要理智与判断力去进行换位思考的,这就必然涉及到对他人经历的价值评估与程度定位。⑥
舍勒在讲述同情的现象学时,延续了亚当·斯密的用法,使sympathy一词具有empathy的特征。舍勒指出,sympathy的本质是一种对他人的情感价值与状态表示同情性的理解、并做出回应的“伙伴感”(fellow-feeling)。“伙伴感”(fellow-feeling)一词早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被认为与compassion是同义的。⑦但是在舍勒的语境中,他人的情感价值与状态不仅包括痛苦、悲惨等消极因素,也包括高兴、愉悦等积极的因素。这与compassion仅表示对他人痛苦处境的感同身受是有所区别的。舍勒强调,这种伙伴感(fellow-feeling)既不是一种在共同的“价值-情境”经历中有着同一感受、相同敏感度的“共情”(community of feeling),也不是一种通过表情动作不自主地模仿他人情感状态、却并未对他人悲喜经验有所认知的“情感感染”(emotional infection),更不是一种将自我与他人完全等同起来的、以他人或自己为中心建立起持久移情习性的“情感认同”(emotional identification)。⑧
纳斯鲍姆没有完全认可舍勒与亚当·斯密对同情的定义。她认为sympathy与compassion在涵义与使用语境上是最为接近的。如果一定要指出两者的区别,那就是compassion要比sympathy更加强烈、所面对苦难程度更深。这种强烈的感觉不仅在受苦之人身上能够体会,在产生同情感之人的身上也有显著体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可以互换使用的。⑨
作为道德情感的同情,主要取英语中compassion的涵义:看到或想象到他人的不幸经历或处境时,由于感同身受而引起的难过情感。由此可以确定同情具有以下几个特性:首先,它一般是指由不幸的经历或处境、而不是欢快愉悦的境况引起的情感。但考虑到多元现代社会中道德内涵的扩展,当同情超越其本能定位,成为一种道德情感时,它所指向的特定情境也应当有所拓宽;其次,同情表示一种平等的情感关联而不含有优越、施舍之义。产生同情情感的人与其同情的对象只是处于偶然不对等的处境中,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具有不平等的人格地位;再次,同情包含对他人经历与处境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而不是受到痛苦境况的感染而简单地复制与模仿他人的情绪与感受;最后,同情是一种“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也就是说,产生同情情感的人必须与其同情的对象在处境上区隔开来,而不是将自己完全代入对方的处境当中,忘我地与他人建立起虚幻的情感认同。
同情的性质:在善与恶之间
不是所有性质和形式的同情都能成为一种政治美德。从性质上看,如果同情被认为是一种恶的情感,那它就不可能与美德相关。关于同情是一种善的情感还是恶的情感讨论,早在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派就有明确的立场:同情是一种恶的情感。斯多葛派晚期代表人物塞涅卡就主张,富有同情心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缺陷,而不是什么美德,被他人受难的景象所压倒是人格软弱的表现。塞涅卡认为,人们应该避免把怜悯伪装为仁慈——怜悯只看到有人在遭难,却不考虑其原因何在。也就是说,怜悯容易加剧人的无知。斯多葛派对后来大陆唯理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陆唯理主义代表人物斯宾诺莎强调,“怜悯对于一个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本身是恶,没有益处。”⑩原因在于,引起人们怜悯之情的对象的痛苦,也会引起人们同样的痛苦,所以怜悯是一种痛苦感觉的传递,这就体现了一种恶。




同情的类型:情感的、意志的与德性的
根据同情的本质结构以及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作用,可以把同情划分为情感的、意志的、德性的三种类型。



第四个层面是行为层面,即主要把同情作为一种外显的行为来对待。把同情视为行为的研究进路,也许看起来要比把同情视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受、体验或动机更为“可靠”。因为,它既是可以被明确观察到的,也是较为容易加以反复验证的。这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得以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受关注的主流学科之一的重要原因。然而,行为显然不会是同情概念的全部内容,同情在感觉、动机等的心理层面有更丰富的内涵。如果仅仅重视同情的外在显现,而忽视同情的内在多元层次结构,同情就失去了值得人们去深入理解的重要涵项。






总而言之,对于作为德性的(美德的)同情来说,理性是必需的。同情需要理性来指引方向、提供知识、保持审慎、约束冲动、检验判断。理性是形成合适而合宜的同情美德必不可少的条件。除此之外,作为美德的同情,突破了同情作为一种情感与一种意志时的个人主观体验与感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回应与社会联系。因此,这样的美德必定是能够提供普遍社会准则与规范的社会性美德。
把作为情感的同情、作为意志的同情与作为德性的同情在类型上相互区别开来,并不意味三者之间是彼此隔阂的。作为情感的同情是对同情本质的描述,是同情的意志与同情的美德共同具有的心理基础。作为意志的同情,表达的是一种稳定的、更具力量感的同情情感。它超越了作为一种被动本能反应的情感,成为满足人类高级需求的具有持久性的信念。作为德性的(美德的)同情,是同情情感与同情意志的升华。它为人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与情感认同赋予了道德的意义,是人类超越动物本能与生存状态获得社会能力、社会地位与社会品质的体现,是能够促进社会融合的“黏合剂”。作为德性的同情,强调同情的内心私密体验与外在共同道德经验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包含了对善的动机与实践的共同考量。这与同情概念本身所体现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相互协调的基本关系是保持一致的。由此拓展开来,成为美德的情感就其本质属性而言,不只是一种体现了自我价值的超验感悟,或者只是一种纯粹利他的道德行为,而是两者之间相互调和与边界确定的产物。作为自然情感与社会道德结合的载体,成为社会美德的道德情感对于高度分化的、不平等的社会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正义指向。

①[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②③④⑨Martha C. Nussbaum,UpheavalsofThought:theIntelligenceofEmotions, pp.301-321, pp.301-303, p.302, p.302.

⑦Thomas Hobbes,Leviathan,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94, p. 32.
⑧Max Scheler,TheNatureofSympath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4, pp.12-18;及其中译本[德]马克思·舍勒《情感现象学》,陈仁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12-14、16-17、19-20页。
⑩[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8页。















〔责任编辑:蒋秋明〕
黄璇,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北京,102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