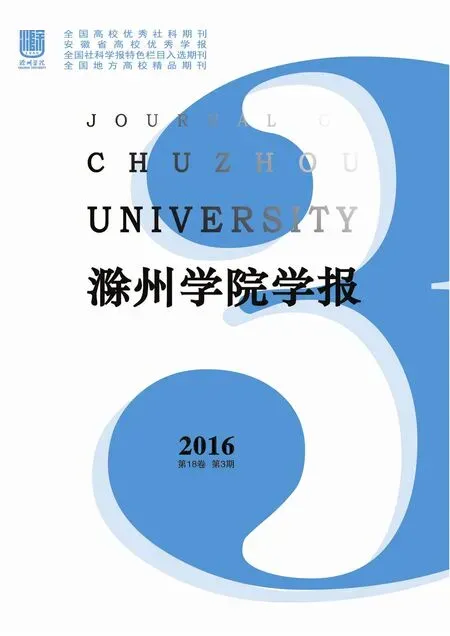多维视角下的凤阳花鼓艺术研究
薛业浩,周 静
多维视角下的凤阳花鼓艺术研究
薛业浩,周静
摘要:凤阳花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2006年申请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成功入选。凤阳花鼓艺术发展与明王朝的兴衰紧密联系,其文化起源、艺术形式以及作为一种输出文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艺术特点。凤阳花鼓的当代创作、演出和文化研究也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常态下,对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使命进行深度解读将在凤阳花鼓的艺术发展和传承方面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凤阳花鼓;起源多义性;形式多样性;输出型文化
凤阳花鼓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2006年成功获批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艺类)。十年来,凤阳花鼓艺术在创作、演出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在起源、流变以及影响方面,具有明显的个体特征,并被赋予历时性的文化因子烙印。其艺术形式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特点,它流传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远性更是展现了其身上所承载的深厚民族文化基因特点。通过多重视角对凤阳花鼓艺术进行全面解读,对于全面审视、认识凤阳花鼓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整体透视凤阳花鼓艺术,必然会在其发展、传承和创作等领域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起源的多义性
“凤阳花鼓”称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与“河北梆子”“天津快书”“河南坠子”等艺术称谓相同。除去共性之外,凤阳花鼓称谓还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表现在,首先,“凤阳”是帝王之乡——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其次,历史中的“凤阳”在明王朝是以“凤阳府”的建制存在的,下辖九州十八县,一度成为明朝建都之地。这些都成为凤阳花鼓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凤阳花鼓起源众说纷纭,经综述之后,可以梳理出两种视野,一是由江浙一带随明初移民引入凤阳,是一种输入型文化;二是产生于凤阳本土。
(一)源于江浙
凤阳花鼓究竟起源于何地,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有起源于江浙一带并于明初传入凤阳的说法。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故土情结”浓厚的他次年便颁诏于凤阳营建中都:“朕今新建国家,建都于江左,然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择淮水以南,以为中都”。①他一方面下令在家乡临濠(今凤阳)修建“中都城”,另一方面从江浙一带强行迁入数量庞大的人口,包括文人雅士和富庶商贾,目的在于充实帝乡人口数量,提高凤阳人口质量和繁荣凤阳社会文化,洪武七年十月,“徙江南民十四万实中都。”[1]“徙江南民”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江南普遍富庶,且多具人文修养,必然对中都凤阳产生良性作用;二是元末,朱元璋夙敌吴王张士诚曾久居江南,江浙民众多不拜天子,朱元璋私访江南被一老妪暗中唤作“老头儿”。“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2]从江南大量移民实则是朱元璋对其进行的惩罚,移民把“打花鼓”艺术带到了凤阳,并在凤阳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早在南宋时期,江浙一带就有打花鼓、花鼓以及花鼓槌的故事流传记载。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和吴自牧《梦梁录》“百戏艺伎”中,均有“花鼓”“花鼓槌”的记载。本土学者姬树明、俞凤斌也持此观点:“凤阳花鼓一般认为始自明代,并且很可能是从浙江绍兴那边传过来的。”[3]清代学者亦有记述:“打花鼓,本昆戏中之杂出,以时考之,当出于雍、乾之际……”[4]从以上几个时期的文献记载来看,凤阳花鼓极有可能是在明初随“移民”流传凤阳,并与凤阳当地民俗、民间艺术进一步糅合而发展壮大的。
(二)源于凤阳
另一种观点认为凤阳花鼓起源于凤阳当地的本土艺术:“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花鼓小锣’、‘双条鼓’等,凤阳花鼓起源于凤阳府临淮县(今凤阳县东部)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汉族民间表演艺术,但以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最为重要和著名,一般认为形成于明代。”史料记载:“吴越间妇女用三棒上下击鼓,谓之三棒鼓,江北凤阳男子尤善……。江北凤阳女皆务农,其夫讴歌击鼓。”[5]凤阳人喜好玩灯、擅于击鼓历史悠久,并有文字记载:“泗州农家之妇,则又执役田作,劳苦反倍于男。前志曰:‘……插秧之时,远乡男女击鼓互歌,颇为混俗。’”[6]学者孙祥宽、孙文海认为:“凤阳风俗男子尤善三棒鼓,插秧时讴歌击鼓,男女击鼓互歌,指的就是花鼓灯锣鼓和秧歌,凤阳花鼓初期的花鼓小锣及唱词秧歌即源于此”。[7]另据民间传说:“原来朱元璋一生不喜爱娱乐,却偏喜爱听花鼓。小时,他家在凤阳太平乡种地,这太平乡一带常常有人打花鼓,唱花鼓歌。”朱元璋幼时凤阳就有“打花鼓、唱花鼓歌”的活动,这也反证了凤阳花鼓并非随明初江浙移民流传而来。以上种种观点均基于凤阳当地的民俗习惯和生产生活传统,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凤阳相邻的怀远县、五河县也都是花鼓灯、民歌的起源地,当地在历史上具有产生凤阳花鼓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和社会基础。“移民说”和“当地起源说”各有特点,在对凤阳花鼓的现有艺术特点考察、分析之后,后者的说法更符合事实情况。
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华夏文明历史悠久,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凤阳花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代表,传承着特定的历史基因和民族文化,它更是皖东区域文化的象征和优秀文化品牌。凤阳花鼓艺术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艺术发展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密切关联,其艺术更是具有综合性。它属“凤阳三花”(凤阳花鼓、花鼓灯和凤阳花鼓戏)中的一枝奇葩,影响最广泛、知名度最高、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同时,其自身也融合了曲艺、舞蹈、民歌等艺术形式,形成了一门综合性艺术。
(一)曲艺
2006年5月,凤阳花鼓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安徽省首批入选非遗中唯一的曲艺类文化事项,自此,掀开了凤阳花鼓研究、演出、创作发展的新篇章。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点和民间意味的表演艺术形式集成,曲艺具有以“说”和“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特征,用“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各种人物、故事表演给听众。凤阳府地处淮河之滨,常年遭受荒年之灾,老百姓以花鼓为道具,通过“唱门头”的方式讨饭(凤阳花鼓表演程式分为“坐唱”和“唱门头”两种。“坐唱”为在街头、作坊、村头及私人客堂内坐在长凳上演唱,多为长篇叙事性故事。“唱门头”即沿门乞讨,即兴演唱短篇,内容基本是吉祥如意的“奉承话”)[8]其中有一首:紧打鼓,慢筛锣∕听我唱个动情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单会唱个凤阳歌∕唱得不好休要赏∕唱得好时赏钱多……[9]曲艺以“说”、“唱”艺术形式为主,新中国之前,凤阳花鼓的艺术功能以“讨饭乞食”为主,“说”与“唱”在乞讨中是有一定优势的,表达情感朴实、道具简易、可以“见物唱物”,比起民歌和舞蹈类形式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灵活,也更易于被民众接受。建国之后,凤阳花鼓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讨饭乞食”的作用已经日趋淡化,作为一种艺术存在在舞蹈、民歌,创作、表演方面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新要求紧密贴合,真实反映了新时期的新变化、新生活,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其知名度在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上都得到深入地拓展。
(二)舞蹈
如今,凤阳花鼓艺术早已经脱胎换骨,不再是“讨饭乞食”的代名词了。1955年凤阳县民间艺人欧家琳、刘明英等代表安徽赴北京参加文艺汇演,在“怀仁堂”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演出,被誉为“东方芭蕾”,从而名声大噪。这次演出是以舞蹈的艺术形式展示的,凤阳花鼓艺术随着其社会功能的变异而发生变化,其已经成长为一种成熟的舞蹈艺术。“……从此‘凤阳花鼓’演变而成的民间舞蹈以‘双条鼓’命名。双条鼓是由凤阳花鼓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舞蹈,……它在花鼓小锣的基础上,省去了说唱,减去了小锣伴奏,同时吸收其他舞蹈技法,丰富了自身的舞蹈语汇,逐步演变成一种以舞蹈为主的民间艺术。”[10]2笔者亲历“非遗”后凤阳花鼓的重大演出,包括三届“中国·凤阳花鼓文化旅游节”和在滁州市举办的历届“中国农民歌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安徽馆的凤阳花鼓演出。这些展演均以舞蹈的艺术形式出现,并均大获成功,向世人展示了凤阳花鼓作为舞蹈艺术的魅力。据调研,滁州市大中小学校都开设有以教授凤阳花鼓舞蹈艺术的课程,包括滁州学院、安徽科技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凤阳县的实验小学等。在各个层次上有力地推动了凤阳花鼓舞蹈艺术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三)民歌
与以“说、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曲艺形式不同,作为“安徽民歌”的凤阳花鼓是以“唱”为主。民歌形式的凤阳花鼓有两个涵义,一是以“凤阳花鼓”命名的民歌,曲调歌词如下:
谱例一:

谱例二:

这两首作品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们的唱词具有明显的历史印迹,真切地反映了明王朝统治下彼时民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也是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二是20世纪以来以凤阳花鼓为基础采风、创作、改编的民歌,其以“凤阳花鼓”“打花鼓”“鲜花调”“凤阳歌”“新凤阳歌”或“凤阳花鼓调”命名。“其中以‘金嗓子’周璇演唱、胜利唱片公司录制的‘凤阳花鼓’名气最大。”[10]9
凤阳花鼓艺术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自诞生起就承载了下层民众的悲苦人生,它是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代言”艺术。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以“乞讨艺术”为主的曲艺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变化的民歌形式和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舞蹈艺术形式。凤阳花鼓的艺术形式多样,除曲艺、舞蹈和民歌三类之外,还曾以戏曲的艺术形式出现,考虑到其影响甚微,本文不再赘述。
三、艺术影响的深远性
凤阳花鼓的产生与明王朝、朱元璋以及凤阳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它的艺术内涵映射着政治、历史和地域的影响。在对其“输入型文化”和“输出型文化”两个维度进行全方位考察、审视之后,凤阳花鼓向世人展示了其作为艺术主体影响的广泛性和深远性。
(一)悲苦文化的象征
凤阳花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一度处于被动状态。凤阳花鼓是一种悲苦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它最初的发端是作为一种“乞讨工具”,被凤阳藉民众和移民群体分别作为“乞讨”和“返乡省亲”的道具。“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其唱歌则曰:‘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11]凤阳中都城罢建以后,朱元璋是严厉禁止移民返乡的,也是忌讳凤阳民众逃荒要饭的。“洪武十四年,全国实行黄册制度后,就严禁迁徙,禁逃亡:‘但有迁民及自愿为民并为事发为民在逃者,所司申部挨拿如有容隐者,不行首官发谴者,拿问如律’。”[12]移民失去了江南文化土壤和尊严,对故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又饱受凤阳土民欺凌,渐生回迁之意。于是,以“回乡省亲”和“逃荒乞讨”为借口逃离凤阳。凤阳花鼓最初就是被作为乞讨工具而成长起来的,这与中国的乞讨文化中的“卖艺乞讨”是一脉相承的。凤阳花鼓发展初期,其词曲均有埋怨“朱皇帝”之意,一方面表现了移民对其移民政策所造成的苦难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凤阳本土人民对其未能给家乡带来繁荣的调侃和抱怨。
(二)输出型文化的代表
我国历史悠久,各地域、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常常在艺人落脚之处就地生根开花,甚或艺人吸收他种艺术来丰富己方艺术,最终促进文化的发展壮大,这种双向交流必然造成了传统文化溯源的困难性。凤阳花鼓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密不可分,随着民众外出乞讨数量增多、历时长久而对其他地域文化艺术种类造成一定的影响,包括民歌、戏曲等。
1.《茉莉花》起源之谜
《茉莉花》被公认为江苏民歌,然而即便在江苏省内,扬州市、无锡市、苏州市、镇江市和南京市也争得不可开交[13],其真正的发源地一时难以确定。2006年,明史专家夏玉润先生提出了:《茉莉花》源于凤阳花鼓这一论断,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茉莉花》最早版本,为清乾隆年间刊印的《缀白裘·花鼓》中的插曲。该剧演一对凤阳夫妻打花鼓卖艺,被浪荡公子曹月娥邀至家中,唱了一首《花鼓曲》(又称《鲜花调》)。……唱词中的‘茉莉花’,即为剧中的‘花鼓女’;想‘采一朵戴’者,为剧中的‘浪荡公子’;‘看花的’为花鼓女的丈夫。”[14]作者以《鲜花调》为着眼点,所提出的论断有理有据,对其中的词意解读也是合情合理。这表明了凤阳花鼓在灾民前往江浙一带乞讨中确实给当地民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甚至不排除《茉莉花》就是凤阳花鼓艺术中的一个分支的可能,这也是输出型文化的一个特征。
2.对他种艺术的影响
凤阳花鼓在流变过程中对各地的民间音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48年,作曲家瞿维根据凤阳花鼓的曲调元素改编的钢琴曲《花鼓》家喻户晓、广为流传。“在民间歌曲、民间器乐曲、民间舞蹈、曲艺音乐、戏曲音乐中与凤阳歌同宗嫡系的曲调有366首之多。”[15]至今,在很多地方还保留有用“凤阳歌”或“凤阳花鼓”命名的艺术种类,如“流行在陕西户县的《凤阳调》其旋律与关中音乐的苦音音阶融为一体……。河北黎昌的《凤阳歌》无论内容还是音乐,都明显带有冀东民间音乐的风格,更富激越凄苦之情。”[10]26凤阳花鼓文化中的“悲苦基因”被迁移到他类艺术细胞之中,得到进一步繁衍壮大。
3.凤阳花鼓的当代使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人民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为建设繁荣的国家和追求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奋斗。凤阳人民早已经摆脱贫困的困扰,凤阳花鼓亦不再是“讨饭乞食”的工具,它的历史使命正发生着深刻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凤阳花鼓成功申遗,逐渐走向国际舞台,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凤阳花鼓曲调等素材成为艺术家创作中争相引用的对象,这更加凸显了凤阳花鼓的时代魅力。近些年,学界对凤阳花鼓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相继出版发表了有关著述和论文,有关其保护、传承和发展的成果更是屡见不鲜。另外,凤阳花鼓已经被当地政府确立为文化品牌,借力凤阳花鼓打造优质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环境资源,凤阳花鼓的发展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四、结语
自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始,就为凤阳花鼓的孕育、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凤阳花鼓随着明王朝的兴衰而发展、流变,这正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有力论证。凤阳花鼓起源具有一定的多义性,其艺术形式具有多样性,影响范围广泛、深远,在对其进行全方位解读中,更能挖掘其中所蕴涵的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和优秀艺术基因。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80. 明朝建立之初,实行“二京一都”制,北京汴梁,南京应天和中都凤阳(凤阳介于二京之间,故得名中都)。
[参考文献]
[1]袁文新.凤阳新书:卷1[M].刻本.1621(明天启元年):80.
[2]徐祯卿.翦胜野闻[M].刻本.清:32.
[3]姬树明,俞凤斌.说凤阳[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36.
[4]徐珂(清).清稗类钞·戏剧类·打花鼓[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5]田艺衡.留青日札(上):卷19,卷39[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346.
[6]曾惟诚.帝乡纪略:卷5[M].刻本.明:122.
[7]孙祥宽,孙文海.漫话凤阳花鼓[M].合肥:文艺出版社,2008:121.
[8]龚庞,丁家干.凤阳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615.
[9]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M].合肥:黄山书社,2003:749.
[10]苏兆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0.
[11]赵翼(清).陔余丛考:凤阳丐者[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12]胡滢.攒造黄册事宜疏[M]//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明经世文编: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62:35.
[13]冯光钰.《茉莉花》花开何处?[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6(12):20.
[14]夏玉润.《茉莉花》究竟是哪里的民歌?[N].文艺报,2006-02-11(004).
[15]冯光钰. 从凤阳歌看“同宗民歌”的传播流变[J].音乐研究,1991(2):80.
责任编辑:刘海涛
中图分类号:G03;J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6)03-0005-04
作者简介:薛业浩,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作曲研究;周静,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合肥 230011)。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课题(SK2016A0094);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377)
收稿日期:2016-02-26
——以凤阳花鼓为例